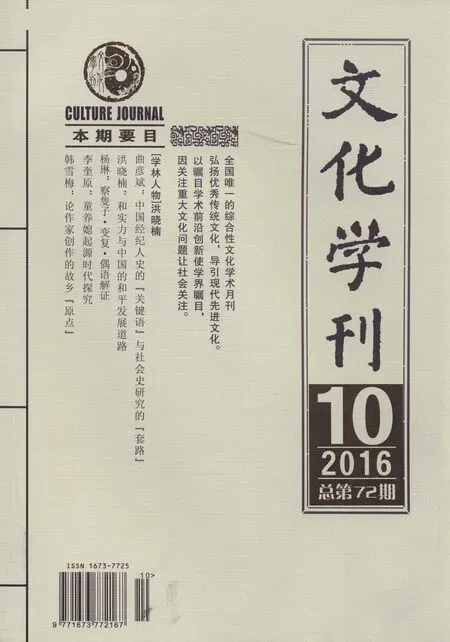淺析海斯特的“罪”與“贖”
張雪靜
(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
【文學評論】
淺析海斯特的“罪”與“贖”
張雪靜
(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7)
在西方,宗教與人們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對人們的生活特別是文學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很多作家筆下的故事大都取材宗教或以宗教為背景。美國作家霍桑的小說《紅字》雖然不是宗教題材,但通過描寫生活在宗教統治下的社會里,女主人公海斯特對自身“罪惡”的救贖,對人性善與惡的思考,引人深思。
霍桑;海斯特;罪惡;贖罪
在19世紀,西方社會女性幾乎沒有自己的權利,沒有社會地位,更沒有話語權,她們扮演著男性附屬品的角色。作家肩負起社會責任,用他們的筆,關注女性,為女性代言,塑造出許多有血有肉、大放異彩的女性形象。其中美國浪漫主義小說代表作家霍桑在《紅字》一書中的海斯特,就是非常特別的一位。
一、作者復雜的性格與深邃的思想
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19世紀美國杰出的小說家,霍桑以其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創作技巧,享譽美國乃至世界文壇。霍桑出生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一個宗教氣氛十分濃厚的家庭,全家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霍桑的祖輩曾參與過臭名昭著的“驅巫運動”。自霍桑出生起,他的生活就被濃濃的傳統宗教氛圍充斥著。在霍桑的父親老霍桑去世后,全家人過著封閉式的生活,久而久之,母子兄妹間竟視同陌路,從此以后,霍桑變得抑郁寡言。正是這樣的家庭背景和家庭生活使霍桑養成了抑郁憂慮,苦想憂思的性格。這種家庭氛圍的影響下,霍桑性格中的抑郁與灰暗揮之不去,正是這種性格上的抑郁,使霍桑的作品蒙上了一層陰沉與古怪的面紗。同時,他又深受加爾文教的影響,對于霍桑來說,清教意識早已深入骨髓,加爾文教一方面強調人的“罪性”,人的一生就是為贖罪而活;另一方面,教會的虛偽與狂熱,也使霍桑開始懷疑宗教。霍桑生活的時期正值美國的文藝復興期間,社會思潮的變化使霍桑開始反思舊的道德觀念。舊道德與新思想在霍桑的意識里沖撞,由此形成霍桑復雜的思想,矛盾的性格,這些復雜與矛盾充斥著霍桑的作品。
霍桑的《紅字》是美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浪漫主義小說,霍桑將自己的困惑與矛盾,對人性以及人的心里狀態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集中地表現在作品中;同時對“原罪”的思考,則是霍桑對宗教問題的深度拷問。這部小說發行至今仍然深受讀者的喜愛,霍桑本人因此蜚聲世界文壇。小說的情節波瀾不驚,但卻扣人心弦,尤其是在展現愛的矛盾,道德的沖突,罪惡的救贖等方面時讓人印象深刻。
二、真愛與舊識的矛盾,理性與道德的沖突
海斯特是舊道德與至真愛的矛盾統一體,這是作者內心情感的矛盾所在。作者深受加爾文教的影響,相信“原罪”,將善惡作為衡量社會的標準;而另一方面他卻憎惡加爾文教所具有的狂熱、虛偽與專橫,因而作者筆下的海斯特也正是作者創作傾向性的體現,霍桑痛恨不合理的婚姻,但卻不敢肯定不“合法”的感情,更不肯使有情人終成眷屬。小說中,海斯特和丈夫齊靈窩斯是合法的夫妻,齊靈窩斯是一個比海斯特年長許多,相貌丑陋的老學究,他們的結合是舊道德下的產物。在齊靈窩斯和海斯特移民美國的過程中,丈夫被印第安人所擄,兩年多來,杳無音信,海斯特以為丈夫由于某種原因已經死去,在遇到了教區內最有道德最有威望的牧師丁梅斯戴爾后,則與之相愛,生下愛的結晶—珠兒。然而在眾人眼中,海斯特和丁梅斯戴爾這份真摯的愛情卻被視為是不合乎規矩的,海斯特這種無夫而孕的行為是違反教條的“通奸”,為此,海斯特遭受了一系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終生佩戴象征恥辱的紅色“A”字,從此海斯特過著遠離人群的生活,珠兒成了她生存生活的唯一支撐。由此可見,海斯特痛苦卻又無能為力。
海斯特是一個敢于追求自由、真愛與幸福的人,因此理性與道德的沖突也凸顯的愈加明了。海斯特本已嫁作人婦,是羅杰·齊靈窩斯的太太,但當她愛上丁梅斯戴爾時,她無法壓抑自己的感情,勇敢的選擇和他在一起。海斯特不顧后果的愛,使她短暫的失去了理性,埋藏了自己的幸福。在事情暴露以后,她為了丁梅斯戴爾的前途選擇自己承受這一切。理性告訴她,即使她深愛丁梅斯戴爾,但卻不能毀了他。她已經是眾人眼中的罪人,為何還要再毀掉一個前途光明的青年呢?我們不難看出,霍桑的清教道德觀與原罪觀使他在對海斯特浪漫主義精神懷有深切的同情甚至是崇敬,他不否認海斯特的“通奸”是錯誤的,卻也表達了對海斯特內心隱秘的同情和尊重,即霍桑斷定這樁婚外情對海斯特自己和與她關系密切的三個人都造成了傷害,但又認為那只是一種欲望的罪惡,并不是出自海斯特的內心。這就體現了出作者內心的矛盾以及對罪惡的思考。
三、隱忍的叛逆,壓抑的痛苦
海斯特胸前那鮮紅的“A”字本是恥辱的象征,而她卻精心地縫制每一個紅色“A”字,手工奇巧,每一個都是精致美麗的藝術品。精致的紅色“A”字佩帶在海斯特樸素的衣物上,顯得格外的神秘,無聲地訴說著海斯特的叛逆。作為海斯特罪惡寫照——珠兒,她身上所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由海斯特自己親手縫制的,每一件都是那么別出心裁。總之,只要有機會她就會用這種方式,甚至是她展示自己的唯一方式。這些出現在總督的皺領上、軍人的綬帶上、牧師的領結上、嬰兒的小帽子上等的繡品,都在證明海斯特的獨特存在。海斯特生活在宗教統治下的社會,在殖民地人們的眼中海斯特就是一個罪人,因此她不得不終生佩戴象征恥辱的紅字,遠離愛人。從對海斯特脫俗的外貌描寫來看,她堅強獨立,本性善良,卻又透著一種無法掩蓋的叛逆。海斯特盡管是眾人眼中的罪人,但她從心底并不認同,她不認為自己與丁梅斯戴爾的愛情是錯誤的,相反,為了愛他,她獨自承擔所有的罪責,但是生活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之下,她不得不接受社會對她的懲罰因此她要以她的能力所及,讓自己依然存在于大家的視線中,這便是她的叛逆。
海斯特的痛苦是來自多方面的,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首先,消失的丈夫意外現身,是她痛苦的加深。家道中落的海斯特不得已嫁給了一個相貌丑陋的老學究齊靈窩斯,他雖然沒給海斯特帶來幸福,卻已是海斯特生命中一個重要的伴侶。在移民途中丈夫被擄,只剩下海斯特一人,讓海斯特倍感無助。而在海斯特“通奸”的事情被暴露以后,當海斯特站在刑臺上受罰之時,丈夫卻意外現身人群里,讓海斯特原本慌亂的心更加煎熬。因此海斯特的內心是痛苦的。其次,只能遙望的愛人。由于海斯特胸前那鮮紅的“A”字,海斯特在眾人眼中,是行走的“恥辱”、移動的“瘟疫”,教區里的人甚至連孩子都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就連自己的好朋友,海斯特都無法輕易靠近,更何況是教區內名聲最好,前程最光明的牧師丁梅斯戴爾,所以,即使海斯特深深地愛著他,卻也只能把自己對丁梅斯戴爾的愛深埋,遠遠地祝福他。最后,天真的女兒,殘缺的家庭。海斯特的女兒—珠兒是一個天真可愛的孩子,她本應該像其他孩子一樣有著完整的家庭,但由于父母間特殊的關系,她不知道父親是誰,甚至在知道父親是誰后也不肯跟他親近。海斯特想要彌補女兒,讓女兒和她的親生父親親近,可是珠兒就好像不受她的控制,總是和她作對,這也是造成海斯特痛苦的原因之一。
四、天使的善良,罪惡的救贖
在小說中作者對人性的善與惡以及人的心理狀態都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小說中,人物的苦難與救贖則是作者對人性的善與惡以及人的心理狀態思考的結果。
海斯特的救贖與故事中兩位男性相比,她的救贖更多的是來自內心的自由與平靜。在《圣經》中,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因偷食禁果,他的子子孫孫身上都負有原始的罪孽,只有禁欲苦行才能得以救贖。主人公海斯特身負“原罪”與“通奸”的雙重“罪孽”,她必須要對自我進行救贖。在監獄中的經歷,在刑臺上的審問,被社會拋棄,獨自撫養活著的“A”字—珠兒,這一切都顯出了她與那個社會格格不入。她的罪惡昭彰,即使遠離人群,她的內心也是平靜的。與海斯特相比,牧師丁梅斯戴爾與齊靈窩斯終日戴著面具行走在人前,表面平靜,內心卻是狂風暴雨一般。丁梅斯戴爾與海斯特犯下了同樣的罪惡,卻沒有承認的勇氣,只能在深夜里獨自懺悔;齊靈窩斯假借拯救牧師健康之名,實則對牧師進行瘋狂的報復。海斯特的罪惡無所隱匿,也就無所失去,所以海斯特的內心是平靜的,這是她自我救贖過程中最辛苦、最艱難的一步。
無言的拋棄,種種的輕視,社會的不公,并沒有使她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她依然對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依然以樂觀、寬容、博大去面對這個世界。海斯特過著寧靜的生活,她幾乎把她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刺繡和照顧珠兒身上,海斯特和珠兒賴以生存的生活來源是海斯特那雙巧手。她用自己的雙手去為教區內的人們繡各種各樣的東西,每一件都是如此精美,以致她總是能有很好的收入。她天性善良,她并沒有把自己所能利用的所有時間都用在讓自己賺更多的錢上,她在艱難地養育珠兒的同時,還不遺余力地幫助別人,在周圍的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她總是無私地給予幫助。她拿出自己的積蓄去救濟那些比她更加貧窮、更加不幸的人,她為窮人縫制粗布衣服,她犧牲了自己的樂趣,放棄了有更多收入的機會,盡管有時換來的是忘恩負義的侮辱和謾罵。海斯特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改善了與周圍社會的關系,改變自我,努力地融入社會,她用自己靈巧的雙手養育珠兒,幫助了他人,用自己火熱的內心給這個冷漠的社會增添了些許溫暖。海斯特以其受苦舍己的善行以及對人心隱情的直覺,讓她信仰清教的鄰居們反思自己的污惡、狹隘,培育內心的寬容與善良。
“紅字”的故事結束了,而關于宗教統治下的人的思想、罪惡的救贖,對人性中善與惡的思考發人深思。小說中的海斯特可以說是“罪孽深重”,但她卻以另一種方式使自己的罪孽得到救贖,可見懺悔不是救贖罪惡的唯一方式。通過海斯特的故事,霍桑曲折地講述了他對人性的感悟,對善與惡的深度思索,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洞察。霍桑雖是浪漫主義小說家,但更愿意接受清教關于人性人類的生存環境的解釋。著名作家麥爾維爾評論說:“霍桑的這種黑色力量來自于加爾文。”
【責任編輯:周 丹】
I106.4
A
1673-7725(2016)10-0062-03
2016-10-18
張雪靜(1993-),女,黑龍江齊齊哈爾人,主要從事漢語言文學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