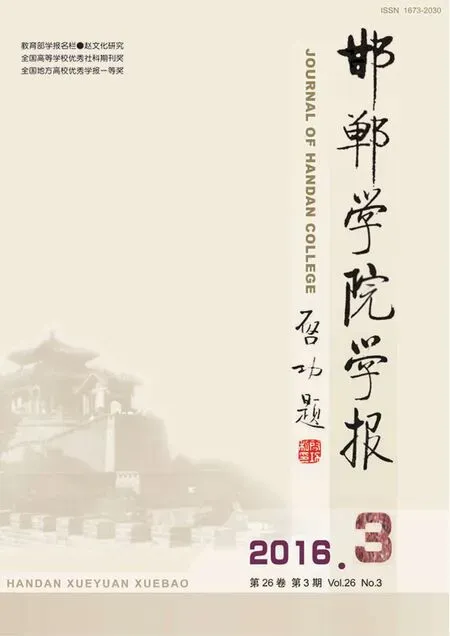由《荀子》“偽”字義論其有關(guān)篇章的作者與時代
廖名春
(清華大學 歷史系、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創(chuàng)中心,北京 100084)
趙文化研究·荀子專題[教育部名欄]
由《荀子》“偽”字義論其有關(guān)篇章的作者與時代
廖名春
(清華大學 歷史系、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創(chuàng)中心,北京 100084)
《荀子》三十二篇中,“偽”字共四十二見,其涵義有三:一是讀為“為”,義為“行為”的,有兩見。二是義為“詐偽”的,共五見。三是具有理性之“人為”義的,有三十五例。其中《性惡》篇最多,占了二十七例;其余《正論》篇有一例、《禮論》篇有五例、《正名》篇有兩例。這種具有理性之“人為”義的“偽”,先秦秦漢文獻“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為《荀子》書所特有,是荀子作品的區(qū)別性特質(zhì)之一。以此來看,如果《性惡》篇不是荀子的作品,否定荀子“偽”有理性“人為”義,那就得將《正論》《禮論》《正名》篇也排除出去。只要我們承認《正論》《禮論》《正名》篇為荀子所作,也得承認《性惡》篇屬于荀子的作品。由此可見,那些以“莫須有”證據(jù),否定《性惡》篇為荀子所作的說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荀子;性惡;偽;人為;詐偽;理性之偽
“偽”字《荀子》書多見,其涵義很富有個性,值得討論。利用它來判定《荀子》有關(guān)篇章的年代,也很有價值。
南宋浙北刻本的《荀子》20卷32篇中,“偽”字共四十二見①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12月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浙刻本。有關(guān)宋浙刻本的意義,詳見廖名春:《二十世紀后期大陸荀子文獻整理研究》,臺灣云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漢學研究集刊》第3期(荀子研究專號),2006年12月。,其涵義有三。
一是讀為“為”,義為“行為”的,有兩見。如:
01. 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非十二子》)
日冢田虎(1745-1832)曰:“偽,恐‘為’之誤。言其行事危險污穢也。”劉師培(1884—1920)曰:“偽、為古通。如《性惡》篇‘為’字均作‘偽’,是也。”北大《荀子新注》曰:“行偽險穢,行為陰險骯臟。”[1]226都是將這里的“偽”視為行為的“為”之假借。又:
02. 其衣冠行偽已同于世俗矣。(《儒效》)
唐楊倞注:“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是讀“偽”為本字。清人郝懿行(1757—1825)則曰:“偽,與‘為’同,行動作為也,注非。”劉臺拱(1751—1805)曰:“《荀子》書言‘偽’者,義皆作‘為’。此‘行偽’,《韓詩外傳》作‘行為’。”王念孫(1744—1832)曰:“‘行偽’二字,本篇一見,《非十二子》篇一見,《正論》篇一見,《賦》篇一見。其見于《正論》篇及《賦》篇者,后人皆已改作‘為’,唯此篇及《非十二子》篇未改,而此篇注遂讀‘詐偽’之‘偽’矣。”[1]317他們的批注盡管角度有所不同,但認識顯然一致,都認為楊倞注錯誤,這里的“偽”應該讀為“行動作為”之“為”。這一看法,應該是正確的,已經(jīng)被今天荀子學界的主流所接受。
二是義為“詐偽”的“偽”,共五見。
03. 詐偽生塞,誠信生神。(《不茍》)
04. 君子審于禮,則不可欺以詐偽。(《禮論》)
05. 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jīng)也。(《樂論》)
06. 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污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性惡》)
07. 三曰言偽而辨。(《宥坐》)
這五例,前四例“偽”或者與“信”、“誠”相對,或者與“詐”并稱,讀為本字,自然不會有異議。后一例楊倞未注,顯然是以“偽”為本字。楊明照(1909—2003)曰:“《禮記·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鄭注:‘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1]1109顯然這里的“偽”也是虛偽的意思。
三是今人以為“人為”的“偽”,例子最多,高達35例。如:
08. 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正論》)
09. 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禮論》)
10.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正名》)
11.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
12.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13.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14. 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人之性偽之分者也。(《性惡》)
15.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性惡》)
16.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于圣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惡》)
17. 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謂之生于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于信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性惡》)
18. 故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性惡》)
19. 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20.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21.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22.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23.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性惡》)
24. 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圣人之于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性惡》)
25. 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
這里的35個“偽”字,《正論》篇1例、《禮論》篇5例、《正名》篇2例,《性惡》篇最多,共27例。其意義內(nèi)涵,頗值得研究。
《正論》篇:“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楊倞注:“偽,謂矯其本性也。”物雙松(1768—1830)曰:“‘以偽飾性’,即荀子家言。偽謂善也。”久保愛(1759—1832)曰:“偽,謂禮也。所謂以禮制心。”王先謙(1842—1917)曰:“偽與為同,謂作為也。”[1]725
又《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楊倞注:“偽,為也,矯也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物雙松曰:“荀子專主禮,其以善為‘偽’者,亦從此中來。”久保愛曰:“‘偽’,謂以禮義師法矯本性也。”郝懿行曰:“偽,自然也。偽,作為也。‘偽’與‘為’,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為矯,全書皆然,是其弊也。”王先謙曰:“郝說是。荀書‘偽’皆讀‘為’,下文‘器生于工人之偽’,尤其明證。”金其源(1789—1961)曰:“以‘為’釋‘偽’,猶不若以‘行’說‘偽’。行者,《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nèi)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以‘人為’釋‘偽’,猶有矯其本性之誤解,不若以‘性行’之‘行’釋之。”[1]935
楊倞認為“偽”字既是形聲字也是會意字,“人”旁表義,“為”表聲,但也兼會意,會“人作為”之意。而所謂“人作為”之“偽”就是“矯其本性”,矯正其先天的惡性,所以這種“偽”也就是“矯”完全是后天的。物雙松進而將這種“偽”釋為“善”,久保愛則視為“禮”,庶幾近之。郝懿行、王先謙以為“偽”當讀為“為”,訓為作為、行為。金其源則以為“偽”當直接訓為“性行”①“性行”,《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是“本性與行為”,并引王充《論衡·率性》“善漸于惡,惡化于善,成為性行”、《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將軍向?qū)櫍孕惺缇瑫詴耻娛隆钡葹樽C。的“行”,不需要改讀。這些“偽”字到底如何釋讀,確實是一個問題。
《漢語大字典》取許慎(58—147)《說文解字》說解“偽”:“偽,詐也。從人,為聲。”因此以“欺詐、假裝”為“偽”的本義。以“人為”為“偽”的引申義。[2]232-233《漢語大詞典》則以“人為”為“偽”的第一義項,以“奸偽、欺詐”為第二義項,以“偽裝、假裝”為第三義項。[3]1675筆者認為,比較起來,《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恐怕要好一些。“偽”是會意字,應該是“從人從為,為亦聲”,所以“人為”當為本義。②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434頁)明確指出:“人為為偽(引申為詐偽)”。但“人為”有邪有正、有好有壞,引申之,就有“奸偽、欺詐”之“人為”,也有合乎道德理性之“人為”。③齊沖天《漢語音義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5頁)名之為“貶義”與“褒義”。《漢語大詞典》正確地依次列出了“偽”的“人為”義和“奸偽、欺詐”義,卻漏掉了“偽”的道德理性之“人為”義。《漢語大字典》不僅忽視了“偽”的道德理性之“人為”義,還顛倒了“偽”的本義與引申義,問題就更嚴重了。
明了“偽”字意義的來龍去脈,我們就可以肯定,《荀子》中《正論》《禮論》《正名》《性惡》四篇的 35例“偽”字,完全不必改讀為“為”,完全可以以本字為訓。但它們到底是指一般的“人為”,還是指具有特殊含義的“人為”,則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從楊倞注“矯其本性”來看,楊倞是將這種“偽”當成了含有特殊義的“人為”,不過它不是“奸偽、欺詐”之“人為”,而是道德理性之“人為”。這一點,物雙松謂之“善”,久保愛謂之“禮”,說得更清楚。
也許是受通行的《說文解字》許慎說的影響,宋儒一般都以“欺詐、假裝”為“偽”的本義,忽視了“偽”還有道德理性之“人為”義的一面,因此對荀子學說頗多誤解。比如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就一再說:“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圣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圣人之道至卿不傳。”④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下同)子部儒家類《二程外書》卷十。“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卻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⑤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二程外書》卷十二。“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圣人?”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二程遺書》卷十八。在程氏兄弟的眼中,“偽”顯然是貶義詞,是“欺詐、假裝”的意思,所以他們對荀子“以禮為偽”、“以禮義為偽”、以“堯舜偽也”予以激烈的批評。
更早一點的劉敞(1019—1068)也是如此。他說:“荀子言圣人之性以惡,言圣人之道以偽,惡亂性,偽害道,荀子之言不可為治。”⑦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公是弟子記》卷三。為什么“荀子之言不可為治”?因為“荀子言圣人之性以惡,言圣人之道以偽”。在他看來“惡亂性,偽害道”。顯然,這種“害道”的“偽”意義是負面的,也就是“欺詐、假裝”的意思。所以他覺得不可理喻。
但宋人也有支持楊倞說的。南宋黃震(1213—1280)《讀諸子·荀子》就指出:“至其以為善為偽,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録。蓋彼所謂‘偽’者,人為之名,非詐偽之‘偽’。若曰人性本惡,修為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為深愛,而后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后世以為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眾罵。不然何至以為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⑧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黃氏日抄》卷五十五。案:原文“人為之名”下衍一“人”,據(jù)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稗編》卷四十三引刪。黃氏雖然認為荀子的“人性本惡”說有“一偏”之弊,但認為荀子“所謂‘偽’者,人為之名,非詐偽之‘偽’”,“古今字義漸變不同”,不能以今律古。尤其可貴的是其“以為善為偽”說,明確地肯定荀子這種“偽”是“善”。可以說是對楊倞注的進一步發(fā)展。
明清之際的傅山(1607—1684)也是如此,他說:“《性惡》一篇,立意甚高,而文不足輔之。‘偽’字本有別義,而為后世用以為詐偽,遂昧從人從為之義,此亦會意一種。”[4]1307這是說,《荀子·性惡》篇屢稱之“偽”字,宋人如二程等“用以為詐偽”,是“昧”于其作為“會意”字的“從人從為之義”而做出的錯誤解釋。“偽”字“從人從為”,本來就有特定的“人為”之義,又何必要刻意地訓為“虛偽”、“詐偽”呢?傅山在《荀子·禮論》篇的評注中又進而指出:“‘性偽’文:‘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此明言禮全是偽也。”[4]1288這是說,荀子與“性”相對的“偽”,內(nèi)涵就是“禮”,是指“人為”中的禮義行為。
到乾嘉時代,同情荀子的學者們就更多了。如紀昀(1724—1805)就說:“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于先王之教。……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偽,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后人昧于訓詁,誤以為真?zhèn)沃畟巍!盵5]770錢大昕(1728—1804)、章學誠(1738—1801)、郝懿行等也看出了這一問題。
上面《正論》《禮論》《正名》《性惡》篇的35例“偽”字,其內(nèi)涵不是與“義”相對,就是與“禮義”相類;不是名之以“文理隆盛”,就是稱之為“禮義法度”之所“生”。特別是從“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于信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諸說來看,這里的“偽”顯然并非指一般的“人為”,而是有著特定的內(nèi)涵,指的是道德理性之為。一般人的行為不足以將圣人與眾人區(qū)分開,只有道德理性之為才是“圣人之所以”“異而過眾者”,這種“偽”,價值內(nèi)涵非常清楚,以一般的“人為”名之,實在是抹殺了荀子所謂“偽”的特定價值,誤讀了荀子。所以黃震、紀昀認定荀子是“以善為偽”,傅山“明言”荀子所謂“禮全是偽”。因此,不論從荀子本文來看,還是從后來有見的學者的分析來看,說《荀子》這些“偽”字的內(nèi)涵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行為、作為,而是指具有特定意義的“人為”——理性之“人為”,完全是經(jīng)得起檢驗的。
梁濤最近著文,提出:《荀子·性惡》篇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之“‘偽’據(jù)郭店竹簡應作‘’,指心之思慮活動、心之作為。”他認為,“‘偽’《荀子》中也用作詐偽之意,……這些偽都是負面的,是需要禁絕的,與荀子正面主張的偽是根本相對的。很難想象荀子會用同一個字去表達兩個相反的概念,合理的解釋是兩個概念是用不同的字來表達的,一個做‘偽’,指虛偽、詐偽,一個做‘’,指心經(jīng)過思慮后做出的選擇、行為,這不僅于文字有據(jù),也符合荀子‘心慮而能在為之動謂之偽’的定義。”[6]71-73此說很有創(chuàng)意,但擅自改字為訓實質(zhì)是對《荀子》這些“偽”字的內(nèi)涵和意義缺乏了解。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梁說的大前提“很難想象荀子會用同一個字去表達兩個相反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古漢語“正反同詞”[7]144常見,《荀子》書也是如此。就是人們所艷稱的“性”與“心”,其內(nèi)涵與功能也往往正反互見。比如同樣一個“心”字,《荀子·解蔽》篇有“心知道”說,《正名》篇有“心有征知”說,《性惡》篇有“心辨知”說,這些“心”的作用,無疑是正面的。但同樣是《荀子》,在《仲尼》篇有“詐心”說,在《大略》篇有“邪心”說,在《勸學》篇說“心利之有天下”,在《王霸》篇說“心欲綦佚”“心好利”。這些“心”的功能,應該是負面的。又比如“性”,《荀子·性惡》篇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人之性惡明矣”,意義無疑是負面的。但《荀子·解蔽》篇又說“凡以知,人之性也”,《性惡》篇也稱“夫人雖有性質(zhì)美而心辨知”,這里“性”,意義無疑又是正面的。既然《荀子》書“性”與“心”內(nèi)涵與功能都有正面義與負面義,為什么“偽”就不能如此呢?
懂得《荀子·性惡》篇的這些“偽”字都是從“從人從為”之一般“人為”義引申出來特殊義——道德理性之“人為”,荀子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說的意義就昭然若揭了。荀子是說,人先天的生性有邪惡的一面,其善良的道德則是后天的理性起作用的結(jié)果。同樣,“圣人化性而起偽”,是說圣人以天生的智性改造了人天生的惡性,人的道德理性行為從此而生。“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是說圣人與眾人不同而遠遠超過眾人的,不是先天的“性”,而是后天的道德理性之“偽”。“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是說我們所看重“堯、禹、君子”的,不是他們先天的生性,而是他們后天的“偽”,他們發(fā)揮道德理性的作用,從而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人類的禮義文明。《荀子·性惡》篇的這些“偽”字既然有了理性人為義,再將這些“偽”字一一改為“從心從為”的“”,恐怕就是畫蛇添足了。
厘清了《荀子》書42個“偽”字的三種涵義,就可以發(fā)現(xiàn)其義為“詐偽”的用法文獻最為常見,許慎的《說文解字》和《漢語大字典》以它為本義,是習慣成自然。而讀為“為”,義為“行為”的用法文獻雖然不多,但也能找出一些來。只有具有理性之“人為”義的“偽”,《荀子》巨多,高達 35例,而其他先秦秦漢文獻則“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幾乎一例也沒有。
《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都以《論衡·明雩》的“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和《荀子·性惡》的“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并列,[2]233,[3]1675以為這里的兩個“偽”字意義相同,其實靠不住。
《論衡·明雩》篇:“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劉盼遂(1896—1966)案:“‘偽’當作‘為’,音于偽反。”[10]670張宗祥(1882—1965)案:“‘偽’疑‘為’訛。”[11]311一般都將這里的“偽”譯為“人為地”。[12]937表面上好像與《荀子·性惡》篇的“偽”意思差不多。但實質(zhì)完全不同。《論衡·明雩》篇的“偽”,是做不該做的事。“時未當雨”,人“偽請求”“天”做不當之事。“天”“下其雨”,其行為,就好像“人君聽請”一樣,是不講原則的“非賢”之舉,故稱之為“妄”。顯然,這種“偽”價值是負面的,與《荀子·性惡》篇“偽”內(nèi)涵的道德理性價值完全不同,怎能把它們混為一談?
王充(27—97)《論衡》一書中有兩個“偽”字與《荀子》的理性之“偽”內(nèi)涵相同。其《本性》篇曰:“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后,勉使為善也。”[10]138不過,這是轉(zhuǎn)引《荀子·性惡》篇之語,不能說是王充自己的說法。除此之外,在先秦秦漢文獻里,筆者尚未發(fā)現(xiàn)有像荀子一樣將“偽”賦予了道德理性內(nèi)涵的例子。
利用《荀子》書“偽”字的這一特殊含義來討論《荀子》書相關(guān)篇章的年代及其真?zhèn)危P者認為標準客觀實在,結(jié)論應該具有說服力。
近些年來,否定《性惡》篇為荀子所作的說法非常流行。周熾成認為:“《性惡》篇在《荀子》全書中是非常獨特的:其他篇都不以人性為惡,唯獨該篇以人性為惡。”依此,他推斷:“《性惡》篇的作者很可能不是荀子本人,該篇在西漢初期還沒有產(chǎn)生,很可能是生活在西漢中后期的荀子后學或與荀學有關(guān)的人所作的。”①周熾成:《荀子韓非子的社會歷史哲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3、9、36-45頁。其說又見周熾成:《荀子:性樸論者,非性惡論者》,《光明日報》2007 年3 月20 日第11 版;周熾成:《荀子非性惡論者辯》,《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周熾成:《荀子乃性樸論者,非性惡論者》,《邯鄲學院學報》第22卷第4期(2012年12月);周熾成:《董仲舒對荀子性樸論的繼承與拓展》,《哲學研究》2013年第9期。顏世安也“懷疑,《性惡》篇不是作于荀子之手,是其后學發(fā)揮性偽分論,與孟子性善論公開對立,以張大學派門戶。提出這個懷疑的主要原因是,如果荀子本人主張人性惡,這樣立場鮮明的觀點,何以在其他篇章中一次都沒有說到?‘性偽分’與‘性惡’雖有相似處,畢竟是不同的思路。”②顏世安:《荀子、韓非子、莊子性惡意識初議》,《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荀子人性觀非“性惡”說辨》,《歷史研究》2013年第6期。這些觀點雖然新穎,但缺乏文獻根據(jù),都是些想當然的似是而非之詞。我們從《荀子》書“偽”字的用法就可以得到明確的結(jié)論。
如上所述,《荀子》書有理性之“人為”義的“偽”高達35例,這是《荀子》書的一大特色。其他的先秦兩漢文獻則一例也沒有。這一現(xiàn)象非常有意思。我們不能說《荀子》書沒有理性之“人為”義“偽”字的篇章就皆非荀子所作,但可以肯定有理性之“人為”義“偽”字的篇章一定屬于荀子的作品。為什么?因為別人的作品沒有這一用法,只有荀子作品才有,這是荀子作品的區(qū)別性特征之一。
這35個“偽”字,《性惡》篇最多,占了27例。其余《正論》篇有1例、《禮論》篇有5例、《正名》篇有2例。《正論》篇、《禮論》篇、《正名》篇我們沒有不認為它們不屬于荀子的,事實上,它們都有理性之“人為”義的“偽”字。如果認為《性惡》篇不是荀子的作品,否定荀子有理性“人為”義之“偽”的說法,那就得將《正論》篇、《禮論》篇、《正名》篇也排除出去。這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不能想象沒有《正論》篇、《禮論》篇、《正名》篇的《荀子》還是《荀子》,因此,也不能想象沒有《性惡》篇的《荀子》還是《荀子》。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根據(jù)那些“莫須有”證據(jù),否定《性惡》篇為荀子所作的說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利用《荀子》書“偽”字的用法來斷定《性惡》篇為荀子所作是不是孤證?筆者的回答是非也。從《荀子》書其他極具特色的用辭我們也能得出同樣的結(jié)論。不過,限于篇幅,筆者另文再作探討。
[1]王天海. 荀子校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字典[M]. 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7.
[3]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 漢語大詞典:第1卷[M].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
[4]傅山. 荀子評注下[M]//傅山全集:第2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5]永瑢. 四庫全書總目[M]. 北京:中華書局,2003.
[6]梁濤. 荀子人性論辨正——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說[J]. 哲學研究,2015(5).
[7]蔣紹愚. 古漢語詞匯綱要[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8]李零. 郭店楚簡校讀記[M]/道家文化研究:第17輯(郭店楚簡專號),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9.
[9]廖名春. 郭店楚簡老子校釋[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10]黃暉. 論衡校釋[M]. 北京:中華書局,1990.
[11]張宗祥. 論衡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2]袁華忠,方家常. 論衡全譯[M].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
(責任編輯:蘇紅霞 校對:李俊丹)
B222.6
:A
:1673-2030(2016)03-0005-06
2016-07-01
廖名春(1956—),男,湖南武岡人,清華大學歷史系、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協(xié)創(chuàng)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