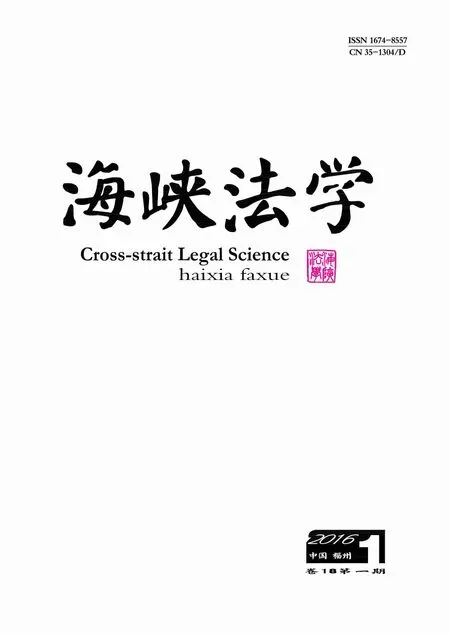農村房屋登記的困境及應對
馮樂坤,楊 揚
?
農村房屋登記的困境及應對
馮樂坤,楊揚
摘要:在我國不動產實行統一登記制度的要求下,農村地區也相應地進行了農村房屋登記,但農村房屋登記往往處于不重視的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立法將房屋占有范圍之內的宅基地規定為集體所有。因農民欲要建設房屋必須要取得宅基地使用權,但立法卻將宅基地使用權人限制為農村集體成員,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實際被限制流轉,相反,立法并沒有限制農村房屋的自由流轉,此種狀態必然導致農村房屋所有權人往往與宅基地使用權人并不一致,農村房屋的價值受損,登記與否就顯得并不重要。盡管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被賦予了生活保障功能,但宅基地的社會保障功能逐漸弱化,財產性功能日益增加,人們在習慣上以及實務中已經將其作為私有財產,即宅基地并非集體所有土地而是私有土地,此種事實必然為進一步宅基地自由流轉奠定了基礎,未來立法應當予以重視。
關鍵詞:農村房屋登記;農村集體成員;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集體所有
我國長期以來不同類型的不動產往往由不同的行政機關進行負責登記,此種分散登記現狀往往形成了增加交易成本以及損害了交易當事人利益等等消極后果,如此,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對不動產進行立法登記的同時,遂又意識到了制定統一不動產登記的重要性,①孫憲忠著:《中國物權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251頁。2007年《物權法》第10條明確規定了“不動產實行統一登記制度”,2015年遂制定通過了《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其中的第5條明確規定實行登記的不動產的權利范圍。然而,不動產包括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著物,房屋登記理應屬于不動產登記的范疇,農村房屋登記目的在于通過對農村房屋的權屬確權而對農村居民以及與其進行交易第三方的利益進行保護,盡管各地均通過制定房屋登記辦法而強調了對農村房屋應該登記,且現實中皆進行了農村房屋的登記工作,②自2007年的《物權法》要求對不動產實行統一登記以后,在2008年原建設部通過的《房屋登記辦法》明確要求各地對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范圍內的房屋進行登記的前提下,各地紛紛制定了各自的房屋登記辦法,由此,全國各地紛紛啟動了農村房屋的登記工作。但受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的影響,農村房屋登記往往處于被忽視地位。③徐曉松:《中國農房登記的制約因素及制度改革思考》,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第18頁。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農村房屋必然要與城鎮房屋一樣進行登記,農村房屋不重視登記的現狀必然致使此種價值功能無法得以彰顯,實有必要對農村房屋登記所涉及的相關問題進行研討。本文特從以下方面進行詳細解讀:
一、農村房屋登記困境之梳理
受我國長期以來實行城鄉二元制度的影響,房屋也就被區別為城鎮房屋與農村房屋,但立法卻一直只比較重視城鎮房屋登記,如1983年12月國務院發布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以及1997年10月原建設部發布的《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就規定了城鎮房屋登記,我國房屋登記其實就是以城鎮房屋為主。不過,在2007年的《物權法》規定應制定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的要求下,2008年制定的《房屋登記辦法》明確要求對城鎮、農村房屋同時進行登記,但農村房屋登記仍然被人們所忽視。因農村房屋登記與其依附的宅基地使用權登記密切相關,為了有效地扭轉人們對農村房屋登記的態度,就需要先對農村房屋登記主體與宅基地使用權登記主體之間的相關問題進行梳理。
(一)農村房屋原始登記主體與宅基地使用權登記主體的非一致性
在我國現行立法明確規定農村集體對農村土地享有所有權的前提下,為了解決農民住房用地,立法又從農村土地用途中劃出了宅基地類型,且歷年來一直將其明確規定為集體所有。①為了應對實務中的兵團職工的住房用地,在借鑒立法為農村居民從集體所有土地設立宅基地經驗的基礎上,兵團管理部門遂為農場職工設立了宅基地,但此種宅基地為國有,而非集體所有。參見李克飛:《對兵團團場宅基地及其房屋流轉的法律思考——兼與農村宅基地之比較》,載《兵團黨校學報》2012年第1期,第23頁。同時,為了便于對農村社會進行管理,我國又以土地為基礎而構建了農村集體組織,農民往往以戶籍為標準而歸屬不同的農村集體,進而,也就成為集體成員而對集體所有土地享有權利,為了確保農民對宅基地享有的使用權利,立法遂又創設了宅基地使用權。只不過,基于確保住房用地的公平,現行立法也就明確規定了農民以戶的名義申請取得宅基地使用權,且實行一戶一宅。②戶是計劃經濟制度下的產物,但戶內成員總是處于不確定狀態,加之,各地對戶并沒有統一標準,實務中所產生的問題較多,未來立法應當取消宅基地的一戶一宅的分配制度(申惠文:《農村村民一戶一宅的法律困境》,載《理論月刊》2015年第8期,第105頁)。不過,現行立法沒有將一戶一宅的宅基地制度明確廢除,為此,本文仍以其為切入點而對宅基地主體進行研究。
因戶是我國基于便于人口管理而實行戶籍制度的產物,一般以子女結婚成家為標志而組成一個家庭戶籍,農村現實中的戶實質上為農村家庭,但農村家庭往往由多個自然人組成,戶其實為農村家庭內的自然人聯合體,③高圣平、劉守英:《宅基地使用權初始取得制度研究》,載《中國土地科學》2007年第2期,第36頁。戶內成員對宅基地使用權其實就處于準共有狀態。④朱巖:《“宅基地使用權”評釋評——<物權法草案>第十三章》,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第87頁。同時,農民成為農村集體成員并不以年齡為標準,現實中主要以出生、婚姻為標準,農村家庭成員其實包括成年人與未成年人。如此,一戶一宅的宅基地使用權以戶為計算單位,宅基地使用權其實就是農村家庭所有成員共享的權利,即農村家庭單獨享有的權利,而非農村家庭成員個體享有的權利,⑤孫憲忠著:《物權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頁。此點恰好與集體成員平均分配所屬集體所有的土地權益現實相吻合。不過,將所有農村家庭成員均登記為宅基地使用權人并不現實,實務中往往需要一位成年人以戶主名義出現,遂將作為家庭成員代表的戶主登記為宅基地使用權人。
當然,農村房屋依附在農村集體土地之上,確定農村房屋所有權的歸屬并不以是否為農村家庭成員為標準,且往往以建設房屋的出資人為標準進行確定,建設房屋的出資人往往被確定為農村房屋所有權人。因實務中不乏存有家庭以外的人員單獨出資或者合伙出資建設房屋的事實,農村房屋所有權就并不一定歸農村家庭的所有成員,數個家庭成員或者單獨的家庭成員乃至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員均有可能成為房屋所有權人,①農民與非農村集體成員在宅基地上共建房屋,且約定了各自對房屋所有權所占的分配數額,此類合同應當有效,非農村集體成員也就相應的取得了相應份額的所有權。參見周舜隆:《農村宅基地上共建房屋的產權歸屬》,載《人民司法》2010年第22期,第20頁。由此,農村房屋所有權登記必然要以自然人名義進行登記,而不能以戶的名義進行登記,無論農村房屋單獨所有或者共有,均在所非問。
此外,農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權的目的在于建設供其居住使用的房屋,因取得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農村房屋建設許可證的過程中均是以戶的名義,多數情形下的農村房屋所有權主要體現為家庭成員的共有,但現實生活中的家庭成員變動性較大,將單獨的農村家庭成員登記為農村房屋所有權的權利主體并不合理,實務中就出現了應當以戶名義對農村房屋所有權進行登記的主張。②任國良:《農村村宅產權登記主體探討》,載《中國房地產》2010年第1期,第43頁。不過,現實中的大多數農村房屋均由成年的部分農村家庭成員出資建設,以戶的名義對農村房屋進行登記就是將其視為所有戶內成員的共有,此種情形必然侵犯了出資建設房屋的其他家庭成員利益,如此,此種主張顯然與現實不符,不應當采納,仍然需要以建設房屋的出資人為標準而確定農村房屋所有權的歸屬。
總之,宅基地使用權人與農村房屋所有權人并不一致,宅基地使用權人往往登記為作為農村家庭代表的戶主,農村房屋所有權人登記為具體的自然人,因房屋與土地的天然聯系使然,房屋所有權人應與宅基地使用權人具有一致性,但宅基地使用權人與房屋所有權人并不一致,兩者登記主體必然有所不同,此種情形一定程度地阻礙了農村房屋的流轉,農村房屋價值也就無法充分體現出來,人們對農村房屋登記的積極性也就不高。盡管2008年的《房屋登記辦法》第8條明確規定了“房屋登記應當遵循房屋所有權和房屋占有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權利主體一致的原則”,但農村房屋所有權人與宅基地使用權人之間不一致的事實卻致使無法實踐此種原則,反而又致使農村房屋登記出現了諸多問題。
(二)非農村集體成員的農村房屋登記與宅基地使用權登記主體的矛盾性
農民建設房屋的目的主要供自己居住,農民理所當然地會其原始取得所有權,但現實中又大量存在著人們通過繼承、買賣、贈與、共建等方式而繼受取得農村房屋所有權的事實。就農村房屋的繼受主體而言,不僅包括本農村集體成員,也包括非本農村集體成員,部分主體甚至為城鎮居民,即農村房屋所有權人就在同一農村集體成員之間以及農村集體與非農村集體成員之間不斷進行變動,農村房屋所有人就并不一定為農村集體成員,非農村集體成員亦可成為農村房屋所有權人,為此,農村房屋登記就必須對此種情形予以面對。③關于將農村房屋轉讓給非農村集體成員的效力,大多數見解并沒有將其認定為無效合同,而是在有所區別的基礎上將部分轉讓合同認定為有效,即非農村集體成員亦可以取得農村房屋所有權。主要文獻參見應秀良:《農村房屋買賣合同效力辨析》,載《法律適用》2009年第7期,第54頁;戴孟勇:《城鎮居民購買農村房屋糾紛的司法規制》,載《清華法學》2009年第3期,第74頁;石鳳友著:《土地法律制度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225頁。盡管我國2008年的《房屋登記辦法》第87條明確規定了對不屬于房屋所在地農村集體成員的繼受取得房屋所有權人不應辦理轉移登記,但農村房屋為農民的主要財產,為了對其財產利益進行保護,理應將繼受取得房屋所有權人登記為農村房屋所有權主體,且不論是否為農村集體成員,均應允許登記。④高圣平:《不動產統一登記視野下的農村房屋登記:困境與出路》,載《當代法學》2014年第2期,第51~53頁。
然而,在立法明確將宅基地使用權人限制為農村集體成員的前提下,農村房屋所有權人理應限制在同一農村集體成員內,但現實中的農村房屋所有權繼受主體已經包括了非本農村集體成員,因農村房屋所有權主體變動必然涉及到了房屋占有范圍內的宅基地使用權主體變動,尤其是非本農村集體成員享有農村房屋所有權的事實已經致使宅基地使用權人突破了僅為同一農村集體成員的規定,①各地關于農村房屋轉讓后的宅基地使用權登記主體的立法并不一致,部分立法允許將非農村集體成員確定為宅基地使用權人,如2008年《海南省土地權屬確定與爭議處理條例》第23、24條之規定,部分立法則不允許非集體成員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如2005年的《臨沂市農村宅基地管理暫行辦法》第 7、9條之規定。此種事實卻與宅基地使用權人為農村集體成員的立法限制相悖,農村房屋流轉必然受阻,財產性價值無法充分得以體現,農民對農村房屋登記也就一直持有無所謂的態度,即使國家一再要求對農村房屋進行登記,仍然無濟于事。
總之,現實中的農村房屋所有權總是在不同主體之間不斷轉移,②鄭尚元:《宅基地使用權使用權性質及農民居住權利之保障》,載《中國法學》2014年第2期,第151頁。農村房屋所有權人已經不一定為農村集體成員,非農村集體成員往往成為了農村房屋所有權人,以往僅將農村房屋的登記主體限制為農村集體成員的立法理念也就不盡合理,將非農村集體成員登記為農村房屋所有人要必然予以面對,但現行立法仍將宅基地使用權人往往限制為農村集體成員,此種情形必然致使農村房屋僅供居住使用,農村房屋價值沒有得到充分彰顯,農民利益無法得以保護。
二、農村房屋登記問題之本質
依前述,農村房屋登記主體與宅基地使用權登記主體不一致的事實致使農村房屋登記并沒有充分地將農村房屋價值彰顯出來,即使將農村房屋進行登記,也不符合現實中對農村房屋的流轉需求,再者,作為宅基地所有權主體的各個農村集體往往具有獨立性,在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此種事實必然進一步限制了農村房屋流轉。不過,形成此種事實的根本原因就是立法將宅基地使用權人限制為農村集體成員,為此,本部分特從農村宅基地使用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與農村房屋關系方面而對影響農村房屋登記的本質問題進行解讀。
(一)農村房屋與宅基地使用權之關系
就房屋與土地之間的關系而言,現實中主要存在兩種形態:一種是房屋所有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為同一主體,另一種則為房屋所有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為不同主體,即房屋與土地分別歸屬不同的權利人。在房屋所有權人與土地所有權為同一主體的情形下,房屋所有權轉移之時,土地所有權隨之轉移,也就形成了房地一致的原則,相反,若房屋所有權人與土地所有權人為不同主體,因房屋所有權轉移必然涉及到土地所有權轉移,實行房地一致原則必然會損害土地所有權人的利益,為此,立法往往采納了賦予房屋所有權人對土地享有使用權,轉移房屋所有權只能將其占有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一并轉移,房地一致原則也就進一步得到了深化,已經從注重所有權轉變為注重使用權。不過,立法對房屋所有人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往往設定了一定期限,期限屆至之時,又通過規定房屋所有權人對土地使用權自動續期或者由土地所有人購買房屋所有權的方式予以解決。
實際上,在我國土地所有權實行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房屋所有權人并不對土地享有所有權,為了應對此種尷尬的困境,立法遂通過創設房屋所有權人對土地享有使用權的模式即建設用地使用權,農村地區又稱之為宅基地使用權。因我國農村地區長期以來欠缺社會保障制度,宅基地使用權往往作為一種福利而由農村居民無償無期的使用,基于彰顯居住權公平以及農村土地所擔負糧食安全等等公共利益之考慮,立法就明確規定了“農村居民以戶的名義申請取得宅基地使用權,且實行一戶一宅以及禁止批準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而再申請宅基地”。③參見2004年《土地管理法》第62條第1款、第4款之規定。據此,宅基地使用權只能由本村集體成員申請取得,且禁止非集體成員申請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尤其是禁止城鎮居民購買宅基地,①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第41條、1991年的《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26~27條明確允許“城鎮非農業人口”以及“回原籍鄉村落戶的職工、退伍軍人和離、退休干部以及回家鄉定居的華僑、港澳臺同胞”可以申請農村宅基地,但1998年修訂后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則又將其予以刪除,農村宅基地申請主體也就被限制為農村居民,相關規范性文件也就一再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買宅基地,如2004年11月的國土資源部發出的《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此種立法設計無疑限制了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的流轉,進而,也就形成了農村房屋滅失后的宅基地由農村集體收回或者由本農村集體收回宅基地使用權而對房屋補償的立法實踐。②劉紅梅、段季偉等:《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繼承研究》,載《中國土地科學》2014年第2期,第47頁。
顯然,農村房屋與宅基地分屬不同主體,立法遂設計了宅基地使用權,農民在取得宅基地使用權后,才能進行房屋建設,農村房屋所有權人也就同時享有宅基地使用權,繼受取得農村房屋的所有權人必然要同時取得宅基地使用權,此種法理邏輯也正好與房地一致的原則相符。然而,宅基地使用權的一戶一宅以及宅基地使用權人只能為農村集體成員的立法限制卻致使繼受取得人只能對房屋享有所有權,除本農村集體成員且沒有享有宅基地使用權以外,取得農村房屋所有權的非本農村集體成員無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權,房地一致原則遂就無法彰顯,農村房屋流轉就受到了限制,僅體現了農村住房的居住使用價值,農村房屋的登記與否就顯得并不重要,農村房屋登記的必要性也就受到了質疑!如此,目前正在進行的農村房屋登記其實就是借助國家行政力量而強制推行的結果,并非農村居民的自愿選擇。
(二)農村房屋與農村土地之關系
為了應對農村房屋與農村土地所有權人不一致的情形,立法創設了宅基地使用權,但僅允許農村集體成員申請取得宅基地使用權,此種宅基地使用權的身份性限制就致使農村房屋所有權的價值受損,農村房屋登記就處于被忽視的困境。究其原因,此種困境無非是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密不可分,盡管現實中的諸多見解極力主張應允許宅基地使用權自由流轉,③目前,我國多數學者認為應允許宅基地使用權流轉(韓世遠:《宅基地的立法問題——兼析物權法草案第十七章宅基地使用權》,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5期;申建平、孫毅著:《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陳小君、高飛等:《后農業稅時代農地權利體系與運行機理研究論綱》,載《法律科學》2010年第1期;王崇敏:《論我國宅基地使用權制度的現代化構造》,載《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賀日開:《我國農村宅基地使用權流轉的困境與出路》,載《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相反,部分學者則持堅持不允許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孟勤國:《物權法開禁農村宅基地交易之辯》,載《法學評論》2005年第4期;陳柏峰:《農村宅基地限制交易的正當性》,載《中國土地科學》2007年第4期;胡呂銀:《中國土地權利立法論綱》,載《揚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韓松:《論對農村宅基地的管理與<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但并沒有對影響其深層次的原因進行解讀,為了有效應對農村房屋登記問題,有必要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為切入點而對其進行探究。
既然我國立法規定農村集體可以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主體,因現實中的農村集體為獨立的社會組織,各農村集體之間并沒有隸屬關系,各農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就具有了獨立性,農村土地的所有權主體實質上并不具有統一性。同時,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基于社會公共利益考慮,立法又禁止集體所有土地通過買賣、出租等形式進行轉讓,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就不能轉讓予任何社會組織與個人,僅僅允許國家為實現公共利益之目的而對其征收,即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只能單向變為國有,不能轉變為任何其他社會組織、個人所有。如此,在立法確認農村集體對土地享有獨立所有權的同時,各農村集體對其所有土地的處分權卻受到了嚴格限制,農村土地必然不能自由流轉。
當然,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相比,立法將城鎮土地所有權明確規定為國有,且往往授權各級地方以國家名義具體管理,但禁止國有土地以各種形式自由流轉。同時,為了對土地使用人的利益進行保護,立法又設計了建設用地使用權。不過,盡管各建設用地使用權人并不一致,作為其基礎的土地所有權主體卻統一為國家,此種主體的統一性恰為不同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流轉奠定了基礎,即使立法為建設用地使用權設計了權利存續期限,但在該權利存續期限之內,也允許其流轉。由此,因土地所有權為同一主體即國家,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就不會在土地所有權人之間形成利益沖突,依附國有土地上的城鎮房屋就可以自由流轉,城鎮房屋價值就得到了充分彰顯,城鎮房屋登記也就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進而,因城鎮房屋登記重視程度與城鎮土地歸國家所有具有本質聯系,城鎮土地所有權的統一性往往為城鎮房屋流轉排除了障礙,此點往往對解決農村房屋登記問題有所啟示,即必須注意土地所有權統一性對城鎮房屋流轉所起的基礎作用。
總之,宅基地所具有的獨立性以及非流轉性就致使宅基地使用權無法自由流轉,即使允許宅基地隨房屋一并轉移,①有人認為,“宅基地使用權不得單獨轉讓,但房屋所有權轉移的,宅基地使用權應當隨之轉移”。參見王利明主編:《中國民法典學者建議稿及立法理由——物權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頁。但在立法仍然固守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的前提下,此種立法設計往往與法理相悖,農村房屋登記問題就無法真正地得以解決。需要注意是,為了解決宅基地使用權在實務中存在的弊端,部分學者主張應通過賦予法定租賃權、地上權、永久性用益物權等方式進行應對,②法定租賃權主要由韓世遠、劉凱湘等人主張(韓世遠:《宅基地的立法問題——兼析物權法草案第十七章宅基地使用權》,載《政治與法律》2005年第5期;劉凱湘:《法定租賃權對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意義與構想》,載《法學論壇》2010年第1期),地上權主要由王衛國、朱慶育、唐文平、高圣平等人主張(王衛國、朱慶育:《宅基地如何進入市場——以畫家村房屋買賣案為切入點》,載《政法論壇》2014年第3期;唐文平:《宅基地上私權處分的路徑設計》,載《北方法學》2010年第6期;高圣平:《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的法律邏輯》,載《煙臺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永久性用益物權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組成的“中國土地政策綜合改革課題組”主張(《強化中國城鄉土地權利:整體性法律框架與政策設計》,載《改革》2008年第3期)。但諸種見解仍然以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為前提,因集體所有主體的非統一性也就致使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農村房屋無法自由轉讓,諸種見解并不能將農村房屋登記問題徹底解決。所以,農村房屋登記問題解決實質上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具有本質關系,只要仍然固守各個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農村房屋登記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
三、農村房屋登記的應對之策
依前述,農村房屋登記問題其實與宅基地使用權以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相關,因農村集體各不相同,各個集體所有的土地必然各不相同,但現行立法禁止各個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自由流轉,加之,宅基地使用權只能由本集體成員享有,農村房屋流轉必然受限,農村房屋登記就顯得無足輕重。因農村居民對農村房屋登記的態度往往由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性質決定,應對農村房屋登記問題其實就要以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改革為切入點進行研討。當然,農村土地往往擔負了社會保障功能,但宅基地的私有財產屬性比較明顯,此兩點因素往往影響了人們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改革的態度,為此,本部分特對其詳細進行解讀:
(一)農村土地的農村社會保障功能弱化
自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在我國將公有制界定為國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后,城鎮地區往往大量發展國有經濟,農村則大量推行集體經濟,但國家為城鎮居民提供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村則設立了以集體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然而,隨著土地承包制度在農村的實行,集體經濟相應地日漸式微,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也就逐步轉變為以家庭和農村土地保障為基礎。③陳少輝、李麗琴等:《60年建構與改革:漸行漸近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5期,第137~140頁。不過,為了應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又進行了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險、最低生活補助、農民工、失地農民等方面社會保障制度的立法構建,但與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相比,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等問題,并沒有達到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水平。至此,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沒有完全建構起來,仍然延續了以家庭和農村土地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制度。
當然,我國的農村集體是以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為標準而具體劃分的結果,土地往往成為了農村集體的主要財產,農村集體經濟必然主要以農村土地的經營為主,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以農村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其實就是以農村土地保障為主。同時,盡管隨著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又以家庭和土地為基礎,但家庭收入主要以土地承包收入為主,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實質上仍以土地為基礎。如此,我國長期以來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其實仍然以農村土地為基礎,為了充分彰顯農村土地所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在農村集體內部,不論土地承包或者宅基地取得,均以農村集體人口數量為基礎而進行平均分配。
就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國家與個人的各自責任限度而言,國家承擔過多責任往往又增加了財政負擔,如何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合理分配各自應當承擔的財產責任也就成為了立法設計者首要的考量因素。①林輝煌:《家產制與中國家庭法律的社會適應—— 一種“實踐的法律社會學”分析》,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2年第4期,第152頁。因我國目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完全構建,農民仍然從集體土地所有權中享有各種財產利益和權利,②韓松:《論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集體成員受益權能》,載《當代法學》2014年第1期,第53頁。農民其實更多地僅關心土地收益與國家的福利,③吳越:《從農民角度解讀農村土地權屬制度變革——農村土地權屬及流轉調研報告》,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2期,第73頁。理應繼續對農村土地社會保障功能予以肯定,堅持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也就具有了正當性。只不過,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會逐漸減弱,④李郁芳:《試析土地保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的作用》,載《暨南學報》2001年第6期,第63頁;韓松:《農地社保功能與農村社保制度的配套建設》,載《法學》2010年第6期,第67頁。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畢竟不夠全面,農村要逐步推進實施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在目前城鄉一體化的背景下,城鎮與農村必然會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如此,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全構建其實有效地應對了農民的生存之憂,此點正好有效抑制了對農村土地所有權改革的顧慮。⑤關于農村土地的改革,目前主要存有私有化、國有化的見解,因農村土地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限制,此種見解也就遭到人們的質疑。實際上,在農村構建社會保障制度后,相關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才有現實價值。參見趙小軍:《對土地私有化之批判—兼論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載《河北法學》2007年第1期,第90~93頁;葉明:《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一體化的法制前提:農村土地國有化》,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第94~99頁;陶鐘太郎:《論城鄉一體化視域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走向》,載《中國土地科學》2015年第3期,第65頁。
總之,農村房屋登記困境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具有本質聯系,有效地應對農村房屋登記就必須要允許集體所有土地可以自由流轉,但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完全構建的前提下,農村集體所有土地仍然擔負著農村社會保障職能,允許各個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自由流轉也就會誘發諸多社會問題,解決農村房屋登記困境必然依賴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完全構建。⑥在制定《物權法》過程中,有人認為,允許宅基地使用權自由轉讓可以解農民的燃眉之急,因缺乏后續的生存手段,往往致使賣地的農民變成生活無著的流民,農村社會出現了社會動蕩(主要文獻參見王利明著:《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2003年版;孟勤國:《物權法開禁宅基地交易之辯》,載《法學評論》2005年第4期)。相反,有人卻認為,農民是理性主體,往往權衡利弊之后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將農民視為非理性主體往往缺乏科學依據(王文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相關理論評述》,載《東南學術》2012年第4期)。須注意的是,我國目前的土地管理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農村土地主要分為農業、建設用地等類型,但不同用途的農村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有所不同,農業用地主要作為農民的生存保障,宅基地主要作為居住保障。因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宅基地的取得途徑已經由繼承、轉讓等方式替代了原來的福利分配,①馮小:《宅基地權屬觀念的地方性建構——基于皖北S村宅基地制度實踐的分析》,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4~6頁。已經突破了居住保障功能,②參見劉紅梅、段季偉等:《經濟發達地區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繼承研究》,載《中國土地科學》2014年第2期,第48頁。財產功能已經日益突出,宅基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日益減弱。③高圣平、劉守英:《土地權利制度創新:從<土地管理法>修改的視角》,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3期,第64頁;余永和、張鳳:《農村宅基地流轉的論證與宅基地制度的完善》,載《農村經濟》2014年第6期,第10頁。據此,宅基地已經成為了農民的主要財產,農村房屋就成為農民的主要財產,實有必要對農民的此類財產利益進行立法保護,允許宅基地隨著農村房屋轉移而一并轉移也就成為了必然。
(二)宅基地的私有化
在目前農村沒有構建完整的社會保障制度的背景下,任何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改革均會影響到社會穩定。但不容忽視的是,農村房屋往往為大多數農民的主要財產,立法所確立的宅基地集體所有以及禁止集體所有土地自由流轉的理念反而又致使農村房屋價值無法體現,農民對其房屋登記態度也就比較消極,即使對農村房屋進行登記也無濟于事。為了充分地對農民的利益進行保護,理應允許農村房屋進行自由流轉,但其基本前提就是要正確理解宅基地的權利屬性。
自上世紀60年代將農村土地確定為集體所有之前,我國農村土地長期以來一直實行私有化,宅基地往往由農民個人享有所有權,宅基地及其房屋往往被稱為祖業或者家產,即使立法已經將宅基地規定為集體所有,受農村房屋私有以及原有的農村土地私有制度的慣性所致,人們習慣上必然將宅基地視為了私有。④黃鵬進:《農村土地產權認識的三重維度及其內在沖突——理解當前農村地權沖突的一個中層視角》,載《中國農村觀察》2014年第6期,第18頁。同時,基于彰顯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功能,農民對宅基地往往無償、無期限使用,農民對宅基地使用權事實上已經享有了永久性權利,宅基地其實處于私有。⑤賀日開:《我國農村自己地使用權流轉的困境與出路》,載《江蘇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第76頁。為了解決農村房屋轉讓問題,有人主張,應將現行對宅基地使用從無償、無期限變為有償、有期限使用(申建平:《宅基地使用權流轉模式的選擇》,載《政法論叢》2011年第3期,第37頁;劉廣明:《“雙軌”運行: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制度解困的可行性》,載《法學論壇》2014年第2期,第108頁),但此種見解無視《物權法》所確立的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自動續期的立法理念,不值得采納。再者,隨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宅基地已經無法通過集體分配而取得,現實中取得宅基地主要通過分家析產、繼承、轉讓等方式,將宅基地視為了私有財產已經毋庸置疑。⑥馮小:《宅基地權屬觀念的地方性建構——基于皖北S村宅基地制度實踐的分析》,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4頁。如此,為了應對農民對房屋享有所有權的事實,宅基地也往往隨著房屋所有權一并流轉,實務中亦有農村集體認可了本集體成員向非集體成員出讓房屋,且將宅基地使用權人登記為受讓人。⑦吳越:《從農民角度解讀農村土地權屬制度變革——農村土地權屬及流轉調研報告》,載《河北法學》2009年第2期,第75頁。
此外,自2008年來,我國開始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尤其是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允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然而,現行立法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范圍并沒有具體規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往往限制為鄉鎮企業用地,將宅基地轉為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于法無據,但在理論界要求放開宅基地流轉的呼吁下,各地方也進行了宅基地流轉的試點工作,典型的就是宅基地置換模式,此種模式實際上就是將宅基地轉為經營性建設用地。⑧侯銀萍:《產權性質視角下的“農地入市”困境破解》,載《法學》2014年第5期,第60~61頁。當然,宅基地換房模式表面上是農民以其宅基地面積換取小城鎮內的一套住宅,實質上是各地已經將農村宅基地視為了私有,此種后果無疑就是間接承認了房屋及其宅基地已經歸農民私有,此種現實恰為反思宅基地的權利屬性奠定了基礎。
總之,盡管現行立法將宅基地規定為集體所有,但農村傳統習慣一直將宅基地視為私有財產,即在立法禁止將農村房屋轉讓給非集體成員的前提下,不僅沒有禁止作為非本集體成員的繼承人進行繼承,也并沒有禁止將農村房屋轉讓給非集體成員,只不過,目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主要是建設在國有土地上的城鎮房屋的交易市場,若允許農村房屋進行交易,兩種土地所有權必然會誘發沖突,立法就將宅基地私有化程度限制在一定范圍。①朱新華、柴濤修等:《土地股份合作制效率的經濟學分析——基于國家、產權和契約的視角》,載《中國土地科學》2010年第6期,第40~44頁。當然,目前對宅基地所有權的改革見解較多,但不容忽視的是,人們已經將其視為了私有財產,宅基地已經成為了農民的私有財產,②實務中已經出現了將宅基地確定了農戶所有的見解。參見徐萬鋼、楊少壘:《城市化視角下的農村宅基地流轉制度分析》,載《社會科學家》2009年第3期,第69頁。宅基地集體所有的權利屬性已經弱化,宅基地自由流轉也就會成為必然,此點恰為解決現實中的農村房屋登記困境提供了有效基礎。
四、余論
現實中所出現的農村房屋登記諸問題其實與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具有本質關系,因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農村土地往往又負有社會保障功能,禁止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自由流轉也就理所當然,農村房屋流轉也就受到了限制。然而,隨著近年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步予以完善,人們其實已經將宅基地視為了私有,為了對農民的利益充分保護,理應允許農村房屋及其占有范圍內的宅基地一并流轉,現實中的農村房屋登記諸多問題也就得到了迎刃而解。只不過,城鎮房屋以國有土地為基礎,土地使用權人已經向國家繳納了土地出讓費,若允許農村房屋流轉,因宅基地為集體所有,宅基地使用權人往往無償使用,此種情形必然致使統一的房地產市場中存有兩種不同類型的房屋所有權,房地產市場必然處于混亂狀態。③參見何博:《從政法傳統看中國的地方變通——以宅基地流轉試驗為切入點》,載《政法論壇》2012年第2期,153~154頁;朱新華、陳利根等:《農村宅基地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啟示》,載《中國土地科學》2012年第7期,第41頁。如此,目前應對農村房屋登記困境的諸多見解并不能徹底解決諸多問題,④為了破除此種城鄉土地所有權二元的現狀,實有必要對兩類土地所有權進行統一而設立統一的土地使用權。參見李鳳章、張秀全:《土地所有權立法之反思:透過歷史的映照》,載《北方法學》2009年第2期,第64頁。有待進一步詳細研討。
(責任編輯:常琳)
【作者簡介】馮樂坤(1972- ),男,甘肅榆中人,甘肅政法學院教授,甘肅省經濟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員。楊揚(1991 - ),男,四川成都人,甘肅政法學院2013級民商法學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村民自治的基本理論研究》(項目編號:10XF0007)、2011年甘肅省高等學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農村集體土地發展權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12-02
中圖分類號:D922.38;F30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8557(2016)01-004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