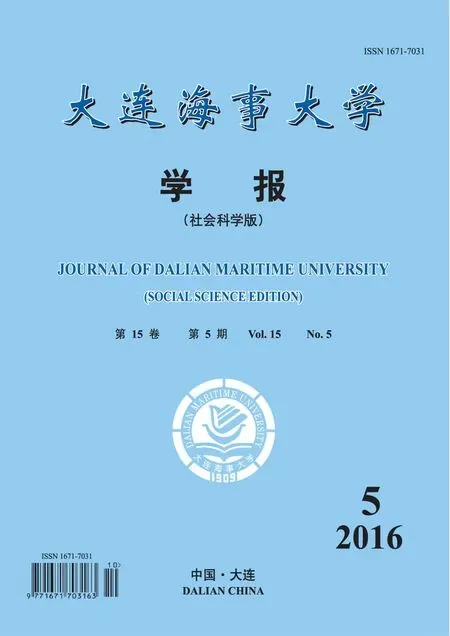“一石二鳥”的批量合同
——海上公法與私法的突破與融合
徐 峰
(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上海 201306)
?
“一石二鳥”的批量合同
——海上公法與私法的突破與融合
徐峰
(上海海事大學法學院,上海201306)
以往的海上貨物運輸,只要要約與承諾一達成,船貨雙方的法律關系仿佛就被設定了,受私法意義上的海商法強制性體系與公法意義上的反壟斷豁免制度制約,承托雙方只能在既定的范圍內討價還價,而《鹿特丹規則》創造的批量合同就是解開這把枷鎖的鑰匙。從批量合同的源頭說起,追溯其歷史演變的過程,并分析該制度的優點與產生的必然性,最后找出中國航運市場在面臨批量合同時的不利之處,并探索解決之道。從“批量合同”這一海上公法與私法的交匯點考察,發現其正逐步改變海上交易的格局,“一石二鳥”地化解了公私法上的兩大困局。
批量合同;強制性體系;反壟斷豁免;《鹿特丹規則》
一、海商法強制性體系與反壟斷豁免的源起
海上貨運法自誕生以來就被認為存在著一個強制性體系,以至于有學者說,海上貨物運輸法發展的歷史就是海上強制性體系的引入史[1]。尤其在班輪運輸領域,提單運輸關系構成了強制性體系的基石,雙方意思自治原則在這里幾乎無從施展。即使是非班輪運輸,適航、禁止繞航等義務依然是承托雙方繞不開的話題。
在民商法領域,縱使在契約自由理論變遷中歷經“契約死亡論”、“契約的再生”等學說的洗禮,意思自治原則在以合同作為手段的交易中一直作為一種神圣的信念為交易者所信仰和遵循著,但在海上貨物運輸領域,強制性體制這一充滿海商特色的傳統航運慣例依然屹立不倒。
而“反壟斷豁免”則是由《1916年美國航運法》所創立的機制,相比于石油、鐵路等已經完全開放的市場,航運領域依舊矢志不渝地堅守傳統,可以說,反壟斷豁免無異于承運人的保護傘,承運人可以自如地操縱運價,壟斷市場。
然而,時過境遷,效率與公平成了當今航運業的主旋律,航運業的不景氣逼迫船東開始反思,認識到船貨雙方利益平衡的重要性,再加上民法中契約自由思潮的影響,這兩大制度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在原有的航運格局下,反壟斷豁免制度與海商強制性體系各司其職,反壟斷豁免代表了運價與數量的公開與固定,海上強制性體制意味著承托雙方權利、義務的不可變更。但批量合同的誕生改變了航運法與貨物運輸法的傳統做法,該規定融合并沿襲了公法與私法的規定,在兩者之間架起了橋梁,同時也意味著航運法在某種意義上正走向了私法化。
二、海商法強制性體系與反壟斷豁免的突破
(一)海上強制性體系發生松動
海商法中公認的強制性體系由《1893年美國哈特法》所創立,其中規定了適航與管貨義務,但最核心的一點,就是嚴格限制意思自治提單項下的意思自治,承托雙方不得隨意增減海上運輸法設定的權利與義務。
在《海牙規則》體系下,盡管其調整對象依然是“提單或類似的權利憑證”而非運輸合同,但強制性體系已經有松動跡象。例如,《海牙規則》第6條針對不可轉讓的單證,運輸特別貨物,允許雙方自由約定。另外《海牙規則》規定了裝前卸后條款,規定了在貨物裝運之前與卸載之后雙方可自由約定權利與義務。
到了《漢堡規則》,雖無“批量合同”之概念,但已涉及其實質,批量合同已初見雛形,其第2條第4款可間接適用批量合同。該款規定:“如果合同規定,貨物將在一個議定的期限內分批運輸,本公約的各項規定適用于每批運輸……”批量合同下的每一次運輸均受《漢堡規則》調整。
(二)反壟斷豁免正逐步取消
1.1916年航運法
反壟斷豁免制度由《1916年美國航運法》所確立,該制度更偏重于保護公共承運人即班輪公會的利益,為其壟斷航運市場、操縱運費提供了合理性與合法性,并作為美國航運法的核心制度延續。在1984年之前,所有出入美國的班輪運費制定權都屬于班輪公會,由其提供固定的價目表,時至今日,該制度依然不乏支持者。例如Stephen Craig Pirrong用“核心理論”來證明在正常供需平衡下產生競爭并不具有效率,容易造成市場不穩定,并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2]William Sjostrom也曾應用該理論,以實證分析的方法支持班輪運輸領域的壟斷,如價格固定、產出確定、準入渠道的控制等,以實現競爭性平衡。[3]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FMC)也有部分委員建議保留反壟斷豁免。
2.國際航運組織的實踐
BIMCO于1982年發布了專門針對散裝貨的VOLCOA包運合同,2004年將其修改為GENCOA重新發布,1980年INTERCOA80油輪合同經國際油輪船東協會發布,[4]但真正對該原則有所突破并完成制度建構的是美國航運法改革。
3.1984年航運法
就《1916年美國航運法》而言,在1984年之前,班輪公會是處在絕對支配地位的,相當于壟斷組織“卡特爾”,他們利用運費表來規范航運市場。這種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75年,一直持續到1984年航運法公約的出臺。有趣的是,在美國對于“處于類似狀況”的托運人而言,差別對待是不被允許的,這種做法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航運服務建立在公開的價目表與運輸服務條款之上,對所有托運人一視同仁,秉承著公平航運市場的信條。[5]
但很快這種現象發生改變。隨著1984年航運法的制定,美國海運貨物運輸機制開始放寬,一些航運公司開始降價競爭。這一切要歸功于1984年航運法允許雙方簽訂服務合同。當然1984年航運法本身也存在著局限性,例如改革得不夠徹底,盡管其允許服務合同的簽訂,但這種許可的功效非常有限,因為根據法律規定,合同的條款必須公開,并向聯邦海事委員會報備,這樣,承運人之間的運價完全透明,從實質上消除了價格競爭。[6]這條規定也被稱為“跟進”條款,由于承托雙方之間的合同已被公開,其他任何托運人都可以在與承運人簽訂合同時要求類似的權利。實質上,航運法服務合同條款試圖用右手給予反運費歧視政策之后,利用左手即“跟進”條款又重建了一回。[7]588
4.1988年航運法改革
《1988年航運改革法》(OceanShippingReformActof1998)是內在動力與外部力量共同驅使的結果。一方面,獨立承運人的力量變強。在過去的20年里,隨著全球化一體化、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加快,集裝箱的日漸普及,航海技術的專業化,跨國公司不再一味依賴傳統的班輪公會,轉而青睞新興的物流企業,承托雙方的關系日益平衡,加上歐盟和美國的航運政策轉向自由化,班輪公會的壟斷空間被越來越嚴格地加以限制,從而使其會員的海運市場份額被逐漸蠶食,班輪公會一家獨大的歷史已成往事,獨立承運人包括中小承運人的勢力日趨龐大,此消彼長,從而催生了1988年的航運法改革。再加上美國作為傳統的貨主國,其國內的托運人對反壟斷豁免一直持反對立場,美國國會中代表托運人利益的集團借航運法修改之際發出聲音也是順其自然的。另一方面,美國在其他領域的改革成功也給予了寶貴的啟示。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在諸多領域內實施管制放松改革,并在電力、鐵路方面取得了成功,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果,但是海運業方面,放松管制改革相對落后,在航運市場低迷的今天,承托雙方自然而然地就將航運法改革這一議題搬上日程表。
《1998年航運改革法》的制定是承托雙方妥協的產物。雖然該法案通過秘密服務合同的簽訂、運價本的電子化,充分調動了航運市場的競爭機制,但該法案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聯邦海事委員會仍得以保留。
5.海德法案——完全取消反壟斷豁免
1998年航運法改革法案生效后的幾個月,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亨利·海德遞交了《自由市場反壟斷豁免改革法案》。該法案是專門針對國際航運反壟斷豁免而產生的。該法案引用了反托拉斯法,認為競爭的初衷是通過合適的價格提供良好的服務與商品。而航運業并非天然具有反壟斷的特權,以往固定價格的做法反而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更依賴于一種高效率的運輸體制,完全開放的競爭市場是班輪競爭政策應該實現的目標。[8]305
海德法案認為,《1998年航運改革法》向更有競爭性的國際班輪運輸體制走出了有限的、卻是堅實的一步,班輪運輸壟斷的壁壘應被打破,讓競爭成為班輪運輸業主旋律,并適用美國反托拉斯法,而不是針對目前的體制縫縫補補,保留舊體制。新的體制將有利于承托雙方、貿易商,甚至終端的消費者,最終受益的還是整個航運市場。
6.美國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
美國反托拉斯現代委員會也持相同觀點,認為應當在1998年航運法改革所取得成果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取消反壟斷豁免,除非該反壟斷豁免能夠給美國帶來利益。
根據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向美國國會遞交的報告,在20世紀初,當時觀點認為在特殊行業(如電力行業、天然氣行業)應當實行壟斷來建立有效的市場結構,過度競爭反而存在風險。結果就是,政府加強了運費以及市場準入的管制。但60年過去了,需要重新審視該觀點。第一,在電力領域,科技進步反而加強了競爭;第二,過度的管制造成了市場的扭曲,人們紛紛質疑反壟斷豁免的必要性。以上兩點促使政府放開了除航運市場以外的管制,并隨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應。1990年,美國在鐵路和航空這兩大非海運運輸領域至少獲得360億至460億美元的經濟收益。
但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卻認為在海運領域仍然應當保留反壟斷豁免,該委員會在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前作證時并沒有主張取消航運法反壟斷豁免制度。但在2006年,聯邦海事委員會一委員向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提交的書面文件中指出,美國應該取消遠洋公共承運人之間固定運價和協商運價方面協議的反壟斷豁免。可見,在聯邦海事委員會內部意見也不完全一致。[8]309盡管目前海德法案與反托拉斯現代化委員會的議案并未被當局采納,但筆者相信,不久的未來,美國的反壟斷豁免就會蔓延到海上貨運領域。
7.批量合同的雛形
(1)OLSA。美國國內法中的遠洋班輪服務協議(Ocean Liner Service Agreements,以下簡稱OLSA)就是在此基礎上構建的。一些大船東為了重新奪得市場地位,開始與貨主簽訂此協議。該協議在1984年就出現了,但經1998年航運改革法的修改得以更加完善。根據美國《1998年航運改革法》第2條第19項,運輸協議通常被視為一種服務合同。
(2)忠誠契約。所謂“忠誠契約”即貨主為了降低運費,或獲得延期回扣,約定將全部或部分的貨物由特定的承運人承運,貨主一旦違反忠誠義務,將被處以罰款。該協議同樣限制了托運人的選擇權,屬于OLSA的變形,因為美國航運法卻沒有授予忠誠合同反壟斷豁免,可見這方面美國具有的特殊性。[8]296美國始終沒有作出取消反壟斷豁免這一最終的決策。
8.歐盟反壟斷與美國同步
歐盟在反壟斷豁免領域走在了美國的前頭,直接取消了航運業反壟斷豁免。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歐盟航運市場的不景氣、各大航運企業惡意競爭,歐共體理事會于1986年通過一攬子方案。其中《歐共體條約第85、86條適用于海上運輸的實施細則的4056號理事會條例》(以下簡稱第4056/86號條例)給予了班輪公司反壟斷豁免。該條例填補了當時歐共體海運領域缺乏競爭法規則的空白,建構了歐盟反壟斷豁免制度。
隨著世界航運市場的不斷發展變化,班輪公會享有反壟斷豁免權也不斷受到挑戰。到了2004年10月,成員國顧問委員會認為,沒有確切的經濟證據表明班輪公會享受整體豁免仍具合理性,建議取消班輪公會整體豁免。2006年9月歐盟理事會正式宣布廢止第4056/86號條例,自2008年10月18日起,正式取消班輪公會的反壟斷豁免權,實現向自由化海運市場的過渡。
三、《鹿特丹規則》——海商法強制性體系與反壟斷豁免的融合
在《鹿特丹規則》制定初期,美國代表團的議案建議借鑒《1916年美國航運法》中創造的服務合同的概念,提出航運服務合同的自由要受到一定限制,即承托雙方在運輸協議中寫明最小貨運量以及對應的價格。有學者甚至認為該服務協議與批量合同可以畫上等號,即都是由承運人在一定時期內經海路分批運送托運人提供的特定數量的貨物,并且都同樣通過班輪運輸方式分批運送貨物……遠洋班輪服務協議與批量合同只是稱謂有所不同,并無實質性差異。[9]值得一提的是,在公約最后的版本中,批量合同界定比美國1984年航運法下的服務合同范圍更廣,因為它不需要承運“特定數量”或“特定比例”的貨物。[10]就是《鹿特丹規則》體系下,批量合同對于美國航運法即海上公法的突破。
就運輸合同雙方的法律關系而言,《鹿特丹規則》大幅度地放開管制,根據《鹿特丹規則》第80條第1款的規定,本公約所適用的批量合同可以自由約定增加或減少本公約中規定的權利、義務和賠償責任。但公約依然設定了底線,承運人仍然要遵守一些基本義務,如適航等。自《海牙規則》以來,海上貨物運輸法一直對“契約自由”有著非常嚴格的限制,《鹿特丹規則》對批量合同的調整方法,可謂“契約自由”在一定范圍內又“復活”了。這也就是《鹿特丹規則》中,批量合同對于海上強制性體系即海上私法的突破。
而《鹿特丹規則》將傳統上的公法規定與私法規定熔為一爐,并結合了公法與私法的發展潮流,借鑒了相關國際公約與美國法的最新司法實踐,打破了陳規,這在以往的國際海事立法中并不多見。
四、批量合同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優點
1.船貨雙方利益的平衡
批量合同極大促進了海上貿易的往來,尤其在班輪領域的大批量貨物運輸,有效平衡了船貨雙方利益。貨主和承運人可以進行平等的協商,改變了以往國際海上貨物運輸法傾向保護承運人的情況。[11]
2.公平效率的基本理念得到提倡
隨著民法領域越來越追求公平與效率以及契約自由,海商法領域也隨之效法。批量合同一方面提高了雙方交易的效率,另一方面使得責任限制制度能夠更為有效地得到貫徹,原因在于責任限制制度是對船東的一種保護,在原本承運人強勢的大環境下,雙重的保護似乎顯得多余,且加劇了承托雙方利益的進一步失衡,而批量合同的產生使得天平稍稍向托運人一邊傾斜,因而,由承運人再享有一些特權似乎可以為其接受。更為重要的是,《鹿特丹規則》適用范圍下批量合同和海上多種運輸方式的規范統一化,能夠為將來全球供應鏈管理的大環境提供較為全面的服務。[12]
3.航運政策的導向
反壟斷豁免在其他領域的成功也漸漸被航運領域所認同,并從國家立法層面上升到國際公約,從1984年航運法到1988年航運法改革再到《鹿特丹規則》,從服務合同中的固定價格到秘密價格再到批量合同,政府當局對航運市場進一步放松管制。
4.批量合同的經濟分析
反壟斷豁免的取消能夠極大地促進競爭,并有效地降低運費水平。由于國際班輪市場的運費統一,航運市場供求關系并不能被有效反映。另外,非公會成員的獨立承運人經常參照公會運價確定自己的運價水平,導致價格競爭不充分,總體運價水平和附加費偏高。[8]301在此情形下,取消反壟斷豁免能夠有效降低運費,不僅有利于大托運人,對于小托運人的拼箱貨,如DHL,聯邦快遞的拼箱公司也會因此受益。[7]589
5.美國政策與歐盟政策逐漸趨同
如果航線兩岸的航運政策有著較大差異,則將會加大運輸的法律與經濟成本,進而影響到貿易的正常開展。在大西洋航線這一海上運輸最為繁忙的版圖上,如果航線一端,如歐盟實行反壟斷豁免,而美國卻未實行,則該協議就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所以,歐盟取消國際航運反壟斷豁免制度,對從事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海運服務的船公司將產生影響。[8]308筆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美國也會步歐盟的后塵,取消反壟斷豁免。
6.公法私法化
二三十年前,公共行政改革運動在西方盛行,這一行政改革與當時西方的“福利政策”的理念背道而馳,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大政府”這一概念,以期激活市場。伴隨“政府失靈”或“回歸市場”的新思潮,“公法私法化”也應運而生。換句話說,該運動貼上了“舍公就私”的通用標簽。[13]航運市場也掀起了“以私法完成公法”任務的浪潮,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公權力干預的減弱,當局對市場管控力度的削減,“反壟斷豁免”這一“公法性質”的產物、昔日班輪公會的特權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
五、批量合同的弊端及其應對之策
1.批量合同的弊端
首先,班輪運輸的承運人屬于公共承運人,受最低的法定義務的約束,但由于《鹿特丹規則》的豁免,即在滿足基本義務的情況下,承運人可以通過合同自由來規避強制性規范,從而使得承托雙方的利益進一步失衡。而我國航運市場的現狀是,大量的中小貨主無法同班輪巨頭在同等條件下談判,在此情形下產生的批量合同往往并非其真實的意思表示。
其次,批量合同加重了一方當事人的義務,雙方可以通過服務合同、物流合同來規避運輸合同,從而使得航運市場變得更加不平衡。
第三,降低運費的作用很可能會被保險費的提高而抵消。更有甚者,一旦有爭議發生,合同中對托運人不利的訴訟條款很可能會加大訴訟成本。[7]600-601
2.解決之道
目前,在我國,批量合同的運用也呈穩步上升的趨勢,據統計中美航線80%以上、中歐航線70%以上的班輪運輸都是通過批量合同進行的,[14]因而盡快找到破解之道對我國眾多中小貨主而言,屬當務之急。
盡管與OLSA相比,《鹿特丹規則》的批量合同特別規定對中小貨主已經做了一定的保護,如第80條第2款(c)給予了托運人按照符合本公約的條款和條件訂立運輸合同而不根據本條造成任何背離的機會,且向托運人通知了此種機會,(d)背離既不是(i)以提及方式從另一文件并入,也不是(ii)包含在不經協商的符合合同中。但是該保護力度以及范圍并不充分。
本文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對于大小貨主之間力量不平衡的現象,眾多小貨主需要聯合起來,將貨物交由大型貨代或者拼箱公司與承運人進行談判,抱團爭取利益。
(2)在批量合同成立在先,提單簽發行為在后,當事人又是同一的情形下,應當視為簽發的提單內容對批量合同內容進行了變更而認可提單記載的內容,以提單記載內容為準,適用《鹿特丹規則》對于提單的相關規定。[15]如此一來,承運人依舊要受到強制性體系的約束。
(3)在我國對外貿易中,FOB術語常為出口方所采用,而進口方又多使用CIF術語,可以看出,我國中小貨主常常扮演批量合同之外第三人的角色。而根據《鹿特丹規則》的規定,只有在第三方當事人收到明確記載批量合同背離本公約的信息并且明確表示同意受到此種背離的約束之時,背離條款能約束第三方。因而在我國貨主發現批量合同中的背離條款有損于己方利益時,大可拒絕接受,繼續享受《鹿特丹規則》中強制性規則的保護。
(4)明確批量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有學者認為,批量合同作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應受《海商法》第四章的調整并強制性使用。也有學者認為,海上運輸合同并不包括批量合同,因而不受第四章調整,承托雙方的權利、義務應適用《合同法》或《民法通則》規定,不再受強制性體系的約束。還有學者認為應視情況而定,……如果某次運輸是采取航次租船合同的形式,那么,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非強制性地適用該章;如果某次運輸采取的不是航次租船合同的形式,而是提單運輸方式,那么,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就應當強制性地適用《海商法》……在《海商法》中引入批量合同并作出明確規定,可以統一對批量合同問題的不同認識,減少法律糾紛,增加法律的可預見性。[16]本文支持第三種觀點。
(5)由于目前我國航運法的制定面臨重重困難,本文建議效仿美國建立運價管理制度。盡管我國《國際海運條例》界定了班輪公會、運營協議、聯營體不正當競爭的行為,但這些規定遠遠不能適應我國日益成熟的航運市場,我國政府應加快航運法的制定,通過航運法與海商法,即公法領域與私法渠道雙管齊下,共同規制批量合同,最大限度地避免托運人與承運人之間力量的不平衡。
[1]A/CN.9/WG.III/WP.88-Transport law: Preparation of a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Joint proposal by Australia and France concerning volume contracts.[EB/OL].(2007-03-14)[2016-06-11].https://daccess-ods.un.org/TMP/1075434.53574181.html.
[2]PIRRONG S C. Application of core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ocean shipping markets[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92, 35(1): 89-132.
[3]SJOSTROM W. Antitrust immunity for shipping conferences: An empty core approach[J]. Antitrust Bulletin, 1993, 38(2): 419-424.
[4]A/CN.9/WG.III/WP.66-Transport law: Preparation of a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Volume contracts: Document present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Working Group by the Comité Maritime International[EB/OL].(2006-02-17)[2016-06-11].https://daccess-ods.un.org/TMP/23101 77.83284187.html.
[5]LEVINSON M. Two cheers for discrimination: Deregulation and efficiency in the reform of U.S. freight transportation, 1976-1998[J]. Enterprise & Society, 2009, 10(1): 178-215.
[6]於世成.美國航運法研究[D].上海:華東政法大學,2006:30.
[7]MUKHERJEE P K, BAL A B.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volume contract concept under the Rotterdam Rules: Selected issues in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2009, 40(4): 579-607.
[8]於世成,相雷.美國航運法反壟斷豁免制度發展趨勢研究[C]//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研究中心.海大法律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294-312.
[9]郭萍,施歌.對《鹿特丹規則》批量合同之解讀[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1(1):222-237.
[10]李天生.船貨利益平衡原則研究[D].大連:大連海事大學,2010:599.
[11]王威.《鹿特丹規則》下批量合同自由法律問題研究[J].社會科學輯刊,2011(1):95-98.
[12]梁勝.《鹿特丹規則》批量合同的起源與解讀[J].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90-94.
[13]金自寧.“公法私法化”諸觀念反思——以公共行政改革運動為背景[J].浙江學刊,2007(5):143-149.
[14]司玉琢.《鹿特丹規則》的評價與展望[J].中國海商法年刊,2009(1-2):3-8.
[15]沈協.論《鹿特丹規則》中的批量合同制度[J].新西部,2005(23):168-171.
[16]司玉琢,韓立新.《鹿特丹規則》研究[M].大連: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2009:28.
2016-07-06
徐峰(1988-),男,博士研究生;E-mail:455766787@qq.com
1671-7031(2016)05-0009-06
D996.1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