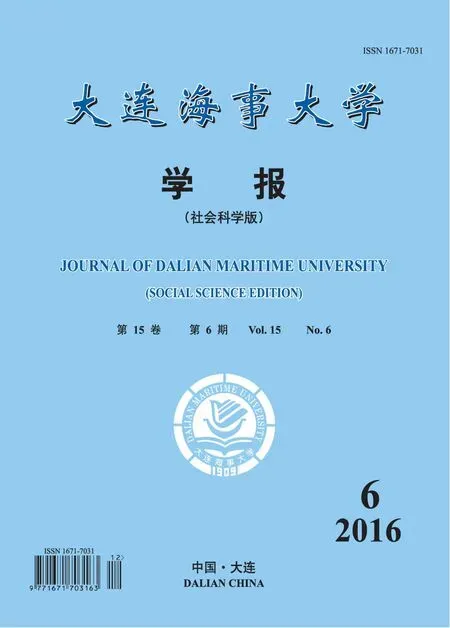國際碳減排義務分擔方案評析及完善
陳貽健,陳敬根
(1.中國法學雜志社,北京 100081; 2.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 200444)
?
國際碳減排義務分擔方案評析及完善
陳貽健1,陳敬根2
(1.中國法學雜志社,北京 100081; 2.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 200444)
國際氣候變化法中的碳減排義務分擔方案從時間上可以大致歸入以《京都議定書》為中心的京都時代和德班平臺開啟的新秩序構建階段。京都時代的減排義務分擔方案主要以“自上而下”模式為主,而新秩序構建階段則以“自下而上”模式為主。《巴黎協定》確立的“國家自主貢獻”方案代表了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最新走向,它通過對“各自能力”原則的貫徹照顧了各國國情并淡化了之前眾多減排義務分擔方案面臨的爭議。但“國家自主貢獻”方案與其他方案一樣都存在局限,尤其是在強調靈活性的同時弱化了減排義務的強制力度。未來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完善需要進一步實現“減排義務分配”與“碳排放權分配”的結合、“國家公平”與“個體公平”的結合、“自愿減排”與“強制結合”的結合。
氣候變化;減排義務分擔;《巴黎協定》;國家自主貢獻
應對氣候變化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全球性風險和挑戰。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以下簡稱《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再到2015年新近簽署的《巴黎協定》,國際社會努力構建了一個應對氣候變化的法律框架。這個框架以減緩、適應、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議題為核心,而其中減緩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途徑,一直以來都是國際氣候談判的重中之重。減緩的目的在于督促國際社會采取減排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化,而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則涉及減排義務分擔問題。從國際氣候談判進程劃分來看,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提出主要可以劃分為兩個重要階段:一是以《京都議定書》為中心的京都時代,該階段可以前溯至1995年《柏林授權》開啟的《公約》下的量化承諾談判,后推至德班平臺的開啟;二是2011年德班平臺開啟的新秩序構建進程,該進程以《巴黎協定》達成為階段性標志,目前仍在發展中。上述兩個階段圍繞“減排義務應如何公平分擔”這一核心爭議提出了相應的分擔方案。通過全面評析這些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優劣,可以為進一步分析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走向和完善提供啟示。
一、國際碳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爭議問題
如前所述,國際氣候變化法中的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提出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重要的階段:一是以《京都議定書》為核心形成的一系列減排義務分擔方案,這些分擔方案總體上以“自上而下”為特征,具體包括關注減排能力的“能者多勞”方案、關注人文發展的碳預算方案、關注人均累積排放的“緊縮趨同”方案等;二是在德班平臺下逐步形成并由《巴黎協定》確立的“國家自主貢獻”減排方案,該方案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減排模式。上述方案提出的減排義務分擔模式雖然存在差異,但都涉及一些需要解決的共同爭議問題,包括歷史排放是否能作為減排責任分配的基礎、以個人還是以國家為單位作為對比排放量的基礎、減排能力能否作為影響減排責任分配的要素、碳排放轉移應否抵消等。通過對這些核心爭議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每個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考量因素。
(一)歷史排放、現實排放責任對減排責任分配的影響
發達國家的高排放支撐著其整個工業化的進程,根據美國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研究和統計,從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間,全球共計排放CO211 222億t,發達國家共排放了8065億t,占全球總量的72%,其中歐盟合計占到27.5%。美國能源情報署的數據顯示,1850年至2004年美國累積碳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一; 截至2006年,美國占世界總排放量的累計百分比高達41%。[1]由于作為最主要溫室氣體的CO2排放至大氣層后,少則50年長則200年不會消失,因此發展中國家堅持認為發達國家對于歷史上的CO2等溫室氣體的排放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并要求發達國家率先承擔減排義務。然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全球排放總量中占有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將逐漸成為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的主力。因此,在發達國家提出的減排義務分擔方案中,往往反對僅以歷史責任為標準來分配減排責任,要求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大國也承擔強制減排責任。
(二)是否以人均排放量作為對比排放量的基礎
緊隨歷史責任之后的是排放量計算單位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類似中國、印度等經濟快速發展而又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以國家為單位的整體排放量是非常驚人的。以中國為例,根據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公布的2013年度全球碳排放量數據,2013年全球人類活動碳排放量達到360億t,平均每人排放CO2為5 t,創下歷史新紀錄。其中,碳排放總量最大的國家為中國,占29%;其次是美國,占15%;歐洲占10%。中國排放總量就已經超過美國總量近一倍,在人均碳排放量方面,中國人均排放量雖然已經超過歐盟,但是仍然離美國和澳大利亞相距甚遠。如果再考慮到歷史排放因素,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公布的數據,美國1850—2005年的溫室氣體人均累積排放量為1107.1 t,英國為1125.4 t,而中國僅71.3 t。[2]鑒于此,發達國家更傾向于將國家作為對比排放量的單位,進而以公平原則為依據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的減排義務。發展中國家則更傾向于以人均單位對比排放量。因為,首先碳排放是與個人的生存和發展相聯系的,對碳排放量的限制也自然將體現在對個人生活水平的影響上。[3]其次,與碳減排義務相對的是碳排放權,人人平等的原則要求人人都能享有均等的碳排放權,這一均等的碳排放權不能因每個人的種族、國籍等因素而不同。
(三)減排能力能否作為減排責任分配的考量要素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存在極大的差異。很明顯,發達國家無論是在資金還是技術上都遙遙領先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認為發展經濟與消除貧困仍然是其第一要務,按照公平原則,發達國家的排放中多為奢侈排放,而發展中國家則多為生存排放,因而,其應具有生存優先權。[4]同時,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將減排能力作為影響減排責任分擔的要素缺乏法理上的支持。理由在于,正如貧窮不能使盜竊免責一樣,缺乏減輕損害的資源以及能力匱乏不能成為應對氣候變化責任的抗辯。[5]在國際法上,對于在一國領土或其管轄、控制下的其他地區進行的活動引發的環境責任通常是作為“跨界損害”來認定,而根據相關國際法文件,“跨界損害”責任的幾個要素為:第一,引起損害的活動未受到國際法的禁止;第二,損害必須對其他國家的人的健康或工業、環境等起重大破壞作用;第三,損害必須是跨界的;第四,損害必須是由這類活動通過其有形后果而引起的。*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ifty-six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10(A/56/10). Paras, 91, 97 and 9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ifty-ninth Session, Supplement No. 10(A/59/10), paras, 175.所以,“跨界損害”責任是一種嚴格責任或結果責任,其關注的是行為的結果而不是行為的合法性,更與行為人的能力無關。[6]國內法也秉持相同的法理,不論是國內的環境法還是侵權法,都不會因為企業盈利能力降低、責任人經濟能力差而減輕其環境污染或破壞的法律責任。[7]
(四)碳排放轉移
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進程的過程中深深意識到工業化生產對環境造成的損害,因此紛紛將高排放、高污染的產業搬往發展中國家,使得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代工廠。這一舉措固然帶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得出口成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但這些活動同時也帶來了大量的碳排放。例如,與中國對美國、日本等大部分發達國家的商品貿易順差相伴而生的是“碳貿易順差”,也就是說,中國生產出口貨物所造成的碳排放量要高于其所進口貨物的生產在國外造成的碳排放量,由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進出口貿易實際上增加了中國的碳排放量。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中國,而是普遍存在于印度、越南等發展中國家。所以,如果說在國際經濟與貿易中發展中國家是碳凈出口國,那么大部分發達國家就是碳凈進口國。基于以上事實,發展中國家認為,國際貿易中的碳排放轉移現象應當作為影響減排責任分擔公平性的因素之一。有學者指出:“在當前多邊減排框架下,一個國家的碳排放是根據該國的生產活動所產生的碳排放來核算的,因此出口生產導致的碳排放由出口國(生產國)負責,而不是消費國負責,即這種以‘生產原則’來測算一國碳排放的做法完全忽視了貿易碳排放轉移帶來的不公平性。”[8]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發達國家這種將制造工廠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行為確實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技術的進步、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業率的上升等利益。因此也有另外的觀點認為,碳排放轉移不應列入減排責任分擔議題的考慮范圍。
二、京都時代的主要解決方案及其優劣
圍繞上述爭議的核心問題,國際社會產生了眾多減排義務分擔方案,這些方案立足于不同的國家利益和立場,反映了各國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理解和態度。在京都時代,國際氣候變化法確立的減排義務分擔方案是《京都議定書》中的量化強制減排模式,該模式以部分發達國家承擔“自上而下”的減排義務為特征,實質上可以看作是“能者多勞”方案的一種版本。下文從公平分配氣候變化權利和負擔的視角,以“能者多勞”方案和其他數個較為典型的方案作為樣本進行評析。
(一)關注減排能力的“能者多勞”方案
碳排放量的多少和一國的工業化程度緊密相關,而一般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其人均國民收入也較高。由此,有學者提出了關注碳減排能力的“能者多勞”方案,典型代表如Baer等提出的溫室氣體發展權框架。該方案認為,富人享受了工業化帶來的成果,因而具有減排的能力并應賦予減排的責任。該方案為區分貧富設置了一個標準,富人需承擔大部分的減排責任,而窮人則沒有減排義務。[9]《京都議定書》確立的部分發達國家率先實行強制量化減排的模式,可以視為方案在國家主體之間的應用。
該方案聯系了歷史排放和現實減排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但是實際上其僅僅關注了世界上享有標準值以上富人(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富人)的減排能力,并未關注發展中國家在基本發展過程中對碳排放的需要,雖然其討論了受益者的責任,但其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在碳排放空間一定的前提下,其整體上并不具有公平性。同時,該方案其實體現了上文討論的一個問題,減排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義務的分配和公平性的考量。減排能力與減緩義務的法理基礎為何,如果說富人承擔減排義務是由于其從碳排放中獲得了收益,積累了財富,其理由并不具有說服力。財富的積累是多方面因素的結果,高碳排放并不必然帶來財富的線性增長。例如,從1950—2000年間的碳排放總量看,發展中國家的馬來西亞高居第4位,巴西和印度尼西亞的碳排放總量仍然排到了第34位和第35位,而發達國家的日本則只排在第41位。[10]因而,只能說,享有財富者更具有完成減排義務的能力,讓富人或富裕的國家承擔多點的減排義務可能最容易實現減排目標,這是一種效率考量。但一旦將責任承擔的理由歸結為“能力”,則無形中將責任問題與道義問題混同了。富人或富裕的國家可以承擔更多的責任,卻是以其自愿承擔為前提。[8]該方案更為深遠的意義是提出了解決減排義務分擔時必須面對的話題:在制訂具體方案之時,能力如何影響減排責任的分配?誠如上文所論述,能力不應影響責任的性質,例如是否承擔法律責任,責任有無,但是,在制訂具體方案之時,其是否可以成為責任承擔方式、先后、大小的考慮因素,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關注人文發展的碳預算方案
該方案是由我國學者在2008年的波茲南會議上提出,其核心內容是在確保氣候安全的前提下公平分配碳排放量。首先應滿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抑制發達國家的奢侈性排放。[11]具體操作方法為:以國家為單位分配碳排放權,但碳排放權的計算基礎應當以個體為標準,再輔之以國際或代際層面上的轉移支付,彌補各國的虧空和余額。該方案的優點主要有:首先,它明確提出了在總體控制溫度變化的目標下,采取自上而下的碳減排分配模式,各國所負碳減排責任具有強制性;同時,其提倡照顧發展中國家的特殊發展需求,抑制奢侈性排放也契合碳排放權本身的發展權和生存權性質;最后,以轉移支付方式彌補虧空也正是建立在碳排放權準物權性質的基礎之上。可以說,相比于歷史上的一些減排方案,此方案已經具有明顯的改進和完善。
但是,也正是由于其在操作層面上的過于細化,使得方案靈活性不足,一些制度也存在一定缺陷,使得其并不足以為各國所接納。例如,該方案在計算人均排放之時并未考慮貿易過程中的碳轉移,忽略這個因素,將使得最終的計算結果出現極大的公平性偏差,從而使得實際操作情況不符合公平內涵。另外,該方案主張先滿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而后再為發達國家的奢侈性排放分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其實,最終的碳減排方案確實需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生存權置于優先地位,然而這是在確定公平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框架之時的考量因素,是其中一個重要指標,而非唯一的指標。所以,該方案考量指標過少,還需增加一些客觀性的標準予以矯正和完善。
(三)關注人均累積排放的“緊縮趨同”方案
“緊縮趨同”方案由英國全球公共資源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ion, GCI)于1995年提出。該方案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較高,大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相對較低,因而,可以選取未來某個時間節點,在這段時間范圍內,降低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使之在將來某個固定的時間點上達到一致,從而維持該水平。
這個方案可以說是站在發達國家視角的典型:其一,其未考慮發達國家的歷史排放責任,單純在未來設置一個趨同的時間和數值,不僅使得歷史責任可能被忽略,而且還給發達國家分配了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然超越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這是極其不公平的;其二,在大多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今天,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著發展基礎設施和經濟的需求,在分配溫室氣體排放空間時本應予以考慮,而該方案卻完全未提及。這種做法忽略了碳排放權的發展權屬性,只是在表面上達到了控制全球溫度變化和人均碳排放量形式上的相同,并不符合公平的要求。
但是,該方案中的“人均碳排放量”概念具有重要的意義,以獨立的個體作為制訂方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權衡公平性與否最為有力的標準。以群體或以國別對碳排放責任的劃分,無形中將會掩蓋個體的發展權和生存權,即使是國家層面的碳排放交易,也需落實到個體來完成。因而,在豐富此概念內涵的基礎上可以形成一個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公平性的方案。
三、德班平臺下的解決方案評析
2011年德班平臺開啟了構建國際氣候法律新秩序的進程,該進程體現出締約主體的廣泛性、談判軌道的一致性以及減排義務分擔的動態性與約束力等特征。[12]德班平臺下出現了歐盟的“分步法”(step wise approach)、美國的“承諾和咨詢”方案(pledge and consultation)、非洲國家集團的“公平參考框架”方案(equity reference framework)等減排義務分擔方案。但最終《巴黎協定》中正式確立的是“國家自主貢獻”方案(INDC),而該方案是在德班平臺下的華沙、利馬兩次會議上提出和細化的,因此應將其視為德班平臺下解決方案的典型樣本。下面將針對該方案進行評析。
2011年,德班平臺開啟了國際氣候法律新秩序構建的進程,這一進程的推進過程正是國家自主貢獻方案的提出和確立過程:多哈氣候大會終結了“雙軌制”并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但沒有涉及德班平臺下新協議的核心內容——減排義務分擔問題;華沙氣候大會最為重要的一項貢獻即是首次提出了“預期的國家自主決定貢獻”,開始在減排義務分擔這一實質內容上區別于《京都議定書》下的量化強制模式;[13]利馬氣候大會則進一步細化“國家自主貢獻”相關信息并明確后續處理進程;[14]《巴黎協定》則在前述會議成果基礎上最終確立了“國家自主貢獻方案”,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國家自主貢獻作為2020年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基本運行模式。
《巴黎協定》確立的這種自下而上式的減排路徑打破了氣候變化談判的法律僵局,“自下而上”模式的優點主要體現在能夠充分兼顧各個締約方的實際情況,各國根據本國國情提出的“國家自主貢獻”方案容易得到實施,同時可以在實施過程中通過“全球總結”和審議對方案作出調整,促使每一個國家都能夠從其自身能力出發進行減排,避免因“自上而下”的減排所可能造成的國內經濟動蕩。同時,它是國際制度安排下的一種具有可行性的“軟減排”模式,具備將國家聲譽等作為達到減排效用的手段和方法。[15]其缺點則主要是在強調自主性、靈活性的同時降低了減排約束力,缺乏京都模式中“自上而下”的強制量化減排義務和遵約制度。從國家自主貢獻方案的確立可以看出,由于利益要求的沖突難以協調,在對公平性問題進行協調的過程中,現實主義替代了理想主義的考量,倫理因素被淡化,實用主義的因素被強化。概括而言,國家自主貢獻方案的不足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國家自主貢獻方案存在以可接受性替代公平性的傾向。一方面,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全球共識,國際氣候談判如果仍然無法就此達成一致性成果,難以在道義上向公眾作出交代;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公平主張,這些主張難以相互兼容或替代。在此情況下,為使談判達成各方可接受的成果,可接受性成為優先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公平性的考慮。但可接受性并不等同于公平性,例如各國基于污染者付費原則承擔減排義務從應然的公平性上來說,并無太多可爭議的地方,但是卻未必能夠得到普遍的接受。
第二,國家自主貢獻方案過多強調“各自能力”在公平原則中的作用。公平原則自身無法提供何為公平的標準。在已有的法律文件中,均將公平原則具體化為共區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共區原則保證了責任劃分的客觀一致,各自能力保證了公平原則的可接受性。為保證談判成果的可接受性,新秩序構建進程中過多強調了各自能力原則。各國自主貢獻方案正是這樣的制度例證。
第三,國家自主貢獻方案表明共區原則仍然缺乏適用的客觀標準。共區原則雖然是公平原則的核心,但對共區原則的理解一直存在誤讀:一是將其視為異質原則,即同時兼具道義原則和法律原則的雙重屬性;二是將其視為以主體身份劃分義務的身份原則;三是將其視為以“能力”為基礎的法律原則。上述理解混淆了共區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區分的意義,導致各方對共區原則分歧嚴重,發達國家陣營甚至試圖取消共區原則。在新秩序構建進程中,盡管經過努力在《巴黎氣候協定》中重新確定了共區原則的地位,但對其適用仍然缺乏清晰的說明,尤其是沒有為如何“區別”、“責任因何而異”問題提供一個客觀的、可操作的標準。國家自主貢獻方案還需要在這一方面作出進一步的明確。
四、未來減排方案的完善
盡管《巴黎協定》確立了“國家自主貢獻”方案,并最大限度地兼顧了締約主體的廣泛性,使得各方可以基于自身的國情,在“各自能力”的范圍內作出減排承諾,但從前面對各種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評析可以看出,暫時不存在一個能夠兼顧各種價值判斷、利益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的減排義務分擔方案。減排義務分擔方案具有雙重性,“除了通過平等協商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利益和負擔進行分配、調整需要符合正義的要求之外,氣候正義的結果還應當與氣候應對的目標相符”[16]。為了制訂這樣一個為各國所接受的公平減排方案,還必須進一步總結各方案經驗,注意以下關系的處理。
(一)“碳減排義務分配”和“碳排放權分配”結合
前述所列方案在注重公平性的某個方面時,往往忽略了對其他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忽略了從減排義務還是碳排放權的分配切入對減排義務分擔方案是否公平具有重大影響。
IPCC第四次、第五次評估報告均指出,未來國際社會應將全球平均氣溫變化控制在2 ℃以內,且傾向于在2050年前把大氣CO2量濃度(CO2-e)控制在450 ppmv之內。[17]因而,即使各種減排方案并未在法案正文中提到這一點,但這幾乎可以看做是所有方案的大前提,是國際碳減排目前可以明確的溫控目標。如此,溫室氣體排放方案是以減排義務還是以碳排放權為切入點就具有重大差別。在450 ppmv的目標濃度確定后,一個固定的時間內,人類可通過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的總量就得以確定(目前世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人均能源消費和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都不可避免地會繼續提高)。[18]如果按照既有的減排模式,全球減排方案提倡發達國家作出一定減排目標的承諾,則在總排放量一定的前提下,即使海洋和陸地今后對排放的碳繼續以56%的比例吸收,全球可排放的總量亦可以計算。[19]如此,則在相關方案賦予發達國家一定的減排義務之后,其余的義務則需要發展中國家來完成。在這種模式之下,非但很難保證達到整體的減排目標,更嚴重的是發展中國家處于極其被動的地位,極有可能實質上承擔比發達國家更重的減排義務。
考慮到碳排放權同時具有發展權和生存權屬性,生存權相對于發展權具有一定的優先性,這就要求碳減排方案應照顧到“最不發達”國家的生存性權利和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發展權利,共同分擔新秩序下要求的減排任務,而非如以往模式那樣,由發達國家率先作出減排承諾,將目標下的其余任務留給發展中國家。在構建氣候變化新秩序的今天,必須注意到,碳減排方案的總體框架需先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以此為切入點,進一步制定具有強制效力的全球性協議。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曾模擬IPCC等著名方案提出的減排措施,并得出四點結論,其中與本部分主題相關的有兩點:一是以“減排”名義提出的方案,極易忽略歷史排放量和當前排放基數等方面的差異,如果以確定各國減排比例作為構建控制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的責任體系,“就會遮掩歷史排放與人均排放的巨大差異,造成不公正后果”[18];二是以人均累積排放為指標,以分配碳排放權為切入點,在排放總量一定的前提下,使得各國國民在一定時間內獲得相同的碳排放量,這是最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18]
因此,由碳排放權的性質可推導出一個原則,未來溫室氣體排放方案的確定應選擇以碳排放權的分配為出發點,進而考慮其他各項涉及公平性問題的因素,完成新秩序要求的減排目標。
(二)“國家公平”和“個體公平”結合
以碳排放權的分配為切入點完善碳減排方案首先克服了部分發達國家承諾“減排義務”、實際掩飾公平的陷阱,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具體分配碳排放權,使得最終方案既能達到控制全球溫室氣體的目的,又能符合公平正義的內涵。
前文已介紹,“緊縮趨同”方案的核心內涵為“一個趨同”,即在一定時間內,發達國家的人均累積碳排放下降,發展中國家的人均累積碳排放上升,最終在一個固定的時間點維持相同的碳排放量。顯然,該方案著眼于未來人均碳排放量的一致,但卻忽略了歷史責任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沒有緊扣公平之內涵。該方案的缺陷使其并不足以為各國所采納,但其提出的“人均累積碳排放”的概念為碳減排方案從“國家公平”到“個體公平”提供了思路。國家是一個集合概念,無論如何強調國家間的公平,都無法回避如何實現各國公眾個體間的公平。如若忽視個體、以國家為標準分配碳排放權,可能造成表面的國家公平而實質的個體不公平。碳排放權的性質要求關注權利義務分配中的人權問題,正是個體對基本人權的需求,才使得碳排放權所指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落實有了具體的對象。因而,以個體為核心討論碳減排責任的分配既是碳排放權性質的要求,也是公平的應有之義。
在以個體為核心的基礎之上,“緊縮趨同”方案關注“人均碳排放量”的未來趨同。但是,未來趨同僅代表了自碳排放量相同之日起的個體公平,卻忽略了發達國家的歷史排放責任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而這二者是涉及公平與否的重要因素。為了彌補這個缺陷,需要在一個趨同的基礎上,再加上另一個趨同,即同時選取歷史中的一個時間點和未來的一個時間點,形成時間區間,在這個區間給定的時間之內,不僅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要最終相同,其人均累計排放量亦需相同,即實現兩個指標上的趨同。例如,選取1900年至2050年時段,在該時段內,截至目前,由于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因而歷史和現今人均排放量都比較高,人均累積排放量高;而發展中國家大多剛進行工業化,人均累積排放量較低。這意味著發達國家需要大幅度減排以滿足在未來的固定時間點達到“兩個趨同”的要求,而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在這段時間內充分利用自己的溫室氣體排放空間發展經濟,實現自己的發展權。[20]
“兩個趨同”方案的計算方法使得碳排放權的分配也有了具體依據,在固定全球升溫范圍后,選定一個固定的時間區間,依據IPCC的最新評估方案所確定的氣候變化事實和確定程度,每個個體所享有的碳排放量以及還剩余的碳排放空間將隨之確定。這種計算方法摒棄了單一的“一個趨同”思維,將歷史排放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同時加以考量,并量化兩類國家人均累計排放量,具有操作性。但是,該方案還需進一步細化,例如是否需選定一個同時適用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時間起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工業化起步的時間各異,如果選用同一個時間點極有可能造成人均累積碳排放量的計算結果的誤差。既然碳排放權具有發展權屬性,對于主體而言,最主要的作用亦是用以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滿足生活需要,那么在選用計算時間起點時可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適用不同的時間起點。甚至,如若存在計算的可能,不同國家和地區亦可以選取本國的工業化起點年限以計算人均累積碳排放量,但為了達到控制溫度變化的效果,最終年限是不能改變的,即2050年。而從實質公平的視角,貿易的碳排放轉移亦需運用“污染者付費原則”計入實際消費國,以統計最終的碳排放量。
此外,既有方案一直未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生存權分開予以討論。碳排放權的生存權性質主要涉及的主體為小島國,這些國家大多經濟不發達,地理環境脆弱,是氣候變化最先和最直接的受害者。碳排放問題對于該類國家而言,直接關乎生存,在人權范疇內,生存權應當具有優先性,如果不考慮小島國的特殊狀況,反而利用其弱勢地位將其忽略,根據基本的公平內涵和碳排放權性質的要求,最終的減排方案將很難稱之為“公平”。因而,減排方案的完善必須考慮賦予小島國一些特殊的照顧。例如,重視小島國提出的減排方案;如果設立減排方案審核和評估機制,應當吸收小島國成員代表;在特殊問題的決議上,給予小島國更多的決定權。
(三)“自愿減排”與“強制減排”結合
上文主要在碳排放權性質的基礎上著重探討碳減排義務分擔方案的實質公平,而最終要實現氣候變化的目標,還必須使減排義務分擔方案從“自愿減排”過渡到“自愿與強制”結合。正如巴黎氣候大會的決定“關切地指出”的,要將與工業化前水平相比的全球平均溫度升幅維持在2 ℃以內,則應將排放量減至400億t,但估計2025年和2030年由國家自主貢獻而來的溫室氣體排放合計總量會達到預計的550億t水平,達不到最低成本2 ℃設想情景范圍。因此,《巴黎協定》確立的“自下而上”模式還需要逐步與“自上而下”模式結合。一個公平并且有效率的減排義務分擔方案需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式共同構成,實現“自愿與強制結合”。“自上而下”模式以AR5對氣候變化事實和確定程度為依據,確立總體減排目標后分配給各個國家,而“自下而上”模式則給予各國以一定的靈活性,根據本國國情提出自己的減排計劃,但也需要配合以國際審查和評估機制,通過強化“全球總結”、評估以及遵約機制,在減排模式的自愿性和強制性之間尋求平衡,并通過逐步調整使“自下而上”方案接近于“自上而下”方案,從而確保《公約》及《巴黎協定》減排目標的實現。
[1]胡昌梅,曹昶輝.歐盟環境保護政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歐中在碳排放問題上的互動[J].法制與社會,2011(1):157-158.
[2]王偉光,鄭國光.應對氣候變化報告2009:通向哥本哈根[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344.
[3]李開盛.論全球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公正分擔——基于羅爾斯正義論的視角[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3):39-56.
[4]杜志華,杜群.氣候變化的國際法發展——從溫室效應理論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J].現代法學,2002(5):145-149.
[5]KOTOV V, NIKITINA E. Norilsk Nickel: Russia wrestles with an old polluter[J].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Polic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996, 38(9):6-37.
[6]萬霞.跨界損害責任制度的新發展[J].當代法學,2008(1):120-126.
[7]陳貽健.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演變及我國的應對——以后京都進程為視角[J].法商研究,2013(4):76-86.
[8]彭水軍,張文城.國際碳減排合作公平性問題研究[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09-117.
[9]BAER P, ATHANASIOU T, KARTHA S, et al. The 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 framework: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in a climate constrained world[R].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2008: 22-37.
[10]POSNER E A, WEISBACH D. Climate change justi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37.
[11]潘家華.人文發展分析的概念構架與經驗數據——以對碳排放空間的需求為例[J].中國社會科學,2002(6):15-25.
[12]陳貽健.國際氣候法律新秩序的困境與出路:基于“德班-巴黎”進程的分析[J].環球法律評論,2016(2):178-192.
[13]張曉華,祁悅.“預期的國家自主決定的貢獻”概念淺析[EB/OL].( 2014-01-10)[2016-10-10].http://www.ncsc.org.cn/article/yxcg/yjgd/201404/20 140400000846.shtml.
[14]李俊峰,張曉華,祁悅,等.利馬氣候大會主要成果及影響[J].世界環境,2015(1):22-25.
[15]GUZMAN A T.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J].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6, 34: 379-391.
[16]陳貽健.氣候正義論:氣候變化法律中的正義原理與制度構建[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225.
[17]IPCC候選主席:達成2度目標的機會在迅速消失[EB/OL].[2016-10-10].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8118--INTERVIEW-Thomas-Stocker-candidate-to-head-the-IPCC.
[18]丁仲禮,段曉男,葛全勝,等.國際溫室氣體減排方案評估及中國長期排放權討論[J].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09(12):1659-1671.
[19]丁仲禮,段曉男,葛全勝,等.2050年大氣CO2濃度控制:各國排放權計算[J].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09(8):1009-1027.
[20]陳文穎,吳宗鑫,何建坤.全球未來碳排放權“兩個趨同”的分配方法[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5(6):850-853.
2016-10-25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3FFX040)
陳貽健(1975-),男,博士,副研究員;E-mail:yijianch@163.com
1671-7031(2016)06-0033-08
D996.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