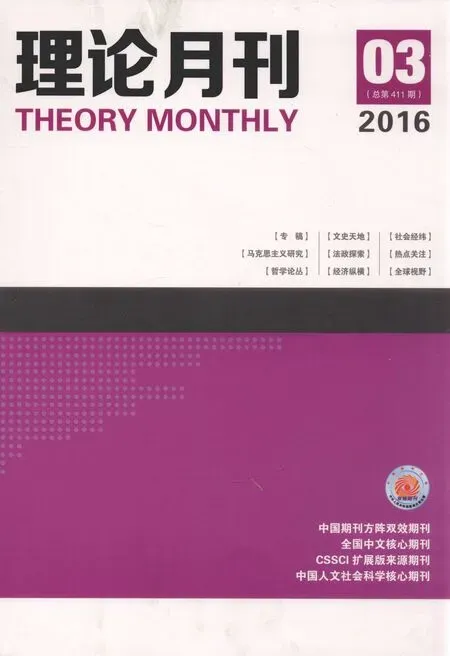論國家經濟社會權力下放地方政府的理論基礎
□葛方林
(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河南新鄉453007)
?
論國家經濟社會權力下放地方政府的理論基礎
□葛方林
(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河南新鄉453007)
[摘要]地方政府在國家政權的“金字塔”結構中處于“基石”位置,與中央政府相比,它在國家經濟社會活動中具有相應的功能定位,主要負責履行微觀經濟社會事物的管理職能。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中央政府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履行更多經濟社會管理職責。然而,這可以產生什么效果,這樣做的理論基礎以及合法性究竟是什么?作者認為,地方性公共產品理論、地方性知識理論、信息和知識的分散性理論以及制度競爭理論是國家經濟社會權力下放地方政府的理論依據。
[關鍵詞]地方政府;地方性公共產品;地方性知識;制度競爭
[DOI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14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一章提出“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1]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經濟社會管理職責。但是中央政府為什么將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這會帶來什么好處,它的理論基礎以及合法性究竟是什么?目前經濟法學界尚未對其做一個有效的回應。此外,在以往的經濟法研究中,對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中的主體——政府,并未從政府縱向層面做一類型化研究,即沒有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進行明確的區分,沒有考慮到二者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差異,而是下意識將中央政府默認為經濟法中的政府,當涉及到經濟干預活動中地方政府的問題時,往往這些理論套用到地方政府身上。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二者在國家干預經濟活動中存在著許多差異。其中,地方政府不僅要履行中央政府代理人職責,執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規,而且還要履行地方利益代表者的職責,克服局部性市場失靈所帶來的福利損失。這就造成了理論研究與現實的法治實踐的沖突,導致了經濟法理論的解釋力不足。基于此,筆者通過探討國家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理論基礎,一方面試圖闡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的理論正當性問題,另一方面為解決法治實踐中的問題提供理論支撐。本文試圖從公共產品理論、法律的“地方性知識”理論、信息學理論、制度競爭理論等幾個方面分別論述國家經濟社會權力下放地方政府的理論基礎。
1 理論基礎之一:地方性公共產品理論
按照經濟學理論,市場機制本身有其內在固有的缺陷,這種缺陷會導致市場失靈,即市場機制難以在一切領域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尤其在公共產品領域,市場機制難以有效滿足公共產品的供給。根據保羅·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對公共產品的經典定義,公共產品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集體消費品,每個人對該產品的消費不減少任何其他人的消費,從而對每個居民和各個集體消費產品而言都有個人消費等于集體消費”。[2]與私人產品相比,公共產品有兩個基本特征: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消費的非競爭性是指在公共產品任一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消費并不會增加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所產生的效用不能為某個人或某些人獨占,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從公共產品的消費過程中獲得效用。由于公共產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如果通過私人生產和市場自由交易方式提供公共產品將難以克服搭便車問題(Free-rider problem),公共產品的供給將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這不僅會導致休謨意義上的“公共的悲劇”,難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且也會由于缺乏公共福利保障而損害個人權利和自由,這些問題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自由交換方式加以解決,必須通過政府公權力的干預,由政府出面承擔供給公共產品的職能,從而克服市場缺陷,這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基本理論依據,同時也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之一。
從公共產品受益的地域范圍來看,公共產品可以分為全國性公共產品與地方性公共產品。全國性公共產品是指受益范圍為全國,能夠為全國居民所共同享有的公共產品,比如國防、中央政府的立法、郵政通訊等,這種類型的公共產品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是指受益范圍局限于地方政府管轄區域內,一般由轄區內居民共同享有的公共產品,比如城市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等,在理論上,地方性公共產品不僅可以由地方政府提供,也可以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相對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作為地方性公共產品的供給者更具有優勢,其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的效率要高于中央政府。首先,從信息的收集、傳導和反饋的角度來看,由于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民族眾多的大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風俗差異都比較很大,各地居民所需要的地方性公共產品存在著較大差別。地方政府相對于中央政府更接近其轄區內的居民,更容易獲取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信息,而且這種需求信息傳遞給地方性公共產品供給者——地方政府所經過的環節相對較少,因而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所付出的交易成本要遠遠低于中央政府;相反,如果由中央政府來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采用提供全國性公共產品這種“一刀切”的方式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這將難以滿足不同地區居民的偏好;但是如果采取“個性化”的方式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這當然可以滿足不同地區居民的偏好,但是這不僅不能發揮其作為中央政府的規模優勢,相反還要付出龐大的交易成本,這是中央政府難以承受的。誠如托克維爾所言:“一個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強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自己去了解一個大國生活的一切細節。它辦不到這一點,因為這樣的工作超過了人力所及。當它要獨力創造那么多發條并使它們發動的時候,其結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勞無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3]其次,從公共產品供給者主觀意愿來看,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的主觀愿望遠遠高于中央政府。如果地方性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來提供,中央政府將是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唯一供給者,地方性公共產品市場將會出現壟斷,而壟斷必然導致效率低下和高價。相反,如果地方性公共產品由地方政府來提供,則地方政府就不是地方性公共產品唯一的供給者,它時刻面臨著其它地區地方政府的競爭,居民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通過對比各地區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和當地稅負水平,選擇適合自己的地區,這相當于在地方性公共產品供給中引入了類似私人產品市場的競爭機制,居民作為地方性公共產品的消費者可以通過“用腳投票”選擇自己滿意的地方政府,這有效的化解了公共產品供給的低效率問題,當前我國各地區間展開的招商引資大戰生動的反映了地方性公共產品供給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誠如地方性公共產品理論的奠基者查爾斯·蒂布特在其經典論文《一個關于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中所言:“地方政府代表了一個在公共產品的配置上(作為對居民偏好的反映)不遜色于私人部門的部門”。[4]
第二,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符合自然樸素的“誰付款、誰受益”的公平原則。稅收是公共產品的對價,稅收分為中央稅和地方稅。根據美國著名財稅學家賽利格曼(R. A. Seligman)的觀點,中央與地方稅權的劃分應當注意三個原則:效率原則、適應原則和恰當原則,其中適應原則強調稅基應與統治權相適應。以稅基的廣狹為劃分標準,稅基廣闊的歸中央政府,而稅基狹窄的歸地方政府。[5]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是地方政府行使統治權的一種表現形式,地方政府相應地也被配置了地方稅權,地方政府的稅務機關向其轄區內居民征收地方稅,從而負擔地方性公共產品的開支;與此相對應,轄區內居民通過向地方政府稅務機關繳納地方稅,這相當于他們支付了所消費的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對價。地方政府與轄區內的居民通過地方性公共產品的提供與消費、地方稅的征收與繳納等行為發生了聯系,他們這種關系類似于私法上的契約關系。轄區內居民將其繳納的地方稅作為他們所消費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對價,這符合民法中公平原則。在實踐中,典型的地方稅種如:城市維護建設稅、土地增值稅、教育費附加等,居民通過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以支付地方政府提供基礎設施的對價,因為地方政府進行了基礎設施建設,居民房產周圍的環境得到了改善,他們的房產在交易過程中得到了增值,地方政府將增值部分征收土地增值稅作為其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基礎設施的對價;同樣,居民繳納教育費附加也是作為地方性公共產品——基礎教育的對價。綜上所述,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符合自然樸素的“誰付款、誰受益”公平原則。相反如果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這對那些交了稅而又沒有受益的其它地區居民而言是不公平的,不僅如此,如果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地方性公共產品配置的公平與否完全取決于中央政府的意志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這不僅可能會出現貧困地區補貼富裕地區、全國人民補貼首都的怪像,而且還會出現托克維爾筆下所描述的“全法國只有一個城市,那就是龐大無比、高高在上的巴黎”現象。誠如亞當·斯密所言:“一項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維持,而其便利又只限于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區域,那么,把它放在國家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國家一般收入維持,總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維持,來得妥當。”[6]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從效率方面考慮還是從公平方面考慮,相對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組織地方性公共產品更具有優勢,這也是地方政府所存在的正當性。因此,在國家干預經濟社會活動中,中央政府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配置給地方政府,由其出面組織地方性公共產品的供給,以克服因公共產品問題而導致的市場缺陷,從而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
2 基礎之二:“地方性知識”理論
美國學者克利福德·吉爾茲提出的“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概念不僅是一種知識形態,而且是一種方法論意義上的知識觀念。地方性知識一方面是指任何具有地方性特征的知識,是與“普遍性知識”相對的一種知識形態,另一方面它強調知識形成的多元化,克利福德·吉爾茲認為:“事務的發展趨異而非趨同”。[7]他的觀點對西方世界主導下傳統一元論的知識觀和科學觀產生了的解構和顛覆的作用,是對近代工業化以來長期主導西方世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觀的一種反思,對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反叛。他認為西方知識體系并不具有普遍的合法性,相反,“由于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對其所處世界的不同理解的產物,文化的各種符號之間的關系取決于該文化中行為者的行為組織方式”,[8]應當承認知識的多元性和差異性,世界發展是由遍布世界的大量地方性知識所推動。同時,克利福德·吉爾茲還將“地方性知識”理論引入法律領域,他認為:“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識。”[9]法律的調整對象是社會關系,是對社會關系確認、抽象和概括的產物,其產生和發展依賴于特定的社會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誠如美國學者布拉萊姆所說:“隱藏在法律理論和法律實踐中的是一系列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不斷重現或‘地方志’。用同一種方式來說,法律以各種形式依賴一系列負載的地方志和區域理解。”[10]
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理論對中國經濟法實踐和理論研究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它是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中國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不平衡的大國,這對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帶來了很大挑戰,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經濟法的統一性與地方性之間的平衡。例如,在當代中國城鄉差距非常大,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之時,面臨著一個實現公共產品供給均等化與城鄉間需求差別平衡的難題。我國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接近第一世界國家水平,西部地區還停留在第三世界國家水平,中央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之時,面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難題。從我國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并存。[11]經濟法是現代性法律,它產生于現代性社會之中,經濟法中的大部分制度是依據現代工業社會基本特點而制定的,而我國許多地區還處于鄉土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前現代社會階段。如何使經濟法在一個由不同文明構成的統一國家之中得到實現,是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如果將經濟法放到一個更宏大的視野下來考察,對破解經濟法統一性與地方性沖突的難題具有一定啟發意義。經濟法是由國家經過正式的立法程序而制定的正式制度,但它只是所有規范國家干預經濟制度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非正式制度,誠如道格拉斯·諾斯所言:“正式規則,即便是在那些最發達的經濟中,也只是型塑選擇的約束的很少一部分。只要略加思索,我們就會發現非正式約束的普遍存在。在我們與他人的日常互動中,不論是在家庭內部,還是在外部的社會交往中,還是在事業的活動中,支配結構的絕大部分是由行事準則、行為規范以及慣例來界定的。”[12]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經濟社會之中的地方性知識,經濟法的實施非常依賴這些地方性知識,經濟法必須能夠與之相契合,才能使經濟法制度得到實現。借用英國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提出的“嵌入”概念,“經濟并非像經濟理論中說的那樣是自足的,而是從屬于政治、宗教和社會關系的。”[13]透過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我們可以發現非正式制度或者說地方性知識。經濟法同樣也是不自足的,它必須嵌入在一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系之中,與非正式制度或者說地方性知識相契合才能得到實現。
在中國經濟法實踐中,經濟法制定和實施既要考慮法律的統一性,也要考慮各個地方的特殊性,作為正式制度的經濟法必須與地方性知識中的非正式制度相契合,這就為我國地方政府干預經濟奠定了智識基礎。比如,地方政府在實施中央政府制定的經濟法過程中,它會從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去理解經濟法精神和規范,它或者會結合本地區實際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或者直接依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實施經濟法,因而,地方政府實施經濟法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就充滿了地方性知識。此外,地方政府針對本地區特有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所制定的經濟法規范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地方性知識的法律。由于每個地區具有一定特殊性,因此,中央政府將相應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承擔相應的經濟社會職責。例如,在我國西北地區,當地信奉伊斯蘭教的居民非常多,由于清真食品問題在全國范圍內不是一個普遍性問題,具有地方特色,難以由國家統一立法加以解決,因此,西北各省針對當地的特殊情況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的地方性法規,由該地區的地方政府承擔清真食品管理的職責。比如《青海省清真食品生產經營管理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清真食品管理條例》、《寧夏回族自治區清真食品管理條例》等,這些針對清真食品問題而制定的食品安全法規顯然是一種地方性知識。
通過上面的分析,筆者認為,在強調經濟法的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前提下,無論從本體論層面還是從方法論層面,我們都必須正視經濟法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從本體論層面來看,經濟法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意味著地方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活動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從方法論層面來看,經濟法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我們要求不僅要重視中央政府在經濟法制度中的“建構”作用,更應該重視如何去發現制度,這就要求必須正視地方政府在國家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功能定位問題。中央政府正是在認識到法律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這一特殊規律,將相應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使其承擔相應的經濟社會職責。
3 理論基礎之三:信息和知識的分散性理論
人不是神,很難做到先知先覺。人們實施的任何理性行為必須要有相應的知識和信息與之相匹配,可以說信息和知識是人類做出理性決策的基礎,充分的信息和科學的知識推動了人類行為的理性化,政府實施的經濟干預行為也同樣如此,它所做出的決策以及對決策的執行需要建立在充分市場信息之上,可以說信息的充分與否直接關系到干預效果的好壞。但是,信息和知識從來都是分散存在的,社會中存在的所有信息和知識不可能集中于某個人或者某個組織之中。誠如哈耶克所言:“我們必須運用的有關各種環境的知識,從來就不是以一種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僅僅是作為所有彼此獨立的個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識而存在的。”[14]
中國的大國特征決定了它內部的信息和知識的超級分散性。中國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大國,遼闊的的國土、巨大的地域差別、龐雜的社會結構和經濟活動導致了知識和信息的極度分散性,這就意味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個人都難以獲得所有的信息和知識,但是決策理性化并不強求決策者能夠掌握所有的信息和知識,僅僅要求決策者掌握與其決策權力相匹配的信息和知識。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所考慮的問題主要是如何贏得市場競爭并在市場交易中獲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它們只要掌握與市場競爭和市場交易有關的微觀信息和知識就可以做出理性的市場決策,這對于市場主體而言并不是什么難題,因為這些用于市場決策的信息和知識符合它自身的分散性特征。相反,政府在獲取市場信息和知識的過程中則會遇到許多困難,它不僅需要與經濟干預決策有關的宏觀性市場信息和知識,而且還需要與實施經濟干預決策有關的微觀性市場信息和知識,這就產生了兩個難題。首先,宏觀性的市場信息和知識并不存在,它需要政府對微觀的市場信息和知識進行加工,當然這種加工并不是簡單相加,而是一種重新整合。誠如哈耶克所言:“知識只作為個人的知識而存在。‘作為整體的社會知識的’說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比喻。所有的個人知識的總和也不能構成一個整體。主要問題在于我們如何才能利用以分散、局部、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的見解的形式存在著的知識。”[15]其次,政府實施經濟干預決策所需要的各種微觀市場信息和知識,散布于結構復雜數量龐大的市場主體之中,由中央政府獨自去面對數量如此龐大微觀市場信息和知識,完成對微觀市場信息和知識進行搜集、加工和整合的任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從時間和資源的角度來看,獲取信息和分析新知識都是代價高昂的。因此無人愿意獲取復雜所需的全部知識。相反,人們更愿意通過自己與他人的交往,設法利用他人的知識。[16]
地方政府處于中央政府與微觀市場主體之間,它的獨特的位置有助于中央政府完成對微觀市場信息和知識的搜集、加工和整合。首先,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在地域上更貼近民眾,更接近市場,更容易獲得第一手的市場信息。尤其是基層地方政府,它是中央政府經濟干預決策的末端,與干預對象——市場主體直接相連接,它可以非常廉價地獲得原始的微觀市場信息,一方面輸送給中央政府用于經濟干預決策,另一面可以直接用于執行中央政府的經濟干預決策。中國作為一個社會經濟發育不平衡的大國,地區之間的差別比較大,許多地區尚處于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前現代性社會階段。理性官僚制政府是工業社會中標準的政府治理模式,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非個性化或者說標準化,符合現代工業社會對政府經濟干預理性化的要求。但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之外,中國還存在著許多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前現代性社會地區,這些地區難以被中央政府理性的經濟干預所涵蓋,也就是說如果中央政府統一的經濟法規范作用于這些地區,則可能表現為非理性。地方政府則可以彌補中央政府理性所不能達到的地方,它從這些前現代性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搜集相關市場信息并加以加工整合,從而用于做出經濟干預決策。其次,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存在著數量優勢,中央政府只有一個,而地方政府則層級眾多數量龐大,尤其是基層地方政府數量非常龐大,它們可以搜集散布于全國各地的各種微觀市場信息,然后輸送給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加以整合,并作為經濟干預決策的依據。基于信息與知識的分散性原因,為了更好的實現國家的經濟社會職能,《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其承擔更多的經濟社會職責。
此外,知識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產物,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發展,因此人類通過社會實踐所獲得知識具有可證偽性。知識的可證偽性導致了人們行為的有限性理性,人們所作出的任何行為只有在一定場景下才是理性的,并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需要不斷進行修正,它永遠都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否則人的行為就會滑入非理性泥潭之中。政府的行為也同樣如此,政府所做出的任何經濟干預行為只有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才具有合理性,超出一定的時空范圍則變為非理性的行為,政府的經濟干預行為需要不斷的進行試錯以適應時空范圍的轉換。在中國經濟法視野下,政府面對著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極度不均衡的大國,由于知識和信息具有分散性的天然特性,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很少出現整體性突變,一般都是從局部發生變化,也就是說中央政府在經濟社會制度的變革過程很少進行整體的建構,而是通過地方試點,由地方政府進行制度創新試驗,通過地方政府的不斷試錯,然后由中央政府總結經驗,最后對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成果進行整合。因此,中央政府,常常將某些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某一地方政府,授權其進行制度創新試驗。事實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一直被視為政策實驗室,許多經濟社會制度的產生和變革最早都源自于地方政府。例如,我國當前的經濟自貿區的目的就是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進行經濟制度創新試驗。
通過上面的分析,筆者認為,信息和知識的分散性決定了國家必須承認地方政府在經濟干預活動中相應的功能定位,賦予地方政府以相應的經濟社會權力,這樣不僅可以提高國家管理經濟社會活動的效率,而且可以實現實質法治;否則,國家不僅不能實現克服市場失靈的目的,而且還會導致政府失靈——政府干預經濟的效率低下,以至于惡化到市場失靈。基于此,理論上由地方政府行使更為合適的經濟社會權力,中央政府將其授予地方政府,因此,《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使其承擔更多的經濟社會職責。
4 理論基礎之四:制度競爭理論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古今中外政府之間的相互競爭一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中國的先秦時期,無論“尊王攘夷”的春秋五霸時期,還是在實現大一統戰國七雄時期,戰爭始終是當時國家生活的主題,而戰爭恰恰是政府競爭最激烈的表現形式;在近現代的西方世界也同樣如此,自大航海時代開啟以來,各個國家圍繞著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無論是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還是后來的法蘭西與不列顛,以及二十世紀的美國與蘇聯,隨著實力的此消彼長,霸主地位在它們之間不斷轉換,盡管美國最終獲得了冷戰的勝利,取得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這被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但是歷史不會終結,競爭還在繼續。透過歷史的迷霧,需要發現國家競爭背后到底是什么。如果將歷史的鏡頭拉長,我們可以發現國家間的競爭最終可以歸結于制度的競爭。
在傳統的法學和政治學理論中,每個法域中的政府都是一個壟斷性和強制性的組織,法律制度作為政府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每個法域中的居民只能被強制去消費這些公共產品即被動的服從法律,而不能有選擇的去消費這些公共產品,遵守對自己有利的法律。然而經驗告訴我們事實并非如此,隨著交通、通訊等技術的進步,以及阻礙資本、貿易和人員自由流動的法律障礙逐漸被破除,在法律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制度市場”,不同法域之間的制度競爭逐漸凸顯。在這個“制度市場”之中,政府是法律制度產品的供給者,居民則是“制度市場”中消費者,居民可以像在菜市場買菜一樣選擇適合自己口味兒的法律制度,例如,企業可以選擇稅負低,公共服務好,勞工、資本和環境管制比較少的地區進行投資;勞動者可以選擇勞工保護標準比較高社會保障比較好的地區進行打工;消費者可以選擇購買不同地區所生產的商品,因為不同地區生產的商品受制于不同的產品質量法規。而政府作為提供法律制度的廠商隨時面臨著其他政府的競爭,它只能盡心盡力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否則作為法律制度的消費者可以通過“用腳投票”和“用貨幣投票”方式選擇其他政府所提供的法律制度。居民不僅具有法律制度消費者的身份,同時也具有納稅人的身份,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令居民滿意的法律制度,它就會面臨著資本和勞工流失、居民外遷以及本地產品銷路不暢的局面,這樣政府就會失去財政收入來源,最終政府機構也無法正常運轉。
制度競爭不僅存在于不同法域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同一個法域之內,因為在統一的法域內還存在著許多“亞法域”,①這是因為,一方面各個地區不僅都有自己地方性法規,而且還存在著各自的習慣、倫理規范、商業習俗等內在制度,俗話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就是這個道理;另一方面每個地區的法律實踐存在著一定差別,因而它們所形成的法律秩序也存在著差異,這樣各地事實上已經形成眾多的相對獨立的“小法域”,由于它們隸屬于主權國家這個大法域,因而我們稱之為“亞法域”。“亞法域”的存在是由法律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所決定的,“亞法域”之間也同樣存在競爭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就是一種“亞法域”意義上的制度競爭。地方政府為了使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率、財政收入以及就業率高于其他地區,通過對經濟的積極干預,一方面提高本地區要素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吸引其他地區的要素。從公共產品理論來講,地方政府的經濟干預行為其實就是對經濟干預對象——市場主體主動提供一系列制度產品,作為競爭對手的其它地區的地方政府同樣也會通過對經濟的積極干預而向市場主體主動提供一系列制度產品,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制度市場,作為制度產品的消費者——企業或者說市場主體可以在制度市場中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制度產品,作為制度產品供給者的地方政府為了獲得市場主體的青睞,即能夠有效的吸引外部資本,它必須通過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將各種高效率的制度產品供給給市場主體。例如,地方政府利用其立法權和執法權,向市場主體提供符合其偏好的經濟法制度,這樣既可以吸引外來投資,同時又提高了本地區企業的競爭力。地方政府利用其稅收執法權通過降低稅率減免企業稅負,通過財政補貼的形式降低企業實質稅負,向企業提供實際稅負更低財稅法律制度,以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通過建設工業園區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以降低企業運行成本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通過廢除或修改各種政府許可和審批制度提供更加自由的法律制度,通過激活市場競爭,從而促使企業主動改進經營效率;通過降低勞動法規和環境法規的執法力度,向企業提供實際用工成本和環境成本更低的法律制度,以降低企業產品的成本,從而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當然,地方政府間的制度競爭不僅是紙面意義上的制度競爭,即法律政策條文的競爭,而且更重要意義上的是法治秩序間的競爭,即“將紙面上的法律轉換為行動中法律”的競爭,抑或是說如何更有效率的實現立法目標。這就要求地方政府改善政府自身的治理水平提高法律實施的效率,從而能夠更有效的實現立法目標。地方政府所積極推動的行政體制改革,其目的就是為了改善政府治理水平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地方政府推行的“大部制”改革、“省管縣”體制、“電子政務”、“建設服務性政府”等,通過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結構和執法能力,從而能更有效的實現立法目標。在制度競爭環境下,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動力提高其法律實施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經濟社會管理職責,從而使相互競爭的地方政府更有效率地實現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目標。
筆者通過制度競爭理論分析,發現國家之所以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其目的就是,一方面在競爭效應的推動下,刺激地方政府積極進行制度創新,破除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另一方面,改善政府的治理水平,提供地方政府法律實施的效率,從而使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目標得到更有效的實現。
5 結語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更多的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與其說是對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重新界定,不如說對經濟、社會和行政管理規律的再認識。地方性公共產品理論不僅論證了經濟社會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必要性,而且闡述了地方政府存在的正當性;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知識”理論在承認了法律的普遍性和統一性的前提下,承認了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地方特殊性,因而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經濟社會權力具有正當性;信息和知識的分散性理論說明了國家基于效率的考慮將經濟社會權力下放地方政府的必要性;制度競爭理論闡述了地方政府在國家經濟社會活動中的能動性,因而,將經濟社會權力下放各地方政府具有合理性。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Z].新華社北京2013年11月15日電.
[2]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6, No.4.(Nov.,1954), P387.
[3]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100—101.
[4]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64, No. 5.(Oct.,1956), P424.
[5]張守文.稅法原理(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70.
[6]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292.
[7][9]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事實與法律的比較透視[A].鄧正來譯.梁治平主編.法律的文化解釋[M].北京:三聯書店,1998.127,126.
[8]克利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M].王海龍,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37.
[10]Nicholas Blomley: Law,Space,and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1994.p. xi.
[11]李永成.經濟法人本主義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0.
[12]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績效與經濟績效[M].杭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0—51.
[13]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M].馮剛,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
[14]F·A·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M].鄧正來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117.
[15]F·A·哈耶克.自由憲章[M].楊玉生,馮興元,陳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47.
[16]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5.
責任編輯趙繼棠
作者簡介:葛方林(1982—),男,河南新鄉人,法學博士,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基金項目:中國法學會2015年度部級法學研究課題(CLS2015D089);河南師范大學博士啟動課題資助項目(qd14102)。
[中圖分類號]D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6)03-00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