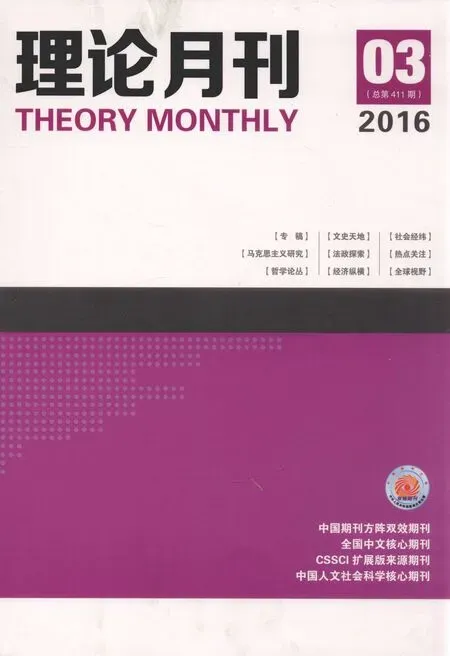梭羅與萊易斯生態幸福觀的比較及啟示
□林麗婷,徐朝旭
(廈門大學哲學系,福建廈門361005)
?
梭羅與萊易斯生態幸福觀的比較及啟示
□林麗婷,徐朝旭
(廈門大學哲學系,福建廈門361005)
[摘要]梭羅作為生態主義的先驅,他從自然的角度出發,提出一種生態主義的生態幸福觀,而萊易斯作為生態社會主義中期的代表人物,他從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提出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幸福觀。盡管他們相隔一個多世紀,但兩者的生態幸福觀共同構成了當代社會幸福觀發展的新方向。并且,他們的生態幸福觀在有關消費與幸福、自然與幸福及社會制度與幸福的論述上表現出一致性和差異性,這對推動當今世界的生態幸福研究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梭羅;萊易斯;生態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幸福
[DOI編號]10.14180/j.cnki.1004-0544.2016.03.009
作為浪漫主義代表人物及生態主義的先驅,梭羅在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之前,就開始反思工業時期的各種幸福觀的弊端,關注人的生存狀態,主動選擇“回歸自然”,體驗“與獸為鄰”的幸福生活,這種從自然的角度出發的生態幸福觀,是一種生態主義的生態幸福觀,它改變了美國人對原有工業幸福觀念的看法。萊易斯作為生態社會主義中期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態幸福觀是將馬克思主義幸福觀與當代的新環境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倡導“不放棄人類尺度”基礎上的“控制自然”的生態幸福觀,是生態社會主義的生態幸福觀的典型。盡管梭羅和萊易斯相隔一個多世紀,但兩者代表的兩種不同形態的生態幸福觀共同構成了當代社會幸福觀發展的新方向。他們的生態幸福觀在有關消費與幸福、自然與幸福及社會制度與幸福關聯的闡述上,既有契合之處,又有著各自的獨特性,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 消費與幸福
相比工業時代所推崇的一種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和物質極大豐富的幸福觀,梭羅和萊易斯都指出這樣一種幸福模式是不可持續性的,因為它將感官享受等同于幸福,是一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在生態時代,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才是幸福的?這引起了梭羅和萊易斯的極大關注。他們各自提出了一種生態生活方式,但其具體樣態有所不同。具體闡述如下:
在所有的自然主義者中,梭羅是為數不多的,通過大篇幅的生態性消費方式來闡述其幸福思想的作家之一。他從生態經濟的角度描述了一種物質需求極少的幸福生活方式。在他看來,人類的必需品是很少的,大致可分為:食物、住宅、衣服和燃料。就衣服而言,梭羅認為,衣服只要能保持身體的體溫和方便我們在社會中把赤身露體遮蔽起來就足夠了,而現代人卻常常把穿衣服的目的搞混了。人們采購衣服時,常常受市場廣告和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導,把衣服看作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最終成為衣架子。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人們關心的并不是真正應該敬重的東西,只是關心那些受人尊敬的東西。”[1](P19)他們過多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很少征求自己內心的真實需求,這樣一種消費需求,不僅沒能體驗穿上合身衣服的愉悅,到頭來買衣服的新奇感也會被市場及大眾的意見所消磨殆盡。事實上,在梭羅看來,衣服是和我們的性格是同化的,充滿了我們的性格印記,盲目追求時尚只會造成異化的消費和異化的人的幸福。因此,現代人不幸福不是因為他們缺少生活必需品,而在于缺少奢侈品。然而,“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謂生活的舒適,非但沒有必要,而且對人類進步大有妨礙。”[2](P12)這就是梭羅對好的生活方式的生態幸福觀的注解。
正如現代人為了能夠生活舒適而尋求更大更光耀的房屋,寧愿花費他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那部分時間來掙錢,只是為了在最不寶貴的一部分時間里享受一點可疑的自由。這在梭羅看來是不值得的,因為即便他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房屋,他也沒有因此生活舒適,倒是更加窮困了,房屋徹底占有了他。因此,梭羅認為,有些事物只適合欣賞,而不適合占有。占有等于禁錮。“這種人看來闊綽,實際卻是所有階層中最貧困得可怕的,他們固然已積蓄了一些閑錢,卻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擺脫它,因此他們給自己鑄造了一幅金銀的鐐銬。”[3](P14)相反,他舉例說原始人因為沒有過多的欲望,反倒生活安逸,赤身露體,充當大自然之中的一個過客。他們待吃飽睡暖,神清氣爽再考慮他們一天的行程,不像文明人一醒來就被房屋包圍著。這也就是梭羅對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幸福困境的擔憂。他說:“當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時候,它卻沒有同時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4](P30)現代文明提高了人的物質財富占有,卻沒有改善人的思想文化,甚至還在倒退。這和后來的羅馬俱樂部所說的:“當人類顯然還在前進的時候,它現在實際上正在退卻,正在進入一個不說是生存上也至少是文化、精神和道德上的衰退階段——因此,人類原來的差距正逐步發展成為鴻溝。”[5](P7)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梭羅在資本主義還在迅速發展,人們還沉浸在大工業所帶來的福祉之際,就超前覺察到人類將不斷被無止境的物質需求消耗掉幸福的危險,從而倡導一種極簡的生活方式。
概而言之,在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好這一問題上,梭羅認為有必要減少個體對外部物質的需求,反對將物質消費與人的幸福指數劃等號。而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萊易斯和梭羅一樣,堅持一種綠色的消費方式。萊易斯指出,在現代工業社會,人們誤以為不斷增長的消費可以彌補其在其他生活領域、特別是勞動領域中遭到的挫折,從而通過各種瘋狂的物質消費來宣泄心中的不滿,只根據消費的多少來衡量自己的幸福程度。這一衡量標準把消費與幸福等同起來,而忽視了人的那些最關鍵和最基礎的需要。這在萊易斯看來,正是當代幸福異化的表征。
不僅如此,正如本·阿格爾所說:“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6](P486)資本主義的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導致了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生態問題的日益嚴重,生態問題成為人們滿足和幸福的極限。面對這一幸福困境,萊易斯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他用“生態危機”理論補充馬克思主義幸福論,拓寬了當代社會的幸福視域。萊易斯指出,迫于生態生存壓力,人們需要在縮減自己的物質消費需求的同時,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方式,改變那種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廣告操縱的消費觀念。也就是說,萊易斯認為在充分肯定工業文明所獲取的巨大物質成就后,人類需要超越物質層面的需求,在精神上繼續生活的目的和意義。這種新的需求結構,包括當前生活條件、生活方式及生產方式的改變,培養文明人逐步從量的消費(多少商品)轉向質的消費,如更好的文化、藝術、精神的享受和實現來確定幸福,這也是未來社會進步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事情。
概而言之,梭羅和萊易斯的幸福觀要求改變以往過度消費的生活方式,從而著眼于一種“否定性的需求理論”來尋求新時代的幸福理念,這正是他們在消費與幸福關聯問題上的共同點。但在如何改變生活和消費方式上,二者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樣的。梭羅主張放棄一切不必要的物質追求,通過最簡單的方式縮減自己的物質消費來謀生,過一種近乎禁欲主義式的生活來實現他的幸福理想。如:他在自己屋邊的沙地上種了些作物,包括蠶豆、土豆、玉米等,用這種簡單而自然的方式掙錢補償建造房屋的額外開支。當然,收成主要是用于讓自己能夠食用自己的糧食來過一種簡單而獨立的生活,體驗自由勞動的快樂和滿足。梭羅認為,“我的生活方式至少有這個好處,勝過那些不得不跑到外面去找娛樂、進社交界或上戲院的人,因為我的生活本身便是娛樂,而且它永遠新奇。”[7](P104)
相反,萊易斯認為人的生活情趣應該重視一定程度的物質幸福生活,這較之梭羅幾近禁欲主義的幸福主義要更容易被現代人所接受。不僅如此,萊易斯還主張人類未來的社會進步的前景還取決于能夠在消費之外的其他活動領域中,主要是生產活動領域中確立人的滿足和幸福感,這一點他比梭羅思考得更遠。可見,萊易斯的生態幸福觀蘊含著對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的雙重要求。他認為,除了要求個人層面的控制消費外,還倡導從國家層面有計劃地縮減工業生產,最終形成一種消費者能夠告訴生產者“生產多少就足夠”的一種生態生產,即“滿足的可能性將主要是生產活動的組織功能,而不像今天的社會那樣主要是消費活動的功能。”[8](P106)這就是二者的生態幸福觀在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上的異同點。
2 自然與幸福
在“自然與幸福”的關系問題上,較之傳統幸福觀用一種人與自然對立的“二元論”來看待人的幸福不同,梭羅和萊易斯一致強調用一種生態化思維來對待人的幸福與自然的關系,即自然觀念的轉變是當今生態幸福觀的必然要求。
作為自然主義和超驗主義的代表,梭羅認為萬物皆有靈,自然是有神性的,是有生命且充滿人性的。自然和人類沒什么不同,可以共鳴。在《瓦爾登湖》中,梭羅指出,螞蟻的廝斗就像人類之間的戰爭,而鳥雀的歌唱、牛的樂聲等,則是不花錢的音樂,所有這些自然景象都在日常的時間里給梭羅增添了許多樂趣。梭羅認為,自然不僅是人類存在的基礎,更是人類精神的泉源,自然和人類的精神是互通的。因此,他說自然是精神的象征,對大自然一草一木、一石一鳥的觀察和體驗皆能使人學到很多東西,包括幸福所需的品格。如大山的寬厚、謙恭以及水的慷慨等品格,都是人類值得學習和模仿的品質,這就是大自然的道德教化功能。不僅如此,大自然還可以給人提供幸福的啟示,人應該到自然界中去尋找樂趣和幸福靈感。在梭羅看來,大自然的精神價值就是大自然改變人的價值觀和幸福觀的價值。概而言之,梭羅站在浪漫主義的立場上,親身實踐“回歸自然”的浪漫,喚醒被工業文明社會所遺忘的一個基本幸福信念,即強調自然的整體性和活力,過一種尊重宇宙法則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同樣,在如何對待自然的觀念上,萊易斯非常重視人類生態生存壓力對幸福的影響。他指出,傳統科技發展和商品生產給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影響了社會進步及人的幸福發展,他認為生態幸福觀具有一定的生態限度。他說:“工業生產和人口的無情增長已使人們把(對穩態經濟的)關注中心由審美的教育轉向生態生存。”[9](P485)可見,當代社會,生態生存壓力比消費經濟更加緊迫,人的幸福觀要和人的精神自由和生態狀況密切關聯。
綜上所述,梭羅和萊易斯都把自然當作一個“社會的范疇”,強調自然及生態生存對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意義,但另一方面,梭羅論述的是具體自然與幸福的密切關聯性,而萊易斯則著眼于對抽象自然的社會幸福意義的論述。也就是說,在自然以何種方式對人的幸福產生功用這一問題上,梭羅和萊易斯的差異是明顯的。梭羅倡導一種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幸福生活,而萊易斯則強調生態幸福取決于人類對待自然的觀念、態度和行為。
可以說,梭羅和萊易斯的生態幸福觀在自然觀念上的差異與他們幸福的價值觀基礎相反有關,具體表現為“與獸為鄰”與“控制自然”的不同主張。梭羅的生態幸福觀以生態主義為價值基礎,追求一種“與獸為鄰”的浪漫主義情懷,涉及一種人與自然的親密交往。梭羅認為,他的本性并非隱士,他和大多數人一樣喜愛交際,任何血氣旺盛的人來時,他都會象吸血的水蛭似的,緊緊吸收他不放。但是,他仍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心靈隔閡常常要比人與自然間的交流復雜得多,有時候人與自然反倒更容易交“朋友”,他把麝鼠當作兄弟,把康科德的植物視為和他一起居住的“居民”,這也是梭羅更愿意沉浸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把自然當作自己的同類和朋友,刻意去掉很多不必要的人際交往的原因。他說:“我更愿意將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棲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會的一分子。”[10](P205)“作為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我獲得了一種奇怪的自由感。”[11](P27)可見,通過與自然的親密往來,梭羅已經完全融入到大自然,成為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的交往不僅沒有使梭羅的生命縮減了時間,反而給他增添了很多健康和歡樂。自然因其自身的內在價值而成為人類幸福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生態主義者梭羅一樣,生態社會主義者也意識到自然對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意義。正如康芒納所說:“為了在地球上幸存下來,人類要求一個穩定的、持續存在的、相宜的環境。”[12](P11)在生態社會主義者看來,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之根。但是,和梭羅倡導的“與獸為鄰”,贊頌本真自然不同,萊易斯倡導通過“控制自然”來保護自然,以此論述自然與幸福生活間的密切關聯。可見,萊易斯基于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立場,提出一種有益于自然的“弱”人類中心主義的幸福觀,這得到后來的生態社會主義者佩珀的支持,佩珀說:“人類不可能不是人類中心論的,人類只能從人類意識的視角去觀察自然。”[13](P41)
萊易斯對“控制自然”的觀念進行歷史分析,他認為,在近代以前,“控制自然”是一種創造性的和積極的觀念,從《圣經》中上帝對自然的控制權派生出來的人類對自然的絕對權威,有助于幫助人們消除對自然的恐懼,鼓勵人們不對生活失去信心,相信人可以改變人的生存的物質條件,獲得一種生存幸福。但自近代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試圖用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自然控制”進行解釋以來,人類社會就開啟了一個新的控制自然的時代,控制自然的觀念日益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東西。此后,“控制自然的觀念總是以普遍的名義把控制自然說成是人類普遍的任務,宣稱它會對整個人類而不是對某個特殊集團帶來利益,‘解除人的處境的困難’是其基本目標。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不相信這種關于普遍性的說教了。”[14](P153-154)也就是說,近代以來,“控制自然”觀念的消極作用日漸顯現,“人類幸福的目標與科學的目標被認為是一致的”,[15](P70)即加強對自然的控制。
的確,從表面看,“控制自然”的概念與生態幸福追求格格不入。那么,要獲得人類的幸福,是否就應該徹底拋棄“控制自然”的觀念而堅持一種“解放自然”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念?萊易斯認為,這實際上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同樣不可取,關鍵在于要對這一觀念加以重新解釋,賦予新的時代蘊含,即把控制自然理解為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他說,“控制自然的觀念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重新解釋,即它的主旨在于倫理的或道德的發展,而不是科學和技術的革新。從這個角度來看,控制自然中的進步將同時是解放自然中的進步”。[16](P168)在萊易斯看來,人控制自然是為了保護自然,并透過保護環境來保護人類自己及維護人類的幸福,自然具有工具價值。并且,萊易斯認為,如果“控制自然”不能給人類帶來幸福而是災難,那么就不能稱為對自然的真正控制。這一點同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的格倫德曼也說過:“一個社會如果沒有考慮到被改造過的自然對社會的反作用,就不能說它完全控制住了自然。”[17](P60)可見,生態危機的出現恰恰是人類缺乏對自然進行合理控制的結果。因此,萊易斯倡導一種科學的“控制自然”觀念,這一觀念意味著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意味著穿透自然現象的帷幕,揭示自然的內在結構和規律,按自然規律生活和生產。也就是說,控制自然的欲望越強烈,自我克制就越自覺,人也就越容易獲得幸福。這正是萊易斯“控制自然”的生態幸福思想。
從自然觀念的轉變來看梭羅和萊易斯的生態幸福觀,梭羅的生態幸福觀具有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情結”,他認為保護自然與追求人類幸福二者都是目的,二者共存共榮。而萊易斯的生態幸福觀的自然觀則堅持“人的尺度”上的“控制自然”,二者區別明顯。
3 社會制度與幸福
作為美國激進的個人主義先驅,梭羅認為人的幸福與否與社會制度關聯不大,他倡導一種個體可以自由選擇其幸福模式的生態幸福觀,極力反對那種千篇一律的生態幸福模式,在他看來,人的幸福可以是創造性的和多樣性的,但唯一的一點要求就是這種幸福觀要有其生態界限。因為即便是他在瓦爾登湖所度過的兩年離群索居的生活,也只能說是他個人“生態烏托邦”幸福生活的理想模式,或者說他特意選擇在1845 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那天進入瓦爾登湖,是表達對社會不滿的手段,但他卻不是要別人效仿他的這一生活。他說:“我卻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也許他還沒學會我的這一種,說不定我已經找到了另一種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個人都能謹慎地找出并堅持他自己的合適方式,而不要采用他父親的,或母親的,或鄰居的方式。”[18](P64-65)在他看來,人的性格不同,對幸福的理解和需要也會很不相同,人的幸福與個性有關,關鍵在于引導人們自由選擇一種符合“生態”的生活,這就是他的激進個人主義觀點在幸福的社會理想上的表達。
同樣,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的萊易斯也認為,以往以瘋狂的物質需求和消費活動的滿足為幸福標志的幸福模式是單一的,是有缺陷的,他認為當今時代的幸福應該是多樣的。在他看來,人有各種能力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說,人們與生俱有康復、種植、縫紉、運動、學習、建筑、安葬的能力,每一種這樣的能力都可以滿足一種需要。只要滿足的手段取決于人們本身能作的事情,很少依賴于商品,那么這種手段就會變得十分豐富。這些活動具有使用價值,而不具有交換價值。交往社會將促使每個人盡可能地直接參與生產活動。[19](P178)他認為,人在縮減自己物質需求的同時,還要盡量創造出滿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使各個個人在自由和自足的條件下決定和滿足自己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就可能在日常生活及生產活動中獲得滿足,而不是完全依賴于市場消費。這樣,他認為人的幸福模式是可以多樣的,并且這種通過自主的勞動來直接獲得滿足是“生態”的,可見,他和梭羅一樣,追求一種多樣性的生態幸福觀。這就是他們生態幸福觀在社會理想上所表現出的一致性。
盡管梭羅和萊易斯都倡導一種多樣性的生態幸福觀,但他們在社會制度與生態幸福的關聯性問題上卻有不同的看法。梭羅作為激進的個人主義者,他并不把人的幸福寄情于何種社會制度,而是單純地向往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主張建立一種“生態烏托邦”社會。而在萊易斯看來,人的生態幸福與堅持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是分不開的,主張建立一種“較易于生存的社會”。
梭羅說:“我誠心誠意地接受這句座右銘,‘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我愿將這句話改為‘最好的政府是什么也不管的政府’。”[20](P85)可見,他所期待的“最好的政府”正是一個不獨裁專政、給個人充分自由的、為人類謀福利的政府。正是他的無政府主義立場,他曾經公然反抗美國對墨西哥的侵略戰爭,幫助流亡的黑奴逃到加拿大去(他是個堅定的廢奴主義者),還因不肯交在他看來不合理的賦稅而被捕入獄,他通過行動表達其對社會的不滿。因此,當他看到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的幸福被物質主義及消費主義等觀念主宰而找不到自我時,他選擇直接遠離喧囂的社會,通過贊頌自然和過一種簡樸的生活來表達對現實的反抗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梭羅亦師亦友的愛默生曾經說過:“這個時期的特點看來是思想的自我覺醒,人變得富于反思和心智發達,產生了一種新的意識。祖輩們都是在這樣的信念下行動的:社會的輝煌繁榮是所有人的幸福,故而一貫為國家犧牲公民”。[21](P494)可見,在這樣一種社會中,常常存在社會對個人幸福選擇的壓制,這對梭羅來說,是致命的打擊。因此,他提出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態幸福理想。值得留意的是,梭羅的個人主義的生態幸福理想是其幸福思想在社會領域的表達,并不同于經濟領域亞當·斯密等人所倡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更不是一種利己主義或唯我主義。正如有學者指出:“英語中最早出現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意指平等主義哲學。有人推測,大約在1835年,愛默生(R·W·Emerson)第一次使用了individualism這個詞。”[22]也就是說,在愛默生和梭羅的時代,他們主要賦予社會領域的“個人主義”以積極含義,此時的個人主義幸福觀意指平等主義幸福觀,強調個人的幸福權利及自然的幸福權利,倡導人應該過一種與自然合二為一的生活方式。
相比梭羅生態幸福觀重視對個體的生態幸福觀的挖掘,萊易斯進一步指出,個體的幸福與社會的生態幸福觀是分不開的,建構一個“較易于生存的社會”,有助于實現和保障個體的生態幸福。在萊易斯看來,較易于生存的社會,首先是把工業發達的各個國家的社會政策綜合在一起的社會,其目標就是減低商品作為滿足人的需要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質減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未來技術的發明都要有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和同環境中積累的殘存工業廢物作斗爭。[23](P484)但是,對于萊易斯來說,“較易于生存的社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促使幸福從量的標準向質的標準轉化的有機的理論觀點,“較易于生存的社會”只是社會改革的一個有力的動態階段。其次,“較易于生存的社會”的特征是降低生產,實行穩態經濟,生產走向小型化和分散化,人類滿足的場域不再是消費,而是生產。這就是萊易斯“較易于生存的社會”背景下的生態幸福觀的兩個基本點。
總的來說,梭羅所倡導的平等主義的“田園牧歌式生活”,而萊易斯的“較易于生存的社會”背景下的生態幸福生活,這正是兩者在社會制度與幸福相關性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異質點。
4 啟示
梭羅和萊易斯的生態幸福觀都把生態問題與人的幸福相結合進行研究,這正是當代生態幸福觀研究的主題。比較二者生態幸福觀的一致性和異質性,可以看出其對世界范圍內的生態幸福研究具有重大啟示。
首先,相比工業文明時期各種幸福觀過于注重幸福的量(物質消費量)的標準,梭羅和萊易斯向我們闡述了生態文明時期的幸福研究必須注重幸福的質的標準。那么,如何實現有質量的幸福生活?梭羅和萊易斯給出相似的解答。梭羅認為好生活并不是無止境消費的生活,相反,他認為只有簡單生活,才能深入到生命的最深處,不被世俗的喧囂左右。在《瓦爾登湖》里,梭羅不厭其煩地羅列自己的各項費用和生活成本,只是向現代人表明:事實上,人只需要一定量的勞動就可以換回人類生活的必需品,而其余時間則可以自由支配——或用于閱讀和思考,或用于豐富我們的生命內涵。他還舉例說,像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的古哲學家那樣,他們外表再窮沒有,內心再富不過。因為這種人免于謙卑的工作,開始向生命邁進。這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來說是一個警醒和啟示。萊易斯也說:“現行的生產和消費活動的體制妨礙人們這樣一種才能和能力的發展,即直接參與可提供滿足范圍廣泛的需求(建造房屋、種植糧食、縫制衣服)手段的活動的能力,相反卻使人的活動完全圍繞市場購買來進行。”[24](P108)可見,在他看來,有質量的生活在于消費之外的其他活動領域之中,他期待人們應該越來越多地在理想的職業中,在生產和參與決策中獲得滿足。在這樣一種生態幸福觀下,人對市場交換的依賴會大幅度縮減,也可以在不以廣告為媒介的適當消費和生產中獲得快樂。總之,梭羅和萊易斯認為現代人不幸福的原因不在于缺少生活必需品,而在于無限制的購買欲望,他們有可能并不喜歡自己的職業,但他們仍然會努力工作以滿足他們的高端消費需要,制造虛假幸福。最終,梭羅和萊易斯教會我們如何更好地生活,即當今的生態幸福關鍵在于重新評價人的物質消費需求,并逐漸將人的需求引向精神文化領域。當然,這并不是要提倡人們回歸原始式的簡樸生活,而是要調整人們對好生活的性質和質量的看法,最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
其次,從梭羅和萊易斯的生態幸福觀在如何改變人的自然觀念上看,不管是梭羅,還是萊易斯,他們都流露出保護自然的情感,認為人與自然要共生共榮。梭羅通過贊美自然之美來重新喚起人類對自然內在價值的關注,暗示保護自然及自然對人類幸福的意義;而萊易斯則通過揭露工業化進程中的大規模“控制自然”導致了人與自然的不和諧來喚醒美國人保護環境的意識,引起全球性的關注。在他們看來,當今的幸福追求并不僅是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問題,人與自然間的正義秩序也不容忽視。梭羅認為,自然對人類具有同情心,是自然提供我們必要的生存條件。他說:“是什么藥使我們健全、寧靜、滿足的呢?不是你我的曾祖父的,而是我們的大自然曾祖父的,全宇宙的蔬菜和植物的補品,她自己也靠它而永遠年輕,活得比許多的老伴兒們更長久,用他們的衰敗的肥胖更增添了她的康健。”[25](P127)因此,梭羅告誡我們,自然和人類一樣,都有獲得幸福的權利。人類要想在地球上好好地生活,就應該學會更多地從生態意義上去思考幸福問題,改變以往對待自然的殘暴態度,做到公平公正地對待自然,維護自然的本真狀態和自然的精神意義。正是梭羅的生態幸福主張,喚起了美國民眾的環境正義意識,弘揚了環境正義主題。并且,較之梭羅時代的環境正義主題主要研究人與自然之正義,萊易斯時代的環境正義主題更主要表現為以環境為中介的人與人之正義。如萊易斯從一開始就明確指出傳統“控制自然”的觀念與控制人及加劇社會矛盾的關聯,他說,以往“控制自然”的觀念把人和自然一分為二,給自然和人類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災難,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態問題。并且,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對自然的技術控制通過操縱需求轉化為對人的控制。”[26](P141)不僅如此,“它們的過分含混有助于掩蓋一系列基本的社會矛盾”,[27](P91)消弭了人對現實世界的批判能力,傳統“控制自然”事實上是對人的幸福的控制。因此,萊易斯認為,生態問題不是單純的自然問題,更不是一種“經濟代價問題”,而是事關人類幸福的社會問題。概而言之,梭羅和萊易斯啟示我們,人要重視環境正義,把自己欲望的非理性部分置于控制之下,善待自然,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構全球性的生態幸福社會。
參考文獻:
[1][2][3][4][7][18][25]〔美〕亨利·戴維·梭羅.瓦爾登湖[M].徐遲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5]〔美〕詹姆斯·博特金,〔摩洛哥〕馬迪·埃爾曼杰拉,〔羅馬尼亞〕米爾哈·馬利察.回答未來的挑戰——羅馬俱樂部的研究報告《學無止境》[M].林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9][23]〔加〕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M].慎之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8][24]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Press,1976.
[10]Thoreau H D,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Volum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6.
[11]Paul Rot(ed.),Walden and Civil Disobedience,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
[12]〔美〕巴里·康芒納.封閉的循環——自然、人和技術[M].侯文蕙譯.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13]〔英〕戴維·佩珀.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正義[M].劉穎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14][19]陳學明.生態社會主義[M].臺北:楊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15][16][26][27]〔加〕威廉·萊斯.自然的控制[M].岳長嶺,李建華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17]Reiner 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London and NewYork: Oxfoxd University Press,1991.
[20]Thoreau H D,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Toronto: Bantam Books,1962.
[21]Emerson,History Notes of Life and Letters in New England,Perry Miller The Transcendentalists: Harvard Press,1879.
[22]盧風.簡評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6).
責任編輯劉宏蘭
作者簡介:林麗婷(1988-),女,福建莆田人,廈門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徐朝旭(1956-),男,福建福州人,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2BZX071)。
[中圖分類號]B7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6)03-00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