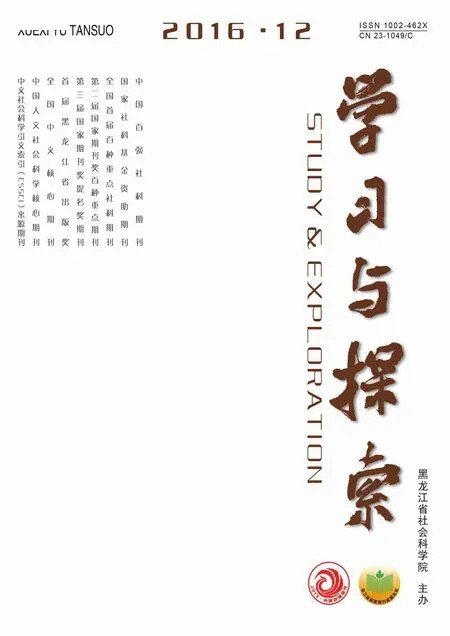土地性別矛盾與鄉村治理探究
李 慧 英
(中共中央黨校 社會學教研室,北京 100091)
?
土地性別矛盾與鄉村治理探究
李 慧 英
(中共中央黨校 社會學教研室,北京 100091)
長期以來,我國鄉村土地性別矛盾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鄉村土地性別矛盾是在農村經濟集體所有制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的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基礎上產生的,近年來具有不斷升級加劇的態勢。應從鄉村治理入手,抓住治理的核心概念——依法維權,使國家與地方政府和基層自治組織實現良性互動,才能有效化解土地性別矛盾。
性別權利;父權制;鄉村治理;依法治理
我國鄉村土地矛盾日益凸顯,有多種表現形式:村委會與政府的矛盾、村委會與開發商的矛盾。近年來,村干部與村民的矛盾,還有農嫁女與村委會的矛盾,土地分配不公的性別矛盾由隱性走向顯性,成為21世紀以來中國多種社會矛盾之一。鄉村土地性別矛盾不同于土地改革時期的地主與貧雇農之間的階級矛盾,也不同于當今城鎮化進程中的小官巨貪的干群矛盾,它是以性別身份為軸心,以男娶女嫁為劃分標準,以性別權益剝奪為特點的。在這里,性別矛盾剝奪的對象是出嫁離異和喪偶的婦女及其家庭,通稱為農嫁女。土地權益包括兩部分,一是耕地和宅基地的直接土地權益,二是間接的土地權益,包括征地補償款、新農村的住房、股份分紅等。
在我國的土地矛盾糾紛中,性別矛盾往往成為盲區。專家學者更多關注的是干群矛盾、階層矛盾和土地征用補償引起的社會沖突,地方政府更多關注社會穩定和政績,農嫁女的土地權益很少納入工作視野,更不要說防患于未然了。然而,“看不見”不等于不存在,正因為“看不見”,土地的性別矛盾在不斷積累和加劇,已經成為全國各個省市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發展速度驚人。根據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顯示,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受到損害由9.2%提高到21%,提升了11.8個百分點,高于男性9.1個百分點。*數據來源:全國婦聯、國家統計局。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內部資料)(2010年10月)。筆者將從鄉村治理的角度對土地的性別矛盾予以關注與探究。
一、土地性別矛盾的產生機制
我國土地的性別矛盾十分具有中國特色。矛盾的形成需要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是在農村經濟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產生的,在農村經濟私有制的條件下,只有家庭和家族內部的分配,不會出現集體經濟的分配問題;第二,是在農村集體經濟的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條件下產生的,農村集體經濟有多種實現形式,在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土地采取的是農民參加集體勞動計算工分,農民并不具有土地使用權,自然不存在農村婦女的土地分配不公問題。1980年以后,土地實行聯產承包,以戶為單位可以分配土地,家庭按照人口平分,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可能產生婦女婚姻流動土地如何處置的問題。
鄉村土地性別矛盾是怎樣產生的?需要兩大土地管理機構和三大要素——即國家政府、村委會和性別規則的交互作用。我國土地管理是雙重管理結構,一重是國家管理機構,即相當一部分的管理權力掌握在國家手里,由國家來確認農村土地的性質、使用方式、承包的單位和時間、征地補償標準以及土地的退出等公共政策。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核心內涵是以“戶”為土地使用單位。農地按照人口的“平均分配”和宅基地的“一戶一宅”[1],都力圖體現土地資源的平均分配原則,所以,土地承包以來,男女同等享有耕地分配權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由于對于性別的盲視,存在著政策漏洞,如沒有詳細規定一戶一宅必須男女平等,給家庭父權制留下漏洞。因為按照鄉土社會父權制[2]的運作邏輯,只有男性在本村結婚娶妻,才有資格形成一戶擁有一宅,女性結婚根本不能在娘家村落戶,沒有一戶的資格,不能獲得一宅。當父權制文化與一戶一宅的政策相結合就發生了化學變化,在農村宅基地的無償分配中,就有了性別取向——只給兒子不給女兒,女兒全部排除在外。這是性別矛盾產生的政策因素。
與此同時,國家政府又將一部分集體分配權力下放到基層自治組織——村委會,即將村集體掌管的土地資源以及相關的收益分配權利賦予村委會。1998年,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規定將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交給村民會議決定,召開村民會議,應當有本村十八周歲以上村民的過半數參加,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戶的代表參加,所作決定應當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通過。該制度在2010年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再次得到確認。這一分配原則在《土地管理法》中也一再得到確認,通常地方政府對于農村空掛戶的軍人、大學生、勞改犯、失蹤人員,都做出明確的規定,不會交給村民決定,唯獨對結婚和離異的婦女是否享有村民待遇,交給了村民和村組干部討論決定。
由村民確定婚嫁婦女的村民資格、根據村民意愿分配資源,無論是事實上還是程序上,都形成了村民委員會的一項重要權力。這使得村委會有了更大的權力按照自身意愿分配集體資源。村委會和村民小組擔負著對于國家土地管理資源規則的具體實施職責,在村集體內部如何進行分配,國家法律規定的婦女集體資源資格能否實現,農村婚嫁婦女的土地權利能否得到保障,這些都需要通過基層農村自治組織決定。這就是基層自治組織管理土地的功能與效力。
村級基層組織依據何種規則確定婦女身份就成為第三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們決定著婦女是屬于內部成員還是外部成員,是同等享有村民待遇,還是不能享有村民待遇。從2005年開始,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成員組成調查組,深入到全國20多個省市進行調查,調查發現絕大部分農村地區村委會都是將“性別與婚姻”作為一項隱性的分類標準:根據與男性的從屬關系,將本村的“婦女”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妻子、母親的身份;另一類是出嫁女、離婚、喪偶婦女或大齡待嫁女的身份。在一段穩定的婚姻關系中,前者的“成員資格”可以依附于男性戶主而得到保障;而對于后者,她們不愿意依賴丈夫,期待改變婚姻模式——從妻居,或者已有的婚姻關系發生破裂,她們即擺脫了本村(原)家庭中對男性戶主的依附關系,又無法依靠丈夫獲得“成員資格”,由此陷入身份認同上的困境。在農嫁女的村民資格的認定中,根深蒂固的父權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父權制凸顯性別與婚姻的因素,強調婚居方式必須服從“男娶女嫁”模式,即女子婚后必須“從夫居”,到男方所在的村落定居。這種婚居方式已經成為民間習俗,成為布迪厄所說的“慣習”[3]63。在當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依然延續著這種古老的慣習。2005年我們在中原農村做調查,發現在漢民族為主的鄉村,依然有99%的婦女“從夫居”。*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課題組2005年在河南194個村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婚姻從妻居比例只占1%。所以,婚姻對于絕大多數農村婦女來說,意味著身份、生產和生活的全方位遷移,即從娘家村搬到婆家村安家落戶,無論是內地封閉的鄉村還是開放的沿海鄉村大多如此。一個普遍的性別居住模式是,男性婚后居住地保持不變,而女性的婚姻居住地則隨婚姻狀況不斷變化。從夫居并不僅僅是居住空間的移動,同時也是家庭和基層單位的轉移,對此,作為女性個人是無權進行自主選擇的,從夫居是必須的和強制性的。
父權制的規則及其弊端在我國的公共政策中極少被意識到和糾正,它誕生于古老的農業社會,而今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父權制一旦與鄉村自治相結合,就會深刻地影響現今農村集體的分配方式,還將在城鎮化的發展戰略中持續發酵,從而產生兩方面的后果:第一,村組干部和村民可以通過集體權力和多數表決,將農嫁女已經分得的土地資源輕而易舉地“拿走”,不需要任何成本,只要通過多數人表決認可,通過村委會蓋章同意,農嫁女的土地權益就不再屬于她本人以及她的原生家庭,而無償地成為其他村民利益的一部分。被“拿走”的土地資源有兩種去向,一是歸入村干部的權力之手,將農嫁女的土地無償占有,然后建房增值投向市場,獲得更多的經濟價值;二是增大村組的“蛋糕”總量,減少土地資源參與分配的人數而增加可分配的份額,使得村集體成員的利益增多。
第二,通過村集體的權力和民主表決,將農嫁女從集體經濟組織中排斥出去,失去集體組織成員資格,從而失去土地資源的收益。農嫁女與村集體組織的關系,發生了調整和改變,她們不再得到集體的庇護和對于需求的“應責”從而獲得國家利益的利好,而是成為集體組織的局外人:國家的土地補償原則對于農嫁女是不適用的,她們的土地不會增值,而土地資源的被征用和被轉移也是無償的。她們從土地承包者和房屋居住者成為凈身出戶的一無所有的無產者。
式中,DOECDit:OECD國家來源國的多樣性指標;DIOECDit:非OECD國家來源國的多樣性指標。
二、土地性別矛盾的轉化升級
土地的性別矛盾產生之后,并未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而是不斷轉化、加劇和升級,從村組矛盾轉化成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從合法維權成為社會維穩控制的對象,從而加劇了農嫁女與國家政府的緊張沖突。
第一,農嫁女與村莊村民的矛盾沖突。絕大多數的土地性別矛盾幾乎都產生于村組兩級“場域”[3]139,在這個場域中,一方是勢單力孤的農嫁女,一方是人多勢眾的村民和掌握權力的村干部,她/他們的力量對比是完全不對等的。農嫁女的訴求是合法的,她們有權利選擇婚姻居住地,村組無權強制只能從夫居,更無權剝奪其原有的村民資格和土地權益,然而,她們根本不能進入村委會,屬于邊緣群體,無法表達自己的合法訴求,更不能參與制定規則;而村組干部和村民在權力和資源上占據支配地位,甚至能夠影響乃至左右村民代表的傾向性。此外,農嫁女的人數十分有限,盡管農嫁女在近郊已經形成一定規模,一個村莊少則20~30人,多則上百人,形成了一種相互利益聯結的群體力量。這支力量與村民相比依然是少數,通常不到百分之一,缺乏鄉村的社會支持力量,受傳統規則影響,乃至自己的家人親屬都會站在父權制立場上指責謾罵她們;而村民們則普遍認同父權制的性別規則,理直氣壯地將農嫁女視為外村人,形成村民、村組和村委會的文化認同和利益共同體,在村民會議上擁有絕對的優勢,農嫁女與村莊的博弈往往以失敗告終。
第二,農嫁女與地方政府的矛盾。在農嫁女與鄉村政治的較量中,政府是不“在場”的。為了爭取合法權益,農嫁女首先考慮到的是找政府,使得政府由缺位轉向“在場”,走向了依法維權之路。在她們看來,所謂的政府就是與婦女權益相關的、行使行政司法和立法權的公共權力機構,這些權力機構理所當然會依法辦事,糾正基層的違法做法。通常的路徑是:自下而上,首先從下級政府——鄉鎮開始,找鄉鎮辦公室、鄉鎮領導、信訪部門,解決不了再找縣級政府、市地政府,乃至省級政府,逐級上升;由點及面,先找婦聯部門——負責維護婦女權益,民政部門——負責糾正村規民約中的違法行為,農業部門——管理耕地資源執行相關政策,土地資源部門——負責宅基地的管理,社會事業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失地農民的安置。再找人大信訪辦——監督各項法律的實施,向各級人民法院投訴——依法糾正各種違法行為。
農嫁女眼中的地方政府是一個樹狀的機構群,由下到上各級政府,涉及幾十家政府部門,而各個層級的政府與部門經常的做法是“踢皮球”,一是部門相互之間推脫責任,無論哪個部門都不愿意攬這些麻煩事,讓她們找婦聯,婦聯回答:我們沒有決策權,只能呼吁,最終還要依靠政府糾正。通常是找來找去,找不到可以解決問題的責任主體。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責任不清晰不明確——誰來承擔,有什么權利與責任,不能履職如何問責,結果導致權利受到侵犯者要維護正當權益,卻投訴無門。二是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推卸責任。與農嫁女由下向上反映問題的方向正好相反,上級政府將解決問題的任務逐級交給了下一級,在科層制的管理體制中,似乎是理所當然不存在爭議的事情,然而,問題就出在這里。需要解決的問題,又重新提交給制造問題的一方。本來是村委會與農嫁女之間的矛盾糾紛,需要上級政府予以仲裁、糾正其非法行為,現在又重新回到村委會手里,村組干部繼續掌握著對于農嫁女的生殺予奪大權。于是,農嫁女的維權之路陷入一個不斷循環而又無解的怪圈,無論到哪里維權,依然回到村莊,問題依然得不到解決。政府的不作為,也給了村委會更大的膽量剝奪農嫁女權益:你們告吧,告到北京、告到聯合國也沒用!*參見: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性別平等政策倡導課題組”2014年4月對青海農嫁女的調查報告。
農嫁女的維權之路是一條無法回頭的路,一旦踏上這條路,與村組干部的關系就緊張對立起來,而且,是對整個村莊傳統性別文化的一種直接挑戰。對于多數農民來說,農嫁女是否合法合理,并不在于你多么符合法律條文,而是能否得到政府法院的支持,將自己的權利爭取到手。否則,就會永無抬頭之日,不僅一無所有,還會備受歧視。所以,很多農嫁女一旦開始維權,就會維權到底,維權到死,用生命來捍衛自己的權利。甚至一次次將村委會和地方政府送上法庭,將下級政府部門告到上級信訪部門——由村級矛盾升級為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第三,農嫁女與社會維穩的矛盾沖突。我國縣鄉兩級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征是壓力型體制,即為實現上級下達的各項指標而采取數量化任務分配方式的評價體系。如經濟增長指標、招商引資指標、社會治安指標、上訪人數指標。這些任務指標采取的評價方式往往是“一票否決制”,即一旦某項指標沒完成,就視其全年成績為零而受到處罰,零進京上訪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標。考核指標對于地方干部是一把雙刃劍,對于積極主動敢于擔當的干部,會想方設法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甚至建立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杜絕大規模的集體訪、越級訪,而對于不善于創造性地公平解決信訪問題的干部,習慣于用拖延辦法處理問題,就十分被動。一方面,對于村莊治理束手無策,還要保住烏紗帽,保住“零進京”。那些長期訪越級訪的農嫁女就成為維穩監控的對象,又使得農嫁女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系加劇,矛盾沖突不斷升級。
對于農嫁女的維穩監控有多種方式,最多的是“盯”,針對農嫁女上訪人員建立維穩領導小組,設置多道防線來攔截上訪,看死盯牢。先是一盯一,再發展到三盯一,堅決阻止農嫁女到北京上訪。為此,各地維穩辦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成為一項日常工作。一旦出現漏洞,農嫁女進京上訪成功,信訪部門就會要求地方政府接人,循環反復,基層維穩經費直線上升,有的縣攔截10位上訪者,幾年下來需花費300多萬元[4]。
在這里,婦女維權與社會穩定也進入一個怪圈。從社會維穩的視角,婦女維權上訪,就會引發社會不穩定,維權與維穩是對立的沖突的,引發婦女上訪維權的真正原因——土地權益被剝奪卻被忽視了,直接將維權婦女作為穩控對象,結果越是維穩就越是不穩定,社會矛盾呈幾何式增多與攀升。
三、土地性別矛盾的有效化解
土地性別矛盾的有效化解,需要改變鄉村管理思路,即從鄉村的社會管理轉向鄉村的社會治理[5],“管”與“治”,一字之差,差之千里。鄉村管理注重控制與服從,忽視個人權利,將維權與維穩對立起來;鄉村治理注重互動與合作,尊重個體權利,將維權與維穩統一起來,將個體權利的保障看作社會穩定的基石,不僅重視鄉村自治,也重視依法治理。尊重和維護個體的合法權利,是鄉村治理的核心理念,個體權利不分階級、民族、年齡和性別,一視同仁。需要圍繞個體的合法權利建立社會治理的運行機制,確切地說,建立促進性別權利平等的鄉村治理運行機制。
第一,建立具有性別敏感的公共政策。鄉村社會治理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政府依法進行社會治理,二是鄉村依法進行自我治理。我國有五級政府,國家和省級政府要制定公共政策,對土地進行管理。這就需要國家政府對土地性別矛盾做出積極回應,滿足作為公民的農嫁女的合法權利訴求,制定保障男女權利平等的具體規定,堵住公共政策中的性別漏洞。
一是要做實家庭土地承包“戶”中的個人或性別權利。土地承包的單位是“戶”,已經成為一項基本制度安排。它可以最大限度調動家庭的積極性,其中隱含的最大危險是,在父權制規則普遍得到認可的情況下,會掩蓋家庭成員的個體權利,會剝奪女性的權利。防止權利丟失的辦法,就是做實戶中的個人權利特別是女性的權利,比如,在一戶一宅的政策中,要明確規定男女結婚都可以單獨立戶,夫妻雙方都可以成為戶主,并在房產和宅基地證書上簽字。并將該規定納入公共政策予以監督執行。又如,在土地確權證上,家庭所有成員都為土地承包共有人,耕地轉租、抵押和流轉,需要共有人簽字認可。
二是啟動公共政策重新界定村民資格,杜絕民主表決村民資格的方式。迄今為止,我國相關土地政策沒有對于村民成員資格進行界定,而原有依照戶籍確定村民資格,又不能適應社會變化。界定村民成員資格應當屬于公共政策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目前,地方已有界定村民資格的成功經驗。2009年末,河北邢臺中院討論通過了《關于審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收益分配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簡稱《審理意見》),對“成員資格認定”進行了明確規定,將戶籍、常住以及與集體經濟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作為成員資格認定的標準。《審理意見》出臺后,邢臺兩級法院積極審理與執行,效果顯著。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2014年在邢臺法院及信訪處的調研發現,婦女土地的法院案件立案數量非但未曾暴長,反而逐年下降。到婦聯上訪的該類案件數量也呈直線下降趨勢,轄區內的婦女土地權益糾紛顯著減少。值得將地方經驗提升為公共政策的頂層設計指導全國。
此外,還應嚴格禁止村民民主表決決定集體成員資格。民主表決只適用于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性)公共事務,比如選舉村主任、人大代表以及進行立法等,而不適用于針對個人基本權利的決定,包括集體成員資格的確定。涉及集體成員資格的認定,不應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而應遵循法治原則。
第二,地方政府要建立維權保障機制。地方政府特別是縣鄉兩級政府承擔承上啟下的責任,一方面要將國家的公共政策予以實施,另一方面要糾正違法違規的行為,這就需要建立維權保障機制。保障機制包括:責任主體,哪個部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承擔責任的部門需要具有哪些相應的權力。有了責任主體,就要接受權利受損者的投訴;要制定罰則和糾錯機制,責任主體對于侵權主體予以制止和糾正。這一機制的建立可以及時接受村民的合法投訴,及時糾正村委會的侵權行為,而不是相互推卸責任。
除了糾錯機制,還可以建立防范機制。縣鄉政府對于村莊分配方案進行審查。通常,依據村組法的規定:鄉鎮政府擔負著對于村莊規則(包括村規民約、分配方案等)的審查職責和糾錯職責。對于村委會分配方案的條款(包括潛規則),鄉(鎮)政府應要求村委會限期予以刪除,并在重新修訂后以書面形式報鄉(鎮)政府備案。為了杜絕征地拆遷中侵犯婦女土地權益問題的持續發生,南寧經開區管委會采取了兩項措施[4]:第一,村委會提交的集體分配方案要體現男女平等,否則政府不予審批與撥款;第二,已經分配過的村莊要從三產中提取就業補助資金給農嫁女。地方政府監管到位,有效預防農嫁女與村委會之間土地矛盾的大量發生,也改善了地方政府與農嫁女的緊張關系,農嫁女提出永遠不再上訪。
第三,村莊自治要依法自治體現男女平等。如果說,政府管理是鄉村社會治理的一翼,那么村莊自治是鄉村社會治理的另外一翼。在這里,民主程序是村莊治理的重要方式,可以有效監督村級權力,但是,民主參與的底線是不能違法,不能侵犯村民的合法權利,就是要依法治理。最佳的基層治理,不僅要民眾參與,還要對村民的合法訴求做出積極的回應,使得國家層面的法律可以落地,使得村民合法訴求得到滿足,將性別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
村莊依法自治,首先要對鄉村根深蒂固的父權制規則進行清理和改造,推動婚居自由,“婚居自由”,是指男女結婚之后,有選擇婚后居住地的自由。我國20世紀80年代的《婚姻法》制定了“登記結婚后,根據男女雙方約定,女方可以成為男方家庭的成員,男方可以成為女方家庭的成員”條款,明確提出“婚居自由”。所有性別不平等的規定,都和“從夫居”的規則聯系在一起。凡違背了“從夫居”規則的農嫁女,都有可能失去村民資格,進而失去集體資源分配的權利。其次,要消除性別排斥的集體分配方案,建立體現男女平等的新規則和資源分配方案。在文化變革的基礎上,建立村莊公平的新制度。增加“純女戶、有兒有女戶的子女婚居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同等享受本村村民待遇”“女性村民代表不得低于50%”等條款。河南登封市的周山村是我國第一個制定性別平等村規民約的村莊[6],從2009年至今三次修訂平等合法的村規民約,得到村民的認可和遵守,無一起上訪案件,為鄉村治理提供了鮮活的成功案例,為依法自治筑起一道堅固的防線。
[1]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中發[1997]11號)[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71380/71382/71481/4854245.html.
[2] 杜芳琴.華夏族性別制度的形成及其特點[J].浙江學刊,1998,(3).
[3] 包亞明.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 王曉莉,李慧英.保護征地過程中的婦女合法權益[J].三農要參,2013,(4).
[5] 俞可平.沒有法治就沒有善治[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1).
[6] 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性別平等政策倡導課題組.修訂村規民約探索農村社區有效治理的路徑[N].農民日報,2015-08-17(13).
[責任編輯:高云涌,張斐男]
2016-10-20
李慧英(1957—),女,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社會性別與鄉村治理研究。
C4
A
1002-462X(2016)12-004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