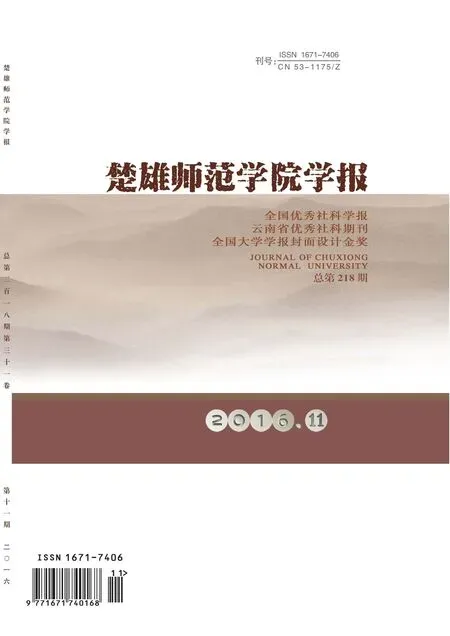文化生態視野下楚雄彝族的耕作與信仰
單江秀
文化生態視野下楚雄彝族的耕作與信仰
單江秀
生計模式和生活方式決定著人們的知識系統、價值系統和信仰系統,以耕耘為主要生計模式的民族,意識形態里也打上相應的耕作烙印。彝族這一山地民族,在固守傳統的旱作文化的同時兼有水田栽插的稻作文化,在具體環境里耕耘出一個個生動的文化——地理單元,壩區和山區兩個文化地理單元中的彝族以滿足需要為原則建構起相應的信仰體系。
信仰;耕作;文化生態;楚雄彝族
一、前人研究
自然崇拜源于原始社會,魏晉南北朝時有所發展,它反映了當時的民間風俗與社會信仰。[1]甲骨文里的“自然崇拜”觀對后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長達千年。[2]《說文解字》中的“示”部的文字大多反映了中國上古時期的祭祀文化。自然崇拜是早期人類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國早期精神文化的主流部分,如初春祭日、中秋祭月。我們不能因為科學發展而簡單地把這些現象斥之為“封建迷信”,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延續。[3]圖騰崇拜是向自然崇拜過渡的必需語言,萬物有靈是從圖騰崇拜到自然崇拜的中介語言。而原始思維以集體表象為特征,神化自然和將自然人格化,為導向崇拜自然打下了必要的基礎。[4]自然崇拜的功能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5]自然崇拜是中國自古有之的宗教習俗,但自然神話是很不發達的,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神話故事。[6]自然崇拜對原始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奠定了感官進化、想象移情、將自然人格化的生理心理基礎,使原始人類的審美心理得以萌生。[7]有學者獨辟蹊徑,從哲學的角度分析黎族自然崇拜的成因。[8]與之相關的口頭神話與民間信仰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二者先后經歷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等階段,并相互促進。[9]西南少數民族的自然崇拜經長期沉淀,形成了自然環保習慣法則,這既是法律規范,又是道德規范,體現出社會、法律兩個層面的功能與價值。[10]云南少數民族的自然崇拜中體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理念,對生態文明建設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11]彝族古老樸素的崇拜和相關禁忌對當今保護自然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和自然運轉,以及倡導生態道德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12]彝族的自然崇拜與儒家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皆表現出對自然界的極大尊重與關愛。在當代社會,反思傳統文化,發掘其中的精神資源,并不是要回歸傳統,而是要通過汲取傳統思想之精華以解決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13]云南彝族體育活動產生于祖先崇拜、圖騰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動。[14]云南壯族的自然崇拜在客觀上對生態保護具有積極意義。但是,這種植根于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心理上的迷信思想,影響壯族現代生態文明觀念的形成。[15]白族的自然崇拜形式多樣,貫穿于白族藝術中的說唱文學、歌舞祭祀、繪畫工藝中,這對弘揚民族文化精華,保護民族文化遺產,促進社會和諧和各民族共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6]有學者從生態系統的保護,人類社會的發展,綠色文化理念的構建等生態人類學視角對荔波喀斯特世居民族自然崇拜信仰的效應與歷史地位進行評述。[17]
綜述以“自然崇拜”為主題的研究,目前有從生態視角研究其環保意義的,有從歷史的角度研究其產生、發展歷程的,有從社會的角度研究其道德規范、教化作用的,有從文化的角度闡釋其文化內涵的。當下的研究強調,切勿因處在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而錯將自然崇拜劃為封建迷信,它是民族的精神文化資源。彝族的自然崇拜與儒家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緊密相連,對解決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研究緣起
萊斯利·阿爾文·懷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進化有兩大創新:文化學與能量學。他強調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在于:人具有象征表示能力,通過該能力適應和開發周圍世界并賦予事物其本身所不具有的某種意義。能量說認為,文化進化即人們把握、利用能量之技術提高的結果。
朱利安·海內斯·斯圖爾德(Juliar Haynes Steward)在繼承懷特的進化論觀點的基礎上又發展出多線進化的觀點。他不僅關注到技術在文化進化過程中所起到的基礎性作用,而且將其視野擴展到與技術密切相關的生態,包括土地、自然資源、雨量、氣候等自然條件,強調文化對自然環境的調適,認為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是相互作用的因果互動關系,并由此建構起他的“多線進化理論”。同時,又由于斯圖爾德對生態環境研究的重視和對文化生態學研究的關注,所以,他的理論又被稱為“文化生態學”。他認為,具體的生態環境中書寫出特定的文化形貌。“數千年來,不同環境里的文化已有極大的改變,而這些變遷基本上可追溯到變化的技術與生產安排所需要的種種新適應。”[18](P37)
與特定的自然環境相適應,楚雄彝族采取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這是文化系統中的技術系統,是人要生存下去而采取的技術手段,它決定社會系統。思想意識系統反映社會系統,解釋人類經驗,并受技術系統制約。楚雄彝族的耕作是人們利用能量,將其投入到生產中服務本民族的技術運用,信仰是彝族對該運用過程的經驗解釋和象征表達,生態環境決定技術運用,技術操作影響信仰實踐,于是,在楚雄這塊土地上編織出一個個意義豐滿而靈動鮮活的文化之網。
三、楚雄彝族的耕作與信仰
歷史上,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差異,彝族地區人們的經濟生產活動具有不同的類型。從事農耕的彝族,曾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從采集漁獵階段發展到農牧并重階段,進而到以農耕為主、畜牧為輔的階段。各彝區進入農耕階段的時間和發展情況是參差不齊的。其農業生產類型又分為三種:壩區稻作型;半山區稻作和旱作兼具型;山區、高寒山區旱作型。楚雄南華縣哀牢山沙坦蘭村有一塊立于大清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的《劉楷墓碑》*《劉楷墓碑》碑文說:“南山中,林木茂,野獸多。我遠祖,農耕少,獵事多,率奴眾,逐禽獸,朝夕樂;鄰侵界,必戰斗。當是時,夏衣麻,冬衣皮,朝食蕎,晚食肉,得溫飽。明洪武,土頭薄,播種一,獲八、九;自此后,農事繁,獵事少,居住定,不再流。楷高祖,天順時,土頭沃,種一升,獲二斗,楷祖時,嘉靖年,開溝渠,稻谷熟。”,碑文上簡述了劉氏的耕作變遷史。
(一)山區旱作模式
為開發土地資源,楚雄州早在元、明兩代就實行屯田制,分軍屯和民屯。明代,政府認為“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糧,邊方之計,莫善于此……宜緩其賦稅之粟,使彼樂于耕作。”同時實行“夷田不加勘丈”,“計戶納糧”的政策,鼓勵開墾耕地。當時,定遠、姚安、中屯等千戶所屯田面積各在1.7―1.8萬畝之間。清代屯田制逐步廢弛,屯田轉為民田。[19](P158)進入農耕時代,相應地也帶來文化轉型。
另外,旱災是楚雄地區的主要自然災害,自明清以來就不絕于書。如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姚安縣2―6月不雨,歉收。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今雙柏、楚雄、元謀、南華等縣春夏干旱,“七月得雨,補種雜糧,收成大減”。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牟定縣大旱饑饉,貧民餓死者甚多。民國6、8、12、19年都有大旱記載。民國32年(1943年)楚雄等13縣,“雨澤全無,曠野無鱗口之漿,田疇荒蕪,生活斷絕”。干旱主要表現為春旱、夏旱和插花性的秋旱。[19](P156)
1.農事安排
旱作,是傳統農耕類型,它在我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占有重要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彝族居住區內除有少數輪歇地外,絕大部分是固定的旱地。根據當地的氣候條件及土地狀況,楚雄州大姚縣的彝族對各種農作物相應的節令安排(以農歷為準)如下:
正月:翻冬地,擇屬馬或屬雞日種洋芋。二月:挑糞堆于地邊,擇屬蛇或屬馬日撒麻。三月:挖地,擇屬狗日撒蕎子。四月:擇屬馬日種包谷。五月:擇屬馬日撒燕麥。八月:擇屬馬日撒小麥。九月:擇屬馬日撒大麥,割母麻。在這里,農業是大姚彝族的主要生產活動,農作物以包谷為主,次為燕麥、蕎子等。旱地都是固定的農業耕地,一年分二季耕種,秋冬種小麥,春夏種包谷等。輪歇地不多,一般二、三年輪歇一次,普遍采用“種火地”方法。
2.山區彝族的信仰
從人們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以旱作為中心,圍繞其生計模式、耕作方式而產生的各種相關的文化如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文化心理結構、信仰和習俗等,就是旱作文化的構成要素。
旱作文化是彝族傳統文化繁育和延續的源頭活水,無論是神話傳說、宗教信仰,還是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以及各種民俗事象等,大多圍繞著這個主題展開。旱作文化是山區彝族文化地標上的重要特征,文化地標除了具有自然地理的坐標性(特定的地理區域與范圍)及人文地理的標志性(主要是一定的文化地理區域內人們的信仰與民俗等)特征之外,它還表現為人們生活的方式狀態,具體到日常的生產、生活方式,甚至具體到人們“做什么,用什么”,“耕種什么,吃什么,怎么吃”,從而形成文化地標上人們的生活形態特征,彰顯鮮明的文化特色。從古至今,楚雄彝族文化地標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旱作文化,尤其是在山區和部分半山區,以農業為主,畜牧業為輔。至今,牛、馬仍然是重要的生產、生活和交通工具。
楚雄彝族原生型旱作文化是粗放型的農耕文化,生產力水平較低,營生方式單一,靠山吃山,生存仰仗于自然。所以,信仰體系中首先是自然崇拜,如對天地神、山神、火神等的崇拜;二是動植物崇拜,如敬牛、敬蕎神、敬莊稼神等;三是祖先崇拜。與此相聯系的習俗是祭天、祭山、祭火、招牲畜魂、招五谷魂等。上述崇拜及其祭儀的核心是求豐、求吉、求人畜平安,這些文化要素大致構成了旱作文化賴以存續的人文生態系統,從中升華出火把節、十月年等農事節日。道光《云南通志·爨蠻》載:“民間皆祭天,以臺三階以禱”,“以六月二十四日為節,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年。至期,搭松棚以敬天”。
(1)火崇拜
火崇拜是旱作民族的共性,查閱彝族的神話、傳說,隨處可見對火的記述。彝族史詩《查姆》講道:“獨眼睛這代人,用火來御寒,用火來做伴,用火來燒東西……人類從此冷暖能分辨,從此生熟能分清。”《梅葛》說:“地上沒有火,天上龍王想辦法,三串小火鐮,一打兩頭著,從此人類有了火。”《阿細的先基》說:“天上打起雷,有一樣紅彤彤的東西,人們沒見過……姑娘和小伙子們,在旁邊的樹叢里,折了一些小樹枝,拿來撬老樹,撬著撬著,嘛,撬出火來了。”史詩里所述人摩擦取火的行為都被神圣化,升華為彝族的宗教祭儀傳承至今。火神、火塘、火把等以火為中心的文化事項與彝族生產生活須臾不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火的功能,外顯的是炊事,是照明,是御寒取暖,是安全屏障,是獲取食物的工具,內隱的是火的神秘的功能與象征,火具有神奇的靈力。
楚雄彝族每年舉行盛大的火把節祭祀火神,驅除家中和村寨中的邪魔,驅除田地里的病蟲害,祈求清吉平安和豐收。火把節那天彝族村寨的人們都要點燃火把,舉著火把從臥室走到灶房,從正房到耳房,從磨房、碓房到畜廄走上一遍,每到一處撤把松香末,唱一支祈求豐收幸福的歌。家里走遍之后,就到田地里去耍火把祭“田公地母”,引谷穗出頭看火把。用火燒死害蟲,然后將火把插在田頭地角,最后才將火把送到村邊空地或火把梁子上,堆積在一起燃起篝火,圍著火堆踏歌起舞,直到天明方休。六月二十五日這天,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節日盛裝,聚集在寬敞的草坪上摔跤、斗牛、打磨擔秋,唱歌跳舞,慶祝節日。關于火把節起源的神話傳說也有多個版本,分為祭祖型、反抗型和征服型三類,都圍繞農耕這個主題,即祈愿戰勝天災、害蟲等災害,追求幸福生活。因此,火把節之火是人畜繁衍興旺的象征,是五谷豐登的美好祝愿,是生命的象征……火把節衍化為以農耕為核心的復合型盛大節日。[20](P84-99)
楚雄州永仁縣迤什廠彝族,正月初二或初三全村舉行祭火儀式,曰“火神會”。
(2)山神崇拜
山神崇拜是中國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種宗教文化現象。天子祀五岳,百姓祭本地名山。晉人葛洪撰《抱樸子·內篇》卷十七《登涉》說:“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則神小。”[21](P128)
生于斯,長于斯,彝民同樣飽含深情,對山神懷著既崇敬又畏懼的雙重心理。山神,在彝語方言中有“白斯”、“宰乃”、“密西”等異稱,其含義也求同存異。山神崇拜,是彝族原生性宗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泛存在于彝區各地。源于先民對山的虛幻感覺和想象,他們認為山是通天之路,撐天之柱,山是神靈的住所。《勒俄特衣》中說:“四根撐天柱,撐在地四方,東方的一面,木武哈達山來撐;西方的一面,木克哈山來撐,南方的一面,大木低澤山來撐。”這里,山即是神,神即是山,山神能撐住天,是諸神中力量最大的,能制服山中各種妖魔。在許多彝族的聚居區,都把山神作為地方村寨保護神。[20](P67)
山神崇拜中也含有祈求風調雨順、莊稼豐收的愿望。各種祭祀活動與生產勞作緊密相連。如正月或二月屬馬日燒地,要用酒、肉、雞祭山神;三月撒蕎之時,要在地中央插三炷香,擺上酒、飯、蕎粑粑祭山神*祭山神,每年農歷三月二十八日,在山神廟梁子舉行。山神廟梁子有一片古松林,其中一棵為山神樹,平時經常有人在山神樹下燒香作祭。到了農歷三月二十八這天,全村人皆到此祭山神,意在祈求山神保佑村民家家戶戶、男丁女口平安,家庭幸福、六畜興旺、五谷豐登。祭山神要殺一頭大肥豬,豬肉煮熟后,獻山神,參與者個個向山神磕頭作拜,拜畢,豬肉連肉帶湯,每戶一份,承辦者原由伙頭負責,后由各戶輪流舉辦。;三、四月點包谷之前,要在地中選一小塊地先點幾塘,象征“入土開播”,然后在地四角插上幾枝馬櫻花樹枝,用酒、肉祭山神后才能點種;蕎麥長出后,要在蕎地中央插一棵三叉松樹枝,鋪上松毛,殺雞祭山神和蕎神;蕎、包谷收獲季節,要擇屬馬日先祭山神,再到地邊祭山神和莊稼神;收割完后,還要在堆放蕎或包谷的曬場上,用酒、肉、飯獻祭山神,感謝山神賜給好收成;農歷冬月初十日舉辦牛王會,答謝耕牛一年來的辛苦耕耘。*屆時家家戶戶舂糍粑(糯米做的粑粑)。節日清晨把牛牽到院子里,每頭牛先喂一瓢糯米稀飯,再在牛角上掛一坨糍粑后吆上山,放牧人帶上炊具上山野炊,太陽落山則回村。楚雄州大姚縣鐵鎖鄉一帶的彝族認為,山神的地位至高無上,人們的吃穿用全仰仗于他,要勤祭拜,否則禍及人畜。因此,每戶都有一塊神圣的山神地,從中挑選一棵高大茂盛的松樹為山神,松樹的長勢象征家業的盛衰,所以要時常獻祭。祭祀分為以家為單位的在自家山神地里的家庭祭祀和以村社為單位的集結在寨神林里的集體祭拜。

表1 山地彝族的農耕活動與祭祀禮儀
(3)虎崇拜
虎,山中之王同時享受著廣大彝民的崇敬和貢饌。滇川黔桂彝族從虎生宇宙萬物的神話傳說,到人虎互變的神話故事,從圖騰崇拜到祖先崇拜,從耍虎舞到崇虎敬虎,從虎歷虎星占到繪虎繡虎、服飾工藝無處不有虎文化。從表層看,意在企盼自己像虎一樣勇猛、果敢、剽悍,具有非凡的生存和競爭能力;從深層看,虎是彝族的圖騰標志、徽號、族號。彝族是虎的后代子孫,與虎自命。
今天還可以看到彝族婦女的頭飾有大量的虎崇拜內容,這些頭飾或繡飾虎形,或繡飾黑白、黃白、紅黑相間的虎紋。彝族小孩普遍戴虎頭帽,穿虎頭鞋。雙柏的羅羅支系至今仍然固守著每年農歷正月初八至十五舉行老虎笙節。節日不但歷時長、規模大,而且全民參與,儀式神圣,信眾虔誠,虎舞古樸,內容神秘。虎除了被看作是羅羅人的祖先之外,在彝族典籍中,虎還是世間萬物的創造者。據彝族傳唱史詩《梅葛》的記述:打死老虎來造萬物,由虎化作天心、天頭、天鼻、天耳、太陽、月亮、星星、云彩、地尾、地膽、霧氣、大海、江河等。[22](P26、28)
據《新五代史·四夷附錄》載:“首領披虎皮”;《南詔圖傳》和劍川石窟”雕像中的武士有披虎皮的;《蠻書》也有“超等功全披”之載。說明“披虎皮”是彝族崇虎的另一形式,它象征高貴身份,因虎為山中之王,極兇猛剛烈,代表王臣、武士雄武威嚴,也象征虎祖英雄氣概。其次在民間也有“披虎皮”之俗,據《南齊書·氐羌》載:甘南羌人,“俗重虎皮,以送死,國內以此為貨”。這可能是表示虎族活人送仙去者歸虎的儀式。清雍正改土歸流以前,彝族在火葬時,要用虎皮包裹死者。另外“披虎皮”還有趨吉避兇之義。相傳阿羅人先祖,居深山野壑,常受猛獸惡人相侵,人禾不防,幸獵殺虎,每人披皮一張,似虎動作相跳,爾后安吉,相沿成俗,發展為最具民族特色的“跳虎節”。由此看出,“虎”又成人們的保護“神”。[23]
(二)壩區稻作模式
生計即人們的謀生之道,謀生之道的思想意識即人們的生計觀念。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工具簡單粗糙,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有限等種種局限下,彝族只能是粗放型的生計模式。隨著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接觸面越來越廣,彝族民眾在不斷的對比過程中,也逐漸意識到“白米飯比蕎面饅頭好吃,旋耕機比老黃牛好使”,以精耕細作為特點的稻作型生產方式比“種一山坡,收一笸籮”的粗放型的刀耕火種更高產高效。于是,傳統的旱作文化歷經適應后轉型為稻作文化,稻作型生產方式及其文化浸潤式地逐漸與彝族傳統文化相圓融、相整合。
自明朝開滇以來,革新耕作技術、改善生產工具、提高糧食產量等農業政策一直是歷代中央王朝邊疆治理的重點,加之大批中原移民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更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在當地土著文化和外來異文化的交流碰撞之后,產生了文化間的吸納、整合,于是,居住于壩區的彝族們較早、較快地接受了稻作生產。
1.稻作歷史
楚雄州的水稻產區主要集中于壩區,半山區次之。
《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其(指夜郎)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這種“耕田,有邑聚”的稻作民族,許多學者稱為“滇文化”,其范圍以滇池區域為中心,包括滇中、滇西的巍山、大理,滇西北永勝、寧蒗,以及滇南和滇東南的元江、澄江、廣南等地。可以肯定,稻谷是“滇人”的主要農作物。彝族農耕的歷史及其演變過程,是人類歷史進入到新石器時代的產物。據《彝州文物資料》記載:距今四千多年前,楚雄地區各部落先后步入新石器時代*據郭家驥著《西雙版納傣族的稻作文化研究》一書考證,云南新石器時代的發生年代遠遠晚于中原、長江中下游及華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發生年代。,先民們擇土地肥沃,水源豐富的地方定居,便于畜牧業和農業的發展。1972年至1973年元謀大墩子新石器遺址的發掘和1978年永仁菜園子新石器遺址的發掘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汪寧生在他的《云南考古》中也指出:“在一個火塘的陶罐中發現了大量的谷物炭化場,經鑒定屬于粳稻。”證明此地稻作民族的遠古居民中有彝族的先民,“他們種植粳稻,飼養豬、牛等家畜,并從事狩獵、捕魚和采集。”[24](P19)另據光緒《大姚縣志》卷二記載:“滇南多楚俗而大姚俗近江右,則入籍者吳人*吳人指百越的后裔。尤多也。”土族與齊民*土族指彝族,齊民指漢族。[25](P532)同尚勤儉,未有不耕之家……耕用雙牛然土薄而瘠,易生葵蓼,栽插一工而薅蕓之工倍之。卻苴*即永仁,當時大姚所轄。十六里用一牛,秋收較豐,亦較蚤……南界村屯夏秋易受水災,所恃惟麥,冬春種者尤多,山地種包谷黃豆,雖雨澤稍遲亦有收成。”這些資料表明,楚雄彝族的農耕文化發展到晚清近代,整體上是旱作與稻作并存。
2.壩區彝族的信仰
任何一段歷史,一種文化的發展都是承上啟下、一脈相承的。彝族的稻作文化也不例外,它的骨髓里帶有旱作文化的因子,從而形成了既區別于傍水而居的傣族稻作文化*作為百越后裔的傣族是最早馴化稻谷,最古老而典型的稻作民族之一,其稻作文化兼有原始宗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因素,如祈求雨水的“滴水”、“堆沙”等儀式活動。,又不同于創造了舉世聞名的梯田稻作文化的哈尼族。同為山地民族的彝族,其農耕文化整體上是旱作與稻作并存,稻作生產集中在壩區和部分半山區,融合了彝族古樸的原始崇拜和祖先崇拜,民眾把與稻作生產密切相關的水及其衍生物——龍集體想象為民族始祖,以期獲得庇佑,實現風調雨順、四季豐收的現實需求。
(1)水崇拜
水哺育了人類文明,使人類的生存得以延續,文明得以發展,同時在與水的互動過程中,關于水的觀念、禁忌、情感等通過認同、宗教、文學藝術、制度、社會行為等方式進行表達,形成了水文化。稻與水的關系是如影隨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二元一體關系。稻作文化的發展離不開水文化的孕育和滋養,所以,旱―稻兼具的生產方式,注定了彝族不僅有豐富的火文化,同時也有其獨特的水文化。彝族口頭文學和典籍中有著豐富的水神話,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大量與此有關的信仰習俗活動,呈現出精彩紛呈的復雜性和多元性。
彝族自古就有“人從水中出”,“人源于水”的說法。流傳于云南楚雄姚安、大姚、永仁、牟定等縣彝族地區的《梅葛》說:“天上撒下三把雪,落地變成三代人”。這與四川彝族地區的“人源于雪”大抵一致。云南烏蒙山區的彝文典籍《六祖史詩》則干脆說到:“人祖自水來,我祖水中生”。《六祖魂光輝》指出:“凡人是水兒,生成自水中”。
楚雄州武定的彝族在結婚時有潑圣水的習俗。姑娘們守在村口,待男方迎親的隊伍到來時便向他們潑水、澆水、灌水……寓意水能夠驅除污穢,帶來吉祥,所以小伙子們盡管全身濕透也仍然樂在其中。各地彝族也有對水神的祭祀習俗。
雨水的多少直接關系到農作物的豐歉,彝族認為水神是掌管水權的神靈,但水神的形象既抽象又模糊,所以水這個自然物被人們由抽象到具體地加以兩次想象處理,經過了水―水神―龍神的發展,最后產生了各種相關的祭龍求雨的習俗活動。[26]
(2)龍崇拜
在中國水文化中,龍的文化現象扮演著重要角色。龍是農耕民族集體想象建構出來的一位掌管雨水豐歉,處理旱澇災害的大神。人們的生產生活用水全仰仗龍的賜予,因而地位極重。農歷二月初二是龍抬頭日,各戶在水井邊祭獻龍王,集體步行到龍王廟祭奠龍王,為即將到來的開秧門等一系列農事活動祈求雨水充沛。
古代天子自稱龍族、龍顏,坐龍椅、穿龍袍,一切與他有關的東西都附上一個“龍”字,以示威嚴和正統。彝族也自認為人祖水中來,而且認為他們是“水中龍族”的子孫,這就使得彝族“水族后代”的觀念更加形象化、具體化了。彝族水文化以水崇拜為核心,而水崇拜又與龍崇拜息息相關。如果說彝族“人祖水中來”是人類起源的美麗神話,那么彝族“龍族”神話就是具體針對彝族本身族源問題。彝族崇拜龍,不僅僅因為龍神意味著甘霖雨露,對農作物收成有保障,更重要的在于他們認為萬物水中生,人祖水中來,彝族是龍族子孫后代的族源觀念。漢文獻《后漢書》中的《九隆神話》及在西南廣大彝族地區普遍流傳的史詩《支格阿龍》皆將其始祖追溯到龍。*概括地講,史詩是這樣追溯彝族始祖與龍的關系:遠古時候,天上飛著群龍,其中一條因妊娠落到地上,啟始了龍在地上的繁衍。地上的龍經歷了巖間、林中、江湖等一代又一代的變遷,最后一代來到了濮梭部(今滇池附近)這個地方,孕育了一位美麗的姑娘,成為人類的始祖。她的子女經歷了一代代的婚嫁過程,最后誕生了美麗的姑娘蒲莫列衣。有一天,天上飛來了神龍鷹,滴下三滴血,落在蒲莫列衣身上,她因此而懷孕,在龍年龍月龍日生下了支格阿龍。
楚雄州雙柏縣彝族在每年的第一個屬龍日要祭龍,第二天轉龍時要跳龍笙,人們分別裝扮成啞巴、牛、布谷鳥、龍女等,舞蹈內容多反映農耕活動。祭龍的地點在神圣的龍林,由龍頭主持,畢摩念請神經:“天神龍王,萬物你為王,風雨雷電,都歸你管,莊稼樹木都求你生長……”當念到:“今年雨水發了”時,龍神開始播雨,把盅內的水灑下,人們高舉著碗、瓢接“雨”,畢摩繼續念道:“正月雨水挖新溝,二月春分撒下秧,三月清明谷雨小秧綠,四月立夏小滿栽早秧,五月芒種夏至中耕忙,六月小暑大暑薅秧忙,八月白露秋分早谷黃,九月寒露霜降秋收忙,十月立冬小雪上皇糧……”龍神播雨結束,人們高興地將接到的“雨水”喝下。儀式結束后,全村男女老少一起跳龍笙,其間貫穿一系列的農事生產過程,以生產工具為道具,把放水、犁田、耙田、撒秧、栽秧、薅秧、收割、打谷等農事活動融入其中。[22](P41-43)
(3)作物儀式
在農業生產中,由于受自然界的約束,人們對自然界產生的一些現象不能理解,所以當地彝族從撒秧到收割歸倉,農業祭祀是一項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動,目的在于祈求老天爺保佑,使百姓人畜興旺,五谷豐登。

表2 河谷地帶彝族的農耕活動與祭祀禮儀
根據水利情況,撒秧時節分春分、清明、谷雨等時節。撒頭秧時一般要擇吉日,俗話說“懵里懵懂,石榴開花要下種”。撒頭秧時,撈起浸泡過的種子,先要打醋湯,以驅除邪氣,再到秧田邊打醋湯,使秧田干凈。在秧田進水口處插三炷香,插上石榴花。撒秧的人作揖叩頭,口中念一些吉利的咒語。撒完后,在田埂上坐上三鍋煙的工夫,確認秧種落穩才放心回家,若有漂種,說明有邪惡征兆,要驅邪潑冷水飯。
栽秧時必須獻田頭,在田的進水口處,都有固定的田公地母神位。捏上三砣泥巴搓成三角形,中間高,兩邊矮,表示三個神像。泥砣頂上罩上雞蛋殼,砍一枝三叉的松枝,插在泥砣前邊,泥砣上擺松毛,燒三炷香,獻飯。祭品有豬尾、雞蛋等,主人家作揖叩三個頭,祈求田公地母保佑糧食豐收。當栽完最后一丘田的秧時叫關秧門。屆時,在這丘田里舉行儀式祭祀田公地母,殺雞、獻飯,全家人一起燒香叩頭,獻畢回家。一路上主人唱著接魂語,把糧魂、畜魂帶回家。到家后,分別在大門上、供桌上、堂屋門上插上一炷香,插完后獻飯,關秧門祭祀結束。
獻田頭是祭獻土地神。農歷六月六日這天,祭祀土地神,祈求風調雨順,不下冰雹,為已經打苞的秧苗求豐產豐收。其說法有三:一是每株秧苗都長得像插的秧標一樣高;二是表示已經祭過土地神了,不會在這些地方刮大風、下暴雨、下冰雹;三是引來益鳥吃掉害蟲。然后,擺上貢品,祭獻的貢品因家境而定,富有的人家殺雞,煮豬尾巴獻給田公地母,這天全家人都去給田公地母磕頭,并在田頭吃飯,吃飯后由家庭主人在后,叫魂回家。貧者,獻田頭時,煮一碗飯,一個雞蛋,回來叫魂時,雞蛋放在飯碗上,回到家祭獻五谷六畜神。
七月初十“吆山”,實際是祭雷神。每年農歷七月初十這天,全村家家戶戶都參與,在老公山梁子祭奠雷神。梁子有一棵雷神樹,祭奠時在樹上擺上松毛,插上香火,用一只大黑山羊(這只山羊不能有雜毛,否則祭奠就不會靈,老天爺就會下冰雹)獻雷神。宰羊時鳴炮三響,羊肉煮熟后按全村戶數,連湯帶肉,每戶一份,費用原由伙頭從收支中出,伙頭制取消后由各戶分攤。“吆山”的目的是祈求雷神保佑全村歲歲平安、風調雨順,不刮惡風,不下暴雨,不打冰雹,保佑村民六畜興旺、五谷豐登。信眾們堅信,雷神看到他們的誠心,會庇佑他們,使他們的莊稼不遭遇冰雹。
嘗新,農歷八月初八,在牛王廟舉行。原由伙頭負責主辦,后來為各戶輪流舉辦。在人們吃新米的時候,首先要敬獻創造五谷的神農黃帝,故而舉行嘗新會。在神農黃帝、軒轅黃帝的像上掛上谷穗,獻飯磕頭,祈求神仙保佑人人平安,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祭土黃,按農業季節,土黃天為十八天,分為三個六天,土黃頭三天是霜降。進土黃那天嚴禁動土,第三天是接土,從自家田中撿來五叢帶土的谷樁,在堂屋東南西北各放一叢,正中放一叢,并在每叢谷樁上插上一炷香,中央那叢要劃成四丫,呈傘狀插在泥砣上,用一個新犁頭立在旁邊,把雞毛插在谷樁上,然后燒香、殺雞,進行祭祀活動。在家供奉半月后舉行送土儀式。送土時,煮好肉,在泥砣上插上香,放在篩盤里,經獻飯、叩頭后,端起篩盤送出大門外,送到田頭,把谷叢放到田里,祭土畢。土黃天的禁忌除了進出土黃那天不得動土外,在土黃天死了人也不能安葬,要等土黃天過完后才能入土。土黃天還不能理發,相傳若在土黃天理發,頭發會白,頭會搖。
從二月初二祭龍求雨水,打醋湯開秧門,祭拜田公地母保秧苗關秧門,到六月初六祭祀土地神求豐收,七月初十祭雷神求風調雨順,再到八月初八嘗新節,祝豐收,冬月祭土黃,土地進入輪歇狀態,為次年的耕種休養生息。祭祀鏈與稻作生產緊緊聯系,農業生產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各種祭祀儀式,農事活動與民俗活動融為一體,農耕類型決定了相應的文化形態。
三、結語
中國的民間信仰產生于民間的生產活動和村落生活。中國古代屬于耕讀社會,“承先祖一脈相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表明民間對耕讀的首肯。在統治階層那里,“民以食為天,國以農為本。”的農本思想同樣把農業的地位提到危及社稷安危的程度。所以,無論對社會大眾而言還是對統治階層來說,耕作的重要性都是無可厚非的,其地位也是無以替代的,于是便建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以耕作為核心的信仰體系。古代有官方組織的以天子為代表的祭天祭社稷的制度性儀式,今天有彌漫在民間的各式各樣的信仰。
不論是官方的社稷還是民間的宗教,不管是彝族的祭山神還是漢族的中秋祭月亮都是農業季節性慶典的社會衍生物,反映的基本上是自然界農作物的生長、衰落、收獲的節奏與民間信仰和儀式的時空對應與交流。祭山神、敬龍王、舞火把、潑圣水、甩龍笙、跳虎舞等儀式都是在特定時空基礎上圍繞耕作活動的進展和農作物的成長階段而展開的人神間信息交流的演習,同時也是對該地域范圍內的家庭和崇拜體系下的成員進行言行規范。“土地是財富之父,勞動是財富之母”人們藉由耕作這一勞動過程,在特別的土地上創造了別樣的財富。生態環境決定生計模式,生計模式塑造文化類型,文化又對該文化制度中的人起形塑作用。壩區和山區兩個文化地理單元中的彝族以滿足需要為原則建構起相應的信仰體系。
[1]張承宗,魏向東.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自然崇拜[J].襄樊學院學報,2000,(4).
[2]吳芬芬,徐小霞.殷墟甲骨文化影響之淺探——自然崇拜的力量[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4,(5).
[3]單曉琳.從《說文解字》“示”部字看上古的自然崇拜[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4]張強.從圖騰崇拜到自然崇拜:人與自然對話的走勢[J].南京師大學報,2001,(7).
[5]南文淵.古代藏族關于自然崇拜的觀念及其功能[J].青海民族研究,2001,(5).
[6]張文安.中國古代自然崇拜與自然神話的歷史考察[J].東北師大學報,2007,(3).
[7]張佐邦.自然崇拜與人類審美心理的生成——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08,(1).
[8]陳思蓮.海南黎族原始自然崇拜的哲學分析[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0,(5).
[9]楊甫旺.口頭神話與民間信仰——云南彝族馬櫻花神話個案研究[J].柳州師專學報,2002,(12).
[10]柴榮怡,羅一航.西南少數民族自然崇拜折射出的環保習慣法則[J].貴州民族研究,2014,(11).
[11]何燕霞.論云南少數民族自然崇拜與生態文明建設[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0,(4).
[12]戴波,蒙睿.云南彝族多樣性圖騰崇拜及生態學意義[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5).
[13]尹玉玲.論儒學對云南彝族自然崇拜的影響及其意義[J].湖北函授大學學報,2012,(11).
[14]饒遠.云南彝族體育與原始宗教關系初探[J].云南社會科學,1989,(2).
[15]楊宗亮.云南壯族的自然崇拜及其對生態保護的意義[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3).
[16]徐習文,謝建明.白族藝術中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J].藝術百家,2012,(3).
[17]袁伊玲,覃碧念,江興龍.自然崇拜在喀斯特生物群落維系中的效應——以荔波世界自然遺產地為例[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0,(2).
[18]Steward,Juliar H..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The Metho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M]. Champaign: Univ.of Illinois Press,1955.
[19]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0]李蓮,曹定安,李子賢.開遠市彝族傳統文化及其現代適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21](晉)葛洪.抱樸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2]陳永香,吳永社.論彝族的山神崇拜[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6,(2).
[23]朱映占.滇中香格里拉——雙柏[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
[24]屈建能.彝族崇虎溯源[EB/OL].http://222.210.17.136/mzwz/news/8/z_8_728.html,2006-11-12
[25]汪寧生.云南考古[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26]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
(責任編輯 劉祖鑫)
(楚雄師范學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楚雄 675000)
Farming and Faith of the Yi People of Chuxiong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SHAN Jiangxiu
(LocalCultureInstitute,ChuxiongNormalUniversity,Chuxiong, 675000,YunnanProvince)
Livelihood and living style determine our knowledge system, value system and faith system. A people mainly farm for livelihood, therefore, have their ideology bearing corresponding farming marks.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the Yi people came to possess the paddy field culture while preserving their traditional dry farming culture and, by doing so, have created a number of dynamic cultures - their faith system created by the Yi people living in both the mountains and the valleys striving for millennia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livelihood needs are met.
faith; farming; cultural ecology; the Yi people of Chuxiong
2016 - 10 - 07
單江秀(1981―),女,楚雄師范學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社會調查。
K892.29
A
1671 - 7406(2016)11 - 0084 -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