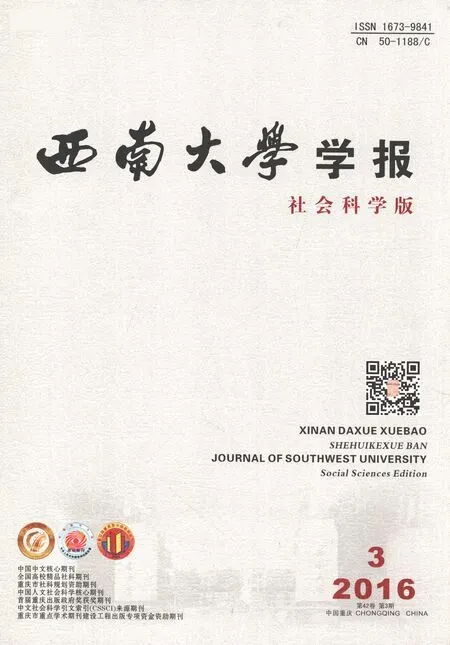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與統(tǒng)帥權獨立
張 東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近代日本的軍國主義與統(tǒng)帥權獨立
張東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摘要:明治維新后,日本為強化天皇統(tǒng)治,逐漸采取軍政分離原則,實現統(tǒng)帥權獨立,避免政黨勢力與民眾政治對軍隊的影響。統(tǒng)帥權獨立的精神構造與天皇制下的國民統(tǒng)治秩序密切相關,忠君尚武精神通過《軍人敕諭》等文本被內化為軍隊乃至國民的道德規(guī)范,對天皇權威的絕對服從與近代憲政精神明顯矛盾,統(tǒng)帥權獨立侵蝕明治憲政,促使近代日本在軍部主導下走向法西斯化。
關鍵詞:日本;軍政分離;統(tǒng)帥權;軍人敕諭;軍國主義;明治維新
日本在明治維新后推行軍國主義,以極端民族主義鼓吹侵略擴張,雖有《明治憲法》約束,但最終軍部能擺脫議會和政黨牽制進而主導政治裹挾整個國家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統(tǒng)帥大權直屬天皇,即統(tǒng)帥權獨立。國內學界對于近代日本侵略擴張的史實及其軍國主義思想已有深刻的批判性研究*代表性論述有:楊寧一,《日本法西斯奪取政權之路: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崔新京、李堅、張志坤,《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蔣立峰、湯重南,《日本軍國主義論》上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代表性論文:張景全,《二戰(zhàn)前日本的現代化與法西斯化》,《日本問題研究》2012年第1期;胡月,《論日本法西斯統(tǒng)治的“國民組織化”》,《沈陽大學學報》第22卷第5期,2010年10月;高洪,《戰(zhàn)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的精神專制》,《日本學刊》2005年第4期;張勁松,《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思想專制述論》,《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構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朗維成,《日本法西斯主義運動之探討》,《外國問題研究》1986第2期;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形成及其特點》,《世界歷史》1984年第6期;張義素,《日本軍國主義教育及對國民意識的影響》,《日本學刊》2005年第4期;崔世廣,《日本近代家族制度與軍國主義的內在聯系》,《日本學刊》2005年第4期。,但遺憾的是,對于統(tǒng)帥權獨立這一重要問題卻無探討,本文即從統(tǒng)帥權獨立的過程、精神構造及其對明治憲政的侵蝕等方面做一考察,以期深化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
一、明治前期的軍政分離
1867年12月,巖倉具視等人發(fā)動政變,實施“王政復古”,廢除攝政、關白及幕府大將軍等朝幕要職,新體制設總裁、議定及參與三職,其下設有九課,陸海軍務課既掌行政亦主統(tǒng)帥。1869年7月,明治政府進行官制改革,軍務官改為兵部省,但其職掌未有根本變化。1871年7月,明治政府再行官制改革,兵部省職掌有明顯變化,一是兵部卿權限加入“征討發(fā)遣”,明確軍政及統(tǒng)帥兩權;二是兵部省內設陸軍參謀局,以“省內別局”的形式掌管軍令,此為參謀本部之淵源,統(tǒng)帥權獨立已有萌生;三是兵部卿資格為“本官少將以上”,兵部大輔及少輔資格“本官大佐以上”及“本官中佐以上”,并限定為武官充任[1]219-220。1872年2月,兵部省廢止,分設陸軍省及海軍省。此時僅陸軍分為軍政和軍令,海軍尚非如此,并且參謀局仍從屬于陸軍卿,軍政軍令在陸海軍卿統(tǒng)理下維持一元化,并無獨立之統(tǒng)帥機關。1873年1月,明治政府施行征兵制,其詔書及告諭中顯示,近代日本軍隊乃基于皇國“古制精神”,同時“民兵之法乃自然之理,非偶然所為,而其制斟酌古今時宜,參照西洋諸國數百年來研究之實踐”[2],征兵可謂“自然之理”,而具體建制則“參酌時宜”,當然,采取軍政分離、維持統(tǒng)帥權獨立也是“參酌時宜”之結果。那么,當時是怎樣的“時宜”促使其走向軍政分離呢?1873年10月,“明治六年政變”(征韓論政變)發(fā)生,不僅使明治政府發(fā)生分裂,也對近衛(wèi)兵產生了很大影響*近衛(wèi)兵,之前叫御親兵,1872年3月改名,由薩摩、長州、土佐士兵組成,其中,鹿兒島、高知的士兵十分推崇西鄉(xiāng)隆盛與板垣退助,大多支持征韓論。。西鄉(xiāng)隆盛回到鹿兒島后,在京都的薩摩藩士兵多有追隨之意,陸軍少將桐野利秋、筱原國幹是其代表人物。桐野提出辭職,在沒得到批準下擅自回到鹿兒島,筱原等人也紛紛效仿。10月25日,德大寺實則奉命向陸軍少將筱原國幹、陸軍中佐白戶隆盛等人下達天皇御旨,其中,筱原稱病未能入宮。29日,德大寺再次奉命召筱原等一百四十多人入宮,筱原依然稱病,其他士兵也多有稱病拒絕的。多數鹿兒島士兵辭職或者回藩,明治政府擔心士兵過激行為,所以并未嚴厲處置。
實際上,此時軍中違紀、犯罪等問題時有發(fā)生,當時報紙稱軍人“好色貪酒,酩酊大醉而高聲放歌,在街市上大搖大擺妨礙行人,掩飾己非,向警官行兇”等[3],軍人被認為沒有紀律、廉恥和愛國心,甚至擾亂社會秩序。從犯罪數量上來看,1874年-1876年間,兵員人數幾乎沒有增減,但是士兵犯罪數量卻從70起劇增到了1 000起。1876年,相繼發(fā)生熊本敬神黨之亂、秋月之亂、荻之亂等士族叛亂,軍紀問題成為明治政府的一大難題。在此期間,即征韓論政變后,在征韓論中下野的板垣退助、副島種臣、江藤新平等人相繼投入政治運動,并在1874年1月提出《民選議院設立建白書》,開展自由民權運動,軍中問題與自由民權運動密切關聯。
1877年2月,西南戰(zhàn)爭爆發(fā),雖政府最終獲勝,但暴露了軍隊組織、教育及訓練的不足,尤其是指揮官戰(zhàn)斗指揮能力的欠缺,參謀組織被認為急需強化。而且,土佐立志社等有協助西鄉(xiāng)的傾向,立志社領導林有造、大江卓等在1877年2月請板垣退助回土佐,計劃與陸奧宗光等舊紀州藩士族聯合,借西南戰(zhàn)爭之機推翻政府而實現立憲政體,但這一動向被政府察覺而失敗。自由民權運動與西鄉(xiāng)隆盛一派的關聯使明治政府產生高度警惕,明治政府開始著手強化軍紀、加強對軍隊控制,防止自由民權思想“侵入”軍隊。西南戰(zhàn)爭剛一結束,東京就發(fā)生了“竹橋事件”,竹橋的近衛(wèi)兵及東京鎮(zhèn)臺炮兵隊士兵200多人殺死上級并攜帶武器向赤坂皇居進發(fā),原因是西南戰(zhàn)爭時立有戰(zhàn)功卻未能行賞,甚至待遇還降低了。雖然近衛(wèi)兵和鎮(zhèn)臺兵將此鎮(zhèn)壓,但軍隊秩序的紊亂、士兵素質低下以及對命令的無視等突顯出來,引起了政府、軍隊當局的強烈關注。
因此,在1878年10月8日,陸軍卿山縣有朋提出建議:“陸軍事務分兩大類,政令和軍令。政令由本省奉行,軍令則由參謀局專任,”“明治七年六月設置陸軍參謀局,至今已有四年,雖有成效卻未能充分擴張本職。陸軍創(chuàng)設十年有余,而參謀局不過四年,時間尚短,其間又有多事掣肘,陸軍政令諸規(guī)漸已確立,學術技藝早有進步,而作為陸軍根基的參謀局尚無相應發(fā)展,”因此,“相對我國陸軍政令之進步、歐洲陸軍參謀局之體裁,我國政令軍令有失平衡,”“如今的參謀局不足以稱其為明治十一年之參謀局,不足以稱為日本帝國之參謀局。”[4]11月,在陸軍省定額金之外,增加25萬日元擴充參謀局,12月5日,廢參謀局而設置參謀本部,山縣有朋任參謀本部長,統(tǒng)轄各監(jiān)軍部、近衛(wèi)兵及鎮(zhèn)臺參謀部。之前的參謀局從屬陸軍卿,而參謀本部則從陸軍省獨立出來,管制“軍中機務、戰(zhàn)略動靜、進軍、駐軍、調軍命令、行軍路程、運輸方法、軍隊發(fā)差等”相關軍令,“參與軍令制定,在天皇親裁之后,軍令由陸軍卿發(fā)出施行,”[1]226-227參謀本部長直屬天皇,是統(tǒng)帥權的最高輔弼機關,優(yōu)于陸軍卿而與太政大臣地位相當*此時海軍并未如此,直到1893年5月,海軍設置軍令部,與陸軍參謀本部相對等。。也就是說,明治政府為維持軍紀,防止自由民權等對軍隊的影響,逐漸采取軍政分離原則,軍隊統(tǒng)帥權直屬天皇。1880年4月5日,明治政府發(fā)布了《集會條例》,其中第七條“陸海軍人及常備預備隊人員、警察、官立公立私立學校教員學生、學業(yè)工藝見習生等不得參加議政論政之講壇集會,亦不準入社”[5],明令禁止軍人參與政治論爭,全面禁止軍隊干預政治。明治政府實施軍政分離,一則保證軍隊的獨自性,不受政局變動影響,更可防止不久后到來的政黨及民眾力量;二則保障政府的穩(wěn)定性,避免軍政不分、軍隊變動影響政局穩(wěn)定。但很明顯,統(tǒng)帥權獨立的最終目的則是維護和加強天皇統(tǒng)治。
二、統(tǒng)帥權獨立的精神構造
從制度上將統(tǒng)帥權從政府中分離出去,并未能充分保證其穩(wěn)定性,還必須在精神層面將之內化為道德規(guī)范。而其內化軌跡又是與天皇統(tǒng)治的強化密切相關,在此過程中,《兵家德行》、《軍人訓戒》和《軍人敕諭》是養(yǎng)成軍隊忠君服從精神之規(guī)范文本。1878年上半年,西周在陸軍將校俱樂部偕行社做講演,后結成《兵家德行》。其后10月,山縣有朋發(fā)布《軍人訓戒》,起草者即為西周。而1882年《軍人敕諭》,其發(fā)起者為山縣有朋,起草者仍為西周。
《兵家德行》主要關注軍隊將領的素質:一是講求規(guī)律的“節(jié)制”,二是道德上的“德行”。對于軍紀的養(yǎng)成,西周首先考慮到的是“節(jié)制”。而這個“節(jié)制”不是“用理性來壓抑欲望”,而是“創(chuàng)造”一個“體系”或者“規(guī)則”,使軍隊士兵“自覺”進入這一“體系”或者“規(guī)則”當中,使他們實現自己對自己的“節(jié)制”。因為近代軍隊更注重整體配合、集團作戰(zhàn),軍隊秩序非常重要,“指揮千軍萬馬亦猶如大將一人之活動手足,因此可將這體系下的士兵成為節(jié)制之兵”[6],強調了士兵紀律性。而紀律性的養(yǎng)成有賴于對“服從”的認可,因此,服從精神十分關鍵,通過服從精神產生一種規(guī)則和體系,并將之內化到士兵的精神世界。而要創(chuàng)造這樣一種“體系”或者“規(guī)則”,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完全基于軍隊自身,因為,若是生硬地用另一種精神體系來維持軍隊的話,士兵從社會進入軍隊、再從軍隊進入社會,不免會有“割裂”之感,反而不利于紀律和秩序的養(yǎng)成,所以,要創(chuàng)造的“體系”或者“規(guī)則”也必須要與社會有某些共通之處,或者說它們是社會規(guī)則在軍隊內的延長,也只有這樣,才能養(yǎng)成真正的“天皇的士兵”、“天皇的軍隊”。西周將日本人固有之“性格習慣”引入軍隊將領之“德行”,一方面是“有所為”,另一方面是“有所不為”,也就是“忠良易直”,將此四字特性延伸開去,就變成了軍隊整體的“德行”和獨特“風貌”。而在明治維新之后,整個日本的社會風貌、經濟秩序和民眾心理都發(fā)生了變化,軍隊亦受影響。西周將明治維新帶來的變化分為三個部分:民權家風、狀師家風、貨殖家風。“民權家風”就是辛勤勞作而使國家富強、進而實現自身的自治自由;“狀師家風”則是主張自身權利,但這一傾向易流于詭辯狡詐;而“貨殖家風”則是民眾勤于貨物錢財,但是,軍隊需講求秩序、服從,這些社會風氣都是應該避免的,這樣一來,西周就將軍人“德行”與社會“風尚”區(qū)別開來了。
而《軍人訓戒》則是在1878年“竹橋事件”后發(fā)布的,當時是以山縣有朋的名義發(fā)布,但普遍認為是西周起草的。它首先講的是軍隊的必要性和現狀,接著指出維持軍人精神的三大要素:忠實、勇敢、服從,高揚武士對主君的忠誠,強調武士對主君的忠誠和軍人對天皇的忠誠,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基于士族叛亂和對抗自由民權運動的,指向性比較明顯。
《軍人訓戒》共有18條,其中,第9條“軍人從列入軍籍之初,就應當有奉戴皇上、忠于朝廷之心”,強調對天皇的崇拜和忠誠;第2條“根據陸海軍服,服從軍隊秩序,行相應禮節(jié),對部下威嚴,但要講求禮讓老功者”,也就是要尊敬上級、年長和在軍隊資歷深者,從而強化階層間的服從和連帶關系。其中還有“私議憲法,討論朝政是非,諷刺誹謗政府布告等言行,與軍人本分相違背”、“動輒憤慨時事,唱民權之義,這些都不是軍人本分,身為武官卻如處子橫議之狂態(tài),此為不可,應深以為戒”[6],提到對民權運動的防備,禁止軍人參與政治。可以看出,《軍人訓戒》為《兵家德行》中所講“節(jié)制”與“德行”的具體化,繼承和擴展了武士道精神,以軍隊內階層秩序為基調強化軍人對天皇的忠誠,防備民權運動等社會風尚對軍隊的“侵入”。
1882年1月,《軍人敕諭》發(fā)布,當時主要是為了防止軍人對政治的參與和強化軍人對天皇的忠誠。《軍人敕諭》有五個德目:盡忠節(jié)守本分;正禮儀;崇尚武勇;重信義;以質素為旨,而貫穿五個德目的是對天皇的忠誠。實際上,這些并不是軍人獨有之道德精神,而是基于日本一般社會風習之道德。《軍人訓戒》開頭提出“如何維持軍人精神”,稱“不過是忠實、勇敢與服從三者,是為維持軍人精神之三大基本”[7]。最重要的是,“敕諭”是天皇作為軍隊大元帥而對軍事教育發(fā)布的一種帶有絕對命令性格的“軍令”形式,它將封建武士道德作為近代軍人道德而復活,將之作為絕對的近代日本軍人思想性格,不僅僅是對軍隊的要求,而且逐漸作為道德約束向國民侵入,以忠節(jié)觀念為核心的向天皇的絕對獻身被視為最高的道德價值。這種觀念隨著士兵的回鄉(xiāng)而被傳播開來,逐漸變成國民道德,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主化發(fā)展。
在1932年《軍人敕諭》發(fā)布50周年紀念會上,有講話提到“(軍人敕諭是)不僅軍人,一般國民也應遵奉之國民道德”、“敕諭不僅是針對軍人的,對一般人也提出了應有之道,帝國之民皆應遵守之道”[6],道出了《軍人敕諭》與《教育敕語》的連帶性,《軍人敕諭》不僅是對軍隊秩序的強化,也是對一般國民的道德約束。這體現出西周構建和創(chuàng)造服從的“體系”、“規(guī)則”的初衷——不是把軍隊作為獨立于社會的封閉的秩序體系,而是將其“規(guī)則”與一般社會溝通、連帶起來,進而將軍隊的服從秩序返回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去。從政治上來講,《軍人敕諭》明確了天皇對軍隊的統(tǒng)帥權,表面上是樹立了軍人不干預政治的非政治化,但在現實中卻不能實現。實際上,敕諭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就是將軍隊置于天皇親率之下,成為明治政府的支柱,脫離行政干預,不管以后議會中民權勢力有多大優(yōu)勢,都不會影響軍隊的統(tǒng)帥權,而軍隊則可容易地通過武力威懾和鎮(zhèn)壓民眾。這其實是對憲法體制的一種政治對抗。軍政分離的統(tǒng)帥權獨立,引發(fā)了后來的國家二元分裂。《軍人敕諭》將天皇統(tǒng)帥權從思想上具體化,成為了二元分裂國家意識形態(tài)上的支柱,確立了統(tǒng)帥權的不可侵犯性。在通過《軍人敕諭》完成軍隊的非政治化之后,卻用天皇制國體來教育軍人,又將軍隊重新政治化,逐漸成為頑固的絕對專制勢力和超政黨的存在。
三、統(tǒng)帥權獨立對明治憲政的侵蝕
1889年2月,《明治憲法》中明確了天皇的統(tǒng)帥大權。然而,近代憲法以責任和分權限權為根本之義,這與統(tǒng)帥權中的絕對忠誠和服從相矛盾。那么,憲法解釋如何來彌合統(tǒng)帥權獨立與近代憲政間的分離呢?而這種矛盾又會生發(fā)怎樣的弊端和后果呢?統(tǒng)帥權獨立又是如何侵蝕明治憲政的呢?
(一)統(tǒng)帥權獨立的合憲化解釋及其破綻
對于天皇的統(tǒng)帥大權(第十一條),《憲法義解》中稱:“中興之初,天皇發(fā)親征詔書,總攬大權,改革舊有兵制,洗除積弊,設帷幄本部,親帥陸海軍,光復祖宗遺烈,本條即指兵馬統(tǒng)一大權專屬天皇大權,屬帷幄命令,”[8]以傳統(tǒng)為由維護統(tǒng)帥權獨立,甚至連提出“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達吉也同樣以“古有舊制”來承認統(tǒng)帥權。
實際上,《明治憲法》中并無關于統(tǒng)帥權獨立的明確規(guī)定,但“一國憲法絕不僅只是指憲法條文,憲法制定前的歷史傳統(tǒng)、憲法條文之外的法律法令、事實性習慣等,都是構成一國憲法之材料,日本的軍隊制度產生于憲法制定之前,軍隊本來就不歸太政官或內閣管轄,而憲法不過是繼承此制度而已”[9]95。對于統(tǒng)帥權問題,美濃部認為,“天皇大權并非是基于憲法而產生,它是自古以來在歷史中形成的,憲法不過是以成文法形式將之明確化。”[10]221除了皇室大權與祭祀大權,天皇大權在憲法上都有規(guī)定,但根據“輔弼機關及責任歸屬”,可分為三種,一是國務大權,需國務大臣輔弼;二是統(tǒng)帥陸海軍的軍令大權,由軍令機關輔弼;三是榮典授予大權。統(tǒng)帥大權不屬于國務,由“帷幄機關”獨立輔弼,這“并非憲法條文所定,只是沿用和維持了憲法制定前的實際習慣及官制”[10]322。而且,美濃部引用《憲法義解》中的說法,承認“兵馬統(tǒng)一乃至尊大權,專屬帷幄大令”,并從軍事本身解釋:“軍隊統(tǒng)帥是針對現在或假想敵軍,以充分發(fā)揮軍隊戰(zhàn)斗力為目標,這就需要軍隊自由靈敏快速活動,不允許局外者掣肘,因此,若有國務大臣參與軍事的話,或可能削弱軍隊戰(zhàn)斗力。因此,從我國憲法習慣上說,軍隊與國務有所分別,軍事行動在國務大臣輔弼責任之外,這也是國法上的兵政分離原則。”[10]322美濃部將日本的統(tǒng)帥權獨立稱為兵政分離主義,“國家統(tǒng)治大權與陸海軍統(tǒng)帥大權相分離,統(tǒng)帥權不屬內閣職責,國務大臣也不對軍事負責”、“兵權和政權皆屬天皇大權,只是輔弼天皇的機關分離。國家統(tǒng)治大權由國家元首天皇總攬,國務大臣任輔弼之責,議會有相應權限,而陸海軍統(tǒng)帥大權由軍隊大元帥的天皇總攬,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等輔弼天皇,議會無干預之權”[9]93。當然,在美濃部看來,兵政分離的前提是兵政兩權皆屬于天皇,所謂分離只是負責機關上的分離,“軍令權與軍政權皆屬軍事大權,但二者性質有別,軍令權是指軍隊的統(tǒng)帥權,由天皇作為陸海軍大元帥親自掌握。憲法第十一條‘天皇統(tǒng)帥陸海軍’指的就是軍令權。軍令權區(qū)別于一般國防,一般國防是由國務大臣負責,而軍令權是天皇作為大元帥而施行,在國務大臣的輔弼之外。軍令權的輔弼機關由元帥府及軍事參議院作為中央軍令機關,陸軍中有參謀本部、海軍中有海軍軍令部。但軍政權不屬于統(tǒng)帥之權,它是維持軍備、向國民發(fā)出命令、支出國費之權,與一般行政作用相同”[11]。
美濃部承認統(tǒng)帥權獨立是基于兩點認識:一是事實性習慣,二是天皇總攬軍政軍令大權。當然,美濃部也意識到了統(tǒng)帥權獨立的弊端,指出:“兵政分離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明確兵權和政權的界限,但其界限在憲法及其他法令中并無明確規(guī)定,只能根據實際習慣而定,所以常有論爭,也會引起政治上的困局,”[9]97他自己也承認,兵權與政權之間的界限難以斷然分清。
事實上,在承認統(tǒng)帥權獨立的同時,卻要對它加以限制,并防止它干預政治,美濃部的這種“理想狀態(tài)”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的日本人通常并不認為統(tǒng)帥權是違憲的,大多數人都以事實性習慣為由將統(tǒng)帥權獨立合憲化了。但吉野作造對此觀點持批判態(tài)度,明確主張參謀本部與海軍軍令部是違憲的制度,他認為:“國防用兵作為統(tǒng)帥之事而與普通政務分離的話,這將妨礙國權統(tǒng)一。戰(zhàn)爭時期自當另說,但在和平時期,國權應維持統(tǒng)一,”“我們應從憲法條文及其精神來斟酌事實性習慣及其附屬法規(guī)的合理性,絕不能將軍令權置于國務輔弼的范圍之外。”[12]25-26
吉野也承認統(tǒng)帥權獨立有其歷史上的因由,但是“現代國務復雜繁多,不可能由一人獨裁,所以才會有大臣輔弼,統(tǒng)帥權當然也一樣。人們以統(tǒng)帥權乃親裁大權為由將之置于大臣輔弼之外,但實際上卻設置有元帥府、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等機構,嚴格上說,如果統(tǒng)帥權不能有別的機構介入的話,那就應該首先撤廢這些機構。所謂統(tǒng)帥權獨立,實際上是忌諱文官大臣的輔弼責任,名義上是天皇親裁而不由大臣輔弼,但實則是職業(yè)軍人專權,以致造成軍事輔弼機關與國務輔弼機關之間的嚴重對立”[12]27-28,吉野從國家統(tǒng)治的合理性上反駁了美濃部等人的說法。
(二)陸海軍大臣造成的政府分裂
純粹的統(tǒng)帥事務稱為軍令,但實際中統(tǒng)帥事務與軍政事務難以截然分開,例如軍隊編制和國防計劃等,這些“交叉事務”可稱為軍機,所以統(tǒng)帥權獨立一般被稱為軍機軍令。但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等統(tǒng)帥機關軍隊編制和國防計劃等只是計劃性的,并不涉及具體的施行,若要施行的話,就必然會牽涉國家財政,這就需要內閣商議。也就是說,統(tǒng)帥權獨立的真正實施,還需統(tǒng)帥機關與政務機關的協調,而居間協調的重要一環(huán),便是陸海軍大臣。陸海軍大臣在國務大臣中有特殊地位,不但作為國務大臣統(tǒng)管軍政,還作為統(tǒng)帥機關有帷幄上奏之權。理論上說,純粹的統(tǒng)帥事務不屬于國務大臣輔弼,因此陸海軍大臣不應干預統(tǒng)帥事務,但實際上,統(tǒng)帥權命令在受到天皇裁可后轉到陸海軍大臣,然后再向軍隊下達命令。1885年12月22日的《內閣職權》第六條:“各省大臣應及時向內閣總理大臣報告所轄事務,但軍機事宜由參謀本部長直接上奏,陸軍大臣將其事件報告內閣總理大臣,”[13]確定了參謀本部長的統(tǒng)帥機關地位以及陸軍大臣的特殊地位。在1889年的《內閣官制》第七條中,同樣規(guī)定軍機事宜除了天皇要求下達內閣的,由陸海軍大臣報告內閣總理大臣。統(tǒng)帥機關與政府之間有陸海軍大臣做溝通,內閣官制亦明文確認此事實。
但問題是,內閣是流動性的,受民眾輿論及議會狀況等要素的牽制,所以在陸海軍大臣協調統(tǒng)帥機關與內閣的時候,為了確保統(tǒng)帥機關的獨立性,陸海軍大臣也必須要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而其途徑便是陸海軍大臣的現役武官制。1891年,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曾就此問題上奏:“為保持立憲君主制而防止大權下移的話,就不能將國家兵權委于議會或者政黨,”“若君主直轄,管理軍政的大臣就不能隨政黨搖擺,與普通政治家相比,軍事上受磨練精于軍制軍律軍人狀況的職業(yè)軍人對于軍制組織來講更為合適。”[14]但隨著政黨實力增強,議會中開始有討論廢除軍部大臣武官制。大正時期,山本權兵衛(wèi)內閣改正陸海軍省官制,削除了陸海軍大臣資格中的現役規(guī)定,除了現役大中將,預備役、后備役以及退役者皆有資格,擴張了任用范圍。但改正僅止于文字,實際上出任陸海軍大臣的仍是現役軍人。陸海軍大臣的特殊性明顯違背了國政統(tǒng)一的原則,有違內閣制度的根本精神,必然造成政府分裂。而且,統(tǒng)帥機關直屬天皇,不負憲法責任,而國務則是有憲法責任的,當統(tǒng)帥機關以天皇權威強硬時,就會侵蝕掉憲政精神,通過陸海軍大臣造成政府的分裂,將國務逼迫至被動地位,甚至將之綁架,軍部進而主導國政。
在大正期,由于國內外的民主風潮,民眾對政黨政治有一定的希求和認同,反對軍部對政治的干涉。而進入昭和期,政黨腐敗等顯露,民眾對政黨持批判和否定態(tài)度,軍部藉此愈加強硬,以民眾排斥政黨的輿論為背景,在政治上增強發(fā)言力度。尤其是“五一五事件”后的齋藤實內閣,雖標榜舉國一致,但軍部比重明顯增加。“二二六兵變”后,1937年2月,廣田弘毅組閣,軍部發(fā)言權更加增大。對于廣田內閣的最初組閣方針,軍部表示不滿,原定陸相的寺內壽一發(fā)表聲明,“新內閣負有打開空前時局之重責,必須要有根本刷新內外時弊、施行國防充實的積極強力國策之氣魄和實行力。不能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現狀維持或者消極政策而妥協退讓。以積極政策刷新國政,這是全軍的一致愿望,妥協退讓不能收拾全局,不僅會令事態(tài)糾紛,還會遺留禍根。不符合如此要求的內閣,能夠克服內外非常時艱嗎,”[15]4對廣田內閣表示懷疑。廣田內閣瀕臨流產。廣田與寺內數次交涉,變更最初組閣方針,發(fā)表新的聲明:“眼下皇國形勢,打開時局需一新舊有弊政,自主積極調整國際關系。此次事件發(fā)生,也使吾人覺得此時需大革新。因此,政黨、軍部、官僚應舉國一致去除積弊,樹立強固國策,閣員人選不拘泥于地位、閱歷,聚集體認時局、有報國至誠之士,一致團結施政,對上奉答圣旨,對下不負時勢期望。”[15]8也就是說,軍部在民眾輿論背景下,以其特殊性增強自身政治地位,并逐漸掌握政治主導權。而在1936年5月,陸海軍大臣資格再次恢復現役將官,從山本內閣的官制改正以來,也僅20余年。
結語
為強化天皇統(tǒng)治,近代日本采取軍政分離原則,避免民眾政治對軍隊的牽制,統(tǒng)帥權獨立于政府而直屬天皇,天皇既是元首又是大元帥,軍隊絕對服從天皇權威。忠君尚武精神又通過《軍人敕諭》等文本灌輸而內化為道德規(guī)范,并擴展至整個國家社會。軍機軍令不受政府干預,經天皇親裁后“回歸”政府而最終實施,這期間需要統(tǒng)帥機關與政府內閣充分溝通協調,造就了陸海軍大臣在內閣中的特殊地位,統(tǒng)帥權獨立必然會侵蝕明治憲政。在整個日本對外擴張的狂熱與執(zhí)著下,隨著戰(zhàn)爭擴大和局勢惡化,軍部更主導政治,將整個國家導向戰(zhàn)爭體制。統(tǒng)帥權獨立與天皇統(tǒng)治密切相關,是近代日本強化軍國主義、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重要一環(huán)。
參考文獻:
[1]山崎丹照.內閣制度の研究[M].東京:高山書院,1942.
[2]渡辺幾治郎.明治天皇と軍事[M].東京:千倉書房,1936:22.
[3]亙理章三郎.軍人勅諭の御下賜と其史的研究[M].東京:中文館書店,1932:63.
[4]徳富豬一郎.公爵山県有朋伝:中卷[M].東京:山県有朋公記念事業(yè)會,1933:785-787.
[5]秋元安平編.行政官吏必読[M].東京:第晩翠舎,1882:26.
[6]岡本晴行.軍人勅諭と西周[J].龍谷大學大學院研究紀要,2010(3).
[7]由井正臣.日本近代思想體系4軍隊兵士[M].東京:巖波書店,1996:164.
[8]伊藤博文.憲法義解[M].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35:28-29.
[9]美濃部達吉.日本憲法の基本主義[M].東京:日本評論社,1934.
[10]美濃部達吉.憲法撮要[M].東京:有斐閣,1932.
[11]美濃部達吉.憲法講話[M].東京:有斐閣,1912:81-82.
[12]吉野作造.二重政府と帷幄上奏[M].東京:文化生活研究會出版部,1922.
[13]鈴木安蔵.太政官制と內閣制[M].東京:昭和刊行會,1944:138.
[14]春畝公追頌會.伊藤博文伝:中卷[M].東京:原書房,1970:788-790.
[15]國民経済新報社.軍人の政治干與と広義國防[M].東京:國民経済新報社出版部,1936.
責任編輯張穎超
網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23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簡介:張東,歷史學博士,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中圖分類號:K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6)03-018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