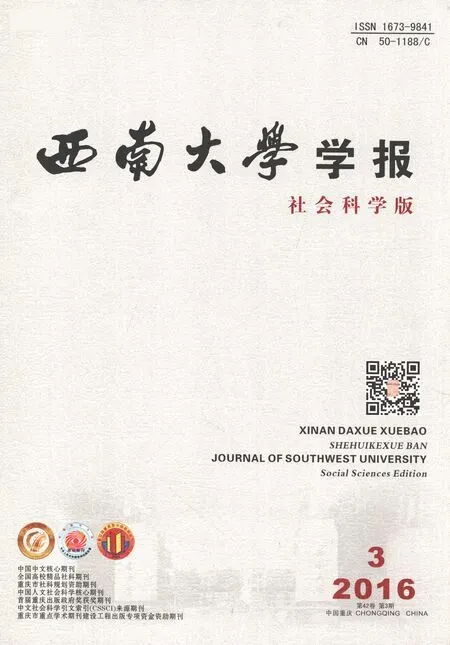現代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興起的歷史考察
李 昕
(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重慶市 400715)
現代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興起的歷史考察
李昕
(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重慶市 400715)
摘要:現代南非白人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指以荷蘭人為主的歐洲白人殖民者后裔為了維護和擴大自身特權,和英國爭奪殖民利益而展開的一系列政治活動。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南非白人經過和英國之間一個多世紀的爭奪,終于將英國排除在外,獨占了南非的統治權。南非白人的民族主義帶有非常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占南非總人口極少數的白人,為了確保自身在南非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的統治地位,建立了復雜而系統的統治結構,從而將不平等的民族和種族關系格局固定下來。這種殖民主義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關鍵詞:南非;白人;英帝國民族主義;殖民主義;荷蘭
南非地處南半球,位于非洲大陸最南端,北鄰納米比亞、津巴布韋和莫桑比克等國,東、西、南三面瀕臨印度洋和大西洋。南非占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航運要沖,其西南端的好望角航線歷來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有“西方海上生命線”之稱。荷蘭殖民者最早開始了在南非的殖民活動。在此后的三百多年時間里,歐洲白人以開普敦為起點不斷擴張,將土著黑人從他們的土地中驅趕出去,建立起對這片土地的殖民統治。以荷蘭后裔為主體的歐洲白人慢慢定居下來,開始繁衍生息。在這個過程中,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歐洲白人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逐漸融合,一個新的民族正在形成[1]1-48。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非洲當地出生的白人在其總人口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他們開始將自身視為本地人而不是外來的殖民者。正因為如此,他們自稱為阿非利卡人(Afrikaner,意為非洲人*即阿非利卡人(Afrikaner)。1652年,荷蘭人占領好望角,建立開普殖民地,之后大量荷蘭人以及少量受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教徒和德國新教徒來到這里,他們的后裔在共同生活中逐漸形成了統一的種族,被稱為布爾人(Boer,意為農民),但他們自稱為阿非利卡人(Afrikaner,阿非利卡語意為非洲本地人)。)。本文將嘗試梳理從大遷徙(Great Trek)到1948年南非國民黨當選執政的南非白人民族主義發展的歷程。正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南非白人民族主義從萌發到日益高漲,南非白人也成為了這片土地的主宰者。以荷蘭后裔為主體的歐洲白人移民通過和英國之間一個多世紀的爭斗獨占了南非的統治權。這既是英帝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體現了殖民主義給非洲大陸帶來的深重災難。考察這一歷史進程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殖民主義以及英帝國的了解。
一、南非白人民族意識的覺醒(1830年代-1880年代)
19世紀初,英國取代荷蘭成為開普殖民地的統治者[2]40-41。后來的英國政府以及英國殖民者與原有的南非白人之間在觀念和現實利益方面產生了諸多的矛盾[3]。和英國當局之間的沖突,使得南非白人開始建構和強化自身的身份認同,民族意識開始覺醒。
英國人和南非白人的沖突始于對南非地區統治權的爭奪。英國在占領開普之后,便要抹去荷蘭殖民者對這里的影響。英屬開普當局先是宣布英語為官方語言,接著又向南非白人征收高額捐稅,同時停用荷蘭盾改用英鎊,在南非白人用荷蘭盾兌換英鎊時還故意低估荷蘭盾的幣值。這一方面幫助英國政府建立了對開普地區的統治權,另一方面也使得兩者之間的矛盾變得尖銳起來[4]3-4。
英國當局與南非白人的矛盾還體現在如何對待土著人的問題上。此時英國想要在南非地區推行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度,因而反對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度,這直接影響到了它與南非白人的關系[5]。英國殖民當局確立了對開普地區的統治后,英國國教的傳教士來到這里,并在開普地區建立傳教農場,把土地分給脫離部落的土著。他們在取得經驗后又將這一類農場進一步推廣開來。接著英國殖民當局又借鑒在印度的統治經歷,招募大批土著充當警察。黑人在開普地區還獲得了到新設置的巡回法庭狀告歐洲主人的權利。到了1815年,一向被南非白人認作奴仆的科伊桑人“甚至”得以以警察的身份來逮捕這些自認為是主人的“白人老爺們”[6]。英國政府的政策引起了南非白人的極大不滿,他們認為這“把我們的奴隸置于與基督徒平等的地位上,這完全背離了上帝的律法和種族、膚色存在天然區別的規律。對于任何正經的基督徒而言,這都是不可忍受的枷鎖,我們因而寧愿撤離以保護我們律法的純潔”[7]。1833年,英國國會通過了釋放奴隸的法令,開普地區四萬名奴隸在法律上成為自由民,給予了南非白人奴隸主最為沉重的打擊[8]3-6。
另一項引起南非白人憤怒的是英國政府推行的土地政策,他們通過各種手段想要強取豪奪土著黑人的土地,英國政府的政策卻壓制了他們的野心。英國政府在殖民地內部推行的教育政策深受英國國教的影響,這又與南非白人自身的加爾文宗信仰形成了沖突[9]。雙方矛盾愈演愈烈,南非白人在1795年、1799年和1815年連續發起暴動,但由于雙方力量差距過大,全都被英國殖民政府鎮壓。
南非白人的不滿情緒日漸強烈,但又清楚地認識到不可能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為了擺脫英國的束縛,大批南非白人決定向東部和北部邊境地區遷徙,開始了南非白人歷史上的“大遷徙”(the Great Trek)時代。在1830-1840年間,大約有15 000南非白人拓荒者離開開普地區。1834年英國在整個帝國范圍內廢除奴隸制之后,南非白人建立在奴隸制之上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被徹底動搖,于是更多南非白人加入到向北遷徙的行列中[2]49-54。在一路向北的過程中,南非白人先后建立了納塔爾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和德蘭士瓦共和國三個國家[2]77-79。
從大遷徙到建立國家,南非白人由于拓荒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難變得更加團結,相互之間的認同也不斷加強,民族意識開始萌生。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首先表現為語言的統一,由于南非地區的人口來源復雜,僅白人就包括荷蘭人、德國人和法國人。荷蘭語、德語和法語也長期并存。這幾種語言相互影響,最終在19世紀中期形成了一種新的語言——阿非利卡語(Afrikaans)。19世紀70年代,一場“語言運動”(Language Movement)于開普地區發端,進而擴展到整個南非地區。這場語言運動一直延續到英布戰爭,運動的鼓吹者們通過利用阿非利卡語寫作、翻譯《圣經》、辦報紙等方式來盡可能的擴大阿非利卡語的影響。杜托伊特(S. J. du Toit)還在1876年擬定了最早的阿非利卡語語法規范和阿非利卡語教材[10]。1878年,這場運動又擴展到政治領域,在揚·霍夫梅爾(Jan Hofmeyr)的領導下,多個南非白人團體向議會請愿,要求在官方活動中有權自由使用阿非利卡語。1882年德蘭士瓦議會通過立法,允許在議會兩院活動中選擇阿非利卡語進行發言[11]。
南非白人民族意識覺醒的另一個表現則是其有意識地將宗教和其民族發展歷程相結合,神圣化自身的經歷從而人為建構起關于本民族的神話。按照南非國民黨領袖馬蘭的說法,“南非白人的歷史是長久以來最偉大的杰作。我們之所以在這個國家占據統治地位應歸結于造物主(Architect of the universe)的意志”[8]1。基于這種理念,整個南非白人民族的歷史被建構成一種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Christianity-Nationalistic ideology)。南非白人民族形成過程中的某些歷史事件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例如里貝克于1652年到達開普,胡格諾教徒由于在母國受到宗教迫害來到這里等被認為是上帝的意旨,開普殖民地草創時期的艱苦歲月則是孕育了南非白人的團結與獨立精神。在這種敘事中,南非白人被定義為由源自西歐的加爾文教徒所構成的民族,受到主的感召,才來到了這里。因此,他們在這里理所應當地享有種種特權。大遷徙被拿來和摩西帶領人民出走埃及(Exodus)進行類比。南非白人把自身比做受暴政迫害的猶太人,反映了其受害者的心態以及對于英國的敵視;同時也給自身加上了追求自由的光環,試圖證明其在大遷徙過程中占據土著土地和建國的合法性[12]。就這樣,依靠著語言和宗教,南非白人初步建立起對自身的身份認同。
二、現代南非白人民族的形成(1880年代-1910年)
十九世紀末,英國和南非白人之間的矛盾加劇,這直接導致了英布戰爭的爆發,戰爭的失敗使三個南非白人共和國喪失了獨立地位,但也使原本分裂了的南非白人重新聯合了起來,促進了現代南非白人民族的形成。十九世紀后期,奧蘭治自由邦的奧蘭治河兩岸地區發現了儲量巨大的鉆石礦。1884年德蘭士瓦又發現了巨大的金礦。1886年,在瓦爾河和林波波河河源之間的威特沃特斯蘭德地區,又發現了世界上蘊藏量最為豐富的金礦——蘭德金礦。蘭德金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礦,含金礫巖礦脈東西綿延80公里,南北寬達30公里。它于1887年投產,8年時間里產量從1.2噸增占到62.7噸,而此時全世界的黃金年產量也不過400噸左右。1885年,德蘭士瓦的黃金產量僅占世界黃金總產量的百分之零點三,到1898年時,已超過了世界總產量的四分之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黃金出產國[1]174。這一地區不再是往日荒蕪的不毛之地,于是英國殖民者開始蠢蠢欲動,想要擴大在這一地區的殖民擴張,和南非白人沖突也隨之而來。
英國的壟斷資本力量試圖憑借著資本的優勢大肆收購金礦,想要盡可能地占據金礦所帶來的利益。而資金有限的南非白人則想要依靠政治的力量,通過實行壟斷經營和強化對采礦相關產業的審批權等辦法來予以回擊。雙方圍繞著礦區所有權、鐵路建設、礦業征稅和關稅政策等問題,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斗爭[4]8-11。
黃金開采業的飛速發展,有力地帶動了相關的鐵路建設、運輸、食品以及炸藥制造等產業的迅速發展,使得德蘭士瓦地區的經濟開始了工業化進程。這改變了南部非洲地區的經濟形勢,使這一地區的經濟中心由南部的開普地區向北方轉移。隨著黃金產量的激增和經濟的繁榮,德蘭士瓦不僅一舉擺脫了財政困難,還野心勃勃地開始向外擴張。德蘭士瓦當政的白人企圖建立起從林波波河到開普地區整個南部非洲地區的霸權。他們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的準備。他們向由英國資本控制的礦業公司征收重稅,阻止英國移民入境,并嚴格限制已入境的新移民的政治權利。德蘭士瓦政府還暗中購買大批軍火:向德國克虜伯公司訂購大炮,又向柏林列維公司訂購步槍。1895-1898年,進口步槍達到四萬枝之多。1897年,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共和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1898年又成立聯邦會議。這些行動威脅了英國在這一地區的地位,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利益。為了爭奪這一地區豐富的礦產和遏制南非白人的擴張,英國不斷進行挑釁,最終導致英布戰爭于1899年爆發。經過為期三年的戰爭,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戰敗,最終向英國投降。
英布戰爭是南非歷史上的轉折點。戰爭使得南非白人想要獨霸南部非洲地區的想法落空了。戰爭之后,原本獨立的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喪失了獨立的地位。1906年英國自由黨上臺后,實行了與南非白人和解的政策,先后準許德蘭士瓦和奧蘭治成立自治政府。為了建立統一的市場,加強彼此在交通、關稅和貿易方面的合作,以及加強政治上對土著黑人的統治和壓迫。四個英屬殖民地于1910年聯合起來,在得到英國議會批準后成立了南非聯邦[13]。
英布戰爭使南非白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高漲。在南非白人看來英國通過戰爭剝奪了他們的民族獨立和自由,戰敗后原四個殖民地聯合成立的南非聯邦也受到英國政府的束縛和壓制,因此南非白人對于英國政府和英國人充滿了敵視。這種敵視的直接反應就是其民族意識的高漲。在為期三年的英布戰爭中,不僅是德蘭士瓦和奧蘭治的南非白人,連開普殖民地的南非白人都聯合成一體對抗英國人,有1.3萬來自開普的南非白人參加了南非白人軍隊。戰爭結束后,原本為“邊界”隔開的四個殖民地在政治上成為一體。此時居住在南非的南非白人已經超過60萬,遠遠超過了英裔白人的數量,他們信仰同樣的宗教——新教加爾文宗(Calvin Reformed Church)。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變得更愿意講阿非利卡語,從1914年起,阿非利卡語成為學校教學用語,1919年成為教堂用語,1925年后同英語一樣,成為南非兩種官方語言之一。大量用阿非利卡語創作的反映英布戰爭和戰后生活的小說和詩歌也受到熱烈地歡迎。而在開普,那些戰時為英國人當差的南非白人則遭到當地居民的鄙夷[1]206-207。
就這樣,有著相近的語言、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的南非白人,借著英布戰爭這一契機,依靠對于英國政府和英國人的仇視形成了統一的民族認同,迅速地向現代南非白人民族邁進。
三、南非白人統治權的最終確立(1910-1948)
英布戰爭的失敗使南非白人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南非白人的民族主義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這反過來也給了南非白人民族主義發展的契機。正如南非學者丹·奧米拉所指出的:“南非白人民族主義有一種受害者心態,他需要給自己造一個妖魔化的外部敵人”。[14]這種受害者的心態在政治上有著巨大的影響。英布戰爭后,各個南非白人政黨都不同程度地將英國人妖魔化以動員大眾來提高自身的影響力。即使是相對溫和的史末資也表示:“一個聯合起來的南非將(給南非白人)帶來最大程度的自由,但前提是來自唐寧街的影響能夠最終被消除,……我們必須能夠自主安排我們的政治生活、我們的行政和立法活動,這樣我們才能將殖民地人民身上最優秀的部分結合以更好地建設國家,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終走向政治上的獨立”。[15]南非白人精英利用民眾對英國的敵視,成功地加強了民族凝聚力,推動了民族主義的高漲,最終確立了自身對南非的獨占統治。
南非聯邦成立后,南非白人精英雖然都主張要擺脫英國的束縛,壟斷南非的統治權,但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也有分歧。以博塔和史末資為代表的溫和派一方面強調要保護南非白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對南非和英國之間的實力差距有著清醒的認識,同時還想借助英國的資本和技術來推動南非的發展。而以詹姆斯·赫爾佐格(James Hertzog)為代表的強硬派則迫切地渴望排除英國對于南非的影響,讓南非白人單獨控制南非。[16]雖然兩派在維護南非白人民族利益這一根本點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處理和英國關系的分歧上仍舊造成了嚴重的紛爭。溫和派最初占有優勢,隨著時間推移,強硬派慢慢占據了上風,并最終取得了勝利。
南非建國沒多久,南非白人內部矛盾就由于一戰的參戰問題激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英國政府要求南非進軍德屬西南非洲,消除德國在南部非洲的影響力。南非白人的領袖們的意見完全對立,博塔和史末資支持英國對抗德國,德拉雷(J. H. de la Rey)和貝葉斯(C. F. Beyers)以及德懷特(C. R. de Wet)反對。德拉雷和貝葉斯指出英國一直是南非白人的敵人,而德國則是唯一在英布戰爭時支持南非的國家,他們質疑南非政府為何要支持英國而反對德國。他們的觀點很有代表性,相當一部分南非白人反對向德國宣戰,甚至在南非內閣和政府中也有許多人反對。強硬派代表德懷特和貝葉斯領導了一場叛亂,結果被博塔和史末資毫不猶豫地鎮壓[2]283-285。這導致了南非白人中溫和派和強硬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嚴重[2]19。與此同時,雖然叛亂很快被鎮壓,激進派的影響力卻不降反升。雖然德懷特在叛亂中死去,其他叛亂領導者在之后也被判處徒刑,但他們卻成了普通南非白人眼中的英雄,甚至是殉道者。這種影響力的上升直接體現之后的幾次選舉中激進派的選票不斷增長,直至1924年赫爾佐格贏得大選。
赫爾佐格登臺后,作為一個老練的政客,他清楚地認識到此時南非完全不具備與英國相抗衡的實力,因而并未嘗試使南非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更多的是努力擴大南非白人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力,以及采取其它一些具有象征意義的措施來滿足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的需要。他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1.象征性措施。為了滿足南非白人的心理需求,從1924年起,南非郵票上不再印有英王喬治五世的頭像,1925年建議英王不再向南非籍公民加封貴族稱號,1927年通過《國旗法》,以南非國旗與英國國旗并掛。2.語言。1925年南非議會正式決定以阿非利卡語取代荷蘭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英語仍為第一官方語言)。3.外交關系。在1926年倫敦帝國會議上各自治領均希望不受其與倫敦政府關系的影響,控制自己的對外政策并確定自治領的確切性質,赫爾佐格政府表現得尤為積極。當英國和各自治領還沒有就自治領的外交決策權問題達成一致時,南非政府引人注目地于1927年設立外交部,1929年開始派駐外交機構。在英國和各自治領共同簽訂《威斯敏斯特條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后南非政府又立即宣布加入國聯。總之,赫爾佐格努力在英國政府能夠接受的范圍之內加強南非的獨立性。雖然這種獨立性更多是形式上的,但對于提高南非白人民族的民族主義熱情,建立南非白人個體對于本民族身份認同仍舊有著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國旗,對于民族國家構建的作用是不可小視的。國旗做為主權的組成部分,意味著南非雖然在法律上仍舊從屬于英國,政治和經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國的控制,但在形式上它和英國是分離的。正如后來的南非總理馬蘭(D·F·Malan)所指出的:“國旗不僅僅是一塊布,它象征著國家的存在,它是有生命的,蘊含了民族的情感。國旗將與國家同在。為了國旗,一個民族可以英勇抗戰,甚至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17]
到了三十年代初,經濟危機蔓延到南非,并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動蕩。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強硬派和溫和派不得已進行合作,先是兩派的代表政黨國民黨和南非黨組建了聯合政府,赫爾佐格和史末資分別擔任總理和副總理,接著兩黨又進行了合并,組成了“南非民族主義者聯合黨”(United South African Nationalist Party,通常簡稱為United Party,即統一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南非再度面對一戰時曾出現過的困境:英國于1939年9月3日向德國宣戰,而南非白人內部也由于參戰問題再一次陷入分裂。赫爾佐格認為南非應當選擇中立,但史末資卻主張南非向德國宣戰。在9月4日的投票中,南非議會以80票贊成67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史末資的提案,赫爾佐格隨即宣布辭職,史末資接任總理,溫和派看起來再一次占據了上風[18]162-163。
二戰結束后,溫和派很快再次喪失了優勢地位。馬蘭帶領國民黨在1948年大選中擊敗史末資的統一黨,得以組閣執政。在此次大選中國民黨的優勢很小,甚至都沒達到上臺所需的半數(總共153席,過半應為77票),僅僅是在得到了南非白人黨(9票)的支持后才得以上臺。[2]710當時和后來都有許多人認為國民黨的勝利有一定偶然性,不僅是國民黨的議席優勢很小,而且統一黨的總得票數其實比國民黨還要多12.5萬張。*南非當時的議席分配中,人口較少的鄉村地區獲得的議席比例高于其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此前史末資作為南非最高領導人和英帝國戰時內閣成員之一帶領南非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他本人還是《聯合國憲章》的起草人之一,在南非的威望高。然而國民黨的上臺自有其社會根源。二戰使得南非白人內部發生嚴重分裂。部分南非白人大資產階級和英裔白人支持史末資加入盟國一方作戰。在戰爭中,他們通過向盟國輸出軍火等工業產品和及煤、木材等原材料以及食品發了大財。但與此同時,南非白人中的小農場主和工人階級卻陷入了困頓,他們成為民族主義極端派的支持者,擴大了強硬派的社會基礎。[19]這種變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馬蘭以及他率領的國民黨在大選中贏得了超過80%的南非白人選民的選票,成為整個南非白人民族的代表。[20]
馬蘭非常清楚國民黨為何能夠贏得大選,他因此組建了南非歷史上首個完全由南非白人組成的內閣[2]377-379。這標志南非白人從此開始獨掌南非政權,并且繼續努力縮小英國的影響爭取獨立。在英布戰爭之后,南非白人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努力,終于再度控制了這片土地。正如馬蘭在贏得選舉后所說的:“在過去,我們就好像是自己國家中的陌生人。但今天,我們再一次成了南非的主人。南非是我們的了,這在聯邦歷史上還是第一次”[18]186。
綜上所述,現代南非白人民族主義的興起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英國控制開普地區之后,其推行的許多政策與南非白人的利益相沖突,南非白人開始了大遷徙時代,并建立三個獨立國家;其次是十九世紀中后期隨著黃金的發現引起了南非白人和英國的矛盾漸趨尖銳直至英布戰爭爆發;最后是英布戰爭之后,南非白人開始嘗試在英國控制的政治框架下進行各種政治活動,具體表現為通過廣泛進行政治團體的抗爭和聯合,一步步地鞏固和擴大手中的權力,直至最后獨掌政權。通過對這段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南非白人民族的形成,實際上是以荷蘭裔為主的歐洲白人移民通過多種形式的政治活動來為自身追求特權的過程。南非白人的民族主義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民族主義有著很大的不同,它所追求的并不僅僅是本民族的獨立自主。無論是早期的大遷徙和建立共和國,還是南非聯邦建立后的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的爭奪,其最終目標都是建立自身對南非的獨占統治。他們從來都是將自身看作是這片土地的主宰者,而不是諸多民族中平等的一員。這種民族主義的實現是建立在對其他民族的奴役基礎之上的,因而有著非常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從數百年的殖民過程中,南非白人掠奪土著人的土地,將他們變成奴隸,直至后來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種族隔離制度,這些都是殖民主義給非洲大陸帶來的深重災難。
在南非白人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一直面臨著英國殖民者的競爭,如何處理和英國之間的關系成為南非白人民族主義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由于受到英國殖民勢力的壓制和束縛,南非白人的利益受到了很大影響,英布戰爭后南非更是直接成了英國的殖民地,因此多數南非白人對英國都極為不滿甚至是仇視。這種情緒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在南非白人政治勢力內部的歷次分化和整合當中,無論強硬派的力量遭受了怎樣的打擊,總能夠靠著民眾的支持迅速地恢復和壯大起來,而南非白人民族主義整體上也變得越來越激進。最終在1948年的大選中,國民黨在其領袖馬蘭的領導下,以反英和種族主義為競選主張,成功地擊敗溫和派領導人史末資領導的統一黨,從而成為南非的執政黨。從此,南非白人中最激進的右翼勢力牢牢把持了南非的政權,殖民主義的毒害也繼續延續下去。
參考文獻:
[1]鄭家馨.南非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DAVENPORT R, SAUNDERS C. 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M]. 5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3]KIEWIET C.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24.
[4]張謙讓.英布戰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3-4.
[5]DUBOW S. Rac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elaboration of segregationist discourse in the inter-war years[M]//Marks S, S. Trapido. Politics of Race , Class and Nation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Essex: Longman, 1987: 71-94.
[6]劉海方.論阿非利卡人的形成與南非種族主義的關系[J].西亞非洲,1999(6):48.
[7]DE KLERK W. The puritans in africa[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6: 33.
[8]MOODIE T. The rise of afrikanerdom, power, apartheid, and the afrikaner civili religion[M]. Berk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9]GILIOMEE H. The beginning of afrikaner ethinic consciousness, 1850-1915[M]//Vail L.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1-27.
[10]SUZMAN M, Ethnic nationalism and state power, the rise of irish nationalism, afrikaner nationalism and zionism[M].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31-35.
[11]PATTERSON S, The last trek, A study of the boer people and the afrikaner nation[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7: 49-54.
[12]PROZESKY M, JOHN W. De gruchy. The living faith in south africa[M].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Ltd, 1995: 27-55.
[13]楊立華.南非[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73-75.
[14]O’MEARA D. Forty lost years: the apartheid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ational party, 1948-1994[M]. Johannesburg: Raven Press, 1996: 476.
[15]HANCOCK W. Smu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99.
[16]WILSON M, THOMPSON L.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M]. Vol.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16.
[17]South Africa, State Information Office. A nation and its leader: Life and policy of Dr. D.F. Malan,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M]. Pretoria: State Information Office, 1952: 5.
[18]THOMPSON L.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M]. New He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2-163.
[19]O’MEARA D. Volkskapitalisme: Class, capital and ide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kaner nationalism, 1934-1948[M].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5-233.
[20]Stultz N[M]. Afrikaner Politcis in South Africa, 1834-1948. Berk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150.
責任編輯張穎超
網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22
收稿日期:2015-10-18
作者簡介:李昕,歷史學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中圖分類號:K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6)03-01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