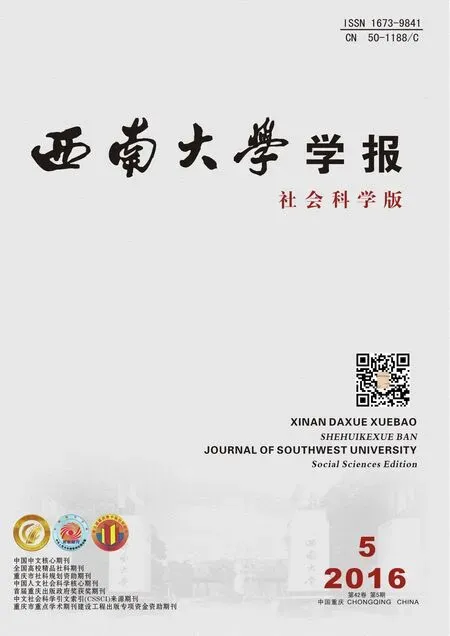發現底層*
——1990年以來中國階層研究的進路與轉向
魏 程 琳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
發現底層*
——1990年以來中國階層研究的進路與轉向
魏 程 琳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社會階層結構被打破重組,以農民、農民工、城市失業低收入群體為主的底層社會逐漸形成,但它并未自始進入社會學階層研究的視野。隨著貧富差距日益拉大,底層抗爭行為日益突出,孫立平等人于1990年代末提出“社會斷裂”理論,這標志著底層社會正式進入階層研究者的視域;然而,幾乎所有學者都將底層社會視為上層(精英)社會形成的必然結果,止于道德化的判斷和呼吁,并且迅即告別底層轉向城市(中產)階層研究。針對學界階層研究的理論貧瘠和經驗困惑,一些學者做出了重返底層的努力,他們重提“階級范式”、面向底層社會經驗,試圖從中提煉出本土化的階層概念和分析框架,以解讀和回應中國社會發展變化中的問題。
底層社會;階層研究;中產階層;社會斷裂;階級范式;本土化;村治研究
階級階層研究是社會學領域中經久不衰的命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馬克思以生產資料占有狀況為標準將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社會沖突理論[1];韋伯則強調生活機會的不同產生的階層地位差異,他指出階級的真正故土在經濟制度里,身份群體的真正故土在社會制度里,政黨的真正故土在權力領域里[2]。后來學者對馬克思的一元分層論和韋伯的多元分層論進行了綜合。吉登斯[3]指出階級是在生產領域中形成的,階級關系的直接結構化包括三個方面:在生產企業內部的勞動分工,企業內部的權威、權力關系以及“分配群體”的影響;而階級的間接結構化則依賴于階級成員共享的消費和行為模式的程度。布迪厄通過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研究指出“消費者的社會等級對應于社會所認可的藝術等級,也對應于各種藝術內部的文類、學派、時期的等級。各種趣味(tastes)發揮著‘階級’(class)的諸種標志的功能”[4]。以上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階層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面臨著何種問題?
1978年以來,中國民眾經歷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全方位的變革,社會分層機制由原來的政治身份變為市場經濟,社會階層結構被打破重組,階層研究隨之興起,相關文獻已是汗牛充棟。在國際研究中較有代表的是倪志偉[5]的市場轉型論,他指出在市場轉型與改革中,共產黨干部相對于私營企業主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隨后,邊燕杰和羅根[6]、周雪光[7]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干部權力在市場經濟轉型中并未受到損害,而是以各種形式發揮了持續的影響。遺憾的是,國內外學界研究多停留在宏觀機制變遷、上層精英和城市中產階層上,忽略了在中國存在的巨量底層社會群體。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至今仍有9億戶籍農民,其中有2億農民工往返于城鄉之間,這個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穩定與否,因而關注底層和農村農民是階層研究的必然進路。總體上看,1990年代以來社會學界對底層社會的研究經歷了發現—遺忘—重返三個階段。本文在回顧既往文獻的基礎上展示各階段研究的不足,并在底層社會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做一展望。
一、發現底層:社會的分化與斷裂(1990-2005)
1980年代末,社會學者逐漸關注社會分層問題。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擺脫傳統階級理論的束縛,在研究中用多元分層理論取代一元分層理論,用“階層”取代“階級”。九十年代前期,研究者主要關注對現實問題的描述和分析。1995年李培林主編的《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8]成為1990年到1995年社會分層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匯總。在書中,李培林指出,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并不必然加劇不平等現象,收入差距并未達到兩極分化的程度。陸學藝1992年主編的《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9]則重點考察了農村社會的變遷,他指出農村社會發生了階層分化,根據職業、生產資料和經營形式可以將農民劃分為8個階層。1990-1995年的階層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階層狀況的整體分析上,并未關注到分裂社會中的底層群體。
1990年代中后期,經濟體制改革令所有人受益的階段結束,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逐漸凸顯,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突出。1994年分稅制的實行促使地方政府加強了對農村的汲取力度,農民收入增幅下降,官民沖突日益加劇,加之國企改革造成大量城市失業群體、半就業群體,城鄉社會出現大批底層貧困人群,底層社會逐漸形成。張宛麗[10]指出,經濟改革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和社會階級階層的全面分化,市場上的佼佼者——私營企業主進入研究者的視線。李路路[11]認為,中國私營企業主的生產方式是精英再生產和精英循環相結合的。戴建中[12]進一步指出,1988年以前的私營企業主大多來自體制外的社會階層,1992年以后出現的私營企業主顯示出越來越多的體制背景。孫立平[13]從宏觀的視角對以上現象進行了總結,他指出總體性精英和上層社會的形成大致分為四步:1.雙軌制與官倒:1980年代中期在“雙軌制”背景下出現了“官倒”現象,大規模的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進行轉換;2.第三梯隊干部:80年代末,第三梯隊干部選拔強調年輕化和知識化,老干部子女成為重點提拔對象;3.“下海”: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講話后,隨之發生官員“下海潮”,這次下海以“圈地運動”為契機,以政治權力為基本媒介;4.“買文憑”:高校為了彌補辦學經費不足,開始賣文憑,而有權有錢之人正需要文憑作為文化象征資本。由此一來,上層精英融匯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本于一體形成了總體性精英,并對社會形成總體性壟斷,影響政策的走向。
2003年,孫立平“斷裂”[14]理論的提出,可以看做是社會學階層研究發現底層社會的標志。孫立平借用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的比喻,表述了中國社會分層的狀況,即從一個金字塔形變為一場馬拉松賽跑,每跑一段,都有人被甩在結構之外,他們甚至不能構成社會結構中的底層。90年代資源重新集聚的直接結果就是:一個具有龐大群體的底層社會在中國形成了,中國社會發生全方位的斷裂,由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失業貧困人員組成的底層社會,給中國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挑戰。同一時期,李強對農民工這一城市邊緣人群體進行了研究,他指出農民工在城市不但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而且遭到排斥和歧視、遭受著“多階剝奪”[15],農民工群體很大程度上決定城市社會的穩定。
社會學強調社會效益,關注社會公平,“發現底層”是社會學領域階層研究的必然進路。從分層理論探討到中國社會分層現狀的整體分析,再從精英群體的形成到發現底層群體,社會學的階層研究逐漸下沉。然而,該階段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在社會學者的理論分析中,底層社會在相當程度上是作為上層社會形成的結果和附屬物,隱含著一個假設,即上層精英的形成和集聚必然造成平民的沉淪和底層社會的形成。所以,社會階層研究在發現底層社會之后,停留在呼吁國家政策予以關注的層面,并未對底層社會作進一步的研究,底層社會作為一個抽象物存在著。
二、遺忘底層:城市和中產階層研究的興起(2005-至今)
1995年以來,西方分層理論和概念分析工具被廣泛引用到中國分層研究中來,社會分層研究的文獻迅猛增多,但這些研究大都局限在專門的、微觀的或者局部的理論驗證或者修正方面,缺乏明晰的問題意識和理論建構能力。社會分層研究在短暫發現和會晤底層社會之后迅速撤離,轉而聚焦到城市社會和中產階層上來。這種視線的轉移,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諸多學者對底層社會的思考止于抽象的貧困和苦難;第二,城市社會更加便于運用西方理論和分析工具。
城市社會階層研究的主題較為廣泛,涉及階層結構、階層意識、消費分層、社會網絡、階層政治等各個方面。李強[16]指出,城市與農村有著不同的社會結構:第一,城市下層群體比例并不高,介于下層與中層之間的群體比例較高;第二,城市有明顯的中間階層群體;第三,資產階級與上層階級的界限不十分清晰。以階層享有的再分配權力、尋租能力和市場能力的差異,劉欣[17]將城市市民分為十大階層,由高到低依次是:1.有技術的權力精英;2.無技術的權力精英;3.國有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4.私營企業主和經理;5.高級專業技術人員;6.低級專業技術人員;7.職員辦事人員;8.自雇者;9.技術工人;10.非技術工人。仇立平[18]通過數據分析指出,上海雖然已經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但它的社會分層結構仍然是“金字塔形”,主要是因為城市化過程中有大量低端勞動力流入上海。以上研究表明,農民和農民工并未進入城市社會階層結構之中,城鄉二元結構在階層流動中仍然發揮著作用。相比農村,城市社會的階層分化結構較為明晰,并在文化消費品位等方面形成了分層,“階級內部以及階級間的分層逐漸地不僅有賴于職業差別,而且也有賴于消費和生活方式的差別”[19]。布迪厄的文化區隔理論以及讓·鮑德里亞和齊美爾的消費理論在中國分層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除此之外,學界還從階層意識的視角關注了城市社會的階層關系,張翼[19]指出階級(階層)認同是一個對社會沖突意識極其顯著的變量,對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可能并不來自于客觀階級所劃定的社會底層,而來源于那些在客觀階級的秩序中地位并不低,但相對剝奪感較強的那些人群。
中產階層是社會分層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學者大都在一個前提假設上展開討論,即中產階級階層在政治上較為保守而且能夠緩和上層和下層的矛盾,因而是社會發展的穩定器、“社會行動的指示燈、社會矛盾的緩沖帶”[20]。不少學者對此提出反對意見。如亨廷頓[21]認為,最早出現的中產階級往往是都市政治的制造者,在傳統社會轉變為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一個中產階級政治參與水平很高的社會,很容易產生不安定”。李普塞特[22]也指出,如果中產階級在擴張過程中,其話語和社會行動空間被約束和壓制,或者其階級意識不能被上層建筑所整合,聽任其以“亞文化”方式蔓延,則其所導致的反彈會日趨激烈,這時政治動蕩就會生成。中國學者對中產階層研究的結論也頗為多樣。李友梅[20]指出,表面看來相似于西方白領階層的上海白領群體,不但與社會管理體制之間缺乏溝通,而且對國家的社會管理體制缺乏深度認識,白領的社會功能值得懷疑。張翼[23]也指出中產階層的社會批判意識漸趨明顯,在政治上并不保守,中產階級不必然是社會的穩定器。陸學藝[24]則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多,白領階層迅速形成,上層和底層社會的比例將會縮小,中國將可能形成一個以中產階層為主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李春玲[25]認為,盡管強烈的個人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使得中產階級喪失了責任意識,但是中產階層總體上還是發揮了穩定器的作用。面對研究結論的多樣性,李路路[26]主張從動態的視角觀察不同環境下中產階層所發揮的不同社會功能。學界對中產階層的研究未達成一致意見的根源在于,在劇烈變動中的中國,中產階層正在形成但并未形成,中產階層本身就是一個復雜多樣的群體,其政治態度是多樣的,其社會功能當然也無法確定。
從精英群體到城市中產階層,社會學的階層研究在意外發現底層社會之后,又在高歌猛進中長期遺忘了底層,直到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將農村社會的穩定功能凸顯出來,農村底層社會才再次引起廣泛關注。在階層研究學者放棄、遺忘底層社會這一陣地時,政治學、人類學學者并未遠離底層,他們引入西方抗爭政治理論和斯科特的“弱者的視角”理論在多個方面取得重要進步,例如近年來興起的上訪研究、訴苦研究,社會學領域的階層研究急需底層視角的歸來。
三、階級歸來:底層研究的復蘇(2005-2010)
2005年前后,學界在階層研究中重提“階級”范式或引入印度底層學派理論[27]。趙書凱[28]對底層理論在中國的應用給予很高評價。他認為底層研究的視角和分析框架有利于對抗頑固的精英話語、有利于政府把握和引導基層政治的走向、有利于農村政策的檢驗和矯正。王慶明[29]則對印度底層研究的知識譜系做了探討。他指出印度底層研究是在批判后殖民主義意識形態、反抗精英史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一種重塑底層歷史的努力。中印兩國不同的轉型背景使得印度底層理論和分析框架在中國的運用非常有限,與斯科特的生存倫理、弱者的武器、隱藏的文本等概念被廣泛運用到社會學研究相比,印度底層研究理論在中國基本上是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存在的。
在馬克思階級理論被遺棄近20年后,學界重新出現了“將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30]、“重返馬克思”[31]、“重返階級分析”[32]的呼吁。當然,現代階級分層理論是一種經過改造、既傳統又現代的分析視角,說它傳統是因為它沿襲了馬克思的階級分層理論,說它現代是因為它融匯了解構主義、消費主義、符號主義等后現代理論思潮。在這方面,沈原、潘毅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沈原[30]認為,處于兩次大轉型交匯點的中國社會正在進行重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工人階級正在再形成,有必要將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面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學者不僅要研究知識分子、上層精英、政府和官員的角色和作用,更應該將目光移向底層,研究農民、工人和其他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和歷史命運”。潘毅[33]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階級歷史”被國家和市場取代,農村務工人員涌入城市為全球資本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打工妹標志著一個由市場、國家和社會三方共同影響無產階級化的新時期的開始,她們在工廠用“尖叫”[34]等形式進行著“機靈的反叛”,翹首以盼“階級分析”的歸來,預示著階級的重生。2009年1月,潘毅、盧暉臨、嚴海蓉等學者[35]開會研討農民工問題時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農民工是改革的產物也是改革的創造者,認為“農民工回到農村進行勞動力再生產的提法”是極其錯誤的觀點,因為農村的土地養活不了農民,城市離不開農民工,農民工的道路只有走向無產階級化。
此外,與潘毅等人不同的是,仇立平、馮仕政等人強調階級的合作而非沖突。仇立平[31]認為,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研究主要采用三種范式——市場經濟、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利益群體,總體上缺乏關系性的社會分層研究;馬克思階級分層理論關注的是問題的深層結構,韋伯的多元分層理論關注的是表層結構,因而只有找回階級分析范式才能為階級合作做好理論準備。馮仕政[32]認為,馬克思和韋伯的分層理論的差異不在于深層和表層結構,而在于前者是沖突論的,后者是功能論的;前者關注社會剝奪和集體抗爭,后者關注低位獲得和市場形勢;1990年中后期以來的中國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失衡,社會不平等現象日趨嚴重,有必要重新引入階級分析范式,綜合使用兩種分層理論以對中國社會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分析。
在西方社會,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失去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基礎,資本主義和技術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國內顯示出一種在工業文明的先前階段聞所未聞的聯合和團結,這是在物質基礎上的團結”[36]。那么,中國孕育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土壤還存在嗎?階級真的歸來了嗎?回答這些問題,不但要從理論上重返底層,而且要對底層社會本身做出分析,然而,基于厚重經驗的底層社會研究還相當匱乏。階級范式雖在復蘇,但與多元分層理論無法抗衡,并且階級分析范式的應用者主要集中在泛左翼陣營,價值預設過強,經驗基礎太弱,對于農村社會的理解存在一定誤會,改進的空間很大。盡管如此,底層社會正在逐漸被關注、被研究,底層社會正在歸來,盡管腳步緩慢、歷程困惑。
四、重返底層:村治研究的拓展(2010-至今)
盡管發現了底層,階層研究并未真正“下沉”到底層,無論是社會“斷裂”論、“丁字形”結構理論,還是當前的貧富差距、勞工階級研究,都對底層充滿了想象和道德化的判斷。當前對城市貧困人群、失業人群、非正規就業人群的具體經驗研究乏善可陳,對9億農村人口的階層分化狀況更是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分析。誰是中國真正的底層?城鄉兩個底層群體是一樣的嗎?底層的分層狀況、分層機制是什么?底層的運轉邏輯是什么?這些問題看似簡單,當前的階層研究卻未做回答。
總體上看,當前階層研究存在以下五個問題:第一,采用西方理論和概念分析中國階層成為主流,缺乏對中國經驗邏輯的具體把握;第二,多城市、中產階層研究,缺乏對城鄉底層社會的關注;第三,將農村視為整個社會結構的底層,缺乏對城鄉社會結構差異、城鄉居民階層歸屬差異的研究;第四,將底層視為抽象的、模糊的、貧弱的人口集合,未對底層社會的階層結構、分化機制進行分析;第五,學界當前的階層研究無法回答下面的問題:社會斷裂日益加深、兩極分化日益加大、基尼系數早已超過警戒線的中國為何能夠保持長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農村社會有9億農民,其中有2億是往返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這個龐大的群體既是全國的底層又是城市的底層,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指示燈”。當前的中國階層研究迷失在尋找印證西方理論的經驗現象和數據里,喪失了對底層社會獨立思考的能力,面臨理論困惑和經驗貧瘠困境,階層研究越來越匠氣、死板、不接地氣。在階層研究的社會學領域之外,一些學者尤其是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為階層研究回歸底層做了努力和嘗試,其中華中村治研究學人的研究頗具代表。
隨著分田到戶在全國農村的展開,農村人口開始外流,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引起了學界注意,陸學藝[37]于1990年提出了農村社會的“八個階層”論,之后學界的農村階層研究大都停留在這個框架之內。然而經過鄉鎮企業改制、分稅制和農業稅費取消等變革之后,農村社會的階層結構再次發生重大變化。2010年,賀雪峰[38]根據人地關系將農民分為“離土階層、半工半耕階層、在鄉兼業階層、普通農業經營階層、貧弱階層”五個階層,并提出“中農”概念。留在村莊的青年人,流轉20~30畝土地自己經營,獲得不比外出打工少的經濟收入,由此形成農民群體的中間階層“中農”。《開放時代》2012年第3期專門組稿“中農研究”,陳柏峰[39]、林輝煌[40]、楊華[41]分別從土地流轉、地方經濟發展和農業經營轉型的視角對“中農”做出了解讀,他們認為中農的產生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產物,中農這一“中間階層”由于利益在村關心村莊公共事務,而成為農村發展穩定的主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華中村治學者對“中農”有著“中產階層”的理想情結。然而,筆者在農村調研發現,“中農”和當今的城市中產階層一樣并不一定發揮“中間階層”的功能。袁松[42]在浙江吳鎮的長期調研也支持這一觀點,他指出中產階層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依附于上層階層。近期,賀雪峰對“中農”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他指出“中農”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起階級范式的“誤會”,此“中農”不同于毛澤東時代階級成分中的“中農”,主要是指農村社會中發揮“中堅力量”[43]的農民——這些農民沒有離村,經濟收入來源在村莊,利益關系、人際關系、情感歸屬都在村莊,關心村莊事務,他們不僅包括種植20~30畝土地的農民,而且包括在村的小商小販、村醫、村干部、小作坊主、養殖戶等人。將“中農”轉化為“中堅農民”的簡稱之后,“中農”概念就具有了很強的解釋力,對城市“中產階層”研究亦有啟發:一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取決于社會中堅力量,而非某個經濟階層。
除了對普通農業型地區農村進行研究外,華中村治學人近年來也對東部發達地區農村的階層分化進行了較為前沿的研究。相比中西部農村,東部發達地區農村的階層分化層級已較為明朗,以經濟為核心的社會分層結構逐漸形成,并延伸到村落政治、文化、消費和人情交往層面。以階層為基礎的村落政治成為關注的重點,不同于黨國英[44]、盧福營[45]等學者大力肯定富人治村在推動基層民主、實現共同富裕方面的功效,賀雪峰[46]、魏程琳[47]等人從村莊政治分層的角度解讀了富人治村導致基層民主萎縮、參政門檻提高、公共資源分配不公、固化階層利益的邏輯。除了階層政治分化之外,發達地區農村展現出與城市類似的閑暇消費[48]等方面的分化。
在一定程度上,華中村治學者是在沒有“重返底層”的意識下進行的底層社會階層研究,他們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是底層農村農民。當然,這同時也成為一個問題,即華中村治學人的階層研究缺乏與學界的對話和交流,多數情況下階層成為一種分析框架而非研究對象,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學界階層研究空白的補充和貢獻。值得一提的是,楊華[49]在最近的階層研究中試圖重構底層階層研究范式,提出從實體論走向關系論,逐步展開了與學界的對話。
五、研究展望與可能進路:底層視角、機制分析與經驗研究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腳步,被裹挾在全球市場經濟之中的農村農民,經歷30余年的發展,發生了明顯而深刻的階層分化。然而,這樣一個龐大的底層群體并未自始進入階層研究者的視角,在被短暫發現之后又被遺忘。不可忽視的是,9億農民構成中國城鄉社會底層的主體,中國政治社會是否穩定主要看他們的階層分化狀況和生活滿意度,這正是采用底層視角開展農村與城市底層社會階層研究的現實意義所在。
受西方理論和分析工具的影響,當前學界的階層研究多采用定量方法。不可否認定量研究方法的優勢,但它的缺陷也很明顯,即無法展現轉型期中國經驗現象的復雜性,無法揭示中國社會分化的過程與機制。當前學界階層研究面臨的經驗貧瘠和理論困惑與此有很大關系。在宏觀理論和微觀經驗之間尋找邏輯關聯,筆者認為偏向中觀層面的機制研究不失為一種良好工具和研究進路。政治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對機制研究做了較為系統的論述:“何謂機制?意指一組被明確限定的事件,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以相同或者頗為類似的方式使特定要素之間的關系得以改變的原理……諸機制的組合則形成過程。”[50]簡單地講,機制就是多個要素之間的邏輯必然性關聯,具體環境的改變并不影響這種邏輯必然性。孫立平[13]在研究“總體性精英”的形成過程中,較好地運用了機制分析方法,將四個步驟或四個要素組合起來,就會發生必然的邏輯關聯——“總體性精英”必然會形成。借用機制分析方法,我們就可以在繁雜的經驗中發現關鍵要素,總結其特征和關系,進而對底層社會的階層分化機制或去分化機制有所了解,最終形成總體性判斷和預測。
“市場轉型”理論、印度底層學派理論以及各式階層分析的概念和工具,在中國學術的應用中表現出的不同程度“擱淺”現象——要么驗證最為一般的中國常識、要么驗證西方的理論結論或者在中國經驗中根本無的放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社會有著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同于印度拉美國家的特殊的歷史和改革背景。這也提醒中國學者:只有面向中國經驗、面向城鄉底層社會,運用底層視角和機制分析工具,才可能創設出獨立自主的分析概念和理論體系,才能夠回應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我們所看到的學界重返底層的努力,也許是一個姿態,或許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1]李強.社會分層十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36-37.
[2]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60.
[3]GIDDENS A.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M]. New York: Haper& Row Publishers, 1975:108.
[4]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Judgement of Taste[M].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4:1.
[5]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J]. Amer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663-681.
[6]BIAN Y J, LOGAN J. Market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1:739-758.
[7]ZHOU X 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105:1135-1174.
[8]李培林.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9]陸學藝.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10]張宛麗.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研究20年[J].社會學研究,2000(1):24-39.
[11]李路路.向市場過渡中的私人企業[J].社會學研究,1998(6):87-104.
[12]戴建中.現階段中國私營企業主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1(5):65-76.
[13]孫立平.總體性資本與轉型期精英形成[J].浙江學刊,2002(3):100-105.
[14]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15]李強.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M].第二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216.
[16]李強.“丁字形”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J].社會學研究,2005(2):55-73.
[17]劉欣.當前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制度基礎[J].社會學研究,2005(5):1-25.
[18]仇立平.當代中國上海社會分層結構形態及其解讀[M]//周曉紅.中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84-101.
[19]張翼.中國城市社會階層沖突意識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5(4):115-129.
[20]李友梅.社會結構中的“白領”及其社會功能[J].社會學研究,2005(6):90-111.
[21]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2]西摩·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M].張紹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3]張翼.當前中國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J].中國社會科學,2008(2):117-131.
[24]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25]李春玲.中產階級的現狀、隱憂與社會責任[J].人民論壇,2011(5):14-17.
[26]李路路.中間階層的社會功能:新的問題取向與多維分析框架[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8(4):125-135.
[27]劉健芝,許兆麟.庶民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6.
[28]趙樹凱.“底層研究”在中國的應用意義[J].東南學術,2008(3):9-11.
[29]王慶明.底層視角及其知識譜系——印度底層研究的基本進路檢討[J].社會學研究,2011(1):220-242.
[30]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J].社會學研究,2006(2):13-36.
[31]仇立平.回到馬克思:對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反思[J].社會,2006(4):23-42.
[32]馮仕政.重返階級分析?——論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轉換[J].社會學研究,2008(5):203-228.
[33]潘毅.階級的失語與發生——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J].開放時代,2005(2):95-107.
[34]潘毅.開創一種抗爭的次文本:工廠里一位女工的尖叫、夢魘與叛離[J].社會學研究,1999(5):13-24.
[35]潘毅,盧暉臨,嚴海蓉,等.農民工: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J].開放時代,2009(6):5-35.
[36]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21.
[37]陸學藝,張厚義.農民的分化、問題及其對策[J].農業經濟問題,1990(1):16-21.
[38]賀雪峰.取消農業稅后農村的階層及其分析[J].社會科學,2011(3):70-79.
[39]陳柏峰.中國農村的市場化發展與中間階層——贛南車頭鎮調查[J].開放時代,2012(3):31-46.
[40]林輝煌.江漢平原的農民流動與階層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為考察對象[J].開放時代,2012(3):47-70.
[41]楊華.“中農”階層:當前農村社會的中間階層——“中國隱性農業革命”的社會學命題[J].開放時代,2012(3):71-87.
[42]袁松.富人治村——浙中吳鎮的權力實踐[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12.
[43]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113.
[44]黨國英.論鄉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兼論中國鄉村的民主政治改革[J].開放導報,2004(12):23-31.
[45]盧福營.治理村莊:農村新興經濟精英的社會責任[J].社會科學,2008(12):55-63.
[46]賀雪峰.論富人治村[J].社會科學研究,2011(2):111-119.
[47]魏程琳,徐嘉鴻,王會.富人治村:探索中國基層政治變遷的邏輯[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8-15.
[48]魏程琳.階層分化、消費競爭與農村老年人閑暇[J].Rural China, 2015,12(2):264-268.
[49]楊華.農村階層研究的范式轉換:從實體論到關系論[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11-17.
[50]查爾斯·蒂利,西德尼·塔羅.抗爭政治[M].李義中,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36.
責任編輯劉榮軍
網址:http://xbbjb.swu.edu.cn
10.13718/j.cnki.xdsk.2016.05.006
2015-10-09
魏程琳,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間階層對農村社會治理的作用和參與機制研究”(14CKS037),項目負責人:劉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階層分化背景下農村社會治理研究”(15CKS022),項目負責人:陳鋒。
C912
A
1673-9841(2016)05-003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