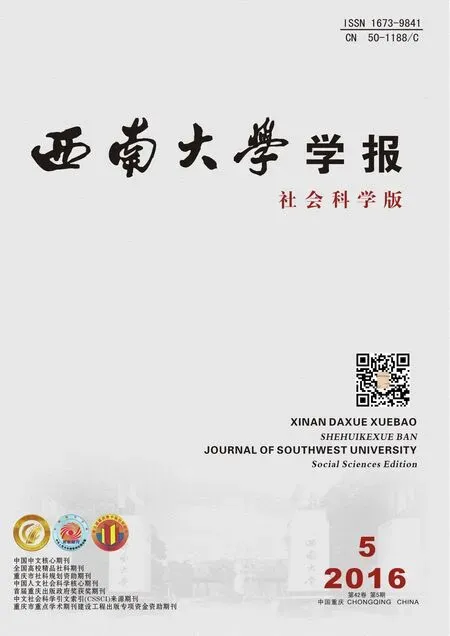從“隱喻說”到“意識形態說”①
——英國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基礎/上層建筑”
韓 昀,周 世 興
(華僑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
從“隱喻說”到“意識形態說”①
——英國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基礎/上層建筑”
韓昀,周 世 興
(華僑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英國馬克思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始終保持著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密切關注。早期研究者將基礎/上層建筑視為一個有機整體而非線性模型,因而致力于擴大兩者所能容納的社會要素,提出應將該命題理解為一種隱喻。隨著社會語境的變化,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活躍的學者將對該命題的思考落實在對意識形態問題的研究之中,以此來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對上層建筑的理解,同時傾向于將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理解為一種功能性關系,從而使英國馬克思主義逐步回歸到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視方面。從整體上看,英國馬克思主義關于該命題的研究呈現出一種辯證發展的總體趨勢。
英國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層建筑;經濟決定論;隱喻;意識形態;文化理論
英國馬克思主義產生于上世紀50年代,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以文化問題為出發點,深入思考了如何在新的資本主義語境中理解并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重要問題,對當代馬克思主義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1946年,英國馬克思主義重要的孵化器“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United Kingdom British Communist Historians Group,以下簡稱小組)宣告成立,成員中既有當時已頗有聲名的A.L.莫爾頓(A.L.Moulton)、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等,也有日后聲名大噪的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E.P.湯普森(E.P.Thompson)、拉斐爾·薩繆爾(Raphael Samuel)等。小組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主要來自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下簡稱《序言》)和《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選集》(1934年譯為英文版)這兩個文本。通過討論、研究這兩個文本,他們不但注重歷史整體性思想,并且認識到階級斗爭在具體歷史階段中的重要性。這樣,原本在傳統馬克思主義中未曾展開的文化問題便成為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關切所在,而“任何針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現代探討從一開始都必定要考慮到具有決定性的基礎和被其決定的上層建筑這一前提”[1]80。誠如斯言,英國馬克思主義中的不少人物都曾針對該問題闡發過自己的見解,而在這些學者中,以E.P.湯普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G.A.柯亨(G.A.Cohen)等學者的觀點最具代表性,影響也更大。本文試圖梳理分析這些學者有關該問題的不同看法,追溯他們學術立場形成的基點,為再現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整體面貌提供一個較好的切入點。而對我國來說,這也將有助于我們反思英國馬克思主義在該問題上的研究得失,更好地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一、蘇聯馬克思主義對基礎/上層建筑的理解及其對英國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為首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用線性歷史進化論替換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和整體性歷史觀,將馬克思主義闡釋成一套經濟主義的自然發生學。這一做法使上層建筑的相對自主性被掩蓋,“人”成為了歷史旁觀者,而基礎/上層建筑也就隨之演變為了一個經濟決定論的命題。盡管第二國際另一位代表人物普列漢諾夫嚴厲地批評了這種“經濟決定論”主張,提出了十分著名的“五項論”來闡釋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的發展;由這個程度(生產力)所決定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由這些人的關系所表現的一種社會形式;與這種社會形式相適應的一定的精神狀況和道德狀況;與這種狀況所產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學、文學、藝術”[2]186),希望借此來豐富此命題所應包含的諸多中間環節,但從根本上來看,他也未能逃離線性歷史觀的思維方式。普列漢諾夫對社會生活各組成部分之間關系的論述方式,極易使人們產生社會各組成部分是按照先后順序排列的理解,從而使上層建筑具有明顯的被規定性。此外,作為創造歷史的“個人”在這一理論中也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盡管如此,普列漢諾夫的觀點還是得到了列寧的認同,后者表示對此“十分滿意”并且“一再閱讀”[3]25。這種思維方式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中達到頂峰。在這本書中,針對蘇聯語言學家馬爾(N·Ya·Marr)的觀點,斯大林表達了自己對上層建筑的看法:“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就是要上層建筑為它服務,要上層建筑積極幫助它形成和鞏固,要上層建筑為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舊上層建筑而積極斗爭。”[4]502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結論:“上層建筑是通過經濟的中介、通過基礎的中介同生產僅僅有間接的聯系。因此上層建筑反映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礎變化以后,通過生產變化在基礎變化中的折光來反映的。”[4]505這樣,上層建筑在斯大林的闡釋下完全背離了馬克思的原意,成為了基礎的附庸品,而且十分狹隘、有限。同時,斯大林也將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為兩個專有名詞,認為基礎就是“社會在其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經濟制度”,上層建筑就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同這些觀點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設施”。[4]501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的成功實踐,該說法被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不加批判地完全接受,而英國共產黨也不例外。即使是被稱為“戰前英國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創性的馬克思主義者”[5]343的克里斯托弗·考德威爾(Christopher Caudwell),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文藝批評時也未能完全擺脫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機械決定論色彩。*參閱Christopher Caudwell. Illusion and Realit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46.
二、打破基礎/上層建筑封閉性的“隱喻說”
情況的整體改觀始于1956年。是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震驚世界。同年,英國出兵埃及蘇伊士運河,蘇聯鎮壓布達佩斯群眾游行,這一系列事件的連續爆發,使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社會主義和英國資本主義產生了雙重幻滅,他們不得不面對“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并實踐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重大問題。而解決這一難題的首要任務則無疑是展開了對僵化的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批判性反思。
在這一反思熱潮中,湯普森率先展開行動。蘇共二十大之后,湯普森和經濟學家約翰·薩維爾(John Saville)迅速創辦《明理者》(The Reasoner)雜志發表異見,但該刊物僅發行了三期就因遭到黨內領導人的批判而宣告停刊。1957年夏,兩人再次創辦《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并將刊物目標準確定位為批判斯大林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期刊的創刊號上,湯普森發表著名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致非利士人書》一文,嚴厲斥責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闡發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提出了建立符合英國本土狀況的馬克思主義即“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愿景。這一批判視角和基本立場在其隨后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class,1963)、《理論的貧困及其他論文》(The Poverty of Theory &Other Essays,1979)等重要著作中均可看到,因而可以將他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探討置入這一理論語境中來理解。
從整體上看,湯普森所理解的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理論特色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湯普森指出了“基礎”應具有的“人”性和實踐性。馬克思曾明確指出,舊唯物主義的錯誤就在于“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6]133。以此,湯普森認為斯大林主義正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舊唯物主義,因為斯大林“想象‘經濟基礎’是由外在于人、僅僅通過技術革新來產生影響的東西——犁、珍妮紡紗機、船塢——組成的”[7]。在湯普森看來,這種做法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使基礎/上層建筑成為一種非人的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原本作為創造這些物質條件的人已經變成了為生產服務的無關輕重的存在。撇開湯普森“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的烏托邦色彩不談,他在論證過程中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確實使人們看到了蘇聯馬克思主義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理解缺失實踐維度。這樣一來,湯普森就較為成功地使作為“基礎”的題中之義的歷史主體(“人”)及其實踐凸顯出來,回到了基礎/上層建筑命題內部,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斯大林主義將“人”排除于基礎/上層建筑之外的錯誤。
其次,湯普森要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總體性歷史觀下看待基礎/上層建筑命題。針對斯大林將組成社會的各要素在基礎和上層建筑中進行分門別類的做法,湯普森尖銳地反駁道:“把一些(如法律、藝術、宗教、道德)歸于上層建筑,把另一些(如技術、經濟、實用科學)放在經濟基礎,而將另一些(如語言、工作紀律)在兩者之間游動,這勢必陷入簡化論和粗俗的經濟決定論中去。”[8]基于此,湯普森試圖在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搭建一個“經驗”(experience)的橋梁,以使基礎/上層建筑成為一個有機辯證的綜合體,從而改變那種將各個社會要素對立起來的做法。在他的理論話語中,經驗并非如人們一般地理解的那樣是作為上層建筑的人類意識活動,而是“經驗1——活的經驗和經驗2——理解的經驗”[9]406,前者作用于基礎,后者作用于上層建筑。這樣,“經驗”就具有了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雙重性質,而且也使作為連接“經驗1”和“經驗2”的橋梁的“人”在該命題中具有了統攝社會各個要素的重要地位。通過這樣的方式,湯普森批判了那種在理論上任意劃分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做法,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的關鍵就是“要求對社會過程進行總體研究,作為社會的總體史就是要匯集其他方面的歷史”[10]70。
再次,湯普森擴大了斯大林主義中僅作為經濟制度的“基礎”所指涉的內容:“斯大林主義者忘了‘經濟基礎’是一個虛擬的描述,它不僅僅指人類肉體的經濟活動,也指他們的道德存在和智力存在。”[7]通過這種增加基礎要素的做法,湯普森用基礎所具有的道德性去抵抗斯大林主義中“基礎”潛在的非人道主義內涵,賦予基礎以社會關系特別是道德關系的新內容,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具有了全新的內涵和研究價值。
為支持上述論斷的理論合法性,湯普森將基礎/上層建筑視作一種隱喻:“這種‘基礎’與‘上層建筑’從未存在過,它只是幫助我們理解實際存在的事物——行動、經歷、思考、再行動的人——的隱喻。”[7]通過“隱喻說”,湯普森超越了斯大林主義模式對人的冷漠,使馬克思主義和英國本土傳統的經驗主義相結合,為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具體理解并實踐歷史唯物主義貢獻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和思考角度。雖然湯普森的這些觀點后來遭到了來自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霍爾領導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兩路人馬的聯合批判,但不可否認,他的研究及其方法論為英國馬克思主義打破僵化的基礎/上層建筑模式開辟了道路。
在早期眾多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中,雷蒙·威廉斯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見解也頗具代表性。同湯普森一樣,威廉斯也將基礎/上層建筑命題視為一種“隱喻”。早在1957年,威廉斯就提出了基礎/上層建筑“僅僅應當被理解為一種比喻”的觀點[11]267。在他后來更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基礎與上層建筑》一文中*該文最早發表于1973年的《新左派評論》中,后來經過修改完善,收錄于1977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一書。,這一觀點則表達得更為直接:“因為就任何實際方式而言,這一用法基本不是概念性的,而是隱喻性的。”[1]83不過,與湯普森的論證邏輯不同,威廉斯否定對基礎/上層建筑的教條式理解,目的是為了重新定義文化概念,以為建立“文化唯物主義”提供理論前提。在威廉斯看來,如果追隨斯大林主義而將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化看成是全然被基礎決定的,那么他所要開展的文化研究從理論邏輯上看就將毫無意義。不言而喻,威廉斯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始終是以研究文化對經濟、政治的作用為核心而展開的。盡管威廉斯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這些見解發表于第二代新左派完全占據領導地位的70年代,但其實早在50年代他就已經對該問題形成了基本論斷,并通過不斷吸收湯普森和葛蘭西的理論而完善自己之前的理論體系。因此,從根本上說,威廉斯的論述更多地是代表了早期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理論特色。
具體說來,威廉斯的重要貢獻是將“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命題中每一個詞語的含義進行了概念上的厘清和富有創見的再定義,以上層建筑作為切入點,否定了那種將法律的、政治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等特定形式的文化視作文化的全部活動的看法。同時,他根據馬克思在具體文本中對“上層建筑”一詞的不同用法,歸納出了上層建筑的三種不同含義*這三種含義包括:“一是指存在著的現實的生產關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二是指特定階級的世界觀的意識形式;三是指人們在全部活動意識到基本的經濟沖突,并對這種沖突進行克服的過程。”詳見雷蒙·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周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頁。,從而改變了斯大林主義對上層建筑的教條式規定。隨后,威廉斯將“決定”一詞的含義分為兩類,認為蘇聯馬克思主義是在神學意義上理解“決定”的,而馬克思、恩格斯則是在社會經驗的意義上理解“決定”的:前者視“決定”為“某種外在力量(上帝、自然或‘歷史’)控制活動過程的結果”[1]13,而后者只是將“決定”理解為“限度的設定”[1]92,因而該詞只能作為社會歷史創造主體的限定語而存在。通過這種調換主語和定語位置的做法,威廉斯使基礎/上層建筑這一命題內蘊了對主體性的重視,使具體的人成為了命題的核心所在。不過,在對“基礎”一詞的考察過程中,威廉斯的看法充滿了矛盾色彩。馬克思曾經在批判施托爾希時說過,不能把物質生產“當做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應該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12]296,而威廉斯則據此認為,在具體歷史階段中,“觀察‘基礎’中的這種外延的特質比起觀察那總是多變的和可變的‘上層建筑’的外延更重要”[1]86。而基于目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語境,威廉斯認為,原本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化已經具有了再生產的能力,那么它現在也應屬于物質生產,應被歸為“基礎”的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后來伊格爾頓對威廉斯擴大基礎的做法的批判傳播甚廣,但威廉斯自己早就有過“自我檢討”,認識到這種將文化納入基礎的做法使后者“已經失掉了鋒芒和特定性”并具有抽離馬克思理論基石的危險性,他只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將基礎作為特指名詞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才這樣做,而“超越這一難題是以后理論討論的事”[1]101了。實際上,這也是威廉斯此后一直力圖克服的理論局限。
就威廉斯和湯普森的研究來說,盡管二人在研究的領域、出發點、目標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對基礎/上層建筑的闡釋方面卻順著同樣的理論邏輯前行:(1)批判經濟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2)應當研究作為有機整體的社會;(3)恢復個人及其實踐在歷史中的作用;(4)馬克思的基礎/上層建筑命題應是一種隱喻。雖然將馬克思的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看作是一種隱喻的做法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就當時特殊的歷史語境而言,隱喻說又確實頗為成功地改變了那種將馬克思主義與經濟決定論畫等號的錯誤觀點,有力地扭轉了蘇聯馬克思主義中“人”的缺席的局面,從而為理解基礎/上層建筑命題提供了新的維度。同時,他們試圖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而不是蘇聯馬克思主義的條框中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做法,使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聚焦點回到了馬克思的具體文本中,為馬克思本人提供了有力辯護,從而使我們看到了由馬克思所創建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豐富內涵。從更深遠的意義上來說,這種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方式,代表著英國馬克思主義已經同之前那種由歷史規律來保障社會變革的思想分道揚鑣,開啟了對歷史唯物主義富有本土特色的研究道路。
三、“意識形態說”的建立及其內部爭論
如果可以將湯普森、威廉斯等為代表的早期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理解概括為“隱喻說”,那么,在60年代末開始活躍的以霍爾、伊格爾頓等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觀點則基本可被概括為“意識形態說”。這些后起的研究者在整體上更多受到了阿爾都塞、葛蘭西等歐陸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影響,對該命題的考察集中圍繞在“意識形態”的相關研究中。正如霍爾所說,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出發點賦予文化以更廣闊的實踐空間,因而“可以無需參考‘意識形態’的概念的意義框架”,而受結構主義影響的后來者“由于堅持了自己更為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路線,‘文化’的概念并不那么突出”,便將研究“大量圍繞在‘意識形態’的闡釋上”[13]。
被稱為“文化研究之父”的霍爾不僅在文化研究領域功勛卓著,更以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保持著對社會現實的積極介入姿態,而其介入社會現實的路徑主要是依靠對意識形態和“基礎/上層建筑”之間辯證關系的思考來完成的。由于經歷了資本主義社會半個世紀的不斷轉型過程,霍爾的思想軌跡也隨著社會語境的變化不斷改變。在50年代,青年霍爾對湯普森、威廉斯等人的基礎/上層建筑“隱喻說”持基本的贊同態度(代表作是《無階級的觀念》,1958)。隨著第二代新左派的興起和其他歐洲國家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不斷涌入,霍爾積極吸收了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理論和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思想,通過將意識形態作為探討基礎/上層建筑的切入點,形成了自己對于這一問題的獨特看法,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比較重要的有《重思“基礎和上層建筑”隱喻》(1977)、《文化研究:兩種范式》(1980)、《“意識形態”的重新發現》(1982)、《意識形態問題——不作保證的馬克思主義》(1983)等。從中不難發現,相較于對“隱喻說”的亦步亦趨,霍爾從意識形態維度介入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思考更為持久,理論成就也更為突出。
1958年,霍爾在《大學與左派評論》雜志上發表了《無階級的觀念》一文,聲援理查德·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提出的關于工人階級意識被逐漸同化的看法。在這篇文章中,霍爾反思了以下問題:社會的經濟基礎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那么為什么進入戰后福利社會的英國工人階級不再具有團體性力量?究竟是何種力量使威廉斯所認為的“整體性生活方式”變為“一系列的生活風格”?針對這些現實問題,霍爾認為原來那種生硬的基礎/上層建筑模型根本無法解釋現今的資本主義狀況,因為當前的社會歷史已經處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文化的異化和剝削變得如此分歧和復雜,以至于它們獲得了獨立的生命力”[14]。因此,為了了解目前具體歷史環境中文化和經濟結構之間的辯證互動關系,霍爾提議將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理解為一種“自由發揮”的關系,即“上層建筑領域的轉變同經濟基礎的轉變同樣具有決定性”[15]。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霍爾將自己稱為“不作保證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必須指出,霍爾的這一看法并不代表著他否認或無視經濟在整個社會秩序中的基礎性作用,因為他理解的“決定”既不同于蘇聯馬克思主義中那種完全控制的排他性意義,也不同于威廉斯所說的“設定邊界”的含義,而是更接近于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對“決定”一詞的使用:“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16]604
隨著英國社會實際語境的變化,文化主義范式逐漸被結構主義范式所取代。作為新研究范式的領導人,霍爾關于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看法也發生了重要轉向,開始積極地將意識形態置于問題理解的中心。一方面,通過借鑒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霍爾改變了早期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單刀直入式地討論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那種方法,轉而使用生產和再生產的視角對上層建筑的特征進行研究,因為按照阿爾都塞的理解,“大廈的隱喻具有局限,它是描述性的,未必能解決由此而來的各種問題”[17]。通過研究,霍爾認為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同樣具有物質生產的形式和能力,這便使上層建筑得以進入屬于基礎的生產領域。同時,霍爾依舊肯定經濟的基礎性地位:“政治、司法和意識形態是有關系的,但是又是‘相對自主’的領域,它們自身的斗爭目標,顯示了一種對于‘經濟基礎’的相對獨立的反作用力。”[18]56另一方面,根據阿爾都塞有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論述,統治階級通過宗教、家庭、學校、媒體等社會機構建構了人們對現實的意識,使人們由個體成為主體,從而達到在整體上復制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目的。在這種理論視野中,意識形態便成為一種單向度的結構機能。然而,霍爾堅信意識形態內部必然存在反抗維度,因為如果確如阿爾都塞所說,意識形態建構了人們的常識,那么又如何才能很好地解釋社會中現實存在的抵抗思想?此時,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則為其主張提供了可借鑒的理論資源。葛蘭西注重意識形態的斗爭內涵,認為領導權是各個階級意識形態的調和,其形成同樣需要被統治階級的認同。受葛蘭西理論的影響,霍爾在傳播學領域運用該理論創建了著名的編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理論,這一理論從側面凸顯了意識形態領域中傳播者(資產階級)和受眾(工人階級)兩種力量的存在及其斗爭過程。隨著70年代末撒切爾政府上臺執政,霍爾更加堅定了對文化領導權的認識:“有些人按照他們的階級地位本來是不會贊成撒切爾主義的,當這樣的人忽然開始發現撒切爾的語言比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的語言更可信,更切合他們的經驗,這就是領導權發生轉移的拐點。”[19]及至80年代,霍爾完全抹消了意識形態和階級地位之間的對應關系:“對所謂的意識形態,我指的是由語言、概念、范疇、形象和表象系統構成的體系構架,不同的階級和社會集團都利用它們來理解、界定和改造社會。”[20]
從宏觀角度看,圍繞意識形態問題,霍爾在整合、改造、發展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的理論過程中形成了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基本看法。不同于威廉斯致力于擴大基礎的理論努力,霍爾更用力于論證上層建筑的相對自主性,繼而將這種自主性建立在生產和再生產的物質過程之中。通過這種改變探討領域的做法,霍爾將上層建筑從那種被動反映的圖式中解放出來,使之具有了斗爭的能動性和自發性,甚至足以起到改造社會的作用。而從微觀角度,即僅從上層建筑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不論是將意識形態作為上層建筑的看法,還是將之作為階級意識的看法,都并非霍爾所探討的意識形態。或許可以這樣說,在霍爾的話語和思想體系中,意識形態已經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而是一個問題域,既有基礎的規定性也有上層建筑的被規定性。換句話說,霍爾反對了以基礎/上層建筑為代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論模式,使上層建筑所內含的要素發生了重要改變。
特里·伊格爾頓在關于意識形態的分析中同樣試圖重構對基礎/上層建筑的理解,這種理論努力值得我們格外重視。伊格爾頓直接探討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文章有兩篇:一篇是1989年的《雷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基礎和上層建筑》,另一篇是1998年的《再論基礎和上層建筑》。此外,他在其他關于意識形態的文章中也較多地涉及了這一問題。*例如《批評與意識形態》(1976)、《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意識形態:導論》(1991)等。
作為威廉斯的得意門生,伊格爾頓繼承了威廉斯在這個問題上的許多觀點,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隨了威廉斯對該命題進行的詞源學闡釋,對他試圖恢復上層建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積極作用的努力給予高度肯定。不過,由于時代變更和革命局勢變化的緣故,伊格爾頓顯然更加認可阿爾都塞的觀點而非英國本土的經驗主義思維方式。因此,較之于威廉斯,伊格爾頓的研究更凸顯了對“基礎”物質性的強調:其一,他嚴厲批判了威廉斯將文化納入基礎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嚴重地“損傷了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獨特性”[21]95,并提出了毫不留情的質疑:“如果一切都是‘物質的’,那么這個術語在邏輯上還有什么力量呢?”[22]169其二,威廉斯在其理論中將主體的意識納入基礎,認為一定歷史階段的“基礎”的形成前提必然是人,而伊格爾頓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文化主義的要害是渾然不顧以下情況,即:不管人類是何種生物,他們首先是自然的物質的客體,”[23]而“威廉斯對文化的概念的分析過多地倚重經驗主義的概念,從而忽略了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模式所蘊含的本體論的思想能量”[21]23。此時,伊格爾頓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威廉斯矯枉過正的做法,使“基礎”以更加辯證的方式回歸到經典馬克思主義。
在上述批判的基礎上,伊格爾頓闡釋了自己對該問題的認識。其一,與多數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樣,伊格爾頓也將“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個表述視為馬克思理論中更為根本性的命題,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和“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兩個命題進行了嚴格區分,賦予二者在馬克思理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前者是一個本體論命題,而后者則是前者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表現,其實也就是約翰·杜普雷所指出的:“沒有將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為一個徹底的范疇來建構。”[24]可見,伊格爾頓承認“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命題的正確性是有條件的,即這種正確性只能在階級社會中得到保障,而到了無階級社會就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觀照下,伊格爾頓重新定義了該命題的當代價值。他宣稱,馬克思努力解答的并非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層建筑和物質生產兩者孰輕孰重的問題,而是到底是什么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樣的問題;不是“什么是導致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而是“你究竟想要什么”[22]175。這樣,威廉斯等早期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命題的努力就被宣布無效,因為在伊格爾頓的視野之下,他們汲汲于論證基礎和上層建筑究竟是什么的做法根本就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理論前提上的,而這一命題顯然“不是一個區分物質與精神的問題”[25]。其次,伊格爾頓認為,上層建筑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指涉作為意識形態的那部分文化,而這部分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化是為基礎提供意識形態支持的;溢出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化,在本體論意義上屬于社會意識,而非上層建筑。同時,由于這種超出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化不再服務于基礎,因而便具有了文化生產的可能性。這就是說,在伊格爾頓的理論中,上層建筑是作為意識形態存在的,是政權為了確立自身合法性而建立的。在伊格爾頓看來,“意識形態不是一套教義,而是指人們在階級社會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們束縛在他們的社會職能上并因此阻止他們真正地理解整個社會的那些價值、觀念和形象”[26]20,而“上層建筑的功能在于為了某一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協助處理這種對立”[23]460。伊格爾頓這些觀點顯然是追隨阿爾都塞而對意識形態所做的功能主義闡釋,由此形成了一種與霍爾不同的理論面貌。
四、柯亨對“隱喻說”和“意識形態說”的雙重批判
在上世紀70年代,“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G.A.柯亨也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做出過重要論述,并通過對該命題的嚴格分析而“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方面一個新的、更嚴格的階段”[27]。
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開篇,柯亨就大篇幅摘錄了馬克思的《序言》來彰顯自己的文本依據,并嚴格遵守馬克思文本中的字面意思對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了狹義上的概念界定。根據馬克思《序言》中關于“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28]2的觀點,柯亨明確提出基礎應該僅包括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結構而非霍爾等人所說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而上層建筑則應當“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非經濟的制度組成的”[29]48。柯亨的這一定義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重視:一是有關生產力的問題。將生產力和基礎區分開來后,生產力究竟處于何種位置?柯亨給出的答案是:“生產力處于經濟基礎的下面。經濟結構是社會的基礎,這并不取消一個特殊的經濟結構得以成立的問題……生產力強有力地決定經濟結構的特點,而又不是組成它的一部分。”[29]33也就是說,生產力是“基礎”的基礎,猶如雕塑的基座。雖然柯亨并不否認上層建筑對基礎的反作用力,但鑒于他認為由生產力到基礎再到上層建筑這一過程并不可逆,因此生產力掌握著最終的決定權,其原因就在于,“生產力是按照結構促進發展的能力來選擇結構的”[29]176。二是當上層建筑作為“制度”存在時,必然是服務性和功能性的。在這個層面上,柯亨與伊格爾頓達成了一致:二人均將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功能性關系。不過,柯亨顯然更進一步:“與其說法律上層建筑被建筑于經濟基礎之上,不如換一種更加生動的說法,那就是,前者的特征要依靠后者的特征來解釋”[30],這就顯示出了他對生產力的極端重視。從這一思想出發,柯亨批判了威廉斯、湯普森等人經常援引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將經濟因素限定在“歸根結底”作用的做法,恢復了生產力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決定性地位,糾正了在英國馬克思主義中占主導地位的“隱喻說”的缺陷。
以上分析表明,從對物質基礎的重視以及對基礎/上層建筑作出功能性解釋來看,柯亨的理論可能更接近于“意識形態說”的觀點。但需要指出的是,“隱喻說”和“意識形態說”雖然描繪了英國馬克思主義自上世紀50年代起對該問題理解方式的大致看法和基本走向,但并不能將所有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觀點盡攬于其中。柯亨既不同意早期英國馬克思主義者試圖模糊化或者擴大化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做法,斥責該方法使馬克思主義本該具有的歷史硬度被消融了,同時也曾直言“無需敘述我與阿爾都塞的特殊的理論分歧,它們是相當大的”[29]5。甚至在他的理論體系中,意識形態問題也基本未曾被提及。這就表明,并不能簡單將柯亨與追隨阿爾都塞的霍爾、伊格爾頓等人歸為同路人,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對該命題的理解是充滿了爭議性的。
五、余 論
縱觀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是他們遭遇最頻繁、思考最深入、體會最真切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31]在上世紀50年代之前,由于蘇聯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逐漸將基礎和上層建筑人為地割裂開來,片面強調它們在時間上的先后順序,而完全忽視了二者作為社會有機組成部分在空間上的共存,這就使他們背離了馬克思“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6]222的基本觀點,繼而見物不見人,最終走向了機械唯物主義。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也與這種機械化的馬克思主義相形漸遠。眾所周知,工黨領導下的英國在上世紀40年代全面步入福利社會,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使工人階級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從而使原本以經濟問題為核心的階級斗爭日益趨向復雜化、多元化。在這種現實與理論的雙重困境之下,早期英國馬克思主義研究者認識到,要使馬克思主義具有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能力,就必須突破那種將馬克思主義理解為經濟決定論的錯誤觀點。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致力于論證上層建筑要素在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因而才有了將基礎/上層建筑理解為“隱喻”的做法。該說法影響既深且遠,甚至不少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現在都基本持這種理解方法。但在60年代之后,社會現實語境的變化促使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內部轉型,一些人開始批判“隱喻說”所存在的多元決定論的潛在危險,一方面從側面進入該命題,以意識形態研究超越原本對上層建筑的理解,另一方面對該命題的主導觀點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回歸了經典馬克思主義所看重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等物質條件之上。由此可以看到,英國馬克思主義關于該命題看法的一條較為明顯的發展軌跡是:由致力于擴大基礎和上層建筑所包含的社會要素逐漸回歸到對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決定性地位的強調。
從整體上看,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并未達成一致意見,也并未就兩者的關系給出一個明確的定位,不同學者所持的觀點甚至是相互抵牾的。但是,如果將他們對該命題所做的理解視作由歷史語境的變化而作出的策略性調整,那么他們的理論主張其實都是為理解英國社會變革所做出的不同方向上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扭轉了蘇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弊端,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深化了對基礎/上層建筑命題的理解維度,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和意識形態理論。不過,從根本上看,他們所做的種種努力以及他們所看重的實踐,面向的不是未來而是過去,只是一種理論的努力而非實踐的存在。因此,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來說,英國馬克思主義在該問題的思考中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應該是他們提出的那些問題,而不是他們所提供的答案。
[1]雷蒙·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王爾勃,周莉,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2]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
[3]列寧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4]斯大林選集: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M].李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E.P.湯普森.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致非利士人書[M]//張亮.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3-49.
[8]E.P.湯普森.民俗學、人類學和社會史[M]//蔡少卿.再現過去:社會史的理論視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84-206.
[9]THOMPSON E P. The Politics of Theory[M]//Raphael Samuel.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1.
[10]THOMPSON E P. The Poverty of the Theory &other Essays[M]. London: Merlin Press, 1979.
[11]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 London: Chatto&Windus, 1959.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斯圖亞特·霍爾.兩種范式[M]//羅剛,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51-65.
[14]斯圖亞特·霍爾.無階級的觀念[M]//張亮.倫理、文化與社會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153-171.
[15]丹尼斯·德沃金.斯圖亞特·霍爾與英國馬克思主義[J].學海,2011(1):72-80.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7]陸揚.論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1):133-139.
[18]STUART Hall. The Politics and The Economic in Marx’s Theory of Classes[M]//Alan Hunt (ed.).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Wishart, 1977.
[19]STUART Hall.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M]//C. Nelson and L. Crossberg (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35-73.
[20]STUART Hall. 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M]//Betty Matthews (ed.). Marx 100 Years On. London: Lawrence&Wishart, 1983: 57-86.
[21]段吉方.意識形態與審美話語[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22]TERRY Eagleto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Raymond Williams[M]//Terry Eagleton (ed.).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3]特里·伊格爾頓.再論基礎與上層建筑[J].張麗芬,譯.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2(5):452-462.
[24]約翰·杜普雷.評伊格爾頓的《再論基礎與上層建筑》[J].蘇東曉,譯.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2(5):463-468.
[25]徐嬌娜.伊格爾頓論基礎/上層建筑——兼論伊格爾頓對威廉斯的批評[J].文藝理論研究,2009(2):82-89.
[26]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27]艾倫·布坎南.馬克思、道德與歷史[C]//林進平,張娜,譯.倫理學與公共事務,2014(1):21-51.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9]G.A.柯亨.卡爾·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一個辯護[M].岳長齡,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30]G.A.Cohe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A reply to Collins[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9(9): 95-100.
[31]張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J].哲學動態,2014(9):22-28.
責任編輯劉榮軍
網址:http://xbbjb.swu.edu.cn
10.13718/j.cnki.xdsk.2016.05.002
2016-05-24
韓昀,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通訊作者:周世興,教授。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重視域中的馬克思藝術生產理論研究”(13EA136),項目負責人:周世興。
B036
A
1673-9841(2016)05-0012-09
①本文采用基礎/上層建筑(Base/Superstructure)這一說法,而非更為普遍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Economic Base/Superstructure)說法(如張亮:《英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哲學動態》2014年第9期)。原因有三:一是英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們在探討該問題時使用的基本為基礎/上層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的表述方式,因此本文遵循他們的原意;二是馬克思本人在不同階段對于該命題的表述方法不同,使用“基礎”一詞能夠更好地展現其歷時性維度。1852年之前,“基礎”還沒出現,馬克思把特定形式的階級意識的起源確定為“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會條件”,1859年,使用的是“現實基礎”,在后來晚期的論述中才使用“經濟基礎”的表達方式(詳見雷蒙·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周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頁);三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內部對“基礎”所包括的社會要素存在較多分歧,因此為避免混淆不同學者的看法,此處使用更具包容性的“基礎”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