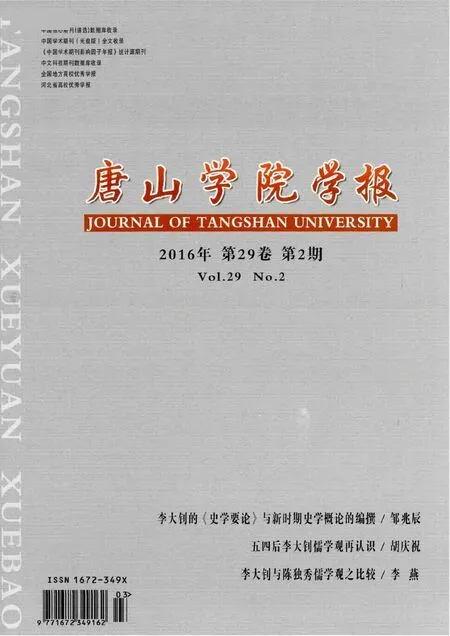試論1925-1927年蘇共黨內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之爭
——權斗背景下的理論分歧
呂佳翼
(浙江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杭州 310023)
?
試論1925-1927年蘇共黨內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之爭
——權斗背景下的理論分歧
呂佳翼
(浙江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杭州 310023)
摘要:在“一國社會主義”論這一看似簡單的命題中,交織著因歐洲革命失敗而使革命孤立在落后一國的無奈和焦慮,蘇共政治舞臺上的派別重組和權力之爭,以及或有一定深度的真正的理論分歧。文章以1925-1927年這一蘇共舞臺上權力重組和理論爭鳴的關鍵時期為特定視域,揭示“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的歷史成因與理論分歧,從而引起對這一問題的批判性反思。
關鍵詞:一國社會主義;托-季反對派;斯大林-布哈林聯盟
“一國社會主義”論之爭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也是國際共運中的重大實踐問題,它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并且一經提出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共運的走向。然而長期以來我們對這一命題并沒有足夠的反思,而這勢必影響到我們對科學社會主義其他理論和實踐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其實,在這一看似簡單的命題中,交織著因歐洲革命失敗而使革命孤立在落后一國的無奈和焦慮,蘇共政治舞臺上的派別重組和權力之爭,以及或有一定深度的真正的理論分歧。1925-1927年,是蘇共舞臺上的政治派別發生分化重組從而幫助斯大林在1927年后實現其權力專斷的關鍵時期,也是蘇共黨內爆發大規模理論論戰的爭鳴時期,“一國社會主義”論便是其中首要的中心議題。因此,本文以這一時期為基本視域,試對“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的歷史成因與理論分歧略加揭示,以期促進對這一問題更加深刻全面的反思。
一、爭論的基本概念和歷史背景
在《列寧主義》一書的前面大半部分,季諾維也夫對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深揭猛批,而在后半部分對新經濟政策和社會主義在一國的勝利等問題的論述中,則把批判的矛頭隱隱地指向布哈林和斯大林,盡管其中仍然偶爾不倫不類地夾雜著某些對托洛茨基的批判。本書寫于1924年末至1925年中,正是蘇共舞臺上權力與理論格局發生某種分化與重組的轉捩點,即:為了排擠、打擊托洛茨基(及以托洛茨基為核心的左翼反對派)而形成于1922年末或1923年初的“三駕馬車”及其后發展成為的“五人小組”“七人小組”發生裂變,其中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成為“新反對派”,并在1926年中與托洛茨基派聯合,共同對抗以斯大林、布哈林為核心的執政當局。本書中前半篇與后半篇之間批判矛頭的這種轉換,正可以看作這個轉捩點的理論反映。就季諾維也夫個人來講,導致這種轉換的原因與前面的“非托”運動一樣,也是交織著權力斗爭的因素與真正的理論分歧,但與前面的“非托”運動不同的是,“非托”運動中權力斗爭占著較大的比重,而這次則理論分歧占著較大的比重。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講,雖然“三駕馬車”成功地排擠、打擊了托洛茨基,但季諾維也夫作為“三駕馬車”中的論戰主力在與托洛茨基的罵戰中雙方都元氣大傷,某種程度上反使斯大林坐收漁利,也就是說在使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威望有所下降的同時卻使原本聲望平平的斯大林開始浮出表面;再加上斯大林在總書記職位上操控紀律的職務之便和善于弄權,使得斯大林已經取代季諾維也夫成為“三駕馬車”乃至“五人小組”“七人小組”的“車老大”。權力座次的這種變化,季諾維也夫在與斯大林的深度合作中才深諳的斯大林的權謀和狡詐,以及一旦得勢之后為季諾維也夫自嘆弗如的官僚和專斷,無疑增加了季諾維也夫對斯大林的嫌隙。但更主要的還在于理論上的分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理論不具有與現實無關的純粹性,理論本身變相而曲折地反映了現實中的權力格局和物質利益。
“一國社會主義”問題是1925-1927年理論對局中的核心問題,它緣起于1924年初斯大林提出“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并在1925年與布哈林一起作出理論論證。由于這個概念容易引起誤解,因此需略作界定。“一國社會主義”不是指在一國范圍內建設社會主義,而是指在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這里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解中的,作為共產主義低級階段或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具有階級、國家消亡,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等特征,而不是現在所說的各種更加初級的社會主義。這里的“一國”也不是指任意一國,而是指像蘇聯那樣具有各種優勢的“一國”。但這個理論一旦形成之后,它自身的邏輯發展就超越了最初對它的這種界定,變成對任何國家都“普適”的理論。因此,當時斯大林、布哈林的觀點就是,不需要世界革命的背景,哪怕只有蘇聯一個國家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它也能建成社會主義——按此邏輯,當然也能建成共產主義。而作為這個理論對立面的托-季反對派則認為必須有世界革命——特別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洲革命的支援背景下,蘇聯才能建成社會主義。而且根據托洛茨基關于革命不平衡發展之限度的理論,蘇聯雖比其他國家早進入社會主義建設,但由于其各方面的落后性,因此要比遲發生革命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晚建成社會主義。這樣就形成了“一國社會主義”論(確切地說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與世界革命論的對立。
二、分歧成因與派別重組
當時所有的爭論都是在列寧主義名義下進行的,爭論各方都需要證明自己的觀點符合列寧主義正統,“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提出也不例外,更由于斯大林后來的理論壟斷,“一國社會主義”論就真被理解為列寧的獨創發明了。其實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故意地曲解混淆,就不會從列寧那里得出“一國社會主義”論的觀點。斯大林和布哈林主要對列寧偶有的一兩段引起歧義的話大作文章,而完全抹煞了列寧關于蘇聯有賴于歐洲革命的眾多論述。關于列寧的這些原話,以及如何正確地理解列寧引起歧義的那一兩段話,季諾維也夫在《列寧主義》中,特別是托洛茨基在后來更多的著作中作了詳盡的摘錄和論述,且筆者在其他論文中也曾就此做過論述,因此這里不再重復。
當1924-1925年斯大林、布哈林提出這一理論時,季諾維也夫是反對的先鋒,當時他與斯大林、布哈林共同反對托洛茨基的陣營尚未破裂,大概是對列寧主義的這種重大修正超出了季諾維也夫的理論底線,使他不能因派別問題而茍同,何況派別內部已有不睦。因此以這一問題為契機形成了1925年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區別于1923年以托洛茨基為核心的左派反對派。而托洛茨基當時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加入這一爭論,這顯然不是因為托洛茨基對此沒有明確的觀點,或者說還需要通過某種觀望以確定自己在權力斗爭中的“站隊”問題,而是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他對此沒有興趣,在經歷了1923-1924年官僚機器完全出于權力斗爭而對他和反對派的打壓之后,他此時正處于一種比較消極無為的狀態。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會發現正是這段時間托洛茨基錯失了許多扳倒斯大林的有利時機,以至于當他決心開始斗爭的時候,發現已經力不從心。他大概覺得“一國社會主義”這種問題根本不是值得爭論的理論問題,它低于批判的水平。但他后來會看到,正是這個在理論上不值得爭論的問題,卻對現實政治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產生巨大影響,于是這個低于批判水平的理論成了他終生批判的對象。另一方面,前一個階段季諾維也夫對他的無情攻擊所導致的嫌隙,也使他寧可對任何一派都處于觀望狀態,而不去認真地看待和加入他們的爭論。因此,盡管從1925年起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在理論上已形成愈來愈多的共識,包括與“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相關的對新經濟政策的理解問題,但直到1926年中兩派才真正聯合,形成托-季聯合反對派,對抗實際執政的斯大林-布哈林聯盟。
我們再來看看斯大林、布哈林這邊,他們為什么從1924年秋起提出“一國社會主義”論?為了打倒托洛茨基完全不需要這個理論,因為通過批判“不斷革命論”以及所謂的托洛茨基與列寧在農民問題上的分歧等等已經足夠了,況且此時托洛茨基已經被邊緣化。若說他們從來相信這是列寧主義的理論,則更是無稽之談。因為不僅在1924年秋之前蘇共黨內從來無人公開正面闡述這一理論,而且就連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初還說著與此相反的話。至于布哈林則一度還是黨內的極左派,當1921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對于德國革命提出“走向群眾”的口號,也就是說因條件不成熟而暫緩武裝起義時,遭到布哈林和整個共產國際極左翼的瘋狂抵制,后者認為資本主義已經不可能有任何的穩定,無產階級必須不停息地進攻,也只有這樣才能挽救孤立的蘇維埃俄國。這使得列寧和托洛茨基反過來壓制這股極左思潮,反復勸告他們:“不要太急于拯救我們,那樣做,你們將只能毀掉你們自己,當然也將使我們遭到毀滅。要有步驟地采取為群眾進行斗爭,以便進一步為奪取政權而斗爭的道路。我們需要你們的勝利,但不需要你們在不利的條件下準備進行戰斗。我們將設法在新經濟政策的幫助下,使我們自己在蘇維埃共和國內繼續存在下去。我們將繼續前進。如若你們聚集你們的力量和利用有利的形勢,你們仍然有時間在適當的時機幫助我們。”[1]75那么他們為什么在1924年秋即列寧去世后不久就開始炮制這個理論?說他們隨著時移世易而發生了某種理論認識上的變化,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特別是對布哈林來說,恐怕還是有一定的理論真誠的。但這顯然不是純粹的理論思辨,也不是發生在書齋里的事情,而是與當時的現實背景有著密切的聯系。再者,就算這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真實的理論轉變,而非弄權之術,這個理論與列寧也并無關系。根據筆者的理解,這個理論的提出基于兩種現實背景。
第一,官僚主義的保守性或者如曼德爾所說的“部分成果辯證法”,即已經取得了部分成果(如在一國奪取政權)之后以保住既定成果為目標,而背叛了原來的目標(如共產主義的世界性事業)。對于蘇聯的既得利益者即執政官僚來說,保住一國的既有政權,盡量避免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正面沖突,當然比推動世界革命安全得多、有利得多。須知世界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可能招致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反撲,而且包括蘇聯無產階級在內的世界無產階級的徹底革命性也會動搖蘇聯官僚的既定統治秩序。因此,“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提出是符合官僚特權集團的現實物質利益的。這一點原因主要適用于斯大林派,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斯大林這個人物從各方面都適于充當這個官僚集團的代言人,所以他在與各派的斗爭中總能獲勝,在他獲勝的背后是整個官僚集團的“坐大”和世界革命的總體性衰退。革命的這種衰退還表現在蘇聯的多數群眾在多年的戰亂之后也希望有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因此他們雖經受過十月革命的洗禮并對托洛茨基抱有巨大敬意,但在本能上卻對主張繼續革命的“不斷革命論”反應漠然,而更傾向于在表面上比較溫和的“一國社會主義”論。這也是托洛茨基以及后來的聯合反對派不能有效地發動群眾,而“一國社會主義”論卻日益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和群眾基礎。
第二,對歐洲革命的殷殷期待落空之后,特別是1923年的德國革命失敗之后,不得不摒棄對世界革命的期待,于是提出“一國社會主義”論。這一點大概對布哈林比較適用。據說布哈林對歐洲革命的寄望最切最極端(否則怎能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成為反對列寧的極左派呢?),因而一當發現這種寄望落空之后就發生了一種急劇的搖擺,索性放棄了對世界革命的依托,這一點大概與布哈林極端的、要求徹底性的思維方式有關。有種說法叫做人總是善于美化自己的處境,“把自己的因緣當成自己的英明”,布哈林之提出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大概就帶有這種心理色彩。但理性地說,在外界環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在一國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終究不等于在客觀上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
三、理論分歧之一:世界經濟視域中“一國社會主義”之不可能性
由于爭論各方都要表明自己與列寧觀點的一致性,而列寧畢竟說過許多關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取得最終勝利的話,因此斯大林、布哈林在提出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時又必須要玩一些文字游戲,以掩蓋與列寧的沖突。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能夠在蘇聯一國建成,但這卻仍不是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的,結論只能是這樣,這樣就在表面上規避了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與一國不能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何以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但這種勝利又不是最終的勝利呢?
據布哈林和斯大林說,雖然蘇聯有憑一國之力建成社會主義的能力和條件,但在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中不能完全地免于外部的武裝干涉和軍事顛覆,因此這種社會主義就沒有最終的保障。根據這種理論,蘇聯所應致力的方向就完全變了,特別是對歐洲發達國家,不僅不應推進它們的革命化,反而應當避免與它們的正面沖突,免得引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以便能在自己的安樂窩里靜靜地建設社會主義,哪怕是以烏龜爬行的速度。這種理論看起來很誘人,但并不因此而得以成立。托-季反對派與斯大林、布哈林聯盟在這個問題上的對立可歸結為:在沒有外部的武裝干涉的條件下,蘇聯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前者反對這一點。托洛茨基認為,在一國之內建成社會主義的主張,實際上是預設社會主義蘇聯可以孤立于世界性的經濟聯系之外,然而這一點正是不能成立的。
托洛茨基指出,十月革命本是世界性的經濟、政治矛盾激蕩下的產物,“如果沒有兩個國際條件,即第一,如果沒有大大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金融資本;第二,如果沒有推動我國無產階級斗爭的國際工人運動的理論基石——馬克思主義,世界上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我國革命。在1917年以前,革命就是通過各種偉大的世界力量的匯合而準備起來的,十月革命就是由于這些力量的匯合并經過世界大戰而產生的”[2]228。那么,在革命勝利之后,又怎能把視野局限在一國之內,認為似乎社會主義的事業可以僅僅是蘇聯一國的事情?托洛茨基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產力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在帝國主義時期這一點更以暴力的方式表現出來,“結果不僅帶來了對外貿易、人力和資本的輸出、強占領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國主義戰爭,而且使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工作在經濟上成為不可能的事”[1]46。也就是說,社會主義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性的經濟政治聯系之外,在一國之內獨善其身,更何況這種社會主義事業本是世界性矛盾的產物。針對布哈林所說的如果沒有武裝干涉,蘇聯就能撇開國際事務,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的說法,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上的發言中幽默地反駁說:“但撇開是辦不到的!全部關鍵就在于此。(笑聲。)如果‘撇開’天氣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間裸體走在莫斯科街頭。(笑聲。)但是我擔心,如果你們要這樣做,無論天氣或是民警都不會撇開你們的。(笑聲。)”[2]227(引文中標注的加粗字體若無特別說明皆為原文所有——下同)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無時無刻不處在相互聯系之中,“問題在于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經濟關系。這種相互關系決不限于所謂武裝干涉這種特殊形式”[2]227,相反地,武裝干涉只是經濟聯系的外在和延伸表現。
布哈林不知道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這種經濟聯系嗎?不會的,他還是放松對外貿易壟斷的主張者,也就是說他還要求增強、放開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聯系,那他為什么還要大談撇開國際事務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在列寧晚年反對放松甚或取消對外貿易壟斷的斗爭中,托洛茨基倒是唯一支持列寧的人,正因為深諳富國經濟的無形沖擊不亞于武裝干涉,所以堅決主張以加強對外貿易壟斷來作為阻擋的武器。但盡管如此,托洛茨基還是強調:“認為對外貿易壟斷制是絕對的保證也是不正確的。其有效程度取決于我國經濟勞動生產率同世界經濟勞動生產率靠近的速度。”(托洛茨基《經濟問題筆記》)從這里又引出了對布哈林另一個錯誤的批評,即所謂以烏龜爬行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布哈林這個觀點實際上正是建立在“撇開國際事務”的前提之下,既然能夠“撇開”,蘇聯以什么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就完全是自己的事了。但在實際上不能撇開的情況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就直接決定了蘇聯受富國經濟沖擊的程度,而蘇聯經濟建設的速度反過來“最直接最尖銳地取決于原料和裝備的進口”[2]228。因此,即便撇開武裝干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也直接、深刻地取決于它的國際環境,獨善其身的一國社會主義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社會主義不存在于真空中。后來布哈林這個以龜行速度建設社會主義的說法淪為笑柄,即便“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支持者也沒人會說撇開國際事務以龜行速度建設社會主義了。“一國社會主義”論在其發展演變中實際上發生了另外的修正,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這個理論一經提出就不再受制于最初的界定。
四、理論分歧之二:“莫須有”的農民問題
布哈林、斯大林對“一國社會主義”論還有另外一些論證,但也同樣不靠譜,如果不是更不靠譜的話。例如,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之所以認為“我國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就無法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我國的無產階級“會同農民發生沖突”。于是,布哈林進而駁斥道:據此推論,只要世界上還有大量農民存在,即便無產階級在世界上取得政權,也還是不能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會同農民發生沖突[3]。但事實上,根據我們上面的論述也可看出,托洛茨基之所以認為“我國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就無法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并非因為無產階級“會同農民發生沖突”。
托洛茨基的確說過無產階級會與曾經協助其奪取政權的農民發生沖突的話——從理論上來說并沒有錯,這種說法不僅是托洛茨基的觀點,也是列寧的觀點,甚至也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列寧雖認為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得到了貧中農甚至全體農民的支持(列寧在這一點上在不同地方的表述略有差異),但也認為隨著民主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將與農民發生沖突,他也確實在十月革命后強調鎮壓富農以及警惕中農與工人國家的對抗。只是在新經濟政策提出后,這一點才有所改變,而之所以改變,并非因為上述理論原則上不正確,而是因為蘇俄的特殊情況(孤立一國、經濟落后、農民多數)導致尚不能直接進行理論上的那種社會主義革命,并向社會主義過渡。這種觀點在農民問題上的表現就是緩和與農民的沖突,與農民達成妥協。而托洛茨基既然贊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也是贊同與農民的這種關系的。但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行,農村的經濟和階級分化日益突出,這就使托洛茨基更加強調對富農的遏制這一方面。但這也并非意味著與農民發生沖突。托洛茨基的設想是通過從政治上遏制富農的崛起,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使絕大多數農民擺脫富農影響,并在經濟上通過剝奪富農,發展工業化,以工業化的成果反哺貧中農。所以托洛茨基即便主張遏制和鎮壓富農,也還是要維護工農聯盟的,并且正是為了鞏固工農聯盟,才防止農民在富農影響下與工人政府對立。這樣說是要表明,布哈林對托洛茨基的農民觀本身是誤解的,托洛茨基也是要通過新經濟政策建立與農民的合作、妥協關系的。
就算退一步,承認在新經濟政策下,列、托之間在農民問題上的觀點有差異,前者強調妥協合作,后者強調對立沖突,那也只是涉及在蘇聯這樣的農民占多數的落后國家,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如何妥善處理工農關系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妥善處理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在一國之內也還是不能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哪怕在農民人口占少數的發達國家發生革命后,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沖突也幾乎不存在,但基于上述的經濟原因,仍然不可能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列寧曾指出,蘇聯這個農民人口占多數的落后國家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才能成功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一是正確地處理與農民的關系,二是及時地得到世界革命特別是歐洲革命的援助。布哈林在這里混淆了這兩個問題,似乎托洛茨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僅僅是因為他錯誤的農民論。其實托洛茨基的農民論本身是遭到誤解或歪曲的,而布哈林在此卻將這個本身被誤解的農民論誤解為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原因,因此布哈林對托洛茨基的這段駁斥是建立在雙重誤解之上的。
五、理論分歧之三:斯大林蹩腳的補充性論證
如果說布哈林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論證多少還帶有一定的迷惑性,那么斯大林的論證就顯得更為不值一駁。斯大林是這樣來論證之所以在馬恩原初的理論中社會主義必須在世界范圍內建成,而到了現在社會主義則可以在一國建成的:“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由于事物發展的進程而改變了自己的方向,開始走下坡路,那會怎樣呢?從馬克思的話中可以得出結論說,在這樣的條件下,否認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根據便消失了。”[4]561斯大林的意思是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走上坡路的時候不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而只能在全世界建成社會主義。這是什么邏輯呢?資產階級社會如果還在走上坡路,恰恰不可能在全世界建成社會主義,更別提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了。斯大林接著說:資產階級社會開始走下坡路,社會主義便可以在一國建成了。這又是什么邏輯呢?如果資產階級在整體上即世界范圍內開始走下坡路,那么意味著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可能。但這個過程仍然是世界范圍內的事業,并沒有因此而縮小到一國范圍。由于資產階級社會走下坡路的過程在各國是不均衡的,因此有可能在落后國家打開社會主義革命的缺口并取得勝利,但恰恰因為落后國家的資本主義潛力尚未釋放殆盡,而比其他國家更遠離社會主義,也就是說更不可能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何況由于上述世界經濟相互聯系的原因,即使富裕一國也不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呢?
又如,斯大林把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規律與“一國社會主義”論掛起鉤來,他認為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帝國主義時期的獨特規律,因此帝國主義時期與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不同,由這種發展的不平衡規律得出可以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而反對派則認為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是整個資本主義的規律,不是帝國主義時期所特有,甚至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發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因此從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得出“一國社會主義”論是無稽之談。應當說,反對派認為不平衡規律是貫穿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是正確的,斯大林強調帝國主義時期的不平衡規律有其特殊性這一點也有合理之處,但從中得出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的結論則是不成立的。如斯大林所說:“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就是:一些國家通過跳躍式的發展超過另一些國家,一些國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國家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以軍事沖突和戰爭災禍的方式周期性地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沖突加深和加劇起來,世界資本主義戰線削弱,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突破這條戰線,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4]576斯大林的這個論述應當說是基本正確的,但這是落后一國發生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依據,而不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依據。斯大林在這里仍然借“勝利”這個模棱兩可的詞匯混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勝利和建成社會主義的勝利。
此外,斯大林和布哈林認為反對派否認蘇聯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否認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等等。這些都建立在對列寧主義和反對派本身的理論的有意歪曲之上,不足深論。如果說斯大林本身是一個使他的理論服務于他的權力需要因而是沒有理論原則的人,那么布哈林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提出和論證則是他理論生涯中的一大敗筆,正如他在1924-1927年幫助斯大林打擊反對派是他人格上的一大敗筆一樣——而這兩者實際上又是聯系在一起的,因為布哈林此時對反對派的抨擊早已逾越了理論爭論的范圍,而是在官僚機器掩護下喪失了基本的理論真誠和正直人格,以至于博得斯大林的夸獎說:“他不是在同他們爭論,而是在宰他們!”(轉引自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版,第333頁)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理論或目的本身是正義的,卑劣的手段也勢必將它們導向不義的方向。這是布哈林的悲劇,當然又絕不僅僅是布哈林的悲劇。
參考文獻:
[1]托洛茨基.列寧以后的第三國際[M].吳繼淦,李潞,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資料室,1965.
[2]鄭異凡.托洛茨基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布哈林文選:中冊[M].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173.
[4]斯大林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責任編校:白麗娟)
The Debate over the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25-1927:Theoretical Differences in Context of Power Struggle
LV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seems to be an easy proposition, but it reflects the anxiety because of the isolation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one backward country due to the failure of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 faction re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ggl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real theoretical differenc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action struggles and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between 1925 and 1927 in the Soviet history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auses and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n order to generate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is issue.Key Words: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Trotsky-Zinoviev” Faction; “Stalin-Buhalin” Alliance
基金項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5YJC710039)
作者簡介:呂佳翼(1986-),男,江蘇無錫人,講師,博士,主要從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
中圖分類號:D5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349X(2016)02-0027-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