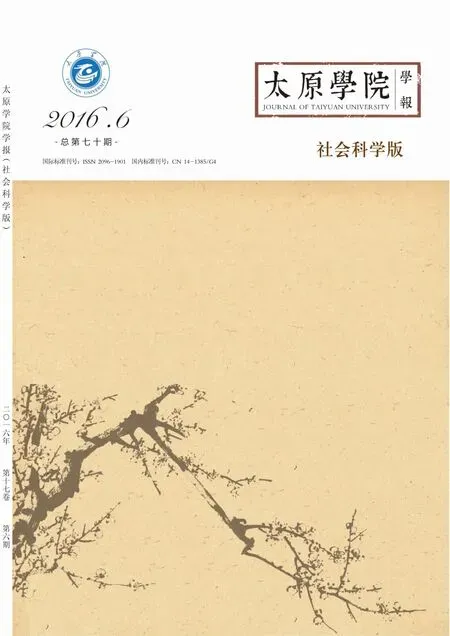《荒野獵人》之現代性反思
蘆 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3)
《荒野獵人》之現代性反思
蘆 婷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3)
《荒野獵人》影片中,唯美大氣的自然圖景與血腥暴力的生命抗爭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冷酷的旋律之下是對現代性深刻的反思。基于反思現代性這一視角,可以解讀出在工業社會這一大背景中,人們選擇逃避,希望回歸自然,在理性中尋求信仰治愈和精神永恒的愿景。
《荒野獵人》;現代性;反思
《荒野獵人》(The Revenant)由墨西哥導演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執導。此前他執導的《鳥人》同樣是一部風光無限,備受爭議的作品。《荒野獵人》講述的是19世紀一名叫休·格拉斯(Hugh Glass)的皮草獵人被棕熊傷害,又遭受喪子之痛后被同伴搶奪財物拋棄荒野,然后于荒野中求生存而奇跡生還開始復仇的故事。 影片獲第73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最佳男主角、最佳導演以及劇情類最佳影片獎;獲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導演獎以及最佳男主角獎。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這部頗有噱頭的電影都是未映先熱。電影上映后,對其評價剖析更是層出不窮,無論是拍攝手法的細膩精致,還是拍攝內容的血腥離奇;無論是導演的匠心獨運,還是演員的敬業拼搏都足顯這部電影的分量和發人深省之處。本文擬從現代性反思這一角度對這部頗受爭議的作品進行分析。
既然是對現代性的反思,那么何為現代性,又為何要反思呢?衣俊卿指出:現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啟蒙運動和現代化歷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理, 它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的地域性關聯中“ 脫域” 出來后形成的一種新的“人為的” 理性化的運行機制和運行規則。[1]現代性幾乎囊括了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他以啟蒙理性為起點,將人類,而非上帝或自然,視為支配者和控制者,在人化的環境中,借助人為手段來支配外部自然, 依照觀念的秩序來建構社會理想, 遵循自律的方式來規范個體生活。[2]然而,隨著現代性的不斷發展,人們在脫離迷信、愚昧和專制,追求理性、科學和自由的過程中也發現現代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某些內在沖突和風險性后果,正如吉登斯所言:“現代性是一種雙重現象。同任何一種前現代體系相比較, 現代社會制度的發展以及它們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 為人類創造了數不勝數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機會。但是現代性也有其陰暗面, 這在本世紀變得尤為明顯。”[3]6全球化的生態危機,虛無主義,精英文化以及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等問題都是現代性在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走向不確定和極端的表現,于是到20世紀隨之而來的對現代性的評判和反思也是遍地開花,以盧卡奇,葛蘭西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以利奧塔,福柯等為代表的后現代批評;以吉登斯,哈馬貝斯等為代表的社會學研究者……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解析或者解構了現代性。因此,可以看出在現代性日益發展并且矛盾激化的今天,對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世界的反思和反抗勢在必行。那么就《荒島獵人》而言,其對現代性的反思又是從哪些方面表現出來的呢?
一、唯美自然與血腥戰爭下的回歸訴求
(一)回歸自然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萊昂納多的獲獎感言是這樣的:……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全球變暖是真實的事件……我們需要支持世界各地那些不為大的污染制造者或大財團說話的領導人,那些愿意為人性和原住民呼吁的領袖……為了那些被貪婪的政治斗爭埋沒了的聲音……讓我們不要覺得生活在地球上是理所當然的。這是他作為演員在作品拍攝結束后的肺腑之言。的確,初看《荒野獵人》,導演花大量鏡頭表現的迷人風光、原始森林以及冰川河流、飛鳥走獸構建了一個與現代鋼筋水泥、鐵路交通完全不一樣的自然圖景。這樣的自然是吉登斯所說的“外在于人類干預范圍之外的自然界……自然是變更之源,與人類無關但對人類生活有廣泛影響”。[4]就影片中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白色、藍色、綠色和灰色組成的冷然世界里居住的是印第安原始部落。印第安部落與自然是融為一體的,他們崇尚自然,信仰的是泛神論,而泛神論的特點之一即是擬人化的自然。水壺上刻有的螺旋圖案,以及并排出現的兩個蝸牛殼便是泛神論的標志之一。螺旋標志的水壺不僅是生命之水的來源,也是格拉斯行蹤的重要線索,象征著主人翁其實一直都受“自然之神”的庇佑。影片中另一個重要意象“鷹”同樣也是印第安人崇尚自然的體現。主人翁的兒子霍克(Hawk)在英語中便是鷹的意思。而鷹在印第安文化中其一是代表勇氣、敏捷和力量;其二,它們也被稱為雷鳥,是大地及其生命的喚醒者, 是太陽的仆人, 是熱和光的傳送者,它們將信息從神傳遞給人。[5]影片兩次出現鷹的意象,第一次是霍克小時候拿著一只鷹在玩耍,第二次是蘇族人和白人的廝殺后,黑煙彌漫的天空幾只孤鷹飛翔,顯然,鷹作為使者傳遞的信息是曾經的祥和已然逝去,民族的未來將是一片黯淡。
然而,這種自然與人、自然與民族的緊密聯系直接遭到了工業化的破壞,自然成為了社會化的自然,供人生存的食物和皮草是人類最重要的目的。從影片設立的背景來看,故事正是發生在19世紀前半段歐洲諸國在北美殖民期間,殖民者于落基山脈的河域和森林中獵取河貍皮毛,從事皮毛交易的事件。這些獵皮人到來后就地建設住所,就地索取木材、水源,他們生活的裊裊炊煙和木質板房與原始自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殖民者的到來強硬地打破了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工業化的發展導致人們為謀求經濟利益而不斷占據更廣闊的空間和資源,本土印第安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模式遭到破壞,正如雷鳴所言:人與自然的矛盾古已有之,但真正現代意義的生態危機如環境污染等問題,最早出現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工業化進程而變為全球性的問題,其結果不僅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而且把整個生態系統推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6]雖然,現代性發展過程中環境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的主體性精神卻通過理性的邏輯對自然進行了絕對的控制和物質利益的瘋狂攫取。人類成為占有性主體,人類中心主義開始泛濫,欲望無限制地向外延伸,大自然成為充填人類欲望之壑的沒有任何靈性可任意肢解的干癟癟的存在。這一點,既是萊昂納多所呼吁的,也是影片中所批判的問題,更是需要引起人類反思現代性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回歸和諧
影片的回歸訴求不僅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作為自然的一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不可忽視的。《荒野獵人》中人與人關系的表征之一就是戰爭。戰爭從來都是伴隨著巨大的災難和無法磨滅的記憶的。世界歷史上兩次大戰給人類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傷痛,戰爭題材以及反戰思想在影視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多方位的表現,1960年美國拍攝了具有反思意味的影片《最長的一天》,開啟了對二戰反思創作之路,此后又產生了《巴頓將軍》(1970)《辛德勒的名單》(1993)《拯救大兵瑞恩》(1998)《父輩的旗幟》(2006)等大批反戰作品。[7]《荒野獵人》對戰爭殘酷的表述與二戰后的反戰思想其實是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戰爭在引發一系列的顯而易見的環境和人口問題的同時也引發了人類的信仰危機和對歷史的思索。此外,作為西部片,其對殖民者與印第安土著之間的糾葛也有所探討,更確切地說就是人類對種族關系的反思。
在《荒野獵人》中,電影開篇就是一段長達6分鐘的印第安蘇族人和皮毛獵人的戰爭。戰爭中雙方死傷慘烈,白人33名,蘇族人數目不詳,但就畫面來看死傷并不比白人少。白人的槍支火炮和印第安人的弓箭長矛令觀眾直面西進運動中人與人、種族與種族之間殘酷冷漠的廝殺,這場不義之戰映射出在向現代性進發的過程中所留下的陰影和痛苦是不可忘卻的。之后還出現了蘇族首領與法國皮毛獵人交易的場面,這也可以看成是一種戰爭,一種暗藏于語言博弈之下的洶涌暗流。博弈之中很清楚就可以理出殖民者與當地土著印第安人在戰爭中孰強孰弱,印第安人就是格拉斯在雪原上看見的被殖民者野狼驅逐逃散的牛群。他們慌不擇路,反抗無門,這讓人不禁想到《與狼共舞》里約翰從湖底扛出的大量牛的尸體,他說:“水里的動物不是給毒死的,而是被槍打死的。但是為什么呢,是射擊比賽嗎?”顯然不是,這是19世紀美國西部擴張過程中政府實施的野牛“大屠殺”政策,這項政策導致野牛數量銳減,從過去的6000萬頭減少到1800年的4000多萬頭,1850年減少到約2000萬頭,到了1870年只剩下1400萬頭。[8]政府對野牛的獵殺其一是出于商業因素,通過野牛皮獲得巨大的商業效益;其二是出于政治因素,擴張西部領土,切斷印第安人基本生存來源。[9]政府對野牛的獵殺就等同于對印第安人的屠殺,在這場弱肉強食的戰爭中白人殖民者通過先進的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技術,以及強烈的對金錢領土的渴望不斷威脅著現代性所想要建設的和諧社會的理想。啟蒙時代所標榜的理性自由和科學發展愈走愈偏,正如吉登斯在對現代性的分析中說道:“工業創新與工業組織和軍事力量的結合是一個過程,它可以追溯到現代工業起源的早期……同以前時代的軍事主義特征相比,新產生的現代性秩序將主要是和平。但實際情況卻是,不僅是人們所面臨的核武器威脅,而且還有實際的軍事沖突構成了現代性在本世紀的‘陰暗面’。”[3]無疑,現代性在發展過程中的負面性從影片中的反戰維度就能清楚地體現出來。戰爭在促進人類向一種現代文明所標榜的方向前進的同時對種族和生命的存在也提出了挑戰。人類歷史到底是一部發展史,還是一部血淚史?例如伊拉克這樣的戰爭暴力手段發展到今天是否也需要現代性為此負一部分責任呢?
綜上所述,《荒野獵人》中對自然和和諧的回歸訴求即是對現代性的抨擊和反思,對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以及對人類進步的古老夢想走向了一條未可知的道路。現代性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所引發的這些矛盾到底要如何解決。影片沒有給出具體答復,但卻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這是在反思現代性之后我們最需要思考的問題。
二、原始語言與宗教靈魂中的文明沖擊
(一)語言沖擊
當現代性遍及到世界的大部分角落,并沒有產生一個單一的文明或制度,而是出現了多種社會或文明的模式。現代性本身或許是單一化的,而它對世界的闡釋應該是多元化的。[10]在現代性理性企圖將人簡單化和平面化,并忽視人性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反理性的聲音。在《荒野獵人》中除了對唯美自然的重現外,對陌生化的印第安語言的重現也體現出這種反現代性傾向。
“語言是構成思想的器官”[11],它作為交際的主要工具有其獨特的語法和文法,對民族文化的記錄與傳承有著重要的意義。《荒野獵人》中主要有三種語言:印第安語,英語和法語。英語和法語自不必說,在全球化發展的今天,老牌英語國家和法語國家依托其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操控著世界格局,這使兩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都得到了廣泛的推廣。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使在場和不在場糾纏在一起,讓遠距離的社會事件和社會關系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12]而另一種語言,印第安語的出現卻讓人著實新奇。在影片中,萊昂納多所扮演的格拉斯只有15句臺詞,其中約一半為英語,另一半為波尼語(Pawnee)。波尼語即是波尼族人所說的語言,同影片中蘇族語一樣,同屬于印第安語言。波尼語在世界關于語言狀況的權威網站“民族語”(Ethnologue:Language of the World)上被評定為8B級(nearly extinct),在世界范圍內約有10人會說這種語言。這樣陌生化的語言為我們掀開了印第安部落神秘面紗的一角,展示出了與現代社會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語言為各自的民族發聲。當把影片看成文本,將語言和人物情節結合起來時,我們可以看出導演在更深層次上對傳統文明的回歸訴求和對現代語言的強烈沖擊。
從語言內容上看,以格拉斯為中心的波尼語要么表達的是父子之間在危險中的扶持鼓舞,要么表達的是夫妻之間在生命攸關時刻的禱告召喚,要么表達的是同族之間的在亡族復仇時的悲愴剛烈。這些情感在影片中并沒有用英語和法語語言表達出來,并非是這些語言不能表現這些情感,而是影片刻意想要強調“邊緣”語言在現代性發展中對現代工業文明的反叛。但就歷史結果來看,這種反叛是并不成功的。現代性以全球化為表征,英語成為全球通用語言,人們為了達到融入社會,在與人交往中獲得一席之地,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中立足的目的,不得不順應這股全球化潮流。學會了法語的蘇族首領便是“先進”語言憑借其強大的工業財富壓迫“原始”語言的初期表現。唯我獨尊的英語和法語以無情的態度對異己語言進行討伐,蘇族首領失去女兒,波尼同族家破人亡都是這場討伐所帶來的殘酷后果。
此外,除了對邊緣語言世界的塑造之外,臺詞語言的缺乏也是對現代性反叛的表現之一。影片中大量的留白,以及影片主角匱乏的語言臺詞無疑是對這個語言魅力時代的一種反抗。但這樣的沉默并沒有抹殺或者削減影片魅力,人物的情感通過演員極富張力的面部肢體表達和外在自然環境的渲染表達出來,強化了影片的神秘色彩,使得觀者在觀影時情不自禁地跟隨影片發展而情感起伏,而不是理性地推演語言表達的淺層深層含義。
(二)信仰沖擊
除了語言沖擊之外,《荒野獵人》中對精神信仰這一神秘力量的追索同樣是對現代文明沖擊的表征之一。現代性肇始于啟蒙運動,其核心是推崇理性,現代化的過程不僅造就了輝煌的物質文明,也生成了按照理性邏輯運行的文化價值。在中世紀之后的新時代,宗教表現出世俗化和解神秘化的的特點,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逐漸被理性權威所取代。宗教信仰對象和主體逐漸分離,宗教和現代理性之間的矛盾也變得越來越不可調和。《荒野獵人》中西方宗教表現得最突出的有兩幕,其一是費茲杰拉德在山洞中與布里吉對話時說道:“上帝會指引我們方向。我父親并不相信宗教,如果你不能養它,殺它,吃它……他說‘我找到上帝了’。”上帝的光輝仍然照亮著這些亡命之徒的內心,個人力量的卑微讓人在艱苦復雜的環境中仍然尋求上帝庇佑,就算是像費茲杰拉德父親那樣唯利是圖的人最終也逃離不了宗教和上帝的束縛。可見宗教力量對現代性的沖擊是不可避免的一種內在精神訴求。第二幕是格拉斯在夢中見到的壁畫和教堂。壁畫上描繪的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教堂是一幅荒涼破敗的景象,只剩下斷井頹垣。作為白人的格拉斯會夢到宗教場景并不奇怪,但他在極度絕望的時刻并不是在向宗教尋求庇佑,反而宗教信仰就像教堂建筑一樣坍塌傾倒了。有意思的是格拉斯夢見的教堂里有一只黑山羊,而在《圣經》中,黑山羊與綿羊相對立,代表著邪惡,有害群之馬之意。宗教的這種轉變與格拉斯經歷家破人亡,慘遭背叛喪子有莫大的關系。波尼族給予他的美好生活體驗與功利物質社會下個人的丑惡的極大反差使得他拋棄原有信仰,人在他眼中是不能被救贖,不能被原諒的,這也是他頑強走上復仇之路的原因之一。
但宗教信仰并不是信仰的全部內容,正如托克維爾所言:“在一切教條性信仰之中,我認為宗教方面的教條性信仰是人們最有希望的。”[13]宗教信仰并不能和信仰劃等號,或者可以說在精神方面宗教信仰是內含于信仰的。信仰存在的方式與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內在相關,信仰是對于人性的終極關懷,表達的是人類對自身超越性的期盼和希冀。但從現代性這一角度來看,信仰到底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呢?在《荒野獵人》之中格拉斯信仰的主要來源就是他的妻子。在被棕熊傷害、生命攸關之際,還魂而來的妻子鼓舞著格拉斯,“當強風來襲,你站在樹前,你若看著樹枝,你會看到它落下,你若看著樹干,你會看到它的強韌。”靈魂是理性不能解決的問題,同樣以靈魂為方式帶給格拉斯支撐生命的強大力量也不是光憑理性能夠說得清的。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精神和信仰對現代性的沖擊——“現代性的真正問題是信仰問題……新的支撐點已經證實是虛幻的,而舊的鐵錨也已沉落水底。如此情勢將我們帶回虛無主義,沒有過去和未來,只有無盡的虛空。”[14]現代性狀況下信仰走向虛空,這是工業社會,物質增長破壞了基于道德原則的人際關系的必然走向。而被妻子所守護的格拉斯在不斷迷失的過程里,心中仍然留有一片凈土,仍然緬懷曾經的幸福生活。影片的結尾雖然沒有給出格拉斯的最終結局,但在雪地里對他微笑的妻子是否象征天國的團圓,即格拉斯對家庭幸福生活信仰的回歸。
綜上所述,《荒野獵人》給觀眾拋出了一個關于人類存在的非理性問題。通過對印第安種族陌生化的語言表達和對宗教靈魂的終極探究,可以看出導演呼吁在有機的社會里,個人需要表達訴求,為自己發聲,需要追索心靈,重建信仰。這是對現代文明所強調的物質、理性和功利的沖擊。
三、英雄末路與復仇執念中的孤勇對抗
(一)格拉斯的反英雄形象
由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荒野獵人》其實是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藍本的。萊昂納多扮演的角色即是美國西部拓荒時期的硬漢英雄——休·格拉斯。格拉斯早年生活經歷已無從考證,現在較流行的版本是:在約1816年,格拉斯被私掠船所俘,被迫當了兩年的海盜,在海盜船駛經加爾維斯頓島附近時,格拉斯跳海逃走。上島之后,又被印第安波尼族人擄走,與當地波尼族女人成婚。之后的故事便有跡可循,《荒野獵人》所選取的歷史故事也是從此開始。1822年,格拉斯應征成為落基山脈皮草貿易公司向導。1823年,包括格拉斯在內的皮草獵人隊伍在密蘇里河平原遭印第安人伏擊。為避免遭遇更多攻擊,獵人隊伍繞道內陸,向黃石河進發。進發過程中發生了令人驚嘆的殺熊事件。殺熊使格拉斯身負重傷,于是獵人首領阿什利不得不只留下吉姆·布里吉(Jim Bridger)和約翰·費茲杰拉德(John Fitzgerald)照看格拉斯。而害怕印第安人伏擊的吉姆和費茲杰拉德決定提前為格拉斯送終。但,格拉斯憑借驚人的意志力頑強復活,并開始復仇。他先找到布里吉,面對著這個充滿希望的年輕人,格拉斯最終放過他。之后,格拉斯毅然決定去找費茲杰拉德復仇。但費茲杰拉德當時已經參了軍,由于殺害軍人是犯法的,格拉斯只能從費茲杰拉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來復槍,也算圓滿地完成了復仇任務。最后,格拉斯回到了密蘇里河,做回了皮毛獵人。于1833年,死于與印第安人的交戰中。
《荒野獵人》在真實歷史事件的基礎上,大大地豐富了格拉斯這一角色。首先,霍克和妻子的出現,從一個側面刻畫了格拉斯的情感世界。其次,格拉斯的回歸之路的艱難歷程被細致地表現了出來。再次,格拉斯對費茲杰拉德的復仇結果是費茲杰拉德的死亡,而不是一把簡單的來復槍。最后,影片并沒有交代格拉斯的去向,而是為觀者留下懸念。那么,這些場景的豐富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這就涉及到對格拉斯這一復雜形象的探究。筆者認為,作為西部拓荒時期的硬漢英雄形象的格拉斯在影片中更多地反應出來的是他反英雄的特質。稱其為英雄,主要原因是他的堅毅果敢、勇猛無敵符合傳統上對英雄的定義。而他作為英雄與其所具有的反英雄特質是不相悖的。賴干堅接受了美國評論家阿布·哈桑的觀點,他認為西方的英雄主義觀念是變化的、發展的。英雄主義從啟蒙運動前的神話英雄向啟蒙后的世俗英雄發展。隨著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小說興起,英雄主義開始崩潰,非英雄出現。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道主義的極度虛妄宣告了理性主義的破滅,反英雄伴隨著后現代主義產生了。[15]
首先,反英雄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具備例如高貴優雅、智慧非凡等傳統英雄的特征了。在影片中,格拉斯更像是人和野獸的結合體。他有人的外形、人的智慧以及人的情感,但他在雨林之中徒手殺熊,在回歸路上生食魚類,剖馬取暖等等行為表現得更像是野獸。而這種野獸的行徑不會被受過教導的人所接受,更加不會成為典范而被頌揚的。其次,作為反英雄形象,其自身是處于一種搖擺不定的困境之中。從格拉斯來看,一方面,西部開拓中發生的戰爭殘暴地破壞了他的家庭,帶走了他的親人和幸福生活;而另一方面,為求生存,他不得不依附于這種開拓運動,成為皮毛獵人的一員。這種矛盾狀態致使他失去兒子,甚至差點失去自己的生命。最后,為了追求自我本質,反英雄會將自己置于與社會對立的地位。根據歷史事件可以推測,《荒野獵人》的預設應該是格拉斯被俘逃跑之后,被波尼族人所救,并成為波尼族女婿。從格拉斯被俘就能窺見當時的社會海盜猖獗,普通人的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利益的驅使使人不再受道德的約束,人在社會中已經走向異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格拉斯的逃脫便開始顯現出其與社會的對立。他從現代社會逃向不被現代社會所容的波尼族群落,他依返自然,逃向真正給予他心靈安逸和家庭幸福的所在。而家破人亡之后,兒子霍克的陪伴和妻子夢中的召喚更是他逃離現實、獲得生存的手段。當這種手段受到費茲杰拉德的迫害之后,他毅然決然的復仇之路也就更顯悲壯了。正如賴干堅所言,“在現代西方傳統的理性原則已受到懷疑, 已難以充當個人行為的準則和維持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標準……個人不過是結構松散的群體社會的一分子……自我既受到本能欲望的驅策, 又受到瞬息萬變、混亂不堪的外在世界的煎迫。自我處在內外攻逼的困境中, 再難以維持自身的平衡, 結果導致精神分裂。”[15]格拉斯便是如此,他在混亂物質的社會中成為非人,在自我追求中失去依靠,精神的分裂反而成為他幾乎變態的執著。作為一個反英雄形象,他的悲劇不僅是現代社會他人施加的壓迫,更是他自己內在矛盾的激化所造成的。
(二)孤勇對抗
格拉斯的反英雄形象固然是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的結果。然而就現代性反思的維度而言,影片在解決現代性問題上其實給出了許多的思考空間。格拉斯對宿命的孤勇反抗和對自我本性的執著追求是對現代社會強有力的一擊,也是時代背景下發人深省之所在。
費茲杰拉德毫無爭議應該是《荒野獵人》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影片中著重刻畫了在留下來照顧受傷的格拉斯一事上,費茲杰拉德與隊伍首領不斷地討價還價,以及在殺害霍克之后,他回到營地并騙取錢財的做法。作為貫穿影片的重要任務之一,費茲杰拉德本身就已經成為物質的代表,在金錢的驅使下,他能不擇手段地騙人,甚至殺人,完全成為現代性之下物化的代表之一。這種物化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盧卡奇認為, 物化不只存在于經濟層面上, 而且在整個資本主義文化領域都是普遍存在的。人的物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機統一相聯系, 而是表現為人占有和出賣的一些“ 物”。[16]120人的物化過程直接與人的理性化過程相關,費茲杰拉德也正是在這條道路上逐漸走向滅亡。格拉斯對他的復仇除了是因為殺子之痛,更深層次上即是對這個變態的社會的復仇,是對失去了信仰,自私冷漠的現代人的復仇。所以,他不會放棄復仇,成為人人敬仰的“以德報怨”的英雄。
然而,他的復仇卻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他不是像歷史事件那樣通過一把來復槍了事,通過對法律的遵守和忠誠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也不是手刃仇人,為子報仇,完成現實意義上的勝利。而是松開雙手,任由蘇族首領終結費茲杰拉德的生命。這一結果正應和了那句“復仇是掌握在造物主手中”的臺詞,也是在遇到波尼族同伴后格拉斯復仇心態變化,個人本質重塑的體現,是“為反撥現代性引致的精神家園破毀與人性異化,擺脫沉溺于現代性功利追求,強調對當下性的發現,重視人的存在及其意義的澄明之境的體現。”[6]119影片最后格拉斯妻子的出現,也正是他精神的回歸。
四、結論
綜上所述,《荒野獵人》在生態、戰爭、語言、信仰以及反英雄等方面都體現出對現代性的反思。這不僅是對自然生態平衡的思考,也是對人類社會和個人本身精神平衡的思考。這種思考超越了時代的界限,在電影藝術里為我們講述了現代社會理性發展的極端化過程中給人類社會和人類精神帶來的巨大創傷,贊揚了信仰與靈魂作為一種永恒的力量能支撐人不斷追索,不斷反抗,甚至是改變因果而追求內心的澄凈。
[1]衣俊卿.現代性的維度及其當代命運[J]. 中國社會科學,2004 (4):13.
[2]楊大春.反思的現代性與技術理性的解構——海德格爾和福柯論現代技術問題[J]. 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2):48.
[3]Giddens Anthony.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4]安東尼吉登斯.自反性現代化[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1:98-99.
[5]伊麗莎白·阿特伍德·勞倫斯.平原印第安人太陽舞動物角色的象征意義[J].馮莉,譯.藝術探索,2006(2):43.
[6]雷鳴.危機尋根——現代性反思的潛性主調[D].山東師范大學,2009:119.
[7]Lawrence,John Shelton. We’ll Always Have the Movies: American Cinema During World War II[J].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2008(1):273-274.
[8]Lott,Dale. American Bison: A Natural History[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167.
[9]蔣棟元.環境變遷中的美洲野牛:美國印第安人的文化圖騰[J].貴州社會科學,2013(8):75.
[10]許丹燕.從《魔戒》看托爾金對現代性的反思[D].浙江大學,2010:20.
[11]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65.
[12]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趙旭東,方文,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223.
[13]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524.
[1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趙一凡,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28.
[15]賴干堅.反英雄一后現代主義小說的重要角色[J].當代外國文學,1995(1):140-141.
[16]張闖.盧卡奇的現代性批判-基于物化理論[J]. 武漢大學學報,2009(6):720.
[責任編輯:何瑞芳]
Modernity Reflection of the Revenant
LU 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Wuhan 430063,China)
The Revenant is absolutely one of the blockbusters in this year. With this film, Leonardo finally ended his career of being nominated for Oscar in the past 22 years and got the Best Actor Oscar. In the film, the beautiful natural image and the bloody violence form a sharp contrast, which, under the cold melody, generates profound reflection to modern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reflection, this paper is going to analyze that in industrial society, people choose to escape, hope to return to nature and seek the spiritual healing and eternal faith in rationality.
The Revenant;modernity;reflection
2016-06-30
蘆婷(1993-),女,湖北武漢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學專業2015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后殖民文學。
2096-1901(2016)06-0073-06
J9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