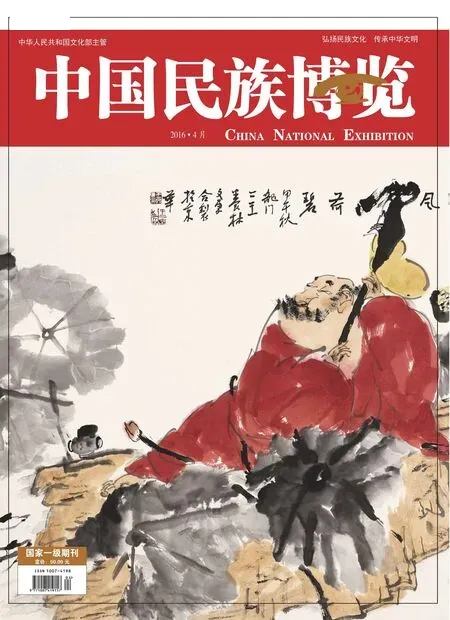“歷史 ·歷時· 流變”-拉卜楞寺儀式音樂“道得爾”研究的三個維度
陶 莉
(西北民族大學,甘肅 蘭州 730030)
?
“歷史 ·歷時· 流變”-拉卜楞寺儀式音樂“道得爾”研究的三個維度
陶莉
(西北民族大學,甘肅蘭州730030)
【摘要】“歷史/歷時”為西方民族音樂學儀式音樂的兩個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儀式音樂“道得爾”的多元歷史證據、儀式音樂與文化建構、“道得爾”歷史流變三個角度,對相關文獻進行整理和研讀,實現對拉卜楞寺儀式音樂“道得爾”在“歷史/歷時” 研究領域的重要個案的理論取向與實踐價值探討。
【關鍵詞】歷史/歷時;儀式音樂;拉卜楞寺;“道得爾”
西方音樂學發展伊始,一些概念(如本文將要闡釋的歷史、歷時)不僅注定成為學術分流的信號,而且在音樂學發展中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使命。19世紀末音樂學家圭多·阿德勒(G uido A dler)將系統音樂學和歷史音樂學進行整合,將比較音樂學歸于系統音樂學研究之下①,歷史 /歷時的關系開始受到關注。文章以拉卜楞寺儀式音樂“道得爾” 研究為主要視域,基于民族音樂學儀式音樂“歷史 /歷時”相關英語文獻的梳理和研讀,呈現拉卜楞寺儀式音樂“歷史 /歷時”研究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儀式音樂“道得爾” 歷史證據
歷史 /歷時作為儀式音樂的重要概念在音樂史學、宗教學及民族音樂學中頗受關注,在方法論上對“多元歷史證據”的吸收及歸納,最能凸顯民族音樂學特征。此外,口述史料、音響制作、現場表演等具有民族音樂學共時特性的資料宜可成為音樂學家們重現過去的重要證據。正如理查德·維德斯(R ichard Widdess)所言“對新近和遙遠的歷史進行觀察,有些口傳資料以及錄音、圖像考古等資料必須一起結合起來做跨學科的研究。②這些歷時與共時文本呈現的不僅是儀式和儀式音樂的歷史、歷時的運動進程,還蘊涵著儀式主體對傳統文化的二度創作與詮釋。
藏族學者就拉卜楞寺儀式音樂的發展大多是以書面史料的記載進行的。史料為主的敘事方式,秉承著對傳統歷史記憶的“書寫”,一直成為東亞國家音樂歷史研究的重要手段。儀式音樂的“真實性”(authenticity)需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這就成為民族音樂學理論研究的目標。國內有關記載拉卜楞寺歷史的諸多史料證實“道得爾”是藏族“政教合一”制度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遷這種傳統音樂逐漸轉化,最初只限定于寺院各種宗教場所表演,故稱為佛宮音樂或叫佛殿音樂, 它與旗隊(Zhal dar pa )、 傘蓋隊 (Vdugs bzung pa)和香火隊(Spos Vdren pa)一起組成嘉木樣大師的儀仗隊。“道得爾”在樂器上盡管沿用了宗教音樂中使用的樂器和法器,在表演形式上也體現了藏族宮廷儀式音樂形式,但表演內容和風格歷經朝代更迭已具有世俗化傾向。附著歷史沉積的“道得爾”沒有固化在博物館,它與時俱進,不斷發展。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探尋其“歷史的真相”,梳理歷史脈絡,對儀式音樂是極為重要的。
1709 年 6 月,一世嘉木樣返鄉途中,由于連日舟車勞頓,隨員便稟呈嘉木樣,想調劑一下單調的行程奏奏音樂。大師經過思考后予以容允。僧侶們煨桑祈禱,燒香叩謝活佛慈悲之恩,每到宿營處,奏樂自樂,相沿成習,成為拉卜楞寺寺規。“道得爾”最初以嗩吶為主要樂器,由“黎明晨曲”、“臥寢曲”等五十余首傳統宗教樂曲構成。拉卜楞寺創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本名嘎丹夏珠卜達吉扎西益蘇奇貝瑯(意即具喜論修興旺吉祥右旋寺),簡稱扎西奇(吉祥旋)寺。康熙五十三年(1714)建成拉章(即嘉木樣佛宮),后“拉章”音變為“拉卜楞”沿襲至今。1711 年,在盛大的慶典典禮上,由幾人組成的樂隊奏樂示慶,“道得爾”樂隊的雛形即以形成。1716 年,嘉木樣大師親臨講授密宗經典以及歌贊音調并將之歸為下續部學院的修習體系中。二世嘉木樣久美昂吾在位期間(1743—1791),貢唐倉·丹貝仲美(1762—1823) 編寫了《至尊米拉日巴語教釋·成就密意莊嚴》一書,將書中“語教釋”改編成“恰木”(Vcham)即“法舞”。該劇結合民間歌舞和神舞藝術,構成了有說有唱、有舞有韻的六場劇目,對拉卜楞寺佛宮音樂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世嘉木樣久美堅措(1798—1855),恬靜簡出,墨守成規,在掌管拉卜楞寺期間對拉卜楞寺佛宮音樂的建樹史料均無記載。從一世到三世,“道得爾”的發展一直限于雛形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演奏的曲目、樂器較少,樂隊編制不固定,并且受限于特定的演出時間、地點的限制,在社會上未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四世嘉木樣尕藏圖丹旺秀在位期間(1860 —1916)對拉卜楞寺舊習進行一系列改革,為“道得爾”的鼎盛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世嘉木樣風度儒雅,善應酬交際,足跡踏遍各大藏區講經護法。對音樂甚是喜愛,自己還會演奏“阿日扎聶”琴。常在別墅奏樂舉行康藏歌舞表演,并親自加以指導。據《第五世嘉木樣紀念集》 記載,嘉木樣到五臺山進行朝禮,僧眾樂隊奏起了渾厚的佛樂,臨行時,帶走了《五臺山》等樂譜。后到雍和宮覲見光緒皇帝及途中路經蒙古,總能聽到優雅的樂曲。決定回去后整編樂隊。五臺山、蒙古、承德等地的喇嘛雖多為蒙古人,但受漢族民間音樂的影響,演奏的樂曲具有別樣民族氣息。四世嘉木樣離開蒙古時,隨行有蒙古族樂師,對“道得爾”進行訓練,演奏技巧有較大提高。
五世嘉木樣·丹貝堅參(1916—1947)正值中華民國肇造之初,百廢待興,雖一生短暫,但其睿智英明,胸懷開闊,治教之余學習漢文、英文,克服阻力積極推行一系列漢藏文化交流、發展民族教育、重視民族團結等舉措。他創辦拉卜楞寺青年喇嘛學校,親自指導喇嘛學習《文成公主》,宣傳吐蕃時期藏王松贊干布與漢藏印尼文化的交融。 “道得爾”隨之也深受安多地區廣大僧俗的喜愛。
“道得爾”非常注重的雙重“口頭性”資料的研究。雙重“口頭性”即原始材料的‘口頭性’,和音樂本身的 ‘口頭性’,其特殊性有別于傳統歷史學的研究。雷古拉·庫萊希(R egula Q ureshi)認為:民族音樂學的“口頭文本”需參考大量非音樂參數進行歷史研究。③現今有關“道得爾”的口頭性資料一部分存于寺院上下續部的史料中,另一部分存在于當下的儀式表演中。流傳于藏區的說唱文學《格薩爾》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口頭性資料,它是由韻文和散文構成的說唱口傳文本,其絕大部分語言至今仍流傳在人們的口頭,只是在語音和構詞上各地藝人各具方言特征。學者們對上述這些口頭性資料進行口述訪談和儀式錄音等相關材料進行整理后認為:第一,各藏區音樂文化遺產的口頭傳承以及圍繞這一傳承的史學觀念問題;第二,專業音樂家群體與口頭傳承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三,藏傳佛教觀念及制度與儀式音樂的歷時進程中“穩定性 /流動性”等基本規律之間的關系問題,通過口述材料和現場材料還原后發現,不同部落的史詩文本存在著較大差別,像《格薩爾》“道得爾”這類表演具有明確的儀式性和宗教性,它需要將特定場合與特定的主題聯系起來共同彰顯地方特色。這類史詩需要對口述、表演及文獻等各種材料進行多重互證方能體現藏族的傳統。所以強調材料的多元性是民族音樂學歷史研究的一大特點,當相關材料作為對歷史的追溯被一一呈現時,它們對還原歷史真實性功能才能顯現出來。
二、“道得爾” 歷史文化建構
人類文化史的形成中,少不了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的參與。梅里亞姆曾在《音樂人類學》中論證了音樂考古學、歌詞等與文化的關系。多角度地論證了在文化史建構中音樂的介入及所起到的作用問題。在諸多“儀式音樂與文化史建構”的個案中,筆者以為埃林森的《曼陀羅之聲:藏人儀式音樂的觀念和聲音結構》(Mandala of Sound:Concepts and Sound Structures in Tibetan Ritual Music.”,1979)一文具有相當代表性,它全面地探討了藏族宗教音樂的發起、傳播等與文化、社會相關的問題,對拉卜楞寺“道得爾”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此外還特別強調了儀式樂隊中樂器的使用,對藏人歷史觀念的塑造極為重要。作者發覺藏族音樂歷來擅于向外來者學習,不斷豐富和擴充樂曲并重新組合、選擇與拼貼之后,在不同時間的同一或不同儀式上展現其獨特的風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拉卜楞寺從 1709 年興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對于一個佛教寺院來說歷史還是短暫的,所以拉卜楞寺的佛教文化更多的吸收了來自其他地區佛教文化的元素,其中包括西藏的佛教文化和漢族的佛教文化,有些甚至超出佛教范圍的宮廷藝術也被采納。“道得爾”之所以發展成今天在海內外頗具影響力的宗教樂隊,與其廣開佛門,兼收并蓄的藝術思想密不可分。然而 “道得爾”在傳承過程中,音樂形式在民族文化中也發生一些變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首先,“道的爾” 主要是在一些禮儀性活動而非重要的佛事活動中使用。其次,“道得爾”是由藏族宮廷音樂與外來民族音樂融合而成,其音樂形體容易發生變異。目前一些學者研究認為“道得爾”音樂形態的來源與西藏佛教寺院的音樂“噶爾”(也叫卡爾樂)有關。國內藏族音樂文化研究專家田聯韜教授在其《藏族宮廷樂舞噶爾考察研究》 一文中認為,“噶爾”是源于今巴基斯坦所屬巴爾蒂斯坦等地的樂舞,后成為拉薩布達拉宮為上層僧侶、貴族、官員服務的樂舞藝術,因其功能、屬性而定為宮廷樂舞。“噶爾” 樂舞使用的樂曲、服飾、表演等方面,體現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殊風格。④西藏音樂學家格桑曲杰在其《西藏佛教音樂文化跨地域、跨民族的傳播與流變》一文中也提到:卡爾樂是一種具有伊斯蘭風格的歌舞藝術形式,產生于巴爾蒂斯坦,而后經拉達克傳入西藏。巴爾蒂斯坦居民最初信仰佛教,后改信伊斯蘭教后卡爾樂隨即產生。⑤美國音樂學者 A.馬克吐溫(A.Mark Trewin)在《西藏宮廷禮儀音樂噶爾》(The Court Ceremonial Music of Tibet)中認為西藏宮廷樂舞“噶爾”來源于巴爾蒂斯坦與拉達克,⑥他在當地獲得第一手材料后得此結論。后來“噶爾”在衛藏和昌都的部分大寺院中成為寺院禮儀音樂。在噶爾瑞(舞蹈音樂)中也使用噶爾伴奏。后來“噶爾”傳播到其他藏傳佛教寺院,音樂形式先后出現較大變異。但經過學者考證,拉卜楞寺中流傳的“道得爾”其音樂形態基本可以認定是“噶爾”的變體。這主要有從幾個方面原因:
第一,在藏文中“道得爾”和“噶爾”的朵達瑪的念法是一樣的,都是指迎請鼓樂的意思。一些史料也記載了“噶爾”隨達賴出行并在宴請、迎接等場合隨時演奏的情況。
第二,在“噶爾”流傳到西藏初期,所有盛大活動中演奏的樂曲形式就是朵達瑪。“噶爾”在五世達賴時期從巴爾蒂傳到西藏。當時西藏在政治和宗教上實現了政教合一制度,最高統治者實際上是達賴喇嘛,拉薩宮廷的“噶爾”也就成為為宗教領袖服務的目的。一些大寺院相繼從拉薩引進“噶爾”歌舞樂在本寺的迎請、宴饗、慶典儀式中使用。一世嘉木樣當時與五世達賴喇嘛一起被當時西藏的蒙古固始汗部首領拉藏漢供奉為上師,一世嘉木樣具有相當高地位與身份, 其在西藏的 41 年中正值五世達賴喇嘛政權興盛期,達賴喇嘛深受清朝康熙皇帝的信任,在蒙藏地區人民心目中威望極高,“噶爾”當時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布達拉宮的宮廷音樂。后來五世達賴圓寂,時局陷入混亂,一世嘉木樣返回夏河并帶回了“噶爾”,這就成為“道得爾”的前生。
第三,“噶爾”的特點之一是它的禮儀功能。“道得爾”盡管三百年來發生了很大變異,但它的禮儀功能也一直沒有變,它不參與法舞、法樂及誦經等純宗教音樂的演奏。所以從禮儀樂隊的性質來看與西藏的噶爾依然一樣。
第四,今天拉卜楞寺的“道得爾”的演奏形式主要是以立奏為主,在過去還有一種是馬上騎奏式,20 世紀 50 年代在拉薩依然可以看到這種演奏形式,這種騎奏式與西藏宮廷寺院的“噶爾”完全一樣。今天的拉卜楞寺的“道得爾”演出過程中的一些場景與當年“噶爾”的演出場景,包括組織形式、機構、演員的人數及演出時的著裝也及其相似。
所以,經過對上述史料的甄別,現今拉卜楞寺的“道得爾”其音樂形態基本上是“噶爾”的變體,這也體現了儀式音樂與文化史建構關系的佐證。
三、“道得爾” 的歷史流變
民族音樂學家內特爾對民族音樂學歷時研究提出了兩個宏觀視域:一是對過去發生事件進行重構,二是對現實中發生事件的變遷進行觀察,并將音樂的變遷與音樂的跨文化研究放置于共時性與歷時性交匯的場域中,這是20世紀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重點。布萊金(John Blacking)、卡托米(MargaretK artomi)和梅里亞姆等一些西方學者都在這一領域進行著嘗試。
“道得爾”作為一種特殊混合藝術形式,其形成與流變中發生的變異既是基于血緣關系的繁衍,又是藏傳佛教音樂傳承發展的一種文化體現,同時還涉及到同宗音樂事項問題。同宗音樂是一個立體、多面的音樂事物,它涉及到歷史、傳播、民俗及人類學的相關知識。“道得爾”在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傳播中,糅合了宗教與民間音樂諸成分,在發展過程中注重保持自己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特色,最終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由于受限于宗教特殊性,當前“道得爾”研究主要涉及一些概述性的文章以及“道得爾”藏文工尺譜方面的研究,而針對“道得爾”歷史流變、同宗音樂事項的世襲以及傳承人等問題尚缺乏“在場”研究,這也引發筆者對藏族宗教音樂研究的一些思考: 首先,與西方學者通常將藏族音樂視為一個統一整體,在一種大環境、大背景中關注藏人與其他國家人群間的跨文化交流所不同,中國學者將藏族音樂分為不同的方言區或色彩區進行研究。由于藏傳佛教音樂包含的內容與形式極為豐富,各方言區與各教派寺院的宗教音樂既有共性又有差異,想要比較全面、細致的考察、研究藏傳佛教音樂的成果,難度頗大。雖然近年來國內音樂學界的漢族學者和藏族學者經過了多年努力,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集中研究藏傳佛教音樂的專著在中國問世。 其次,相對于西方學者的研究視域,中國學者更關注于世俗音樂,特別是民間音樂中的民間說唱、民間歌曲、民間歌舞、藏族戲曲、民間器樂。在這些世俗音樂中最流行的表演形式就是各類歌舞,因而各類歌舞風格的研究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他們多從“美”的角度強調藏人創造音樂的娛樂性功能。而西方學者關注的焦點通常是藏族宗教音樂,研究的重點通常是不同類型的記譜法和儀式表演方式。20世紀除了發表一些學術性的文章外,還出版了一些頗有分量的專著。再次,隨著近年來的國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中西方在一些領域的交流合作已經取得一些成績。 但就對國內、國外的有關藏族音樂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后發現,我們與西方學者在某些學術領域的交流還是很
欠缺,更不用說引用對方學界的研究成果,希望今后能通過互相學術往來,加強溝通與交流,共同促進民族音樂學的繁榮與發展。
注釋:
①詳細內容參見阿德勒發表于1885 年的重要文獻《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的》中相關論述。Adler,Guido’s.1885.“The Scope,Method,and Aim of Musicology”(1885).A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an Historico -Analytical Commentary,translated by Erica Mugglestone.Yearbook foe Traditional Music 13(1981):1-21.
② Widdess,Richard.1992.“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in Myers,Helen ed.Ethnomusicology:an Itroduction.New York:W.W.Norton.
③Qureshi,Regula.1991.“Sufi Music and History of Oral Tradition.”In Blum,Stephen;Bohlman,Philip V.and Neuman,Daniel ed.Ethnomusicology and Modern Music History,pp.103-1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④宗喀·漾正岡布,謝光典.《河南親王與拉卜楞寺關系考》寧夏大學學報,2011,1。
⑤田聯韜.《藏族宮廷樂舞噶爾考察研究》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3,1。
⑥格桑曲杰.《西藏佛教音樂文化跨地域、跨民族的傳播與流變》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2, 2。
參考文獻:
[1]楊曉.歷史證據、歷史建構與歷時變遷—儀式音樂研究三視界[J].中國音樂學,2011(3).
[2]瞿學忠.“道得爾”:此音傳自拉卜楞寺[N].中國民族報,2010(7):13.
【中圖分類號】J608
【文獻標識碼】A
作者簡介:陶莉,女,甘肅省蘭州人,西北民族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音樂學、音樂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