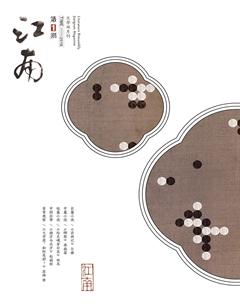下南洋
2016-01-08 01:19:24老四
江南
2016年1期
一
徐文多發來一張照片,是他與同伴的合影。在熱帶陽光的安撫下,他胖了,也更黑了,但與身旁的同伴比起來,依舊顯得白里透亮。我把興趣點集中到同伴身上,問道:“黑人?”徐文多發過幾個“No,no,no”,說:“我聽不懂他說話,一會兒說孟加拉,一會兒說母加拉,我猜應該是孟加拉。當年學的英語,我現在只記得ABC,還有Yes、No,其他的都還給珍妮婦女了。”珍妮婦女,是我們的初中班主任兼英語老師。
我問他在那邊怎么樣,他發來幾行字:“整個工地連個女人的毛都沒有,我看到母雞都忍不住渾身哆嗦。”
才半個月,徐文多就忍不住了。說到女人,我就想起前女友——徐文多見過的,還說她是平胸,不小心被前女友聽見了,對他一直不待見。前女友也去了新加坡,我是半年前才知道的。當然,我早就結婚了,前女友就是去南極也和我沒關系。
我忍不住說:“你還記得鄒嵐嗎?”
他立即回復:“那個平胸?你不是把她甩了嗎?”
我讓他嘴巴放干凈點,然后打過去幾個字:“她也在新加坡。”
徐文多好一會兒沒回復,后來問我她在那里干什么。我說應該是留學吧,要不就是嫁了老外,移民過去了。誰知道呢,我刻意回避她的任何消息,直到現在,一想起她我的大腦里就出現SM的圖影:并不肥大的雙乳在我眼前晃動,她手握鞭子,抽打像乳豬一樣伏在床上嗷嗷待哺的我。
——我用了十多年時間試圖遠離這個女人,當我真的失去了她,一種曠世孤獨的挫敗感油然而生。
徐文多發來一個哭泣的表情,說:“我來打工,人家來享受,不是一個階級。……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