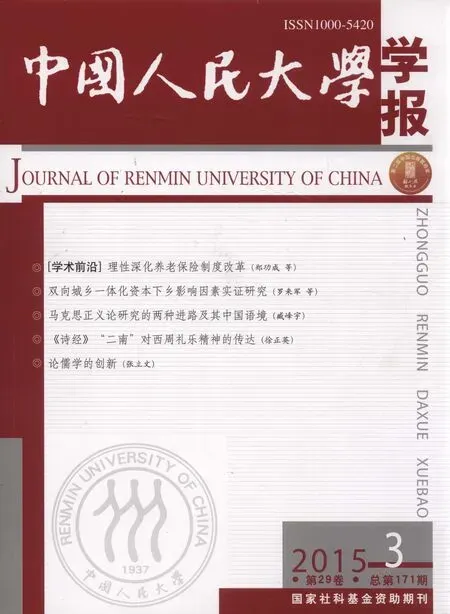空間、消費黏性與中國低消費率之謎
石明明 劉向東
?
空間、消費黏性與中國低消費率之謎
石明明 劉向東
低消費率尤其是居民消費率過低,是目前困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居民消費偏好既依賴于家庭遺傳性和內生性,也依賴于社會形成機制。消費行為受到空間建構和分布的影響,城鄉消費空間的差異會導致居民消費行為也存在較大異質性:一是由城鄉社會形成機制差異導致的消費群體的異質性,二是由信仰、觀念、社會等級等家庭資本遺傳導致的消費者個體異質性。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將導致兩類擴大消費效應,即由于城鄉空間重構和居民區位移動,消費者群體重新選擇消費方式及消費行為的“空間轉換效應”,以及在深度城鎮化的過程中,異質性消費個體面對城市“消費空間”的變化而改變消費方式和消費內容的“消費升級效應”。將空間維度和消費黏性引入“低消費率之謎”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拓展消費行為的微觀基礎研究,揭示我國城鎮化進程中擴大消費的內在機理。
空間;消費黏性;低消費率之謎;消費者異質性
一、導言
消費率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費率過低,是目前困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消費率(居民消費率)是指最終消費(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近年來,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國民經濟步入中速增長軌道,如何有效地激發居民消費需求逐漸成為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的關鍵,也對世界經濟均衡穩定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但與我國GDP持續快速增長顯著背離的是,我國的居民消費率一直處于“異常”的低水平。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標準普爾公司、麥肯錫公司等國際機構近年相繼發表評論,將這一現象稱為“低消費率之謎”(low consumption ratio puzzle)或“低消費率難題”(low consumption ratio problem)。與此同時,中國的消費問題也引起經濟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學者的關注。詹姆斯·莫里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埃德蒙·菲爾普斯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知名經濟學家鄒至莊等分別就中國的消費率過低問題表示憂慮。著名地理學者布魯恩·斯坦利也認為,中國消費者的世界觀和倫理觀以及中國特色的消費主義,是未來值得中國地理學界深刻思考和研究的七項關鍵主題之一。[1]
總體而言,我國“低消費率之謎”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從全球經濟地理范圍來看,我國居民消費率大幅低于世界發達國家和相同水平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3年發布的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的居民消費率僅為34.65%,在25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246位,遠低于世界60.49%的平均水平。同時,這一消費率既低于高收入國家,也低于中低收入國家。比較而言,距高收入國家的61.60%相差近27個百分點,其中,比美國的68.64%低34個百分點,比日本的60.91%低近26個百分點,比歐盟的58.58%低24個百分點;距中等收入國家的54.77%相差近20個百分點,其中,比巴西的62.34%低28個百分點,比印度的60.25%低25個百分點,比南非的61.23%低26個百分點;距低收入國家的77.64%相差43個百分點。二是從我國區域發展來看,各省消費率普遍較低且省際差異十分顯著。根據尹希果和孫惠等的研究,我國各區域和各省居民消費率整體較低且分布極不均衡。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呈“U型”,上海呈“直線上升”,貴州呈“倒N型”,其余27個省、市、自治區(西藏除外)都大致呈現出改革開放后三四年內逐步上升,此后一直下降的趨勢,呈現出“倒U型”走勢。近年來,省際居民消費率的離散程度呈現擴大趨勢,居民消費率的差距日益拉大。[2]三是從我國的消費政策來看,各項擴大消費的政策存在一定程度的弱有效性。近年來,我國政府分別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完善社會保障、鼓勵家電等產品下鄉等一系列措施以刺激消費,但目前消費疲軟的狀況仍沒能得到改善,居民消費率和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仍然呈下降趨勢。很多學者開始注意積極的消費政策對刺激消費(尤其是提高消費率)的有效性。鄒至莊教授認為中國政府刺激消費的政策不會成功。[3]
關于低消費率現象的成因,主要有三類代表性觀點:(1)歷史文化說。即認為我國的居民消費率之所以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歷史和文化傳統因素的影響是第一位的。葉德珠認為,東亞儒家的“節儉”思想會對消費產生抑制作用,由于對儒家思想的作用機制認識不足,政府刺激消費政策出現干預無序和無為的局面。[4]但是從實際情況看,上述觀點只能部分解釋我國的“低消費率之謎”。盡管東亞國家的總體消費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從個體情況來看,這些經濟體并沒有低到中國的程度。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蒙古的居民消費率大多在50%以上,比我國高出15個百分點以上。除蒙古的有關數據劇烈變動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消費率都較為穩定,35年來始終維持在較高的水平。(2)階段抑制說。這種觀點認為,我國現階段高投資和高政府支出的發展模式會“擠出”消費,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流動性約束、消費渠道不順暢會“制約”消費,未來的不確定性會“抑制”消費。但是,從后發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其他典型經濟體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盡管消費率也偏低,但遠遠沒有低到中國的類似程度。例如,日本在快速發展的1980年居民最終消費率為55%,韓國1990年為52.3%,馬來西亞1990年為51.8%,泰國1990年為56.6%。這些國家的消費率都比中國當前高出十幾至二十幾個百分點。另外,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各種刺激內需政策的出臺,低消費率的狀況并未發生明顯改善,這說明預防性儲蓄理論[5]和流動性約束理論[6]并不能完全解釋我國的低消費率問題,還存在其他重要的影響因素。(3)數據失真說。針對消費率明顯偏低的現象,少數學者開始質疑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統計方法。朱天和張軍認為,目前關于中國消費率太低的觀點是基于失真的官方統計數據;官方統計數據大大低估了中國的消費水平,中國的真實消費率應該比官方公布的數據高10到15個百分點,達到GDP的60%至65%。事實上,在過去的20年間,該比率一直穩定在60%左右的水平。[7]這一觀點實質上不是對“低消費率之謎”的解釋,而是從根本上消弭了這一問題。
二、跨理論視角中的消費增長:空間、黏性與行為
基于前述問題意識,我們認為中國的低消費率問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僅依靠單學科的解釋只能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過度抽象化和嚴格假設,從而缺乏解釋力,因此,關于低消費率問題,應從中國基本現實出發,借助經濟學、經濟地理學、行為學等多學科、多范式的相互融合來進一步加強創新性研究。近年來隨著經濟學科的發展,行為因素、地理因素等越來越成為經濟學理論的重要依據,這也為跨學科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撐。例如,后凱恩斯主義學者明確提出,要反對新古典消費理論所貫穿的“非社會”的、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轉而強調人們消費行為的社會歷史性。[8]從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對話的理論構建來看,空間消費理論強調的商品在“專精化”空間中形成新的認同形式過程,本質上也對應于消費函數理論特別強調的“偏好外部性”(preference externality);信息的漸次傳遞和被接受的過程,在消費經濟理論中往往也會通過“黏性信息”(sticky information)概念來進行刻畫。經濟學自身在經歷了“棘輪效應”、“示范效應”、“過度平滑”、“隨機游走”等一系列的消費現象探討之后,逐漸形成新的科學概念即“消費黏性”(consumption stickiness)。而新零售地理學也相信社會的交換秩序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地理學應該成為能夠處理消費者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場景中,在意義的結構網絡當中,在物質界線里,帶著商品,如何、為什么與在哪里行動與互動的研究架構。[9]在經驗研究中,一些跨學科的研究,如弗萊基(Furaiji)等證明文化因素、社會因素、個體因素、心理因素、產品因素、價格因素、促銷因素、地理因素與消費行為具有強關聯。[10]萊萬(Lawan)和贊納(Zanna)將階層、社會規范、時尚、風格、地理、節日、服飾傳統、著裝標準等文化地理因素作為外生變量,將收入、預算、家庭規模、供給、基本需要等經濟因素作為工具性變量,將年齡、教育、生活方式、直覺等個體因素作為內生變量,證實地理環境、階層、社會規范等對消費行為存在顯著影響。[11]上述研究狀況表明,不同學科對話的條件正在逐漸成熟。
從當前理論研究對消費問題的總體把握來看,經濟學通過構建與不斷完善一般性消費函數理論,為消費問題研究確立了基礎性的邏輯框架。新經濟地理學從廠商空間集聚的角度在城市空間層面為消費與空間的互動建立了研究框架。而行為學、消費空間理論等則為居民消費行為與消費空間的相互依賴關系確立了微觀機理。上述三個方面既各有側重,同時也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
(一)黏性信息、習慣形成與黏性消費增長
從1936年消費函數概念提出開始,西方經濟學界陸續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相對收入假說、生命周期假說、理性預期—持久收入(RE-PIH)假說等一系列消費理論,并從理論的可信度與經驗研究的角度,產生了預防性儲蓄假說、流動性約束假說、λ假說等理論假說。近年來,經濟學逐漸將習慣、心理等因素引入消費函數的研究。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卡羅爾等提出的黏性消費增長理論框架。該框架主要包括黏性信息與習慣形成兩大核心概念[12],很好地繼承和吸收了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后凱恩斯學派等關于消費函數理論的研究成果,為解釋現實中出現的諸多經濟現象提供了更為合理的、基礎性的概念框架,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認可。這一理論框架主要基于以下兩大支柱:
(1)黏性信息。經濟學歷史上形成的多種消費理論,如絕對收入理論、恒久性收入理論、相對收入理論、生命周期理論等,大都沒有考慮未來信息流約束的影響,或隱含地假定了充分信息。如恒久性收入理論就隱含地假定人們對未來的恒久收入具有完全信息,意外收入沖擊不能改變人們的恒久性收入,臨時收入增長不會促使人們增加當期消費,減稅與補貼之類的政策并不會像凱恩斯認為的那樣具有平抑經濟周期的作用。例如,霍爾假定人們對最優統計預測所需要的所有變量具有充分信息,在理性預期假設下,消費的增長是隨機游走,不可預測的。而坎貝爾和曼昆等人認為,消費對過去已知信息具有過度敏感性,對持久收入沖擊的反應具有平滑性。[13]黏性信息常常假定消費者的預期調整是泊松過程,且在每一期,更新信息的概率不變,一旦人們更新了信息,就得到了完全信息,對未來的預期是理性的,黏性信息假設使得當期消費既受對未來消費預期的影響,也受滯后信息的影響。在黏性信息下,雖然消費者的預期是理性的,但只會間隔一段時間更新其信息和調整計劃,新信息是漸進地傳播給消費者的,總消費因此而具有過度敏感性;當出現恒久性收入沖擊時,只有一部分消費者會注意到這一沖擊并及時做出反應,總消費對恒久性收入沖擊的反應就具有過度平滑性,或其敏感性較低。由于總消費對沖擊的反應具有遲滯性,遲滯程度取決于信息成本與收入波動的大小,因此,黏性信息能夠同時解釋消費的過度敏感與過度平滑之謎。
(2)習慣形成。近年來,“習慣形成”成為國外主流經濟學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例如,斯米茨(Smets)和沃特爾斯(Wouters)、艾德(Edge)等、安德里森(Andreasen)建立了含有消費習慣的中等規模經濟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GE)模型,發現消費對沖擊的反應更加遲緩,會產生一個“駝峰型脈沖響應”,而不是簡單的衰退曲線。[14]上述結論也與克里斯蒂安諾(Christiano)等人應用向量自回歸模型和美國數據,以及卡羅爾等應用工具變量回歸和13個發達國家數據的經驗研究相符。[15]盧比奧-拉姆利茲(Rubio-Ramrez)、埃米塞諾(Amisano)和特里斯坦尼(Tristani)、多哈(Doh)、霍爾等對非線性的消費習慣模型進行了驗證。[16]安格里尼(Angelini)認為,習慣形成的影響越大,消費者就會變得越謹慎,勞動收入風險對消費的影響也就越小。[17]對于“低消費率之謎”,國外學者應用黏性消費增長框架進行的研究還比較少,且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習慣形成”對謹慎性儲蓄的影響方面。卡羅爾等估計了13個發達經濟體中消費增長的黏性程度,在控制測量誤差之后發現,居民消費增長有很大程度的自相關性,各國的平均黏性系數為0.7。黏性消費增長模型比卡貝爾和曼昆的拇指規則能更好地描述累積消費增長。迪安茲(Diaz)等在一個新古典框架下考察了“習慣形成”對謹慎性儲蓄的影響,發現習慣形成使消費者更注重消費的平滑性,從而會持有更多的資產。[18]史密斯(Smith)認為習慣形成使消費波動的方差減小。[19]
目前國內對“消費黏性”的研究還比較少,且大多集中在“習慣形成”方面,而對“黏性信息”的研究非常少見。根據我們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經濟與管理”類別的檢索,題目中含有“消費黏性”或“消費粘性”的核心期刊文獻僅有1篇,發表于2011年;含有“信息黏性”或“信息粘性”的核心期刊文獻總計5篇,均發表于2010年之后;含有“習慣形成”的核心期刊文獻共有32篇,其中,2010至2012年形成一個研究的小高潮,3年發表論文18篇,占論文總數的56%,但從內容上看,其中9篇文章均為金融或資產定價領域研究。已有的經驗研究文獻表明,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消費均具有習慣形成特征。
(二)空間集聚、城鎮化與消費增長
從城市空間維度對消費進行的研究,主要出現在經濟學與地理學的交叉學科——新經濟地理學中,集中反映在城市化過程與消費增長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文獻中。新經濟地理學認為,消費增長與廠商的空間集聚存在“累積循環因果效應”。藤田(Fujita)和克魯格曼(Krugman)將集聚的發生表示為較大的規模經濟、較低的運輸成本,以及制造業產品在消費支出中較大的份額和一種結果。[20]消費者對產品的多樣性需求和廠商對規模經濟效益的追求,使得消費者(勞動力)和廠商有動力在城市這一能產生集聚效應的地區集聚。隨著廠商數量的增多,這個地區能生產更多的產品,進而使得市場上的產品和均衡價格與其他地區相比更低。產品價格下降的結果將對當地的勞動力/消費者產生正向的收入效應,即地方工業品供給的多樣化提高了勞動力/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工業發展的前向效應)。同時,也會引起更多的人向這個地區遷移,進一步引起更多的對工業品的多樣化需求和廠商集聚,即空間集聚和消費需求增長是互為因果的,空間集聚不僅增加了消費的總量,也會提升消費傾向,從而提高消費率。
(三)城市消費空間、消費決策與消費增長
與消費經濟學和新經濟地理學從一般性消費函數、城市空間聚集進行研究的角度不同,一些學者從個體行為決策的層面對居民的消費行為進行了分析。這類研究盡管沒有對“消費率”問題給予直接的關注,但對空間或外部環境與消費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大量深入細致的探索。主要有三個方向:(1)行為經濟學理論。行為經濟學將心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修正了主流經濟學關于個人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偏好一致性等基本假設,圍繞情境理性、框架效應、損失規避等核心概念,建立了有別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框架。(2)行為地理理論。由于消費者的購物行為會受到來自外界環境和內在屬性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地理學也對消費行為決策和商業設施物質空間結構、城市商業環境設施與空間分布、日常生活空間、居民的屬性特征等給予關注,側重于描述影響居民購物行為空間決策的各種因素,包括購物地選擇的信息來源、出行方式、可達性、消費心理等主觀態度因素以及購物地離家距離、購物地所提供的商品種類豐富程度等客觀因素。相關文獻先后提出了零售引力法則、中心地理論、引力模型、購物中心層次性系統發展模型、空間需求模型、消費者鏈式購物模型等理論。(3)空間消費理論。空間消費理論一般將消費視為一種社會過程。消費空間不是簡單的地理與物理的空間交集,不是單純的買與賣的地方,而是需要承載諸多功能的社會空間。正如鮑德里亞所述,消費領域是一個富有結構的社會領域。不同收入、性別、年齡、品位、職業諸多社會類別之間的差異,通過商品與服務的組合、品牌符號的編碼嵌入消費空間的意義體系里。消費生活方式的完成過程實際上是空間化的消費生活方式過程。居民的不同消費屬性和消費階層及其消費行為構成,能充分體現城市內不同消費場所的社會空間構成與消費(需求)質量水平。消費場所也體現了他們對應空間化消費的生活方式。[21]例如,城市是一個坐落在有限空間內的各種經濟市場(住房、勞動力、土地、運輸等)相互交織的網狀系統。這種集中的特點使得現代城市成為推動消費發展的關鍵場所。同時消費和消費者具有非均質性和流動的特征,空間不只是消費發生的背景,而且與商品、社會和文化共同構建著個體和集體的消費活動,消費在地方發生,地方又影響著消費的具體過程。
經濟學、地理學、行為學等都對消費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但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跨學科和跨理論研究較少,相關研究還有待加強。當前消費經濟學基礎理論還缺乏對消費空間的重視;新經濟地理學對消費的研究更多的是從生產聚集角度開展的;而地理學更側重于消費空間和城市居民個體消費行為之間的關系。各學科交叉融合、相互印證的程度還需要提升。二是對“消費黏性”和“消費率”問題的研究還比較少。從目前消費經濟學最前沿的進展來看,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二元分野正在消失,跨學科研究的基礎和條件正在成熟。但無論是消費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還是空間消費理論等,都沒有對彼此之間的深厚關聯關系予以充分的重視,盡管有學者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同時,截至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黏性消費”的研究還很少,正處于前沿理論的初步引進階段。三是我國關于“低消費率之謎”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與低消費率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形成顯著對比的是,盡管目前我國許多研究已經注意到“低消費率”這一現象,但受到理論工具、基礎數據等條件的制約,還缺乏對其內在機理、決定因素、歷史階段性、臨界轉換條件等深入細致的研究。
三、城鎮化擴大消費的機理: 一個探索性分析框架
從加強對中國基本現實的解釋力出發,考慮到城鎮化進程與消費空間的密切關系,基于前文對黏性消費、空間與消費互動已有研究的分析,我們從跨理論視角和黏性消費增長框架出發,將空間與消費聯結起來,力圖深入研究居民消費行為與空間的互動機理,提出一個基于我國城鎮化進程與消費關系的探索性分析框架。
(一)空間與消費的聯結
聯結空間與消費,研究個體的消費活動與空間環境之間的關系機理與互動機制,對于揭示我國“低消費率”現象的微觀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政策含義。正如區域經濟學之父伊薩德(Isard)所述,考慮到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地點獨立發生的特質,以及明顯存在的區域差異和不同地區人民福利間的巨大不平等,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理論或社會理論應該包括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空間”是可以被區分、分離并評估出其空間效用的。忽視空間差異性(spatial differentiation)和空間非平穩性(spatial non-stationary)的存在會極大地影響理論對現實情況的解釋能力,也會降低模型的預測分析能力。[22]從規范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國消費空間差異的最顯著特征是城鄉差異,將空間與消費聯結直接形成了兩類在空間上相互分隔的異質性消費群體。
在“低消費率”這一現象背后是我國微觀家庭消費傾向過低和消費支出增長乏力。在消費黏性即當期消費與前一期消費的自相關特性下,居民當期的消費將導致下期同等消費效用水平的下降,從而使得消費者不僅平滑消費水平還將平滑消費增長。由于消費在本質上是空間性建構與分布的,居民消費行為本身與消費空間環境構成具有互逆與相依性質的關系,因此,不同消費空間會形成不同的消費行為。空間環境(諸如城鄉空間結構、家庭區位、區位選擇、所在地社會經濟結構和文化制度等)影響人們的偏好與消費行為,反過來,人們的消費偏好與消費選擇行為又影響到空間結構的變化(比如,通過人口的區位遷移、行為轉換等)。相關的關系機理與互動機制是揭示我國“低消費率之謎”的微觀基礎及城鎮化擴大消費的內在機理的重要路徑。
消費是微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分析的關鍵樞紐,承擔著解釋宏觀經濟運行的總量波動與結構變遷原因的重要職能。低消費率問題具有重要的經濟地理特征:一是世界各國消費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經濟地理差異,我國各省區消費率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二是從微觀的家庭消費行為來看,居民在消費行為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尤其是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傾向存在顯著的城鄉差異。三是消費增長存在顯著的政策響應黏性。從世界范圍來看,消費率對于經濟增長和政府政策均具有一定的響應黏性。以世界經濟發展和政府健康支出為例,消費率與各國人均GDP和健康公共支出之間的關系極其微弱(如圖1所示)。

(a)世界各國人均GDP和消費率的關系

(b)政府健康公共支出與消費率的關系
圖1 消費率對經濟發展及公共政策的響應黏性
以上特征使得研究我國的“低消費率之謎”具有一定的難度。當前,我國大多數消費研究都將提高居民收入作為擴大消費的關鍵點,這實際上混淆了絕對意義的“消費”與相對意義的“消費率”之間的重要區別。從統計相關性上看,居民收入與消費支出之間存在無可爭議的高度相關性,但居民收入與消費率之間則不僅不存在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而且還可能存在凱恩斯所述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我們認為,關于消費問題的研究更根本的是要回到消費本身,即從長期來看,我國擴大消費的關鍵點應是提高消費率,而提高收入應是收入分配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因此,低消費率問題的首要關注點是,我國居民消費率有哪些內在決定因素,即構成我國消費黏性的內生機制和外生機制是什么?從現象上看(如圖2所示),我國的城鎮化率與居民消費率呈現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如何理解城鎮化率與居民消費率相背離的現象?即我國城市化與消費黏性增長之間的深層次互動機理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上述背離現象,扭轉二者背離趨勢的臨界條件是什么?在解答上述問題的基礎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的一個關鍵點是,從現實性上考慮,城鎮化對消費黏性的沖擊到底有多大,即我國城鎮化擴大消費的潛力到底有多大,技術上如何進行合理測度,相關沖擊的響應過程如何發生和變化?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就這一消費問題對各項政策的反應及其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做出評價。上述方面,均需要將空間因素和消費問題聯結起來,重新構建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特征、針對性解決我國現實問題的消費理論。

圖2 我國居民消費率與城鎮化率的背離
(二)消費行為的微觀基礎與空間差異
當前各類文獻對消費黏性的類型有多種不同的表述。例如,部分文獻把縱向的比較效用稱為“習慣形成”,而把橫向的比較效用稱為“追趕瓊斯”(catching up with Joneses);把前者歸結為“個人資本”,而把后者看成是“社會資本”,并在“世代交疊”(OLG)經濟中,提出了第三種習慣資本(habit capital)——家庭資本(familial capital),即子女的消費偏好會受到父母消費的影響,父母過去的消費水平給子女的消費效用設定了一定標準的偏好,并稱之為“遺傳或繼承偏好”(bequeathed tastes或inherited tastes)。[23]盡管不同研究者采用的術語不同,實際上以上消費黏性類型最重要的區分在于,黏性是通過自己過去的消費經驗累積而成(習慣形成),還是通過人際間比較(黏性信息)或者跨代傳遞而形成的一種消費外部性。
基于上述區分,低消費率的微觀來源可能包括兩類:一是消費偏好的家庭遺傳性和內生性,即居民消費偏好形成的內生性和環境依賴性或者說消費黏性所具有的路徑依賴性,亦即過去的經歷或歷史的經驗對一個人的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為人們從消費中得到的效用或滿足程度將依賴于過去的經驗,依賴于過去經驗的強度與持久性的結果。二是消費偏好的社會形成機制。在信息黏性、偏好外部性等基本假設的基礎上,人們的消費活動同時也是學習過程,學習過程對于人們消費需求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居民在消費過程中,消費成本與具有類似偏好的人數相關,一個消費者改變自己購買行為的權利就會影響到其他消費者的福利,出現效用相關和行為依賴,即U=U(ξ1,…,ξn)。此時,消費行為的多樣性和消費方式的差異化主要是由空間上的聚集程度(如城鄉差異)來區分的。在不同的消費空間中,人們總是觀察與模仿其他人的消費模式。例如,在現實中消費者是怎樣安排他們面臨的新的支出機會;如何學會利用他們新增的購買能力;信息如何在消費之間傳導;消費需求升級過程如何進行,如何模仿和學習較高等級群體的消費方式與行為等。
城鄉作為不同的消費空間存在巨大的空間差異,這種差異會對居民的消費行為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拉帕博特(Rappaport)的有關研究[24]),其作用機理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空間聚集與消費增長存在因果循環累積關系,即城鎮化過程中的偏好外部性及集聚效應,與消費黏性、消費增長之間存在互動關系。一方面,根據新經濟地理學的思想,消費的多少一般源于自身可支配財富的多寡,財富的多少從根本上決定了消費商品的多少和種類。平均來看,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比生活在非城市中的居民獲得的收入要高。格萊澤(Glaeser)等人發現,城市工人的收入要比非城市工人的收入高33%。城市規模和工資水平具有很強的正向關系,城市規模越大,工資水平相對越高,城市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帶來消費數量和種類的增加。[25]同時,城市中消費的可能性更高,真實工資水平較低,這是因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購買,而農村居民生活所需的很多必需品根本不需要到市場購買。[26]所以,在城市選址要比在農村地區更接近需求市場,城市居民的消費傾向較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企業所生產的商品上。另一方面,沃爾夫岡(Waldfoge)等學者認為,集聚也會強化消費。市場的擴大、人口的集中使人與人之間直接交流的機會增加了,這會使人與人之間滲透著彼此的偏好和習慣,從而產生“偏好外部性”。[27]這種偏好外部性不僅使雙方的消費習慣趨于一致,而且彼此之間在消費商品的數量和種類上也互相攀比,居民的消費福利可能取決于其他消費者是否也偏好于他所購買的商品。一般而言,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人們會越來越偏好于消費更奢侈的商品。
二是消費黏性與城鎮化率存在著內在關聯,我國將消費作為經濟內生增長動力,需要建立新的穩定均衡。錢納里和塞爾奎因曾經全面深入地分析了1950—1970年101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消費率的變化,發現消費率的演變過程呈平緩的U型曲線。在工業化初期,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分別為86%和73%;工業化中期,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分別下降到80%和66%;工業化末期,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下降至76%和60%,即在整個工業化階段,消費率是下降的,在工業化階段結束或經濟達到發達階段以后,消費率將趨于穩定。[28]將這一理論與城市化理論相聯系,可以得到如下假說,即隨著工業化進程的發展,我國低消費率會在某一時點出現逆轉。以上假說意味著,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我國居民的消費黏性會發生改變,原來經濟均衡穩定增長的條件將被打破,經濟將進入新的穩定均衡增長狀態。這一假說在日本、韓國的發展歷程中得到了部分驗證。20世紀50年代初期,日本的最終消費率高達77%,而在1970年下降到谷底59.7%,到20世紀70年代又回升到67%以上,之后一直較為穩定。韓國1970年的最終消費率為83.9%,之后穩定下降到1988年的59.7%,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逐漸平緩上升,進入到21世紀以后,維持在70%以上。2014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從一種均衡增長路徑躍遷到新的均衡增長路徑,居民消費率的拐點是否來臨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和驗證。
三是居民在城鄉空間轉換過程中的區位選擇影響消費行為。城鎮往往發揮著生產中心、商品流通中心、消費中心的職能。城鄉居民家庭會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選擇適當的居住區。居民家庭的居住區與公共消費品的區位選擇與消費成本之間具有互動的影響。例如我國大多數農村居民的消費更注重實用性,而大部分城鎮居民則更關心商品的符號價值,商品強烈的等級屬性強化了農民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從而會阻礙其深度融入城市消費社會。
(三)城鎮化擴大消費的空間效應
居民消費行為研究可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研究消費的生命周期配置問題,也就是消費者在一生總資源的約束下,如何配置各期消費;第二個層次著眼于各期消費支出如何在各類消費品間配置,即消費結構問題。與這兩個層次的研究相對應,在引入“空間維度”和“黏性消費”以后,我們認為在城鎮化背景下,消費者異質性主要有兩類:一是城鄉社會形成機制的差異所導致的消費群體的異質性;二是由于信仰、觀念、社會等級等家庭資本遺傳導致的消費者個體的異質性。這兩種異質性會導致兩類不同的空間效應:一是由于城鄉空間重構和居民區位移動,消費者重新選擇消費方式及消費行為的“空間轉換效應”;二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異質性消費個體面對城市“消費空間”變化選擇改變消費方式和內容的“消費升級效應”。
如圖3所示,在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消費者在空間轉變過程中會存在“缺口問題”及“空間轉換效應”。我國城鄉及不同地區居民消費問題存在差異性,這一結構特征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居民的消費行為。在理想情境下,城鎮化過程本身會構成一項“持久性沖擊”,使遷徙后的居民整個生命周期上的效用函數曲線發生向上的躍遷(L1→L2),從而帶來消費傾向的“空間轉換效應”。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城鎮居民消費會帶來結構升級效應。消費結構升級即消費層次結構的遞升,是一個社會的消費需求由代表低一級的消費時代的主流商品到代表高一級消費時代的主流商品的變革過程。在黏性消費增長的框架下,隨著我國城鎮化的發展,消費升級的具體條件、結構變化(Cn-1→Cn)和時間間隔特征(即tn-1→tn)都可能對居民消費傾向和消費黏性產生重大影響。
總體來說,將消費黏性和空間維度引入“低消費率之謎”的研究,可以更有效地揭示個體消費行為與空間環境之間的關系機理與互動機制,拓展消費行為的微觀基礎研究,也可以深入揭示我國城鎮化擴大消費的內在機理。可以看到,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及相關配套機制的建立,經濟空間格局將進一步優化,居民消費將呈現新的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費將逐步轉變為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模式并成為主流,這要求消費政策必須更加注重市場和心理文化因素,從深層次上緩釋消費增長的黏性程度,釋放消費增量的空間。


圖3 城鎮化過程中的空間轉換效應和消費升級效應
四、未來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幾個方向
在本文中,我們綜合經濟學、地理學、行為學等學科的相關理論,對我國的低消費率問題進行了探討。未來還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
一是建立包括地理信息系統(GIS)數據、城鄉居民家庭消費支出、代碼化家庭特征數據等在內的體系完備、可綜合印證比較的大樣本數據庫,為相關研究提供數據基礎。一般而言,總量數據中無法控制的不可觀測的異質性可能會夸大習慣效應。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微觀數據的逐步積累,國外經濟學家主要采用家庭層次的數據對前沿消費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其中,海恩(Heien)和德哈爾(Durhaln)是最先運用微觀數據對消費習慣進行研究的學者。[29]此后,麥格海爾(Meghir)和韋伯(Weber)利用美國CES(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數據[30],嘉里格利亞和羅斯利用英國BHPS(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數據[31],加萊索(Carraseo)等利用西班牙ECPF(Spanish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數據[32],阿賴澤(Alessie)和提帕(Teppa)利用荷蘭DHS(Dutch Household Survey)數據[33],對前沿消費問題進行了檢驗。目前,國內有關研究主要基于中國家庭住戶收入項目調查數據(CHIPS)、密歇根大學中國健康與家庭生活調查(CHFLS)等,而綜合GIS數據信息,采用先進的數據整合方法和技術性調整(如設置等價尺度和進行敏感性分析等),涵蓋地理信息、家庭規模、年齡結構、世代結構、信念信仰、文化心理等異質性特征的數據庫體系還沒有形成。
二是基于空間差異和消費者異質性量化評估城鎮化擴大消費的空間效應。本文對城鎮化過程中將出現的消費“空間轉換效應”和“升級效應”的解析,可以為我國城鎮化影響消費增長的有關研究和政策評估提供一個基礎性的分析框架。構建評估城鎮化擴大消費的經濟模型,并基于GIS和微觀調查數據對我國城鎮化擴大消費的潛力進行實證研究,考察習慣形成等消費黏性因素對相關經濟效應的影響,是未來深化我國城鎮化影響消費增長的有關研究的重要內容。
三是基于黏性消費增長框架,建立涵蓋多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擬評估消費率的政策響應過程和對其他部門的沖擊過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目前已經成為經濟學領域進行政策分析及經濟預測的主要工具。近期我國學者雷瀟雨和龔六堂、徐朝陽等對應用這一框架分析我國消費率問題做了初步探索[34],未來將引入空間異質性和消費黏性,構建涵蓋家庭、最終品廠商、中間品廠商、政府部門等在內的,分析我國居民消費動態調整過程的DSGE數量模型,模擬研究在我國城鎮化擴大消費過程中,黏性消費增長對各項擴大消費政策沖擊的響應過程,以及消費黏性變動對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的影響。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研究方向,具有較強的綜合性和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同時對我國消費政策的制定也將具有積極的政策參考價值。
[1] 布魯恩·斯坦利:《地理學展望:2050年的地理學》,載《地理科學進展》,2013(7)。
[2] 尹希果、孫惠:《居民消費、空間依賴性與經濟增長條件收斂——基于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載《中國經濟問題》,2011(4)。
[3] 鄒至莊:《刺激消費政策會成功嗎?》,載《英國金融時報》,2013-01-10。
[4] 葉德珠:《儒家思想與高儲蓄、低消費之謎——基于行為經濟學的視角》,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
[5] 劉兆博、馬樹才:《基于微觀面板數據的中國農民預防性儲蓄研究》,載《世界經濟》,2007,(2);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度的時序變化與地區差異——基于中國農村居民的實證研究》,載《經濟研究》,2008(2)。
[6] 趙霞、劉彥平:《居民消費、流動性約束和居民個人消費信貸的實證研究》,載《財貿經濟》,2006(11);高夢滔、畢嵐嵐、師慧麗:《流動性約束、持久收入與農戶消費——基于中國農村微觀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載《統計研究》,2008(6)。
[7] Zhu,T.,and J.Zhang.“Is China’s Consumption Rate too Low? ”.FTChinese,2012-12-31.
[8] R.Dennis.“Consumption Habits in a New Keynesian Business Cycle Model”.FederalReserveBankofSanFranciscoworkingpaper,2008.
[9] L.Crewe.“Geographies of Retailing and Consumption:Markets in Motion”.ProgressinHumanGeography,2003(27).
[10] Furaiji,F.,Latuszyńska,M.,and A.Wawrzyniak.“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 Behaviour in the Electric Appliances Market”.ContemporaryEconomics,2012(6).
[11] Lawan,L.,and R.Zanna.“Evaluation of Socio-culture Influencing Consumer Buying:Behavior of Clothes in Borno State,Nigeria”.InternationalJournalofBasicandAppliedScience,2013(1).
[12] Carroll,C.,Sommer,M.,and J.Slacalek.“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Sticky Consumption Growth”.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11,93.
[13] J.Hall.“Nonlinear Consumption Dynamics in General Equilibrium”.MPRAPaper,No.43933,2013.
[14] Smets,F.,and R.Wouters.“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A Bayesian DSGE Approach”.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7,97;Edge,R.,Kiley,M.,and J.Laforte.“Natural Rate Measures in an Estimated DSGE Model of the U.S.Economy”.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08,32;M.Andreasen.“An Estimated DSGE Model:Explaining Variation in Nominal Term Premia,Real Term Premia,and in Ation Risk Premia”.SSRNeLibrary,2011.
[15] Christiano,L.,Eichenbaum,M.,and C.Evans.“Nominal Rigidities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 Shock to Monetary Polic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5,113;Carroll,C.,Sommer,M.,and J.Slacalek.“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Sticky Consumption Growth”.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11,93.
[16] J.Rubio-Ramrez.“Estimating Macroeconomic Models:A Likelihood Approach”.ReviewofEconomicStudies,2007,74;Amisano,G.,and O.Tristani.“Euro Area in Ation Persistence in an Estimated Nonlinear DSGE Model”.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10,34;T.Doh.“Yield Curve in an Estimated Nonlinear Macro Model”.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2011,35;J.Hall.“Nonlinear Consumption Dynamics in General Equilibrium”.MPRAPaper,No.43933,2013.
[17][31] V.Angelini.“Consumption and Habit Formation when Time Horizon is Finite”.EconomicsLetters,2009,103.
[18] Diaz,A.,Pijoan-Mas,J.,and J.Rios-Rull.“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under Habit Formation Preferences”.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03,50.
[19] W.Smith.“Consumption and Saving with Habit Formation and Durability”.EconomicsLetters,2002,75.
[20] Fujita,M.,and P.Krugman.“When the Economy Monocentic:Von Thu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1995,25.
[21] Wrigley,N.,and M.Lowe.“Introduction:Transnational Retail and the Global Economy”.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2007(7);Wrigley,N.,Coe,N.,and A.Currah.“Globalizing Retail:Conceptualizing the Distribution-Bas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ProgressinHumanGeography,2005(4).
[22] W.Isard.“Location and the Space Econom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6.
[23] Croixa,D.,and P.Michel.“Optimal Growth when Tastes are Inherited”.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1999,23.
[24] J.Rappaport.“Consumption Amenities and City Population Density”.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2008,38.
[25] Glaeser,E.,Kolko,J., and A.Saiz.“Consumer City”.JournalofEconomicGeography,2001(1).
[26] Tabuchi,T.,and A.Yoshida.“Separating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JournalofUrbanEconomics,2000,48.
[27] Waldfogel,J.“Preference Externalities:An Empirical Study of who Benefits whom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 Markets”.RandJournalofEconomics,2003(6).
[28] Chenery,H.B.,and M.Syrquin.“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1975.
[29] Heien,D.,and C.Durham.“A Test of the Habit Formation Hypothesis using Household Data”.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1,73.
[30] Meghir,C.,and G.Weber.“Intertemporal Nonseparability or Borrowing Restrictions? A Disaggregate Analysis Using US Consumption Panel”.Econometrica,1996,60.
[32] Carrasco,R.,Labeaga,J.,and J.Lopez-salido.“Consumption and Habits:Evidence from Panel Data”.EconomicJournal,2005,115.
[33] Alessie,R.,and F.Teppa.“Saving and Habit Formation:Evidence from Dutch Panel Data”.EmpiricalEconomies,2010,38.
[34] 雷瀟雨、龔六堂:《城鎮化對于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理論模型與實證分析》,載《經濟研究》,2014(6);徐朝陽:《供給抑制政策下的中國經濟》,載《經濟研究》,2014(7)。
(責任編輯 武京閩)
Space, Consumption Stickiness and the Low Consumption Ratio Puzzle
SHI Ming-ming, LIU Xiang-dong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Low consumption rate, especially low consumption rate of residents, is a major problem plaguing 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reality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urbanization expanding consumption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a cross-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stickiness in consumption growth. Some researches have proved that consumer preferences not only depend on the family hereditary and endogenous, but also rel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mechanism.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spaces have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s, which makes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residents heterogeneous. While the group heterogeneity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the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can be attributed to family capital, such as the belief, concept, and social class and so on. Therefore, in China’s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onsumption effect, namely, space conversion effect from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resident immigration, and consumption upgrade effects from individuals changing their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content in the process of deepening urbanization.
space; consumption stickiness; low consumption ratio puzzle; consumer heterogeneity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我國擴大內需長效機制的微觀基礎與政策構建——基于家庭消費函數與大樣本調查的研究”(12YJC790158);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黏性消費增長框架下城鎮化擴大消費的潛力評估與效應模擬”(41401124)
石明明: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講師;劉向東: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