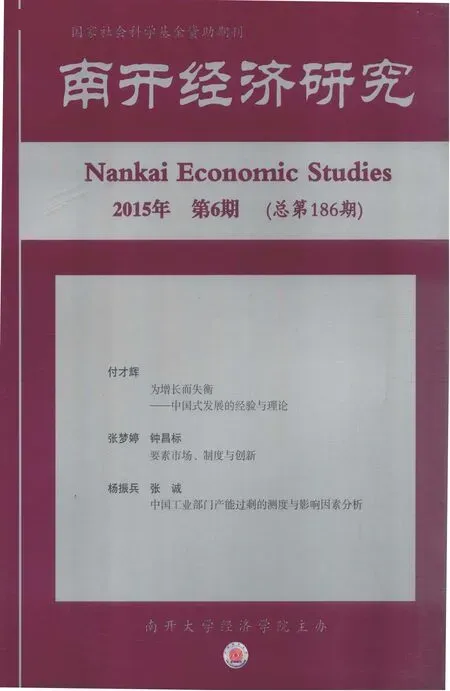中國科技金融創新支持效率研究——基于企業層面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
葉 莉 王亞麗 孟祥生
一、引 言
確立企業科研主體地位、引導創新要素企業聚集,是我國“十二五”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亦是修補當前創新“短板”所面臨的艱巨任務。科技型中小企業以全國65%,的專利發明量、75%,的企業技術創新以及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占比(張靖霞,2012),為推動技術升級做出突出貢獻,是科技創新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作為創新養料的直接“供應商”,我國科技金融對中小科企的資金供給并非盡如人意,現行科技金融的完善升級可謂迫在眉睫。究竟如何有針對性的引流創新活動資金供給,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效率,不同資金來源的創新效用探討就顯得尤為重要,相異融資渠道的科技支持效能無疑是首要議題。
就現有研究來講,西方國家“科技”與“金融”本具有相當的現實嵌合度,故理論上“科技金融”的獨立完整范疇并未形成,相關討論亦多集中于一國宏觀金融對創新產出的作用效果。Saint-Paul(1992)通過多假設模型討論,發現市場化金融可通過風險分散緩解資金主體“惜貸”與科研高風險之間固有矛盾,促成高創新度科研項目實施,繼而推動技術進步。King 和Levine(1993)將Frank Knight(1951)的模型予以拓展,深入探討了完善金融市場對技術創新的積極影響,并進一步將其作用途徑具化為以下四種:最優創新項目的自發選擇、科技研發的資金輸送、項目風險的轉移分散以及創新潛在收益的系統揭示。基于金融市場化差異,Tadesse(2002)將銀行主導型金融中加入市場主導型,通過對比分析發現金融部門發展程度對金融科技效率的決定作用——國家金融機構職能完善時,市場主導型金融對科技創新有絕對優勢,反之銀行主導型金融更有裨益。依照相似思路,Atanassov 等(2005)借助1974—2000 年美國上市公司數據,采用實證方法得出市場主導型金融對高創新度科技研發優勢顯著,而銀行主導型金融對低新穎度創新支持效果略勝一籌的論斷。Benfratello 等(2008)則通過對意大利眾多企業實證考察得到對立主張,強調一國銀行發展程度對企業創新進程的巨大影響,并指出尤其對依賴外部融資的科技型中小企業而言,銀行業發展將削弱企業對固定投資現金流支出的敏感度,繼而提升企業創新活動積極性,促進科技產出。
相較國外研究多集中金融視角,國內學者則多立足宏觀層面,對科技金融做一整體探討。自1993 年我國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首次提出“科技金融”一詞以來,普遍認為趙昌文等(2009)首次對其理論意義予以界定:科技金融是指促進科技開發、成果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與金融服務的系統性、創新性安排,是由向科學與技術創新活動提供融資源的政府、企業、市場、社會中介機構等各種主體及其在科技創新融資過程中的行為活動共同組成的一個體系,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和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我國學者大多將研究聚焦于科技金融的產業層面,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文獻。段世德和徐璇(2011)將科技金融看作促進科技創新和推動成果產業化的重要力量,系統闡述了將同質金融資源與異質科技創新相結合,以推動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發展的方向方法,并突出強調了其中科技金融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樣立足高新技術產業,趙稚薇(2012)將科技金融按資金來源劃分為三類:政策性科技投入、市場性科技貸款與創業風險投資,采用數據包絡法對其創新支持效果進行了實證考察,并得出以下結論:政策性科技投入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效率顯著為正,金融科技貸款具有推動作用但并非顯著,創業風險投資則表現為強烈的抑制作用。借助相似思路,崔艷娟和趙霞(2013)將科技金融替代指標簡化為政策性資助與市場性貸款兩類,在生產函數模型基礎上對其科技支持效率予以檢驗,印證了“政策性科技金融有助于技術創新,金融性貸款波動不利于科技發展”的論斷,為科技金融體系的完善升級提供思路。
從既有研究成果來看,國外學者通常關注宏觀金融的科技效率差異,國內學者則更多立足中觀產業,以資金創新支持效能為探討核心。鑒于此,本文立足科技型中小企業,一方面將“政策性基金資助”納入Atanassov 等(2005)上市企業融資模型中,將其改進為適用我國中小科企的三方三階段博弈模型,從而在“政府-企業-銀行”三方框架下,實現對企業科技創新中各方資金主體相互作用機制及不同融資方式創新支持差異的理論探討;另一方面,針對模型所得結果,同時借助靜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已得結論進行實證檢驗,繼而完成理論論斷統計層面的現實支持。
二、基本模型設定及相關命題演進
(一)模型設定
考慮我國主要科技金融渠道:創新基金、股權資金、債券資金與銀行貸款,按創新項目決策權的實際歸屬將其劃分三類——政策性融資、自主型融資與被動型融資。政策性融資指代創新基金資助,國家相關部門的資金決策將直接決定創新項目實施與否;被動型融資以銀行借款為主,銀行對項目的全程監控及其資金的分期供給,均將削弱企業自身決策力度,致其陷入被動從屬境地;自主型融資包括股票與債券籌資方式,二者實際投資者數量眾多且相對分散,為企業掌控項目決策營造良好條件。由此涉及創新活動三方行為主體:政府部門、銀行機構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假定均呈風險中性。創新活動存在 t= 0,1,2三個關鍵時點:t =0 時企業面臨創新項目投資決策,且所需款項I0必須全部外部籌集;此時企業存在已有投資活動,t = 2時將產生確定資金流入 Y2。1. 自主型融資主導下的創新項目
此處雖視企業為一整體,稱股權、債券融資為“自主型”,其內部決策目標卻迥然相異。作為股東權益的忠實代表,董事會B 以投資者利益最大化為行為準則——若某資金結構未來可使企業整體價值得到提升,相應融資方式將予以采納;經理人M 則完全置股東收益于腦后,以最大限度放大個人私利為決策目標,諸如移用企業資源、尋求額外津貼等都是常見方式。換言之,企業管理層存在“委托代理”問題。需要指出的是,經理人這種“自利決策”只有在股東無法監督時才能實施,至于董事會可監管之處,礙于行政級別與職能差異,經理人將不得不服從董事會決議。另外,依照Hart 等人(1995)“控制權相機轉移”思想①如若還款稍有拖延,經理人將失去包括企業現金流在內的全部資產控制權。,此處假定經理人并無動機拖欠銀行貸款。
自主決策情況下,項目成功率為1μ。若項目失敗,企業期末收益為0;若成功,則t= 2時項目價值上升為,其中 vl< vh,故 t= 0時項目期望價值為:
2. 政策性融資主導下的創新項目
政策性資金不單是企業強大的資金后盾,其附加的信息服務與專業培訓,甚至隨之而來的正向輿論效應,均使創新項目成功率 μ2陡然提升( μ2> μ1)。假定企業申請國家創新基金資助成功率為δ,與項目創新程度正向相關 δ′( n) > 0,其中 n∈ [ 0, 1]為科技項目“新穎度”,新穎度n 越高,企業獲得國家基金支持可能性越大。由此可得到創新基金支持下,企業 t= 0時項目期望價值(此處創新基金資助方式為無償,且款項金額恰為項目所需):
3. 被動型融資主導下的創新項目
采取被動型融資的科技企業,銀行已相當程度上介入創新進程。出于風險規避固有屬性,銀行機構 t= 0時只提供期限為“1”的“短期”借款,并按照 t= 1時項目成功率的新生信號對貸款活動再次決策:若新息①即t=1 時與企業項目發展情況相關的新生信息,稱其為“新息”。顯示項目 t= 2時會順利完成,則該信號為正向信號( s+),概率為 φ < 1,即項目成功) = φ,反之銀行捕獲信號為負( s-)。不難發現,雖然正向信號預示著項目將會成功,負向信號的產生卻不僅僅源于項目失敗的可能性,銀行對項目未來走向的判斷失誤亦可能引起相同效果,故φ 可理解為銀行對“潛力”項目的正確識別率。按照Scherer(1984)觀點②銀行機構對科研項目成功率的正確判斷,很大程度上正比于對科技創新的熟悉度:銀行在處理相似科研項目時,新息判斷相對可靠,而對頗具開創性的“根本性創新”,其信息處理準確性將有所降低。,此處假定 (n) 0 φ′ < 。若t= 1時新息不利,企業將面臨項目中斷風險,屆時相關資產將被折價清算,剩余價值為。其中,資本回收率β 取決于項目創新度n,依據Titman 與Wessels(1988)“產品獨特性”理論③對于某種獨特性強、創新度高的“產品”來講,其相關資產的其他用途亦非常有限,即新穎度對創新項目資產清算有負向影響。,有 β′ (n) < 0。需要指出的是,t = 1時新息只有銀行機構可以獲取,個體投資者規模較小且能力有限,缺乏有效渠道;此外,貸款利率、銀行監管及信息收集成本均忽略不記。因此,被動型融資主導下,企業 t=0 時項目的預期價值為:

其中,表達式前一項是銀行收到正向信號(s+)時的期望收益,后一項是負向信號(s-)出現時項目中途清算可得收益。
綜上,企業創新項目的融資選擇及實施過程可由圖1 表示。

圖1 創新項目的融資選擇與資金運作
(二)模型均衡與結論假說
1.“委托-代理”與債務融資
談到企業自主決策,其內部“委托-代理”問題無疑需首要剖析。依照前文假定,項目終止日 t= 2時,若最終現金流流入及成本花費較難準確衡量,則為經理人M 挪用θ > 0部分現金流私用提供可能,“委托-代理”問題隨即出現。因此,經理人為增大期末現金總流入,總有實施項目的決策傾向。與此同時,經理人毫無拖延銀行貸款動機,意味著銀行貸款風險利率為0 的情況下,企業貸款越多,期末經理人可轉移現金流越少。故若企業在 t= 2時總現金流入為,無銀行貸款條件下,經理人轉移使用后,投資者實際占有數目為;而若企業有銀行債務,股東與債權人總期望資產可達:
顯而易見,償還銀行貸款削減了經理人可挪用資金量,故于董事會而言,最優融資決策即與銀行機構“統一戰線”,將企業負債最大化,最大限度遏制委托代理問題。
2. 企業創新與最優融資方式
在決策主體利益分歧與行為牽制得以闡明的基礎上,本部分以企業固有的逐利屬性將其創新活動與融資方式巧妙聯系,得到與創新價值最大化所對應的最優融資方式。



(a)(b)命題的內在邏輯并不繁復——當項目創新度較低時,銀行信息質量與項目資金回收率相對較高,故采取被動型融資,將項目決策權交由銀行可謂最佳選擇;當項目創新度不斷提高,銀行信息質量與項目終止資產回收率均會相應下降,銀行決策則失去優勢。此外,與自主型融資相比,企業對政策性融資的唯一顧慮是項目初始否決風險,而隨項目創新度逐步上升,直至達到甚至超過國家創新基金批準標準時,該風險則得以有效抑制,此時政策性融資將以其無償優勢為企業帶來最大福祉。由此可見,隨著科技活動創新度提高,自主型與政策性融資將保證更優創新產出。
3. 引入證券市場準入費用與創新基金申請成本假設
上述分析忽略了證券市場準入費用與創新基金申請成本,作為創新產出量m 的引入橋梁,現將兩者納入分析框架。一方面,若考慮市場準入成本,對首次發行證券企業而言,機構評估等前期費用將帶來一筆很大的固定支出,故通常意義上講,尋求證券融資的企業在未來仍會繼續經由資本市場籌集資金。因此,假定市場準入費用為F,企業未來預期證券融資m 次(即企業創新活動預期數),每次融資費用記為 f ( m),且f ′( m) < 0;另一方面,科技型企業在首次申請國家創新基金時,相關資料(企業營業執照、國稅地稅登記證及公司章程等)的在線注冊及書面郵寄同樣耗費企業相當時間與財力,此固定花費不容忽視。故此處假定基金申報成本為E,且企業有意繼續申請政府資助,預計次數與企業未來預期創新數m 一致。因此,企業單次基金申請成本可表示為 e( m),且 e′ ( m) < 0。
基于上述假定,企業采取政策性融資、自主型融資時,創新項目 t=0 時的期望價值分別變換為公式(5):和公式(6):。此處要求與成立。將這兩種融資方式分別與被動型融資比較,即可判斷考慮固定籌資成本后,政策性融資、自主型融資相較被動型融資的創新效率優劣。

從成本收益角度考慮,預期創新數(即未來融資次數)增加會稀釋單次籌資成本,繼而使自主型、政策性融資創新價值相對提升。
4. t =0 時的最優資產結構選擇
基于企業融資選擇,可對其資金結構做進一步討論。限于篇幅,此處直接給出命題2①詳細證明可通過掃描本文二維碼,到本刊官網“附錄”中查看。:董事會在t =0 時將以如下原則確定企業資產結構:
簡言之,(a)部分表述了被動型融資主導下,銀行機構如何通過資金借貸控制創新進程,繼而實現創新項目期望價值最大化的情形。其核心在于,無論 t=1 時項目相關新息是正是負,銀行均可借助貸款量掌控創新活動進一步走向——既保證在消極新息產生時收回已有借款,又確保在積極新息出現時項目順利進行。(b)部分充分體現了董事會最大限度借助債券融資,以削弱經理人對企業現金流獨裁控制的利益分歧現象。(c)部分則對政府資助提升企業價值,進而加大股票發行籌碼的狀況予以描述。

命題3 以命題2 為基礎,后者闡釋了不同融資方式下相異資產結構的形成機理:相較自主型融資,銀行機構將項目終止的潛在價值予以考慮,故企業在 t=0 時所獲銀行貸款數大于債券融資額;也正是考慮到創新項目中途清算的可能性,銀行控制下的股票融資較企業自行決策時數量較少。因此銀行主導項目決策時將導致較低的權益負債比。政策性融資則潛在增加了企業創新項目價值,權益負債比隨之增大。再結合自主型、政策性融資的創新優勢特點,不難得到企業權益負債比隨創新項目新穎度與創新期望數增加而提升的結論,即命題3。
至此,基于效用最大化原則,立足創新結果對關鍵科技金融方式創新效果的理論探討已基本完成。從融資構成角度出發不難發現,相對于被動型融資,自主型、政策性融資對應更多數量、更高質量的科技產出,尤其政策性資金與高新穎度創新成果表現出極強的契合度。鑒于此,本文從科技創新的二維屬性出發,分別基于“數量”和“質量”兩層面對自主型、政策性融資于科技創新的正向關系進行驗證。具體實證中,本文沿用Atanassov 等人(2005)研究方法,統一以創新產出作為因變量,一方面便于同時檢驗各關鍵融資變量與創新成果的內在關系,另一方面亦使各主要融資工具的科技創新效果得以考察。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這很可能引致不容忽視的內生性問題,對此本文將在實證模型的選擇運用中予以有效修正。依據前文結論,本文作出如下實證假設:
假設1:其他條件一定時,獲得政府創新基金支持、采取較多自主型融資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所對應的創新產出數量更多。
假設2:其他條件一定時,獲得政府創新基金支持、采取較多自主型融資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所對應的科技成果更具創新價值。
三、實證模型設計與相關數據獲取
(一)計量方法與變量選擇
基于前文假定,本文基本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因變量反映企業創新能力,依據科技產出“數量”與“質量”的二維屬性,此處分別用企業年專利申請授權數 Pait(Shyama,2002;Guan,2005)及其年專利被引數 C Pait(Trajtenberg,1990;Albert,1991))具體衡量。Fit表示自主型、政策性融資工具變量序列,鑒于前文假定,主要包括普通股、企業債融資額(自主型)與創新基金資助情況描述變量(政策性),以企業股權價值比、債券價值比(Atanassov,2005)以及是否獲得政策資金的二值指示變量 GFit分別替代。具體說來,E、P 各自指代企業股票及發行債券的賬面金額,A 表示企業資產總值;對于虛擬變量 GFit,企業獲得政府資金支持時取值為1,反之取0。Zit是外生控制變量向量,遵循Hall 等(2001)的研究思路,此處引入企業科研投入RD 和產品銷售額S,并分別以其自然對數ln( RD )it、ln( S )it作為企業規模控制變量。此外,本文亦將企業年齡(Age)、經營現金流、利潤總額、留存收益及有形資產價值()等其他控制指標納入模型,以消除由企業自身差異引致的創新產出分化。其中,R、Cash 與T 分別代表企業留存收益、經營現金及有形資產賬面價值。另外,δt表示時間非觀測效應,反映除 Fit外其他隨時間變化因素對企業創新產出的影響,ηi表示地區非觀測效應,用以描述企業研發能力的地域差異。
進一步考慮因變量數據特點不難發現,企業年專利數及其后續被引量均屬計數型,故使用線性回歸模型會引致計量偏誤,因此本文借鑒Hausman 等(1984)的研究思路,引入泊松模型對自主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創新推動效果進行驗證,具體形式表述如式(8):

根據泊松分布特點,有:

換言之,樣本方差與其均值一致是該分布成立前提。事實上,由于不確定性等非觀測效應存在,樣本條件方差往往遠超過其條件均值,表現為過度離散。此時泊松假定不再成立,負二項回歸模型成為其最合適的替代模型,具體形式為:

可以看到,當過度分布附屬參數θ 為零時,二項分布則退化為泊松分布。
一般而言,運用固定效應法雖能一定程度上去除靜態面板模型中的個體異質性,但產生于聯立性、遺漏變量與測量誤差的內生性問題卻仍舊存在。因此,本文引入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內生性問題予以緩解。回歸模型進一步修正為:

(二)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有鑒于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本文數據主要涉及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專利申請數量及其后續被引次數、企業普通股與債券融資數額以及創新項目政府基金資助情況,同時囊括企業自身屬性相關描述,諸如企業年齡、科研投入、經營現金流、留存收益以及有形資產價值等指標均不可或缺。參照《科學技術部、財政部關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的暫行規定》(1999)、《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2003)中科技型中小企業相關界定②科技型中小企業為:主要從事高新技術產品研制、開發、生產和服務業務,企業負責人具有較強創新意識、較高市場開拓能力及經營管理水平,通過創新產品生存并成長起來的創新型中小企業。企業職工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科技人員占職工總數比例應不低于30%,企業每年用于高新技術產品研究的開發經費當不低于銷售額的3%,直接從事研究開發的科技人員亦應達到職工總數的10%以上。,本文遴選我國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創業板上市,基本符合標準的科技型企業322 家(中小板企業173 家,創業板企業149 家),同時考慮到企業年齡因素限制與數據資料完整性制約,將研究時間跨度確定為2006—2014 年。數據具體來源于《中國知識產權年鑒》、SooPAT 專利搜索網以及和訊網相關企業年度報告。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1 簡要列出了關鍵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及其相關系數。其中,Panel A 反映了樣本期獲得專利企業與未獲專利企業的屬性差異,其均值差別在5%,,水平下表現顯著。可以看到,就資產結構來講,無論普通股的資產占比,亦或公司債的價值份額,專利企業均呈較大數額,表現為更高的“自主型”籌資量,其政府基金資助額亦以年均419.2 萬元的差值高于無專利企業。前理論假設已得到統計結果初步支持。除此之外,有創新成果企業往往具有更大規模,正如表1 所示,諸如有形資產、銷售收入等企業規模屬性變量,專利企業均無一例外處于更高水平,顯示出科技創新能力與企業物質設施及市場經驗的正向關系。值得一提的是,科技產出最為直接的影響因子——科研投入,在兩類企業間表現出最大程度差異:專利企業創新投入較非專利企業三倍有余,這不僅與科研資金強力創新支持作用的主流觀點(Demirel 等,2001;何慶豐等,2009)一致,亦符合投入產出正相關的經濟直覺與預期。
Panel B 基于樣本期專利企業,以專利年均被引數(中位數4)對觀測值進一步劃分,相關結果與Panel A 如出一轍。總體而言,相對低專利引用企業,被引數高于均值水平的企業通常表現為更大的企業規模與更高的創新投入,其融資結構中自主型、政策性的資金占比亦明顯高于前者,同樣與先前假設不謀而合,此處不再詳述。Panel C 報告了關鍵解釋變量的相關性檢驗結果。從各相關系數可以看出,本文自變量間并不存在多重共線性,模型設定相對合理。細察各融資工具變量,一方面,企業股票融資與債券融資的相關系數很小且為負(-0.029),反映出自主型融資方式內部的輕微替代性;另一方面,政策性資金與自主型資金關系卻相對復雜:系數0.033、-0.028 分別顯示出政府資金支持與企業股票融資間細微的促進效應,及其與企業債券融資間微弱的抑制作用。對此,可能的解釋是,創新基金獲批可理解為政府對科研項目的一種肯定,由此引致的正向社會輿論效應將無形中衍化成企業股票的利好信息,繼而推動股價上行,企業股票籌資額隨之增加,債券融資額相對下滑。加之企業既已在股票市場獲得充盈資金,其債券發行絕對量亦將減少,進而企業債券融資占比進一步走低。總之,此處僅初步顯示了描述性統計結果,下文將以專利產出作為關注焦點,就融資特點與創新成果的對應關系進行驗證,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融資工具的創新支持效果,即科技金融效率。

表1 樣本的統計描述與變量的相關系數Panel A:基于專利數差異的企業屬性

Panel B:基于專利被引數差異的企業屬性

Panel C:主要變量相關系數
(二)回歸分析
1. 專利數量回歸結果
表2 前三列給出科技金融專利產出數的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對應式(5)、式(6)與式(8))回歸結果①對式(5)對應的隨機效應模型進行Hausman 檢驗,檢驗結果接受固定效應模型,故此處未提供隨機效應相關結果。。可以看到,線性回歸、泊松回歸及負二項回歸模型中,政策性融資與自主型融資變量系數均顯著為正,對科技產出數的正向關系得到初步印證。事實上,各系數值進一步反映了融資工具的創新推動效果。以列(3)為例②專利數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均值為12.018,標準差為31.976,將近前者三倍,故此處負二項分布模型較泊松分布模型更為合適。,普通股、企業債資產占比每增加10%,將分別引致專利產量提升2.16%與3.09%,政府資助企業專利產出數亦超過其他企業40.5%。其他兩列經濟解釋基本類同。
如前所述,受內生性問題影響,上述結果極可能有偏且非一致,故表2 后五列引入專利數一階滯后項,運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式(9))對原假設進一步考察。不難發現,各列滯后項系數始終顯著為正,揭示出創新活動的連續性與積累性,亦側面印證了動態模型設定的必要性。列(4)針對關鍵融資變量回歸,其系數無一不正向顯著,政策性、自主型融資于專利產出的積極效應不言自明。為檢驗結果穩健性,現將控制變量納入模型,回歸結果于表2 后四列呈現。顯然,無論單一融資工具,亦或融資工具組合,其回歸系數均為正且表現顯著,一方面印證了與創新產出的正向關系,另一方面亦衡量了科技金融的創新效果。正如列(8)所示,企業普通股系數在5%,,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股票籌資占比每擴張1 單位,即期專利數相應提升0.118,長期增長量將至0.263(0.118/(1-0.552));同理可得債券融資對專利產出的長期效應為0.310(0.139/(1-
0.552));此外,較未獲政府支持企業,受資助企業長期專利產量將超過前者0.417(0.187/(1-0.552)),創新基金的巨大科技效能表現無遺。另外,科研投入、有形資產、銷售收入及息稅前利潤的資產占比均顯著為正,與Caves(1998)、Atanassov(2005)等學者結論基本一致,亦符合通常意義的經濟直覺。可以認為,自主型與政策性融資工具與專利產出的正向關系已無可厚非,對科技創新的支持效力亦清晰可見,假設1 得到有力佐證。表2 底部給出了Hansen 檢驗與序列相關性檢驗結果,工具變量選擇的有效性與GMM 估計量的一致性得以驗證。

表2 面板數據回歸結果(專利數)
2. 專利引用次數回歸結果
本部分將企業專利平均引用數納入分析框架,用類似方法考察融資方式與創新價值的對應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就其專利質量作用效率予以挖掘,相關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面板數據回歸結果(專利引用數)

續表3
根據表3,引用次數回歸結果與專利數量統計結論可謂不謀而合。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列(1)~(3))結果顯示,自主型與政策性融資變量系數均顯著為正,揭示出普通股、企業債及創新基金與專利價值的強烈正相關。考慮變量間內生性而將專利引用數一階滯后項引入模型后,當期專利被引數受前期被引數影響顯著,顯然創新產出質量亦是一連續調整過程。類似專利數分析思路,列(4)~(8)分別對應僅有關鍵融資變量、囊括單一融資工具及融資工具組合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就自主型、政策性融資變量表現顯著的正向系數來看,其專利價值的促進作用已不言而喻——仍以列(8)具體分析:普通股、企業債及創新基金對專利引用量的短期效應可由系數直接得到,分別為0.136、0.161 與0.238,依照前文述及方法亦可算得三者的長期效應:0.284、0.336 及0.497。值得注意的是,相對表2,表3 中各融資變量系數均不約而同的表現為更大數值,反映出關鍵資金渠道與創新質量間更為緊密的相關關系。以創新基金為例,后者長期作用超過前者8 個百分點,暗示著政策性資金對提升專利被引數的更大貢獻度。類似規律在普通股及企業債融資工具上同樣清晰可見。究其原因,確切觀點尚未形成,而專利被引數本就建立在專利成果數之上,繼而產生一定“疊加效應”不失為一種可能解釋。總之,專利引用數經驗結果顯示,普通股、企業債及政府基金均與專利被引量顯著正相關,昭示著自主型、政策性融資方式對提升專利價值的巨大推動作用,本文預測2 得以印證。
五、主要結論
作為創新活動的主要實踐者,科技型中小企業可謂當之無愧的“創新生力軍”。隨著其“科技馬達”帶動力的日趨強勁,企業視角的科技金融效率研究必將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本文立足我國科技型中小企業,分別基于“政府-企業-銀行”三方三階段博弈模型與靜、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以科技金融方式與創新產出的關系論證為跳板,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對企業主要融資工具的相異科技產出效率進行探討,對其關鍵融資渠道的創新支持效能差異予以揭示。具體結論如下:
首先,相較被動型融資,自主型、政策性融資的創新價值優勢與企業期望創新數成正比,即企業創新產出預期數愈多,被動型融資主導的科研項目總價值愈受局限,自主型、政策性融資創造更高創新價值的可能性愈大。換言之,唯有自主型、政策性融資才能實現高創新產出企業的價值最大化,因而對應于更高數量的創新產出。事實上,融資方式的高產亦是創新實際決策權的高效,由此,“企業自主決策、政府輔助支持”的科研模式無疑大有裨益。針對銀行資金的決策干預,可通過金融工具創新,于“被動型”貸款工具中逐步引入“自主型”因素,適度放松銀行機構對科技項目的監督控制,實現創新決策從“被動”向“主動”的積極轉變。
其次,相較被動型融資,自主型、政策性融資的創新價值優勢與創新成果價值含量成正比,即企業科技產出新穎度越高,被動型融資引致的科研項目總價值越有限,自主型、政策性融資越有可能帶來更高的創新價值。從融資構成角度講,即相對銀行借貸,普通股、企業債及創新基金對應更高質量的科技產出。究其根源,科技項目新穎度愈欠缺,銀行機構相關信息掌控就愈準確,被動型融資所發揮的創新支持作用愈重要;隨著項目新穎度逐步提升,銀行機構新息辨別力愈漸下滑,自主型、政策性融資工具的高支持效能則愈發顯現,尤其當其新穎度達到某一水平時,政策性融資的創新推動效力將表現出絕對優勢。這一方面揭示出政府基金對高創新度項目的強大助力,強調了適度加大政策性科研投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亦反映出銀行機構信息判斷“短板”對高新科技產出的相對阻滯作用,為我國金融部門信息系統的強化升級敲響警鐘。
最后,立足企業融資結構,被動型、自主型及政策性融資方式的權益債務比(股票價值/債務價值)依次增大。驅使于逐利性本質屬性,隨創新成果數量、質量提升,銀行貸款將逐步退出融資范圍,企業權益債務比相應攀升。換個角度講,高權益融資占比對應大數量、高質量的創新產出,股票融資的科技支持效率可見一斑。由此可為我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優化提供思路:就增強創新推動力、提升自主研發水平而言,合理降低資本市場準入門檻、確保科技企業普通股順利發行,不僅滿足了企業權益債務比的相應提升,亦為其最大限度享有創新決策權提供了條件,可謂“一石二鳥,一箭雙雕”。
[1] 崔艷娟,趙 霞. 科技金融與中小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實證分析[J]. 經濟與管理,2013(10):82-85.
[2] 柴國俊. 地方政府為何熱衷拆遷?——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4(12):27-37.
[3] 段世德,徐 璇. 科技金融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研究[J]. 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14):66-69.
[4] 何慶豐,陳 武,王學軍. 直接人力資本投入、R&D 投入與創新績效的關系——基于我國科技活動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 技術經濟,2009(4):1-9.
[5] 張靖霞. 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成長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機理分析及體系構建[J]. 改革與戰略,2012(7):129-131.
[6] 趙昌文,陳春發,唐英凱. 科技金融 [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7] 趙稚薇. 科技金融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效率研究[J]. 金融經濟,2012(20):67-69.
[8] Arellano,Manuel,Stephen Bond.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227-97.
[9] Atanassov Julian,Nanda Vikram,Amit Seru. Finance and Innovation:The Case of Publicly Traded Firms [R]. Ross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2005,No. 970.
[10] Benfratello Luigi,Fabio Schiantarelli,Alessandro Sembenelli. Banks and Innovation:Microeconometric Evidence on Italian Firm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8,90(2):197-217.
[11] Blundell,Richard,Stephen Bond.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43.
[12] Caves Richard 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nd New Findings on the Turnover and Mobility of Firm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36:1947-82.
[13] Guan Jiancheng,Liu Shunzhong. Comparing Region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of PR China-Based on Dat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Paten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5,32(3):225-45.
[14] Hall Bronwyn H.,Jaffe Adam,Manuel Trajtenberg. Market Value and Patent Citations [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36:16-38.
[15] Hall Bronwyn H.,Ziedonis Rosemarie. The Determinants of Patenting in the U. S. Semiconductor Industry,1980—1994[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32:101-28.
[16] Hart O. D. Firm,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7] Hausman Jerry,Bronwyn H. Hall,Zvi Griliches. Econometric Models for Count Data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ents-R&D Relationship [J]. Econometrica,1984,52(4):909-38.
[18] King Robert G.,Ross Levine. 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3-42.
[19] Albert,M. B. D. Avery,F. Narin,P. McAllister. Direct Validation of Citation Counts as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ly Important Patents [J]. Research Policy,1991,20:251-59.
[20] Pelin Demirel,Mariana Mazzucato. Does Market Selection Reward Innovatiors?[J]. The Open University,2001,7:1-26.
[21] Saint-Paul Gilles. Technological Choice,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763-81.
[22] Scherer K R,Paul Ekman. Approaches to Emotion [M]. Hillsdale,N. J:Lawrence Erlbaum,1984.
[23] Shyama V. Ramani,Marie-Angele De Looze. Using Patent Statistics as Knowledge Base Indicatiors in the Biotechnology Sectors:An Application to France,Germany and U. K [J]. Scientometrics,2002,54(3):319-46.
[24] Tadesse Solomon.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Evide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2002,11:429-54.
[25] Titman Sheridan,Roberto Wessels. The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J]. Journal of Finance,1988,43:1-19.
[26] Trajtenberg Manuel. A Penny For Your Quotes:Patent Citations and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32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