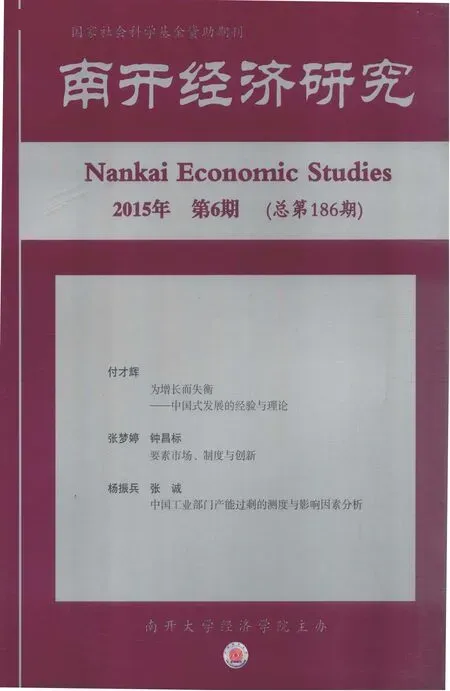為增長而失衡——中國式發展的經驗與理論
付才輝
一、中國式發展的特征: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
發展的目的不外乎就是把蛋糕做大而且相對公平地分享。效率和公平是評價任何發展模式的兩個基本維度(Basu,2000)。就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總量增長相對單一,而結構失衡涉及的面則相對廣泛——重要的方面包括居民之間的差距、城鄉之間的差距、地區之間的差距、產業之間的差距、環境問題等長期問題,以及國際收支差距、投資與消費結構等短期問題(項俊波,2008)。那么,中國在這兩個維度上的發展績效如何呢①限于框架的統一性,本文對于短期的投資與消費、國際收支以及環境問題不做作分析,對中國結構失衡的概括性描述可參見項俊波(2008)和王保安(2010)等等。林毅夫等(1994)的《中國的奇跡》一書對改革開放前重工業趕超戰略的系統扭曲與其后漸進式改革的成就與問題也有全面闡述。Brandt 和Rawski(2008)主編的《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也有較為全面的評述。?
圖1 直接從構成經濟總量的部門結構層面統一了“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這兩個發展的維度。在增長維度上,1953—2008 年這56 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8%,,以上,1953—1977 年這25 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6%,,以上,1978—2008 年這31 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高達9%,,以上。就三次產業部門結構失衡來看,1953—2008 年這56 年的年均熵指數高達30%,,以上,1953—1977 年這25 年的年均熵指數高達40%,,以上,1978—2008 年這31 年的年均熵指數高達26%,,以上。盡管改革開放是一個“結構虛擬變量”,改革開放之后總量增長增大、結構失衡減少,但增長與失衡的伴生關系特征并未改變。因此,總體上看中國的發展績效是:總量增長成就突出,結構失衡代價沉重。更重要的是,圖1 還展現出了“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相互伴生的動態趨勢:經濟總量擴張必拉大經濟結構失衡程度;反之,經濟結構失衡程度亦隨經濟總量回落而縮小(袁江和張成思,2009)。因此,中國不應該對總量增長過于沉迷,當然也無需對結構失衡過于沮喪。增長與失衡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收益和代價罷了,關鍵是要理解為什么中國經濟發展會呈現出這種特點。

圖1 中國式發展: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伴生關系
二、中國式發展的緣由:尋找政府主導經濟的阿基里斯之踵
(一)增長與不平等:由來已久的理論爭議
正如公平與效率是人類古老的話題一樣,增長與不平等的關系也是經濟學重要的主題。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Kuznets(1955)就提出了為后世廣為爭議的假說:在收入水平較低階段,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擴大相伴隨,但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增長會緩解收入差距①Piketty 和 Zucman(2014)利用更長的歷史數據認為庫茨涅茨倒U 曲線只不過是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后的短暫現象,資本回報率大于經濟增長率鎖定的不平等始終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一個長期的持續現象。。20 世紀60 年代和70 年代教科書中的基調是,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勵,從而也有利于增長(Ahgion et al.,1999)。然而,在20 世紀80 年代及90 年代隨著新增長理論的興起,這些傳統的觀點遭到了駁斥,新的觀點認為削減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有利于增進窮人的機會和教育并擴大市場,從而有利于增長,增長反過來又有利于緩解不平等。因此,更高的平等是增長自我維系以及良性發展的條件(Murphy et al.,1989;Todaro,1997)。來自20 世紀80 年代之前數據的分析結論模棱兩可(Ahgion et al.,1999)。在爭議尚未平息的20 世紀80 年代及90 年代之后,OECD 等發達國家又出現了新一輪的(工資)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涌現了偏向型技術進步、貿易自由化、組織方式變化三種流行的解釋增長放大收入差距的觀點(Acemoglu,2002;Akerman et al.,2013)。這些爭議確實凸顯了發達國家市場機制的復雜性①可參考Ahgion 等(1999)對不平等與增長的關系做的綜述。。但是正如Garcia-Penalosa 和Turnovsky(2007)總結道:“實際上,這些爭論都忽略了扭曲稅的角色。然而,一旦意識到這點,政策制定者顯然會面臨潛在的兩難取舍(trade-offs),即促進增長的政策可能與稅前稅后的收入分配相抵觸”。亦即,過去的文獻忽略了政府財政政策在增長與不平等之間的兩難效應(trade-offs)。Garcia-Penalosa 和Turnovsky(2007)在一個帶有初始財富不平等和勞動供給具有彈性的理論模型中發現,增長增進型政策會引致不平等。
我們也猜測存在增長與失衡的伴生關系內生于政府政策的機制②當然,不排除其他市場自身因素驅動的增長與平等關系,比如Bandyopadhyay 和Basu(2005)。,但這個機制在中國有其獨特性。除了居民個體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總量增長關系之外,構成經濟總量的地區部門、城鄉部門、產業部門等部門之間的結構失衡問題可能發展中國家也有其根本性的不同之處。雖然在卡爾多特征事實所刻畫的平衡增長之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或者正在經歷由庫茨尼茨特征事實所刻畫的部門結構的變遷,但如圖2 所示,美國經濟增長率與三次產業結構失衡并沒有表現出中國那樣的特征(圖1),總量增長和結構失衡都非常溫和,尤其結構近乎均等化狀態。那么,究竟存在內生增長與失衡伴生關系的中國式因素嗎?

圖2 美國式發展:“總量與結構”相對平穩
(二)中國的國情: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
如果要找到增長與失衡伴生關系背后關鍵的中國式因素,那么勢必需要從中國式增長說起。如果從建國后的計劃經濟時代,再到漸進式市場轉軌,就整個六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應該是一個基本特征事實。這一點可以從財政收支占GDP 的比重及其支出結構得到直觀的體現。1952—2008 年,財政收入占GDP 比重年均高達22.47%,財政支出占GDP 比重年均高達23.18%。當然,這個比例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更重要的是,中國財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拉動經濟增長的經濟建設費平均就占到了49%,,以上。雖然1978 年改革開放之后,政府已經把定價權讓位于市場了,但通過國企、市場準入限制、深度介入的產業政策、地區政策(包括特區政策)、城鄉政策等等依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和市場經濟主體的激勵機制。正如前所述,中國經濟的增長成就斐然。因此,中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也被譽為“發展型政府”;中國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也被冠以經營轄區經濟的“政治企業家”。無數的文獻和學者努力地尋找著中國經濟增長奇跡背后的原因和動力機制,歸納出了眾多的“中國模式”,諸如“中國式聯邦主義”(Qian 和Xu,1993;Qian 和Weiganst,1997)、“網絡資本主義”(Boisot 和Child,1996)、“為增長而競爭”(張軍和周黎安,2008)、“中性政府”(姚洋,2009;賀大興和姚洋,2011)、“地區性分權式權威主義”(Xu,2011)、中國式增長(Song et al.,2011)、發展戰略理論(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1994、2012)等等①許多人也認為中國發展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Heston 和Sicular(2008)在《中國與發展經濟學》一文中就沒有概括一個模式,只是通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較概括了一些中國式發展的特征,并指出中國的經歷特別,難以效仿。。
(三)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阿基里斯之踵:部門專用性政策
1. 政府主導經濟的得失
文獻中所歸納的各種中國模式,在肯定政府主導經濟的增長成績時也都指出了其帶來的負面后果,比如中國式聯邦主義誘發的保護主義(Li 和Zhou,2005),網絡主義陷入的規則困境(Li,2000;王永欽,2006、2008),為增長而競爭所扭曲的民生支出(付勇和張晏,2008),粗狂式增長(吳敬璉,2005)。王永欽等(2007)以及王賢彬和徐現祥(2014)就較為系統地總結了分權式改革的代價以及官員引領發展的風險。聶輝華(2013)也系統總結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下政企合謀誘發的一系列“事故”——礦難、高房價、食品安全等等。林毅夫等(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林毅夫和蘇劍,2007;林毅夫,2008;陳斌開和林毅夫,2013;林毅夫和陳斌開,2013)反復強調了政府的重工業趕超發展戰略導致的三位一體的系統性結構失衡的負面后果,比如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分配惡化等失衡問題。賀大興和姚洋(2011)也指出了“中性政府”為追求增長而把有限資源分配給高生產能力群體的做法勢必擴大收入差距。總之,正如Heston 和Sicular(2008)與其他國家對比所總結的中國式發展的幾個重要特征:增長與脫貧成就表現優良,失衡與不平等表現嚴峻,政府及其官員在決策中的權力巨大。
因此,在此背景下將“增長與失衡”視為政府主導經濟的得失并無不妥。恰如許成綱概括的(Xu,2011):“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表明,這種根本性問題的答案由不同政府干預形成的成本和收益取舍(trade-offs)所決定”。雖然前述文獻所指出的政府主導經濟存在的得失對于理解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很有啟發性,但是在同時內生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邏輯上并不清晰流暢。姚洋的“中性政府觀”雖然細致地揭示了中性政府追逐增長的機制,卻未深入揭示失衡的機制。聶輝華的總結過于瑣碎,缺乏一個相對一致的宏觀分析框架。王永欽等、王賢彬和徐現祥、許成鋼等的總結更多的偏向于評述而非建構。Brandt 和Rawski(2008)的總結過于全面而無一個核心的邏輯架構。因此,未來的研究還迫切需要一個同時內生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統一分析框架。現有文獻的積累不但極具啟發性,而且對于構建這樣的框架也提供了理論前提。本文直接承前于姚洋等的“中性政府觀”和林毅夫等的“新結構經濟學”。
2. 中性政府的行為
姚洋等(姚洋,2009;賀大興和姚洋,2011)認為,中國政府是一個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這樣的政府不會遷就某些特殊利益群體,其經濟政策與群體間的非生產性特征無關,能夠放開手、腳把資源分配給那些最具生產力的群體,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必然會擴大群體或地區之間的差距。他們詳細論證了非民選政府策略性選擇成為中性政府所具有的效率含義。雖然尚未揭示失衡的機制,但這個思想其實已經蘊涵了政府為增長而失衡的可能性。賀大興和姚洋(2011)理論模型的一個重要推論是:一個中性政府會選擇性地采取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政策,哪怕這些政策會造成收入的不平等。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采取這些看似歧視性的政策,恰恰是因為它是中性的:并不特別地照顧任何群體的利益,它才可能放開手腳采取“有偏”但與生產能力匹配的經濟政策①本文不打算深究中國式發展的政治基礎,中國政府是一個中性政府的觀點可視為本文的前提。與中性政府不同,民選政府通過中位數規則選擇的再分配政策是有利于緩和不平等的(Persson & Tabellini,1994);與利益集團專制政府不同,中性政府的增長訴求更為一般化,而無需與利益集團“利益相容”(Olson,2000)。事實上,Acemoglu 和Robinson(2002)也認為不同的政治因素決定了不同的發展與不平等關系模式。他們認為歐洲國家之所以遵循庫茨涅茨曲線的原因是:在工業革命之前政治權力由少數權貴獨享,絕大多數政策有利于權貴,少有對普通民眾的再分配;工業革命的推進提高了經濟不平等,但同時也加劇了社會動蕩與革命的威脅;權貴為了防止社會動蕩和革命,作為可置信承諾,公民權力被擴大,擴大了對大眾的再分配,降低了不平等。專制災難之所以在非洲等國家發生,是因為非洲國家的政治流動性(Political Mobilization)非常低,難以產生有效的革命威脅,初始的非民主體制得以長期持續。。
通過農村改革和特區政策兩個具體的例子,賀大興和姚洋(2011)認為,“在具體政策上,把政府看作是一個精于計算的主體還是合適的,因為具體政策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較明顯的。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總要在社會群體之間進行取舍。”如此說來,主導經濟的政府確實有動力實施“為增長而失衡”的政策動機。但是,這樣的政策的特征是什么?什么樣的政策能夠同時內生增長與失衡?機制何在?他們尚未深入闡述,不過林毅夫(2012)在新結構經濟學中的論述對此極具啟發性,為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提供了思路。
3. 新結構經濟學的詮釋:部門專用性政策
在賀大興和姚洋(2011)的模型中,“政府決定兩個政策,一個是稅率,一個是政府服務。在現實中,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決策理解為政府政策對不同群體的損失和收益的實質性影響”。因此,這樣的政府政策的關鍵特征就是群體專用的。正如Kruger(2011)所指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能夠稱為新的部分是如下斷言:協調和基礎設施升級應該以某種方式與一些特定產業相聯系”。林毅夫(2012)進一步解釋到:“事實上對發展中國家制定成功的發展戰略來說,甄別新產業和優先利用政府資源來發展這些產業都是至關重要的。為什么呢?因為基礎設施的改善往往是產業專用的。看看非洲國家最近一些成功的案例,你就知道甄別產業的必要性。例如:毛里求斯的紡織業、萊索托的服裝業、布基納法索的棉花產業、埃塞俄比亞的切花業、馬里的芒果產業和盧旺達的猩猩旅游業。它們都需要政府提供不同類型的基礎設施。把埃塞俄比亞的鮮切花運往歐洲拍賣地點需要在機場和正常航班上有冷藏設備,而毛里求斯的紡織品出口需要港口設施的改善,二者需要的基礎設施顯然不同。類似地,萊索托服裝產業所需的基礎設施與馬里的芒果生產和出口或者盧旺達用以吸引猩猩觀光者所需的基礎設施是完全不同的。因為財政資源和實施能力的限制,每一個國家的政府必須設立優先級,以決定哪些基礎設施應予優先改善以及公共設施的最優位置應設在哪里,這樣才能取得成功。鄧小平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初期就解釋了這種實用智慧,他同意允許一些地區和人們先富起來,最終使所有中國人能實現共同富裕。”
賀大興和姚洋(2011)模型中的群體專用性政策與林毅夫(2012)新結構經濟學中的產業或地區專用政策在促進增長作用上是一致的,并且新結構經濟學中的部門專用性政策也只有在中性政府的前提下才能夠發揮到極致。實際上,如賀大興和姚洋(2011)所言,任何部門專用政策都會產生得利者和失利者,得到政策優惠的群體獲利,沒有得到政策優惠的群體可能還要承擔政策成本。也如Kruger(2011)所言,“你可以想象,要求保護力度更大、時間更持久的保護的政治壓力會有多大。大家都知道,保護一些產業就意味著不保護其他產業,所以改革的收效必然會被削弱。”因此,也只有具備強權的中性政府才能頂住各種政治壓力去實施會在不同群體之間引起利益沖突的部門專用性政策。在民選或者民主政府中,部門專用的政策會遭到受損者的政治壓力,迫使政府難以實施這樣的政策。如反映中國增長與失衡的圖1 與反映美國增長與失衡的圖2 之間的反差,可能就反映出了這種根本性的政府行為差異。
如果說部門或群體專用性政策是內生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關系背后直接的政策工具,那么中性政府則是實施部門專用政策的保證。林毅夫(2012)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了這種發展的部門專用性政策的思想,并指出了傾斜程度過于違背比較優勢的嚴重后果,如舊結構主義的主張。賀大興和姚洋(2011)不但指出了這種群體專用的政策有利于增長最大化,還可能誘發收入差距。Kruger(2011)也擔心這種部門專用性政策誘發部門之間失衡的風險而質疑了林毅夫(2012)。因此,部門專用性政策可能是解釋中國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伴生關系的核心變量,并且可能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概念。倘若不是如此,那么有哪個發展中大國能夠以將近兩位數的增長率持續數十年之久呢,然而又有哪個發展中大國在取得如此驕人的總量增長成就的同時又面臨著如此嚴峻的不平等和結構失衡呢(Heston&Sicular,2008)?
事實上,自從Barro(1990)的開創性研究以來,政府的公共服務(稅收政策與公共支出)在內生增長中得到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細致地分析了稅收種類(勞動稅、消費稅、資產稅、所得稅以及遺產稅(在代際交疊模型中))與稅率,以及公共支出結構(生產性支出、消費支出、混合性支出)與轉移支付(包括在多級政府架構模型中的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及其規模等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是,具有部門專用性政策特征的財稅政策在這個主流的框架中卻被忽略了。部門專用性政策實際上是根據施政群體對象不同而實施不同的政策。即 {τ1,… ,τn}在現有文獻中是n 種類型的稅,而部門專用性政策則意味著 {τi1,… ,τim}是第i 種類型的稅(比如勞動稅)所針對m 個群體實施的群體專用性稅(比如以戶籍身份為標準的差別性勞動稅)。同樣,{ G1,… , Gn}在現有文獻中是n 種類型的公共支出(服務),而部門專用性政策則意味著 {Gi1,… ,Gim}是第i 種類型的公共支出(比如公共教育支出)所針對m 個群體實施的群體專用性公共支出(比如以戶籍身份為標準的差別性公共教育支出)。現有文獻雖然也探討了不同的稅和公共支出的類型組合對經濟增長以及不平等可能有不同的影響(如Easterly&Rebelo,1993;Devarajan et al.,1996;Fiaschi,1999;Jha,1999;Scully,2003;Garcia-Penalosa &Turnovsky,2007),但是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的部門專用性政策對總量增長與結構不平等的影響并未得到關注——部門專用性政策所具有的結構性特征可能才是中國等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廣義上的)公共政策的核心①其實,累進制個人所得稅及其補貼也反映出了針對“窮人”與“富人”的群體專用性政策特征。米增渝等(2012)在一個政府對個人征收所得稅和補貼教育的環境下,發現稅收多征于富人且窮人得到更多補貼的時候,收入不平等減少,增長上升;反之則相反。他們也基于1998—2006 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發現中國的稅收多征于窮人而富人得到了更多的補貼,收入不平等加劇,增長放緩。然而,中國的教育支出占政府公共支出的比例在過去60 年中微不足道,并且中國在20 世紀80 年代才開始實施個人所得稅,所以他們的發現可能不足以概括中國增長與失衡的長期模式。郭凱明等(2011)也提供了類似的分析。更有趣的是,Zheng 和Kuroda(2013)使用286 個城市的數據對中國地區不平等和增長的研究發現,不同的基礎設施類型對增長和地區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同,交通基礎設施在地區平等和增長之間存在取舍(trade-offs),而教育基礎設施不但可以提高增長也降低了收入差距。雖然公共基礎實施可能是部門通用的,但是對地區而言可能也是地區專用的。這些經驗例子也暗示了部門或群體專用政策在增長與平等關系上有重要影響。。
部門專用性政策的重要性在于其具有結構效應。部門專用性政策可以利用其結構效應制造更高的總量增長,但正因為如此同時可能誘發結構失衡。新結構經濟學的這個部門專用性概念可能會突破傳統公共經濟學以及AK 內生增長模型的思路,但是新結構經濟學在其理想的政府與市場關系定位分析中也可能忽略了其負面后果。所以,本文將其引入Barro(1990)經典模型來解釋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具有理論創新性,進一步在新結構經濟學關于政府與市場關系定位理論的基礎上夯實發展戰略的成本與收益理論(付才輝,2014、2015)。
三、結構失衡:概念與測度
盡管各種結構失衡現象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但本質特征都是一種不均等狀態。自Pareto 以來產生了一系列研究如何用精確的指標來衡量不均等程度的文獻。Cowell(2000)在《收入分配手冊》中將現有文獻中不均等指標研究方法分為三類:第一類指標通過先驗的選擇性過程來界定不平等,比如基尼系數和方差都有著非常直觀的統計學和經濟學意義;第二類指標由公理性方法推導出來,比如廣義熵測度族——泰爾熵指數就是這一類指標;第三類指標是在福利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統稱為Atkinson 指數。
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主要是體現在部門之間,相對而言部門內部的失衡程度較之于部門之間的失衡程度要低得多。政策異質性也基本上表現為部門專用,而不是個人專用。加之本文的任務是分析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伴生關系,因此分析單元應該設置為加總成經濟總量的部門,比如產業部門、地區部門、城鄉部門等等。所以,以部門為分析單元的話,第二類分析方法較為合適。比如以個體為分析單元的基尼系數就難以將部門之間的差距分解出來,而且對中間階層的收入較為敏感,而對兩端部門之間的差距不太敏感,從而難以度量城鄉部門以及地區部門之間的差距。所以,文獻中就常常使用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純收入之比度量城鄉兩部門之間的差距,但是這種做法沒有考慮城鄉人口比重,也就沒有考慮城鄉兩個部門在總量中的相對重要性。因此,許多研究就廣泛引入泰爾熵指數測度城鄉部門、地區部門、產業部門之間的差距(王少平和歐陽志剛,2007;干春暉等,2011;萬廣華,2013;等等)。因此,鑒于泰爾熵指數適合于以部門為分析單位的研究,而且具有公理化形式邏輯和直觀的經濟學含義以及便于分解的優點,本文也遵循大量文獻的做法采用泰爾熵指數來研究部門之間的結構失衡。當然,有必要坦誠交待的是,盡管我們在前文中將居民個體之間的(收入或工資)不平等現象也納入到結構失衡中,但后文模型的分析單位與分析居民個體收入差距的單元還是有所不同,即便思想上并無二致①以居民群體為分析單位討論政策異質性對兩極分化的影響可參考付才輝(2015)。。
為了不顯得過于抽象,我們以產業部門為例來討論下結構失衡的概念與測度,地區部門與城鄉部門等類似。任何一本產業經濟學教科書都會提到產業結構變遷的兩個基本維度——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也就是狹義上的產業結構變遷(產業升級),即庫茨尼茨特征事實或克拉克定律——農業份額的持續減少和工業和服務業的份額持續增加。產業結構失衡就直接對應于產業結構合理化。按照已有的界定,“產業結構合理化,是產業之間協調程度的反映,也就是說它是要素投入結構和產出結構耦合程度的一種衡量”(干春暉等,2011)。就這種耦合而言,研究者一般采用結構偏離度對產業結構合理化進行衡量。經濟越加偏離均衡狀態,產業結構越不合理。由于經濟的非均衡現象是一種常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更為突出(Chenery et al.,1989),從而結構偏離度為零便是理想的基準情況。干春暉等(2011)也認為結構偏離度指標將各產業一視同仁,忽視了各個產業在經濟體的相對重要程度。因此,遵循他們的做法,本文也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引入了如下的泰爾熵指數來測度產業部門之間的結構失衡程度(見公式(1)):

四、政府主導經濟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一)CRRA 偏好與線性最終產品加總
遵循常規,我們的模型經濟采取連續時間并且采納具有如下偏好的代表性家庭:

為了盡可能保持模型的簡潔,我們抹去了非一致性偏好與技術進步差異這兩個因素,而引入部門間的要素密度(或產出彈性)異質性——但我們不分析其對結構變遷(非平衡增長)的影響(類似的文獻可參見Acemoglu & Guerrieri,2008;Ju et al.,2015)。因此,在抹去非一致性偏好之后,最簡單的最終產品加總方式便是如下的線性加總:

式(3)可以視為更加一般化的CES 加總方式的特例。當然,式(3)的加總方式沒有考慮到城鄉部門、農業與非農業部門、重工業與輕工業部門生產的產品之間的異質性,但是我們的模型也希望容納地區部門,這是由于各個省市生產的產品可能同質性大于異質性。由于地區之間結構失衡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內容,為了捕獲城鄉、地區以及產業等部門間的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伴生關系的共性,最終產品的線性加總不但簡單而且更加合意。
同樣為簡化分析,設定人口增長率為零,即經濟體的人口L 為常數,單位化為1。C(t)表示t 時刻經濟體家庭的總消費,人均消費為c(t)=C(t)/L;W(t)表示t 時刻經濟體的家庭持有的實際總資產,人均實際資產為a(t)=W(t)/L;初值a(0)給定。同樣出于簡化的目的,假定家庭成員在任何t 時刻都無彈性地供給1 單位勞動,亦即無工作與閑暇的選擇。此外,假定不同部門內部均有足夠多的個體以保證市場是競爭性的,即行為者是工資w、利率r 的接受者。因此,家庭預算約束就為:

(二)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與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
借鑒Barro(1990)、Barro 和Sala-i-Martin(1992,2004)、Turnovsky(1996,2000)、Angelopoulous 等(2006)處理政府公共支出進入生產函數的方式,以及Acemoglu 和Guerrieri(2008)設置的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我們將第i 部門代表性企業采取的生產函數設為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形式:

以部門i 的人均形式表示之:

我們不妨將式(6)表示為:

其中:

按照Barro(1990)的分析思路,部門專用的政府公共支出與部門人均資本比可設置為政府的政策操作工具,那么式(7)其實就是部門層面的AK 模型,從而部門加總之后的總量增長也具備AK 模型的內生增長特征。因此,政府可以通過政策工具影響推動部門的內生增長,但邊際增長效應遞減,即
依部門i 而定的 Gi以及 χi刻畫了政府支出層面上的部門專用的政府政策。同樣,從政府收入的層面上,政府也可以設置部門專用的稅收政策τi。假定政府向部門i 按產出征收賦稅,稅率分別為 τi∈ ( 0, 1);并對其進行生產性支出 Gi。因此,政府的總收入與總支出分別為。此外,為盡可能更簡化,假定政府支出不進入消費函數,政府也無自身消費,但必須滿足預算平衡:

如果我們假定政府對每個部門的支出形成了部門內部共享的公共品,但對其他部門不具有外部性,那么政府支出就能夠形成具有俱樂部品性質的公共品。其實,這就是前文提到的林毅夫(2012)所強調的部門專用性政策。差別性的稅率與公共支出反映出部門所面臨的外在的政策異質性(或者稱之為政策傾斜),或者稱之為部門專用的政策。部門專用的政策在資源誤配學派中也可稱之為異質性“稅收和補貼①idiosyncratic policies/individual-specific “taxes and subsidies””(Restuccia & Rogerson,2013),這里的“稅收和補貼”是非常廣義的,不僅僅限于政府的財稅政策,可以寬泛地指政府針對部門實施的一系列影響部門損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姚洋和賀大興,2011)。因此,本文的模型實際上就從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與政府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兩個向度上拓展了Barro(1990)的經典政府公共服務內生增長AK 模型,或可稱之為結構AK 模型。
(三)代表性家庭最優化行為

可得最優化的一階條件為:

通過一階條件變換可得Euler 方程:

由力效用函數以及式(12)可得我們熟悉的消費增長方程:

(四)企業最優化行為與流動性均衡下的加總
任意部門i 的代表性廠商在任意時刻最大化本期利潤,所面臨的問題為:

其中δ 為折舊率(為簡化起見,假定所有部門折舊率均相同)。式(14)最優化的一階條件(FOC)為①按照資源誤配學派的觀點(Restuccia & Rogerson,2008、2010;Hsieh & Kleonw,2009),從靜態的局部均衡來看,式(8)中的部門專用異質性政策會導致要素市場扭曲,從而使得面臨不同要素市場扭曲程度的企業邊際產出不相等,資源誤配通過削減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抑制總量增長。與之不同,在政府公共支出具有外部性的情況下,從動態一般均衡來看,本文發現部門專用的政策異質性反而能夠制造總量增長。作為一種有待進一步論證的猜想,我們覺得這或許好像是資源誤配持續存在的根源。面對資源誤配學派未能夠清楚地解釋資源配置的來源與原因(Restuccia & Rogerson,2010;鄢萍,2012),Banerjee 和Moll(2010)發問到:為什么資源誤配會持續存在? 按照本文的思考方式,我們覺得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資源誤配其實可能內生于其經濟增長方式之中,尤其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方式。資源誤配學派強調的效率損失的根源在于外部干預將資源過多配置給了低效率的企業,本文中則可能正好相反,即政府將資源過多配置給了高效率(高資本密度)的企業。本質上講,資源誤配學派的見解沒有超過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批評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取了結構主義的發展觀導致了嚴重的扭曲,需要削減政府干預導致的扭曲并且保持價格正確。然而,正如Stigliz(2011)在后華盛頓共識中的反思——華盛頓共識錯把工具當目標,我們認為政府干預必有代價也必有收益。:

競爭性市場的對稱性均衡條件(Symmetric equilibrium condition)下,上述FOC(式(15))對所有部門的代表性企業i(i=1,2,…,n)均同時成立,也就是說要素的流動使得工資與資本利率在所有部門均相等,即 ri= rj= r、wi= wj= w,從而有:

由式(16)可得:

式(17)對任意的 i、j 均成立,對上式兩邊乘以 Li并對i 加總可得:然后將其以人均形式表示為:


從而得到對后文至關重要的加總關系式(也是資本的競爭性均衡配置方式):

將式(20)帶入FOC 式(15)可得資本利率與勞動工資在對稱性均衡下的加總式:

(五)動態一般均衡
由于通過最終產品的線性加總而簡化了產品市場的均衡,而勞動供給不帶彈性的假定也簡化了就業市場,所以根據瓦爾拉斯法則,在一般均衡時只需要資本市場出清即可: a (t ) = k (t)。將資本利率與勞動工資式(21)帶入消費增長方程式(13)、家庭預算方程式(4)可得該經濟體的總量增長動態方程系統,再將式(20)與式(7)帶入泰爾熵指數式(1)中可得結構失衡的狀態方程,最后將二者聯立便可得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動態一般均衡伴生系統:

式(22)中包含了加總的平均變量( k ,c ),也包含部門層面的參數與變量直觀上看還不能夠斷定該模型經濟存在如Barro(1990)模型中那樣的內生平穩增長大道(BGP),但我們可以證明拓展模型存在BGP①限于篇幅,平衡增長路徑存在性的證明(附錄1),可掃描本文二維碼,在本刊官網“附錄”中查看。,即:
(六)政府推動的內生增長與結構失衡


對式(24)化簡為:

這就是競爭性市場的對稱性均衡條件的式(16)。
綜上,政府可以使得該模型經濟直接登上增長率為γ(式(24))的平穩增長大道,起點為 k (0)、c (0) = (η - γc) k (0)、y (0) = ζ k (0)。模型經濟不存在轉移動態,如圖3 所示。

圖3 政府推動的內生經濟增長的相圖
因此,我們就得到了用以解釋第一部分中圖1 所描繪的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伴生系統:

五、為增長而失衡的機制
從式(26)中我們可以看到就結構性變量而言,政府的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由 Gi傳導,而 Gi與τi由政府的預算約束聯系在一起,所以直觀的 政 策 異 質 性 是以 及 市 場 的 部 門 要 素 密 度 異 質 性均可能同時影響到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如前所述,我們的模型正是從這兩個方向拓展了Barro(1990)的政府公共服務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第一個方向是將同質性的部門拓展到異質性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第二個方向是將政府的同質性政策拓展到異質性政策(部門專用政策)。
(一)基準情景(退化情景1):既無要素密度異質性,也無政策異質性
第一種情景便是在兩個方向上都做退化后的Barro(1990)基準情景。第一個方向上的退化意味著對任意部門i 均有αi= α,即所有部門的要素密度相同。第二個方向上的退化意味著對任意部門i 均有τi= τ與 Gi= G,這意味著公共支出是部門通用的,而且所有的(廣義上的)稅收政策也是平等的。在此既無要素密度異質性也無政策異質性的退化模型經濟中,參數變化為 zi= z、ki= k、ω = Aα、υ = A(1 - α),以及政府預算約束變化為G = T = τY,由于沒有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加總后可知整個經濟的代表性廠商的生產函數為:


因此,系統式(22)中的經濟增長動態系統就退化為經典的Barro(1990)政府公共服務內生經濟增長的基準模型:

再將式(28)帶入式(29),便可知此模型以式(30)的增長率在平衡大道(BGP)上運行(可直接參見Barro(1990))。

根據Barro(1990)的分析,政府在預算約束下通過政策組合(τ ,G)設計可以使得增長率式(30)最大化,即政府面臨的問題可以表述為:

規劃式(31)的最優解為:

此時,將式(32)帶入退化后的增長與失衡伴生關系式(26)可知:

式(33)中的最大化增長率便是Barro(1990)的基本結論。與此同時,在前述退化的Barro(1990)模型經濟中,式(26)中的泰爾熵指數始終為零,不論增長率最大化與否。
(二)市場自身的問題(退化情景2):在退化情景1 中納入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
第二種退化情景是只在第二個方向上的退化,這就意味著對任意部門i 均有τi=τ與 Gi= G,即不存在政策異質性。但是,部門之間依然存在要素密度異質性,即。因此,系統式(22)中的經濟增長系統就退化為:

政府的預算約束也退化為τ Y =G ,再將加總式(20)帶入退化后的部門i 的生產函數可得:

再將式(35)稍作變形并將退化后的政府預算約束帶入其中可得:
然后,對式(35)進行加總可得:
由式(37)和式(35)可得:

將式(38)帶入式(36)可得:

然后,將滿足式(39)的χ 帶入式(34)可知該模型經濟以式(40)的增長率在平穩大道(BGP)上運行。

與Barro(1990)的分析思路一致,政府在預算約束下通過政策組合(τ ,G)設計可以使得增長率式(40)最大化,即:



此時,該模型經濟的總量增長率和結構失衡程度為:
式(43)是在只存在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而不存在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的模型經濟中,政府最大化總量增長的情況下的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由此也可以看到,單單由市場自身的異質性也可能引發結構失衡,那么政府的干預就可能加劇或者抑制結構失衡。
(三)一般情景:在退化情景2 中再納入部門專用的政策異質性
在退化情景2 中再納入部門專用的政策異質性便是本文模型的一般情景。同樣,政府面臨的問題也是在預算約束下最大化總量增長率。首先,將加總式(20)帶入總的政府收入中:

再將加總式(20)帶入總的政府支出中:

因此,政府的預算約束變為:

那么,政府面臨的問題便是:

規劃式(47)的解為:


此時,該模型經濟的總量增長率和結構失衡程度(式(26))為:

式(49)其實刻畫了解式(50)中所包含的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程度或者說是政策傾斜程度。這樣的政策傾斜(不妨稱之為最優政策結構)實現了經濟總量增長率的最大化,然而必然也會導致部門結構之間的結構失衡。我們將這一結論概括為如下的為增長失衡的理論命題①限于篇幅,這里略去該理論命題的證明(附錄2),有需要者,可通過掃描本文二維碼在本刊官網該文的“附錄”中查看。:若,則 TL ≠ 0,存在這樣的i ≠ j(i、j=1,2,…,n)使其成立。
前述命題所反映出來政府追求總量增長率最大化所實施的部門專用政策誘發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或結構失衡的結論,與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重工業趕超戰略導致收入差距的結論是一致的(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林毅夫,2012;林毅夫和陳斌開,2013),但是與他們前期對增長的看法有所不同。按照“為增長而失衡”的機制,總量增長便可視為政府發展戰略的收益,而結構失衡則可視為政府發展戰略的代價。那么,如果考慮外部性,全盤否定重工業趕超戰略的觀點(林毅夫、 昉李周和蔡 ,1994;烏杰,1995;于光遠,1996)便十分欠妥,姚洋和鄭東雅(2008)就強調了這一點。
(四)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分解
為了更加清晰的揭示總量增長作為政府發展戰略收益的這一點,我們不妨在抹去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后與Barro(1990)基準模型做一比較,便可以看到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的單獨作用。在抹去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后,式(50)中的最大化增長率變為:

然后,將式(51)減去式(33)中的Barro(1990)基準模型中的最大化增長率可得:

我們曾在第三部分討論結構失衡時提到泰爾熵的一個優點是便于進行具有經濟學含義的具體分解,通過這個分解機制我們就能夠更加直觀的理解前面復雜的機制。于是可用式(1)進行如下分解:

再由式(48)中的解可知:

因此,將式(54)帶入分解式(53),便可把結構失衡分解為:
同樣,我們可將式(48)中的解帶入式(50)中的增長率,并將其分解為:


其中:

與前面Barro(1990)的基準情景相對比,式(57)對應于在既無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又無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模型中的增長率,而式(58)可稱之為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制造的結構性增長。
六、結構失衡的經驗分析
(一)具有理論基礎的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前面結構失衡的分解方程式(55),可將基準的計量模型設定為:

如前所述,X1刻畫了與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相關的結構失衡的來源,X2刻畫了與政策異質性(結構性干預)相關的結構失衡來源,X3刻畫了與政府干預程度相關的結構失衡的來源,ε 為隨機擾動項。鑒于式(59)的計量模型是從理論模型中推導出來的,具有嚴格的理論基礎,我們不輕易納入其他控制變量。此外,考慮到改革開放前后有大的差異,設置一個虛擬變量D 以反應其前后變化。如前所交代的,由于變量X1、X2、X2的加總權重原因,其系數符號可正可負,正的符號表示誘發作用,負則表示抑制作用。
(二)來自二元經濟的經驗分析
1. 變量與指標
我們首先選取城鄉二元經濟部門(農業與非農業部門)為例(即n=2),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失衡最為嚴重,更主要的是因為城鄉政策異質性涇渭分明。中國的城鄉政策差異不僅僅體現在財稅政策上,在諸如戶籍、選舉權等等制度層面的政策上也有較大的異質性。如圖1 所示,農業與非農業的二元經濟結構失調與三次產業的熵高度一致,相關系數為0.997,4。城鄉二元結構失衡與農業和非農業兩大部門劃分的產業部門間的結構失衡較為一致。當然,要量化廣義上以及更加細分產業部門的政策異質性具有一定的難度。在此,我們簡要對經濟結構進行非農與涉農二元劃分,以此建立相應指標,見表1。

表1 變量、計算公式與說明及其含義
2. 數據來源與樣本構建
通過二元經濟結構劃分之后,《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有財政支出以及支農支出的數據,因此可利用表1 中的公式計算出X2、X3。限于財稅政策的統計口徑,2006 年前后非常不一致,因此我們的樣本也截止到2006 年。與政策異質性一樣,市場異質性的測度也并非易事。為了盡可能的捕獲到市場異質性,我們采取多角測度策略,構建多個樣本。第一類樣本是部門要素密度不隨時間變化,第二類樣本則是要素密度在不同的時間可能會不同。參考中國資本份額的已有研究,由于農業部門是勞動密集型,α1取值為0.3 或0.4;非農業部門是資本密集型,α2取值為0.6 或0.7。因此,α1、α2不同的取值組合便可以構造四個樣本:樣本1(α1=0.3、α2=0.6)、樣本2(α1=0.3、α2=0.7)、樣本3(α1=0.4、α2=0.6)、樣本4(α1=0.4、α2=0.7),可用作穩健性比較。在第二類樣本中,章上峰等(2009)測算了中國1979—2005 年的平均資本密度。利用農業與非農部門的兩組權重(0.3,0.7;0.4,0.6)可構造兩個要素密度時變的樣本:樣本5(權重為0.3 和0.7)、樣本6(權重為0.4 和0.6)。
3. OLS 回歸結果
附表1①限于篇幅,附表1~附表15 均未在文中報告,請感興趣的讀者掃描本文二維碼在本刊官網該文“附錄”中查看。是樣本1 的OLS 回歸結果。第二、三欄是單獨回歸刻畫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的變量,不論控制時間趨勢與否,變量X1的系數均不顯著,沒有太大的解釋力;第四、五欄是單獨回歸刻畫政策異質性的變量,不論控制時間趨勢與否,變量X2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調整的可決系數均超過0.63;第六、七欄是完整設定模型的回歸結果,在沒有控制時間趨勢的模型中,除了X3外,X1、X2的系數均顯著;在控制時間趨勢的模型中,變量X1、X2、X3的系數均顯著;并且變量X1的系數為負,而變量X2、X3的系數為正,表明市場異質性可能對結構失衡具有抑制作用,而政策異質性卻有著非常顯著的誘發作用;模型的調整可決系數在0.8 左右,具有較高的擬合效果。附表3 是改革開放之后要素密度時變樣本的OLS 回歸結果,刻畫政策異質性和政府干預程度的變量對結構失衡都有顯著的誘發作用;而刻畫市場異質性的變量的作用只有在單獨回歸的第二、三欄中表現出了顯著的誘發作用②限于篇幅,我們沒有在文中報告樣本2~4 與樣本6 的OLS 回歸結果,基本上也是穩健的。。
4. ARIMA 回歸結果
由于在時間序列數據中隨機干擾項可能存在自相關,因此OLS 估計可能有偏。鑒于此,我們重新采取ARIMA 方法對樣本1~6 進行了回歸。附表2 是樣本1 的ARIMA 回歸結果,與OLS 回歸結果一樣,刻畫政策異質性和政府干預的變量X2、X3的系數顯著為正,在完整設定模型的第六、七欄中刻畫市場異質性的變量X1的系數為負。附表4 是改革開放之后要素密度時變樣本5 的ARIMA 回歸結果,同樣政策異質性相關的變量X2具有顯著的誘發作用,刻畫政府干預以及市場異質性的變量的誘發作用不太明顯③限于篇幅,我們沒有在文中報告樣本2~4 與樣本6 的ARIMA 回歸結果,基本上也是穩健的。。在要素密度時變的樣本中,我們進一步采取了GMM 估計,附表5 是其結果,結果依然是穩健的。總之,政策異質性對結構失衡有顯著的誘發作用,市場異質性反而表現出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來自區域經濟的經驗分析
1. 變量與指標
如前所述,除了二元經濟表現出嚴重結構失衡之外,就要數中國區域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了。相對于二元經濟而言,區域經濟的市場異質性可能較之政策異質性程度要大得多,而區域政策異質性的區分可能更加明顯。同樣,除了財稅政策的區域差異之外,諸如特區政策之類的廣義的政策異質性也較難以測度。由于海南省缺乏改革開放之前的數據,我們將其排除在樣本之外,令n=30。表2 是以省市為單元構建的變量指標。
2. 數據來源與樣本構建
要構造變量X1的樣本,需要省市的要素密度,由于缺乏近六十年整個時間序列的要素密度數據,我們以傅曉霞和吳利學(2006)測算的省級平均資本密度作為近似。其余數據均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表2 變量、計算公式與說明及其含義
3. OLS 回歸結果
附表6 是區域經濟樣本的OLS 回歸結果。不論是單獨回歸(第二、三欄)還是完整回歸模型(第六、七欄)中,刻畫地區要素密度異質性的變量X1均非常顯著地誘發了地區之間的結構失衡。這表明市場異質性在地區收入差距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可決系數超過了0.8)。在單獨回歸模型(第四、五欄)中,刻畫政策異質性相的變量X2也具有顯著的影響(可決系數超過了0.6),但是在完整的回歸模型(第六、七欄)中不顯著。這表明政策異質性在地區結構失衡中的相對重要性較市場異質性要低得多。刻畫政府干預程度的變量X3在所有回歸模型中均不顯著。這意味單單觀察政府對經濟的介入程度的意義可能遠不如觀察政府部門專用政策這樣的政策結構特征。整個模型的可決系數將近0.9,可以說市場異質性和政策異質性確實是地區結構失衡最重要的兩股因素。
4. ARIMA 回歸結果
同樣,在時間序列數據中隨機擾動項也可能存在自相關,基本的OLS 估計可能是有偏的。我們進一步對區域經濟樣本采取ARIMA 回歸,附表7 是其回歸結果。刻畫地區要素密度異質性的變量X1的系數大小和顯著性并未發生太大的改變,市場異質性確實對地區結構失衡有著重要而穩健的影響。在單獨回歸模型(第四、五欄)中,刻畫政策異質性的變量X2的系數也顯著為正,但是有意思的是DX2的系數顯著為負,這可能意味著改革開放之后的財政政策尤其是轉移支付可能對地區結構失衡確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整個回歸模型(第六、七欄)中,與OLS 回歸結果是一致性的。
5. 區域經濟與二元經濟結構失衡成因的差異及其可能的原因討論
在結構失衡的成因上,區域經濟和二元經濟在回歸中表現出了較大的差異:首先,市場異質性的作用方向不同,二元經濟中起的是抑制作用,區域經濟中起的是誘發作用;其次,政策異質性的作用力度不同,二元經濟中政策異質性在誘發結構失衡上起到了主導作用,而在區域經濟中則相對市場異質性而言重要性較低;最后,改革開放之后,政策異質性加劇了二元經濟結構失衡,而對區域經濟結構失衡有一定的緩和作用。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二元經濟的要素密度異質性在收入差距中的重要性要比區域經濟低得多,被模型忽略了的區域經濟的集聚效應可能與市場異質性密切相關;第二,較之二元經濟而言,用財稅政策測度的政策異質性可能低估了區域經濟的政策異質性,例如對于區域經濟的特區政策而言中央政府采取的是“給政策權力而不給錢”;第三,地區轉移支付可能比城鄉轉移支付力度要大得多,從而影響了政策異質性程度。
七、經濟增長的經驗分析
(一)具有理論基礎的計量模型設定
將式(48)中的解帶入式(50)中的增長率,并進行對數線性化稍作整理可得:


(二)來自二元經濟的經驗分析
1. 變量與指標
與前面的二元經濟劃分一致,這一部分我們分析二元經濟中的總量增長。由于農業或農村部門與非農業或城市部門之間在要素密度異質性以及政府的部門政策異質性上較為突出,通過二元經濟劃分能夠揭示總量增長的結構性市場動力和結構性政策動力。表3 是構建的二元經濟指標。

表3 變量、計算公式與說明及其含義
2. 樣本構建與數據來源
與前面結構失衡的二元經濟分析中的數據口徑一致,我們可以構建相應的數據樣本。技術水平我們以全要素生產率(TFP)指數測度,相關數據來自張軍和施少華(2003)以及趙志耕和楊朝峰(2011)。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資本密度依然分別取:0.3 或0.4,0.6 或0.7。不同的取值組合生成不同的樣本。其余所有數據均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3. 回歸結果
附表8 是二元經濟樣本(以農部門為基準,α1=0.3、α2=0.6)的回歸結果。在所有的回歸模型中,刻畫技術水平的變量Z1的系數均非常顯著,這意味著技術水平始終是經濟增長穩健的動力。刻畫部門專用稅負的變量Z4的系數為正,盡管不太顯著,但是系數值相對而言特別的大。刻畫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的變量Z3的系數為負,盡管也不太顯著,但系數值也相對較大。這可能表明雖然技術水平驅動的增長是穩健的,但是來自市場異質性和部門專用政策的影響可能更大。另外,在增長模式上,改革開放前后并無顯著性的差異。同樣,在此時間序列樣本中隨機干擾項也可能存在自相關,我們進一步采取了ARIMA 回歸,附表9 是其回歸結果。整體上與OLS 回歸結果是吻合的①限于篇幅,我們沒有在文中報告以非農部門為基準構造的樣本的回歸結果。。
(三)來自區域經濟的經驗分析
1. 變量與指標
與前面的區域經濟劃分一致,這一部分我們分析區域經濟中的總量增長。與總量增長的二元結構一樣,區域結構也是重要的結構性增長內容。由于海南省缺乏改革開放之前的數據,我們將其排除在樣本之外,令n=30。變量的內容和計算方式見表4。

表4 變量、計算公式與說明及其含義
2. 數據與樣本
同樣,計算變量的值需要省市的要素密度,由于缺乏近六十年整個時間序列的要素密度數據,我們以傅曉霞和吳利學(2006)測算的省級平均資本密度作為近似。其余數據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3. 回歸結果①限于篇幅,我們只報告了資本密度最高(上海)和最低(江西)的省市為基準的樣本和回歸結果,沒有逐一報告以其他每一個省市為基準的樣本回歸結果。
附表10 是區域經濟樣本(以資本最不密集的江西為基準)的OLS 回歸結果。同二元經濟中的增長一樣,刻畫技術水平的變量Z1也是顯著的增長來源。然而,與二元經濟有所不同的是,刻畫部門專用稅負的變量Z4的系數顯著為負,DZ4的系數為正。這意味著改革開放前后部門專用稅負對增長的影響有較大的差異,改革開放之前對勞動力最密集的省市實施的部門專用稅負不利于增長,而之后卻有正向的調整。在附表11的ARIMA 回歸結果中,除了刻畫技術水平的變量Z1的系數在整體回歸模型中的發生了不顯著的改變外,其他的結果相對穩健。
4. 對增長效果擬合相對乏力的討論
在二元經濟樣本以及區域經濟樣本中,模型對結構失衡的擬合效果較好(調整可決系數均超過0.8),而模型對總量增長的擬合效果不太好(調整可決系數還均未超過0.4)。換言之,在上述經驗回歸中,“為增長而失衡”的機制生成的計量模型很好地解釋了二元經濟以及區域經濟之間的結構失衡,而對總量增長的解釋相對較差。究其原因,我們猜測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因素值得討論。其一,限于數據,本文采取的財稅政策可能不足以測度更加廣義的政府政策,盡管財稅政策是政府政策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有可能低估政策對增長的影響。例如,黃玖立等(2013)基于中國海關細分貿易數據考察了經濟特區的制度,發現憑借各種優惠和政策,除了擁有更多的平均出口之外,設立經濟特區的城市在契約密集型行業上具有比較優勢,這種制度優勢主要是沿著集約的邊際實現的。其二,過度的公共支出削弱了其正外部性迫使邊際收益出現遞減(嚴成樑和龔六堂,2009;王麒麟,2011)。當然,還有許多因素不可能在一個簡單的模型都考慮到,這也是出現上述增長解釋相對乏力的原因。
八、增長與失衡伴生關系的經驗分析
(一)計量模型設定
首先,我們設置一個似不相關方程組模型(SUR)來觀察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互不影響而只是市場異質性和政策異質性的兩個內生結果的情景:

其次,我們再設置一個聯立方程組模型(SEM)來觀察總量增長和結構失衡互相影響并且也是市場異質性和政策異質性的兩個內生結果的情景:

(二)來自二元經濟的經驗分析
由于數據來源和口徑都一樣,我們將前面的二元經濟中解釋結構失衡的樣本和解釋總量增長的樣本結合起來分析增長與失衡的伴生關系。由于兩個子樣本均有多個生成的數據樣本,也因此有多個樣本組合①限于篇幅,文中沒有報告其他樣本組合的回歸結果,盡管其他變量的影響有所不同,但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伴生關系均穩健,整體上不同的樣本組合回歸結果是穩健的。。附表12 是回歸方程組(62)對二元經濟樣本組合(1-1)的似不相關(SUR)回歸結果。方程組的似不相關估計考慮到了結構失衡方程和總量增長方程的隨機干擾項之間(由于受共同的背景因素影響)可能存在的相關性進而提高顯著性。對比前面的單方程估計,可發現顯著性以及調整可決系數并沒有發生較大的變化,整體上看市場異質性和政策異質性確實是增長與失衡強有力的共同影響因素。但是,為增長而失衡的機制對結構失衡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度,而對增長的解釋相對乏力。同前一樣,不論控制時間與否,反映市場異質性的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均顯著地抑制了結構失衡,而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卻顯著地誘發了結構失衡;技術水平依然是總量增長的穩健性增長動力,部門專用稅負和市場異質性均對增長有重要的影響。附表13 是回歸聯立方程組(63)對二元經濟樣本組合(1-1)的三階段完全信息最小二乘(3,SLS)回歸結果。其他變量與附表12 相差無幾,而結構失衡和總量增長表現出了顯著的伴生關系,且增長對失衡誘發作用相對失衡對增長的刺激作用要低得多。
(三)來自區域經濟的經驗分析
同樣,附表14 是回歸方程組(62)對區域經濟樣本組合(1-1)的似不相關(SUR)回歸結果②限于篇幅,文中沒有報告其他樣本組合的回歸結果,盡管其他變量的影響有所不同,但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伴生關系均穩健,整體上不同的樣本組合回歸結果是穩健的。。相對于單方程回歸而言,除了技術水平變量Z1的顯著性降低之外,其他變量以及模型的調整可決系數也并無大的改變。與二元經濟一樣,為增長而失衡的機制對結構失衡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度,而對增長的解釋相對乏力。附表15 是回歸聯立方程組(63)對區域經濟樣本組合(1-1)的三階段完全信息最小二乘(3,SLS)回歸結果。也與二元經濟的回歸結果一樣,區域經濟中增長與失衡表現出了顯著的伴生關系,并且失衡對增長的刺激作用高于增長與失衡的誘發作用。
九、結論性評述
耀眼的總量增長與堪憂的結構失衡相互伴生是中國六十多年來發展的一個典型特征。站在新的歷史時期,總結中國長期的發展特征背后的規律,以及反思前人對中國發展特征的總結,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意義都非同小可。本文旨在為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的伴生關系這一中國長期發展的特征事實提供一個理論分析框架:
(1) 基于中性政府理論(姚洋等,2009、2011)和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等,2012)對政府行為和經濟發展的解釋以及中國的城鄉政策、地區政策(包括特區政策)、產業政策等部門層面的特征,本文提煉出了政府部門專用性政策這一核心的概念作為解釋增長與失衡伴生關系的核心變量。
(2) 本文將寬泛的結構失衡問題聚焦于長期的直接構成經濟總量的部門之間的結構失衡,將中國非常嚴重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產業差距等問題統一定義為部門結構失衡,用常用的泰爾熵操作化了部門間的結構失衡。基于部門專用性政策的概念,拓展了Barro(1990)經典的政府公共服務內生增長AK 模型來內生解釋增長與失衡的伴生關系。在任意的n 部門要素密度異質性與政府部門專用政策異質性的一般情景設定下,我們的模型經濟存在平穩增長大道(BGP),而在BGP 大道上卻存在部門之間結構失衡的狀態。在經典的Barro 模型中,由于政府公共服務具有正外部性而不會使得邊際收益遞減,從而使得模型經濟具有AK 型的內生增長。相比于經典的Barro 模型,部門專用性政策異質性通過結構效應可以制造更高的總量增長,但是會誘發結構失衡,這個理論機制本文概括為“為增長而失衡”。
(3) 理論上講,增長與失衡便可視為政府主導經濟的收益與代價,而部門專用性政策是其政策操作工具。因此,對應的政策建議也是非常明確的:熨平傾斜性的部門專用政策是治理結構失衡的首要切入點。在具體的可操作的政策設計來講,尤其是產業政策,在設計實施力度和范圍時,需要設置有限傾斜原則。比如,為支持六位數層面的產業(當然是該產業中的企業獲得政策優惠),那么相應的補貼來源可以設定在該六位數產業所屬的五位數、四位數或兩位數產業范圍內(當然是該產業中的企業承擔政策負擔)。設置這樣的產業政策隔斷機制,可以有效避免政策優惠過度支持某些企業進入某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規避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大量出現,進而減緩結構失衡。舉例來講,為支持一個六位數層面的太陽能新能源產業,其補貼資金數額應該控制在來自四位數能源行業稅收總量的一個比例之內,而不應該過度來自其他兩位數的非能源行業。
[1] 巴蘇(Basu,K. ). 論發展的目標[A]. In:邁耶,斯蒂格利茨(主編).發展經濟學前沿:未來展望[C]. 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2] 勃蘭特,羅斯基(主編). 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C]. 方穎,趙楊等譯. 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 Chan K. W.,Henderson V. J.,Tsui K. Y. 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因素 [A]. In:勃蘭特,羅斯基(主編). 方穎,趙楊等譯. 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 [C]. 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陳斌開,林毅夫. 發展戰略、城市化與城鄉收入差距[J]. 中國社會科學,2013(4):81-102.
[5] 付才輝. 發展戰略的成本與收益——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目標、爭議與拓展的探討[J]. 南方經濟,2014(1):29-48.
[6] 付才輝. 金融干預的成本與收益:產能過剩與技術進步[J]. 當代經濟科學,2015(4):1-13.
[7] 付才輝. 市場、政府與兩極分化——收入分配的新結構經濟學[D].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工作論文,2014.
[8] 傅曉霞,吳利學. 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地區差距中的貢獻[J]. 世界經濟,2006(9):12-22.
[9] 傅 勇,張 晏. 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偏向: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 管理世界,2007(3):4-12.
[10] Heston A.,Sicular T. 中國與發展經濟學 [A]. In:勃蘭特,羅斯基(主編). 方 穎,趙 楊等譯. 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C]. 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 干春暉,鄧若谷,余典范. 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與波動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11(5):4-16.
[12] 郭凱明,張全升,龔六堂. 公共政策、經濟增長與不平等演化[J]. 經濟研究(增刊),2011(2):5-15.
[13] 賀大興,姚 洋. 社會平等、中性政府與中國經濟增長[J]. 經濟研究,2011(1):4-17.
[14] 黃玖立,吳 敏,包 群. 經濟特區、契約制度與比較優勢[J]. 管理世界,2013(11):28-38.
[15] 林毅夫,蔡 昉,李 周.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6] 林毅夫,蔡 昉,李 周. 中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地區差距分析[J]. 經濟研究,1998(6):3-10.
[17] 林毅夫,陳斌開. 發展戰略、產業結構與收入分配[J]. 經濟學(季刊),2013(4):1109-1140.
[18] 林毅夫,劉培林. 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地區收入差距[J]. 經濟研究,2003(3):19-25.
[19] 林毅夫,蘇 劍. 論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J]. 管理世界,2007(11):5-13.
[20] 林毅夫. 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1] 林毅夫. 新結構經濟學[M]. 蘇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2] 米增渝,劉霞輝,劉窮志. 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財政均衡激勵政策研究[J]. 經濟研究,2012(12):43-54.
[23] 聶輝華. 政企合謀與經濟增長:反思“中國模式”[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24] 萬廣華. 城鎮化與不均等:分析方法和中國案例[J]. 經濟研究,2013(5):62-73.
[25] 王保安.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基本特征、深層原因與對策建議[J]. 財貿經濟,2010(7):8-12.
[26] 王麒麟. 生產性公共支出、最優稅收與經濟增長[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5):21-36.
[27] 王少平,歐陽志剛. 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度量及其對經濟增長的效應[J]. 經濟研究,2007(10):44-55.
[28] 王賢彬,徐現祥. 官員主導發展的得失[J].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5):69-81.
[29] 王永欽,李 明. 理解中國的經濟奇跡:互聯合約的視角[J]. 管理世界,2008(10):5-20.
[30] 王永欽. 市場互聯性、關系型合約與經濟轉型[J]. 經濟研究,2006(6):79-90.
[31] 烏 杰(編). 中國經濟文庫[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
[32] 吳敬璉. 中國增長模式抉擇[M]. 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5.
[33] 項俊波.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測度與分析[J]. 管理世界,2008(9):1-11.
[34] 徐朝陽,林毅夫. 發展戰略與經濟增長[J]. 中國社會科學,2010(3):94-108.
[35] 鄢 萍. 資源誤配置的影響因素初探[J]. 經濟學(季刊),2012(2):489-519.
[36] 樑嚴成 ,龔六堂. 財政支出、稅收和長期經濟增長[J]. 經濟研究,2009(6):4-15.
[37] 姚 洋,鄭東雅. 重工業與經濟發展:計劃經濟時代再考察[J]. 經濟研究,2008(4):26-40.
[38] 姚 洋. 中性政府:對轉型期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解釋[J]. 經濟評論,2009(3):5-13.
[39] 于光遠(編). 中國理論經濟學史[M].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40] 袁 江,張成思. 強制性技術變遷、不平衡增長與中國經濟周期模型[J]. 經濟研究,2009(12):17-29.
[41] 張 軍,施少華. 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變動:1952-1998[J]. 世界經濟文匯,2003(2):17-24.
[42] 張 軍,周黎安(編). 為增長而競爭:中國增長的政治經濟學[M]. 上海: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3] 章上峰,許 冰. 時變生產函數與全要素生產率[J]. 經濟學(季刊),2009(2):551-568.
[44] 趙志耕,楊朝峰.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與解釋:1979—2009[J]. 財經問題研究,2011(9):3-12.
[45] Acemoglu D. Technical Change,Inequa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1):7-72.
[46] Acemoglu D.,Robinson J. 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Kuznets Curve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2):183-203.
[47] Acemoglu D.,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3):467-98.
[48] Aghion P.,Caroli E.,Garcia-Penalosa C.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Growth Theori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9,37(4):1615-60.
[49] Akerman A.,Helpman E.,Itskhoki O.,Muendler M-A,Redding S. Source of Wag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 & Proceeding,2013,103(3):214-19.
[50] Angelopoulos K.,Economides G.,Kammas P. Tax Spending Policies an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Evidence from the OECD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23(4):885-902.
[51] Bandyopadhyay D.,Basu P. What Drives the Cross-Country Growth and Inequality Correlation?[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5,38(4):1272-97.
[52] Banerjee A. V.,Moll B. Why Does Misallocation Persist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0,2(1):189-206.
[53] Barro R. J.,Xavier Sala-i-Martin. 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2,59:645-61.
[54]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S103-S125.
[55] Barro R. J.,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M]. McGraw Hill,New York(2,nd edition),2004.
[56] Boisot M.,Child J. From Fiefs to Clans and Network Capitalism:Explaining China's Emerging Economic Orde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4):600-28.
[57] Chenery H. B.,Robinson S.,Syrquin M.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58] Cowell F.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A]. In:Atkinson,A.,F. Bourguigno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 Amsterdam:North Holland,2000.
[59] Devarajan S.,Swaroop V.,Zou Heng-fu.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37:313-44.
[60] Easterly W.,Rebelo S.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417-58.
[61] Fiaschi,D.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an Endogenous Fiscal Policy Model with Taxes on Labor and Capital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5:727-46.
[62] Garcia-Penalosa C.,Turnovsky S. J. Growth,Income Inequality,and Fiscal Policy:What Are the Relevant Trade-offs [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7,39(2/3):369-94.
[63] Hsieh,Chang-Tai,Peter J. Klenow.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124(4):1403-48.
[64] Jha S. K. Fiscal Policy,Income Distribution,and Growth [R]. EDRC Report Series,No. 67,1999.
[65] Ju Jiandong,Lin Justin Yifu,Wang Yong . Industrial Dynamics,Endowmen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y Economics,2015,forthcoming.
[66] Krueger A. Comments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by Justin Lin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1,26:222-26.
[67]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1-28.
[68] Li Hongbin,Zhou Lian .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9-10):1743-62.
[69] Li S. Relation-based versus Rule-based Governance:An Explanation of the East Asian Miracle and Asian Crisi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3,11(4):651-73.
[70] Murphy K. M.,Shleifer A,Vishny R. W. Income Distribution,Market Size,and Industrializ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9,104:537-64.
[71] Olson M. Power and Prosperity: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M]. Basic Books,New York,2000.
[72] Perotti R. Political Equilibrium,Income Distribution,and Grow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755-76.
[73] Persson T.,Tabellini G.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3):600-21.
[74] Piketty T.,Zucman G. Capital is Back: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1700-2010[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4,129(3):1255-310.
[75] Qian Yingyi,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83-92.
[76] Qian Yingyi,Xu Chenggang.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993,1(2):135-70.
[77] Restuccia D.,Rogerson R. Policy Distortions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with Heterogeneous Establishments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8,11(4):707-20.
[78] Restuccia D.,Rogerson R. Mis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3,16:1-10.
[79] Scully G. W. Optimal Taxation,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Public Choice,2003,115:299-312.
[80] Song Zheng,Kjetil Storesletten,Fabrizio Zilibotti. Growing like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1,101:202-41.
[81] Stiglitz J.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2011,26:230-36.
[82] Todaro M. P. Economic Development [M]. London:Longman,1997.
[83] Turnovsky S. Fiscal Policy,Elastic Labor Supply,and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5:185-210.
[84] Turnovsky S. Optimal Tax,Debt,and Expenditure Policies in a Growing Economic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6,60:21-44.
[85] 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1,XLLX:1076-151.
[86] Zheng D.,Kuroda T. The Role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Growth: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J].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51(1):79-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