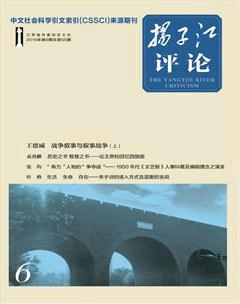生活 生命 存在
葉櫓
凡是有詩的閱讀體驗的人,都會從自己的閱讀經(jīng)歷中積累并總結(jié)出一些可以稱之為經(jīng)驗的東西。在這些經(jīng)驗中,人們會逐步地發(fā)現(xiàn),原來在許多具有各自不同的藝術(shù)品質(zhì)的詩中,它們的內(nèi)涵和底蘊是如此地迥異,而這些藝術(shù)品質(zhì)迥異的詩,往往會各自受到不同的人群的喜愛。甚至同一首詩,在不同的讀者中都會得出相距甚遠的評價和結(jié)論,所以便有了所謂“詩無達詁”的說法。
我之所以想到寫這樣一篇文字,是因為許多不同詩篇所帶來的閱讀上的愉悅、迷惘、困惑和思考讓我聯(lián)想到,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呢?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詩的現(xiàn)象本身的復雜性所導致的;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為讀者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藝術(shù)修養(yǎng)的差別而造成的。所以我試圖從這個話題中說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有關(guān)詩與生活的話題,可謂是老生常談的了。以往對文藝制作有一種很普遍的說法就是“源于生活”,不過后來為了說明“生活真實”同“藝術(shù)真實”之不同,便加上了“高于生活”作為補充和完善的理論。但是仔細想想,這“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說法,其實是不夠嚴謹?shù)摹J裁唇凶觥案哂谏睢保克遣皇呛髞硇纬伞凹佟⒋蟆⒖铡钡奈乃噭?chuàng)作現(xiàn)象的一個理論基因呢?所以我比較傾向于“源于生活”并到此為止,至于是否要“高于生活”,那得觀察一下這個“高于”的內(nèi)涵竟是什么。如果“高于”就是讓作者站在生活的高處來向讀者指引前進的方向,那就往往是靠不住的了。
在詩的創(chuàng)作中,詩人源于生活的感受而產(chǎn)生“情動于衷”的現(xiàn)象,因而賦詩填詞,這是合情合理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所以我們在大量的詩作中讀到對生活現(xiàn)象的描述,并從中體察到作者賦予這些生活現(xiàn)象的愛憎好惡。這種源于生活的詩,只要表現(xiàn)的是真情實感,一般都能得到讀者的認同和喜愛。實事求是地說,一般人之所以能夠在閱讀詩歌時獲得共鳴,大體上都是因為在生活中有感同身受的體驗,才會逐步走上熱愛詩歌乃至進而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的。所以“源于生活”既是進入詩的起步,也是日后更深層次地體察詩的奧秘的基礎(chǔ)。
正因為如此,許多表現(xiàn)日常生活現(xiàn)象和體驗的詩,特別是其中的優(yōu)秀之作,往往能夠眾口相傳而成為經(jīng)典。唐詩中的許多名篇,甚至成為我國詩歌的“敲門磚”,從牙牙學語的童年而步入青壯年甚至直到老年,有些名篇可以伴隨我們一生,是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年齡層次中讀出了它們不同的內(nèi)涵和韻味。
如果回顧我國現(xiàn)代詩的進展過程,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曾經(jīng)廣為人知的詩,其最初的扣人心弦,往往也是因為同人們的生活感受息息相關(guān),或者是在某些感情領(lǐng)域里表現(xiàn)得獨具特色的。在現(xiàn)代詩的早期生長時段中,由于著眼于對白話體的建立,受胡適“話怎么說詩就怎么寫”的影響,所以很多詩都是以說理的身份出現(xiàn)的。后來出現(xiàn)的以“新月派”為代表的聞一多、徐志摩、林徽因等人的詩,不僅注意到詩的抒情性,也同時關(guān)注到詩體的形式追求,因而受到普遍的關(guān)注。像《死水》 《再別康橋》等一些代表性詩作的出現(xiàn),把詩的情感表達同人們的日常感受聯(lián)系起來,并且具備一些諸如象征聯(lián)想之類的詩性特征,而且與人們對我國古典詩歌的閱讀方式和文化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融合與聯(lián)結(jié),這就極大地推動了人們對現(xiàn)代詩閱讀的興趣。而李金發(fā)、戴望舒、艾青、何其芳、馮至等人的相繼出現(xiàn),更是把現(xiàn)代詩同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諸多的感受聯(lián)系起來。現(xiàn)代詩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得以確立,可以說首先是因為它同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諸多感受相聯(lián)系才得到承認的。所以我對詩歌“源于生活”并表現(xiàn)生活這一基本的出發(fā)點和立足點始終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更重要的還在于,有一些表現(xiàn)日常生活感受的詩,因為其在體現(xiàn)人們生活體驗和感情狀態(tài)的真實和動人而具有很強的藝術(shù)魅力。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這樣的詩。它的藝術(shù)魅力之所以得以體現(xiàn),除了情真意切的感情而外,更得力于那些詩性語言所呈現(xiàn)和傳達的生活細節(jié)。從對大堰河的“墳?zāi)埂薄ⅰ肮示印薄ⅰ皥@地”和“石椅”的那些附加語的渲染,到對她的“含淚地去了”那諸多“人世生活的凌辱”的感喟,艾青筆下的“大堰河”以極具生活實感的形象成為一座藝術(shù)雕塑。也許是因為這樣的生活場景離我們的現(xiàn)實漸行漸遠,有的人對它的苦難內(nèi)涵有點隔膜,反而對其語言的“拖沓”表現(xiàn)出冷漠苛求。其實,詩的語言方式是存在著多種姿態(tài)的。艾青的語言不是“拖沓”而是復沓,是為了適應(yīng)其情感的復雜糾葛而有意為之的。
如果說像《大堰河——我的保姆》這樣的詩,因為它的生活內(nèi)容而使有的人感到隔膜的話,那么,在眾多表現(xiàn)當下現(xiàn)實生活的詩篇中,我們依然可以讀到不少優(yōu)秀之作。我曾經(jīng)多次提及并撰文推薦過傅天琳的《夢話》,它的全詩不長:“你睡著了你不知道/媽媽坐在身旁守候你的夢話/媽媽小時候也講夢話/但媽媽講夢話時身旁沒有媽媽//你在夢中呼喚我呼喚我/孩子你是要我和你一起到公園去/我守候你從滑梯一次次摔下/一次次摔下你一次次長高// 如果有一天你的夢中不再呼喚媽媽/而呼喚一個陌生的年輕的名字/啊那是媽媽的期待媽媽的期待/媽媽的期待是驚喜和憂傷”。這首詩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實在是它的那種集復雜感受于瞬間,同時這種復雜的感受又是真情與時代氛圍水乳交融的表現(xiàn)和傳達。詩的溫馨之情與幸福期待,在十二行詩中得到了相當完美的呈現(xiàn)。
可是由于社會進展過程中的日益復雜化的人際關(guān)系,以及某些社會機制形成并造就的隔膜和冷酷,近些年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日漸呈現(xiàn)出對這種現(xiàn)象的揭露與鞭笞的批判傾向。詩人的創(chuàng)作動機,依然是源于生活的感受而體現(xiàn)在詩的表現(xiàn)時,卻有著一種變形或虛擬的形態(tài)。像頗受關(guān)注的雷平陽的《殺狗的過程》,它所呈現(xiàn)的那種形式,看起來很生活化,其實它的場景不過是詩人心目中的“過程”而已。這首詩并不是簡單地表現(xiàn)“人不如狗”這樣一種人性與狗性的對比的。它的深層次的內(nèi)蘊,或許隱含著更為深刻的社會觀察。沒有對歷史過程和生活現(xiàn)實的悉心體察,不可能產(chǎn)生這一“殺狗的過程”的藝術(shù)構(gòu)思。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是寫生活現(xiàn)象的詩,其實表現(xiàn)的卻是隱藏在生活深處的一種機制。這是我們在讀這類詩時切切不可忽略的。
最近恰好讀到《揚子江》詩刊上王小妮的一組《致另一個世界》,她筆下的“另一個世界”其實都是我們生活在其間的“影像”或者說是“倒影”。其中《致有晚霞的黃昏》一詩,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不妨引出全詩:
天空正粗心地翻烤它的食物
胡蘿卜云變得更紅
很小的飛機穿過火線撒出大團的鹽
金子撲過來打扮玻璃
迎面過去的路人
還不知道他們的背后在流血
嘿,那就是不知道疼的苦難。
天空糊了,就眨眼的一會兒
焦了的荊棘
一條條黑刺身鉆進我心里
現(xiàn)在才發(fā)覺害怕
天已經(jīng)變臉
夜晚的布袋子就要來蒙住我的頭。
這種源于生活感受卻在自然景象中獲得靈感,并且以“變形”的意象出之的詩,如果讀者自身不具備想象力,同樣是很難進入其深層的藝術(shù)空間的。
可見寫生活現(xiàn)象的詩,不一定就是淺薄和幼稚的。關(guān)鍵在于詩人自身是否具備足夠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表現(xiàn)能力。
一般來說,從生活而進入詩的體驗和體悟,這乃是正常的規(guī)律。但是,人作為生命的主體,在對客體的體驗和體悟的過程中,必須具備一種主體的精神品質(zhì)。這種精神品質(zhì)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命意識。所以對于詩人來說,在生活過程中如何實現(xiàn)自身的生命意識的自覺性,乃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品質(zhì)。這就是我要在此文中涉及的第二個話題:生命。
生命意識之于詩,是體現(xiàn)在對自身生命的清醒認識里。在我國現(xiàn)代詩的發(fā)展進程中,由于西方意識形態(tài)和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的不斷進入,對我國傳統(tǒng)的生命觀產(chǎn)生著不容忽視的沖擊。孔老夫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入世觀念,左右著許多人的行為。人們樂于談生而忌諱談死,其實對于人的個體生命而言,如果說生是種偶然,而死則是必然。所以死亡是人生中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有人說生命意識就是死亡意識,是為了提醒人們?nèi)绾紊拼皇枪膭钊藗兿麡O地對待生命。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被我國翻譯成五言絕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雖然是意譯的成分較重,但是它把“自由”作為生命的第一要義,卻是同“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一致的。李金發(fā)有一句很著名的詩是:“生命就是死神唇邊的微笑”。他的詩化語言把生命的短暫和美麗表達得十分耐人尋味。然而我們同樣應(yīng)該看到,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詩人們對于生命的自覺認識與把握,往往顯示出復雜的感悟和內(nèi)涵。艾青寫于1937年那首《太陽》如是說:
從遠古的墓塋/從黑暗的年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震驚沉睡的山脈/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
它以難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樹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帶著狂歌奔向它去
當它來時,我聽見/冬蟄的蟲蛹轉(zhuǎn)移于地下/群眾在曠場上高聲說話/城市從遠方用電力與鋼鐵召喚它
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撕開/陳腐的靈魂/擱棄在河岸/我乃有對于人類再生之確信
這首寫于將近80年前的詩,至今讀來依然令人為之動容,深切地體驗到一種對生命覺醒的感悟和沖動。詩人對于太陽的“震驚沉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這種感受,可以說是詩人對時代脈搏涌動的心有靈犀,更是對自身生命價值實現(xiàn)的焦慮與渴望。在大動蕩的時代里詩人對生命價值的認同,體現(xiàn)在他審視自己的行為時那種迫切要求投入時代潮流的主觀愿望上。我們不能因為那個時代的遠逝而對詩人的心境產(chǎn)生隔膜。歷史上一切表現(xiàn)了詩人真誠內(nèi)心追求的詩,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魯迅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都可以說是詩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一種追求和認同。所以我們對詩人在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的生命意識和價值的表現(xiàn),始終看成是評價其詩的真正價值和品格的一種重要的標志。
然而在對生命意識和價值的認識上,不同的詩人之間卻是存在著很大差異的。任何一個詩人,當其處于特定的生存狀態(tài)時,對自身生命價值的審視是具有各自特點的。可是有一個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在追求一種永恒的東西。因為既然意識到個體生命的短暫和死亡的必然,那么,詩人借助于詩的表現(xiàn),如何能實現(xiàn)這種對永恒事物的追求呢?于是我們便讀到了大量的以對大自然中各類具有永恒性事物為寄托的詩篇。不同的詩人以多姿多彩的筆墨寫下的這些詩篇,讓諸如太陽、月亮、星星、大海、江河、高山,甚至石頭這樣一些無生命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被詩人賦予了各具生命色彩的意象。這種創(chuàng)作現(xiàn)象之得以綿延不斷地出現(xiàn)和存在,是與不同時代的詩人們對自身生命的審視和思考的歷史意識密不可分的。所謂“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存”的對人物的褒貶,“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對人的情感領(lǐng)域的追問,“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人生慨嘆;如此等等,無不隱含著詩人內(nèi)心深處對永恒事物存在的追求與叩問。
在我前引艾青的《太陽》中的詩句是:“我乃有對于人類再生之確信”,這句詩把個人對生命的感悟轉(zhuǎn)化成“對于人類再生之確信”,其實就是想從對個體生命的消失轉(zhuǎn)化成對“人類”這一集體生命的永恒實現(xiàn)。的確,只有人類的永恒存在,才會有永恒的觀念和永恒的追求。
不過當我們把目光轉(zhuǎn)向一些具體的詩歌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時,我們還是不得不對一些具體詩篇作些探討。
如果把個體生命的消失同集體人類的存在理解為一種永恒性的循環(huán),那么,就正如把一滴水放到大海中去一樣,它的消失也就是永恒的存在。有的詩人在表現(xiàn)這種生命的循環(huán)時,是以另一種方式呈現(xiàn)的。李琦的《冰雕》寫水成為“冰雕”而后又在春天時“它們會融化的”這個過程;始而因“冰雕”而“美麗”,由“柔弱”而“堅強地站立”,繼而再融化成水,但“融化也不會嘆息/畢竟有過驕傲的站立啊”。就是這樣一個過程的描述,便暗含著一種生命循環(huán)的過程的永恒性。詩人寫這首詩,也許寄托著她的勵志的意味,但是它所暗含著的意味,似乎遠超出了詩人主觀的寄托。李琦對于生命價值的關(guān)注,反而從另一個層面上揭示出生命的循環(huán)的永恒性,應(yīng)該是詩歌鑒賞中的應(yīng)有之義。然而她對于生命存在形式的把握與認識,傾向于溫馨的向往,這可能同她的生存狀態(tài)習習相關(guān)。
詩人的生存狀態(tài)對他進入生命的體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在另一類屬于落難型詩人的詩作中,看到的則是頗為不同的風景。在牛漢、曾卓、昌耀這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詩人身上,我們能夠讀出可以稱之為經(jīng)歷了煉獄之后而醒悟和提升的生命價值觀。牛漢的《遠去的帆影》一詩,極其真切地寫出了親歷其境和飽受煎熬的生存狀態(tài),但是他在詩前特別地寫了一句類似“按語”的話:“這個美妙的題目,是立在岸上的人擬的”。他是試圖以此來說明處在不同的生存狀態(tài)中的人,其內(nèi)心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當一些人在經(jīng)受著深重的苦難時,另一些人卻把它當成風景來欣賞。因此他們的生活體驗是各自不同的,而對生命價值的認同也存在很多差異。而在曾卓身上,我們都會記得他那首《懸崖邊上的樹》,特別是“他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這兩句詩,我認為其體現(xiàn)的內(nèi)涵和塑型,實在是可以成為經(jīng)典性“詩眼”的。昌耀寫過一首《紫金冠》,似乎不太為人道及。我個人認為這是他的經(jīng)典之作:
我不能描摹出的一種完美是紫金冠。
我喜悅。如果有神啟而我不假思索道出的
正是紫金冠。我行走在狼荒之地的第七天
仆臥津渡而首先看到的希望之星是紫金冠。
當熱夜以漫長的痙攣觸殺我九歲的生命力
我在昏熱中向壁承飲到的那股沁涼是紫金冠。
當白晝透出花環(huán)。當不戰(zhàn)而勝,與劍柄垂直
而婀娜相交的月桂投影正是不凋的紫金冠。
我不學而能的人性覺醒是紫金冠。
我無慮被人劫掠的秘藏只有紫金冠。
不可窮盡的高峻或冷寂唯有紫金冠。
作為象征物的“紫金冠”,是有形中的無形,無形中的有形。但是它卻是昌耀的生命意識和生命價值的追求中始終形影相伴的精神支撐。理解了他筆下的“紫金冠”,就能夠進入冒耀的內(nèi)心深處和精神領(lǐng)域。
什么是詩人的生命意識,什么是詩人的生命價值判斷?我們或許無法以一種簡單的方式給以回答,但是我們卻可以在詩人眾多的詩篇閱讀和感受中,以精神浸潤和靈魂陶冶的方式獲得啟悟。我們正是從不同的詩人筆下呈現(xiàn)的生命形態(tài)和生存狀態(tài)中,逐漸地認識他們的生命價值的。
當歷史轉(zhuǎn)入新的運行軌道之后,我們從所謂“朦朧詩”出現(xiàn)以后的詩人身上,似乎窺視到了另一種覺醒。當北島宣告“我不相信”并說“在沒有英雄的時代,我只想做一個人”時,他似乎是在“降低”詩人的生命價值觀。其后出現(xiàn)的后一代人,更是連北島的“人”也被認為是“英雄”。這種對于所謂“崇高性”的顛覆,就思潮的角度而言,韓東的《有關(guān)大雁塔》可以說是極具代表性的一首詩。對于這種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降低詩的品格的現(xiàn)象,其實質(zhì)卻是隱含著詩歌觀念的改變的行為。
如果我們仔細回顧現(xiàn)代詩的發(fā)展過程,可以隱約地疏理出一種現(xiàn)象,就是每當詩人對于自我的生命價值的認同趨向于所謂“大我”時,他們的詩卻往往會喪失個性,而當他們從“小我”出發(fā),寫出了獨特的內(nèi)心感受時,反而會從個性的表現(xiàn)中獲得一種時代感。北島從“迷途”到“回答”,寫出了個人的迷惘和覺醒,而被稱為“第三代”的詩人們,則是從“低處”著眼以表達卑微欲望為旗幟,實質(zhì)卻是對自身生命價值的一種認同。當他們要“pass北島”時,其實是想確立更為“平民化”的生命價值觀。這種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在降低詩的品格的行為,隱含的卻是筆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的清醒意識。我們曾經(jīng)習以為常地認定“抒豪情,寄壯志”的表現(xiàn)方式,如今在一些年輕人的筆下已經(jīng)很難再現(xiàn)。直到前些年以“下半身”為標榜的詩歌出現(xiàn),不免會使一些人產(chǎn)生困惑。難道詩人的生命意識和價值觀,就是一句“下半身”所能囊括的?其實,“下半身”亦如當年的“pass北島”一樣,只是一種策略性的口號,爭取到自己一份社會的承認才是他們的目的。事實上,這些不斷出現(xiàn)的青年詩人群體是在不斷地通過他們的生活體驗來表達和表現(xiàn)他們的生命意識和價值認同的。
詩歌創(chuàng)作中對生命意識和價值的認同,并不僅是只有“抒豪情,寄壯志”的氣宇軒昂,它同時還可以抒寫多種復雜的人生體驗。這就像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可以寫英雄人物,也可以寫凡人小事一樣。說句極端一點的話,一個“阿Q”在藝術(shù)價值上的意義,是要遠勝于若干“高大泉”式的人物的。所以從詩的表現(xiàn)和表達上說,我欣賞像韓東的《有關(guān)大雁塔》,欣賞伊沙的《結(jié)結(jié)巴巴》,因為它們真實地表現(xiàn)和表達了普通人的真實感受和生存狀態(tài)。從根本上說,詩并不是充當社會學意義上的幫助人們認識現(xiàn)實的科學,它只是表現(xiàn)和表達人的內(nèi)心深處一種對生命的真實而深刻的感受。人們之所以寫作和閱讀詩歌,是為了從人的感受和生命意識中,更深刻地理解人作為“存在者”而進入的“存在感”。所以詩的存在感應(yīng)該是作為最高的藝術(shù)品質(zhì)而獲得認同的。
我國的古代詩歌中一些眾口相傳的經(jīng)典之作,諸如屈原的《天問》、曹操的《觀滄海》、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杜甫的《望岳》、王之渙的《登鸛雀樓》,以及蘇軾的《題西林壁》。這些詩的一個共同點都是詩人在面對大自然時發(fā)出的感慨。詩人們在時空流逝中感悟到的人生短暫而又永恒的生命意識,使他們的詩得以流傳,是因為這種生命意識中的存在感,不但使后人警悟,更加深了后人的敏悟和感受的能力。這樣的詩歌呈現(xiàn)出的種種心境與大自然環(huán)境的天人合一的體驗,正是人類在與大自然共生共存中所產(chǎn)生的意志與思想共同飛翔的境界。正是基于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我國歷代的詩人們才寫下了如此眾多的具有中華民族的生存意志和觀念的優(yōu)秀詩篇。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典詩歌才具有了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民族特色。
然而在五四以后的現(xiàn)代詩,由于處在一種文體大轉(zhuǎn)變大改革的過程中,詩的“實用性”與“革命性”所面臨的任務(wù),似乎遠大于詩的“本體性”和“藝術(shù)性”的追求,從而使“詩性”的本質(zhì)和內(nèi)在要求受到了較為嚴重的輕視和傷害。作為一種歷史現(xiàn)象和發(fā)展過程,這應(yīng)當是難以避免也可以理解的。可是在短短的一百年中,我們?nèi)匀怀霈F(xiàn)了一些可以稱之為偉大或優(yōu)秀的詩人。這是絕對不應(yīng)被忽視或輕視的。
當我們考察一個詩人的“存在感”時,不應(yīng)當忽視他所生存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huán)境。像艾青的“若火輪飛旋于沙丘之上/太陽向我滾來”這種對于光明追求的動感;昌耀在《斯人》中所呈現(xiàn)的融宇宙于一體的瞬間感受;洛夫在《漂木》一詩中所傳達出的那種靈魂安置的動蕩不安的生命感受。這一切都表明,處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存環(huán)境之中,詩人們的存在感是呈現(xiàn)著多種內(nèi)涵和多重層面的。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們從眾多涌現(xiàn)出來的青年詩人中,可以隱約地感受到,盡管他們的多種藝術(shù)追求和表現(xiàn)能力還存在著一些爭議和質(zhì)疑,但是從總的趨勢和傾向看,他們的藝術(shù)追求的自覺性和對于生命主體意識的張揚,都是表現(xiàn)出強大的生命力的。當北島、舒婷這一代詩人的身影日漸淡出而作為一種象征在歷史背景中存在著時,另外一些更為年青和具有影響力的詩人的出現(xiàn),乃是歷史進程中的應(yīng)有之義。
一般來說,我們判斷一個詩人的藝術(shù)價值,不會以年齡或出現(xiàn)的早遲為尺度和標準,有青年人寫出衰老的詩,也有老年人寫出青春的詩。不過在我看來,持續(xù)性的寫作而且藝術(shù)質(zhì)量能保持在較好的水平上,才會是有藝術(shù)生命力的詩人。在當下的詩壇,我比較看重的是于堅、西川和王小妮。我覺得他們的詩,使我讀出了一種時代的氛圍,感受到一種歷史進程中的心態(tài),作為人的較為復雜的生存感受。于堅的天人合一的處處有詩的感知;西川的仰望或俯視;王小妮的冷峻和深度,這些屬于詩的內(nèi)在本質(zhì)的東西,在不同程度上都在他們的詩中得到了體現(xiàn)。當我們的后代在閱讀大量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時,他們是否能從這些詩中讀出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們的感情狀態(tài)、生存感受以及這個時代的社會氛圍,將是評價這些詩作的基本標準。
我說過,詩人作為時代和社會的良知,他們的任務(wù)也許不是從理性上引導人們?nèi)绾稳フJ識社會和歷史,而是從內(nèi)心的深層次上表現(xiàn)和表達一種詩性的感受。至于這種感受在何種程度上能夠獲得人們的認同,那就不是任何所謂權(quán)威人物所決定的了。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程中,政治權(quán)威也許是一定歷史時期中左右局勢的決定性力量,但是它們的勢力不會持久,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為最好的說明。然而只有作為普通人的詩性感受,卻會是隨著人類命運的進程而持續(xù)存在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它的清醒意識,同那些力圖制造長生不老藥的封建帝王相比,何者睿智,何者猥瑣?所以我相信詩性永存,詩的存在感才是真正的睿智。
我在此文中把詩分成生活、生命、存在三個層面來加以分析,并不是簡單地給它們劃分等級,而只是從詩的表現(xiàn)方式上給以區(qū)分。在我看來,詩只有好詩和差詩的區(qū)別。寫生活層面的詩,只要寫得優(yōu)美動人,照樣可以眾口相傳,寫生命意識和價值呈現(xiàn)的詩,固然會引發(fā)人們一些較深的思考,提高人們對生命的自覺意識,但同樣以寫得優(yōu)美動人為前提,那些只顧從哲學或哲理的深度上闡述生命意義和價值的空泛議論,其實是同詩風馬牛不相及的。關(guān)于寫存在感的詩,我以為不宜在這上面過于專注。這是一種自然生成的過程。人的生活閱歷、學識睿智、生存體驗,到達了一種境界,它有時會自然而然地“得來全不費功夫”。當然,這得有一個前提,就是你需是一個生活中的有心人。渾渾噩噩者是絕不可能進入此境界的。
寫到這里,不禁想到了眾所周知的卞之琳的《斷章》。這首只有四行的“絕句”,可以肯定會成為現(xiàn)代詩的不朽之作。它可以說是涵蓋了我所說的三個層面的詩篇。從生活的層面閱讀它,可以是一幅生動鮮活的生活場景,也可以是優(yōu)美的愛情畫面;從生命意識的層面閱讀它,就是如李健吾所說的,它暗示著一種生命陷于“裝飾”的悲哀。而在存在的哲學意義上,就是卞之琳自己說的,他是要表達一種“相對性”的存在。一首只有短短四行的詩,居然可以讀出這么多的意味來,這不是現(xiàn)代詩的一種奇跡嗎?
如果我們現(xiàn)代詩,能夠一直朝著這種方向努力,我們還有必要為它的前途和“合法性”擔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