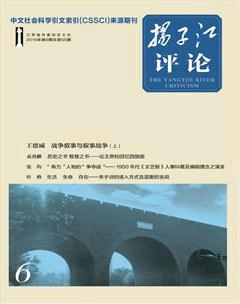路內長篇小說《慈悲》讀札
徐勇
就表現內容而言,路內的最新長篇《慈悲》(2015)與《花街往事》有一定的重合,都是從“文革”前后的歷史語境出發,以表現數十年來社會歷史的變遷,但兩部小說的思路及其訴求明顯不同。如果說《花街往事》帶有追溯、重述和反思歷史的傾向的話,那么《慈悲》則一變而對歷史和現實處境中作為個體的“人”的生存命題的關注。在這里,從歷史到個人,顯示出路內創作演變的軌跡,如若聯系作者的其他創作來看,這一演變更加明顯,因而也就更具癥候性。
一
雖然說小說采取的是回憶式的重溯,但這一敘述上的起點卻非小說故事的起點。兩者間的差異,是進入這部作品的很好角度。對于敘事文學而言,選擇哪個時間點作為起點看似隨意,實則暗含玄機。幾十年的歷史(20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至新世紀初),小說選取的是這中間的一個點并以此展開敘述。這一點即主人公水生進工廠的那一年(“文革”期間)。小說沒有從水生隨父母災年逃難那一年寫起,相反,它是把這一段經歷作為記憶植入水生的此后人生,以此呈現歷史同現實間的種種分合斷續關系。就《慈悲》而言,從中間開始敘述的好處是,可以采取雙線結構同時展開,一方面是回敘,一方面是故事沿著敘述的起點向前發展,發展到最后,是故事進入到90年代以來的現在時空,而時斷時續的回敘也在這時結束,雙線合二為一。這與《花街往事》有點不同。《花街往事》采取的是單一的線索,從歷史的某一點(1966年)出發,沿這一軌跡向前發展。雖然說雙線結構比單線結構稍顯復雜,但并不能因此而斷言前者就比后者高明。正如杰姆遜所言,形式背后有其某種意識形態訴求存在,路內的這一雙線結構,應有其自覺不自覺的意圖隱現其中;從這個角度看,雙線結構毋寧說也就是一種對話結構,其所彰顯的應是歷史與現實間的對話、辯駁及其最終的和解,所謂的“慈悲”之名即帶有此一含義。也就是說,小說的敘事雖然始自苦難(即故事的起點,而非敘述的起點),最終導向的卻是對苦難歷史的救贖與和解。但作者/敘述者又似乎充滿困惑與矛盾,歷史和苦難本身雖可以原諒,但對于歷史中的某些個體——暴力的施與者——惡的一面,卻又難以釋懷。小說最后,水生仍難對惡人宿小東釋懷即是明證。這與《花街往事》中對個體的原諒和對歷史的批判性反思形成鮮明對照。
可以肯定,這一對照所顯現出來的,某種程度上是作者/敘述者對待個人與世界(現實和歷史)看法的改變。個人與世界的關系,一直以來是路內所思考并試圖加以表現的主題。個人在世界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位置?如何生存并安置自己?生活的意義何在?等等之類的問題,都在路內的小說創作和路小路這一核心形象中顯現出來。作為“70后”的路內,他做不到像“80后”作家(如七堇年、笛安和楊則緯)那樣從兩者(個人與世界)割裂的角度表現個體的悲歡離合,在那種情況下,歷史的“上下文”一旦被剝離或淡化,個人的苦難就會被放大;同樣,他也做不到像他的前輩作家那樣固執甚或偏執。“60后”作家(如蘇童)可以表現出理想破滅后的解構的持續熱情,“50后”甚或更早出生的作家(如丁玲,如賈平凹),又會表現悲壯而頑強的退守的固執。從這點而言,“70后”一代具有過渡性質,他們有著殘余的歷史感,但卻無堅定的歷史意識,可以說,正是這點,決定了路內小說的雙重性征。路內是一個代際意識較為明顯的作家,他的小說有持續的表現歷史的沖動,但又無法做到對歷史進程的一以貫之的認同。這種矛盾某種程度上造成了他的小說在對待個人與世界關系時的猶豫不決和進退失據。
具言之,路內始終是從個人與世界的互文性的角度來安排、表現主人公們的人生的,他不可能真正做到把兩者割裂開來。世界或者說時代語境仍是理解小說《慈悲》的重要“上下文”。與《花街往事》不同的是,在《慈悲》這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工人階級的革命豪情,也感受不到他們當家做主的自信。他們既不關心革命,也不關心國家的前途,他們關心的只是個人的日常生活,但歷史卻以悖論的形式決定著他們的命運:他們會因生活作風問題(男女通奸)而被審判,他們隨腳踢踢閥門也會以破壞生產罪之名而被關進牢房。路內當然知道,在當年那種風云激蕩的年代,任何個人都不可能做到置身事外,在這部小說中,他把個人從時代的主題中剝離出來,實則是為了凸顯個人的渺小和無助,以及被大時代的邏輯所忽視的個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說,這也正是小說的意圖所在。所謂革命、改革之類的宏大敘事對主人公而言是沒有意義的,生存本身才真正構成他們日常生活的本質。而事實上,只有當個人從時代的宏大敘事中剝離出來,生存本身才顯示出其堅硬的內核與固有價值。換言之,這里的生存,雖與革命等宏大敘事密不可分,但其指向的卻并不是對歷史的反思和批判,而毋寧說僅僅只是人的生存處境。
因此,同樣是表現個人的無能為力,這種無能為力在《慈悲》和《花街往事》兩部小說中其內涵是截然不同的。在《花街往事》中,戴城的工人們在“文革”的武斗中一個個慷慨赴死,并非因為什么豪情滿懷抑或壯志凌云,而只是不由自主,他們都是被歷史的潮流裹挾而失去了自己,小說通過表現他們在時代巨變下的無能為力,只是為了表明個人被歷史綁架下的無意識而往往充當了革命邏輯的符號式存在。相比之下,《慈悲》中的工人雖一個個有著自己的主體意識(這都是些有個性的人),但在面對人生苦難時仍然束手無策。這就是作為個體的“人”不可掙脫的宿命,其雖某種程度上同“革命”(繼續革命)糾纏一起,但更多是自然(非人力)與人力之間永恒矛盾的反映:個人并不總能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樣來看,兩部小說中的“惡”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質。《花街往事》中個人只是符號性的存在,個人的“惡”并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有問題的只是歷史,而不是個人,這也是作者為什么能原諒其主人公的原因所在。相反,《慈悲》中的這一“惡”卻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本體論(是一種宿命)意義。人既不能抗拒生而苦難這一永恒的宿命,便只能屈服,正所謂“放下執念”。但如果像宿小東那樣,他的“惡”與歷史無關而僅指涉著人性的陰暗面時,便不可原諒了。正是這點,使得小說主人公水生(包括敘述者)一直耿耿于懷,難以真正放下。
二
這里需要看到,這樣一種個人的不由自主和不能自主,并不是作者/敘述者自己一代人的歷史處境,它所表現的主要是父輩一代的生活狀況。就此而論,小說也有別于作者此前的大多數創作。路內一直以來熱衷于表現自己“70后”一代的成長/反成長歷程,這在他的“追隨三部曲”和《云中人》都有集中呈現。對于這樣一種傾向,如若聯系《花街往事》能更清楚看到其來源和演變。在《花街往事》中,作者把“70后”一代的成長置于父輩一代“革命”經歷的背景下展開,某種程度是想告訴讀者,子一代的逆向成長(即反成長)歸根結底其實是父一代對革命熱情的無謂耗盡的結果,換言之,是父輩的革命熱情的耗費導致了子一代的虛無、失落和失重。從這里可以看到,路內其實是把自己一代人的成長置于歷時或歷史的“上下文”中展開的;對他而言,歷史始終是一個繞不開,也不可能繞開的遺產兼債務。因此,在他那里,寫現實其實為了反思歷史,同樣,寫歷史也是在表現現實:歷史與現實之間具有某種互文性。這樣來看《慈悲》,就會發現作者的變與不變的內在關聯來。
首先,就像前面指出的,這一變表現在,這是一部著力表現父輩一代的小說,但這種表現卻又是置于同革命現代性的邏輯相分離的框架下展開。《花街往事》的前半部寫的也是父輩一代的“文革”經歷,但在那里,這一經歷是同繼續革命等時代主題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慈悲》卻有意淡化這一歷史語境,可以說,它之淡化語境,其實是為了凸顯歷史語境下帶有普遍性的人生苦難。這與葉彌在《風流圖卷》中刻意凸顯革命邏輯下的個人之生動活潑有異曲同工之處,不同的是,在葉彌那里,作者凸顯的是個人的主動性,至于其所受到的束縛甚或苦難則被淡化與改寫,路內則不同。他之遠離革命邏輯的目的似在于凸顯個人在歷史與現實中的渺小與不能自主(被動);歷史自有其潛在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內在邏輯和異化的力量,這時再去要父輩為歷史負責似已無太大意義,至此,不難看出作者表現出來的同歷史和解的訴求。其次,這是對新時期以來傷痕、反思等苦難敘事的揚棄。新時期以來的傷痕書寫,其主人公多傾向于知識分子或老干部,很少以工人的身份出現,即使有(如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也是放在革命或改革的框架下表現,工人的傷痕與他們的“革命”經歷(“文革”中的“革命”表現)密不可分。路內的《慈悲》則相反。他努力把工人從“革命”(繼續革命)的邏輯中解放出來,而表現存在于他們身上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存困境。就此而論,他的這一小說可以算是重寫了“革命”年代工人階級的歷史處境:他們雖根正苗紅,作為領導階級,但卻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雖任勞任怨,卻難以維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工人階級的身份并不能改變他們的渺小與微末的人生宿命,更不用說特定歷史語境中備受打壓排擠的知識階層,從這個層面看,路內通過對特定年代工人階級的苦難書寫,其實是強化了人類所面臨的普遍困境。
對于中國當代很多作家而言,工業領域并非他們熟悉且擅長,他們的工業題材小說要么被拔高、被抽象(如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鄧剛的《陣痛》),要么被寓言化而成為底層的化身,像曹征路的《問蒼茫》。路內與他們都不同。路內是把工人當做一個個“個體”來寫的。“去革命化”的語境,使工人們的日常生活被放大,就此而論,他與劉慶邦比較接近。都是作家兼工人出身,都是表現工人——一個是化工廠工人,一個是煤礦工人——的現實日常,但他們的作品又明顯不同。劉慶邦的小說雖然融合了他的工人經歷,但他很少寫出工人兼知識分子的人物形象,農村高中畢業生宋長玉(《紅煤》)雖有過短暫的煤礦工人的經歷,但他更多是作為于連式的野心家出現,他身上的知識分子氣息并不重。路內則不同。他的小說中,知識分子兼工人的形象比較突出,《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里》和《慈悲》等等都是以技工(技術工人)作為主人公。技工的形象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建國后常見的工業題材小說,在彼時的工業題材小說中,技工是作為工人階級的陪襯形象出現的,他們的尷尬命運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他們的雙重身份:只有通過向工人的無條件的靠攏才能顯示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價值。換言之,在當時的小說中,技工是不能有自己的獨立的意識的,他們只能作為革命的符號存在。路內的小說中,技工則常以主人公的形象出現。技工的形象有一個特點,他在某種條件下(比如在工廠里)既是知識分子又是工人,因而他們的命運某種程度上就代表或象征了知識分子和工人在不同時代的命運變遷升降來,從這個角度看,技工這一核心形象其實也是作者看待世界、人生的視角和方法。《慈悲》中亦是如此。
三
對于《追隨她的旅程》和《天使墜落在哪里》來說,它們的年輕主人公們是因為不好好讀書,考不上大學而被放逐到中專等職業學校(如化工技校),畢業而成了工人。就他們人生軌跡的思想背景來看,他們的這一命運變遷,顯然帶有時代的標記在內,小說中多次提到90年代即是明證。《追隨她的旅程》中有過多次提到1991年夏天,這一年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主人公18歲了,18歲標志著主人公的成長完成(即成年),但同時也是主人公逆向成長、頹廢向下的起點。在路內的年輕主人公們身上,理想目標的失落、同社會規范及其價值觀的分裂,與他們不愿好好學習而酗酒、打架、早戀之間,構成互為前提和結果的關系,考不上大學,而又要進入社會,職業學校就成為他們人生的過渡和無奈選擇。可見,他們從高中學生到成為技工的過程,其實也就是宏大敘事的失效和解體的過程。小說以他的主人公成為技工的過程表達了一代“70后”針對宏大敘事的態度。
雖然說路內的小說中,工廠和工人的描寫極富現實現場感,但對他而言,表現工人的經驗卻不是最為首要的任務,他的目標在于借知識分子而兼工人的雙重身份及其境遇來表象現實和歷史。對于大多數工人而言,慣性與惰性中的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內在邏輯,就像劉慶邦的《黑莊稼》和《黑白男女》那樣,純粹的知識分子又會顯得似乎悲天憫人形而上學,知識分子而兼工人則不同。他們既是工人,又是知識分子,這一雙重身份決定了他們也常動用自己的腦子,他們也有自己的意識和人生信條,他們是思考的工人;這一雙重身份使得路內的主人公們極富象征意味。以“追隨三部曲”為例,路內把他的主人公的人生成長置于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下展開,這一社會轉型和理想主義的失落使得他的主人公們不知道如何思考怎樣生活了。他們沒有目標,而時代也似乎不需要他們有自己的意識,于是乎就一個個變得無所適從起來。可以說,路內小說中主人公們(路小路)的失落與失重是與他們的雙重身份息息相關的。他們不可能做到像一般的工人那樣渾渾噩噩靠慣性和習慣生活,但又不知道應該追求什么,且又不甘于平庸和瑣碎,故而便顯得與時代社會格格不入且背道而馳。不難看出,在這些小說中,作者是以技工的雙重身份介入到對歷史的批判和反思中去的。
《慈悲》則有所不同。水生成為技工雖很偶然,但他作為技工的命運卻是被歷史決定著的。技工出身對于主人公水生而言,既不需要承擔“革命”(繼續革命)的重任,也并不必然意味著要去思考或批判,而毋寧說是聯系著他人生境遇的多變:他的大半生的人生經歷都與技工這一雙重身份有關。在“文革”期間,他被分配到工廠車間當工人(技工的身份決定了他很難被重用),“文革”結束后因為國家的知識分子政策而當了技術員(所謂的工程師),境遇和地位有很大提高,那是他的黃金時代;90年代后期在國企改革的大潮中為避免下崗而又不得已重做了一線工人,此后,他又憑借熟練的操作技術和設計水平“下海”并在市場經濟的邏輯中致富。比較《慈悲》和“追隨三部曲”可以看出,對于水生和他的后輩們而言,技工的身份其意義是截然不同的。在《慈悲》中,作者借水生這一形象,毋寧說表達了一種放棄思考的訴求。他并不是不想讓他的主人公思考,而只是表明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活著比追求意義來得更重要而切實際得多。他們既然被牽制著前行而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又何來余裕或必要去思考個人在歷史中的位置?事實上,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生活或許才是最最重要的命題。這就像余華的《活著》,都是一種大徹悟。所不同的是,對于余華的主人公而言,活著是對生死的參透和死亡的淡然,而對路內的主人公水生而言,活著則同時是一種對思考的放棄和對苦難的和解。從這個角度看,技工這一雙重身份在《慈悲》中就意味著一種拒絕、抗拒與重寫。此前的反成長寫作令作者也令他的主人公們太過疲憊,他們無所適從,而又渾渾噩噩,但如果不去思考不去追求,轉而直面生活本身,就會發現,生活本身的堅硬和痛感比所謂意義的追求更能顯示出其存在的價值,在這一情況下,再去“追隨”或尋求似已無足輕重不值為意了。
在小說中,這一使得意義的追求變得失效的是饑餓這一苦難敘事。小說從“文革”起筆,本可以不寫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饑荒,其之所以念念不忘,無非是想表明,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饑餓及其有關饑餓的記憶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的重要位置。小說主人公水生的父母死于那一自然災害,他的師傅曾為申請困難補助而向車間主任下跪,水生的表哥土根因為家庭困難而“賣”女兒,等等,小說正是以這些作為敘事的軸心來貫穿始終。就《慈悲》的敘事而論,這一苦難既非理想主義失落后令人窒息的日常之苦悶和艱難(如新寫實),也不是全球化時代被放大的底層苦難(如蟻族、蝸居之類),更不指向針對苦難的精神超越(如傷痕反思敘事背后,總有一個光明的前景與之遙遙對應),其指涉的毋寧說是生活本身所可能內含的苦難宿命。小說結尾水生與弟弟云生間的對話讓人深思。水生對宿小東的東順假廟耿耿于懷,弟弟說“人生的苦,我嘗夠了”,“真廟假廟,都是一種虛妄”,重要的是“虔誠和幸福是真的”,所以,他提出“勘破生死,放下執念”。“執念”是什么?無非就是真假是非的辨認,和對所謂價值觀和倫理觀的維護。小說最后以佛教推崇的徹悟與慈悲來對待生之苦,即所謂的“放下執念”。但這并不意味著,小說作者/敘述者要去否定是非曲直,而只是表明,在生之苦的面前,以一顆虔誠之心去追求內心的平靜和淡泊似乎才更重要。在這當中顯現出來的,是一種新的歷史觀與現實觀和人生觀的耦合。革命或改革等宏大敘事如果不能滿足老百姓的生活生存的需要,其意義和價值就很可疑。同樣,意義追求或理想目標,如果脫離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也同樣沒有價值。從這點不難看出作者的通透和務實來。既然想不出出路(《追隨三部曲》和《云中人》),也無所謂理想目標,那就去生活吧。而事實上,對于大多數人而言,生活本身才似乎是最大的真理。只是沒有想到,年齡還不算太大的路內竟然有了如此徹悟,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想必讀者諸君也難以作出決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