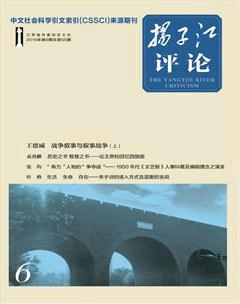從紅色理想到血色浪漫
王曉漁
楊沫和老鬼,這對文學界的“母與子”分別以《青春之歌》a和《血色黃昏》b而聞名。他們以“自敘傳”的方式,描寫了兩代“知識青年”林道靜和林胡c長大成人的過程。“成人”不僅是生理上的脫胎換骨(“脫胎換骨”一詞后來也被賦予精神含義),更是精神上的洗心革面。楊沫筆下的林道靜是“一二·九”一代,老鬼筆下的林胡是“文革”一代,兩代人相隔近30年,他們的成長經歷卻有同構之處。
在老鬼的《母親楊沫》里,楊沫的成長是一個“尋父”的過程。老鬼稱“楊沫小時像個孤兒”,“孤兒”是革命青年普遍擁有的身份,并不等同于父母雙亡,主要指精神上的迷失狀態。“一二·九”一代面臨“國破”和“家亡”的雙重孤兒境遇,這激發了他們尋找精神父親的需求。精神父親和紅色理想是重合的,最終的結局是“孤兒”向兩者同時“獻身”。在楊沫的《青春之歌》里,“尋父”和“尋夫”互相重疊,從“詩人兼騎士”的余永澤到共產黨人盧嘉川,林道靜不僅在選擇自己的丈夫,也在選擇精神父親。老鬼的《血色黃昏》講述了一個知青的“戀母”過程。他出于紅色理想的誘惑,自愿扎根邊遠地區,但在血色浪漫的殘酷現實面前,紅色理想的位置最終被女神取代,這個女神有現實的原型,但是他對女神的追求并不受原型的影響,即使那個原型對他保持沉默,他依然對女神保持著永遠的單相思。
母與子,一個“尋父”、一個“戀母”。但兩者的境遇相反,林道靜最終與精神父親生活在一起,女神卻離開了林胡。老鬼對女神的態度,也是對紅色理想的態度。兒子比母親更具反思性,然而這種反思也是有限的,其中的自我批判沒有擺脫“訴苦”的邏輯。
在路上
清晨,一列從北平向東開行的平沈通車,正馳行在廣闊、碧綠的原野上。茂密的莊稼,明亮的小河,黃色的泥屋,矗立的電桿……全閃電似的在憑倚車窗的乘客眼前閃了過去。
……
車到北戴河,女學生一個人提著她那堆樂器——實在的,她的行李,除了樂器,便沒有什么了——下了火車。留在車上的旅客們,還用著驚異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臺。
——《青春之歌》
1968年11月底。
從張家口下了火車,我們沿著一望無際的公路向北徒步行進。自大串聯后,養成了扒車的習慣,能蹭就蹭,不能蹭就步行,反正這是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大方向絕對正確,自信憑我們的本事,早晚能截個車。
——《血色黃昏》
“成長小說”的常規步驟是第一步“娜拉出走”,第二步“在路上”。《青春之歌》和《血色浪漫》的開篇,都以“在路上”為開端,但是林道靜和林胡出走的原因不盡相同。林道靜不是孤兒,勝似孤兒,她的母親是一個童養媳,“丈夫”尚未成年就死去,林道靜是母親被城里地主強奸的果實。從血緣上說,林道靜是個“混血兒”(也會被稱作“雜種”),混合了鄉村和城市、貧農和地主的血脈。在成長過程中,“混血兒”充滿內在的緊張和沖突,要比“根正苗紅者”更具戲劇性。因為家庭逼婚,林道靜獨自乘上火車。這次出走一方面是“逃婚”,另一方面也開啟了“尋父”/“尋夫”的歷程。
林胡出走的時候父母正在受到沖擊,父親有叛徒嫌疑,母親可能是假黨員。與林道靜被迫出走、此后在路上遭遇紅色理想不同,林胡的出走具有一種主動性,他是因為擁有了紅色理想才選擇在路上。出身從革命家庭變成“牛鬼蛇神的子弟”,林胡“決心和父母決裂,投身世界革命”,正是為了在革命的煉丹爐里純凈自己的血緣。所以,林胡對自己有一個總結,“我是反血統論的。但在思想深處又有血統論的思想。”“反血統論”,是因為他被視為“牛鬼蛇神的子弟”;“有血統論的思想”,因為他是革命家庭出身。這是一種辯證法,預設兩種相反的可能,然后根據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解釋。
林道靜在“被看”的目光下現身,讀者先是通過旅客的眼睛觀看林道靜:“這個樸素、孤單的美麗少女,立刻引起了車上旅客們的注意,尤其男子們開始了交頭接耳的議論。”但楊沫對旅客的視角又是不以為然的,漫畫式地描述著火車上的洋學生和胖商人。林道靜走下火車,終于擺脫了旅客的視角,這時讀者開始和楊沫的目光重合:“車到北戴河,女學生一個人提著她那堆樂器——實在的,她的行李,除了樂器,便沒有什么了——下了火車。留在車上的旅客們,還用著驚異的惋惜的眼色目送她走出了站臺。”
《青春之歌》使用了“全知全能”的敘事方式,楊沫仿佛擁有“第三只眼睛”,既能跟隨獨行的林道靜,又能深入她的內心。在開篇的短短幾百字內,讀者就經歷一次視角轉換,這也是對讀者的規訓,提醒他們“成長”是一種自我否定的過程,也提醒他們“第三只眼睛”的權威性。林道靜此行是為了尋找表哥,一路基本順利,只是最后撲空,表哥已經遷往他處,目標明確的出走迷失了方向。此后經歷的種種危險,都是目標產生變故之后的連鎖反應。林道靜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對終極目標的選擇,余永澤和盧嘉川象征著不同的方向,一旦方向確立林道靜將義無反顧地“獻身”。
終極目標對林胡來說不是問題,“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是他的基本路線,也是當時的惟一道路。林胡和朋友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正是由于目標明確,林胡才會對溫順的牧主貢哥勒進行階級斗爭。但是,當他把牧主家的狗視為“階級敵人的狗”、執意捕殺時,一位貧農半路殺出,站在了牧主的一邊。陣線分明的階級分析,在現實中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圖景,此后“在路上”的種種經歷更是把林胡的紅色理想不斷拉回到地面。曲折的道路沒有指向光明的前途,當他效忠于紅色理想,卻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反面,甚至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手淫、同性戀和女神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征途中的首要問題。唐僧一路收下三個徒弟,在他們的保駕護航之下終成正果。在路上,既是取經的過程,也是尋找同志的過程。林胡和雷廈、金剛、吳山頂,結成了出走的統一戰線。但是他和后兩者不算熟識,和雷廈也因為“第三者”插足一度關系破裂:兩人共同的舊識想來內蒙,林胡因為他當初沒有參與出走,送上告密信試圖阻止此事。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林胡都是孤家寡人。林胡最初把孤獨等同于勇敢和堅強,但是,勇敢和堅強這些道德品質無法戰勝生理需求。唐僧師徒四人都是和尚,吳承恩無須考慮他們的生理需求,即使如此,依然設置了豬八戒這個“花和尚”的形象。林胡無奈地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自己對異性的興趣越來越強烈。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英雄大都不近女色;在革命敘事傳統里,禁欲是基本前提。只有才子會和佳人聯系在一起,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是知識青年試圖劃清界限的,避之惟恐不及。“偷偷想女人和革命戰士的稱號很不相稱”,林胡把對異性的興趣視為“原罪”,在給老師的書面材料中也對此進行“靈魂深處鬧革命”。
轉移對異性的生理需求,通常有兩種辦法:一是手淫,一是同性戀。這兩者形成互補,構成了林胡的業余生活。在毛主席語錄中,有這么一句家喻戶曉的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在毛澤東那里,卑賤和高貴形成倒錯關系。但林胡需要面對的是神圣的理想和卑賤的行為之間的沖突,追尋紅色理想而來,卻在日常生活中陷入難以公開的手淫和同性戀,這使得林胡處于自我撕裂的狀態。
手淫只能加劇而非緩解原罪感,違背了“取經”的目的,相比之下,同性戀是一種更為有效而且也是更具正當性的選擇。在路上,是尋找同志的過程。“同志”在今天具有雙重涵義,一重是志同道合者,另一重是同性戀。在林胡那里,“同志”的雙重涵義同樣成立。他用戰友代替女性,曾和雷廈彼此發誓,同生共死。同性情誼不足為奇,但是林胡和雷廈的關系超出這一層面,具有了排他性,兩人相約不再跟異性相好。林胡這樣形容兩人之間的關系:“一種神秘的初戀般的感情繚繞在我們中間。”除了身體接觸,在情感層面上,兩人已與同性戀無異。當雷廈準備送給一位異性筆記本,林胡擔心雷廈被奪走,告訴自己的這位“同志”,那位異性對他印象不佳。有次雷廈亡命在外,林胡在家中吃飯,想到他啃饅頭、就大白菜,潸然淚下,以至母親大驚失色,認定兩人是同性戀。林胡并不諱言他和雷廈的關系:“確實,他是我一生中最愛的男人。”
在革命敘事傳統里,同性戀的道德是負面的,同志的道德是正面的,但沒有身體接觸的同性戀,可以歸入同志的范疇。所以,同性戀對林胡構成的道德壓力遠遠小于手淫,甚至還被賦予正面含義,因為它有尋找同路人的效果。手淫滿足著在路上的生理需求,同性戀則滿足了在路上的精神需求。這個組合隨著林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被瓦解。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林胡由于“莫須有”的罪名被抓。日記泄漏了手淫的秘密,手淫成為罪證。此前他和雷廈已經恢復“同生共死”的關系,在各個擊破的戰術下,關系再度破裂。手淫和同性戀,都不再可靠。
與此同時,林胡恢復了對女性的想象。韋小立是S省委第一書記的女兒,父親被整死,全家被洗劫一空,這個“走資派的女兒”喚起了林胡的同病相憐。隨后林胡的處境陡轉直下,在手淫和同性戀已經不再可靠的情況下,想象的女神從天而降。幻想需要現實中的異性作為投射,韋小立成為林胡“苦難中的希望”。想象無須征求當事人的同意。在現實中,韋小立對林胡保持沉默,這恰好留下了想象的空間。林胡眼中的韋小立,具有跟其它異性不同的因素,此前林胡對于異性幾乎來者不拒,縫得勒的牧主婆兒、罕達的老婆都曾成為性幻想的對象。他對韋小立的想象不具性的因素,“從不敢讓一絲絲淫邪念頭碰碰她的身體”。甚至連相貌都不再重要,林胡對她的評價是“算不上漂亮……讓人覺得不順眼”,“但也不丑”。女神是一種特別的異性,林胡對她更像是對待母親(“兒不嫌母丑”),只有想象,沒有性幻想。
在修訂版中,老鬼增添了一個細節:在快離開草原時,于寂寞難耐中與一位女知青有了人生的第一次——這絕非可有可無。現實中的女知青和想象中的女神,就像手淫和同性戀一樣,分別解決了林胡的心理問題和精神問題。這個分工非常明確,那位女知青具有顯著的性別特征,“身材豐腴,臀部性感”。
但是,林胡對這位追求者幾乎沒有任何感情可言,僅僅是滿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在《母親楊沫》里,老鬼透露,母親離開10年后,他還在冬天戴母親的粗毛線帽子,偶爾穿母親的尼龍襪和肥褲衩,午休時天天蓋母親的大羽絨服,一直保留著母親的口紅。d這些有點異常的舉動,與“戀母”情結密不可分,楊沫的形象與女神的原型也有相似之處,楊沫是“大圓臉、金魚眼、扁鼻子、闊嘴巴都極有韻味”,韋小立是“圓臉、小鼻子、脖子很短……嘴唇特鮮艷。
手淫、同性戀和女神雖然截然不同,但都與林胡生命深處的激情有關。在私人生活缺乏正當性的時代,激情只能以一個出口釋放,那就是革命和以革命為名義的暴力,性處在被壓抑的層面。當激情以性的名義釋放,它是沒有合法性的,于是只能偷偷地來、匆忙慌亂地來、手腳錯愕地來,這就是手淫。同時激情也可以改頭換面地來、喬裝打扮地來,這就是“同性戀”。激情在林胡那樣不諳世事、滿懷理想的青年那里,升華成一幅女神的形象,是那個時代激情唯一可以附著于意識層面的表達形式。
血的動力學
在路上,熱血是革命的能源。在《血色黃昏》的第一章,林胡們喊出了:“萬歲!熱血。”熱血是青春的激情、革命的浪漫情懷,也是暴力的蔓延、仇恨的循環。在這里,暴力和仇恨不再是貶義詞,而是被視為男人的血性、歷史的車輪。把激情、浪漫、暴力、仇恨捆綁在一起,是知識青年追求革命后的普遍癥狀。激情和浪漫是他們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思維遺留,暴力和仇恨則是追求革命的必要品質。它們之間有沖突,但更多的是一種銜接關系,擁有激情才能夠施展暴力和仇恨的才華,把暴力和仇恨浪漫化才能使得知識青年獲得行動的合法性。在路上滿足了所有這些條件,光明的前途提供了激情和浪漫,曲折的道路刺激了暴力和仇恨。
熱血不僅是隱喻,還成為精神和肉體的粘合劑。被手淫和同性戀割裂開來的精神和肉體,通過熱血融為一體。在小說里,“血書”反復出現。書寫血書的前奏是自殘,與其說這種行為需要勇氣,不如說它需要對紅色理想的絕對忠誠。同時,自殘還是能量的自我耗散。在手淫被道德否定、同性戀破裂的情況下,性欲激發的能量必須以其他方式釋放。林胡一度熱愛摔跤,這也是一種能量轉移,但缺乏精神含量。相比之下,血書通過自殘釋放身體的能量,非但不用承受道德指責,還可以獲得道德嘉獎。血液和精液在中國的民間傳統里有著直接轉換關系,所謂“一滴精、十滴血”。血書成為禁欲時代的“放血療法”,將肉體的欲望轉換成精神的追求,提供著革命的能量。對于林胡這種因為出身問題而出走的知識青年來說,血書更是戰勝血統的法寶,前者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而后者則是先天指定的。
林胡第一次寫血書是為了在內蒙牧區落戶,他們先是直接尋找當地安置辦公室,被告知沒有安家費,紅色理想在經濟基礎面前表現出脆弱的一面。在“獻身無門”的情況下,他們通過聯絡軍區司令員兒子,將血書交給了軍區司令員,最終如愿以償。第二份血書已經展現紅色理想的另一面,中蘇關系緊張,全連有1/3成員書寫血書,申請發槍。連里當時有4個山頭:復員老戰士、錫林浩特知青、北京知青、天津知青,很多北京知青寫了血書,但沒有一個拿到槍支,沒有一個書寫血書的錫林浩特知青,卻有很多都發了槍。林胡從家庭中出走,正是為了改變出身,他以熱血為能量,沒想到血書還是無法戰勝血統。等到第三份血書出現的時候,林胡幾乎走到窮途末路,他因反革命罪名被關押,不得不再次祭出這一法寶。從“獻身”到“申冤”,血書的功能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它的效用也不斷降低。
熱血不是綠色能源,也不是清潔能源,生產熱血的成本太高,難以適應漫長的革命征途。在路上的第一步會征用熱血,第二步是尋找替代性能源。當血書逐漸失效,女神喚起了林胡的人性,讓他意識到:“狂風暴雨固然壯美,但不能成天是。成天狂風暴雨也令人乏味。”
《青春之歌》著力證明紅色理想的價值,《血色黃昏》試圖對紅色理想進行反思,這是兩部小說的顯著差異。老鬼呈現了紅色理想的血色浪漫一面,“血色”一詞喚起的不僅是激情,還有殘酷。當知識青年們戰天斗地,團里的干部卻坐在溫暖如春的辦公室里打撲克,還有的貪污糧食、倒騰公物、干風流勾當……其中最荒謬的莫過于知識青年8年的努力不僅是一場無效勞動,還是一場對草原亙古未有的生態環境大破壞。然而,林胡對紅色理想的反思是極為有限的,他對“曲折的道路”提出質疑,卻不愿意批判“光明的前途”,他想把兩者區別開來,卻沒有意識到兩者是無法剝離的。
林胡曾經表示:
心中所愛的姑娘是現實中那個韋小立所消滅不了的。她是一尊最神圣的女神,我將永遠保持對她的單戀。
這段話也可以理解為他對紅色理想的態度,紅色理想是現實中的血色浪漫所消滅不了的。林胡對血色浪漫的不以為然,不是出于理性反思,僅僅是因為自己受到了傷害。林胡對紅色理想的單戀沒有受到血色浪漫的影響,盡管他對“青春的血”表示無限惋惜,對紅色理想依然是飛蛾投火。對女神/紅色理想的單相思(林胡的手淫和同性戀,也同樣具有單相思的成分),取代熱血成為革命的能源,它更具可持續性。值得注意的是,熱血和單相思,這兩種革命的能源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兼容的。林胡回首青春,發出這樣的感慨:
這些回憶,在情感上所激起的瘋狂,無論多么歇斯底里,也不足以使我對內蒙兵團來個徹底否定。盡管自己被兵團定成敵我矛盾,我卻不忍心也從沒想到要給它定個敵我矛盾。我沒有理由全盤否定它。
林胡依然沿襲著“歷史目的論”,他否定自己走過的“曲折的道路”,但是并不否定“道路是曲折的”,更沒有反思“前途是光明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手段和目的的關系缺乏反思,而是表示“以毒攻毒是良方”。林胡不會意識到,這藥方同時也是疾病的癥候。
林胡為何親歷血色浪漫,依然缺乏對紅色理想的反思力度?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答案。林胡無法否定自己的激情、無法否定自己的過去,這使得反思不可能抵達問題的核心。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那就是林胡在路上除了短期的同性戀、除了有想象的女神相伴,絕大部分時間處于孤獨一人的狀態,這對他的思考能力構成根本性的傷害:
隨著思想的貧乏,說話能力也日益低下,愛用簡單句。對事物只用“好”,“壞”兩個概念判斷,很少附加定語、狀語。不想費腦子組織句子,單詞量也越來越少。
經過長期的孤獨生活,林胡終于不再把孤獨等同于勇敢和堅強,而是意識到它也有可能“淫蕩、冷酷、丑惡”。一般而言,當年有思想部落可以交流的知識青年大都具有相對深入的思考能力,當年是孤魂野鬼的知識青年大都是單向度思維。這不僅是林胡的處境,也是老鬼和那一代知識青年共同的精神狀況。
《青春之歌》的全知全能敘事,把林道靜放在“被看”的目光下,這是“改造”主題經常使用的敘事方式,改造首先要把自我他者化。《血色黃昏》的第一人稱敘事,是“訴苦”主題的慣用模式,也最為適用于長期自言自語的林胡。它還可以產生“憶苦思甜”的效果,所以,林胡在痛訴個人歷史之后,還是表示:
感謝你啊,內蒙兵團,給了我一段很苦很苦的經歷。這也是一種財富。
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血色黃昏》在一些細節上更具文字的審美效果,不像當年的“傷痕文學”那么粗糙,但是它沒有超出“傷痕文學”的反思水準,屬于遲到的“傷痕文學”。
【注釋】
a楊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
b老鬼:《血色黃昏》,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血色黃昏》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引文以修訂本為準。
c老鬼在1996年撰寫的修訂本前言中交待:“馮牧同志曾向我建議不要用冷僻字做書中人物的名字,此次特將主人公林鵠(hu)改名為林胡。”參見老鬼:《血色黃昏》修訂本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d老鬼:《母親楊沫》,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