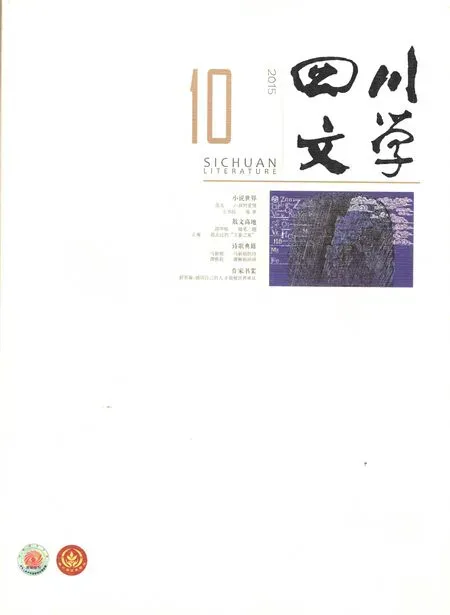感動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認—非訪談劉震云
舒晉瑜/文
大多數時候,劉震云是不動聲色的,包括他的幽默。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目光平和,有時候看著你,有時候了不知道看誰,旁若無人地自顧自地說。在平常的閑聊中,劉震云大概是使用對話最多的作家。他會隨口編一段對話,涉及的兩個人,也許一個是上海人、北京人或其他人,但另一個肯定是河南人。他甚至會用不同的方言(也許不太準確)去完成這個對話,扯著扯著,眼看不著邊際了,陡然間一句話就能把你帶回到原來的主題。你才發覺,被他繞了一個大彎子,雖然繞遠了,但卻饒有興趣,就是你心甘情愿跟著他的語言走迷宮,到了終點還意猶未盡。
這就是劉震云的魅力。所有他在的場合,能帶給大家無窮的樂子。你就聽他講故事,聽得懂就會心地笑,聽不懂的也能被他的神態迷住。他比較常用的口頭語是,“這樣的話呢”,說完這個就表示故事又有了遞進。他是一個比較會寫故事,也比較會講故事的作家。《甲方乙方》《手機》《我叫劉躍進》等影視作品的成功,使劉震云打響了中影集團打造的“中國作家電影”第一炮。他幾乎成了“專業賀歲作家”。
為什么是劉震云?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個人,不用上班,過著規律甚至有些閑適的生活。他早晨六點半起床,跑步一個半小時,上午工作兩小時,下午工作兩個半小時,晚上九點半就睡覺。不寫作時看書,或者出門見人,要么就去買菜,和菜市場的人交朋友。他喜歡有生活品質的人,這與職業無關。他和賣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幫忙挪水果箱,也會邀請他去水果攤后的大帳篷里嘗嘗剛出鍋的餃子;他和釘鞋的湖北師傅成了朋友,湖北師傅習慣帶著手套釘鞋,縫完拉鏈會反復用肥皂打磨,特別認真,這使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種尊嚴感。裝修房子,他又和賣石材的老趙成為朋友,老趙只跟他說心里話:“像我一個賣石頭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話了。”這讓劉震云無比感動,那一刻,他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極其不普通的人。他讀了20多遍《論語》,總結孔子有三大特點:“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過去我認為他是忠厚的人,其實不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是因為孔子和身邊的人沒有話說。刻薄的人有見識,刻薄的背后,藏著對所有人的悲憫。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兒往深刻里說,是把深刻的東西往家常里說,這種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說的,過去我覺得是大師,但現在我意識到其實那是學徒。第三,孔子說話繞,繞半天就不知繞到哪兒去了。這三個特點,經琢磨。”
《一句頂一萬句》是一部大書
不知道此言一出,劉震云是否會得罪朋友。但是聽他講完故事,便知道這又是肺腑之言,是這個時代毫無意外的結論。雖然簡要地概括一部作品可以有不同角度,比如認識的角度、面對世界的角度,或者情感的角度。但是概括《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云是以故事的角度:兩個殺人犯,一個人特別想找到另一個人,找到他就是想和他說知心話。
好朋友的意思,不是你缺錢的時候他借錢給你,而是面對事情、面對世界、面對生活的態度相同,具體到某一件事上有默契。劉震云說,在生活中找一個朋友不容易。人神社會和人人社會的最大區別,是多出一個可以說話的地方。也許神不存在,也許無處不在。神可以使你痛苦、憂愁、想懺悔的時侯,有個落腳的地方。中國的社會,如果你有懺悔、有憂愁,沒有上帝,只好在人與人之間找一個知心朋友。“人找人,話找話不容易。” 神不會背叛人,但是朋友會變得不是朋友,如果他把你的話兜出去,知心朋友會變成一把刀扎向你的胸口。所以有時候,知心的朋友是危險的。
“一句頂一萬句”是林彪1966年說過的話,時隔43年,劉震云拿出來做書名,有何用意?他說:“我今天說這句話,跟林先生是話同音不同意。他的話是政治指向,要達到政治目的,我指向的是生活。我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賣豆腐的、剃頭的、殺豬的、販驢的、喊喪的、染布的、開飯鋪的,還有提刀上路殺人的……我對他們說的,是一句知心話。”他進一步解釋說,“一句頂一萬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他的發明,這意思古來有之,已被人說過幾千年。比如說“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語定乾坤”,“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說的都是“一智”、“一語”的重要。
在《一句頂一萬句》中,楊百順和牛愛國戴“綠帽子”,原因并不在楊百順和牛愛國身上,而是他們的老婆出了問題。楊百順和牛愛國發現自己身邊出了西門慶和潘金蓮時,提刀上路就要殺人,當找到時又突然發現錯不在他們,而在自己。自己的“綠帽子”,原來是自個兒縫制的。楊百順和牛愛國發現,“綠帽子”只是個表象,看似是男女間的事,根子卻不在這里,而是因為他們跟他們的老婆之間沒話,老婆與給他戴“綠帽子”的人,倒能說到一起。偷漢子的女人和奸夫,話語如滔滔江水。說了一夜,還不停歇:“咱再說些別的?”“說些別的就說些別的。”從有話無話的角度講,給他戴“綠帽子”的兩個人,做得倒是對的。當他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從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
“從男女關系的角度說,潘金蓮該殺,但從有話無話的角度,從知性的層面講,他們是對了。”劉震云說,自己無意為潘金蓮平反,而是不同的角度。他采取的是公眾視角,從虛的角度講這個故事,西門慶和潘金蓮沖破了所有的束縛和規矩,沖破了人類所有的道德底線,奮不顧身,越過高山大海也要到一起去,他們是英雄。
寫作就是找朋友
寫作的圈子,影視的圈子,媒體的圈子……劉震云出進自如,他的人緣很好,幾乎沒有聽到過負面的反映,也沒看到過負面的報道。即使是有爭議的評論,也是就作品論作品。然而,朋友滿天下的劉震云,內心又是孤獨的。當他說,他在作品中找朋友時,我感覺到他的悲傷,就像一個熱衷于擺積木的小孩子,擺好了,推倒再擺,沉迷于自己搭建的世界,孤獨抑或自得其樂,無人得知。
“我的寫作讓我意識到,寫小說是認識朋友的過程。寫《一地雞毛》的時候我認識了小林,他告訴我,家里的一斤豆腐餿了也不扔,比八國首腦還重要,我就說這是一件大事;寫《手機》的時候,嚴守一問我:你覺得謊話好不好?我說不好。嚴守一說:你錯了,是謊話而不是真理支撐著我們的人生,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寫《我叫劉躍進》時,劉躍進問我:世上是狼吃羊還是羊吃狼?我說廢話,當然是狼吃羊。劉躍進說錯了!他在北京長安街上看到羊吃狼。羊是食草動物,但羊多,每只羊吐口唾沫,狼就死了。到《一句頂一萬句》時,楊百順和牛愛國告訴我:朋友的意思是危險,知心的話兒是兇險。我說有道理,我吃這虧吃得特別大。”劉震云說,寫作對自己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是可以在書中找到知心朋友。書中的知心朋友和現實中的不一樣,書中的朋友永遠是有耐心的,這本書中的人物可以說是我最真心的朋友。什么時候去找他們,他們都在那兒等著你。這是他寫作的動機,也是寫作的目的。
“我一直努力堅持我在文學和生活圈子的關系,我喜歡就不能零碎地做這些事。要全面、整體、多方位地找書中的朋友,調整文學生活和自己的關系。”劉震云說,大致有4個系列,一是故鄉系列,二是“一”字頭系列,比如《一地雞毛》《一腔廢話》《一句頂一萬句》;三是官場系列,有《官人》《單位》,后來看到好多人在寫,他就不寫了;四是“我叫某某某”系列,下一部書肯定會是“我叫XXX”,也許有一天會寫一部“我不叫潘金蓮”。
我不直腰,所以割麥子比別人快
劉震云將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語言方式,歸結為是因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響者,則是外祖母。
“我受外祖母影響非常深。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她年輕的時候,在我們那兒是特別大牌的明星,她的名氣相當于朱麗婭?羅伯茨,朱麗婭成為明星不奇怪,因為她是演員。外祖母成為明星不容易,她是長工。那時她在地里割麥子,三里路長的麥子割到頭不直腰。她的‘轉會費’非常高,像羅納爾多。外祖母說,我為什么比別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別人快’。”
“真正的好作家首先得是思想家。”劉震云說,見識是考驗作者的最根本的標尺。“作者的寫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驗不在寫作中,而是在寫作前,在于你能不能從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發現。就是作者的見識是否獨特,凡是好作者,見識與其他人必然不同。”
考量一個作者,看其是否具有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至關重要。劉震云解釋說,這里的思考有兩個層面:一是整體思考。開始寫之前要想好到底寫多深多長,思考兩天和兩個月不同,思考兩個月和兩年又不同;二是寫作時的具體思考,細節、人物、情節、對話都要照顧到。還有一個是持久思考,要對自己的創作體系有整體考慮,不能亂槍打鳥。“寫完《一地雞毛》,再寫《一地鴨毛》,讀者喜歡,評論家也喜歡。但是我希望改變。”“寫出好作品,在寫作前和寫作時深入思考,寫作后迅速遺忘也特別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個山頭,從零開始。不斷把自己歸零,也是我的習慣,不管是生活還是寫作,我習慣不斷重新開始。我相信以后能寫出好作品。”
結伴去汴梁
常常有人問劉震云:你是怎么想到寫《我叫劉躍進》的?他不直接回答。他說:“我常拿結伴去汴梁打比方,倆人在一個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來都是去汴梁。吸煙,說話,又投脾氣,于是結伴而行。走著走著,更熟了,開始說些各自的煩惱和壓在心底的話。到了汴梁,一個往東,一個往西,揖手而別。過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興許磕著煙袋想,‘老劉也不知怎么樣了?’”
在劉震云那里,這種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地雞毛》《溫故1942》《故鄉面和花朵》《一腔廢話》《我叫劉躍進》體現的是他的思考與創作處于不同階段時的狀態。他一路走過來,在那段路上碰到小林,經過一段路又碰到300萬災民,再走再碰到一大批胡思亂想的人,走到現在就碰到劉躍進,這種相遇不是亂竿打棗。這個變化在外人看突然,在他內心是必然。這是作者創作體系的問題。
《溫故1942》的創作使劉震云第一次意識到能“結伴去汴梁”的重要性。“我在生活中碰到一個朋友,他要編一部百年災難史。其中有1942年河南旱災餓死了300萬人,作為河南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調查這場災難。我去問活下來的當事人,問我外祖母當年的情況,我外祖母就問:‘哪一年?’我說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還是問:‘餓死人的年頭多了,到底是哪一年?’深重的災難竟然瞬間轉變成另一個事:遺忘。你們家死了這么多人都不知道?忘了。我就急了,遺忘使我震撼。這種態度比前面的考察都重要得多。”從此開始,他就不斷地“遇”到能夠相知相交的“伴兒”。
寫完《一地雞毛》,誰也不會想到他會寫300萬災民。以劉震云的創作軌跡,寫完《我叫劉躍進》,絕不會有《我叫李躍進》。“我再有什么作品,也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意想不到,不但對讀者重要,對我也重要。”
誰是賊?劉震云才是“賊”
和劉震云接觸多了,你會發現,他是一個特別善于琢磨、善于領悟,更是一個特別善于學習的作家。他真誠地說:“不是我謙虛,是確實不懂,我對世界知道得不多。如果知道得少,假裝知道多,容易把自己架在半空中。身邊好多朋友說的道理我不明白,后來明白了是因為學習了。‘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實兩人行就有我師。發現別人一百條缺點,于你無補,發現優點才有好處。誰是賊?劉震云才是賊,從別人身上學東西,是深入思考能力的營養補充。”所以,只要有時間,他不拒絕和任何人一塊兒坐一坐。
在《甲方乙方》中,劉震云扮演了一個失意青年;在《我叫劉躍進》中,他扮演了只露了一面的打哈欠的人。雖然鏡頭不多,劉震云卻又學到無數東西。“最大的收獲是發現電影對話的趣味,過去小說對話是順著下來的,‘吃了么’,‘吃了’,‘吃什么’?‘紅燜肉’。電影中不這樣,這一句說:‘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張這家伙不是東西!’再接下來可能說:‘老李這兩天可沒閑著。’對話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極有趣味性,這種形式放在小說里,更有趣味性。學到很多書外的東西,沒壞處。”
“還有一個收獲,接觸到了不同的人。比如導演、演員、攝影師、搬道具的小伙子……他們都是過去我沒見過的人。由于行業的不同,他們說話的習慣和做事的方式不同。這對我有兩個好處,一是對生活面了解得更寬了,二是,發現每個人都是一個哲學家。搬道具的、群眾演員……千萬不要小看他們,他們思考世界的角度會對你有啟發。”
“我在《農民日報》認識一個校對老姚,我們倆關系特別好,他是哲學家,他愛指出我作品里的錯別字,每次都很嚴肅。我說:‘您不是一字師,是幾百字師。’生活中,他教我好多道理。比如說餓著肚子千萬不要上街,那樣容易亂買東西,吃飽了上街省錢,我試了試,果然是對的。”
劉震云讀書,也能讀出別個無法體會的味道來。他把書分三類:一類像白開水,作品和生活一樣,不讀也罷;一類像酒,但喝多了會變形;一類是酒精、酵母,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是作者寫完就完成了,而是讀者讀完也沒完成,只完成一半,好多年過去,又讀了兩遍,和作者的心相通了,會心一笑,這時作品才完成了。“過去有一句話,叫功夫在詩外,同樣,功夫在書外。《論語》并不長,為什么不懂?是因為字之外的東西多,越讀越多,這樣的書費勁。這個費勁就證明,讀者和作者的碰撞是一次完成不了的。真正的好書不是作者一個人完成的,是激發讀者思考感受的觸發點,這樣的書,才真正能夠使讀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共同的寫作。書讀完了,真正的讀書才剛剛開始。這是讀書的比較好的境界。”
一個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來到河南一個縣傳教,傳教40年一共發展了8個教民。一天,傳教士碰到了殺豬匠,就想發展他。傳教士問他:你信主嗎?殺豬匠說,我不信,我信主有什么好處?傳教士說,主能讓你知道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殺豬匠說我現在就知道,我是一個殺豬的,從張家莊來,到李家莊去殺豬。傳教士想了半天說,你說得也對。接著又說,你總不能說你沒有憂愁。殺豬匠說,我有憂愁。牧師說,有憂愁你不找上帝,你找誰呢?殺豬匠說:上帝能告訴我什么?傳教士說,信主,主馬上會告訴你,你是一個罪人。殺豬匠馬上急了,說我跟他一袋煙的交情都沒有,怎么還沒有見面他就說我錯了呢?……傳教士死后,殺豬匠打開了傳教士設計的教堂圖紙,那是一座宏大的教堂,彩繪的玻璃,精致的座椅……殺豬匠發現教堂上面的鐘在轟鳴,所有的窗戶全都推開了,自己心里的窗戶也被推開了。這個時候,他知道這個傳教士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師……
“傳‘教’給我喜歡的人,也是我奉行的準則,把‘教’傳給漢學家和批評家,這事我不干。”劉震云認為,感動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