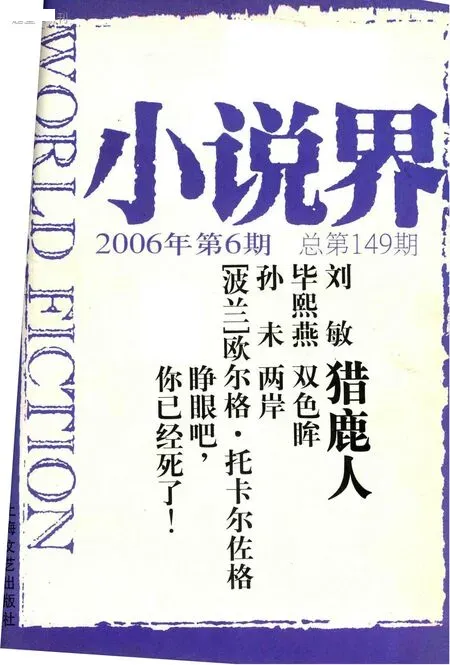情史失蹤者
阿乙
1976年出生。當(dāng)過(guò)警察,當(dāng)過(guò)編輯,現(xiàn)為文學(xué)主編。出版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下面,我該干些什么》,小說(shuō)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里》《模范青年》,隨筆集《陽(yáng)光猛烈,萬(wàn)物顯形》《寡人》等。曾獲華語(yǔ)文學(xué)傳媒大獎(jiǎng)最具潛力新人獎(jiǎng)、《人民文學(xué)》中篇小說(shuō)獎(jiǎng)、蒲松齡短篇小說(shuō)獎(jiǎng)、林斤瀾短篇小說(shuō)獎(jiǎng)、《小說(shuō)選刊》雙年獎(jiǎng)等。
2013-10-09
星期三
九月初五
癸巳年(蛇年)
壬戌月戊申日
宜:祭祀 祈福 求嗣 開光 開市
忌:嫁娶 作灶 修墳 安門 入宅
我從夢(mèng)中完全醒了過(guò)來(lái)。一位陌生人站在黑暗中。因?yàn)榇┲铑伾钠ば㈤L(zhǎng)褲及高領(lǐng)毛衣,他的身軀融化進(jìn)黑暗中(此時(shí),光明就像大軍從緊閉的絳紫色窗簾外浩浩湯湯地經(jīng)過(guò)),而那張黧色的形同老尸的臉猶如一盞點(diǎn)亮的許愿燈,懸浮在我眼前,挺嚇人的。他向后退卻,就好像不是他不事聲張地站在這里嚇壞了我,而是我的蘇醒嚇壞了他。他試圖掩蓋什么,卻什么也掩蓋不了,或者說(shuō),也沒什么具體的東西需要去掩蓋。后來(lái)我從他那總是盯著一個(gè)人看形若癡呆的眼神覺察到,他要掩飾的正是對(duì)我的長(zhǎng)久注視。他是在我睡覺時(shí)潛進(jìn)來(lái)的,一直看著我睡(在睡眠中咂嘴,像一條毛毛蟲那樣蠕動(dòng)與翻轉(zhuǎn)身體,有時(shí)還拿爪子在胯襠?癢)。他一邊看著我一邊比較他自己,然后不服氣地想:
這個(gè)人何德何能啊。
他也不瞧瞧他自己。
醒來(lái)時(shí),房間里多出一人,而且還是名男性,我卻不害怕,或者說(shuō)害怕也只是程序性地害怕(就像一個(gè)走慣夜路經(jīng)常遇劫的人最終能打著哈欠說(shuō),都在這兒呢),這讓我對(duì)自己感到不可思議。隨著我們僵持的時(shí)間越長(zhǎng)(他將右手半舉在左胸前,呈半握拳狀,左手撫摸著腹部,八字胡與絡(luò)腮胡連結(jié)在一起,頭發(fā)卷曲然而卷曲得不太自然就像是被他姨公硬生生扯成這樣的。毛線衣顯得松垮肥大,肩膀又過(guò)于瘦削,因此整個(gè)人看起來(lái)像是一株被遺棄的悲傷的黑色圣誕樹——在他身上散發(fā)著一股自以為是的悲傷感、正義感,一舉一動(dòng)都有很強(qiáng)的儀式性,他這會(huì)兒正半歪著頭,眼帶一絲哀求,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看著我——他的臉顯得小,額頭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唇小,下巴頦兒小,眉骨倒是挺高,就像是立著的一處高墈,從陡峭的眉骨下到深陷的眼窩那兒可能還需要縱身一躍呢),我心里就越出現(xiàn)一個(gè)念頭。這個(gè)念頭要我,一名被害人,去同情、幫助或者說(shuō)是寬恕已來(lái)到面前的擅闖民宅的強(qiáng)盜。我估摸著他年齡比我還要大,應(yīng)有四十。這是個(gè)來(lái)自時(shí)間深處、遙遠(yuǎn)地界、像是重復(fù)過(guò)多次甚至有點(diǎn)喋喋不休的念頭:對(duì)他好點(diǎn)。就像他是名弱智、小孩或者說(shuō)是需要安撫的失敗者。我越是這么強(qiáng)調(diào),越是控制不住自己(就像有人捉著我的雙臂讓我不由自主地去干了這事)。在他從背后抽出那把刃長(zhǎng)19cm、柄長(zhǎng)12cm、寬度最寬只有3cm的妄稱是不銹鋼的裁紙刀后,我粗魯?shù)貖Z過(guò)了它。這真是一把滑稽的刀啊,將將能切動(dòng)西瓜,鉛筆都削不了。正因?yàn)樗z毫起不了恐嚇的作用,我只用一只手去奪它。不過(guò)當(dāng)它在糾纏中割壞他長(zhǎng)著不少毛細(xì)血管的透明耳朵并使耳廓那里汩涌出一滴飽滿的血時(shí),我還是為它所擁有的破壞力感到吃驚。他摸摸,搓捻搓捻,懊惱地看著指尖黏糊糊的血跡,說(shuō):“有紙嗎?”
于是我扯出一張又一張一共四張抽紙給他。
他叫馬丁。跟著他來(lái)的那伙人就沒那么好說(shuō)話了,在聽見樓上的動(dòng)靜后,他們沖上來(lái),以飽滿的激情(我們常在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那里見到這股激情)踹開我所僑寓的這間屋子的房門。插銷給踹脫了。你媽×給臉不要臉是吧,他們連出數(shù)掌,將我推向墻邊。馬丁厭煩地走到他們和我之間,埋怨他們。可以想見,起初他們是想一起上來(lái)的,被阻止了。馬丁說(shuō):“讓我一個(gè)人先上去試試。”而這可能還是她的意思。不要得罪他,她凄凄切切,病病殃殃地躺著,聲音微弱地向她的表哥馬丁交代。
他們不是出于惡意(我愿以名譽(yù)發(fā)誓),而僅只是認(rèn)為這樣做效率更高,才將我架起來(lái)。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云端飛翔了一會(huì)兒,然后被塞進(jìn)一輛黑色的沒洗過(guò)的奇瑞轎車?yán)铩\噧?nèi)滿是煙蒂被殘茶浸泡過(guò)的氣息。他們放了一會(huì)兒Lady Gaga、刀郎與龐龍的歌,盡顯京郊農(nóng)民本色。途中,我突然抓了一下馬丁的上臂,說(shuō):“你還是單身吧。”
“你怎么知道的?”他顯得詫異。
“你臉上有一股像秋霜一樣嚴(yán)峻的東西。”我說(shuō)。
我就沒說(shuō)我注意到他總是拿鼻子去嗅自己慣用的那根食指,或者說(shuō)總是將那根慣用的食指湊到鼻子跟前去嗅。在偵破學(xué)里,犯罪的人總是控制不住想回到作案現(xiàn)場(chǎng),以排查是否仍遺留有證據(jù)。仰仗手淫的人也如此,在潛意識(shí)里擔(dān)憂指間還殘留有精液那像是生石灰或魚腥的味道。
他的母親叫丁弟英,舅舅叫丁本領(lǐng),表妹叫丁婕妮。若不是他這次前來(lái)綁架,我可能要永遠(yuǎn)忘記丁婕妮的名字了。世上有很多人是這樣,只有走到你跟前,你才確信自己是認(rèn)識(shí)對(duì)方的。遺忘有時(shí)是因?yàn)橐粋€(gè)人無(wú)論在長(zhǎng)相還是舉止上都毫無(wú)特色,有時(shí)則是因?yàn)槟阍跐撘庾R(shí)里就想躲掉對(duì)方。你嫌棄此人。這種對(duì)對(duì)方的否決,在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后,你會(huì)忘記,然而只要重新近距離接觸一會(huì)兒,你就會(huì)記起當(dāng)初為何會(huì)否決了。于是你又找個(gè)借口,悄悄地開溜出你們的友誼(或者愛情)。
我是在當(dāng)時(shí)還健在的錢柜KTV套間認(rèn)識(shí)她的,或者說(shuō)是她在那里認(rèn)識(shí)我的。當(dāng)時(shí)我與身邊一位長(zhǎng)相豐腴的女孩相談甚歡(不知道為什么一想到白嫩豐腴的女人我就心頭發(fā)緊,喘不過(guò)氣來(lái),靈魂進(jìn)入一種亟待痛飲的干渴狀態(tài)),直到我違背祖訓(xùn)——“緊閉嘴,慢發(fā)言”。我的父親這樣屢次交代——輕易置評(píng)當(dāng)時(shí)流行的某位明星(我認(rèn)為雙棲是一個(gè)人在躲避自己兩方面的無(wú)能),挨到對(duì)方的一頓狠戧。我望著茶幾上像塔樓一樣林立的330ml喜力酒瓶,隨意放置的五葉神煙盒、白色七星煙盒、ESSE煙盒(這是胖女孩抽的,不像別的煙盒只剩幾根煙,它還留了大半包),積滿煙蒂的煙缸,藍(lán)金邊窄口骨瓷帶把手的咖啡杯,諾基亞或愛立信手機(jī),遙控器,點(diǎn)歌本及臺(tái)卡,等等這些東西,懊喪極了,我想還不如直接往我臉上澆一杯酒呢。這次打擊給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或者說(shuō)是心理陰影——以至于至少有三周的時(shí)間我都不敢怎么評(píng)議他人。我哪知道到處都是這歌星的粉絲。我以如廁為名義,離開錢柜。有人為這次周末常有的男女聚會(huì)留下了一幀照片。當(dāng)時(shí)我處在右二,右三是胖姑,而丁婕妮處在右六,也可說(shuō)是左一——那是個(gè)沙發(fā)轉(zhuǎn)角的地方。她雙手抱頭,仰著臉,靜聽在房間內(nèi)沖來(lái)撞去的孤獨(dú)而兇狠的歌聲以及將頭發(fā)梳向后頭的我對(duì)鄰座的恭維。那時(shí)我表現(xiàn)得像一名雄辯家,像一頭獅子。幾十天后,我對(duì)胖姑娘沒演說(shuō)完的東西,滔滔不絕地對(duì)丁婕妮說(shuō)完了。我說(shuō)得是那么痛快和意猶未盡。我想起一位賣力的球員,在得到教練的明確指示后,上場(chǎng)將幾乎能碰見的對(duì)手都鏟翻了,鏟完大嘴一咧,齒上還掛著痰涎。當(dāng)時(shí)我們坐在一把對(duì)角線長(zhǎng)5m的海藍(lán)色遮陽(yáng)傘下,她南我北,雨急切地來(lái)了一陣,打落在傘布上的錚錚淙淙的聲響讓人想起歌劇院經(jīng)久不歇的掌聲。《新京報(bào)》最后一版預(yù)測(cè)這是場(chǎng)“廿年不遇的大雨”。然而一會(huì)兒它就變小了,毛毛細(xì)雨在意外出現(xiàn)的日照里斜飄著。其間,一架飛機(jī)從平地起飛,在上升的過(guò)程中,都能看見它收起機(jī)輪就像鷂鷹縮回雙爪并將之貼緊于腹部。我靜靜地看了一會(huì)兒森白的機(jī)腹,接著講了下去:不敢相信這樣的事實(shí)竟然就在眼前發(fā)生,哇嗷,那種緊張簡(jiǎn)直難以用筆墨形容。她一直饒有興致地聽著,簡(jiǎn)直入迷了(盡管我看出這其中摻入了一些禮節(jié)性的堅(jiān)持)。是她找到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找到我的朋友要到我的聯(lián)系方式的,我們?cè)赒Q里聊了會(huì)兒天,商定來(lái)這兒喝上一杯。我喝的是冰鎮(zhèn)伏特加,她喝的是一杯袋泡茶。我在顧盼自雄的演說(shuō)途中,順帶審視了她的樣貌。如何說(shuō)?她比胖妞要漂亮不少,卻缺乏致命一擊的東西。或者說(shuō),她有很多可稱作美的地方,這些美卻無(wú)一例外,都打了折扣,不能往里細(xì)究。比如牙齒緊密,上頭卻有一層用什么牙膏也洗不脫的黃漬,如果笑得開放點(diǎn),還會(huì)露出大塊的法魯紅色牙齦。鼻子雖筆挺,也不是什么鷹鉤鼻,鼻前孔處卻又平又翹,像是用搪膠材料塑成的一捏就會(huì)吱吱叫的玩具鼻子。無(wú)脫發(fā)征象,然則頭發(fā)少而薄,好似就那么一小綹。身材比例好,一身瘦骨,但同時(shí)你也別奢望她有什么乳房。她穿什么我忘記了。我不知疲倦地講著,直到縮起鼻子,像狗一樣四處嗅起來(lái)。就像是雨水沖垮泥沙,從而使被掩埋的死鼠露了出來(lái),這股子臭味越來(lái)越濃烈。后來(lái)我們離開這里很久,我都回到自己家了,這股味道還是沒消散掉。在送她的途中,本著一種勢(shì)必要將事情按一二三四五的程序做完的態(tài)度,我拉起她的手,雖說(shuō)我確信自己并不愛她。我拉起她的手而她委婉地拒絕,直到,幾乎是她自己下定了決心,又許可我握住它了。沒什么感覺,手很小,有一種克服不了的陌生感,像是握住松鼠濕潤(rùn)的紅色小肉掌。在一條兩側(cè)長(zhǎng)滿梧桐、瀝青因雨澆而變得漆黑和分明的寬闊街道(在那樹叢中我竟然分辨出一棵出自印度至喜馬拉雅地區(qū)的雪松),在下午將盡的時(shí)分,我們分道揚(yáng)鑣,一名從使館區(qū)走出來(lái)的老年男人摘下絲織白手套,優(yōu)雅地伸出胳膊,讓她挽住,一起走了。那是她父王,背挺得像一名將軍。
她的皮膚說(shuō)不上黑也說(shuō)不上黃,總之不顯白(我總覺得這是帝京水土的問(wèn)題,在南城那些老年人的臉上我常看見與實(shí)物酷肖的塵土、溝壑與癤瘤,這簡(jiǎn)直是對(duì)他們所處惡劣環(huán)境的一種擬態(tài))。
我們便不再怎么聯(lián)系。多日后的一個(gè)晚上,我做完所有的事,靠在椅子上,對(duì)著電腦發(fā)呆,一發(fā)數(shù)小時(shí),就像躺在一葉舴艋內(nèi),任其在音樂(lè)的海水里漂蕩。直到她在QQ上登錄。她閃了幾下,像是街道上有間鋪?zhàn)娱_了門。我百無(wú)聊賴地走上岸來(lái),我發(fā)現(xiàn)自己死活記不起她的本名來(lái)。記不起同時(shí)又無(wú)法忍受這種失憶的痛苦,因此就有了對(duì)話框內(nèi)一行無(wú)禮的字:
你是——
丁婕妮。她答道。
我們無(wú)話。我將雙腿擱在工作臺(tái)上,整個(gè)人與大地平行,視若無(wú)睹,望著那打開就再?zèng)]合上的對(duì)話窗。左上角是她頭像。此時(shí)是凌晨一點(diǎn),人尤其寂寥,就好似整個(gè)城市睡熟了,上帝留下我值守,他自己也走掉了。也許還有幾輛封閉的盜狗車在高架橋上狂奔吧。有一陣口琴聲自音響內(nèi)吹響(這聲音讓我想起一把隨著海濤綿延起伏的高貴的帶著金色流蘇的鐮刀,它在刈割著什么)。我心間忽然充盈起對(duì)目前這個(gè)女人的愛。我想表達(dá)出來(lái)(也許歌聲結(jié)束這種感覺就不存在了不是嗎,我們經(jīng)常遭遇這樣的事情)。我很難形容那晚上的自己,就是現(xiàn)在的自己也難形容。也許我是個(gè)讓自己都膽寒的無(wú)恥之徒。我能堂而皇之地忘掉對(duì)方,然后又能恬不知恥地向被自己遺忘的對(duì)方索要那已明顯由其收回去的愛情。我在這方面從不慌亂,處變不驚。就像一名被揭露的騙子,伎倆全然敗露,卻還是能拿著行騙的道具赤裸裸地逼問(wèn)對(duì)方:“可是它便宜不是嗎它就是便宜!”我記得有一次一名女子突然對(duì)我聲討,說(shuō)男人沒一個(gè)可信就連我也是,我耐心等她發(fā)泄完,弄清是我和一位哥們兒的閑談(在這種酒局里,人們總是不可避免地評(píng)價(jià)女性)——我向他“掏心掏肺”的東西——被他出賣給了她。我打開手機(jī)通訊錄,將他刪了。我一邊刪一邊認(rèn)真地看著她,慷慨陳詞:只因我感受不到就像我愛你那樣的你愛我的熱度你知道嗎,我感受不到;我渴求的是滾燙的情感,而你給我的連熱水都算不上。直到她抱緊我一再求我別這樣了,我還在說(shuō):我們多多少少都是恐怖分子你知道嗎,在愛情里。有時(shí)我以這樣的理由——難保對(duì)方就不是逢場(chǎng)作戲——來(lái)寬慰自己并不道德的行為,或者說(shuō)提前安慰可能失敗的自己。
我忘記自己(第一次)因何逃開對(duì)方。我覺得那個(gè)逃離的人真是傻鳥,竟然錯(cuò)失掉這樣一位好姑娘。我記起她一切都算好的地方。我為什么會(huì)放棄這樣一位臉?gòu)尚〉脝问志涂晌兆〉南褚恢混`鳥的姑娘呢。這會(huì)兒,我都沒辦法管理自己洶涌而至的愛了(正如有人動(dòng)不動(dòng)就哭)。我開始以一個(gè)愛情追求者的身份(簡(jiǎn)直是勝券在握,然而我卻一定要表現(xiàn)得像一名恭順、諂媚的廷臣或下人),鄭重地向她跪求那張照片。這種行為讓我想起自己在二十歲前堅(jiān)韌地請(qǐng)求一名女孩脫下她的褲子。哪張。她問(wèn)。旋即她又表示出拒絕。就像她才覺察出這種騷擾的無(wú)聊。在這方面我經(jīng)驗(yàn)可豐富了。趁著是在網(wǎng)上(一個(gè)外人沒有),就像是在密室,我盡情向她撒潑打滾,又是哀求又是禮贊,什么肉麻的稱呼都使用上了。最后她終于將那張一個(gè)人站立在奧運(yùn)會(huì)結(jié)束后的湖景東路的照片(也就是她的頭像照片)傳給我。那時(shí)候殘奧會(huì)都結(jié)束了。她一只手拿草帽(是那種由真的金色稻草編織而成的紋理粗糙的草帽)壓住左腰,一只手拎著高跟鞋的鞋跟,光溜著長(zhǎng)腿,赤腳,立在橘色的夜燈下,扭身回首,看著鏡頭。我能通過(guò)飛舞的發(fā)絲、被吹得一干二凈的街面感受到照片里的風(fēng)。只有在這時(shí),一個(gè)人才會(huì)擁有城市。只有當(dāng)大家都放棄了對(duì)這里的占有,都打烊了,她才擁有了這條街道。和那些鬼魂一起。
我們又是約在白晝見面。她穿著淡青色的打底褲(不知怎么讓人想起行立的僵尸,有很多人在一些令人側(cè)目的顏色上建立起了怪異的安全感)、白色百花襯衫(印花和翻領(lǐng)都不錯(cuò)),背華倫天奴的包,戴Ssur黑底白字小帽子,著黑色耐克鞋。外套是一件牌子叫“事竟成”的藍(lán)色中年男士加厚夾克,應(yīng)該是她那將軍父親穿的。她這樣罩一件御寒的衣服,像是演員在冬天演夏日的戲,這會(huì)兒還沒叫到自己,且休息著呢。或是大病初愈,弱不勝衣。她看起來(lái)是如此怕冷,臉上卻又淌滿汗。汗水在化好的妝上犁開道道槽,新的汗又將這槽泥沖垮,因此滿臉黏糊,像是魚兒臨死前在這上面吐了很多泡,或是鳥兒拉了很多屎,又或是鋼筆尖刺入蛋清,藍(lán)黑墨水在里邊已有些洇開。渾濁的拖泥帶水的汗水沿著下巴尖滴下來(lái)。她一邊包緊自己的牙齦笑著,一邊用倉(cāng)促折好的“心靈手巧的小玩意兒”,一把小紙扇,扇著風(fēng)。“嗯……”我眼睛骨碌碌地轉(zhuǎn),望著她,嘴上支應(yīng)著,“這個(gè)……”有時(shí)實(shí)在說(shuō)不出什么來(lái),我就保持一種看似誠(chéng)摯的微笑,一邊端起咖啡杯將嘴湊向它,一邊貌似感興趣地抬眼看她,聽她說(shuō)話。此時(shí)我心中已洞明,當(dāng)初為何會(huì)金蟬脫殼,跑個(gè)沒影了。脫離實(shí)際的想象是個(gè)壞東西,是毫無(wú)原則的濫情主義者,它總是教唆主人做對(duì)他自己不利的事情,近距離觀察才是忠誠(chéng)而理性的仆人,總是本著負(fù)責(zé)任的態(tài)度告訴你底線在哪里,提防你犯錯(cuò)。為了尊重這名老仆的意見,我在歸來(lái)后,刪除與她的聯(lián)系方式,甚至加了黑名單。想想還棄用了這一QQ。雖說(shuō)她看起來(lái)就不是糾纏不休的人,我也沒什么把柄落(我喜歡北京人將它讀成là)在對(duì)方手里。事情就此終結(jié)。她就像一頭看似龐大的抹香鯨,孤獨(dú)地死在我記憶的腦海里,被腐食者及多毛類和甲殼類小型生物進(jìn)食4-24個(gè)月,悄然分解。我一生中要忘記很多這樣的人,經(jīng)過(guò)我的,我經(jīng)過(guò)的。幾百個(gè),成千個(gè),上萬(wàn)個(gè)。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你勸自己也沒辦法喜歡。
馬丁對(duì)發(fā)生在其表妹身上的悲劇(一些事之所以被定義為悲劇是因?yàn)樗鼘?dǎo)致了讓人追悔莫及的后果)的簡(jiǎn)明扼要的講述,讓我想起M.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里所寫的一句話:法蘭克公主被殺的當(dāng)夜,原來(lái)由金鏈吊在現(xiàn)在后殿那個(gè)地方的一盞水晶燈忽然脫鉤落下,燈罩沒有破碎,火焰也沒有熄滅,只是砸進(jìn)了石頭,燈的分量居然使頑石塌陷。2012年8月8日,一顆直徑700mm的花崗巖石球(有時(shí)它會(huì)被放在公園做景觀用,有時(shí)被放在小區(qū)要道當(dāng)車阻石)從天而降,有如急墜的隕石,將北五環(huán)一處人行道的地面砸碎,甚至使地皮起了一層漣漪。《京華時(shí)報(bào)》、《新京報(bào)》、《法制晚報(bào)》、《北京晚報(bào)》及稍后的北京電視臺(tái)“法制進(jìn)行時(shí)”節(jié)目對(duì)此事均有報(bào)道。很難界定這起墜石事件與丁婕妮臥床一事之間的關(guān)系,實(shí)際上它也成為法律的難題。
它當(dāng)然不是什么讖緯,不是什么芝麻灰色的圓球的墜降預(yù)示著她將遭受一場(chǎng)禍害,而是它直接就禍害到她。然而又不是這起碼有五百公斤重的石球直接將她砸得腦漿迸裂、脊椎粉碎性骨折或者索性將她拍成一張肉餅(這些形容都是她那激動(dòng)的表哥說(shuō)的)。它僅僅只是在距離她六七米開外的地方什么也沒傷著(除開那塊大理石地面)地落下。這是個(gè)在訴訟上毫無(wú)說(shuō)服力的距離。如果僅僅以此就支持前去討要說(shuō)法的丁婕妮的父親,那么整個(gè)北五環(huán)的人民都可以據(jù)此來(lái)討要損失。然而它帶給目擊者丁婕妮的精神損傷又是如此巨大:她感覺雙手的指尖像摸到光溜溜的球面,甚至感觸到其陰涼,然后她就被彈出去,像水珠濺開那樣,彈了出去。她坐倒在地,有幾天說(shuō)不出話來(lái),并且失禁。
從肉體上說(shuō),她毫發(fā)無(wú)損。然而精神之船(應(yīng)該說(shuō)她還是個(gè)小女孩啊,她的表哥這樣悲傷地評(píng)論)卻一勞永逸地被擊沉在水底。她情形日漸艱難,終致奄奄一息。她的父親數(shù)次向事故責(zé)任方提出索賠,他強(qiáng)調(diào)的是,無(wú)論如何,一個(gè)石球從樓上滾下來(lái)都應(yīng)該算作是安全生產(chǎn)責(zé)任事故。人家承認(rèn)了這點(diǎn),卻聲明這樣的安全事故和令愛令人遺憾的病情不存在什么因果關(guān)系,道歉可以,要說(shuō)賠償,一個(gè)子兒也甭想。丁父盛怒難平,索性到紀(jì)委舉報(bào)(他拍攝下對(duì)方辦公桌上有一包撕開待用的黃鶴樓1916香煙),誰(shuí)知還真把人家告下課了。也算是沒有空手而歸。“閨女啊,他不看好自己的職工,他的職工不看好樓上的球,導(dǎo)致你這樣,現(xiàn)在,他被免職了,永不錄用,你要早早地好起來(lái)。”他柔情似水地說(shuō),然而并不管用。
“她看起來(lái)不行了。”馬丁一邊纏著頭巾(他走車?yán)锍冻鲆粔K長(zhǎng)3米的黃褐色抹布,里三層外三層,斜著走頭上纏起來(lái),遮住耳廓上的傷口。要不要緊?要是要緊的話我就揍死他!車上那幫年輕人惡狠狠地問(wèn)他。這有什么要緊的他說(shuō))一邊說(shuō):“因此,我們找到你,你能理解么?”
“我理解。”我說(shuō)。
“你理解就好。”
他沒有說(shuō)得太明白的意思,下車后,由他舅媽,也就是丁婕妮的娘補(bǔ)全了。“你就是小牛啊,”她迎上前,端詳著我,一邊摸了我的左腕一下,“早應(yīng)該請(qǐng)你來(lái)的,(今天)請(qǐng)的方式不對(duì)。”
“沒有,沒有。”我說(shuō)。
此后一路的交談,她都恭敬地陪侍一旁,像衛(wèi)隊(duì)長(zhǎng)那樣謹(jǐn)守身份,保持著隨叫隨應(yīng)的姿態(tài)。我差不多也這樣。有時(shí),她會(huì)忍受不住好奇的滋擾,用余光窺測(cè)我(這個(gè)讓她女兒吃了不少感情的苦的男漢),就像她只是女兒的一門遠(yuǎn)親。她的眉毛掉光了,光光的磨得像鵝卵石一樣的額頭,下頭隱約保留兩條高聳的眉路。她如此瘦削,臉上卻沒存留什么刻薄的東西。我想是自許的高貴令她如此。她將發(fā)髻梳成羊角狀,額骨邊上一邊一個(gè)。向后梳理得干凈的頭發(fā)上搭著一塊讓人喪氣的類似洗碗布那樣的白色頭巾,它垂掛在雙耳旁,直達(dá)肩部,這使她看起來(lái)有點(diǎn)像斯芬克斯。她是穿著深紅色的睡袍出來(lái)迎接我們的。這地兒塵土飛揚(yáng),不知怎么讓我想起自己出生的鄉(xiāng)鎮(zhèn),有著雞屎、尚在調(diào)和中的水泥(鐵鏟還插在里邊)、難以忍受的暮色、穿大人衣服的小孩和那些需要他們不時(shí)吸回去的鼻涕。院落或平房有很多是紅磚砌的。到處是殘缺的水泥臺(tái)階,野草從罅隙處像旗幟一樣孤傲而愚魯?shù)厣L(zhǎng)。不過(guò)這里畢竟是京畿寶地,和我那南方的老家不可同日而論。讓我詫異的是,在她臉上呈現(xiàn)的一直是一股置身事外的冷漠,就像赴死的不是她的女兒,而只是鄰居家的誰(shuí),她只不過(guò)是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過(guò)來(lái)搭把手(興許,這就是緩慢的死亡與猝死之間的區(qū)別吧。據(jù)說(shuō)有時(shí)對(duì)死亡的等待太過(guò)漫長(zhǎng),親屬還會(huì)祈祝絕殺的時(shí)間早點(diǎn)降臨)。我感受著她身上的這股濃重的矜持與清高的氣息。正是這種自珍自愛、自我欣賞、自己生產(chǎn)、自己消化、悠然自得的態(tài)度,使她對(duì)世界采取了聽之任之的態(tài)度。即使——我想到一個(gè)惡狠狠的場(chǎng)面——惡魔齜牙咧嘴,橫眉瞪目,將她那正在凄厲叫喊的女兒活生生從她面前拉扯走,她也不會(huì)形諸聲色。她與她這具軀殼之外的事物完全撇清,保持著足夠遙遠(yuǎn)、遠(yuǎn)到任何泥水也濺不到她身上的距離。途中她隨意問(wèn)了一聲馬丁:怎么纏上布條?未等回應(yīng),她就又向我繼續(xù)介紹丁婕妮的病情。他回答說(shuō):“自從得了頭痛病以后……”她一耳兩用,接口道:“要真纏的話,你最好是用開司米頭巾。”接著她又對(duì)我稍微一笑,說(shuō),“他怪里怪氣的,我們且不用理他。”說(shuō)實(shí)在的,我很喜歡和她相處,因?yàn)閾Q做別的老娘,我不知道她會(huì)不會(huì)用鋒利的指尖掐住我的脖子對(duì)著我怒吼(都是你!都是你)。這種冷漠可能還有一種解釋,就是她還有別的后人。后來(lái)我從馬丁處探知到她果然有一子在巴黎第十一大學(xué)念書。她沒有將婕妮患病的消息告訴他。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啊,我長(zhǎng)嘆一聲,情有可原。
“以后(我指的是死亡這件事)也不告訴了嗎?”我問(wèn)。
“不知道。”馬丁說(shuō)。
丁婕妮罹患怪病后,先后在友誼醫(yī)院、安定醫(yī)院就治,后轉(zhuǎn)院至協(xié)和,最后從協(xié)和東院遷到西院,眼見著將病號(hào)服越穿越大。而自打本年入秋后,她就一次床也沒起過(guò),總是側(cè)躺著,失神地望著外邊。有時(shí)怕她得席瘡,給她翻身,才翻,她又艱難地自己翻回來(lái)。有時(shí)在她眼前晃動(dòng)手掌,她也不眨下眼,直到她自己覺得困乏了,才眨那么一下,用時(shí)比一次呼吸還長(zhǎng)。“說(shuō)起來(lái),我婕妮命怎么這么苦啊。”大概是覺得身為一女之母,多少得有些表示,因此這位母親抽出紙巾,擦起眼瞼來(lái),爾后小心疊好什么也沒打濕的紙巾,將它放回右側(cè)的小口袋,“我問(wèn)有得治么,醫(yī)生說(shuō)怎么說(shuō)呢,有,只是走這個(gè)科室出去的,也沒一個(gè)治愈的,只能說(shuō)是治,不能說(shuō)治好。你看現(xiàn)在——她吃了大量的激素,因?yàn)槌约に赜殖粤舜罅康拟}片,常常抽筋——她身體都吃變形了。該瘦的地方胖得不行,該胖的地方瘦骨嶙峋,就是一張皮搭在骨頭上。骨頭挑著皮。真惡心。”
“阿姨您別難過(guò)。”我忽然充滿想哭的欲望。我毫無(wú)察覺地抓住她的手,引它來(lái)摸我的臉,“您瞧,我也這樣,吃激素就是這樣,滿月臉。還有水牛背、向心性肥胖。您瞧我的肚子,已經(jīng)起來(lái)了,就像孕婦。我的腿還是像竹竿那樣瘦,肚子卻像是孕婦懷了六七個(gè)月的胎。”我說(shuō)。她抽回自己的手,冷漠地看了一眼我的肚腹。“你說(shuō)我的命怎么這么苦哦。”她補(bǔ)充道。然后繼續(xù)講述丁婕妮越來(lái)越糟糕的病情,就像是要用丁婕妮的病情來(lái)和我的病情賽跑一樣。因?yàn)閷?shí)在找不到有據(jù)可查的可對(duì)癥配制的藥方,每天就是為著預(yù)防感染而吊一些藥水,醫(yī)院決定讓丁婕妮出院。出院后丁婕妮像意識(shí)到自己被放棄,身體壞得快了,終于到了大咳不止的地步,有時(shí)眼見著死去了。“后來(lái)我們想起來(lái)什么——說(shuō)起來(lái)就像是一拍腦袋,啊,恍然大悟一樣,就過(guò)去問(wèn),婕妮啊,你有什么想說(shuō)的就說(shuō)吧,我們?nèi)マk。現(xiàn)在想起來(lái)她是多么害羞啊,都這時(shí)候了,她還是拖延了三天才告訴我們,她心里有這么一個(gè)男人,這男人就是你,小牛。”這冷靜的母親說(shuō)。
我對(duì)婕妮的這股子濃情[我想盡快走進(jìn)她最后退守或者說(shuō)被遺棄的臥房,坐在那注定已變灰的白色床單邊,拉起她骨瘦如柴的硬邦邦的手——啊,現(xiàn)在,她那張黑黃的皮一定顯得松弛,勉勉強(qiáng)強(qiáng)搭在弓起的肋骨上,也許胸部那里只剩兩顆干癟的比新疆葡萄干大不了多少的乳頭——久久而深情地望著她,告訴她,您所經(jīng)受的一切我都清楚,天父也清楚。我還要展示不久前我也做過(guò)的手術(shù),雖則只是微創(chuàng)手術(shù)。我將講述手術(shù)結(jié)束后提著引流桶(就像提著兩到三加侖的石榴汁)在醫(yī)院走廊走來(lái)走去的事情。引流管走腋下某處插進(jìn)身體,不時(shí)有污血或膿水自胸腔內(nèi)流出來(lái),滑進(jìn)那讓人欲哭無(wú)淚的閉式塑料桶。人啊就這樣悲哀地提著半桶子鮮紅的積液,去如廁,進(jìn)食,還有睡眠(醫(yī)生總是交代不要翻身)。還有就是解除麻醉,人醒來(lái)后總是問(wèn)同樣一個(gè)問(wèn)題,問(wèn)過(guò)還問(wèn),因?yàn)橛洃浟€沒恢復(fù)到正常水平。“現(xiàn)在,這里只剩下三兩處可恥的口子,像是生銹的鐮刀,”我噙著淚水,緊緊拉著她那失去力量的手,指點(diǎn)我身體右側(cè)所遺留的傷痕,“而且您看,因?yàn)榉帲乙呀?jīng)胖得不行了,我注定是要消失在這肥胖所決定的平庸中了。”接著我聽見另一個(gè)自己,嚯地站起來(lái),當(dāng)著她的面,無(wú)情地譏諷我:“朋友,難道您現(xiàn)在就很偉大么?”],隨著我穿過(guò)她家那早年刷了白漆因而現(xiàn)在愈加斑駁的院墻而頃刻消散。院內(nèi)這會(huì)兒聚集著許多本地農(nóng)夫,正抬著一個(gè)煩躁的人。話說(shuō)他們抬著他就像蟻群搬運(yùn)巨蟲。蟲向左傾,他們疾趨向左,向右,又齊奔向右,人人之間競(jìng)相提醒,一時(shí)喧嘩不已。“畜生!畜生!”我聽見那因?yàn)樽钄r而被抬到空中的男人舉起一柄漆黑的足有幾十斤重的斬肉斧對(duì)著我喊。我知道重量是因?yàn)樗谒斏匣蝸?lái)晃去,幾次要墜落下來(lái)。我頭腦一片空白。他就像得了瘋病,或者狂犬癥,正大口吐著唾沫朝我砍來(lái)。然而隨著我嘗試讓自己兩腿不要發(fā)抖,并且好好在這院子里站上幾秒,我就感到不那么害怕了。潮信雖兇,但只要我站在安全距離以外(我甚至可以用手去撩那浪尖),它就不能奈我若何。同理,強(qiáng)弩之末,勢(shì)(必)不能穿魯縞。我想到“將權(quán)力關(guān)進(jìn)籠子”這句話,目下這伙著藍(lán)色工服的農(nóng)夫的任務(wù)就是盡職盡責(zé)地將這條瘋狗關(guān)進(jìn)籠子。我還想到加西亞?馬爾克斯自認(rèn)為掌控得最好的那篇小說(shuō),《一樁事先張揚(yáng)的兇殺案》,“兇手千方百計(jì)找人阻止他們行兇,得到的卻是所有人的漠視、旁觀”。那真是一個(gè)巨大的諷刺啊,孿生兄弟最終為了讓自己看起來(lái)像一個(gè)說(shuō)話算數(shù)的人,不得不打起精神,將圣地亞哥?納薩爾,當(dāng)?shù)匾幻H有家業(yè)的年輕人,給辦了。我還想到法庭上一些受害者的親友,試圖沖破法警的包圍去毆打被告,然而沒有法警的話他們也絕不會(huì)動(dòng)手。我覺得我要是猛喊一聲,“這地上到底是誰(shuí)掉了一張一千塊錢。”那些一早就趕來(lái)服役的解勸者,定會(huì)撇開防護(hù)對(duì)象,跑地上尋找去了。屆時(shí),這憤怒的父親可就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興許還會(huì)跺腳罵他們。一想到這兒,我就禁不住為自己,也為他,這叫丁本領(lǐng)的老男人感到悲哀。您就演吧,我冷冷地看著他。不久,我見他果然節(jié)節(jié)敗退,像發(fā)動(dòng)機(jī)那樣無(wú)奈地熄火,只不過(guò)還要讓皮帶空轉(zhuǎn)幾圈。
“她就是讓你死,你也得死。”
“她說(shuō)什么你都得答應(yīng)。”
“肏你媽的。”
這些話都是他說(shuō)給我聽的,也可以說(shuō)是說(shuō)給他們聽的。我盡力表現(xiàn)得震怖懾服。然后隨著這股子恐懼消失,我倍感頭暈(剛才我就覺得有點(diǎn)頭皮發(fā)麻,我以為是被大斧頭給嚇的)。我聞到這伙人身上洋溢著一股嗆人的味道。而隨著一位熱情的中間人牽引我過(guò)去請(qǐng)罪,我又意識(shí)到,這令人恐怖的味道其實(shí)只濫觴于丁本領(lǐng)一人。就像走進(jìn)一間堆滿尿素的倉(cāng)庫(kù),我開始哭泣。當(dāng)我的睫毛不受控制地?fù)溟W時(shí),我依稀記起某部黑白電影里有一只被系住腿部的烏鴉,在受到驚嚇以后,瘋狂而徒勞地?fù)浯蛑岚颍ù龝?huì)兒我將借此東風(fēng)向他鞠躬:叔,都是我的錯(cuò)。)不一會(huì)兒,我就感覺渾身上下覆蓋了一層灰泥。就像雪夜過(guò)后仍滯留路邊的小客車,車身特別是車窗蒙上了一層黃色的泥團(tuán)。這世上一切的蒙冤者啊,我在心里悲嘆著。
我想起朋友們?cè)诰蹠?huì)上肆無(wú)忌憚地座談體味(包括深懷這門絕技的人):
——遇到一個(gè)人,那味兒,辣眼睛。
——嗆得人眼睛都睜不開(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噙著淚水)。
——分分鐘熏死你。
——被熏得肚子疼,回想的過(guò)程中嘔吐了。
——鄰村一人說(shuō)他高考時(shí)室友腳臭,其他人湊錢買香水,但抹上后更難聞。忍了兩天,大家一起落榜。
——我們迫于無(wú)奈在他的桶里噴了殺蟲水。
——立馬感覺一股味道撲面而來(lái),于是拿橙子皮放鼻子邊捂住。沒用,因?yàn)槭乔昂髪A擊。后來(lái)被嗆出眼淚,我沒下課便逃出去呼吸了。
——感覺一股塵土朝我卷來(lái)。
——嘔吐,眩暈,窒息。
——公交車,車窗拉開很大但外面一陣陣的風(fēng)更增加了這股味道的沖擊力。
——兼具厚重與尖銳的質(zhì)感。
——排隊(duì)時(shí),突然聞到一股餿掉的炒河粉味,正納悶,四處探尋,左邊的人往自己這邊靠近,那股味道更重了。然后就發(fā)現(xiàn)大家都在躲避那股味道,但是那個(gè)人卻渾然不覺。
——你上帝都大馬路上打幾十個(gè)出租車,就有感覺了。
——感覺呼吸道被灌進(jìn)糨糊,上不去下不來(lái),憋著。
——我一同學(xué),像是出生在化工廠里的。
——連她去過(guò)的公司衛(wèi)生間都留著濃郁的味道,你沒體會(huì),簡(jiǎn)直無(wú)法形容那種難受的感覺。
——熏得犯病,直咳嗽。
——推門進(jìn)去,嚯,都睜不開眼了。
——走出房間要抖三抖。
——盛夏來(lái)福州坐公交車,包你滿意。
——貴陽(yáng)公交歡迎你去體驗(yàn),不謝。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他們身上這種奇怪的味道,直到有一天我在超市發(fā)現(xiàn)一大堆促銷的洋蔥頭。那天我去晚了,沒遇到熱鬧的哄搶場(chǎng)面,但發(fā)現(xiàn)余下的接近腐爛的洋蔥頭,發(fā)出了同樣的奇怪味道。
——我老公呀,孜然味。
——小時(shí)候補(bǔ)習(xí)數(shù)學(xué),家教叔叔差點(diǎn)把我熏死在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