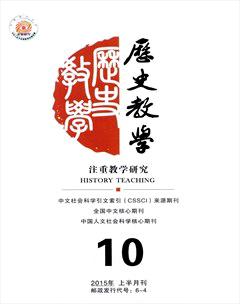抗戰(zhàn):中國復(fù)興樞紐
[關(guān)鍵詞]抗日戰(zhàn)爭,中國,中華民族,復(fù)興
[中圖分類號(hào)]G6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B [文章編號(hào)]0457-6241(2015)19-0023-04
九一八事變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剛剛統(tǒng)一不久的中國重新陷入分裂。而且,這一次分裂并不單純?cè)醋灾袊鐣?huì)內(nèi)部勢(shì)力沖突,而是嚴(yán)復(fù)所說的“這些廣闊的地域連同它的人民勢(shì)必要?dú)w屬附近的某個(gè)強(qiáng)國”。①中國不可能繼續(xù)按照蔣介石給出的路徑按部就班建設(shè)自己的國家。不過,出乎預(yù)料的是,巨大的外部危機(jī)帶來了巨大機(jī)會(huì)。九一八事變打開了中國復(fù)興之路。
事變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迅即召集緊急會(huì)議,決定動(dòng)員全體黨員深入民間發(fā)動(dòng)群眾,組織反帝大同盟,反對(duì)日本帝國主義占領(lǐng)滿洲。第三天(9月20日),處于國民黨軍隊(duì)“圍剿”狀態(tài)的中共中央就“日本帝國主義強(qiáng)暴占領(lǐng)東三省事件”發(fā)表宣言,譴責(zé)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號(hào)召人民拿起武器,以民族自衛(wèi)戰(zhàn)爭驅(qū)逐日本侵略者退出中國。從此開始,抗日救亡成為中國政治的主旋律。
但從那時(shí)中國政府的立場看,九一八事變確屬重大危機(jī),但中國是否由此就要與日本全面對(duì)抗,還是一個(gè)值得討論的問題。張學(xué)良、蔣介石究竟是誰主導(dǎo)了“不抵抗”還可以探究,不過正如那時(shí)許多知識(shí)精英所意識(shí)到的,日本帝國主義決不會(huì)容許中國從容地建設(shè)一個(gè)新國家。但這些知識(shí)精英在那時(shí),卻都又自然感覺出一種新的興奮,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顧一切,努力利用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間隙,好好建設(shè)自己的國家。
幾年時(shí)間,中國經(jīng)濟(jì)、國防,均有很大提升,沿江、沿海重要文化教育機(jī)關(guān),大型工業(yè)設(shè)施,可移動(dòng)的文化寶藏,中國政府也有相應(yīng)安排。這為后來全面戰(zhàn)爭奠定了一個(gè)比較扎實(shí)的基礎(chǔ)。
中方委曲求全并沒有換來和平,反而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日本操控的所謂“滿洲國”宣布其領(lǐng)土并不局限于東北,而是包括熱河省。此后,長城內(nèi)外就成了日軍蠶食對(duì)象,成為中日爭奪的戰(zhàn)場。
1931年1月3日,日本關(guān)東軍攻占山海關(guān),預(yù)示著日本將進(jìn)一步擴(kuò)大對(duì)中國的侵略。第二天,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嚴(yán)正抗議,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加緊進(jìn)攻熱河的準(zhǔn)備。2月13日,板垣征四郎奉命趕到天津設(shè)立特務(wù)機(jī)關(guān),密謀收羅張敬堯等成立華北偽政權(quán)。23日,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借口熱河省內(nèi)中國軍隊(duì)危及滿洲國的存在,要求中國軍隊(duì)立即退出熱河全省。不待中方回應(yīng),日軍于當(dāng)天向熱河發(fā)起進(jìn)攻,中國軍隊(duì)不戰(zhàn)自潰,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于3月3日棄城逃跑,使日軍僅以123人先頭部隊(duì)沒費(fèi)一槍一彈,如入無人之境,輕易占領(lǐng)了熱河省會(huì)承德。前后僅僅10天,熱河全省失陷。
熱河失陷,日本關(guān)東軍向長城以內(nèi)迅速推進(jìn),中國面臨“九一八”以來最嚴(yán)重的危機(jī),先前力主沉著應(yīng)對(duì)的知識(shí)精英終于坐不住了,以為再不抵抗,亡國就在[前。胡適1933年3月2日的一則日記,大致可以反映北平知識(shí)界的一般看法:
晚上到張學(xué)良將軍宅吃飯。他說,南凌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duì)合作,甚至危害軍隊(duì)。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熱河境內(nèi),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會(huì)派人去做點(diǎn)宣傳工作。
我忍不住對(duì)他說:事實(shí)的宣傳比什么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實(shí),我們?nèi)绾文馨l(fā)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huì)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duì)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shè)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說:湯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記在張漢卿先生的賬上。
張將軍只能嘆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里,那得不亡國?
十幾年前,我曾說:“中國不亡,世無天理。”今日之事,還有何說!
熱河淪陷,舉國一致譴責(zé)蔣介石、張學(xué)良,以及南京國民政府。3月7日,監(jiān)察院高一涵等6名委員,彈劾失職者張學(xué)良、湯玉麟,要求軍法嚴(yán)懲。為平息眾怒,也為了替蔣介石擔(dān)責(zé),張學(xué)良3月8日引咎辭職。
接替張學(xué)良暫代軍事委員會(huì)北平軍分會(huì)委員長的為何應(yīng)欽,何應(yīng)欽按照蔣介石的指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抵抗是為了給國人一個(gè)交代,以扭轉(zhuǎn)胡適日記中所說的那種傾向,讓人民留存一絲希望;交涉是因?yàn)橹袊牧α看_實(shí)不足以抵抗,雙方實(shí)力懸殊太大。
3月13日,胡適、丁文江、翁文灝等華北學(xué)術(shù)界領(lǐng)袖至保定謁見蔣介石。丁文江熟悉地理,深知熱河失陷后,北平即已無險(xiǎn)可守。而北平是一座具有1000多年歷史的文化古都,其意義非同小可,決不能讓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毀這筆人類文明財(cái)富。
學(xué)術(shù)界的意見引起了蔣介石的重視。事實(shí)上,蔣介石此時(shí)也沒有與日本對(duì)決的信心。有了學(xué)術(shù)界的意見,蔣介石更愿意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機(jī),暫時(shí)保全平津。4月9日,蔣介石致電黃郛,稍后任命他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wù)整理委員會(huì)委員長,指示他把握時(shí)機(jī)爭取與日本達(dá)成諒解,維持暫時(shí)的和平。
和平不易獲得,戰(zhàn)爭繼續(xù)進(jìn)行下去更困難。4月19日晚,正在北平指揮作戰(zhàn)的軍政部長何應(yīng)欽,在華北集團(tuán)軍第一軍團(tuán)總指揮于學(xué)忠陪同下,與胡適、蔣夢(mèng)麟、丁文江等學(xué)術(shù)領(lǐng)袖座談,鄭重討論怎樣才能結(jié)束戰(zhàn)爭,重建和平。鑒于當(dāng)時(shí)的情況,他們希望與日本達(dá)成停戰(zhàn)協(xié)議以換取必要的準(zhǔn)備時(shí)間。他們建議由蔣夢(mèng)麟以私人身份往訪英國公使藍(lán)浦生,詢問英國能否居間調(diào)停。他們提出的條件是:調(diào)停只限于停止雙方的敵對(duì)形勢(shì),不涉及東三省或其他問題,并且只作口頭而非文字上的協(xié)議。
蔣夢(mèng)麟與藍(lán)浦生的交涉并沒有結(jié)果,但5月31日,中日雙方達(dá)成《塘沽協(xié)定》。根據(jù)這個(gè)協(xié)定,中國軍隊(duì)繼續(xù)后撤,實(shí)際上承認(rèn)了“滿洲國”,承認(rèn)長城是中國的北部邊界。這個(gè)協(xié)定一方面保全了華北尤其是平津暫時(shí)不受日軍破壞,為幾年后全面抵抗贏得了時(shí)間。另一方面,這個(gè)協(xié)定讓綏東、察北、冀東,成為日軍自由行動(dòng)區(qū),為日軍進(jìn)一步控制華北提供了便利。
就中國全局而言,《塘沽協(xié)定》是一個(gè)屈辱協(xié)定,但其一方面激活了國內(nèi)民族主義情緒,為兩年后一二·九運(yùn)動(dòng)、3年后西安事變、4年后盧溝橋事變積蓄了動(dòng)能,另一方面為切實(shí)進(jìn)行戰(zhàn)爭準(zhǔn)備發(fā)布了一個(gè)實(shí)際上的動(dòng)員令。此后的中國,大致進(jìn)入一個(gè)“準(zhǔn)戰(zhàn)爭狀態(tài)”,讀蔣夢(mèng)麟《西潮》很容易感覺那時(shí)在華北地區(qū)繼續(xù)堅(jiān)守的知識(shí)人,通過長城抗戰(zhàn),都比較清楚中日決戰(zhàn)不會(huì)很遠(yuǎn)了。
1935年11月19日,蔣介石有一個(gè)政策宣示,強(qiáng)調(diào)和平?jīng)]有到絕望時(shí)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guān)頭,亦不輕言犧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犧牲有犧牲的決心,以抱定最后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dá)奠定國家、復(fù)興民族之目的”。顯然,朝野各界對(duì)日漸趨強(qiáng)硬,中日全面沖突,以戰(zhàn)爭決勝負(fù)只是一個(gè)時(shí)間問題,只等待一個(gè)契機(jī)。
20天后,在北平爆發(fā)了蔣夢(mèng)麟所說的七七事變前7年唯一一次大規(guī)模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這個(gè)被后來命名為一二·九運(yùn)動(dòng)的政治事件,極大促動(dòng)了中國人的覺醒,中國社會(huì)各界放棄幻想、準(zhǔn)備戰(zhàn)爭的情緒漸趨上風(fēng)。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撤回關(guān)內(nèi)五六年的東北軍不堪繼續(xù)忍受“不抵抗”而丟失東北的歷史指責(zé),他們寧愿血染沙場,也不愿繼續(xù)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1936年12月12日,張學(xué)良、楊虎城在西安發(fā)動(dòng)兵諫,扣押親臨前線督戰(zhàn)“剿共”的蔣介石,以“兵諫”的方式要求蔣介石放棄內(nèi)戰(zhàn),領(lǐng)導(dǎo)抗日。
在共產(chǎn)國際、中共介入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成為中國政治的新希望,包括中共在內(nèi)的中國社會(huì)各階級(jí)普遍擁戴蔣介石為抗日最高領(lǐng)袖。這是一個(gè)歷史性巨變,表明中國人已走出先前十年自相殘殺的歷史,兄弟睨于墻共御外侮,中華民族全面抵抗只等待一個(gè)命令。
半年后,盧溝橋事變發(fā)生。二十九軍將士奮起抵抗,這是抗日自衛(wèi)戰(zhàn)爭的起點(diǎn),甚至可以說是東方及太平洋地區(qū)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起點(diǎn)。10天后(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fā)表談話,表示中國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zhǔn)備應(yīng)戰(zhàn),而決不求戰(zhàn)。盧溝橋事變的推],關(guān)系中國國家整個(gè)問題,此事能否結(jié)束,就是最后關(guān)頭的境界。事變能否不擴(kuò)大為中日戰(zhàn)爭,全系日本政府的態(tài)度;和平希望絕續(xù)的關(guān)鍵,全系日軍的行動(dòng)。蔣介石鄭重宣布: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中國依然希望和平,但“如果戰(zhàn)端一開,那就是地?zé)o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zé)任”。蔣介石廬山談話,確定了準(zhǔn)備抗戰(zhàn)的國家戰(zhàn)略,迅速贏得中共,以及云貴川等地方實(shí)力派支持,中日全面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
其實(shí),據(jù)后來研究,蔣介石廬山談話以強(qiáng)硬姿態(tài)所要達(dá)到的目標(biāo)并不是戰(zhàn)爭,而是和平。但這個(gè)談話并沒有被日本政府準(zhǔn)確解讀,日本不僅沒有和平解決盧溝橋危機(jī)的誠意,反而持續(xù)向平津增兵。26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向中國守軍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全部撤出平津地區(qū)。宋哲元嚴(yán)詞拒絕,并向全國發(fā)出自衛(wèi)通電。日本政府也不示弱,增調(diào)20萬軍隊(duì)至平津。28日,日軍按計(jì)劃向北平發(fā)動(dòng)總攻。29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失守。此后一年,從北到南,從東到西,中國軍隊(duì)在正面戰(zhàn)場進(jìn)行頑強(qiáng)抵抗,用行動(dòng)粉碎了日本迅速戰(zhàn)勝中國的夢(mèng)想。
日本不僅沒有力量迅速征服中國,相反,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激活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中華民族經(jīng)過這場戰(zhàn)爭洗禮,鳳凰涅■,浴火重生。這場戰(zhàn)爭因此成為“中國復(fù)興樞紐”。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中國已被各種分離主義勢(shì)力弄得四分五裂,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分離主義運(yùn)動(dòng)依然沒有停止,顧頡剛在《中華民族是一個(gè)》中說:“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為撣族故居,而鼓動(dòng)其收復(fù)失地。某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nèi)之土司,近更收納華工,志不在小。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禍。”近代以來最美好的政治名詞“民族”,竟然一變而成為分裂主義的借口。
中華民族是一個(gè),是中國歷史的事實(shí),也應(yīng)該是中國政治的現(xiàn)實(shí)。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的中國歷史學(xué)家、思想家,竭盡全力論證滿洲自古以來屬于中國,論證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gè)包容性超強(qiáng)的民族,是一個(gè)整體,而不是多民族搭起來的積木。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顛沛流離之際撰寫《中國歷史講話》,倡言五族同源,以為:“中華民族,由漢滿蒙回藏五族構(gòu)成之。故分言之,則有五族;統(tǒng)稱之,則唯華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則有伯仲;統(tǒng)稱之,則是一家骨肉也。”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個(gè)大家庭。分言之,中華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言之,五族就是中華民族的內(nèi)涵。這是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思想界的一大貢獻(xiàn),也是民族危機(jī)空前時(shí)刻所尋找到的重要思想資源。由此,中國人方才有理由堅(jiān)信:“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歷史依據(jù)的充實(shí),是一個(gè)民族不會(huì)被輕易打敗的根底。
“中華民族是一個(gè)”的討論,引起進(jìn)步知識(shí)界的積極回應(yīng),繼傅斯年、顧頡剛之后,白壽彝、楊向奎、翦伯贊、吳文藻、費(fèi)孝通等學(xué)者都有相關(guān)文章發(fā)表,他們的討論是對(duì)近代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反撥,是對(duì)中國文明傳統(tǒng)的復(fù)歸,至抗戰(zhàn)勝利,中國人的民族意識(shí)有了很大提升,抗戰(zhàn)前、抗戰(zhàn)中以“民族自決”為幌子的分離主義運(yùn)動(dòng)漸趨結(jié)束,“中華民族”的概念至此終于成為中國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認(rèn)同。抗日戰(zhàn)爭既是中華民族全體一致的抵抗,也是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重構(gòu)中的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
空前危機(jī)帶來空前機(jī)遇。一盤散沙的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刺激下振作起來了,正像顧頡剛1935年《旅行后的悲哀》所意識(shí)的那樣,如果沒有日本武裝侵略帶來的劇烈沖擊,中國或許將在渾渾噩噩中度過,慢慢地被民族主義、分離主義消解,“二三十年之后,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現(xiàn)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diǎn)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chǎn)業(yè),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斗力,使得我們這一點(diǎn)希望能夠化成事實(shí),這是一個(gè)極好的機(jī)會(huì)”。
一個(gè)全新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經(jīng)抗日戰(zhàn)爭一役得以確立,中華民族不僅沒有被打敗,反而經(jīng)此刺激浴火重生,鳳凰涅。
【作者簡介】馬勇,男,安徽淮北人,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研究方向?yàn)橹袊贰?/p>
【責(zé)任編輯:吳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