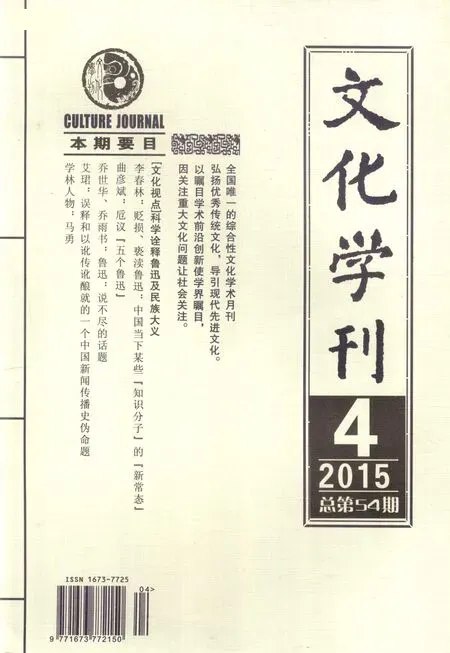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角下的生態價值觀研究
楊海燕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035)
生態批評視角下的生態價值觀研究
楊海燕
(大連職業技術學院,遼寧 大連 116035)
生態困境直接催生了生態批評思想的問世,迫使人類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深刻反思人們行為的價值取向。生態批評認為,生態問題不僅出現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同時也發生在精神領域里,人的生態與人的心態密切相關,生態問題的解決首先有賴于人類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取向,生態價值觀作為一種精神因素,將為生態文明建設注入新的推動力和活力。
生態批評;生態價值觀;大地倫理;詩意的棲居
現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比較中印歐三大文明特征時說,人這一生總要解決三大關系,而且順序是不能錯的。首先要解決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其次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最后一定要解決人與內心之間的關系(梁漱溟)。這一命題恰好也是生態批評思想的宗旨和任務。生態批評認為,只有妥善處理人與自然(物)的關系,其余的兩個關系,即人與人、人與自我(內心)之間的關系才會有解決方案。
縱觀人類社會文化歷史的發展進程,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視線就不曾中斷過。由于人類不合理的行為活動,人類物質與精神價值取向的顛倒,導致生態系統的破壞和生態危機,人的生存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可以說,生態困境直接催生了生態批評思想的問世,迫使人類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深刻反思人們行為的價值取向。由此,生態批評者指出,人的生態與人的心態密切相關,生態問題的解決首先有賴于人類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取向,生態價值觀作為一種精神因素,將為生態文明建設注入新的推動力和活力。
一、“寂靜的春天”:生態價值觀的里程碑
《寂靜的春天》(1962)一書通常被視為是生態批評浪潮中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生態價值觀創立的一個里程碑。這部劃時代的著作“改變了歷史進程”,“扭轉了人類思想的方向”,[1]開創了生態時代的新文明,一場聲勢浩大的現代生態保護運動應聲而起。
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是一名海洋生物學家、生態作家,以其代表作《寂靜的春天》拉開了生態革命的序幕。《寂靜的春天》主要描述了使用化學藥劑對生物的危害以及對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動物、植物的影響與人類之間的密切關系。春天本應是一片萬物復蘇、郁郁蔥蔥、生意盎然的生動景象,但在《寂靜的春天》里,由于人們濫用殺蟲劑的結果,到來的春天卻是死寂沉沉,沒有百花爭艷、沒有鳥語花香,一切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通過這個寓言,卡森警示人們,倘若繼續濫用這些“死神靈藥”會影響整個生態系統,一個無鳥鳴唱的“寂靜的春天”會不期而至。
《寂靜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實和科學依據揭示了濫用殺蟲劑對生物界、自然界的破壞和對人類健康的損害,抨擊了這種依靠工業技術來征服、統治自然的生活方式、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念。“當人類向著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標前進時,他已寫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壞大自然的記錄,這種破壞不僅僅直接危害了人們所居處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與人類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2]
在西方的文化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它充滿著整個精神文化空間,即認為科學是知識和真理的至高權威。1687年,牛頓完成了宏大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用英國哲學家 A.N.懷特海的話,就是整個世界進入了“嶄新的時代”,即工業時代。然而,牛頓的宇宙觀和世界觀是機械的、工具的,他認為自然世界是一種客觀存在,大自然是為了人類利益而存在的,人完全可以憑借著科學來征服和統治這個世界。始于 17世紀啟蒙運動倡導的理性主義,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和諧圖景完全被打破了,一個有機統一的世界被分裂開來。在啟蒙運動之光的照射下,人類憑借著理性知識,憑借著科學技術的無窮力量,向大自然展開了全面的進軍。18世紀的西方產業革命帶來了物質的富庶、繁榮,也帶來了環境災難、資源貧乏和人口膨脹等生態問題。從17世紀以來笛卡爾和牛頓開始的機械的自然觀,人類成了自然的主人,人類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對自然肆意掠奪,最終把人類自己置于空前的生態困境之中。
《寂靜的春天》之所以成為一部偉大的生態批評文本,不但是因為卡森揭示了殺蟲劑對生物和人類的危害,更大的原因是她對人類控制自然提出了質問,質疑了科學技術社會對自然的基本態度,指出“隱藏在干預和控制自然的行為之下的危險觀念”,她說,“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哲學觀點,放棄我們認為人類優越的態度”,[3]因為人們的生存受到威脅不是來自于自然世界,而是人類對大自然所抱有的那種傲慢、無禮和狂妄的態度和行為所導致。卡森試圖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原有的自然觀、哲學觀,建立起全新的生態思想和生態哲學觀。
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大自然的淡出和缺席已成了此后社會文明中一切缺憾的根源,卡森和她的《寂靜的春天》對改變人類傲慢的自然觀和世界觀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正如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談及到《寂靜的春天》時所說的那樣,“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4]自 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人類面臨的生存困境日益緊迫,生態批評家、生態思想家和生態倫理學者把人類對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觀念的歷史性反思和哲學批判一直觸及到《圣經》,美國生態學家、史學家林恩·懷特一針見血地指出,“猶太—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5]人們當今所面臨的生態問題,是自啟蒙運動和工業文明以來,支配自然、違背自然規律、干預自然進程、破壞生態平衡的必然結果,人類自己應當做出深刻的反思,人類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應當改變。
二、“大地倫理”:生態價值觀的哲學思考
全球性生態危機的出現,具有深刻的認識論和價值論的思想文化根源。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不僅作為一種理論選擇具有現實的和策略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哲學倫理學或價值論上的合理性。早在《圣經》“創世紀”第一章里就這樣寫到:“凡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都必須驚恐懼怕你們。連地上一切昆蟲并海里的一切的魚,都交付你們手中。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為你們的食物,如同我賜給你們的蔬菜。”在這里,“人類中心”,“人類至上”,人類與自然的對立、對抗全都被這位“上帝”敲定了。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體系中,自然界是非人類的,只具有工具價值,它本身沒有獨立于人類的價值,是一個沒有內在價值的客觀存在,它被人類利用,受人類驅使,任人類宰割是理所當然的。
在以理性和技術至上的啟蒙精神的指引下,人們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對大自然攻掠式的無度開發,毀壞一個物種就像撕掉一張紙那樣隨意,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是和諧統一的、相互依存的,而是緊張、對立的關系。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的辯證法》中,針對啟蒙運動導致的人與自然相對立的理性文明,提出了批判和質疑。他們運用辯證的方法,指出了啟蒙運動已經走向了它的反面。他們認為,“人對自然工具性的操縱不可避免地產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類把“自然界貶成了統治的對象,貶成了統治的原料”,[6]人類實際上就把自己貶成了統治的對象和原料。
在工業文明的進程中,恩格斯就向人們提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取消了。”[7]自然界與人的全面價值關系,如生命價值、審美價值、倫理價值等,都被碾壓在工業文明的滾滾的車輪中。可見,生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科學技術的問題,更是一個信仰問題、審美問題、哲學問題和倫理問題。最根本的還在于改變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即改變人們的機械的還原主義的世界觀,建立整體的、多樣性的、生態的世界觀,以及相互聯系的價值觀。
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美國生態思想家,是生態整體主義的理論創始人。他的遺著《沙鄉年鑒》(1949)被譽為是“現代環境主義運動的一本圣書”。該書的最后一章“大地倫理”,通過探討人類與大地的關系,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生態中心論的環境倫理學,顛覆了以往只有人類之間才存在倫理的觀點。
大地倫理的宗旨是人們要從道德上關懷大地,利奧波德指出:“我不能想象,在沒有對大地的熱愛、尊重和敬佩,以及高度贊賞它的價值的情況下,能夠有一種對大地的倫理關系。”[8]他從生態整體利益的高度,去檢驗每一個問題,去衡量每一種影響生態系統的思想、行為和發展策略。他的大地倫理的檢驗標準是“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9]利奧波德把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視為最高的善,最高的道德觀,他從倫理維度上為生態意識和生態價值觀奠定了哲學基礎。
大地倫理認為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自然萬物都擁有自己的價值和意義,都擁有自身存在的權利,它們之間存在著普遍的相對相關的聯系。如果說在這個生命共同體當中,人類是最高生物,那也只意味著人類對于維護自然在整體上的完善、完美承擔更大的責任,對保護生命共同體的完整性、多樣性擔當更多的倫理和道德責任。而這正是現代西方工業社會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所缺乏的東西,因為現代工業文明在高揚人的主體性的同時,造成了人和自然的深刻的分離和對立。大地倫理則要改變這種理所當然的價值哲學思想,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觀。人類是大地的一個成員,而不是凌駕于大地之上的統治者。
大地倫理把倫理的邊界從個人推及到共同體,要求人們“熱愛、尊重和贊美大地,高度評價它的內在價值”。利奧波德的這個主張得到了生態哲學家和環境倫理學家的擁護。阿爾貝特·施韋策發出泛愛萬物的感想,“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陽光下的冰晶,不摘樹上的樹葉、不折斷花枝,走路時小心謹慎以免踩死昆蟲。”[10]漢斯·薩克斯在他的《生態哲學》一書中寫到,“把人視為宇宙的中心,這種學說雖然容易讓人理解,但這畢竟是一種粗糙的推斷。對自然的考察使我們詳細地看到人是整體中的一個成員。整體怎能只為其中眾多成員中的一個而存在,即使這個成員是最杰出者?把人類視為宇宙中心之說完全忘記了自然。”[11]R.F.納什在《大自然的權利》一書中指出,大地倫理“把一種至少是與人相等的倫理地位賦予了大自然。它的對立面是‘人類中心主義’,后者認為人類是所有價值的尺度”。[12]大地倫理給人們的啟示就是,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應當受到尊重,甚至大自然的一切,包括山脈、河流、天空、大地在內都體現了宇宙間一種神圣的和諧,它們的存在都應當受到尊重,它們的完整性、穩定性都應當受到維護。
三、“詩意的生存”:生態價值觀的實踐
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把人從外在的自然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同時,也使人的內在自然受到工具理性、科技設置和組織管理的奴役,人的思想、精神、個性、感性深受壓抑和扼制。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人們面臨的最大的困惑或焦慮,莫過于自我認同的危機。不斷變化和日益模糊的參照系,使人們很難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難把握到一個相對穩定的“自我”,人與自然天然統一的紐帶被切斷了,人成了無根基的存在,普遍帶有一種“被連根拔起的感覺”。科技的發展、人的異化擾亂了人們的價值活動,倫理價值被剝奪了普遍的有效性。
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導致了社會偏重于理性和理智、偏重于技術和工具、偏重于概念和規則,人們變得越來越趨于物質、技術、使用、功利,越來越重視眼前的和現實的利益。人們不再追求價值理性——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目標。人們更多的是表現出工具理性的行為,即只顧眼前的和現實的利益和需要。西方馬克思主義流派代表人物之一馬爾庫塞指出,當代技術的發展同時意味著統治人的力量的發展,物質生活條件已成為外在的強制性力量。
價值理性的萎縮使得人們不再扼守道德、審美、宗教的原則,眼前的、現實的利益高于一切。價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消解則意味著人文精神受到冷落、遭到排擠,在衰落。人類要高揚價值理性的大旗,只有人類徹底改變對自然的態度,才能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才能去矯正被扭曲了的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關系,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看來,重整破碎的自然與重建衰敗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人與自然相處的最高境界是人在大地上“詩意的棲居”。
“詩意的棲居”對于人們來說是一種生態價值取向的生活,是踐行價值理性,因為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充實可以削減對外在物欲的追求,精神能量的升華可以替代物質能量的流通,是人類有可能選擇的最友好、最可行,也是最“低碳”的生存方式。人與萬物擁有一個自然世界,人類只是這個大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人類是其中進化的最好的生物,那就更應該懂得人類要與自然保持一種平等、友好、親切的關系,而不是蔑視、敵對、緊張的關系。人類要想長久的生存和發展下去,就要調整自己的行為方式,對于大自然的任何索取都要謹慎為之,學會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保證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符合自然規律。
提及到“詩意的棲居”,人們自然要想到美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梭羅和他的名篇《瓦爾登湖》。梭羅對自然的虔誠態度,他對自然萬物的細微觀察,他對自然給予人的精神營養和審美價值的贊嘆,以及他對他那個時代所流行的物質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批判,都為人們詩意的筑居、詩意的棲居和詩意的生存提供了獨特的靈感和支持。
梭羅的《瓦爾登湖》(1854)則是生態價值觀的一個具體的實踐。1845-1847年間,梭羅獨自來到了瓦爾登湖畔,在他的小木屋里度過了兩年多的隱居般的生活。每天他徜徉在瓦爾登湖畔,沐浴在陽光下,觀察、思考、閱讀、記錄大自然的點點滴滴的變化。湖里銀光閃閃跳躍的魚兒,大地上奔跑的各種動物,如松雞、野鴨兔子、土撥鼠等都是他的伙伴。在物質生活上,梭羅過著最簡單、最簡樸的原始般的生活,自己種菜,有時靠打點零工支付每個月最基本的生活費,但在精神生活上,梭羅是富有的、滿足的、恬靜的。作為一位自然闡釋者,梭羅通過自己親身的實驗,以詩意般的語言把大自然的美麗、動人和他對自然的深厚感情都寫進了他的《瓦爾登湖》。
就像許多西方生態批評學者從東方哲學汲取營養一樣,梭羅本人也深受中國“天人合一”的生態哲學觀的影響,他的《瓦爾登湖》就是中國古典詩詞中所描述的人和自然相伴相生的現代寫照。“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描繪出萬物生機勃勃、錚錚向榮的景象。春末夏初,飛奔的野雉,飽滿的蠶繭,荷鋤而歸的農夫勾勒出天、地、人那么和諧、優美、令人神往。也許有人會說,這種古代農業文明已是蹤跡難尋的往事,但現代人恰恰缺乏的是對自然體貼入微的親近,在自然之母面前,變得冷漠、麻木不仁,對大自然的贈予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梭羅的《瓦爾登湖》告訴現代人,自然不僅給予人類豐富的物質,還可以凈化人們的靈魂,撫慰人們的精神。同樣,這樣的哲思也見諸于中國古典詩詞中:“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山林中這位隱逸者,如同梭羅一樣,置身于大自然中,完全可以拋棄個人的名利、虛榮和欲望,聞到大地的芬芳便滿懷喜悅了,完全是一種詩意的棲居。人們的這種生態價值取向的生存方式,正是體現了馬克思的斷言,“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13]
“詩意的生存”可以幫助人類這個最后可能打亂生態系統的物種進行自我節制、自我約束,順應自然、敬畏自然,回歸自然、親近自然;而“詩意的棲居”就展現在美國生態學家艾倫·杜寧為人類提出的五個“回歸”的設想當中:“接受和過著充裕的生活而不是過度地消費,文雅地說,將使我們重返人類家園,回歸于古老的家庭、社會、良好的工作和悠閑的生活秩序;回歸于對技藝、創造力和創造的尊崇;回歸于一種悠閑的足以讓我們觀看日出日落和在水邊慢不得日常節奏;回歸于值得在其中度過一生的社會;還有,回歸于孕育著幾代人記憶的場所。也許亨利·戴維·梭羅在瓦爾登湖邊告訴了人們一個真諦:‘一個人的富有與其能做的順其自然的事情多少是成正比’。”[14]
四、結束語
啟蒙主義曾讓人類驕傲地認為他可以戰勝自然,取代自然,高踞于自然萬物之上,工業文明給人類社會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卻破壞了生態系統,造成了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技術與情感、智慧與良心的割裂與對抗。以卡森《寂靜的春天》為標志的現代生態運動的興起,使現代社會中一路飆升了三百多年的科學技術的地位受到質疑,生態文明正是對啟蒙理性主義至上、科學技術主義至上、工具理性至上的反思,審視與批判。信仰的執著、哲學的反思、詩意的生存再度喚起人們對于生命的敬畏,對于自然的親近,對于倫理價值的思考。大地倫理強調大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人與自然萬物是一種平等關系,是來自一個大家庭的親情關系,它體現了人和自然地和諧、協調與一致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而這正是生態價值觀所具有的超時代的價值觀。

泥模藝術——喂豬
[1][3]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227.293-294.
[2][4]雷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M].呂瑞蘭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87.
[5]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Cheryll Glotfelty&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6- 14.
[6]霍克海默,阿爾多諾.啟蒙辯證法[M].洪佩郁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35.
[7]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8.
[8][9]奧爾多·利奧波德.沙鄉年鑒[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216
[10][12]R.F.Nash.大自然的權利[M].青島:青島文藝出版社,1999.73.9.
[11]漢斯·薩克斯.生態哲學[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59.
[1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9.
[14]艾倫·杜寧.多少算夠[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3.
【責任編輯:王 崇】
I0-05
A
1673-7725(2015)04-0226-06
2015-03-06
楊海燕(1956-),女,教授,主要從事英美文學、西方文論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