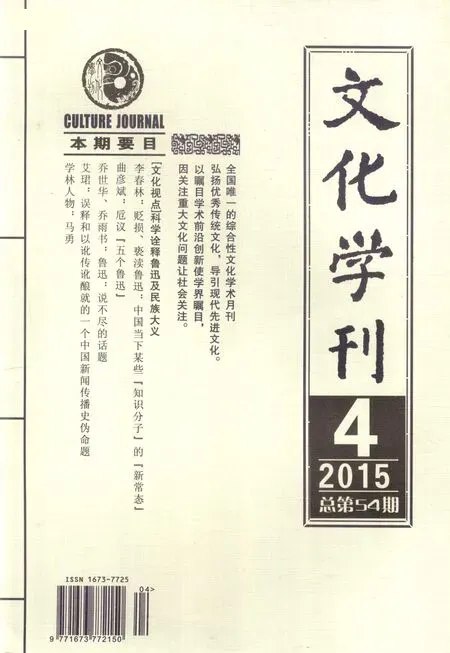外軍形象文學建構
陳月豐
(廣州軍區75906部隊,廣東 廣州 510540)
外軍形象文學建構
陳月豐
(廣州軍區75906部隊,廣東 廣州 510540)
外軍形象在軍旅文學創作中長期存在,但長時間沒有被納入軍旅文學研究的范圍。實際上,外軍形象文學體現了軍旅作家對外軍的想象和對現實世界的判斷,但客觀上卻存在創作局限性和不足的狀況。
軍旅文學;外軍形象;現代化
作為當代文學的重要板塊,軍旅文學在重現革命戰史、書寫軍人群體等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六十多年來,軍旅文學在不同歷史階段塑造了難以計數的人物形象,從不同角度折射或再現了中國軍隊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其中,外軍人物雖未能如我軍英雄形象一般層出不窮,令人印象深刻,但仔細觀察其衍變過程,仍不難顯現出外軍軍旅創作文化內涵的潛在變動。
一、軍旅文學中外軍形象的基本風貌
外軍形象在軍旅文學中的出現,幾乎與軍旅創作的興起同步。1949年以來,《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取材于抗日戰爭的長篇小說中就不乏作為侵略者的日軍形象,這些言語粗俗、行為殘暴的鬼子形象隨著小說、戲劇、電影等衍生藝術形式傳播給受眾。這類形象特點鮮明而固化,承載并有效利用了民族的抗日歷史,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相當一段時間內軍旅作家思考與創作的維度。這種創作景致初見改觀是在“文革”結束之后,相對得到更多關注與贊許的是徐懷中的短篇小說《西線軼事》,小說以1979年我國第一次對越自衛反擊戰為背景,描寫六個女電話兵和一個男電話兵的部隊生活,重點塑造了干練機警的女兵班長嚴莉和沉默聰明的女兵戰士陶坷的感人形象,這部小說為軍事文學的發展開拓了一條新的道路。徐懷中在另一篇取材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阮氏丁香》中,相當少見地塑造了一位被俘的越南女軍人形象。作者對小說敘事節奏的精準把握,對女俘心理的傳神捕捉,都是此前軍旅文學創作所匱乏的,同時也從側面印證和折射了社會與文學的雙重變革的到來。
上世紀 80年代,集中筆力在外軍“園地”進行開掘與創造的要首推劉亞洲。借助報告文學這一當時走俏文體,劉亞洲將一股域外新風引入當代文壇,特別是軍隊、軍人的另類視野。蛙跳攻擊、特種作戰等自他肇始的詞匯和概念至今仍在被廣泛使用。其長篇小說《兩代風流》在全面再現當時部隊大院和軍人生活之余,通過對個性剛愎的巴索夫將軍細致入微的刻畫透射出當時大國角力的復雜態勢,較早并充分展現了劉亞洲在創作之中的杰出才思。
通過對革命歷史的重新闡釋、對和平時期軍營現實的深刻發掘,軍旅在世紀之交迎來“第四次浪潮”,外軍形象也由此逐漸摒棄了“鬼子化”“敵寇化”的傳統套路,尤其以書寫軍隊強軍變革的長篇小說最為突出,軍旅作家在著力對接現實軍營,塑造新世紀強軍英雄之余,似乎不時浮現出為之尋找境外“標靶”的沖動。一為“假想敵”,他們往往頗具實力,作為強軍英雄的對手出現,如《明天戰爭》中的考夫特,《賭下一顆子彈》中的帕特遜,《沙場點兵》中的弗斯特等,他們在與強軍英雄接觸交往時不免咄咄逼人,但又不乏惺惺相惜之情;二為“新朋友”,他們同樣自信滿滿,短暫接觸后就跨越語言障礙,并與強軍英雄引為同道,如《超越攻擊》中的安德烈,《利劍》中的阿廖沙等,這種情誼相對簡單而直接。這些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未必會占據較大比重,但對展現強軍主題、調控敘事節奏等具有重要價值與意義。
新時期以來軍旅文學中外軍形象不斷迎來新變,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對外開放形勢使然。國門既開,各種理論、信息自西方劈面而來,軍旅作家們從內在理念到創作實踐都受到強烈沖擊,不少人出于職業特性支配,接觸并了解到外軍動態,轉而思考中國軍隊規模龐大卻落后的原因,內心油然滋生出頗為濃烈的改革之念。他們開始嘗試將眼光投諸世界范圍,將所思、所想、所推崇的軍隊改革融于創作之中,并借此達到傳播火種、引發反響的目的。劉亞洲在上世紀 80年代連續發表《攻擊,攻擊,再攻擊》《惡魔導演的戰爭》《這就是馬爾維納斯》等作品,頗為罕見地對沙龍、尼坦雅胡中校、伍德沃德將軍等進行了贊許式描述,這些外軍形象可以算作軍旅文學人物的“新人”,他們甚至與中國、中國軍隊并無瓜葛,卻扮演著合乎時宜的他山之石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是軍隊現實的間接影射。隨著軍隊與外國、外軍交流的發展,聯合軍演、海外維和、外派留學、參觀訪問等涉外活動大幅增多,自然會對軍旅作家創作產生影響。苗長水的《超越攻擊》就直接將中俄聯合軍演設為敘事的背景成分。這其中或許有作家的自主選擇,但大的時代背景的作用不可忽視。
二、軍旅文學中外軍形象的總體特征
軍旅文學中外軍形象具體可感,體現出軍旅作家對外軍的想象與言說。這些外軍形象中,如層出不窮的日軍形象,近年來依然保持著受眾熟悉的“鬼子化”風格,而著意于強軍改革的作品中的外軍形象則大多帶有對比映襯的職能。綜合分析相關作家的人生經驗與創作過程,不難發現,其中大部分作家現實中未必與外軍有過直接接觸,其經驗獲得與創作實踐主要得益于報刊雜志、電視網絡、采風觀摩等渠道。這些外軍形象雖是軍旅作家個人想象的產物,但不止是一己之力收獲的“蓓蕾”,而更應被視作一國軍事文化對國外同行的集體假設與言說。透過時代發展而表現出的新變,則可以一窺軍事文化主潮的變動,以及軍旅作家們內在的思想振蕩。
這些形象背景明確,反映出軍旅作家對世界秩序的理解與認知。這些外軍形象,無論是著意于控訴的日軍形象,還是和平軍營題材中偶露崢嶸的歐美軍人,其所屬文學作品的背景因素并不復雜含混。日軍形象自不必贅述,“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一直充當著相關題材作品的主旋律。以取材于軍隊強軍改革的眾多小說為例,不難發現個中微妙之處,《明天戰爭》中的考夫特等“假想敵”總是來自西方某個“獨立的時間并不長,談不上有多少文化積累”的超級大國,而安德烈和阿廖沙們幾乎可以望文及義地判定其俄軍身份,人物形象鮮明對比的背后,大國對抗與博弈的痕跡已然清晰可見。將《超越攻擊》與二十年前的《兩代風流》并論,從作品中對安德烈和巴索夫的不同刻畫,不難看出冷戰與后冷戰時期軍旅作家對世界格局近乎顛覆的理解和描述。外軍形象的存在,首當其沖的始終是其政治性,軍旅作家即便能如《賭下一顆子彈》中將帕特遜描述的既與中國軍人惺惺相惜,又不掩飾忌憚與遏制之意,但這種描述更進一步襯托出中國軍人的自信與優秀,而帕特遜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又或可以看作是對時下復雜多變的中美關系的折射。這些形象相對單薄,透射出軍旅作家對深度挖掘的局限與欠缺。
世界文學范疇內戰爭文學精品不在少數,涉及外軍描寫的同樣不乏力作,尤其是美、蘇兩國取材于“二戰”的文學作品,不少對作為對手的德軍進行了細致刻畫。與此相比,從早期日軍形象的“鬼子化”到近些年來功能化的“假想敵”和“新朋友”,進行涉外書寫的中國軍旅作家有意無意地更偏重于國家和民族利益。這樣的描寫,一方面有助于民族自信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迎合受眾心理的初衷。但置于世界文學平臺進行衡量,這恰恰又是制約其難以更上一層樓的原因之一。外軍形象單薄呆板,看似是軍旅作家相對保守的選擇,但同樣傳達出軍旅作家在對戰爭真實性、復雜人性的領悟與把握上底氣不足,作品中即使偶有個別性格鮮明的人物,其言行舉止也更像是囂張而非自信。如劉亞洲在《惡魔導演的戰爭》中對沙龍在歷次作戰中的驚人選擇及其戰果進行了詳盡描述,對同為沙龍一手炮制的“吉貝亞村慘案”卻不置一詞,結合劉亞洲此后人生軌跡,不難看出其在創作時更多趨于“文以載道”,而非著意挖掘和叩問人性本質,這在外軍形象塑造中絕非個例。

泥模藝術——戴面具
【責任編輯:王 崇】
I206.7
A
1673-7725(2015)04-0105-03
2015-02-05
陳月豐(1987-),男,河北邢臺人,主要從事中外軍事文學及對外宣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