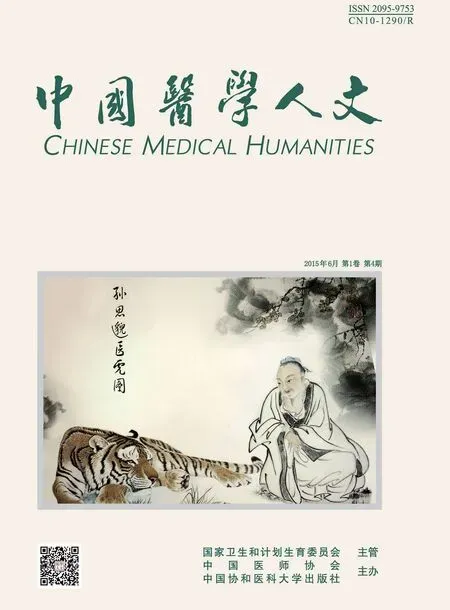一次醫學與人文科學的對話
文/許嘉璐
一次醫學與人文科學的對話
文/許嘉璐
編者按:王寧利,中華醫學會眼科學分會主任委員,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黨委書記、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副院長、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中心主任、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所長。2015年5月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新作《臨床與科研——臨床需求導向的科學研究》。全書分為正文和附錄兩大部分,正文包括緒論、課題研究、技術規范、重要課題組介紹及學術產出共計五篇。王寧利教授邀請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漢語文化學院院長,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為著作作序。于是,有了“醫學與人文科學的對話”。
我曾是一名患者,對醫學一竅不通,怎么可以為這位蜚聲國內外的眼科醫學大家寫序呢?沒過幾天,樣書送來了,接過來,又嚇了一跳:16開,500多頁,沉甸甸;翻看目錄,在第二篇《課題研究》、第三篇《技術規范》中,竟有10章,49節,我連每節的題目和圖片都看不懂!但是,第一篇《緒論》和附錄《人文故事》卻吸引了我,四、五萬字,一口氣讀完了。
王寧利教授在《緒論》里以“我和我的導師們”等3篇文章告訴我們,科學技術的傳承靠的是人,靠的是奉獻精神、忘我精神、團隊精神、勤奮精神和由聰穎、悟性生發出的大膽設想(假說)。讀后,我不禁掩卷而嘆:這不就是偉大的人文精神么?在他的字里行間,滲透著對4位杰出導師的崇敬和感激,從“醫生、團隊、平臺、使命”一文中噴射出的,是從導師們那里繼承來的“大醫精誠”之愛,是任何設備不可代替的嚴謹,是對科學發展規律的執著探索。

專注 攝影/劉伯運 北京武警總醫院
《緒論》讀罷,我情不自禁地進入了書的第二篇。雖然面對繁多的術語、數據和圖表如墮五里霧中,但是反復翻閱,似乎忽有所悟:事實-問題-假說-驗證-再次面對事實-再次發現問題-再次提出假說,這一思維和實踐過程,不僅適用于眼醫科學,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自然科學;王寧利教授成長的過程,他給學生們所指出的前方之路,實際是人類對自然、對自身不斷進行有效思考、成功探索的必由之路。對這一可謂方法論頂層的總結,正是人文社會哲學領域中事。不止此也,充滿在其各章節中的,是他對偶然與必然、共性與個性、宏觀與微觀、發現與創新、已知與未知、有限與無限、黑暗與光明、艱難與成功、個人與群體種種對立而統一關系的親身體驗。天哪,在我所從事的語言學、文化學和跨文化交流領域里,不是也時時刻刻不能離開人類的這些智慧結晶嗎?隔行如隔山,但我清晰地聽到了山那邊響亮而悅耳的琴聲——隔山、隔知,但隔不住普世的真理呀!
人類現在生活在戰爭陰云、環境惡化、社會離散種種危機之中。用德國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話說,我們所身處的,是“世界性風險社會”。撇開戰爭硝煙背后的陰謀陽謀不說,單看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在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生活質量的同時,現代化農業、食品加工業和新的生活方式帶給人體的直接和潛在的威脅,人類向大自然無限度的攫取,以及“權威機構”公布的對這些危害“可以承受”的標準、“沒有異常反應的記錄”之類的說辭、提示,幾乎都是經過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之腦、之手而出臺的,但其研究、試驗、測量的詳情社會不得而知。在其背后,有沒有最高端的企業家指揮的身影呢?誰說自然科學和人文無關?
對“現代”“現代化”“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對,已經持續了半個多世紀。這其中也不乏把反對甚至仇恨的矛頭直指科學理性和技術應用的聲音。雖然現在還沒有人在批判有關現代的一系列問題之后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甚至對天天打來打去和含毒素工業產品的增產沒有發生絲毫遏制的作用,但是,中華文化反求諸心、推己及人、天人合一、仁義道德等主張,越來越吸引世界的注意。依照中華民族的理念,除了應視自然、宇宙與己一體,對由于種種自身和環境的原因而出現或造成的疾病,既已發生,就應該盡力予以治療,同時力求尋其緣由,提高療效;同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帶著對地球前途的關切,對人類(擴而大之應該涵蓋一切生命體)的大愛,研究創新技術工具和應有的規范標準。王寧利教授大作的第二篇,其中第四章不就是“儀器設備研究”嗎?但是,是我的思緒沒有離開他的這部精彩之作呢,還是他沒有和我所從事的行當分家呢?
他在書尾收進的一篇優美的散文:《一步之遙——與最終結論失之交臂》,給了我答復。“夜幕降臨時,一首小提琴曲打破了秋日的寧靜,是Por Una Cabeza 中文譯名《一步之遙》。……這首(著名的探戈舞曲)怎么叫‘一步之遙’呢?就像暗戀中的人,最終沒有表白;相愛的人,最終沒有結婚;分手的人,最終沒有挽留。”由此他聯想到,“在科研工作中,有時雖然只差一步,但這一步卻比之前的成百上千步更為困難,更為艱辛;可能你已經來到一個寶藏的門口,卻不知道如何打開這扇大門。如果你認為這扇門永遠打不開,放棄吧,那么,大門后的精彩,就永遠不是你了。”讀到此,我驀然明白了:怪不得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就,原來在他心里,醫學和人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游刃其間,由此及彼,由彼反此。他以博大的人文情懷投入到為眼疾患者解除痛苦的事業中,又以他所掌握的前沿技術和精細的觀察、診斷、治療、手術以及不懈的奮斗來報答他的4位恩師和所有的人們,包括走在他身后,將會打開更多寶藏大門的后來者。
他還說過這樣的話:“科學是‘求真’,人文是‘求善’;求真、求善是生命的初衷,促使科學與人文永遠并存。沒有人文的科學是枯燥的,沒有生命力的;沒有科學的人文是僵化的,也是短命的。”原來,我草草讀了他的心血之作,又感于他的成就和為人,于是坐下來寫這篇序,實際是我們兩人在進行一次醫學與人文科學的對話。我希望這樣的對話能夠繼續下去,因為這是時代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