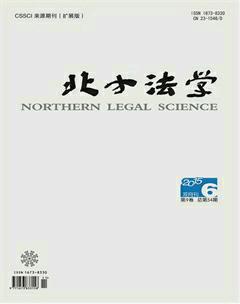俄羅斯刑法上的國際刑法規定
葉薩科夫G.A
摘要:由于冷戰后俄羅斯學界對國際刑法研究不重視,目前《刑法典》中僅存有關普遍管轄權和訴訟時效的規定。但刑法典總則對缺席判決下普遍管轄權的適用、指揮責任和排除違法性理由的判斷標準規定模糊,而分則的犯罪體系過于粗略和封閉,沒有規定反人類罪和非武裝沖突中對戰爭手段和方法的使用等,需要根據“日內瓦公約”和“海牙議定書”予以重構。
關鍵詞:俄羅斯刑法 日內瓦公約 海牙議定書 羅馬規約
中圖分類號:DF6(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5)06-0152-07
一、導 論
如果俄羅斯人民通過歷史之鏡回顧國際刑法領域,他們會為本國為該法所發揮的驅動作用而感到驕傲。俄羅斯帝國是首批落實后來被命名為“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犯罪立法的國家之一。①繼俄羅斯首倡之后,國際社會分別于1868年、1874年和1899年召開會議,在1899年的國際會議上,俄羅斯費爾多·馬滕斯(Fyodor Martens)教授提出了以其姓氏命名了“馬滕斯條款”。②在20世紀40年代,蘇聯積極參加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但遺憾的是,這些立法和科學研究后來衰敗了。盡管這里有許多原因,包括冷戰氛圍和俄羅斯在總體上的社會和經 濟不景氣,但最明顯的一個原因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刑法在俄羅斯的科學研究中實際上被忽略了。其余燼猶存的最后跡象是1996年《刑法典》(the CrC)第34章③標題為“違反和平與人類安全罪”。該章是《刑法典》最后一章,并且起草得很拙劣——只有用過時的和高度抽象的詞句規定的8個罪名,而且根本沒有規定反人類罪。有關普遍管轄權(第12條第3款)和訴訟時效(第78條第5款、第83條第4款)的規定是國際刑法在《刑法典》中的唯一遺跡。
本文以兩個推定為基礎。第一,國際刑法規定是俄羅斯刑法的一部分,應當在俄羅斯刑事立法當中予以適當的貫徹。該貫徹意味著根據當前的國際法對犯罪進行可行的定義,與之相關的一般條款體系也應當適合于這些定義(比如管轄權、判決理由及辯護理由等)。現行《刑法典》是一個拼湊的和過時的版本,包含對國際法的總體性參考。例如,使“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罪行化的《刑法典》第356條第1款是一個高度抽象的規范,描述的禁止行為需要援引大量條約法。④導致的后果是,由于其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抵觸而被推定違憲。它將“海牙規則”和“日內瓦公約”的相關法律混合在一起,但并沒有對國際性武裝沖突和非國際性武裝沖突做出區分。它還對一些由國際習慣法所禁止的行為未加處罰。⑤而且,因為這些原因,俄羅斯的國際義務并沒有通過“普通的”刑法覆蓋這一領域而得到充分履行,這些普通的刑法條款是“對人類生命和健康的犯罪”(《刑法典》第16條)、“侵犯財產罪”(《刑法典》第21條)。也就是說,因為其規定的刑罰明顯與國際層面所規定的犯罪的嚴重程度不符,“普通的”刑法不懲罰某些形式的被國際法所認可為犯罪的行為,⑥但針對“普通的”犯罪的訴訟時效規則卻可以適用。第二,國家希望將國際刑法納入其國內立法是基于多種原因。應當承認,懲罰國際犯罪(從定罪到量刑)主要是國內司法管轄權的職責。現行國際刑法的一般原則只是一個補充,這被反映在1998年《羅馬規約》序言第6條和第10條中(該條款規定:“對那些對國際犯罪負有責任的人行使刑事管轄權是每個國家的義務”,并且“根據本規約建立的國際刑事法院是對國內刑事司法權的補充”)。盡管《羅馬規約》并不直接強制各國立法以懲罰由《羅馬規約》所確定的國際犯罪,但出于實際的和重大的理由他們卻應當這樣做,這是一個廣為流傳的信念。⑦
③ 所有俄羅斯聯邦的聯邦法律和其判例法均引自俄羅斯電子資料“Consultant Plus”。
④ 整個國際人道法的歷史和內容主體都被體現在第356條的幾行表述中。第356條第1款規定了“殘酷對待戰爭或平民囚犯、將平民驅逐出境、掠奪被占領區的國家財產和在軍事沖突中使用俄羅斯聯邦參加的國際條約所禁止使用的手段和方法”的責任。這些犯罪將被處以最高刑期達20年的監禁刑。第356條第2款規定了對使用俄羅斯聯邦所參加的國際條約所禁止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處罰。對這類犯罪所處的是10年到20年的監禁刑。
⑤ 參見主要的俄文批評性文獻:ГИБогуш, ЕНТрикоз(ре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уголовный суд: проблемы, дискуссии, поиск решений (Москва, 2008); ГИБогуш, ЕНТрикоз(ре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суди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осква, 2009);還可參見BTuzmukhamedov,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8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2003) 385,pp389—391; SVasiliev and AOgorodova,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in Russia, 16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 197, pp212—216
⑥ 例如,“普通的”刑法沒有規定構成危害人類罪的諸如滅絕、性奴役、強迫懷孕和種族隔離罪的責任,并且這些犯罪在《刑法典》上并沒有以任何方式給予分別處罰。
⑦ 參見GWerl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2nd ed, The Hague: TMCAsser Press, 2009, pp27、117—119; JSchense and DKPiragoff,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ome Statute, in MNeuner (ed), National Legislation Incorporating International Crimes,Approaches of Civil and Common Law Countries,Berlin: Berliner Wissenschafts-Verlag, 2003,pp239、 244—245; MGoldmann, Implementing the Rome Statute in Europe: From Sovereign Distinction to Conv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16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 pp5、12; GWerle and FJessberger,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Is Coming Home: The New German Code of Crim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13 Criminal Law Forum (2002) ,pp191、194—195
⑧ 更多介紹,請參見MBenzing, The Complementarity Regim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between State Sovereignty and the Fight against Impunity,7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03,pp591、 614—617; Werle, supra note 7,pp118、120; Goldmann, supra note 7, p15
俄羅斯在2000年簽署了《羅馬規約》,但在本文寫作時該規約尚未被批準。然而,俄羅斯將來有可能想批準《羅馬規約》,并因此受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18條的約束。當然,在執行過程中的不作為就足以符合該公約第18條,但是正確的做法在于將遵守《羅馬規約》納入國內立法作為批準的先決條件。比如說,國內立法中條款的缺失將導致《羅馬規約》第17條第1款(a)和第17條第3款的適用,這些條款的相關部分規定:“為了確定在特定案件中不具備審判訴訟能力,法院應當考慮,是否由于一個國家……國內司法系統無法利用,這個國家……沒有能力執行這一訴訟程序。”⑧進一步而言,國際法有時明確地強令各國懲處某些形式的危險行為。俄羅斯聯邦已經批準了1949年《日內瓦公約》[《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1公約);《改善海上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及遇船難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2公約);《關于戰俘待遇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3公約);《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即日內瓦第4公約)],以及1977年通過的上述公約的第1議定書和第2議定書。然而,由于沒有納入國內法,這些公約和議定書中義務的履行是通過推定這些規范違憲的方式,或者根本不可能履行(特別是第1議定書第11、85和86條的規定)。
最后,一個國家的國際聲望明顯地依賴于其防止和處罰被國際刑法所規制的犯罪的意愿和能力。俄羅斯目前即面臨這種處境,因為迄今為止俄羅斯還沒有更新國內立法以規定因關涉國際因素而被加重的罪行,而且在這方面也沒有采取積極措施。
本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刑法典》總則中有關國際刑法的規定,第二部分將集中于具體罪行規制的一些方面。筆者試圖通過對《刑法典》相關規定的討論,去發現這些規定存在的缺陷以及提出補救方法。
二、《刑法典》總則部分中的國際刑法
與《刑法典》總則部分有關的國際刑法問題是規范的更新以及如何適當地將其引入現存刑法規范體系的建構。
(一) 普遍管轄權
如果一個沒有在俄羅斯永久性定居的外國人或者無國籍人在俄羅斯聯邦屬地管轄權之外犯罪(《刑法典》第11條),其刑事責任在俄羅斯刑事立法上只能根據幾個管轄原則來判定。《刑法典》第12條第3款規定:這些人“在下列情況下應當根據本法典承擔刑事責任,即如果實施了違背俄羅斯聯邦利益的犯罪,和在俄羅斯聯邦所參加的國際條約有規定的情況下,除非他們在另一國家被定罪并且在俄羅斯聯邦領土范圍內針對他們提起刑事訴訟”。這個規范涵蓋了屬人管轄原則和保護原則(違背俄羅斯聯邦利益)以及普遍管轄原則(俄羅斯聯邦參加的國際條約有規定)。
普遍管轄權和對它的適當限制對今天的國際法發展提出了開放性問題。日內瓦法規定了普遍管轄權(日內瓦第1公約第49條、日內瓦第2公約第50條、日內瓦第3公約第129條、日內瓦第4公約第146條),但是國際犯罪的廣闊范圍并沒有被條約法所涵蓋。⑨例如,種族滅絕并不包括在內,因為1948年《預防和懲處滅絕種族罪國際公約》沒有規定普遍管轄權。發生于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的反人類罪和戰爭罪也沒有被條約法所涵蓋。這一管轄權原則作為一項國際習慣法規則的可行性和它的內容是需要廣泛討論的事項。⑩如果不在更多細節上對這些事項進行探討,可以說,國家可能在國內法上提供了普遍管轄權,困難在于如何確定其界限。
⑨ 關于條約的批評性評價,參見ACassese et al,Cassese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pp285—290
⑩ 相反觀點可進一步參考 MNShaw,International Law ,6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668—686; I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05—307; 前引⑨ Cassese et al書, supra note 9, pp278—281; 前引⑧ Werle書, pp62—68; ACassese,Is the Bell Tolling for Universality? A Plea for a Sensible Notion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1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2003),pp589—595; CKreβ,Universal Jurisdiction over 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th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2006) ,pp561—585根據俄羅斯的學說,普遍的觀點是,接受關于國際犯罪的普遍管轄權作為一項國際習慣法的規則。參見ИАЛедях,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юрисдикция как принцип уголовного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наказан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уголовном праве,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 C. 14 и сл(Юрист-международник, 2008, № 2); ГАКоролев,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юрисдикция: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применения, 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 C. 95—96 (Журнал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а, 2009, № 3); ВНРусинова,Пре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в н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на основе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го принципа юрисдикции,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 C. 25—48 (Военно-юрид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2006, № 5); ПШтурма,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юрисдикция и наказание за серьезные нарушения Женевских конвенций 1949 г, Правоведение, 2010, № 4, C83—92
《刑法典》第12條第3款完全是基于條約承認普遍管轄權(僅“在俄羅斯聯邦參加的國際條約有規定的情況下”),這一做法由于過度限制和忽視國際習慣法而遭到批評。B11如果立法能夠針對《刑法典》第34章涵蓋的所有犯罪都提供普遍管轄權,那么才有采取進一步措施的可能。
根據普遍管轄權進行的缺席審判,國內法的規定也是不明確的。《刑法典》第12條第3款規定追究刑事責任的訴訟應該在俄羅斯聯邦境內提起,但是這句話在俄羅斯法上的確切含義指向不明,一方面,被告在俄羅斯境內的存在有可能是被推定的。另一方面,自2006年以來,刑事訴訟立法允許法院審理被告沒有在場的嚴重案件(例如《刑法典》第15條第4、5款),如果這個人在俄羅斯境外,或者這個人的缺席是為了逃避審判(《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247條第5款)。在被告不能被引渡的情況下,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含蓄地支持缺席審判的做法。B12如果普遍管轄權原則被擴大到涵蓋《刑法典》第34章列舉的所有犯罪,它應該被稱為有條件的普遍管轄權,它需要犯罪嫌疑人在被提起刑事訴訟之前身在俄羅斯境內。B13
(二)指揮(上級)責任
第1議定書第86條第2款的規定尚沒有落實到俄羅斯的國內立法當中。《刑法典》的分則部分并沒有單獨規定這種犯罪的責任類型。B14《刑法典》第42條適用于作為辯護理由的命令和指示的執行,但并不適用于上述(指揮或上級)責任,因為它規定的是在行動中下屬的責任,而不是不作為的責任。指揮責任不能用共犯規則處理,上級的不作為并不符合《刑法典》第33條所規定的任何共犯的要件。
B11 參見ВСКомиссаров, НЕКрылова, ИМТяжкова (ред),Уголовное пра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Общая часть (Москва, 2012; 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C.1441—1443); ВНРусинова,Преследование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совершенных в н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на основе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го принципа юрисдикции,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 C. 52
B12 參見2009年12月22日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決議第13條第28號:“規制刑事案件審判準備工作的刑事訴訟立法規范由法院適用”。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的全體會議決議由全法院根據《憲法》第126條通過,其作為對法院在應用程序和實體規范方面有約束力的指導而發揮作用。這些決議是俄羅斯法律體系的獨特成分,因為它們是基于對基層法院一般做法的分析而對實踐問題作出的司法解釋。
B13 絕對的普遍管轄權是當今各國立法的例外。比如,《德國刑事法典》第1條所規定的絕對的普遍管轄權甚至通過刑事程序規則在實際上被轉化成有條件的普遍管轄權。參見HSatzger,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Criminal Law(Sinzheim: CHBeck, 2012), pp292—293;TWeigend,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te of the ICC in Germany, in KLigeti (ed), Current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Criminal Law,Lectures in Memory of Imre AWiener (Toulouse: ditionsérès, 2010) 67,pp75—77; MNeuner,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Germany, in前引⑦ MNeuner (ed)書, pp106—108; Werle and Jessberger, supra note 7, pp212—213
B14 一般而言,《刑法典》第293條有關官員失職的責任能夠適用于一些情況,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的情況,特別是不能適用于事實上是上級行使權力的情況。《刑法典》第356條第1款也是無效的,因為指揮責任不構成“在軍事沖突中使用俄羅斯聯邦所參加的國際條約所禁止使用的戰爭手段和方法”本身,但卻是其他人違法行為的一種特殊責任形式。
B15 最后一次嘗試使用這樣的技術是立法機構在2009年規定的加重情節上,對性犯罪中受害人的年齡(《刑法典》第131—135條)重新定義,任何過錯因素(“明知”)的引用都被刪除了。這一修正案背后的意圖是在性犯罪中允許加重刑事責任,因為對受害人的年齡認識沒有任何過錯因素(采用普通法制度的做法,創造一種“嚴格責任”的犯罪)。2011年,這一修正案幾乎被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在《刑法典》第5條(過錯原則)的基礎上逆轉了,法院指出,有關國際犯罪情節因素的過錯因素應當是準確的或者是蓋然性的知識。
B16 關于兩種途徑的更多差異,參見前引⑨ Cassese et al書, supra note 9, pp191—192
落實第1議定書第86條第2款的一個可能途徑是創造一種特殊的犯罪。這種犯罪的其中一個要件是不作為,如上級在自己的權限內未能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去阻止或者抑制特定戰爭罪行的發生。而且,這種犯罪還需具備的要件是武裝沖突。這種犯罪不作為責任的成立對國家立法機構而言也不是普遍的,因為這需要行為人是在有意識的狀態下(比如故意)的不作為,能夠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犯罪將要被下屬實施(過失),或者意識到這一點(惡意欺詐)。從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而言,作為犯罪情節因素的過錯不應該包含過失。B15這種犯罪有爭議的因素將是所有可行的措施和上下級關系的概念。
另一種落實實施的途徑是使用共犯規則。處于上級的人能夠被視為沒有被阻止的犯罪的行為人(如同《德國刑事法典》第4條第1款規定的那樣)。B16《刑法典》第33條第2款可以通過添加作為上級的另一種“行為人”的定義而得到修訂,這一上級在武裝沖突期間沒有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去阻止或者抑制至少一種為《刑法典》相關章節所規定的罪行,如果這一上級已經意識到犯罪正在實施或者試圖實施,或者這一上級能夠知道或者應該知道犯罪正在實施或者試圖實施。
(三)豁免和刑事責任
刑事責任的豁免在俄羅斯學說中并沒有被廣泛討論。絕對的訴訟豁免在俄羅斯是不被承認的。有關訴訟豁免和撤銷豁免的規則規定在《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第447—451條中。《憲法》第93條規定:“俄羅斯總統如果涉嫌叛國或者其他嚴重犯罪將可能被彈劾。”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俄羅斯官員沒有國際刑事犯罪的刑事責任豁免權。
(四)法定時效
《刑法典》第78條第5款和第83條第4款規定,《刑法典》第353、356、357和358條所確定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或處罰不適用法定時效。B17因為一些戰爭罪和所有的反人類罪還沒有受到處罰,必須修訂第78條第5款和第83條第4款的罪行名單,以遵守1968年《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不適用法定時效國際公約》第1條的規定。
(五)排除行為違法性的理由B18
排除行為違法性的理由是直接針對“普通”刑法的,具體包括自衛(《刑法典》第37條)、必要性(《刑法典》第39條)和脅迫(《刑法典》第40條),其不符合《羅馬規約》第31條所反映出的國際刑法當前的發展趨勢。這些理由在種族滅絕罪、反人類罪和戰爭罪中的適用性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主題。B19
B17 在俄羅斯刑法上,免除刑事責任和免除處罰是有區別的(分別規定在《刑法典》第11章和第12章中)。免除刑事責任意味著國家拒絕對被告人提起或繼續刑事訴訟。免除處罰則是在定罪以后因為表現良好、生病、大赦或者赦免這些因素而不予處罰。而法定時效則是對任何沒有及時被提起刑事訴訟或者沒有被及時執行判決的被告給予免于刑事訴訟或處罰的強制性理由。
B18 排除行為違法性的理由是俄羅斯刑法上的一個特殊概念,包括自衛、對一個犯罪的人施加傷害、必要性、脅迫、正當風險和執行命令或指示(分別規定在《刑法典》第37—42條中)。在寬泛的意義上講,這些理由有可能被用來與《羅馬規約》第31條排除刑事責任的理由、普通法上的正當辯護事由以及德國刑法上的正當化事由相比較。
B19 參見ЭДавид, Принципыправавооружённыхконфликтов (Москва, 2011), C.955—958,translation of EDavid, Principes de droit des conflitsarmés Quatrièmeéd,Bruxelles: Bruylant, 2008
B20 更多舉例,參見前引⑧ Werle書, pp224—227
然而,存在更多問題的是《刑法典》第42條,它規定對命令或者指示的執行可以作為排除違法性的一個理由。該條規定:“因身負職責執行命令或者指示而對法益施加侵害,這種行為不能視為犯罪。這種傷害行為的刑事責任應當由發出非法命令或指示的人承擔”(第1部分)。而“明知執行的命令或指示是非法的還故意實施犯罪的人,通常條件下應當承擔責任,但未能執行明知是非法命令或指示的情況下,將排除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第2部分)。但“明知命令或指示是非法的”的標準(《刑法典》第42條第2款)并不明晰。它應該是以“普通人”的標準,還是以個案的“案中人”的標準?因為缺乏明晰性,迫切需要在法典中納入與《羅馬規約》第33條第2款相似的條文。另外,發布明知是非法的命令或指示的主體的法律地位也必須確定,該主體應該被定義為組織者(《刑法典》第33條第3款)。
排除違法性的新理由也應該在俄羅斯刑法學說上給以釋明(比如報復和軍事必要性)。B20
三、《刑法典》分則及其國際犯罪體系概述
《刑法典》第34章題名為“違反和平與人類安全罪”,具體規定了如下刑事責任:策劃、準備、發動或開展侵略戰爭(第353條);公開呼吁發動侵略戰爭(第354條);復辟納粹主義(第354條第1款);開發、生產、儲存、收購或出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第355條);使用禁用的戰爭手段和方法(第356條);種族滅絕(第357條);生態滅絕(第358條);充當外國雇傭兵(第359條);襲擊享受國際保護的人員或機構(第360條)。現行《刑法典》反倒比舊法更槽糕,因為它沒有規定有關搶劫或非法使用或者濫用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標志的特殊規范(這些規范被分別規定在1960年《俄聯邦政府刑法典》第266條和第269條中)。有推論說,這些行為已經被現在《刑法典》第356條第1款涵蓋了,但對此存有爭議。
有必要對《刑法典》第34章進行重大修改。該章對國際犯罪的概略和過時的描述應當予以重造。如何對這些罪行建立新體系化以及對它們的犯罪事實進行確切措辭顯然是開放性的問題。這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設計,因為每個國家的法律都有自己的技術細節。但是這些定義應該和《羅馬規約》的定義相契合。之前提出的界定模式建議,B21都采用了類似的諸如“國際地”而非“犯罪地”措辭。
有些基本問題和觀點必須予以考慮。這種設計的進一步擴展應當根據《羅馬規約》第5條第1款所提出的犯罪體系進行。例如,盡管國際人道法在“日內瓦”法和“海牙”法分支上存有爭議和有限分歧,但是必須單獨規定兩種犯罪,懲罰在武裝沖突中使用禁用的戰爭手段和方法的行為,以及在武裝沖突中嚴重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
《刑法典》第356條第1款只對“在軍事沖突中使用了俄羅斯聯邦所參加的國際條約禁止使用的戰爭手段和方法的犯罪”予以處罰。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指出:“規定了犯罪行為處罰要件的國際條約不能被法院直接適用,因為這些條約明確闡述了國家的義務,即通過國內(國家)立法規定對某些犯罪實施懲罰以確保對條約義務的履行……”(2003年10月10日第五號決議第6條規定的可適用情形是:“由具有一般管轄權的法院適用國際法上和俄羅斯聯邦所參加的國際條約公認的原則和規范”。)但如果“《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的條款明確建立了適用國際條約的必要性”的情況下,最高法院允許通過直接引用國際法而直接適用國際法(上述決議第6條)。如最高法院援引了《刑法典》第355條和第356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