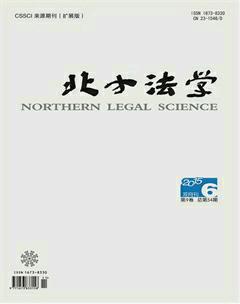民事立法形式之憂
姜朋
摘要:歷史地看,“法典”與法表、刑鼎等一樣,都屬于早期成文法的表現形式,且其得名與使用的材質關系密切。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后,為了因應社會經濟形勢的變遷,民事單行法或特別法游離于法典之外幾乎成為一種趨勢。此時繼續保留相當程度上被掏空了的法典的民事法律母法的名義,其意義究竟何在,不無疑問。編纂民法典,對于中國的立法機制和法律適用傳統都是一種挑戰,新的法典與之前既存的民事單行法的關系究竟有何不同,如何協調其與過往前數十年間基于民事單行法所形成的法律運作體系的關系,如何確保后者不因新法的制定而被割裂、舍棄,都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
關鍵詞:民法典編纂 法律匯編 民事立法
中圖分類號:DF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5)06-0016-06
恩格斯曾提到:“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一致的表現……‘法發展的進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設法消除那些由于將經濟關系直接翻譯為法律原則而產生的矛盾,建立和諧的法體系,然后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影響和強制力又經常摧毀這個體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這里我暫時只談民法)。”①其實,關于“法發展”的話題,除卻內容上需要與時俱進的更易外,法律形式上的變化也不容小覷。
2015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向全國人大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提出,“抓緊研究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這意味著編纂“民法典”再次提上了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議事日程。盡管如此,筆者認為其中“民法典”的提法只應當理解為是立法機關對學界慣用術語的援用,而并不代表未來制定出的民事法律文件在名稱中會繼續保留“法典”字樣。因為按照中國以往的法律命名慣例,還沒有哪一部法律在名稱中使用“法典”這一稱謂,《刑法》這一處于同樣法律位階的基本法律就是例證。當然,立法的表達并不是決定學理采取哪一學術術語的唯一標準,因此,為了討論的方便,本文也會繼續使用“民法典”一詞以指代中國未來可能出現的民事立法。
在討論“編纂民法典”話題時,有兩個問題必須認真面對:如何看待“法典”這種立法形式?②如何看待法律與實踐,如何評價在先前民事單行法之下形成的民事法律實踐(包括民事司法以及大量未進入司法程序的民事活動)?
一、“法典”詞考:成文法的一種表達形式
根據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的解釋,英語中code(對應拉丁文中的codex)原指將樹干劈成木板,進而指用以書寫的木板,在法律上又引申為法律書籍:“Wooden tablet for writing [hence, book: in LL. (Ec), code of laws]orig, tree trunk, wood split into tablets”。③另有資料稱,拉丁語中“法典”(code,codex)一詞的出現不早于公元1世紀:
已知拉丁詞Codex第一次出現是在公元85年,馬爾西亞筆下。最初指的是一片小木板(拉丁語:caudex),隨后引申為用繩子捆綁固定的幾片小木板的集合,上面記錄了一些賬目或其他沒有長期保存價值的資料。
冊子在帝國時代的羅馬并不是必需的,在那兒,書籍仍然是紙莎草的卷軸,羊皮紙和冊子本僅用于更快速,尤其是更短暫的工作摘錄或草稿。冊子本的普及僅始于三四世紀:(綿羊)皮經過準備,被用作書寫材料,一旦文稿謄好,就將其對折或三折組成一本書貼。依次相疊的書貼被縫合在一起并置于封面下,這就是書,以我們今天廣為認識的形式存在的書。
已知最早的封面來自埃及:書被縫合在一起,用夾書板固定。所謂夾書板,是由2片小木板組成的(ais)。在西方,縫合技術變化多樣,但通常都是以2個針上線長度的類型為基礎上建立起來的。④
這種木板形制的法律載體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歷史上著名的古羅馬十二表法(the Twelve Tables of Rome)以及其參照模仿的古希臘梭倫立法。按照普魯塔克《傳記集·梭倫傳》中的記載,梭倫(前638年—前559年)于公元前554年制定的法律采取的是木板制成的法表的形式:
③ David B. Guralink, ed.,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2nd college ed. (New York and Cleveland: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④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劉陽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頁。
⑤ 《普魯塔克〈傳記集〉選》,吳于廑等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5—35頁。有關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憲政和司法制度的變革,可見《格羅特〈希臘史〉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德拉克馬(Drachmae)為古希臘貨幣單位,6000德拉克馬=1塔蘭特(Talent)。2009年3月,筆者訪問美國羅德島州議會大廈時看到,美國憲法、羅德島州憲法等法律文件被裝在木框中,木框的一邊固定在一根木軸上,如同葉片垂直的風扇。觀者可以輕轉木框翻頁觀看。“阿格松”或許就是這種形制。
⑥ [德]特奧多爾·蒙森:《羅馬史》(第二卷),李稼年譯,劉澍泖校,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5、36頁。
梭倫的第十三塊法表載有他的第八條法律,文曰:“凡在梭倫任執政官以前被剝奪選舉權者,除因被控謀殺罪或殺人罪,或圖謀建立僭主政治罪,經‘元老會議或‘執法長老,或國王在國事堂(普里坦尼厄)中判罪,并于本法律公布時仍放逐國外者外,一律恢復其權利及選舉權。”……
[第十六塊法表]估算祭神的供品的時候,一頭羊和一布奢耳谷物都估價一德拉克馬[Drachmae]。地峽競技會上的優勝者所得獎金為一百德拉克馬,奧林匹克競技會上的優勝者所得獎金為五百德拉克馬;帶來一頭狼的人可得五德拉克馬,一頭幼狼可得一德拉克馬。根據法勒里人德米特留斯的說法,前者是一頭牛的價錢,后者是一頭羊的價錢……
他所訂的一切法律有效期間為一百年,寫在名叫“阿格松”或木板上面,安置在長方形框子里,可以轉動。我在雅典時,這些木板還有少許參與保存在國事廳里……元老會議用共同宣誓的方式批準了梭倫所訂的法律,而每一“典法執政官”(原為三人,后增至九人,其中位次低者六人)又分別站在市場內傳令石上,宣誓說,如果他以任何方式違反了這些法律,他就要在達爾斐獻立一座有相當價值的金象。⑤
古羅馬人在制定十二表法時,也學習了古希臘的立法技術。特奧多爾·蒙森記述道:
到了300年(前454年)妥協終于達成,元老院在主要方面作了讓步。起草普通法典的事議決了,為此,作為一種非常措施,百人隊會選出了10人,一方面來修訂法典,同時又代兩執政官充任最高長官,而且不但貴族可被選任此職,平民亦然……在此以前,羅馬已派使者前往希臘,把梭倫的法律和其他希臘法律帶回本國,他們回國后,十人才被選為303年(前451年)的長官……303年(前451年)的十人政府將他們制定的法律提交人民,得到人民的認可后,就刻在十塊銅表上,銅表樹立在市場上的元老院前面的講壇旁。由于還要做些補充,于是在304年(前450年)又任命十人,他們又增加兩塊銅表;羅馬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法典于是肇始,這就是《十二銅表法》。⑥
而彭波尼《教科書》(單卷本)則提到:
為了使這種狀況不再持續下去,成立了一個具有公共權威的十人(委員會),通過他們從希臘的城市中尋求法律,并使羅馬城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十人(委員會)把這些法律整理在一起,完整地書寫在象牙表上,并安放在公共講臺前以使法律被更為普遍地了解……這十人(委員會)認為第一部法律還缺失什么,因此第二年他們又增加了另外兩表:這樣,因增加的兩表被稱為“十二表法”。有些人說,一個被流放意大利的叫做艾爾莫多魯斯的埃菲索人,曾向十人(委員會)提出擁護十二表法的立法建議。⑦
由不成文的習慣法到成文法,是法律形式上非常重大的一次變異。成文化后,因使用材質的不同,法律的表達形式也有多種。目前人們已知的早期成文法,有的被摩寫在石頭上(如漢謨拉比法典),有的被謄寫或刻寫在板材上(木板、石板、銅板或象牙板,如猶太人文獻中所述的上帝于西奈山賜予摩西兩塊約板上書十誡,⑧又如古希臘的梭倫立法和古羅馬的十二表法),有的被鑄造在青銅器物上(如中國戰國時期鑄造的刑鼎與刑書)。再后來,人們還用纖維織物(如中國的帛)、紙草、動物皮革(如羊皮)、更為短小的木板或木條(如中國的竹木簡)等材質來書寫法律。⑨這意味著采取繩穿木板形式的早期“法典”與法表、刑鼎等一樣,都屬于早期成文法的稱謂,且其得名與使用的材質有關(或說是基于對所用材質的直接描述)。
二、法典編纂與法律匯編
按照法理學教科書的說法,法典編纂與法律匯編皆屬于規范性法律文件系統化的形式(此外還包括法律清理),但二者區別明顯:
法律匯編又稱法規匯編,一般是指對現行的規范性文件按一定的標準(按其頒布年代的順序或按其內容或性質)進行整理編排,匯集成冊。法規匯編不改變規范性文件的文字和內容,僅作整理、匯集和技術性的處理,不是國家的立法活動。
法律編纂是指對某一部門法或某類法律內部現行法規進行審查、整理、補充和修改,在此基礎上制定完善的法律的活動。法律編纂并不是單純的技術工作,而是國家立法活動。這種活動如果是以制定法典為目標,就稱之為法典編纂。⑩
⑦ D.1.2.2.4.《學說匯纂》(第一卷),第23頁。
⑧ 馮象:《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65頁。
⑨ 中國古時用帛或用皮條串聯起來的竹簡書寫,寫完后卷起來收藏,因而習慣于用“卷”作為古書的計量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608頁。
⑩ 馬新福主編:《法理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頁。
B11 [日]穗積陳重:《法典論》,李求軼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4頁。
B12 法律匯編可以按照制定的年代排序,也可能是按照法律的主題分類匯集。當然,兩者結合也并非不可行。1956年,國務院法制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編輯委員會開始編輯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1959年改由國務院法制局、國務院法規編纂委員會編輯,1960年初由國務院秘書廳、國務院法規編纂委員會編,下半年起僅署國務院法規編纂委員會。1954年憲法制定前,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輯《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5卷。其編輯方針均是按照法律(令)法規制定的時間劃段,每卷中先載法律,后刊法規。法規部分再按主題分類,同類中按發布時間排序。
B13 前引B11,第57頁。
然而,若據此便說可以很直觀地將民法典編纂與民事法律匯編區別開來,卻倒也未必。日本學者穗積陳重指出,“法典編制的體裁,從古至今不出一軌……或者伴隨法律發達的順序而編成,或者按法令頒布的年月而編輯,或者根據國號的順序而整列法規,或者依邏輯的分類法而排列法規”。按照他的概括,法典編制體裁可以分為沿革體、編年體、韻府體(筆者稱之為字典體)、論理體四種。其中以論理體的法典“范圍甚廣”。B11據此來看,即使僅是把法律按照頒布時間順序排列起來,也可以構成一部法典,從而明顯不同于有的學者將法典編纂和法律匯編嚴格區分開來的觀點。B12
比如蒂利安皇帝時,薩爾維烏斯·尤里安努斯編纂的《永久告示法典》仿十二銅表法,其內容依次為:第一編關于召喚,第二編關于對審,第三編關于附托物,第四編關于盜竊,第五編以下為有關主法的法規。B13
又如《狄奧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是羅馬帝國第一部正式的官方法律匯編,于429年和435年兩度編輯,438年編成。429年,狄奧多西二世任命了一個委員對法律進行編纂,但未能實現他編纂全部法律的計劃,于是他決定將一般諭令重新編纂在一部法典中。這項工作于435年至438年完成,內容涉及自君士坦丁皇帝以降的3000多種諭令,B14共分16卷:第一卷法院構成,第二卷訴訟法,第三、四、五卷契約法、遺囑法以及繼承法,第六、七、八卷行政法,第九卷刑法,第十、十一卷租稅法,第十二至十五卷地方行政法,第十六卷寺院法。B15438年2月15日,狄奧多西法典在帝國東部地區生效。該法典被傳到羅馬的元老院,并與439年1月1日在帝國西部生效。B16
再來看優士丁尼的《國法大全》。其中的《法典》結構為:第一卷寺院法官,第二卷訴訟、律師,第三卷訴訟、地役,第四卷附托,第五卷婚姻監護,第六卷奴隸、繼承、遺囑,第七卷時效、判決以及控訴,第八卷養子、贈與,第九卷犯罪,第十卷財政、公務,第十一卷船舶、土木,第十二卷位階、職業。B17
到優士丁尼《法學匯纂(Pandecta)》中,各卷的內在邏輯才比較明了:第一卷總則,第二卷法官,第三卷物權法,第四卷質入法、借貸法、婚姻法、監護法等,第五卷遺囑法,第六卷繼承法、債務法,第七卷契約法、私犯法、刑法、控訴法、市府法、解釋法。B18但這種安排與其說是法典編纂技術上的進步,還不如說是該匯纂作為教科書所必需的。
和《學說匯纂》一樣,由特里波尼安、狄奧菲爾和多羅特編輯的優士丁尼《法學階梯》被稱作是法學教科書也許更為合適。其共分4卷,于533年11月21日公布,12月30日生效。B19優士丁尼皇帝在世時就規定,《法學階梯》要成為學習法學第一個學期的教科書,然后要在第四個學年結束前的各個學期中學習《學說匯纂》;最后要在第五學年學習《法典》。B20朱塞佩·格羅索指出:
優士丁尼皇帝在公元533年12月16日的諭令中提供的【了】關于教學次序的信息,皇帝在這項諭令中決定根據編纂工作開展法律教學的改革。優士丁尼在這里似乎談的是在各學年中閱讀的著作;但在所提及的著作中只有三部涉及古典學者,即蓋尤斯的《法學階梯》(以此開課),帕比尼安的《解答》和保羅的《解答》(以此結束四年級的課程)。其他著作只要求閱讀有關的內容,它們是四部單編本(libri singulares),一部涉及早期的嫁資規范(de illa vetere re uxoria),一部涉及監護(de tutelis),第三部和第四部涉及遺囑和遺贈(de testamentis et legatis);這些單編本配合第一學年對蓋尤斯《法學階梯》的閱讀。此外還提到的有:一部“第一部分法律(prima pars legum)”,其中的一些章(quibusdam certis titulis ab ea exceptis)應當在第二學年教授(tradebatur);一部“關于審判的法律(pars de iudiciis)”和一部“關于物的法律(pars de rebus)”,這兩部分中有些章是在二年級閱讀的,有些章是在三年級閱讀的。
B14 費安玲主編:《羅馬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
B15 前引B11,第57頁。
B16 [意]斯奇巴尼:“序”,《學說匯纂》第一卷正義與法·人的身份與物的劃分·執法官,羅志敏譯,[意]紀蔚民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頁。
B17 前引B11,第57頁。
B18 前引B11,第57頁。
B19 [意]朱塞佩·格羅索:《羅馬法史》,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頁。關于《法學階梯》的公布時間,《Imperatoriam敕令》第8條稱“12月前的第11日發布于君士坦丁堡”。前引第一版序言給出了正確的日期。[意]桑德羅·斯奇巴尼:“第一版序言”,載《法學階梯》,徐國棟譯,阿貝特魯奇、[意]紀蔚民(朱塞佩·德那其那)校,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I頁。但中譯本第二版對諭令第8條的注釋有誤。
B20 前引B19桑德羅·斯奇巴尼書,第I、II頁。
B21 前引B19朱塞佩·格羅索書,第336—337頁。
第一部分法律,關于審判部分和關于物的部分同《學說匯纂》的前三部分相對應。優士丁尼在進行教學改革時決定:這三部分仍應閱讀,但應當采用“完全經過更新和潤色”的文本,因此,這更像是對先存的教學匯編的修訂和完善,而不像是一種重新(ex novo)創造。
在這里有可靠的根據可以確認,那三部分在教學中閱讀的法律是優士丁尼編纂者在《學說匯纂》的相應部分中加以利用的連鎖材料。上述四部單編本也同樣如此[關于這一點,人們注意到,優士丁尼及其同時代的人把《學說匯纂》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各編稱作“單編本(libri singulares)”]。B21
由上可知,歷史地看,法典與法律匯編之間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法典名下,可能只是既有法律文本的匯集,也可能是用作教科書的內容。即使以“法典”為名,其所記錄的內容之間卻未必有非常合乎邏輯的關聯。
前引法理教科書作者雖然說“法律編纂是規范性文件系統化的高級形式”,但其同時也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單行法形式的立法較多,法典已不像之前那樣盛行”。B22事實上,近代以來,西方大陸法系各國民事立法雖然極大地強化了內部的邏輯結構,但這種努力卻又受到法律在因應社會經濟變遷過程中不得不進行修改的影響。穗積陳重很早就已指出,法典編纂的完成并不能停止法律發展的腳步。B23回顧《法國民法典》以來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立法實踐不難發現,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民事單行法不乏先例:《瑞士民法典》B24之外另有《瑞士債務法》;日本也通過單行法對其民法典加以修改,“依單行法或特別法的制定的修改,則為數很多,這是日本民法典修改最常見的方式”。B25由于“特別法適應于特定的事項以及特殊類型的關系,抽空了法典法體制的內容,表達出具有相當普遍的重要性的原則”,B26因此,意大利法學家那塔利諾·伊爾蒂寫道:“如果伴隨著特別法緩慢但頑強的侵蝕,涉及最具有社會意義的事項的規定已經從民法典中剝離,而使得它成為對一些剩余的事項的規定,那么確認民法典的普通法的特征又有什么意義呢?”B27
鑒于此,中國在準備自己未來的民事法律時也需要認真思考采取的立法形式問題。在中國,犯罪與刑罰、民事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規定,B28但全國人大會期短暫(每年十幾天),議程又非常緊張,B29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于一部法律至少要進行三次正式審議,B30舉輕以明重,這意味著全國人大多次審議一部卷帙浩繁的“法典”在操作性上幾無可能——若是僅經過一次審議便付諸表決通過,未免有走過場之虞——因而可能的結果便是將“民法典”拆解開,化整為零,分別表決通過,最后再合而為一,統一印成紙本。然而若真要這樣做,問題便也隨之而來:保留目前既有的單行立法模式(當然要對其加以適時修改)到底有何不妥?在網絡時代法律數據庫發達便利的情況下,制定一部巨無霸式的“法典”,其必要性究竟何在?
B22 前引B10,第329頁。
B23 穗積陳重的原話是“法典不能伴隨社會的進步”、“不能包含法律之全部”、“不能終止單行法”、“不能終止裁判例之必要”、“未必會減少訴訟”。前引B11,第17—23頁。
B24 《瑞士民法典》,殷生根、王燕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B25 陳國柱:“譯者前言”,《日本民法典》,陳國柱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
B26 [意]那塔利諾·伊爾蒂:《解法典的時代》,薛軍譯,載徐國棟主編:《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4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頁。國內討論“解法典”的論文參見陸青:《論中國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現象》,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6期,第1483—1499頁。
B27 前引B26那塔利諾·伊爾蒂文,第97頁。
B28 《立法法》(2015)第8條。
B29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常委會會議一般兩個月舉行一次,有特殊需要時可臨時召開。據周偉教授統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每年的會期為:前六屆都未超過30天;第六屆會期共258天,平均每年51.6天;第七屆平均每年41.2天;第九屆會期共166天;第十屆共159天,平均每年31.8天。而第九屆和第十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的議案總數分別為427件和462件,其中有關法律的議案分別為232件和160件。支振峰:《中國立法:人大主導還是行政主導?》,資料來源于網易財經:http://money.163.com/15/0402/11/AM60DJVT00253B0H.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9月8日。
B30 《立法法》(2015)第29條。
B31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引用法律、法令等所列條、款、項、目順序的通知》(1956年12月22日)。
B32 比如,梁書文、回滬明、楊振山主編的《民法通則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就是以《民法通則》條文為綱,間或加入評釋和其他法律、司法解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一部民事法律匯編。因其目錄只開列了民法通則的條文,因此要查找具體的規范,往往要逐頁翻找查詢才行,使用上并不便利。而且由于法律來源蕪雜,一旦出現某部法律文件更替,該書就要做傷筋動骨的手術。這對一部工具書而言,也許尚可接受,但對一部有法律效力且效力長久的“法典”來說,則會是個致命傷。
B33 當然,《刑法》在修訂時已經采用了修正案的方式,刪除條文時其條文序號仍然保留;增加條文時,只列為“第N條之一”,值得稱道,也值得其他法律修訂時仿效。
篇幅過大除了會給立法制造不便外,在之后法律實施和修改中也會帶來高昂的成本。面對一部繁厚的法典文本,使用者需要依賴目錄的指引檢索具體條文。但中國立法通常區分的編(總則、分則、附則)、章、節、條、款、項中,款無序號,條以下無名稱,B31因此讀者依靠目錄只能查到節一層,想要具體到條,就需要逐頁翻檢。B32此不利之一。不利之二是,目前中國的法律修訂大多采取將被刪除的條文連同原來的序號一并去除,然后再“刷屏”重新確定條文序號的方法。B33此舉固然會使法律最后的條文數等同于法律的全部條文數量,但也導致修訂后的文本與先前文本之間出現斷裂,給司法實踐和學理研究引用法律帶來麻煩。
三、法典編纂與民事司法實踐
制定“法典”面臨的更大問題則是如何處理新規定與之前既有的法律規則與實際做法的關系。優士丁尼頒布《國法大全》時,試圖廢除先前所有的法律;拿破侖在編制法典時也廢除了新法適用范圍內的舊法的效力,以期創立一個全新的法律秩序。B34盡管這事實上并不能阻止舊有法律進入新法典,但對于既有法律體系而言,仍然會造成割裂的后果。
在未有“民法典”之前,中國的民事立法絕非白紙一張。經過30余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由《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擔保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繼承法》《收養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等在內的內容相對完整的民事法律體系。由這些民事法律又派生出許多行政法規、司法解釋和判決。
圍繞著如何處理既有的民事單行法與“民法典”的關系問題,至少有兩條進路可供選擇:一是小修小補,將民事單行法串聯貫通,再冠以“民法”之名;二是推倒重來,將既往民事單行法律悉數舍棄,找一張白紙,“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問題是,前一進路與坊間常見的民事法律匯編在形式上的差別著實有限;而后一選項不僅直接影響到既有民事單行法律的去留,也會波及到衍生規則的取舍。一個可資類比的例子是,2013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公司法》進行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即于次年2月通過了《關于修改〈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決定》(法釋[2014]2號),用《公司法》(2013)中新的條文序號替換掉司法解釋中援引的《公司法》(2005)中的條文序號。在采取單行立法模式下,由母法的改變造成的影響其范圍尚屬有限,而在匯眾為一的“法典”模式下,一旦作為基礎的法律改易過于頻繁,或是改動的條文數量過多,就會產生明顯的杠桿效應或多米諾效應。大量既有規則的突然更動,容易在實踐中引發混亂,更不要說之于學界的“立法者修改三個詞,就會使所有文獻成為廢紙”的宿命。B35
B34 [美]約翰·亨利·梅利曼:《大陸法系》,顧培東、祿正平譯,李浩校,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頁。
B35 [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頁。
B36 前引B26那塔利諾·伊爾蒂文,第83頁。
如果為了制定嶄新的“民法典”而更易法律規則,有時會迫使包括司法判決在內的一些既有做法失去法律依據,而“中斷傳統和變動不居不僅改變個人的規劃,使預期落空,而且違反自然法”。B36這顯然不利于法律經驗的積累和凝聚。有鑒于此,中國未來民事立法所要采取的形式,仍然是個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
Abstract:Historically speaking, as an early form of statutes, “code” was named from its materials on which it was written similar to table and metal tripod. In modern times since the World War II and as the social economy evolves, it has become a trend that particular or special statutes of civil law have deviated from the civil code. Thus doubts arise 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ivil code as mother law since its substance has been depleted. Nowaday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ivil code in China would be a great challenge for both legis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aw. In specific, several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such as what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code and the existed special statutes; how to coordinate the new code with the previous legal system which has been performing for decades; and how to ensure the previous system would not be split or deserted by the new code.
Key words:codification of civil law consolidation of law legislations on civi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