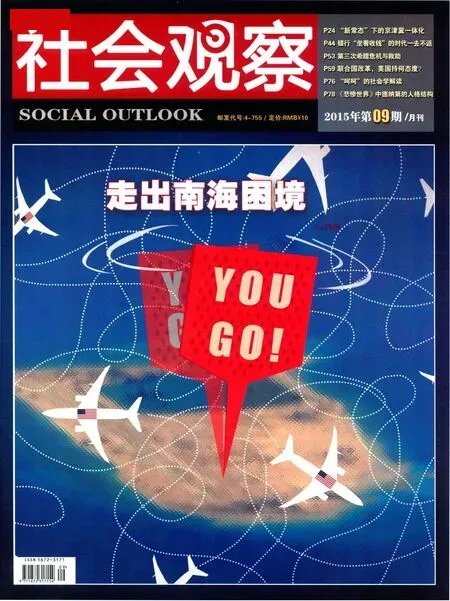“新常態”下的京津冀一體化
文/叢屹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是“新常態”下的重大國家戰略:作為歐亞大陸橋的東北亞支點,與“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呼應勾連;作為東部沿海區域,內含“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國家戰略;作為東部三大經濟圈域之一的環渤海區域核心地帶,“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其轉型發展的重要內涵。
“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重大國家戰略自2014年初提出至今,經過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多方探討,已經形成“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并發布。盡管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從設計框架看,規劃綱要基本上確定了以北京為“中心”的三地分工布局。很明顯,從戰略規劃提出的意圖看,“一體化改革”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核心目標。
眾所周知,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結構性失衡。十八大以來,新一屆政府關于“三期疊加”、“新常態”的論述,高度概括了我們當面經濟形勢所面臨的問題,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勢在必行。不僅產業結構面臨升級調整的壓力,區域結構也同樣面臨升級調整的壓力。
從區域和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區域結構調整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內涵,京津冀區域的問題具有典型意義。截至“十二五”末,盡管京津冀三地在總量增長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其發展中的結構性問題非常突出:三地產業結構互補性差、合作水平低,規劃發展上行政區隔、地方競爭行為明顯;經濟落差大,“先進的歐洲城市”與“落后的非洲農村”并存的現象突出,京、津兩個超級大城市周邊就是“環京津貧困帶”;區域城市體系分布極不合理,北京“大城市病”突出;資源、環境壓力巨大,對可持續發展構成挑戰;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區域計劃色彩較濃,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較差;等等。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傳統政府管理的體制機制困境,而要突破傳統政府體制機制障礙,就必須“打破一畝三分地”,采取頂層設計,以“一盤棋”的思路來實現協同發展。
對“一體化”目標的認識
歷史是不可逾越的,不同區域在文化、基礎、制度變遷路徑上的不同,決定了其模式選擇往往不能全盤照搬,也不可能簡單地搞全國“一刀切”,必須因地制宜尋求創新突破。與長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水平較低,其實現“一體化”目標客觀上需要體制機制的轉換時間,應當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盡管目前各界對“一體化”還有一些不同認識(例如,近期內童大煥、任志強等人的看法),但從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區域一體化是提高區域整體發展水平的必由之路。“一體化”并非“均質化”,從“行政區隔”到區域一體化,顯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逐步推進、不斷完善的過程。
區域一體化的推進,不僅涉及增量調整,而且涉及存量調整,甚至涉及“觸動靈魂”的問題,其現實難度遠遠比書面上的研究要復雜得多,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因此,在現實推進的步驟和進度安排上,不但要考慮區域內各地方的資源、基礎和制度條件,還要考慮發展的階段性要求和經濟形勢的階段性特點,協調好“一體化”各個子目標的先后次序和銜接關系,由易及難、重點突破、層層遞進、堅持不懈。
協同發展中的“一體化”邏輯
“一體化”是協同發展的目標,協同發展強調的是分工合作,因此,“一體化”也就并非“均質化”,而是合作制度框架下的市場一體化、要素一體化。

資源條件、環境約束是京津冀區域合作發展的基礎。目前,京津冀三地的總體發展共同面臨資源約束和環保壓力,三地既需要共同承擔“節能減排降耗”的任務,又要面對三地在發展水平上客觀存在的梯度差異,協調好成本分擔和轉移補償的關系。補償性原則在三地協同發展中是需要考慮的,歷史上先進城市對落后地區的虹吸效應,是形成區域內發展落差的主要原因,現階段需要先進城市對落后地區進行反哺,才能由“先富”帶動“共富”。這種關系,不僅存在于京、津兩個超大城市與河北之間,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于京、津兩地之間。所以,正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北京作為首都,因功能過多和資源過于集中出現了嚴重的“擁堵”,需要對外疏解“非首都功能”;天津需要提高發展能力和水平;河北則需要發展機會和優化產能。由此,也不難理解,實現協同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對資源配置進行存量上的調整,以擺脫現有的“馬太效應”。這不是簡單地靠市場機制所能解決的問題(其實這些存在的問題本質上是一種市場失靈現象),需要“政府有為”,在總體規劃上進行頂層設計,這也是規劃綱要的本質所在。
交通一體化、信息一體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先期目標。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一體化,是協同發展的基礎條件,協同發展不但要盡快解決各自為政的“斷頭路”現象,還要盡快實現以公共交通為核心的交通體系和以通信為核心的信息基礎體系的互通互聯。基礎設施的一體化,是協同發展的血脈,“主動脈”和“毛細血管”構成的網絡,要在不斷優化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全覆蓋。其中,主要城市節點應盡快實現快速軌道交通網絡的覆蓋,壓縮區域交運的時間成本。
金融一體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市場一體化的重要內核。“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需要資本力量的支持。但單純依靠市場力量的金融創新,往往難以擺脫資本的逐利屬性和短期屬性,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往往只會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引導社會資金投入到區域開發領域,往往需要政府層面主導的金融創新,組建區域開發銀行、采用PPP模式等。我們現在有幸看到了這方面的舉措和創新正在積極開展。
社會管理一體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最終實現形式,也是市場一體化的終極制度基礎。新型城鎮化最終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人的流動自由,往往是市場一體化的最高形式。社會管理一體化的核心內容是公共服務的一體化,正如目前積極推動的“包括建立區域內統一的公共就業服務平臺和勞務協作會商機制,落實養老保險跨區域轉移政策,統籌三省市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等”。社會管理一體化的實現,預計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需要逐步推進,“成熟一項、推出一項”。
需要格外關注的幾個問題
區域一體化,是城鎮化的高級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城鎮化,曾經一度成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但截至“十二五”末,以往的城鎮化與投資驅動型的增長模式、加工貿易為主的外需拉動模式以及土地財政為主的城市開發模式連為一體,導致了嚴重的“不完全城市化”現象,最終導致我們在城市化速率最快的時期(城市化率達到50%左右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卻開始放緩,出現了理論與現實的悖論(有學者定義為“城市化陷阱現象”)。所以,區域一體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策略選擇,不能沿襲老路,必須充分吸取之前的經驗和教訓,闖出一條以效益和質量為核心的新路。
首先,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的典型案例,也是我們對傳統城鎮化的糾偏,是對各自為政、以GDP為核心、土地城鎮化過快的城市化路數的修正。新常態下,傳統的城鎮化面臨困境,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產能結構粗放、效益下滑,產業結構調整困難重重。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僅要解決三地之間的結構優化,更要結合當前國家宏觀上的產業結構調整方向。自2012年起,作為東部沿海三大經濟圈域之一的京津冀,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結構升級的壓力逐漸凸顯。所以,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是“新常態”下的重大國家戰略,與其他國家戰略是相互支撐、相輔相成的關系:作為歐亞大陸橋的東北亞支點,與“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呼應勾連;作為東部沿海區域,內含“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國家戰略;作為東部三大經濟圈域之一的環渤海區域核心地帶,“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其轉型發展的重要內涵。
其次,按照2013年“7.30”會議提出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思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改的框架設計要求,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要內涵是創新,是治理模式創新、行政體制改革、深化市場經濟、社會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創新綜合。一些傳統增長模式的積習和弊端,必須予以修正。例如,比較突出的現象,前期熱炒保定房價、近期通州房價上漲,實際上反映的仍然是土地財政思維和投資驅動增長的傳統路數。我們現在必須深刻認識到,靠以土地開發和房地產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走到盡頭了,其過度超前發展已經嚴重破壞了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平衡關系。房地產、股市等虛擬經濟的發展,一旦脫離實體經濟發展所需,就產生泡沫化風險。所以,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所提出的土地市場一體化,我個人認為,不是簡單地把土地買賣放在一起,而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包括耕地和建設用地)的制度創新。創新城鄉用地制度,才能避免走過去土地財政的老路,把實體經濟的發展成本降下來。如果不是依靠這樣的創新支撐,局部房地產市場即使因為規劃熱起來,即使通過傳統“國N條”的調控模式,也難以獲得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了。這方面的問題,必須慎之!
再次,談一談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眾所周知,京津冀區域的“人與資源”和“人與環境”的關系是比較緊張的,生態系統已經相當脆弱。即使我們現在遭遇增速放緩的壓力,也不應該放棄淘汰落后產能、淘汰“冒煙”產業的決心。生態環境的保護,必須在形成共識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聯動機制,避免以往地方政府出于GDP政績觀考慮的地方保護主義的出現。對于一些能耗大、污染重的重化工業,一方面要采取經濟手段(如建立統一的排放權交易市場)和法制手段督促其通過技術創新節能減排;另一方面必須通盤考慮,在規劃布局上適度規模集中,杜絕各地分散發展的問題。
最后,談談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以創新為內核。相較其他區域,近年來京津冀區域的創新體系和創新能力發展迅速,但區域內的創新格局并不均衡,創新資源和創新能力評價上,北京遙遙領先于天津和河北,在科技研發和科技金融方面尤其如此。從規劃綱要上看,北京作為科技中心作好基礎研究創新,天津研發轉化,河北推廣應用。大體格局如此,但目前仍缺少聯動機制。創新的轉化應用,需要完善的區域創新系統和產業氛圍。從目前區域科技創新評價體系評估的結果,我們不難看出,京津冀區域的短板主要在于國有經濟占比過高,民營經濟總量小、活力不足。所以,行政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為加快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打好基礎,才能逐漸提高市場機制決定資源配置的能力,激發區域創新發展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