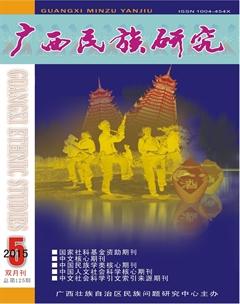駱越文化研究一世紀(下)
覃彩鑾 付廣華 覃麗丹
【摘要】駱越是商周至秦漢時期我國南方百越民族中生活在嶺南西部地區的重要一支,因其分布地跨今中國和越南兩個國家,與中國壯侗語民族及東南亞侗臺語諸民族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關系,而且文化燦爛,特色鮮明,因而很早就引起中外史學界特別是中國和越南學者的關注。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外學者便開始對駱越歷史文化進行研究,至今已近百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本文通過對百年來駱越文化研究的回顧、反思與辨正,以進一步充實、拓展和深化其研究。【關鍵詞】駱越文化;壯侗語民族;銅鼓文化【作者】覃彩鑾,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付廣華,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民族學博士;覃麗丹,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民族學碩士。南寧,530028【中圖分類號】 K28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5-0091-008ONE CENTURY OF THE LUO YUE CULTURAL STUDIES (PART Ⅱ)
Qin Cailuan, Fu Guanghua, Qin LidanAbstract: The Luo Yue group w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the ethnic Bai Yue (hundred groups of the Yue people) inhabite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of China from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territory of their distribution covered across the present China and Vietnam. There are close historical and ethnic original links between Luo Yue and ethnic groups of the Zhuang-Dong linguistic family in China and of the Kam-Tai linguistic family in Southeast Asia. They boasted rich culture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thus attracted attentions of historia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specially the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cholars from very early. Scholars from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tarted to conduct researches on the Luo Yue culture since the 1920s, nearly a century till present. Many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y reviewing, rethinking and distinguishing right from wrong of the century-old studies on the Luo Yue culture, this paper further substantiates, expands the fields and intensifies the research.Key Words: ?Luo Yue culture; ethnic groups of Zhuang-Dong linguistic family; bronze drum culture(接上篇)二、越南學者關于駱越文化的研究今越南是古代駱越分布的重要地區,因而,越南學者與中國學者一樣,是駱越問題研究的主體。不僅研究的學者人數眾多,投入的力量大,其中既有學者自覺的研究,也有國家研究機構組織開展的研究,而且研究領域廣,持續時間長,取得的成果多。需要說明的是,自秦始皇統一嶺南后,今越南一直處于中國封建王朝的統一管轄之下,在其地設置郡、縣或部、府、州等;宋代以后直至明清時期,越南歷代雖然建立了獨立政權,但仍然屬于中國的“藩屬”,一直流行使用漢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因此,越南學者研究駱越歷史文化所依據的文獻資料主要是中國史籍。越南官修的典籍最早成書的時間是13~15世紀,如用漢文編纂的《大越史記》(1272年)、《越史略》(1377年)、《嶺南摭怪》(1492年)、《大越史記全書》(1479年)等;而《越史通鑒綱目》《大南實錄》《大南列傳》等則是19世紀才刊印問世。這些官修典籍中關于駱越的記載,也多是轉錄中國史籍中的記載。20世紀初,越南已有學者對駱越歷史問題進行研究。如1917年,在河內師范學校任教的著名歷史學家陳重金出版了《初學安南史略》,1918年更名為《越南史略》再版,此后連續五次修訂再版(1992年由戴可來譯成中文并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時更名為《越南通史》)。1954年越南(北方)解放后,相繼建立了歷史、考古、民族、藝術等研究機構,加上各大學從事歷史教學的專家學者,形成了一個歷史、考古、民族、文學、藝術的研究隊伍,包括駱越在內的越南歷史研究逐漸發展起來。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越南全國的統一,越南歷史研究進入了繁榮發展的新時期。尤其是越南當局實行親蘇反華政策,其歷史研究被烙了深深的政治印跡,“越南民族英勇抗擊北方侵略”“中國侵略論”等貫穿于各類史著中。駱越史研究亦然。
綜觀越南學界對于駱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駱越起源與分布,駱越建立的初級國家及雄王、越南青銅文化、東山銅鼓研究,越南民族與駱越關系研究等方面。
(一) 駱越起源與分布
關于駱越的起源與分布問題,同樣是越南史學界研究的重要問題。在陳重金《越南通史》、明錚《越南史略》、陶維英《越南民族的起源》(1950年)、《越南歷史》(上下冊,1955)、《越南古代史》(1957年)以及越南教育部《越南歷史概要》(1955年)史著中,認為越南歷史上來源于中國北方,駱越始祖為“炎帝、神農氏之后”,“炎帝、神農氏之后才有駱越、雄王”。20世紀70年代以前,這一觀點為許多越南學者所認同。越南學者在論述越南民族祖先駱越的來源時,多引用《大越史記全書》(1479年)外紀卷一中所云:“初,炎帝神農氏三世孫帝明,生帝宜。既而南巡至五嶺,接得婺仙女,生(涇陽)王……(雄王)建國號文郎國,分國為十五部:曰交趾、曰朱鳶、曰武寧、曰福祿、曰越裳、曰寧海、曰陽泉、曰陸海、曰武定、曰懷歡、曰九真、曰平文、曰新興、曰九德。以臣屬焉。其曰文郎,王所都也。”[1]97-98認為越南境內的駱越先民是由北面(即今中國)的長江、揚子江流域或東南沿海一帶遷徙過來的。陶維英在《越南民族的起源》(1950年)中認為,越南北部的駱越屬百越的一支,應是福建一帶的閩越漁民從海路遷徙而來。這一觀點在后來出版的《越南古代史》(1957年)中得到了進一步堅持。不過,在河內建設出版社出版的另一套《越南古史》中,陶維英提出了新的觀點:“西甌是由陸路從北方來到這里的(指越南北方—譯者),駱越是從海路來到這里的。這兩支不是親屬關系,而是鄰居關系。”[2]
關于駱越的分布,包括陶維英、陳重金在內的多數越南學者認為古代駱越集中分布在今越南北部地區;而分布在今中國廣西地區的是西甌。多數越南學者認為生活在今越南北部地區的是駱越,也有部分甌越(即西甌),故時常稱為甌駱。陶維英認為,駱越的祖先是遠古時代分布在揚子江流域的越族,聚居在荊州和揚州;遷居今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一帶以后,逐漸被中國典籍稱為“駱越”。在《越南古代史》(1976年中譯本)一書中,陶維英提出了上述說法的證據:“《交州外域史》(由《水經注》引)與《廣州記》(由《史記》索隱引)中有關交阯的積雒將、雒侯、雒民、雒田的記載,直到越南民族的貉龍君傳說,都有助于證明雒越是相當于今日越南北部地區。”[3]129 1971年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編著的《越南歷史》認為,甌越主要居住在越南北部山區,駱越則生活在越南北部平原地區。[4]41-42
綜上,越南學術界一般認為駱越來源于今中國江南地區的越族,是通過海路遷居至今越南紅河三角洲一帶的,其后才有了“駱越”之稱。從分布上看,駱越人絕大多數都居住于今越南北寧以北的紅河沿岸和底江沿岸一帶。(二)駱越建立的初級國家及其君主研究
關于駱越建立的初級國家“文郎國-甌雒國”,產生了君主“雄王-安陽王”的問題,是越南史學界重點研究的問題,不僅研究學者多,而且成果也多。在諸多越南歷史著作中,如明錚《越南史略》(1958年中譯本)、陳重金《越南通史》(1992年中譯本)、陶維英《越南民族的起源》(1955年中譯本)、《越南歷代疆域》(1973年中譯本)、《越南古代史》(1976年中譯本)以及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1977年中譯本)等著作中,都設有專門章節詳細論述。
越南學者主要是根據《大越史記全書》《嶺南摭怪》等古籍中相關神話傳說,認為越南先祖為神農氏第三代孫,叫帝明,他開創了鴻龐氏時代,其子孫先后創立了赤鬼國和文郎國,其地域廣闊,由越南北部至洞庭湖,包括中國湖南及兩廣地區。其中,最有名的是貉龍君的傳說:貉龍君娶嫗姬,生百子,50子從母歸山,50子從父歸海。鴻龐氏時代,越南國王先后稱涇陽王和雄王,傳18世,共計2622年,君王20易,平均每位君王在位150年。學者們以此為據,認為越南歷史為上下5000年。
然而,對于駱越建立的初級國家——文郎國及第一代君王——雄王的問題,越南史學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即無論是老一代歷史學家(如陳重金、陶維英),還是60后的史學研究者,其共性都是站在民族主義、維護國家利益和“抗擊北方侵略”的立場上,宣稱“文郎國-甌雒國”是越南歷史上建立的早期國家,產生了第一代君主——雄王,從此開始了時刻抗擊來自北方(中國)侵略的使命。如1971年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編著的《越南歷史》中說:“反抗外來侵略的需要變成了促進文郎社會迅速成長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雄王時期的越南人剛剛擺脫了密林、池沼、暴風、洪水、野獸等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困苦,立刻又要奮起抵抗外來的侵略者。”[4]32-33基于這樣的思維定勢及既定觀點,越南學者對秦始皇統一嶺南、秦末漢初趙佗統一嶺南、建立南越國,以及漢武帝平定南越國,重新統一嶺南等行動,統統都視為是對越南“甌雒國”的侵略。
20世紀60年代以前,越南學者對于駱越問題的研究表現得相對較為客觀。如陳重金于1954年出版的《越南史略》及后來修訂的《越南通史》中,對一些學者津津樂道的“駱越建立的文郎國”和國君“雄王”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認為駱越時期建立的“文郎國:貉龍君封其長子為文郎王,稱雄王,定都于峰州。……縱觀從涇陽王至雄王18世,君王凡20易,而從壬戌年(公元前2879年)計起至癸卯年(公元前258年),共2662年。若取長補短平均計算,每位君王在位時間約150年。雖系上古時代之人,也難有這么多人如此長壽。觀此則足可知道,龐鴻時代之事,不一定是確實可信的”[5]14;又進一步說明:“我們應該知道,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在混沌初期,誰都希望從神話之中尋找自己的根源來光耀自己的民族”[5]17,一語道破關于文郎國和雄王神話傳說的真諦。
陶維英是越南著名歷史學家,熟悉中國史籍,對駱越和越南古代史的研究有很深造詣,成果殊多。自1950年以來,陶維英先后出版了《越南民族的起源》《越南古代史》《越南古史》《越南歷代疆域》等著作。在《越南古代史》中,陶維英提出:“吳士連是第一個將《龐鴻紀》載入我國歷史(《史記全書》)的人。吳士連對龐鴻氏的記載是根據中國載籍中關于交阯與越裳氏的記述,以及后來又依據《嶺南摭怪》一書中有關龐鴻氏的傳說……而寫成的。”[3]34根據中國史書記載及徐松石的觀點,陶維英認為駱越屬百越的一支,駱越是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3]128,與鴻龐氏沒什么直接關系。1971年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編著的《越南歷史》中也認為:“雄王傳十八世,這個數字不一定準確。”[4]36
20世紀60年代特別是70年代以后,越南史學界加強了駱越史的研究,1968年12月在河內召開的“雄王歷史時期研討會”,把駱越史及雄王研究推向高潮。越南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的專家學者代表出席了這次研討會,時任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理范文同親自出席會議并致辭稱:“研究雄王這段歷史是一項有重要意義的工作,而對其即將取得的成果,無論怎么估計也是不會過高的”[6],使出席研討會的學者深受鼓舞。學者們從各自學科的視角,對雒越的起源、越南早期國家的建立、形態、性質、作用及雄王信仰的相關問題進行廣泛探討,會后出版了論文集[7]。與會學者認為“甌駱的主體在越南北部” “駱越是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駱越在四五千前建立文郞國,其北境至洞庭湖;雄王是越南民族始祖”;“越南同中國一樣,是世界文明古國,東南亞文明的中心”等。此次會議后,越南學界掀起了研究駱越歷史、文郎國和雄王的熱潮。越南社會歷史研究所還組織力量,研究和撰寫雄王時代歷史。1970年,由文新、阮靈、黎文蘭、阮董之、黃興五人組成課題組,分工寫出《雄王時代》一書,1976年由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有五大部分:文郎國的疆域、國名和居民;經濟狀況;手工業;社會和政治體制;文化生活;安陽王的甌駱國—雄王時代的結束。作者根據14世紀《嶺南摭怪》《大越史記全書》等史籍中的記述的神怪故事,勾畫出文郎國的疆域:(1)疆域狹小的峰州地區——雄王50個兄弟的居住地。雄王是長子被推崇為王,在此建地國;(2)疆域寬廣的文郎國,“北至洞庭湖南至胡孫國(即古代占城國)” ;(3)疆域范圍較小的文郎國,即由雄王兄弟分別管轄的15個部合并而成,只包括現在廣西的一部分和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北面。1971年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編著的《越南歷史》中稱:“在青銅器發展的時代,越南的歷史進入了雄王時期——文郎國時代。”[4]22又說:“文郎部落的首領在歷史發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他挺身而出統一了雒越部落,建立起文郎國。他自稱皇帝,史稱‘雄王。”[4]23“‘雄王是越南建國初期那些首領的總稱號。我們祖先首先居住的地主是越南北部。領土不很遼闊,人口也不很多,但卻具備了充分的立國條件,具備了足夠的生存和發展的能力。”[4]23
此后,又相繼出版了吳文富等《雄王與雄王廟會》(1996年)、劉雄章《雄王時代》(2005年)、阮克昌《雄王傳說》(2008年)、孟黎《雄王時代:詩歌》(2008年)、文新《雄王時代:歷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2008年)、阮維形《駱越文明》(2013年)等書。
越南學者否定越南自秦朝以來一直是中國封建王朝統一管轄的歷史事實,把中越關系史描繪成“中國侵略史”,聲稱“從四五千前建立文郎國—甌雒國”以后,就遭受北方“中國”強大的封建王朝的侵略;把本來是東漢封建王朝統一管轄下的反抗與征伐(即東漢時交趾征側、征貳姐妹率眾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和馬援率兵前往鎮壓的事件)的性質說成是反抗外來侵略,“二征”也被越南譽反抗中國侵略的“民族英雄”;極力回避越南封建統治者多次派兵侵略中國南境的事實,聲稱:“在整個封建時期一直到今天……從未發生過越南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而據史籍記載,僅公元995年到1214年的200多年間,越南前黎朝、李朝和陳朝三代侵略中國宋朝南境就達十二次之多,其中以1075年李朝侵略宋朝欽、廉、邕三州(今廣西境內)的規模最大,殺害十多萬中國軍民(絕大部分是和平居民),掠奪了七八萬婦女和兒童。[8]一些學者還把越南出土駱越時期銅鼓的年代前推比中國出土銅鼓的年代早,進而斷言越南是銅鼓的發源地,提出中國滇桂川等地的銅鼓是由越南傳入等武斷之論。在越南各類歷史教科書中,大肆渲染中國對越南的侵略,極力頌揚越南抗擊“中國侵略”的“光榮歷史”和“英雄氣概”。
(三)越南青銅文化、東山銅鼓研究東山文化1932 年,R·海涅·革爾登 (R Heine Geldern) 在《遠東印度支那地區金屬鼓的來歷及意義》 一書中首先提出并提議以“東山文化”來稱呼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以外的東南亞全部青銅時代文化。和銅鼓是越南境內駱越時期青銅文化繁榮發展的代表。其青銅器不僅數量眾多,形式多樣,而且紋飾精美,鑄造工藝精湛,風格獨特,堪稱是駱越燦爛文化的重要標志,其中的東山型銅鼓則是越南青銅文化的精粹。因而,東山文化和銅鼓一直是越南歷史學、特別是考古學界著力研究的重要對象。
自20世紀20年代東山遺址被發現并進行發掘以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越南以及國外歷史、考古和民族學界便開始對東山文化進行研究。隨著東山文化類型的遺址的不斷發現、發掘和出土遺物及銅鼓的不斷增多,研究也隨之深入,特別是越南歷史、考古學界,不斷組織專家學者開展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不僅刊發了一系列論文(集)和發掘報告,而且還出版了許多專著。如陳文甲《銅鼓與越南的奴隸占有制》(1956年),陶維英《東山文化與駱越文化》(1957年)、《駱越銅器與銅鼓文化》,黎文蘭《關于古代銅鼓起源的探討》(1962年),黎文蘭、范文耿、阮靈《越南青銅時代的第一批遺址》(1963年),黃春征、褚文晉《東山文化的內容、類型和年代》(1969年),阮文煊、黃榮《越南發現的東山銅鼓》(1975年),范明玄、阮文煊、鄧生《東山銅鼓》(1987年),范明玄、阮文好、賴文德《越南的東山銅鼓》(1990年),黃春征《越南東山文化》(1994年),范明玄《東山文化:同一性與多樣性》(1996年),賴文到《古螺城遺址出土的東山文化青銅器》(2006 年)等。在越南出版的各種版本的通史中,如陳重金《越南通史》、陶維英《越南古代史》、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等,也都設有專門章節對東山文化、銅鼓文化及銅鼓進行論述。
學者們對東山遺址出土的青銅器的種類、形制、紋飾、風格特征及起源、族屬以及對東南亞以至中國西南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等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基本觀點是:東山青銅文化是越南祖先駱越人創造的燦爛文化,對北部(中國)的滇、桂、川地區青銅文化產生影響。東山銅鼓是越南民族祖先最早發明鑄造的,而后從越南傳播到北方的滇地(云南)、桂地(廣西)、蜀地(四川),向南傳播到馬來、椰島(印度尼西亞);歷史上,越南祖先駱越創造“紅河—湄公河”文明;越南與中國一樣,都是世界文明古國。
(四)越南民族與駱越關系研究
關于越南民族與駱越的關系,一直是越南歷史和民族學界重點研究的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在進行研究,70年代達到高潮,其中不僅有廣大學者的研究和發表的文章,而且還有由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機構組織開展的研究。其成果和基本觀點集中體現在幾部重要的越南通史中,如前述的明錚《越南史略》(1958年中譯本),陳重金《越南通史》(1992年中譯本),陶維英《越南民族的起源》(1955年中譯本)、《越南古代史》(1976年中譯本)以及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1971年)中,其基本觀點是駱越或甌雒是今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與中國的壯族及壯侗語諸民族無關。綜觀目前越南學者關于駱越文化的研究情況,有幾個重要的基本歷史事實需要辨正:
1關于駱越的分布問題,中國和越南學者的意見不盡相同。中國學者根據史書較為明確的記載,認為駱越屬中國南方百越族群居住在嶺南的重要一支,分布于今廣西紅水河流域以西至越南北部的紅河流域,南至今廣西郁江流域、廣東雷州半島以及海南島,地理上相連成片;今廣西柳江與潯江流域,為駱越與西甌交錯區域;東北部和東南部為西甌分布地。越南老一輩的歷史學家如陳重金、陶維英等,大體也持這種觀點。但是,后來的研究者則認為駱越分布在今越南北部地區,并且有西甌人南遷至越南北部山區,故統稱之為甌雒。這種觀點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2越南學者所勾畫或構建的駱越時期建立的“獨立國家”(也有說是“首個國家形式出現萌芽”):文郎國(前2897—前258)→甌雒國(前258—208),開國國君:雄王→安陽王,而且把建國年代的上下限及歷代國君的在位時間勾畫得如同信史,其主要是依據成書于14世紀后的《嶺南摭怪》《越史略》《大越史記全書》等越南古籍中的神話傳說(如《金龜傳》《鴻龐氏》《涇陽王》《貉龍君》《安陽王》等)來推定。按照歷史學的常識,作為古代民族史的研究,應以翔實的文獻史料和明確的考古資料為主要依據,并對之進行客觀、科學、嚴謹的考證,以揭示歷史的真實。因而,在歷史研究中,神話傳說只能作為間接的旁證資料,起到輔助印證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僅僅依據神話傳說來認定民族歷史,只能是一種推斷,而僅僅依靠推斷是不能成為信史的。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常識,也是研究者應有的科學、嚴謹態度與學術精神。因此,對于越南一些學者所構建的文郎國、甌雒國以及國君,老一代著名史學家陳重金早就提出質疑,認為是無稽之論,認為“雄王共十八世系平均不可能活到150歲”[5]14。就連代表越南官方觀點的《越南歷史》一書中也承認:《越史略》中的記載“雄王傳十八代世,這個數字不一定準確。”[4]36盡管如此,越南學界依然津津樂道,并以如此悠久的建國歷史而自豪。撇開政治因素,就歷史研究的方法、原則和學術精神而言,僅僅以后世的神話傳說便認定文郎國、甌雒國及雄王的真實存在,本身就不科學、不嚴謹、不可信。
3 關于越南學者所稱的“文郎國→甌雒國”的國家形態與性質問題。近年來,中國學者關于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分期和國家形態、性質的研究,提出了新理論和新的分期法,如蘇秉琦先生根據中國考古學及文獻資料的研究,提出了古國、方國、帝國的分期模式,這是一種新的分期法。他提出的“古國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在原始社會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間或五千年前的若干個地點都已涌現出來。像遼西的紅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前,有祭坊、女神,積石冢和成批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已是古國的形態,即是原始國家形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統發展的各地,古城、古國紛紛出現,中華大地社會發展普遍跨入古國行列。古國時代之后是方國時代,大約距今四千年。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的、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夏以前的良渚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別代表了中國南北早期方國典型例子。方國之后才是帝國。[9]131-197壯族學者鄭超雄在《壯族文明起源研究》一書中認為,方國的出現有如下標志:(1)人口增多,社會分工明顯,有穩定的聚落群;(2)大型墓地出現,有貧富分化的埋葬制度;(3) 開始鑄造青銅器,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青銅文化;(4) 有象征王權身份、地位的文物出土,如銅鼓和各種青銅禮器;(5) 有復雜的宗教祭祀儀式;(6) 有遠程文化交往。[10]比照以上的劃分標準,文郎國(前2897—前258)的年代,相當于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晚期,越南學者根據神話傳說推定的文郎國建立時間為公元前2897年,距今約5000年,此時尚處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還在制作和使用石制工具,由此可以判定,即使當時出現“國”(文郎國早期),實屬古國性質,距離嚴格意義上的“國家”(帝國)尚遠。到了“文郎”后期至“甌雒國”(前258—208)時期,距今約2200多年,相當于中國的戰國晚期,此時出現了青銅器,而且數量眾多,器型多樣,紋飾精美,工藝精湛;出現了城池(螺城),其國性質當為方國,相當于中國商、周或春秋戰國時期的地方方國類型,絕非越南學者想象的“國家”(帝國)。無論是古國還是方國,都是原始社會的氏族向部落、再向部落聯盟發展的必然結果。當時在駱越及其先民分布地區,古國或方國林立,后來,隨著部落兼并戰爭的加劇,一些弱小部落被較為強大的部落兼并后,形成勢力日趨強大、范圍也日趨擴大的部落,古國或方國便應運而生。因而,當時在同一區域的族群內,相互間的戰爭或兼并、以強并弱乃正常現象,并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侵略或反抗侵略的問題。因此,越南歷史上的所謂的“文郎國”“甌雒國”,即使出現過,也是在部落基礎上形成的地方性方國性質,況且終究還是一種推測,尚缺乏直接證據。即使如此,作為追溯一個國家的歷史,構建其歷史發展序列,倒還可以理解。若是以神話傳說當作信史,并以此來編造或確立所謂“獨立國家”的悠遠歷史,并且借此作為攻擊或誣蔑“中國侵略”的歷史依據,那就需要認真考究和辨正了。
4關于秦始皇派兵南征與“秦甌之戰”的地點問題。根據中國史籍《史記》《淮南子》等記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遣五十萬大軍,兵分五路,發起了統一嶺南的戰爭。當秦軍一路軍翻越越城嶺,進入西甌聚居區(今廣西興安縣境)時,即遭到西甌部族的頑強抵抗。初時,面對秦軍的凌厲攻擊,西甌首領譯吁宋戰歿,其部族退入山林,重新集結,推選首領,化整為零,采用游擊戰術,四處襲擊秦軍,使之損失慘重,其統帥屠睢也被擊斃,使秦軍處于進退維谷的困境,只好固守待援。由于秦軍進攻受阻,秦始皇急令史祿主持開鑿靈渠工程,以打通珠江與長江的水路交通。靈渠修通后,秦軍援兵和戰爭物資便可通過靈渠,源源不斷運抵前線。得到兵員和物資補充的秦軍重新組織進攻,很快就擊敗西甌的抵抗,然后長驅直入,很快就抵達珠江三角洲的今廣州,完成了統一嶺南大業。也就是說,秦甌之戰是在靈渠南面附近進行,即今廣西興安縣北境,這是明確的歷史事實。對此,中國許多學者已作了考證和認定,并且形成了共識。另一方面,沒有資料證明,秦軍曾深入今越南境內駱越地,在今越南境內也未曾發生過秦軍與駱越的戰爭。秦軍占領今廣州一帶后,便標志著統一嶺南之戰的完成。秦始皇在今越南設置的象郡,只是象征性的宣示主權羈縻而已,其勢力并未深入其地。然而,代表越南官方觀點的《越南歷史》(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編著)一書中,卻把這場“秦甌之戰”移至今越南境內,而且含糊其辭地說:“秦朝軍隊侵占了長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領土,設立了閩中郡(福建)、南海(廣東)、桂林(廣西北部)和象(廣西西部和貴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當秦朝軍隊越深入到越族地區,它就越遭到甌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甌雒人和其他各民族暫時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們組織抗戰力量,推選杰出的人材做將領,趁夜伏擊秦軍。越族人堅持長期抗戰達十年之久。消滅秦軍十余萬。秦軍的主將屠睢也被擊斃。”[4]49“一支龐大的秦朝侵略軍被打敗和后來趙佗多次侵犯都被我國人民擊退,這一切都充分證明了我國人民具有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同時也說明我國人民已經掌握了抵抗外寇的本領。”[4]51按照該書的表述或邏輯關系,似是在說明秦始皇統一嶺南、設置郡縣之后,秦軍繼而深入甌雒地區,并與甌雒人作戰。這場本是發生在今廣西北部的興安縣境內的秦甌之戰,被越南學者們移到千里之外的今越南北部,以此來彰顯越南民族反抗外來侵略的精神。顯而易見,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5關于駱越是越南民族直接祖先問題。在越南學者出版的諸通史中,都聲稱駱越是今越南民族的直接祖先。眾所周知,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演變的漫長過程。古代民族與現代民族會有一定的歷史淵源關系,但古代民族并不等同于現代民族,古代民族發展成現代民族,經過了長期的演變、分化、重組、交融的復雜過程。這是現代民族形成的基本規律,也是民族學的基本常識。
此外,越南學者所論的以東山文化為代表的越南青銅文化和銅鼓文化的起源、傳播問題,認為越南是銅鼓的起源地,而后北傳至中國云南、廣西、四川,向南傳播到馬來、椰島(印度尼西亞)。對于這些觀點,中國學者已用大量實證資料與研究成果進行了論述和辨正,茲不贅述。三、德國、法國、日本學者關于駱越文化的研究
自20世紀20年代西方學者在越南發現東山遺址并進行發掘以來,特別是越南發現的東山型銅鼓及其它青銅器,引起了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學者的關注。20世紀之初,西方學者就開始對駱越文化的研究,其中以駱越時期的東山文化、青銅器,特別是東山銅鼓的研究者及成果居多。
法國學者沙畹、鄂盧梭等依據中國古籍資料,對駱越和越南民族起源問題進行研究。沙畹認為,越南民族起源于中國浙江省中北部的越國。鄂盧梭在《安南民族之起源》一文中,進一步發揮了沙碗的觀點,認為“廣西南部和越南中北部的部落,最古的名稱,在周時名駱越,在秦時名西甌,一名西甌駱,或名甌駱。可以說,他們代表公元3世紀安南封建部落的全部,分布在廣西的南部到越南的廣南。安南人起源于百越或雒民。這些越人是從浙江、福建遷徙到廣西南端、廣東西南境和越南中北部,是越族中的西甌,或駱民,也就是安南人的祖先。……如此看來,我敢斷言今日的安南人,直接系出紀元前333年滅亡的越國之遺民。而其祖先在紀元前六世紀時,立國于今日浙水流域之浙江省。”[11]117
日本學者對駱越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如松本信廣《越人考》(1943年)、山本達郞《安南史研究》、河源正博《秦始皇對嶺南的經略》(1954年)、藤源利一郞《安陽王與西嘔—越南古代史小考》(1967年)等,主要也是依據中國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進行研究,其觀點與法國學者大同小異。
關于越南東山文化和東山銅鼓的研究,時間早且成果突出者,首推德國籍學者弗朗西·黑格爾(Franz Heger)。他于1902年在萊比錫出版了《東南亞古代金屬鼓》(上、下冊)。黑格爾運用豐富的器物學的知識,把當時所見的165面銅鼓,按照形制、花紋的不同,分為四個基本類型和三個過渡類型,分別探討了它們的分布范圍、鑄造年代和所反映的文化內容。他對銅鼓實體的測量,花紋圖案的傳拓和臨摹,金屬成分的測定,都做了開創性的工作。該書成了二十世紀銅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影響極大。此后近一個世紀以來,不少學者研究銅鼓都是遵循他的觀點,并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斷加以充實和闡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法屬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博物學院成了世界研究銅鼓的重要基地,學者們對亞洲遠東出土的各類銅鼓做了大量研究。1918年,法國學者巴門特(H Parmentier)在河內《遠東博物學院集刊》發表了《古代青銅鼓》,在黑格爾著作收錄的銅鼓之外,新增加了23面銅鼓,進一步充實了黑格爾關于銅鼓的研究。30年代初期前后,法國學者戈鷺波(V Goloubew)發表了《北圻和北中圻的銅器時代》和《金屬鼓的起源和傳播等論文》,根據越南東山遺址同時出土的漢代遺物,確定東山銅鼓的年代為公元一世紀中后期,并對銅鼓的鑄造工藝的來源做了新的解釋。1932年,研究東南亞石器時代的著名的澳大利亞學者海涅-戈爾登(Rodert Heien-Geldern)發表了《后印度最古金屬鼓的來歷和意義》,介紹法國學者戈鷺波關于越南北部的青銅器時代的論文并加以評論。在巴門特《一些新銅鼓》(1932年)、高本汗《早期東山文化的時代》(B Karlgren, 1942年)、蓋勒爾(U Gueler)《關于金屬鼓的研究》(1944年)、萊維(Paul Levy)《第1類型銅鼓鼓式的起源》(1948年)等專著中,學者們發表不少研究越南東山銅鼓的文章。雖然西方學者對銅鼓研究了近一個世紀,但是對銅鼓的起因、功能等問題還是沒有明確的解釋。[12]結語綜觀以往國內外學界對于駱越文化的研究,雖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也存在諸多不足:一是缺乏系統性、整體性的研究及其成果,目前尚未有全面、系統、深入研究和揭示駱越文化的成果;二是中國和越南學者主要是對本國境內駱越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駱越歷史文化及其研究的不完整性;三是應站在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維度,對古駱越文化屬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原文化對駱越文化的深刻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揭示;四是中國學者缺乏對越南學界編造駱越時期建立的“文郎國、甌雒國”“雄王”及“中國侵略論”等進行系統的批駁或辨正;五是尚缺乏對駱越歷史文化資源的全面、深入發掘,缺乏對駱越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與利用的對策性研究。所有這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加強和不斷深化。
參考文獻:[1]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M]陳荊和,編校東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刊行委員會,1984
[2]范宏貴關于越南民族起源問題的論爭[J]印支研究,1982(3)
[3]陶維英越南古代史[M]劉統文,子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
[4]越南社會科學委員會越南歷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5]陳重金越南通史[M]戴可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6]楊立冰評越南史學界對越南古代史的“研究”[J]學術論壇,1983(2)
[7]范輝通,等雄王立國[C]//越南研究會議論文集(越文)河內:社會科學出版社,1973
[8]楊立冰評越南史學界歪曲中越關系史的幾個謬論[J]印度支那,1985(1)
[9]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10]鄭超雄壯族文明起源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
[11]鄂盧梭安南民族之起源[G]//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編北京:中華書局,1958
[12]蔣廷瑜銅鼓研究一世紀[J]民族研究,2000(1)
﹝責任編輯:黃潤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