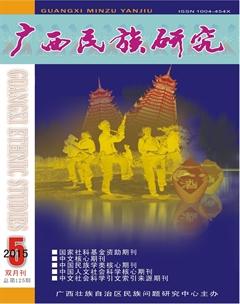國家認同如何可能?
【摘要】國家認同因其對國家、社會安全穩定的重要作用而成為國家建設的主要內容。建構國家認同的基礎要素可從生物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三個層面來理解。但在當下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要素。實際上,國家認同建構是一個需要雙重用力的綜合架構,應在具體的歷史情境邏輯中來理解。從中西方古代王朝國家認同至近現代民族國家認同建構的歷史來看,建構國家認同的基礎要素,從血緣系譜、歷史傳統與文化到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系統,呈現出清晰的演進脈絡。
【關鍵詞】國家認同建構;基礎要素;歷史邏輯
【作者】暨愛民,吉首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教授,歷史學博士。湖南吉首, 416000
【中圖分類號】 D0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5)05-0011-008
HOW IS THE NATIONAL IDENTITY POSSIBLE?:
BASIC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LOGIC
Ji Aimin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becomes a main par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in term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comprehended in biologic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The institutional ele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esent day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however. Actually,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hich needs dual forces functioning together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Seen from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dynasties to modern nation-stat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esent a clear evolutional context from blood ties,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to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basic elements; historical logic
一般而言,國家認同主要是指人們對其所屬國家的贊同、支持和效忠,反映了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與民族團結有著重要作用,體現出一個國家的生命與意義。[1] 近年來,學界主要圍繞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少數民族地區的國家認同等問題展開研究,取得了相應成果。
參見錢雪梅:《從認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周平:《論中國的國家認同建設》,《學術探索》,2009年第6期;高永久、朱軍:《論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林尚立:《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李禹階:《華夏民族與國家認同意識的演變》,《歷史研究》,2011年第3期;龍耀、李娟:《西南邊境跨國婚姻子女的國家認同——以廣西大新縣隘江村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本文擬在民族政治、社會與歷史的學科視野中探討國家認同建構的基礎要素、主要指向以及歷史邏輯,以期對國家認同問題研究有所推進。
一、基礎要素:生物性、文化性與制度性
在有關認同建構的討論中,曼威·柯司特提出了三個值得注意的觀點:1所有認同都是建構性的;2在認同問題中,真正重要的是,“認同是如何、從何處、由誰、以及為什么而建構的”;3建構認同的材料來自歷史、地理、生物、生產與再生產的制度、集體記憶、個人的幻想、權力機器以及宗教啟示等,但這些材料的意義卻由集體認同的建構主體及其目的來決定。[2]7-8
曼威·柯司特之論提示:第一,國家認同的建構性過程及其復雜性;第二,建構國家認同基礎性要素的多樣性和層次性——既有權力和政經制度等政治性要素,又有血系、生物、歷史、地理、宗教信仰等生物性與文化性要素;第三,個人或社會群體的目的或目標、計劃,決定了建構國家認同諸要素的內涵、意義及其具體的功能發揮。在相當程度上,這些要素在建構國家認同中的定位和重要性,主要由建構者的目的、意志和計劃來決定。由此,建構國家認同的要素,如國家認同的同一性基礎特質,國民身份所蘊含的政治、社會權利與義務,以及歷史記憶與政治期待,已盡在曼威·柯司特所言“材料”的范圍內。
就當下世界各國的實際情形來看,國家認同的建構實踐并沒有一種固定模式。有的走加強政治制度和國家權力建設的道路,有的選擇強調血緣和歷史文化傳統作用的途徑,有的從國民品性、國家公德意識的精神構筑著力,還有的則是綜合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式進行國家認同建構,等等。不同的國家認同建構所定位的基礎要素各不相同,因此,關于國家認同的理解,應遵循具體的情境邏輯。在從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歷史中檢視,上述之基于“族群”“文化”和“政治”認同模式都先后有過明確展現。這也說明國家認同建構在具體時空架構中各自不同的限定性。而就當下世界各國之國家認同建構實際來看,確實很難說是以族群血緣譜系、歷史文化傳統,還是以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因素作為國家認同的依據。
為了更清晰地理解國家認同建構的基礎要素問題,我們可以從生物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三個層面來展開討論。
首先是生物性要素。這主要是指建構國家認同所依據的基礎要素,主要來自于血緣紐帶或族裔身份——更多體現出了一種生物學意義上客觀給定的屬性,即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用以辨識“我們”之一致以及與“他們”之相異、并依此加強“我們”彼此之間一體感的依據,是“我們”之間與生俱來的血緣關聯,或者是某些能證明“我”與其他人同屬于一個族群的自然信息(當然,其中也不乏源自某種具體需要的選擇和改造)。
然而,這種基于族類血緣系譜等“共同特征”而建構起來的國家認同,因目的和計劃對其材料的“創新安排”而有明顯的內在困境,那就是各民族自身認同要素本有的狹隘性和局限性,以及基于這些認同要素之上的共同體認同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大體是以自我族類為其認同中心的。實際上,如古典國家時期依據血緣系譜或族裔身份得來的共同體認同,就表現出明顯的外群偏見。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國家與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主要基于血緣或宗族系譜因素的認同并不能適應國家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所以在國家認同的整體結構中,其主體地位逐漸被基于其他要素的認同所取代。
其次是文化性要素。這主要是人們依據共同的歷史、語言、風習、集體記憶和宗教信仰等要素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從而形成之于政治共同體的一致的歸屬感。需要注意的是,相較于族群認同所強調的血緣關系的生物性內容,文化認同更為凸顯其地域性。因為文化的生成與發展往往有賴于固定地域內長期穩定的社會生產和生活過程,所以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只要是具有較長歷史的國家,在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一般都相當強調對其歷史文化要素的運用。在這樣的國家中,人們更重于以在共同歷史中形成的共同語言、習俗和宗教等文化要素作為辨識自己與他人是否歸屬同一共同體的主要依據。
但以文化要素為多民族國家中國家認同建構的主要依據,也有需要注意的問題。那就是國內不同民族在建構國家認同時,都易于傾向以自我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特質作為起點和依據,導致民族間文化差異的凸顯和強調,不利于緊密的一體性社會聯系和交往交流交融,而民族的自我中心意識則可能趁機發榮滋長,成為建構國家認同的重大阻礙。
最后是制度性要素。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人們就在具體的公共空間中共享具體的人際關系及其建制,并產生了一體的感覺以及延續、維持這種一體性的要求。在這一意義上,人們并不單憑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生物性特質來結成一個共同體,而是在密切的行為互動或相互期待的基礎上,主要依據一系列的政經制度和社會公共規則聯結起來。在由此結成的共同體中,血緣譜系與文化屬性并非其成員集體認同的主要依據,而強調的是政經制度、公共空間規范和公民共同的政治觀念與價值。相較于建立在文化或民族要素基礎上的國家認同,這種建立在政治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基礎上的國家認同顯然反映了國家的更為開放的政治體系,能有效克服共同體內“中心”與“邊緣”、“主體”與“從屬”之間的差異,以及各自因“外群偏見”而產生的排他性和歧視性。
但是,如同基于血緣與文化因素建構國家認同存在著諸多問題一樣,以政治制度、公共規則作為基礎要素建構起來的國家認同,其實踐效果也并非如理論預設中的那樣明顯,而是仍有一些限制。如就近代以來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觀之,國家認同的建構往往也顯示出或多或少的暴力痕跡和政治系統不同程度的強制性操作。以后史實表明,如此之國家認同建構論主要是緣于一定程度上缺乏對國家生成基礎等根本性問題的完整理解,有可能造成對族群、文化因素作用的忽視而埋下國家認同危機的隱患。尤其是,在具體的國家認同建構實踐中,國內各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實際與國家政治體系并非完全相應或同步并進,以致政治制度與公共規范在其作用發揮時因與實際情形的“錯位”而不能收預期之效,從而引發人們對國家政治體系的不滿,產生國家認同危機。
綜觀當下世界各國,絕大多數國家認同的建構實踐表明,往往是以制度性要素為主,同時綜合其他因素而成。如果說古典時代的國家主要靠血系要素與文化認同來維持其成員對該共同體的歸屬的話,那么在自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中,雖然文化認同仍為構成國家認同之不可或缺的重要選項,但更多則得靠政治系統尤其是合理、良善、高效的制度體系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向心力。[3]15-17也就是說,在實際國家建設過程中,人們之所以認同某個國家,不僅因為有著相同的血緣系譜、共同的地域空間或歷史與文化傳統,而且更是因為這個國家在政治組織、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政策等方面能切實滿足國民利益和生活幸福平安的需要,并為之提供保障以及實現更好生活的期待,即合理良善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使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獲得了廣大民眾自愿且持久的支持、信任和效忠,后者亦因此而成為其政治系統合法性的標識。反過來,如果一個國家在制度上不能滿足國民基本的政治權利、生存條件和安全保障的話,那么國民就很有可能不愿認同這個國家。此即謂在當下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要素。
盡管不同的認同主體,在理解國家與建構國家認同時有著不同的視角。如有人認為國家是維護民族文化、實現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組織,所以在建構對這樣一個國家的認同時,強調得更多的是民族國家對自我實現的意義以及自我對國家的情感、歸屬和忠誠奉獻。而有的人則認為國家是應社會生活的有序和人們彼此之間的行為互動的需要而組成的政治共同體,故在建構國家認同時強調認可國家對社會中個體的政治權威和法律制度。就前者而言,其建構國家認同的基礎要素,主要是體現特殊主義價值的血緣種姓、歷史神話、語言宗教和生活習俗,等等,這些都是在過去漫長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因此建構國家認同之族群與文化的基礎性要素往往帶有回向過去的特點,且在特定時期或特定場合下(如傳統國家時期以及由古代王朝國家向近代民族國家轉型的前期)突出表現為一種回溯式、尋根式活動。[3]21—22但在現代社會,國家的組織形式與政治結構已經脫離了血緣與文化紐帶的規制與整合邏輯,而是通過一套清晰有效的政治系統和制度運作,將固定區域內的廣大民眾整合為一個共享該政治安排的共同體,也就是在現代國家之下,人們通過國家的政治體系獲得利益、幸福與安全的保障。所以,認同產生共識的基礎,已經不再是血緣或歷史文化那些太特定而實質的東西,而只能是具備價值與工具合理性的國家政治結構。
也正因為如此,建構國家認同的基礎要素,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才有著明顯區別,在古代王朝國家時期主要表現為血緣譜系和歷史文化傳統,而進入民族國家時代,則主要是具有現代意義的國家政治系統。
二、歷史邏輯:從王朝國家認同到民族國家認同
然而,一般性的討論很難清楚地說明國家認同是如何、由誰建構起來的,以及建構的目的和計劃是什么,建構的結果如何等問題。只有在具體的歷史邏輯中,這些復雜的國家認同建構的理論問題才可能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脈絡和明確的經驗回應。
古代中國的國家認同建構,綜合來看,也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結構,既有依血緣而來的對王朝君主及其宗族系統的認同,也有依傳統政治結構和儒家政治文化而形成的王朝政權認同,還有基于中國傳統歷史文化而來的歷史文化共同體的認同。需要注意的是,這三種基于不同要素而建構起來的認同并非決然可分,在具體的王朝國家中,它們往往同時并存,共同表現出其時國人的政治態度和文化心理。當然,其中也有差異,尤其是不同認同的要素依據,各自突出的程度明顯不同,以致對共同體認同的表現各異。如夏商周時期國家認同就主要表現在基于血緣和宗法政制要素的國家認同,秦漢以后則主要體現為以大一統中央集權和儒家倫理政治文化為核心的國家認同。但不管在哪一歷史時期的國家認同建構,中華的歷史文化傳統卻總是貫于其中,促進或深化不同血緣系譜、不同地域空間和不同文化及宗教信仰群體之間的一體感、認同感,更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而在國人認同結構中,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凝聚民族意識與精神的力量。這也提示在理解古代中國的國家認同時,不能將三者割裂或孤立開來,而要有具體歷史情境下關于國家認同的綜合視野。另外,不管哪朝哪代以及其國家認同的基礎性要素為何,古代中國人的認同構成也與近代人的認同構成一樣清晰,政治認同、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宗教認同、地域認同等相互交融,[4]44共同構成古代中國人的情感世界,表達他們對王朝國家及其政權系統、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服從、贊同和奉獻。
這種在根本上由文化要素建構起來的國家認同,在古代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未發生本質性改變。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方現代文明沖擊之下,人們的王朝國家觀念轉向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觀念,國家認同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傳統的王朝國家認同轉向認同新型的民族國家體制和政治形態,其國家認同依據的要素也就轉向建立在對西方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理解基礎上的政治模式。隨著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與民族危機逐漸加深,尤其是“甲午”戰后,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的精神動力,新型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促使人們的認同對象與認同結構發生變化。但直至20世紀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王朝國家、專制國家才真正完成了向人民國家、共和國家轉變,新型的民族國家認同才完全取代了舊的對專制王朝的認同,并不斷鞏固、深化。
再看西歐的民族國家認同建構,它是在近代以來民族國家確立(nation—building)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眾所周知,民族國家起源于西歐,民族國家認同亦發端于西歐。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原生性、典型性的民族國家認同形成過程,反映了西歐民眾、民族與國家三者之間關系的形成與互動過程。簡單地說,在民族形成與民族國家確立的過程中,民眾一方面將其忠誠集中到民族、國家這兩者相結合的對象即民族國家身上,另一方面,他們又依新確立的民族國家來界定自我個人身份及其所屬群體,同時亦區辨“他者”。
歷史地看來,中世紀初期的西歐,邦國林立的事實表明其時并不存在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組織形態,整個西歐只是一個由教會以其宗教的力量統整起來的“大社會”,其文化要素的作用在這樣的社會形態整合中表達得淋漓盡致。但自13世紀始,世俗王權開始強大,統一的國家機構逐漸形成,挑戰宗教普世主義及其支撐的政治權力。隨著社會變動和王權不斷加強,現實王權脫離了教會控制,建立起了領土相對完整、主權獨立的國家。在相當程度上,這時期世俗王權自然地成了新型國家的標志和象征。在一個統一空間中,共同的經濟關系得到深化,民眾之間的交往得以加強,民族語言迅速傳播,民族文化和教育得到發展,整體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得到升華。以世俗王權為中心,包含國家主權、國家利益等內容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亦逐漸形成。在西歐這一政治組織形態改變和權力轉移過程中,西歐社會廣大民眾的心靈性活動亦隨之發生重大轉向,形成了大眾忠于王權的新的政治認同——由對封建領主和教會的認同轉向了對新出現的民族和國家的認同。但要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王權成為整個國家的最高權威及其管轄范圍內社會各集團的最高效忠對象,圍繞世俗王權而確立起來的文化系統,使民眾通過國王來認同國家,將對國王的忠誠與對國家的熱愛等同起來,所以國家認同的依據主要表現為不同文化要素之間的內部轉換,且血緣因素也時有呈現。誠如后來法國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描繪:“國王的神話粉碎了領土割據,建立了適應經濟需要的遼闊共同體,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聯結在一起。” [5]59
其實在此種狀態之下,西歐民眾關于國家、民族的認知難言清晰。民眾這種對政治現實模糊不清的認識和理解,致使他們表現出來的政治情感——即伴隨著政治認知而形成的好惡、愛憎、親疏,影響著他們的政治辨識、態度和行為選擇——最后,將對國家認同投射在王權身上。不過,在行為主義的政治學理論框架下或具體歷史的情境邏輯中,這種以王權為中心的國家認同其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國家認同作為人們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的一種心理和意識上的歸屬感,它既是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態度、政治信仰等政治文化的幾個基本向度相互作用的政治心理活動,同時又受到政治關系、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6]27-28正如有學者之解說:此際人們對國家的認識尚處于一種朦朧與模糊狀態之中,只有尋求王室成員的具體形象以確立起對國家的認同。也正緣于此,君主與國家等同起來,國王、王朝被人們視為國家的象征和標志,忠君與愛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人們以對君主的熱愛和忠誠來表達對自己所屬國家的熱愛和效忠。所以,隱于王權至上表述思路背后的是,民族或國家等于國王化身以及認同國王即是認同國家的含義。[7]39-40這與古代中國的王朝國家認同在形式與內容上高度相似。從本質上言,西歐民眾這種投射在王權身上的國家認同更多地凸顯出其文化認同的成色。
但從西歐民族國家建構的思想史角度言之,西歐民眾這種以王權為中心的“朦朧”的國家認同仍有重要意義——它以一種社會集體意識形式,描摹著近代民族國家的理想圖景,表現出對民族國家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期望,為近代民族主義興起奠定了社會心理和思想基礎,從而推動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
14世紀后,法國、英國、德意志和意大利等西歐各國的知識與政治精英,圍繞民族國家建構,展開了一系列論述,強調國家獨立、統一、主權和國家利益,要求所有成員認同正在形成的以民族為基礎的政治共同體,服從和效忠民族國家這個最高目標。而實際上,西歐民眾在政治上形成了對王權認同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種共同的文化心理——主要表現在民族語言的形成以及運用民族語言撰寫本民族歷史等方面。在此基礎上,民族意識、民族情感也迅速加強,這種意識與感情表現為“對民族、對祖國的熱愛與歌頌,對祖國不幸的悲哀”,也就是在深層的心理和內在情感上,個人與祖國息息相連,“為祖國的光榮而自豪,為民族的不幸而悲哀,為祖國的未來而祈福”。[7]54這一通過強化民族文化認同,在文化層面表達出來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一方面成為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追求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一種內在動力。因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基礎,除了一致的心理、意識和情感,更需要具有內在一體性的文化認同。歷史地看來,在這一時期,西歐各個民族都在努力完善共同語言、信仰、風習與行為方式,以增強民族文化認同。
但在17、18世紀,隨著西歐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與力量增長,前述之世俗化的王朝國家卻因其專制政治制度而越來越明顯地阻礙了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的建構。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國王完全背離了整個國家的公共利益,人民沒有自由、權利和幸福。由是西歐一批精英開始質疑并抨擊國王作為國家和民族的化身和象征意義,轉移對國王的忠誠。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啟蒙思想家就曾清楚地告知民眾,突出國家中的政治要素:“祖國”是一種新型的民族國家,不僅是一個由土地、河流、山川等構成的自然共同體,而且是以人民的自由、權利、利益和幸福為目的的一種政治共同體,人民與國家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成為國家的公民,有著具體的現實權利和利益。在祖國中,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權利,獲得利益和幸福。祖國和公民之間建立了一種積極正向的對應關系,那就是國家通過政治組織和相應的經濟、法律制度及其有效運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幸福,公民則以熱愛和效忠來表達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國民這種對祖國的親愛情感,產生了巨大力量。一如狄德羅所言:對國家的親愛之情,使得互為競爭甚至是敵對的人們團結起來,調合彼此之間的分歧,相互視為國家的重要成員,在愛國之心的激蕩之下,人們努力地為公眾謀福利,為國家而不惜犧牲自己。[8]250莫里斯·迪韋爾熱則對西歐民眾這種以政治要素為依據的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有著思想史意義的解釋:“君主專制只能構成一種過渡性的神話”,并不能產生新的國家政治實體、制度與相應的觀念體系,并獲得廣大民眾的心理贊同,因為它阻礙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而后者則是要求一種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礎之上的政治意識和政治競爭秩序,但以國王為中心的國家結構卻希望仍“維持一個完全建立在世襲國王基礎上的政府”。[5]59顯然,這必將導致在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權利結構與人們新興政治期待之間的猛烈沖突。因此,其時的歐洲,需要有一種新的不同于君主專制及其觀念框架之下的制度體系和思想聯系,催生祖國觀念,并使全體民眾產生對自己國家的熱愛之情。
迪韋爾熱的解釋說明了其時西歐民眾關于民族、國家認識的深刻變化和建立新型民族國家的要求——這樣一個政治共同體,已非專制王權時期的君主、領土與臣民結構,而是建立在平等的政治原則與制度基礎上的,由全體公民組成的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公民認同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國家則通過各種機器、制度,保護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而公民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熱愛和忠誠于自己的祖國。如法國歷史學家索布爾所觀察到的:此時歐洲各民族,皆完成了各自的整合,“全體公民都匯成一體”,如法國,就由全體法國人結成了法蘭西民族。[9]475
亦可見,其時西歐民眾國家認同的重要轉向,即由以國王為中心的王權和王朝利益轉向了以“祖國”(民族國家)為中心的人民主權和民族利益。也就是,人們在民族文化如民族語言、情感、風習和行為方式等認同的基礎上,確立了一種新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認同,其核心是民主、自由的現代政治制度和價值原則。也就在此基礎上,實現統一民族國家認同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建構。于是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與民族國家的建設(nation—building)趨于一致,民眾對民族國家的希望、追求、忠誠和熱愛,正是民族國家認同的具體表達。
三、結語
從上述歷史事實中,可以發現國家認同建構實際是一個需要雙重用力的綜合架構。具體而言,一方面,需要民眾這一認同主體的用功;另一方面,國家也同樣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其具體的政治組織、法律制度、政治運行措施和價值觀念、意識形態與民族成員形成積極的雙向互動。如建立民主政體與良善的制度體系,以保障每個民族成員的自由、平等和權利,設法培養并強化民族成員對國家的熱愛和忠誠,以及他們與國家的一體感、連帶感,將原始的自發的血緣關聯和基于文化認同上的民族意識與情感引導到充滿理性的政治意域中,實現每個民族成員主動的政治參與,從而使民族成員對政治共同體產生積極的政治認知和政治情感,通過服從、支持和效忠的政治行為來表達人們之于國家的政治態度,最終形成對民族國家的認同。
回到前述之曼威·柯司特關于“認同是如何、從何處、由誰、以及為什么而建構”的問題,并將其引到關于國家認同建構問題的分析上,我們發現,這些問題可具體分解為強調國家認同建構的過程及其基礎要素的作用,建構國家認同的邏輯起點,國家認同建構的主體、客體及其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國家認同建構的目的或目標等問題。具體就近代西歐民眾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來看,在歷史過程中,關于民族國家認同建構這幾個問題的回答其實是很清晰的。西歐民眾經過了從中世紀以來對地域權利和普世主義的宗教認同到以世俗王權為核心的王朝國家認同再到以人民主權、民族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民族國家認同的變化,由基于文化要素而來的超越層面的宗教權力和普世的宗教關懷,到基于民族文化要素的具體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識的養成而產生明確的一體感和歸屬感,最后產生了建立在民主政治與自由價值、平等權利基礎上的政治認同。民族國家認同建構的邏輯起點、過程和終點,建構民族國家認同的基礎要素及其作用皆清晰地呈現出來。
由于國家認同在界定個人自我身份與歸屬的同時,更明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基本關系,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認同主體對其作為國家成員的地位的認知和評估,并由此而產生的價值與感情傾向,因此它至少包括個人關于認知層面的歸類,以及由此歸類而產生的情感和評價等方面的內容。[6]29也就是,圍繞關于國家認同問題中的“我是誰”“屬于哪”“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或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國家”等一系列問題,在認知、情感和評價層面的回答和選擇。在西歐廣大民眾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人們不斷明了或更新自我的身份與歸屬,希望、追求一個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保障他們自由、平等、權利和利益的民族國家。相應地,他們也接受、效忠于這個國家政治、文化體系,信奉、服從這個國家的制度、法律及其安排的秩序,接受國家體系對他們個人的要求和所安排的社會角色。另外,這種民族國家認同也體現出民族國家為鞏固、加強民族成員的對它的認同,而在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等方面所進行的自我形象塑構的努力,以及民族成員國家認同的文化價值皈依、所承擔的與國家象征相聯系的國民角色,接受民族國家之于個人的各類規范。
總體言之,作為一種歷史事實,中世紀時期,西歐即開啟了民族國家的進程,經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以全民族的名義呼吁自由、平等人權和幸福的政治共同體,在民族主義的推動下,完成了對民族共同體的確認。且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勝利,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由西歐向外擴展,推動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進程,民族國家認同亦隨之在世界范圍內興起、展開,影響了現代世界的歷史進程和國際政治格局。但是,西方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認同建構經驗所展示出來的是一種內源型的發生和運作模式,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較之西方模式,卻要復雜得多。如果說西方國家由于民族建構與國家建構往往結合在一起而致其國家認同相對直接且呈單一線性特征的話,那么非西方國家則內因其歷史傳統、族群結構、文化風習、生存環境和發展階段與西歐的明顯差異,以及外有近代以來西方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殖民化程度不同,致其民族(nation)建構與國家建構取徑各有不同而體現出復線的歷史形態。如其民族的形成與國家的形成并不一定同時并進,有民族形成早于國家者,亦有國家先于民族而成者。[7]5前者體現的是由民族而國家的建構進路,后者卻表現為在國家建構完成后,通過國家政治力量的發揮來促進國家民族的建構。這也就使非西方的民族國家認同呈現出遠較西方復雜的情況。
然而,觀乎不同非西方國家的民族國家認同建構,卻還是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一些共通之處。
首先,近代以迄,非西方國家大都因西方列強政治、經濟、文化的入侵而面臨政治、文化和民族的深層危機。因此,在反抗這種外來殖民主義的斗爭中,人們產生了對新的政治共同體的迫切期待。
其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非西方國家大都受西方民族國家現代政治文化和價值觀念影響,人們開始反省自身民族之歷史傳統和文化之于挽救國家危機的有效性,其國家認同發生了現代意義的轉向。
第三,在每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非西方國家內,原本有各自政治或文化歸屬的民族,因面臨西方列強這個共同的強有力他者的挑戰,國內不同民族能求同存異,追求確立新型的民族國家共同體,以解決民族與國家面臨的危機。也就是說,在近代以來反抗西方殖民壓迫和民族救國的斗爭中,殖民地人民很快地完成了自我的身份界定和情感歸屬,主要在政治要素的基礎上建構起一致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認同。
參考文獻:
[1] 林尚立.現代國家認同建構的政治邏輯[J].中國社會科學,2013(8).
[2] [美]曼威·柯司特.認同的力量[M].夏鑄九,黃麗玲,等,譯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
[3]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M].臺灣:揚智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4] 彭豐文.兩晉時期國家認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5][法]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M].楊祖功,王大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6] 楊妍.地域主義與國家認同:民國初期省籍意識的政治文化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 李宏圖.西歐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研究——從啟蒙運動到拿破侖時代[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8][法]德尼·狄德羅.百科全書·立法者[M].梁從誡,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2.
[9][法]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