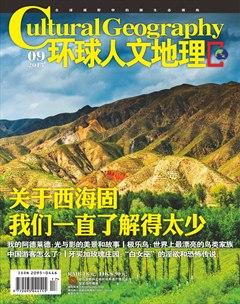歷史城市的空間形態
唐曉峰
在地圖上,城市都是大小不同的點,但實際上,城市是一個社會空間。講城市如果沒有把“空間”講明白,則城市還是一個符號或者“虛體”。地理學研究城市,總是腳踏實地研究城市的實體空間。但城市的空間形態各有不同,背后依托的社會制度及禮法觀念也不一樣,把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才能把城市的一些基本問題說清楚。研究今天的城市是如此,研究歷史城市也是如此。
現在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建筑史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是最重視城市空間形態的,在這些學科的研究中,總要畫出城市的平面圖,雖然是些不甚完善的復原圖,卻也令人有一個清楚的空間印象,知道古代城市是什么“樣子”。有些研究,說了半天城市,到頭來,還不知道城市的東南西北,這能說對城市有“深刻認識”嗎?
比如說,知道秦始皇定都于咸陽的人很多,但秦始皇的咸陽到底是什么樣子,恐怕能講明白的人并不多。知道咸陽城的樣子有什么用?知道了咸陽城的樣子(也就是空間形態),才能理解中國歷史的那場時代巨變,才能知道中國第一位皇帝是何等人物,才能體會他在“統一海內”后“得志而小天下”的氣派。
秦始皇的咸陽是一個極寬廣的地帶,著名的阿房宮,僅其中的一座前殿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而在阿房宮的基礎上,又“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這是何等壯觀的景象!賈誼形容秦始皇“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崤函為宮”就是以崤山函谷關之內的整個關中地區為宮室。果然,后來阿房宮向南的建筑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終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這種無限擴展的都城宮室空間格局,反映了大帝國勝利者無拘無束的宏觀視野。
又如,漢代名臣蕭何曾為劉邦設計未央宮,“宮闕壯甚”,但底層出身當皇帝不久的劉邦不理解,問蕭何:“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夫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后世有以加也。”
城市空間的樣式,不是一件毫無想象、可以隨意而為或無意而為的事。《考工記》是講王朝城市平面規矩的一部書,做皇帝、做大臣的無人不知。另外,每個朝代掌權的人又各有自己獨特的想法。比如曹操,對他的魏都鄴城就有一番獨特的想法,結果造出一座平面空間形態整齊有序的城池,與前朝的城市都不一樣,在中國城市規劃史上具有劃時代的地位,后來的隋唐長安城都受到鄴城規劃的影響。
當今的人文地理學家說,世上有三類基本的記錄與傳播知識信息的“文本”,一是口傳文本,二是書寫文本,三是景觀文本。在景觀文本中就包括了我們所說的空間形態問題。我們“閱讀”空間形態文本,可以明白或發現許多東西。例如,到北京大街轉一遍,就知道當年皇親國戚與草根階級天壤懸隔,大宅門與小胡同各有分辨。
任何社會生活形態在完熟的過程中,都會相應地形成一套空間行為規范,從家庭到社會,從一人到千萬人,無不在空間系統中建立規范。一個時代有一個空間系統,一段歷史有一段空間進程,沒有空間進程不成其為歷史。
西方的一些左派地理學者早已把資本主義的地理進程分析補充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中。他們認為,馬克思原來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忽略了空間問題,因此他們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涉及全球的地理問題。
所以,我們如果不深入完整地觀察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城市的空間形態,會被許多表象所誤導,以為那里的城市普遍繁榮、遍地光彩。地理學家不承認有“均質空間”,比如美國城市地理學家就不斷提醒人們注意那些繁榮城市的“爛掉的心”,即城市內部的貧民窟。大都市空間中的“腐爛”部分與“腐爛”過程是美國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課題。
總之,城市空間形態是城市研究中不可忽視、也不可淺嘗輒止的一個關鍵問題。如果對一座具體的城市沒有什么空間討論,對于城市社會的各個層次只有縱向而沒有橫向的定位,這樣的城市研究只能算是半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