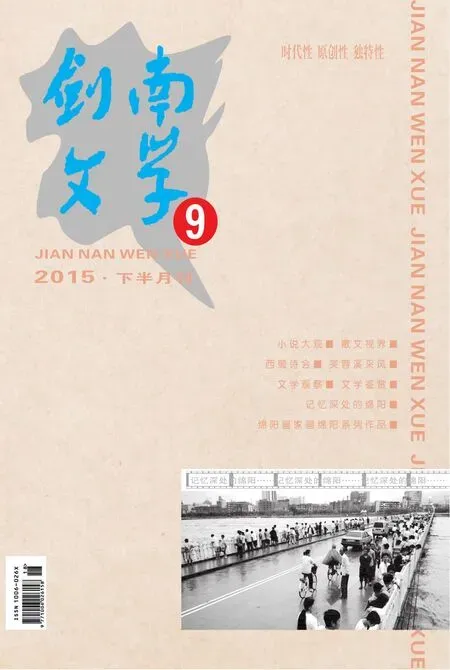對李漁戲曲理論之現代結構思考
■鄧 欣
本文從李漁的立主腦、減頭緒、密針線、脫窠臼四個方面來進行探討來說明。這里說的“結構”不是把現成的各個部分組織起來的形式構造,而是各個部分賴以產生的內在根據。
戲曲結構是李漁在戲曲主題的影響下對全劇人物、情節、矛盾沖突等設計和安排,它在戲曲的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李漁把戲曲結構的作用上升到比音律、詞華更高的高度,提出“結構第一”的觀點。他把“結構”(即指全劇的構思布局)放在首位,這和前人首重音律或首重辭采就有著明顯不同的理解。我認為,站在李漁的戲劇結構概念,不僅僅是“構思”或“布局”,并且包含了結而構之的方法、過程和樣式。結構是指戲劇的整體性,李漁的“結構第一”本意,不僅強調結構在諸要素中位居第一,而在于強調根本性的關鍵要義:戲劇創作必須從整體性的結構開始,結構先于音律,而不是從局部的音律詞采入手。
李漁提出:“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把結構問題提到了“首重”的位置。他用“造物賦形”和“工師建宅”作比喻,來闡明結構的極端重要。在《閑情偶寄結構第一》中“工師之建宅……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后再籌一架,則便于前者不便于后,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戲曲創作也是如此,劇作家“不宜卒急拈毫”,匆忙動筆,“袖手于前,始能疾書于后”,只有結構成熟,方可奮筆疾書。結構是否妥善完整,關系到劇作的成敗優劣,不能等閑視之。只有構思精當,才能揮筆寫作。他的這一觀點與明代王驥德《曲律》中關于戲曲結構的命意相似,但李漁在這兒提出的“結構”卻是出于舞臺搬演的考慮,“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為繡口”,在認識上比王驥德更為深入。李漁緊接著站在戲曲接受的立場上,詳述了當時戲曲創作中存在的缺陷“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局規模之未善也。”研究戲曲結構,元明曲論家已經開始。但大都局限于論述套數曲,即劇曲的布局、章法等等。李漁則在此基礎上提出把注意力集中到“結構全部規模”,開始研究戲曲的矛盾沖突。這對于戲曲的發展,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姚文放在《中國戲劇文化的美學闡釋》提到:李漁這里的結構,“并不完全等同于現代文藝理論所說的‘結構’,還關涉到人物塑造、戲劇功用、藝術真實、藝術創新等方面,比現在所說的作為藝術形式要素的‘結構’更寬泛,包含著某些藝術內容的成分”。
李漁在“結構第一”之下,列有“立主腦、脫窠臼、密針線”等專節,開拓研究戲曲結構的新領域。李漁提出了“立主腦”的原則,即要求戲曲創作要為“一人一事”而設,并以此體現“作者立言之本意”。“立主腦”是李漁結構論的主干,就是體現作者“立言之本意”的主要人物和主要情節。李漁認為沒有“主腦”的劇本,充其量不過是斷線之珠,有見識的藝人必然望而卻步。“立主腦”,離不開“減頭緒”和“密針線”。一個劇本如果頭緒繁多,“旁見側生之情”眾多,其戲劇沖突必然枝蔓不清。頭緒既清,緊接著還要“針線”緊密。李漁有一個妙喻,“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這些見解精辟地揭示了編劇構思的特殊規律。一件結構十分完好、巧妙的藝術品,常常贏得人們 “天衣無縫”的贊譽。然而,藝術畢竟是人工的產物,是具有一定思想感情的人以審美的方式對自然的寫照,對現實的把握、反映和表現。那么,藝術品又怎么能被制作得如此“巧奪天工”呢?如果單從表現方法上來考察,那應該說主要是得力于藝術家運思、結構、布局的細密和精當,這是一個藝術家布局、結構的才能和工力達到爐火純青地步的一種標志。狄德羅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有美妙的想象力;考察事物發生的順序和聯系;不怕難寫的場面,也不怕工作費時;由主題的中心直入;仔細辨明劇情開始的時機;看明白哪些東西應該放在后面;知道哪些場面能感動人;這就是人們據以布局的才能。”戲劇作家必須培養和鍛煉自己的這種才能。而李漁的“密針線”,正是論述了戲劇結構才能的一個重要方面。
“密針線”要求緊密情節結構,前后照應,使全劇成為渾然一體,不能有一點疏漏;“減頭緒”則要求曲家思路不分文情專一,使戲中主線清楚明白。“脫窠臼”,即題材內容應擺脫陳套,追求新奇,重視創意;在“立主腦”這一原則的敘述中,李漁在《閑情偶寄》中說:“后人作傳奇,但知為一人而作,不知為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則可,謂之全本,則位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卻走也。”在表達“密針線”和“減頭緒”的方法時,李漁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觀眾應接不暇,演員頻上頻下,舞臺混亂,審美價值缺失。俞為民在 《曲論研究》中提到,“李漁所說的‘主腦’,不是劇作的主題或作者的創作意圖,而是指一部傳奇的核心關目,即‘一人一事’。”“一人”是指劇組的核心人物,“一事”指傳奇的關鍵情節。李漁對戲曲結構的強調,不僅是指對各類型材料的剪接組合,而且是指由一事作為生發點、關鍵點,有此貫穿全劇,組合成為有機和諧的藝術整體。李漁的“一人一事”說與金圣嘆的“一人”說有著承繼關系。金圣嘆在《西廂記讀法》中說:“西廂記只寫得三個人,一個人是雙文,一個人是張生,一個是紅娘……譬如文字,雙文是題目,張生是文字,紅娘是文字之起承轉合,有此許多起承轉合,便令題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題目也。”李漁要求戲劇結構必須“脫窠臼”,主張“非奇不傳”,也是從總結傳奇創作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經驗而來,特別是力圖對當時戲劇創作中的某些不良傾向進行針砭,起到積極的匡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