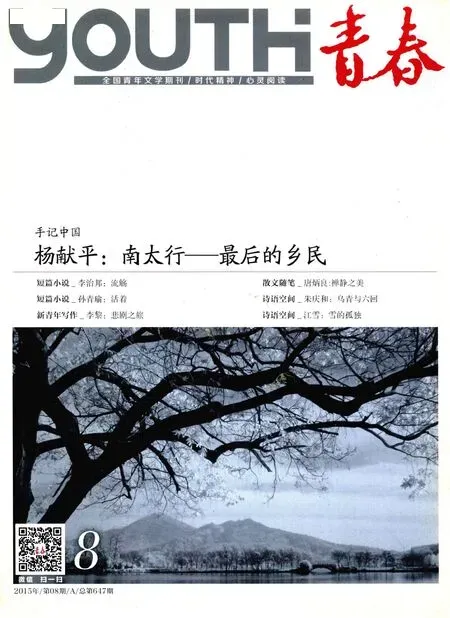時光,植物
2015-11-19 01:03:12吳祖麗
青春
2015年8期
吳祖麗
爬山虎
五月,爬山虎已經很綠了,綠里透出海水一樣的藍。清晨的陽光從樓頂照下來,爬山虎的葉子染上了金色,反射著海水般的粼粼波光。整個五層大樓的西山墻綴滿綠色葉片,一絲空隙也沒有。葉葉向上,承受光芒又穿透光芒,葉脈縱橫交錯,一如我們手背蜿蜒行走的血管。一些虬曲纏繞的老根忠實地守在低處,則像黑色雕塑,印著刻刀的沉默。一陣小風吹過,葉子微微翻轉,羞澀地露出淺綠的另一面,像在尋找風從何來。
20年過去了。20年的光陰緩慢而耐心地雕刻了一株爬山虎,也只不過令它從纖細的幼苗變成滿墻綠蔭。
但是,20年對一個人來說,是漫長的跋涉和剝奪,是近乎四分之一生命的流逝,說起來想必都是一言難盡的。
那時候,爬山虎剛剛培土新植,映在一樓玻璃門上的身影,是一襲藏青背帶裙配白襯衫,在立繅車臺里浸泡過的雙手捧著一疊表格,猶自散發著淡淡的腥味。是蠶蛹尸體腐爛的味道。那段日子,我認識了一些年輕美麗的女子,跟一些泡得浮腫發白的手指的主人做了朋友,漸漸習慣周圍無處不在的腥膩味道。
實習結束,我坐到質檢科最末的一張桌子前,爬山虎已經攀上二樓陽臺,秋陽滑過,葉葉肥美,蜜蜂終日縈繞不去,原來葉子底下竟有了細碎的淺金色花蕾。辦公室六個人,都是女的,每天下午四五點鐘,就會有五個孩子放了學,拖著書包來找媽媽,吵吵嚷嚷地在走廊打鬧,偶爾也伏在辦公室里溫書寫作業。……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