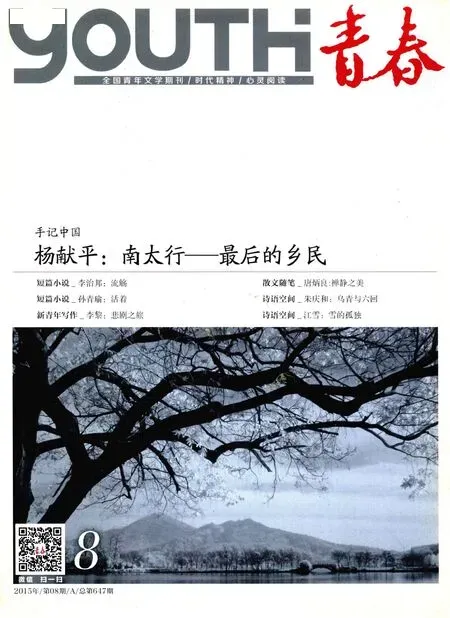流觴
2015-11-19 01:03:12李治邦
青春
2015年8期
李治邦
一
李重3歲才張口說話,這期間,他父母到處找醫生給他看病,怕他是一個啞巴。李重張口說話的第一個詞匯,我餓了,而不是喊爸爸媽媽。那一句我餓了,把他父母嚇得臉色雪白沒有明白什么意思,李重又重復了一句,我餓了。
李重父母都是市里重點中學的老師,一個教語文,一個教數學,這就是天作之合。所以李重6歲上小學時,家里人都認為他是個不用怎么下工夫就能成為好學生的孩子。可沒有想到他語文和數學總是排在全班倒數第二或者第三,弄得他父母沒有顏面。可李重就是一張好嘴,討得老師和同學們都喜歡他。到了他上中學,父親已經是學校的校長,就想方設法給李重弄到自己學校,他要親自看著孩子有沒有長進,因為再沒有起色就可能考不上大學。李重依舊不怎么樣,有次考數學竟然不及格。為此,他母親大哭一場。父母讓他跪搓板,李重就跪在那開始叨叨,天文地理,說得亂七八糟,就是不停嘴。最后父母無奈讓他起來,因為實在忍受不住耳邊的聒噪。到了高中,李重的成績依舊不見好轉,倒是在學校組織的一次演講中一鳴驚人,拔得頭籌,他演講的題目是:你要到巴黎和倫敦看看。就這么一個不著邊際的主題,聽得大家聚精會神,鴉雀無聲。他父親也不明白,李重這個逆子怎么有這么好的演講能力,其實就是在臺上胡說八道,因為他說的很多巴黎和倫敦情況都是他自己瞎編,因為他帶著李重去了一趟上海和廈門,里邊的很多事情都發生在那里。……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