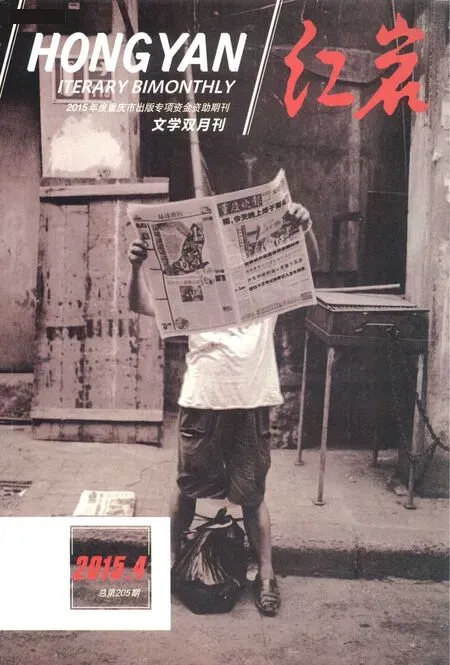頑固之石
趙衛(wèi)峰
一直以來,雨田在詩界里的頑固之態(tài)有目共睹。他自足地建筑那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與喧嘩的時勢潮汐保持距離,保潔沉思,像急流后、浪淘過的強(qiáng)硬之石,一位對包括自我的一切都一如既往地苛刻的頑固派。
“你像我一樣 生長在一個殘疾的時代真的/我們在崇高 自由和愛的陰影里掙扎/直到人世間沒有喧嘩 也沒有痛苦……”(《西峽銀杏樹》)置身于一個殘疾的時代,無力與憂郁難免,在這里,詩人的孤獨(dú)與平衡感借助銀杏而煥然;出身在幾億年前的銀杏號稱“活化石”,同類與同伴們都已仆倒滅絕,投降于滄桑變換,但這“堅強(qiáng)不屈的美人”頑固地活著,讓詩人嘆為觀止,心曠神怡。
上引這詩可能不算詩人的代表作,它蘊(yùn)含的相對的“溫柔”勁對于雨田也并不常見,卻可窺見詩人精神的某一層面。而一塊很硬度很密度的頑石,有沒有接近它的捷徑呢?
在集中地讀到雨田數(shù)十首以游歷或風(fēng)景為表面主題的詩作后,我注意到,“水性”的波紋暗暗地圍繞這塊“頑石”, 河流印象或以此為過渡的相關(guān)表達(dá)不時呈現(xiàn),它們多是低抑和暗淡的。在這透明透亮而又彎曲粘連的流動中,雨田或沉靜,或不安,沮喪感時有體現(xiàn)。在《城市與河流》一詩中,雨田對河流的低度描述更為明顯,對河流的大多不愉的印象,潛在地反映著詩人對“動蕩不安的時代”的矛盾心情?
不安自然是必須的,沮喪也并非貶義,強(qiáng)硬之石當(dāng)然亦需要借力運(yùn)行和自我調(diào)整。河流、流水、水對于人的意味,往深處聯(lián)想多有滋潤、孕育、包容、洗刷、清新等功能,而對雨田來說,我更愿相信每當(dāng)他在觸及這種軟濕的半明半暗的意識流時、他在需要適合的表達(dá)工具的同時,有意無意地涉及的還有自我凈化的潛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