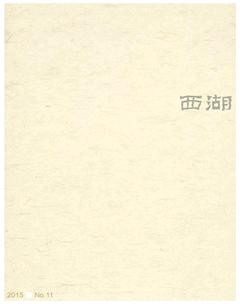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項靜
林森的長篇《關關雎鳩》與他的中短篇小說集《小鎮》有很多重合的部分,從人物到故事,以及那些影影綽綽的與作家自身經驗重合的部分,帶給我們一個異樣的海島小鎮世界。但他的中短篇小說并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青春期的故事見聞和原生態的人物故事,都點到為止,像皮影戲幕布上激烈晃動的人物故事,又像這些年來我們習以為常的文藝片,那些在大時代里東倒西歪走形的人生,對外面的人來說新奇而熱烈,但跟常見的期刊小說并無多少差異,很難吸引一個外來者去投射出自己的情感,并且深感自己也活在這個世界的一部分里。這或許就是許多寫作者的一個誤區,以自造的特殊性制掣了小說世界本身的寬松余裕,以及由此而來的直面生活和自己的機會。
莫里斯·迪克斯坦在梳理小說歷史的時候說,人們曾經有過這樣的共同假設:賦予文學以意義的一切其他要素——對語言和形式的精通,作者的人格,道德的權威,創新的程度,讀者的反應——都比不上作品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那么重要。我們無需費力追究論證是否真的曾經有過這個假設,但這的確是一個好問題,好問題的價值就在于,即使它經不起推敲、容易帶來反例,但依然是一種啟示,而好的小說也往往就是一種啟迪,比如巴烏斯托夫斯基對蒲寧小說的評價:“它不是小說,而是啟迪,是充滿了怕和愛的生活本身。”有各種自成一格、圓滿自足的小說學,但我們依然無法否定,小說就是關于我們在文學之外的生活的,關于我們的社會活動、情感生活、物質生活以及具體的時空感。
我也會問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為什么要閱讀一個作家的長篇,去經歷一次跟自己沒有關系的漫長生活,在多如牛毛的長篇中,不是應景,又如何選出一個作家一篇值得閱讀的小說?評論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一句話深得人心,“這個作家處理語言的方式或者看待生活的觀點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他們就像魔鏡一樣,讓我們窺見半隱半現的自我,并經歷認識自我的震撼。”《關關雎鳩》滿足了這個要求,以至讓我覺得這是這一代人(陳舊的“80后”作家的稱號)中到目前為止,最為成熟的長篇小說之一。林森在《百感交集的聲音》一文中說:“生活那么豐富,可我只能選擇一種。回到島嶼——文學總要回到飽含生命熱度的狀態中去,不會永遠都和話題、時尚、娛樂有關……沒有辦法走向一個更廣闊的天空的時候,我們只有往回走,找到那個可以遮風擋雨的故鄉。有一天從海島上傳出去的聲音,肯定會帶著海風的味道,帶著碧藍的顏色,也帶著綠意盎然的勃勃生機。”《關關雎鳩》是一個來自島上的聲音,它平實而凄厲,敦厚而喧鬧,它敞開了滿載著愛和怕的生活本身,龐大的生活軀體,讓人無暇顧及島嶼的痕跡。我們從來都是對生活本身感興趣,不是對某種生活的獵奇,忠誠地寫出自己的生活要比刻意地強化自己一隅的生活來得有力量。
一
《關關雎鳩》以一九九四年軍坡節為開端,這個兼具傳統、封建、迷信、狂歡、榮耀、記憶、惆悵的節日,像波瀾壯闊統攝一切的大海,每一個小鎮人的神經都會隨之起伏。小說中的人物,以潮汐的方式,一寸一寸爬到沙灘上來,往返不停,突然掀起巨浪,來到軍坡節這個節點。明媚燦爛的一面是,一九九三年夏天,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正在神州大地上生機勃勃,鎮上成立了以殺豬佬歪嘴昆為校董的私立小學,并且延請到退休的教出奧數獲獎學生的老師。經過一九九三秋到一九九四夏整整一年的努力,私立小學已初見成效,不少學生在考試中力壓瑞溪鎮中心小學,殺豬佬天天嗓門奇大酒量倍增,滿嘴“拔你母”都帶著光榮與驕傲。少年潘宏億們天天吹號子,正在等待他們生活中最重要的節日——軍坡節,裝軍游行,一個回望和重振古代威風的節日。如此聲勢浩大、隱忍著巨大能量的開端,就像特地為了宣告另一個時代的開始,而且是一個虛弱、走形、喧嘩、堰塞聲聽的時代。吸毒佬曾德華的偷盜行為就像一只耗子,賊溜溜地進入這個空間一閃而過,帶著不祥的氣息,半瘋半癲的落魄大學生王科運張貼大字報揭發曾德華,由此,二人的混戰幾乎搶了軍坡節的風頭。這是一個粗野、混沌、熱鬧、但向上的故事開端,每一個故事中人都像沒有瀝干水的抹布,帶著濕漉漉的原生態,每一個人都掏心掏肺地活著,毫無遮掩,打架、偷盜、賭博、罵人、嘲笑、嫌棄,連少年潘宏萬都那么正義凜然,要拼盡力氣去追趕盜賊。
而整個小說中最年長、最有生活經驗,也是最主要的人物老潘和黑手義,卻是兩個心事重重的老者,兩個人在這個民眾狂歡似的節日里,陷入各自的惆悵,他們深陷在各自的“病根”里苦苦掙扎。老潘因為年輕嗜賭,間接導致老伴早逝,這個往事讓他始終生活在愧疚中。他的身體在心事壓力下,變得幻聽嚴重,被似真似幻的小號聲折磨得幾近崩潰,他心里發虛,迫切地感覺到生命中的晚年正劈頭而來,心口抽緊,眼皮亂跳等等,他一直都覺得是去世的老伴,糾纏著他。不過一九九四年的裝軍游行,治愈了他的憂郁,小說對游軍做了一番熱血昂揚的描述,“整個游行隊伍已經不是在裝軍了,他們本身已經是冼夫人的將士,滿腔豪情,即將揮灑血汗,滅盜平賊。他們的腳步踩出力度,他們的神情飽含榮耀。”這給老潘陰冷鬼氣的生活帶來了蕩滌出新的機會,他被洗禮出陽氣和健康,“老潘隔著人群,隔著些許的距離,隨著隊伍,走進迷蒙又清晰的往昔。近來那些糾纏著他的事,在此時,在隊伍過去又折返之后,漸漸清晰又漸漸散去。他沒確定是不是已經看清了午夜醒轉時墻壁上的空無,是不是已經清楚那間日本樓里的隱藏,是不是已經聽清楚那時時回旋在耳的鳴響,但,這都不重要了。天氣這么悶,他出了一身汗,衣服淋漓,他想,該下樓沖一個涼水澡了,然后,去買些菜回來,準備招待今天到家里來的親朋。”
黑手義是最害怕過軍坡節的一個人,每年進入六月他就開始失眠、流汗、暴躁,最嚴重時還會嘔吐發燒。病根就是他頭婚的大兒子,在軍坡節上門尋祖,卻被群打誤傷,而后又遭到現在老婆兒子們的反對阻攔,無法入得族譜。大兒子后來英年早逝,留下孤兒寡母,兒媳楊南帶著孫子孫女來到鎮上討生活,他們像歷史的遺腹子,一直盯著他,讓他無法忘記過去。黑手義的軍坡節恐懼癥,和楊南從今年年初把女兒、兒子安置在新街有關,和當年那場發生在他家里的打架有關,和楊南的兒子垂首等在他門前有關,和他拒絕幫楊南有關。臨近軍坡節,黑手義不得不把每件事情都與自己的心病聯系起來。不過對于黑手義來說,軍坡節的停辦也是病情的緩解劑。
一九九四年是一個轉折之年,以軍坡節停辦劃下一道線,在小說中,則是神明不肯附身“降童”,“每個人都沒料到,這一年之后,安穩、靜默、封閉、單調又雜亂無章的日子,隨著裝軍的遠去而頻生變化。”林森的《關關雎鳩》沒有做出“關心世界”的姿勢,但小說講述的年代還是泄露了許多時代的密碼,一九九三年的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市場經濟興起,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由此拉開序幕,八十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劇褪去,老潘和黑手義這樣從村里奮斗到鎮上來的尋夢之旅也逐漸變得困難。從小鎮外面的世界來看,房地產市場、股票證券市場、開發區建設等一下就使得市場化的潮流涌動起來,在拉動經濟的同時,導致急劇的分化和腐敗,這些宏大的詞匯都在小鎮生活中有所體現。黑鬼這種有關系、腦子活,敢于搞事情的人成為小鎮上的成功者,他開賭場、暗中慫恿白粉市場的存在;蛤蟆二這種兼具黑社會、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角色,一路通吃;鎮政府形同虛設,政府官員的高度腐敗與整體性道德敗壞,經歷了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無賴,最后走向黑社會化的一個過程。在小鎮居民彷徨無措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向政府伸出手,王科運這個喜歡報告的人也轉而依靠在鎮上到處貼大字報。中國市場經濟確立的時間大概在1993—1995年間,這個時間段位于士紳社會、人民公社之后,在這兩個階段,小鎮或者鄉村的居民,從精神到倫理上,都有一套“群社會”的結構,有一套生活政治、公共政治的法則,包含了各類生產關系組織形式,也承繼了家庭文化的精髓。但一九九四年以后,小鎮居民是被趕到了荒野上,個人、國家(基層政府)、集體(家族或者村社)三層結構幾乎等同于一個結構,都成了孤零零的個體,地緣鄉情的紐帶七零八落。
二
軍坡節的時候,黑手義的孫女張小蘭想起自己的父親(張英杰),“不能不想起他衣服上的油污,不能不想起他在省城那家窄小的修車鋪,不能不想起他用胡子扎她時的麻癢。她當然更想起父親在時,她就是一個溫柔羞澀的女孩。她更忘不了那個把全家人的一切都帶走的時刻。”最令人驚醒的一句話是:“父親離開之后,她變得暴戾而尖刻。”整個瑞溪鎮在“軍坡節”停辦之后,無疑也走在一條暴戾而尖刻的路上,人們無所依傍,人們因茫然而到處投靠,《關關雎鳩》之中一直有一個“問鬼神”的路線,瑞溪鎮上的人們一旦生活事業上有了問題,在危機的關頭,總會去問石頭爹、六祖婆、五海公,甚至去問被降童的王科運。可能有人自然而然地把海南島上小鎮的生活方式簡單類比成一個馬爾克斯式的文學問題,其實這可能是一個誤解,這只不過是一種當地人或者說當代中國小鎮居民精神迷茫的形式和寓言式呈現。人們從一種安穩、直接、親近自然、天地一體的鄉村社會,來到小鎮社會或者說行政體制上的鄉域社會,在經濟大潮的直接粗暴沖擊下,在缺少國家政治層面的精神引導,和民間組織內部的歸屬和規范時,每一個人都成了被撒在荒野上個體,每一個人都驚慌失措,病急亂投醫。鎮上的生活是一點一點開始變化的,而青年們是最早被投入慌亂和漩渦中的人群,比如青年隊群體的歸屬感和儀式感的尋找,鎮上的生活乏味枯燥,每個青年人都喜歡讀武俠小說,喜歡看香港傳過來的武打片,于是紅毛升成立了龍虎會,在同學之中耀武揚威,讓青年潘宏萬很羨慕,但是他又被排除在外,無法進入到這個組織中。于是,潘宏萬在翅膀硬起來之后,首要的目標就是在高中成立了一個小幫派,小弟二十幾個,橫行校園里,威風八面。張小蘭退學跟黑鬼住在一起,后來帶著弟弟張小峰也住進來,黑鬼開賭場。張小蘭對跟黑鬼住在一起也是猶猶豫豫,但對一個失去父母保護、被爺爺黑手義拒絕的少女,在瑞溪鎮橫行的黑鬼是一個安全感的來源。黑手義的兒子許召才本來老實勤懇,但他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震撼,看到賭客一捆一捆地賺錢,頓時沖垮了他的安心和本分。小鎮的環境已經完全改變,家破人亡屢見不鮮,打架、賭博、嫖娼都在人們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所以許召文在永發鎮的發廊里找妓女,本來聰明并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潘宏億去吸毒,就勢在必然,就是讓黑手義、老潘這一輩人痛感的無力回天。
王科運的瘋癲歷史就是一部分當代知識分子的生活史,陰差陽錯地卷入政治事件,沒有成為烈士,卻葬送了個人前程,于是一個個性張揚、試圖走向廣場的知識分子,被拉回到小鎮生活政治的圈子里。實際上他仍然還有其他選擇:成為初中物理老師、成為小學老師,甚至成為一個小商販(他的粽子很受歡迎),但是他一直在延續廣場政治時期的被迫害的思維方式——告發與揭露擰結在一起。他告發學校領導貪污教室修建錢款,被停職,后來一發不可收,到處貼大字報,從貪污腐敗到個人私事的兄弟分家、婆媳爭吵都是他貼大字報的內容。他像一根長長的魚刺,扎在小鎮人們的生活中,吐不出咽不下。他會揭發曾德華吸白粉偷盜的事,也會因為賭博的啤酒機往縣城、縣委書記“便民信箱”上投信,上書“瑞溪人民期盼安寧生活,希望政府給下一代營造一個無賭的健康環境”。
王科運的生活發生改變是在一九九七年,他自稱五海公“降童”在他身上,自從末屆軍坡節之后,五海公就再也沒有顯現過,此時他毫無預兆地降臨,降臨到王科運身上。王科運的能力就是挖掘瑞溪鎮人們的秘密,搞得小鎮上人人提心吊膽,害怕被他曝光,同時他的預言能力,也讓瑞溪鎮上的故事充滿了荒誕和“絢爛”的色彩。王科運這個人物特別類似2011年導演韓杰的《哈嘍,樹先生》,同樣都是直面底層現實的視角和“冷靜地呈現變革中國及其人物命運和傷口”式的人文情懷。生活在城鄉結合部的大齡北方青年樹,性格懦弱,生活工作郁郁不得志,且因童年時期父親錯殺哥哥一事留下陰影,神智開始有些錯亂。口中常常念叨先知式的預言,而他的預言荒誕離奇,卻成為地方實力派和富翁眼中的“大師”。王科運在集資事件、吸毒、賭博等事件中,都扮演了拆穿者的角色,他用降童的方式,讓人們半信半疑;卻又像預言者,每一次都言中揭穿了人們遮遮掩掩不敢相信、不忍直視的真相,他以妖魔化的方式為小鎮降魔除妖,這個妖魔主要是指心里的妖魔。
小鎮的混亂終于走到了極端,迎來一個階段性的最重打擊——為錢瘋狂,大家瘋魔了一樣把錢投給三多妹,等待不勞而獲錢滾錢。王科運依然堅持不懈地搗毀這些迷幻,每天醒來,街上就多了無數張字跡清晰的紙,寫著:某某,某某和某某某,到三多妹那里投了多少錢。王科運沒有多加評論,只在每張紙的最后,用紅色的筆寫了一行字:“小心被騙。”之后就是王科運被打,被打斷手指,讓他無法書寫,這是對他貼大字報的報復。這一次連王科運都要求助于五海公顯現,“抽掉他王科運內心所有的迷亂與癲狂,所有的死腦筋和不識相,所有的痛心與傷懷,讓他在這場雨水之后,重新做人?”這是小鎮人們心中的瘋子王科運第一次帶有自我反思的語言,連瘋子都知道自我反思了,那真正瘋狂的就不是王科運,而是他人。“王科運想,誰被騙,誰不被騙,關我什么事呢?那些人貪錢,舉止何嘗不比自己更加癲狂?我又管他們是否被騙呢?關我鳥事?被騙了才好,誰讓他們貪得無厭?”王科運終于正常思維了,不再是偏執的思維,而是像蕓蕓眾生一樣,以自我為中心,不再關心他人的偽裝、苦難、公共的福祉、廣場上的事情,他被瘋狂的人們趕上庸眾的舞臺。小鎮上的最后一次預言,已經不是王科運的手筆:“三多妹不見了。”剩下的就是小鎮上瘋子們的游戲和表演,父子反目,夫妻分離,層出不窮。
三
祭祖歸家是作品中一直渲染的一種最重要的生命的儀式感。張英杰一家每一個人都在對此求之不得的路上,成為嚴重的心病。每到清明、春節等節日,張小峰的同學都有老家可以去,有墓可以掃,有祖可以祭,而他家人從沒有過,他隱約能感覺到父親張英杰為什么會回來認黑手義。黑手義一直對六角塘祖婆的預測耿耿于懷,“前面的事情做不好,后面的事怎么能做好?房子的地基沒埋好埋正,墻能不歪?”而老潘的親家公打鐵公,則是一個被兒子們拋棄的人,這讓他死不瞑目,尸體都不肯就范,以致師傅公不愿意為之舉行齋事,他說:“打鐵公跟鐵一樣硬,肯定是心中有事,肯定是有一口氣還沒順過去。氣還堵著,事還憋著,都還沒理順,我哪敢做齋?你們把他的身子順過來。”全家人都在石頭公面前痛哭流涕,訴說往日的怠慢與漠視,原先還只是應付一下,假裝懺悔,十幾分鐘后,真情上涌,悲戚難掩,真的覺得以往過于沒人情了,哭聲此起彼伏。老潘一手拎一塊鐵皮,一手捏著鐵棍,全都擲于地下,發出乒乓之聲。老潘說,拿到打鐵公面前敲,越響越好。用力敲,敲出打鐵的聲音。打鐵公的身體漸漸軟了。這是老潘事先安排好的懲罰不肖子孫的橋段,也陰差陽錯地理順了打鐵公的生命秩序,獲得了生命應有的尊嚴,他獲得兒孫們的愛戴,真誠地懺悔,并且回到了自己完整的生命形式——打鐵中去。
這個鎮上的人會擔心,多年前埋下的壞種子,會在某一天發芽,長出歪斜的花朵和果實。這就說明傳統的生命形式和生活倫理依然在老一輩的心中扎著根。
然而小說中還有一個細節,老潘勸瀕臨精神崩潰的歪嘴昆去找妓女,這個動作讓小鎮上的老者,家庭的道德柱石老潘倍感失落。失落的原因,他說不清,接下來是老潘的一大段內心獨白:“連歪嘴昆這樣內心澎湃的人,都有尋死的心了,還有什么不能發生的?賭場、毒品……像風一樣,正在瑞溪鎮各個角落彌漫,正在日漸滲透寧靜的日子,正在把一棟建好的房子的地基抽掉,今后還會有什么呢?一切都會崩塌,一切都在淪陷——連讓歪嘴昆提振精神的法子都是讓其去嫖妓了,還有事什么是堅貞不變的?這種改變從何時開始,又會到何時結束?小鎮上發生的一切是不是很快就要蔓延到他家里來了?他沒有任何方法阻止,也不曉得即將面臨的災事將會以何種方式出現,但他預感到了。”
對于一個從農村走出來扎根到小鎮的居民,老潘和黑手義還有打鐵公等老一輩人,都是頑強的打拼者,他們以自己的勤勞和獨一無二的技術,安頓自己的家庭、精神和生命,他們還抱著澎湃的心情期望能延及子孫,帶來長久的昌盛和不斷地長進。現實帶給他們的是一重又一重的打擊,以及對他們所渴望的圓滿和秩序的無情毀壞,連老潘這樣的守護者都只能勸歪嘴昆去嫖娼,對自己孫子的再次染毒不忍說破,懼怕面臨家人精神的徹底崩潰。于是老潘和黑手義的原鄉情結就不是虛泛的抒情,而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潘宏億吸毒逃跑,在驚慌無措中,老潘主動回到鄉下,肯定是無計可施了,只能求救于逝去的先人,讓他們幫助慌亂無措的子孫,于是老潘要去修繕祖屋。黑手義甚至開始懷念七月初七的裝軍了,雖然那會對他內心造成重創,可他習慣了。他有時會覺得,鎮上的所有的壞事,都是從裝軍停止后開始的,賭博、吸毒、販毒、發瘋以及越來越躁亂的人心,都在裝軍停止之后集中爆發了。躁動不安的鎮子,讓他有搬回村里的念頭了。賈平凹在寫完《秦腔》后說:“風俗民情這些東西都是人在吃飽飯以后人身上散發一種活力,它依附在人身上的。就像農村做飯一樣,沒有火自然也不會有煙。……在商業化浪潮的沖擊下,我們原有的文化傳統、民俗風情發生了改變,古老的純樸的情感正在離我們遠去,人性變得異化、復雜、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邊,人的丑惡慢慢露出來,欲望成為我們行進的動力,我為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魔幻、裝軍、降童其實代表了一種原初的秩序,一種在亂世中人心的安慰歸屬和原鄉情懷,六角塘祖婆婆說前面的事情搞不好,子孫如何能好的話,不會算命的石頭爹能應承各種場合,不過都是在重復一些鄉村小鎮日常生活的常識,再以“封建”的形式復原我們被金錢迷障的情感。林森在小說的結尾也不失時機地批評;鎮政府的無能,間接地導致了無序混亂的社會秩序,蛤蟆二的“江南不夜城”被曝光后,媒體報道的題目是“為什么沒有任何文化生活?”鎮政府的見風使舵,為凸現政績、挖掘地方民風民俗、申報歷史文化名鎮,大張旗鼓要恢復裝軍節,“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瑞溪鎮政府形同虛設的,多年來沒被任何人注意,這一回,可算是少見地有魄力了一回,贏得了不少的好口碑。”但這個差強人意的恢復舉措還是胎死腹中,因為鎮上和村里裝軍隊伍的資助問題,而引出“維穩”的問題,這個讓大家精神一振的火焰被掐死了。
重新恢復“軍坡節”,小說里用了“一個燃燒的夏天”這樣熱烈的詞匯,大概是在表達一種迫切的重整人心、重振精神氣的愿望。小說以對降童的聲音呼喚式的描寫結束,像一針強心劑:“那聲音翻山越海穿透晨光,淹沒了所有方向盡失的癲狂,淹沒了所有人聲喧鬧的癲狂,也湮沒了所有獨自面對無邊夜色的癲狂。那聲音在南渡江水面上光澤溫婉,終于漾上江岸邊的小鎮,把一切喧囂帶走,把緩緩涌動留下。那聲音鼓震人心。”
四
社會學家孫立平借用法國社會學家圖海納的概念“馬拉松結構”來描述當代中國社會,馬拉松式的社會結構與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不同,人們在金字塔中雖然占有不同的社會/空間位置,但始終處于同一結構之中,而馬拉松的游戲規則是不斷地使人掉隊,“即被甩到了社會結構之外”,剩下那些堅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納進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就業者。在這個意義上,參與游戲的與被淘汰的處于結構性的“斷裂”之中,一旦裂開就再難加入一起跑的隊伍。其實就整個社會來看,一部分鄉村、小鎮乃至島嶼,也處于這種“斷裂”式的社會結構中,不僅僅是本地的人們外出打工、丟棄祖屋,而且還有無法恢復的、受到關注的本土的一切,小鎮上老者們的絕望和瀕臨崩潰,就是這種結構的一個暗示。不過作家好像還是對這個小鎮懷著難以割舍的情愫,所以作家讓黑手義以不辭而別、自我犧牲的方式,獲得兒子們對張英杰一家的接納,完成了大兒子一家形式上的完整,并留給子孫以“查黑”的方式重新整理家族故事、理順情感的機會。潘宏億從籠子里出來之后,跟張小峰一起散步,跑到了學校,他說:“我來看看,有沒有小學儀仗隊在訓練。我想確認一下,今年軍坡節,裝不裝軍?”在潘宏億心里,那份裝軍時刻的驕傲一直都在,這是他在張小峰面前唯一可以夸耀的東西。這些預示著生活依然還有可以擦亮的部分,不管如何仍然有一線生機。
林森在《雜記:關于閱讀與寫作》中說:“初中的那三年里,我患了一個很奇怪的毛病——非要躺在四處通風的樓頂才能睡著。現在想起,其實那些夏天也并不太熱,而且還有春天秋天兩季,我也仍要睡在樓頂上,一抬頭就看到滿天的繁星或者烏云。那樣的日子很難熬,天一黑就開始心慌,我嘗試過在房屋里,把風扇開到最大,還是覺得氣悶,翻身到了四點以后,仍舊要抱著草席和被子,摸著壞了燈的樓梯,爬上五樓的樓頂,睡到被陽光曬醒,被子拉起蓋住臉,接著睡,直到陽光變得強烈。那是小鎮上農業銀行的樓頂。”這些經歷都被他轉化到張小峰的個人生活中去,以林森這樣的年紀,很容易把這部小說寫成一個少年成長經歷中的瑞溪鎮生活史,難以逃脫青春憂郁的窠臼與各種永恒正確但沒有生活熱度的視角。林森正是在這個地方隱藏了那種廉價的情感宣泄,他以一個成熟小說家的穩重,將兩位老人老潘和黑手義作為小說的主角,讓他們葆有整個鄉域世界的秘密和沉痛,給古老的、日漸衰敗的鄉鎮世界,乃至當代中國的一部分發展歷程作了一個最恰當的注腳。小說題為“關關雎鳩”,古人以雎鳩之雌雄和鳴,以喻夫妻之和諧相處,雌雄有固定的配偶,又被稱作貞鳥。但在這部小說里,我愿意將它理解為共同經歷漫長一生的老潘和黑手義兩個老人悲傷無解的友誼:黑手義跟兒子們吵架后,到老潘家過夜,兩個老頭在空空蕩蕩的屋內說話。話少的時候,煙癮就重,煙頭的火光在黑沉的夜色中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兩雙老眼相對,把夜晚無限拉長。小而言之,兩個人是瑞溪鎮無力的守護者,大而言之,他們是活力充盈、給子孫們安居的廣廈式中國鄉村、小鎮社會老去的背影,而《關關雎鳩》就是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責任編輯: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