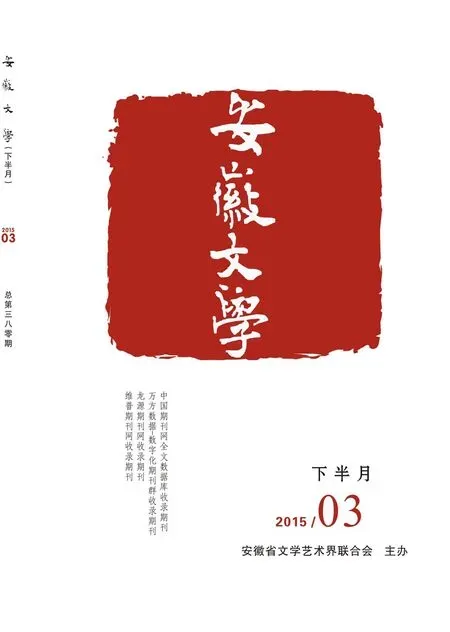生命的靜與動(dòng)——論廢名《橋》與沈從文《邊城》的生命意識(shí)
蔣旻君湖南師范大學(xué)
生命的靜與動(dòng)
——論廢名《橋》與沈從文《邊城》的生命意識(shí)
蔣旻君
湖南師范大學(xué)
摘要:廢名與沈從文的作品同屬于京派文學(xué),遠(yuǎn)離現(xiàn)實(shí)而貼近自然,并在田園牧歌中對(duì)生命做出終極思考。小說《橋》與《邊城》是廢名與沈從文的代表作,二者均體現(xiàn)了作家對(duì)生命、對(duì)存在的思考與認(rèn)識(shí),并構(gòu)建出理想的生命形式與存在家園。然而二人的思想與創(chuàng)作也同中有異,其理想的生命形式呈現(xiàn)出不同面貌,廢名選擇了靜謐,沈從文則在靜謐中展現(xiàn)了生之力度。本文將從《橋》與《邊城》兩部作品入手來分析廢名與沈從文不同的生命意識(shí)。
關(guān)鍵詞:廢名沈從文生命
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史上,廢名與沈從文這兩個(gè)名字常常同時(shí)提及,因二人作品類型、風(fēng)格的相似常被劃分到同一派別,諸如鄉(xiāng)土文學(xué)、抒情文學(xué)、京派文學(xué)。他們的作品確有諸多相似之處,同屬于京派文學(xué),遠(yuǎn)離政治、遠(yuǎn)離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而向自然貼近,在田園牧歌中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自覺地向抽象的生命本體追尋。然而我們對(duì)兩個(gè)作家的比較不能只停留在共性層面而忽略其個(gè)性的一面,廢名與沈從文雖同樣以生命哲學(xué)為核心來展開審美、創(chuàng)作,但二人的思考方向卻是相異的,這一相異之處在二者作品中得以體現(xiàn)。
廢名的早期創(chuàng)作是偏向現(xiàn)實(shí)主義一派的,而小說《橋》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其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的轉(zhuǎn)向,這一轉(zhuǎn)向不僅僅是創(chuàng)作手法的改變,更是廢名思想的轉(zhuǎn)變,其人生觀、生命觀在作品《橋》中充分展現(xiàn)。而沈從文的《邊城》也可以說是其巔峰之作,創(chuàng)作《邊城》時(shí)的沈從文正新婚不久,整個(gè)人生發(fā)生巨大轉(zhuǎn)變。從一個(gè)鄉(xiāng)下人變身為小有名氣的作家,并娶到了心儀的妻子,這一翻天覆地的人生轉(zhuǎn)變促使他思考人生、命運(yùn),向生命的深度探尋,《邊城》則是沈從文思考的產(chǎn)物。廢名、沈從文這兩位作家都將其對(duì)生命的關(guān)注注入作品中,巧合的是《橋》與《邊城》確有許多相似點(diǎn)。同樣將人物放置在世外桃源般與世隔絕的小城,同樣是年邁的老人撫養(yǎng)著年幼的孫女,小城的人同樣善良淳樸,作品都具有田園牧歌氣息也兼有憂傷的基調(diào)。廢名與沈從文都將自己對(duì)生命的認(rèn)識(shí)與思考融入桃源之中,重新構(gòu)建桃源,然而他們的桃源卻各具特色,呈現(xiàn)不同的面貌。本文將對(duì)廢名的《橋》與沈從文的《邊城》展開比較分析,從而探究廢名與沈從文的同而不同的生命觀。
一、死亡意識(shí)下的生命悲憫
“死亡”一詞帶來的恐懼常常令人對(duì)它避之不及,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對(duì)死亡的關(guān)注素來少見。直到“五四”給中國(guó)新文學(xué)注入了新鮮空氣,海德格爾、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哲人的死亡意識(shí)開始在中國(guó)傳播。然而自覺關(guān)注死亡、直接描寫死亡的作家仍在少數(shù),廢名、沈從文便在這少數(shù)之列。他們二人對(duì)死亡的關(guān)注或許是受西方死亡哲學(xu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與自身經(jīng)歷有關(guān)。廢名從小體弱多病,疾病的折磨不僅令他的身體與死亡靠近,也讓他在思想上更加關(guān)注死亡,由死亡延伸出對(duì)生命的思考。沈從文的死亡意識(shí)則源于他親眼目睹大量殘忍殺戮和一次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的切身經(jīng)歷,這些經(jīng)歷使他明白死亡是人類無法逃避的存在,無法逃避則只好面對(duì)承擔(dān),“向死而生”。
基于廢名、沈從文的死亡意識(shí),他們?cè)谧髌分泻敛患芍M死亡,并且有意識(shí)地描寫死亡。廢名的《橋》尤其明顯。《橋》中有大量與死亡相關(guān)的意象,諸如“墳”“塔”“碑”等,也描寫了“送路燈”“村廟”等許多與死亡有關(guān)的民俗,這些描寫是廢名有意為之,其自覺的死亡意識(shí)必然導(dǎo)致他將筆觸伸向死亡。在認(rèn)識(shí)到死亡的無從逃避之后,廢名開始接受死亡、欣賞死亡,甚至借小林之口道出“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在《橋》的下篇第三章《窗》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小林凝視著熟睡的細(xì)竹聯(lián)想到生老病死,進(jìn)而聯(lián)想到佛像,感嘆“藝術(shù)品,無論它是一個(gè)苦難的化身,令人對(duì)之都是一個(gè)美好,苦難的實(shí)相,何以動(dòng)憐恤呢”?這是典型的廢名創(chuàng)作手法,隨著意念流動(dòng)的描寫道出思考的核心。死是無法避免的存在,美與死同時(shí)存在,在死亡面前美愈發(fā)顯出光芒與可貴,同時(shí)也不免令人心生憐憫與憂傷。在這一認(rèn)識(shí)上沈從文與廢名不謀而合,沈從文相信“愛與死為鄰”,①認(rèn)為“極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義務(wù),‘愛’與‘死’”,“一個(gè)人過于愛有生一切時(shí),必因?yàn)樵谝磺杏猩邪l(fā)現(xiàn)了‘美’,亦即發(fā)現(xiàn)了‘神’”。②死與愛、美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存在。沈從文在《邊城》中并沒有像其他作品一樣過多描寫死亡、殺戮,然而死亡意識(shí)同樣存在。故事中有這樣一段:翠翠被爺爺丟下一個(gè)人站在河邊時(shí),“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黃昏把河面裝飾了一層薄霧。翠翠望到這個(gè)景致,忽然起了一個(gè)怕人的想頭,她想:‘假若爺爺死了’”。黃昏的落日象征著老人遲暮,象征著死亡。翠翠面對(duì)落日,心中油然生出對(duì)爺爺死亡與自己的未來的擔(dān)
憂,這種擔(dān)憂也體現(xiàn)在爺爺身上。同樣是一段黃昏時(shí)候的描寫,翠翠坐在溪邊,望著溪面為暮色所籠罩的一切,或許是基于同樣的擔(dān)憂開始呼喚在船上的爺爺,爺爺一面回答道:“翠翠,我就來,我就來”,一面卻自言自語到“翠翠,爺爺不在了,你將怎么樣?”死亡意識(shí)存在于祖孫兩個(gè)人的心中,在表面單純美好的生活背后潛存著因死亡而起的擔(dān)憂、恐懼以及對(duì)生命的悲憫。因此,《邊城》不僅僅是一曲田園牧歌,它更是對(duì)生命悲憫的哀嘆。不管是廢名的《橋》還是沈從文的《邊城》,都是在田園牧歌的外衣之下訴說生命的悲憫、存在的困境,這種悲憫的成因除死亡之外,也由不同形式的命運(yùn)導(dǎo)致。
二、命運(yùn)未知下的生命思考
“命運(yùn)”一詞并不令人恐懼,人人皆有自己的命運(yùn),真正使人擔(dān)憂的是命運(yùn)的未知,偶然性與不確定因素直接導(dǎo)向人類生存的變數(shù),從而產(chǎn)生對(duì)生命不可思議的慨嘆。廢名、沈從文作為關(guān)注生命哲學(xué)的作家,思考生命的終極意義,自然也不會(huì)忽略命運(yùn)的不確定性。并且他們?cè)谧髌分胁粩啾憩F(xiàn)和感慨著命運(yùn)的未知與變數(shù)。小說《橋》并不熱衷人物描寫,更多的是思維、心念的表現(xiàn),然而廢名也在交代人物命運(yùn)的同時(shí)表現(xiàn)出對(duì)命運(yùn)變數(shù)的慨嘆。小說中的三啞叔曾經(jīng)四處流浪靠討米為生,終于在討到史家奶奶門下時(shí)命運(yùn)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成為史家的長(zhǎng)工。小林遇到的和尚曾做戲子扮趙匡胤、扮關(guān)云長(zhǎng),最后流落到關(guān)帝廟做和尚,終日對(duì)著關(guān)公像發(fā)笑,偶然因素令其命運(yùn)發(fā)生改變,卻又巧妙地仍將他與關(guān)公聯(lián)系在一起。小林與琴子、細(xì)竹三人出門看海,遇到的大千、小千與他們有著相似的境遇,小千暗戀姐姐的丈夫(與細(xì)竹相似),大千丈夫的死去又消除了姐妹之間的尷尬氣氛,讓二人重歸于好、相依為命。而小林與琴子、細(xì)竹三人的命運(yùn)又將如何?這仍是未知數(shù)。所以琴子才會(huì)感慨“人與人總在一個(gè)不可知的網(wǎng)中似的,不可知之網(wǎng)又如魚得水罷了”。廢名感慨命運(yùn)的未知與變數(shù),沈從文亦是如此。《邊城》里造成翠翠命運(yùn)轉(zhuǎn)變的偶然因素是大老的死,大老是弄水的好手,常年在水上活動(dòng)從未出事故,可以說偶然性是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正是這一偶然事件造成翠翠命運(yùn)的轉(zhuǎn)變。試想如果大老不死,兩兄弟仍每日為翠翠唱歌,翠翠最終或許與二老會(huì)有個(gè)圓滿結(jié)局。未知與變數(shù)其實(shí)并不可懼,畢竟變是一種永恒的存在,它只會(huì)讓人在回望歷史時(shí)感慨命運(yùn)的不可思議,真正令人感到生命沉重的是命運(yùn)的變數(shù)所帶來的哀與樂。因此,廢名、沈從文才會(huì)在作品中不斷描寫命運(yùn)的偶然變數(shù),在感慨命運(yùn)的不確定的同時(shí)對(duì)生命肅然起敬,對(duì)人的存在展開終極思考。
三、自然生命下的靜與動(dòng)
自然是廢名與沈從文不可忽略的共性,他們對(duì)生命的認(rèn)識(shí)與思考在自然中展開,規(guī)避一切現(xiàn)實(shí)來還原生命的本真。這里的自然有兩層含義,一是指自然環(huán)境,在遠(yuǎn)離俗世的自然環(huán)境中展開對(duì)生命的思考,以自然之靜來襯托生命的靜謐。另一方面是指最自然的生命形式,即生命的本來面貌,從而找到生命的終極意義。然而這兩方面的自然在廢名、沈從文的筆下是合二為一的,二者不可分離,相輔相成。
廢名的《橋》將人物放置在自然山水之中,在自然中進(jìn)行他們?cè)娗楫嬕獾娜松U≌f中沒有父親的角色,父親代表著父權(quán)文化,而廢名似乎有意規(guī)避它。他認(rèn)為“母親同小孩子的世界,雖然填著悲哀的光線,卻最是一個(gè)美的世界,是詩的國(guó)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凈化”。母親與孩子的關(guān)系是最原始、自然的存在,廢名否定父權(quán),所渴望實(shí)現(xiàn)的正是這種貼近自然的本真存在。因此他讓在外求學(xué)的小林又回到史家莊,回到自然的懷抱。然而史家莊絕非廢名理想的桃源,真正的桃源在于夢(mèng)。小林重返故園,仍在因生老病死而對(duì)生命產(chǎn)生悲憫,仍對(duì)人的存在產(chǎn)生慨嘆,他真正的理想家園在夢(mèng)里、在思想意識(shí)與靈魂里。因此才會(huì)說“我感不到人生如夢(mèng)的真實(shí),但感到夢(mèng)的真實(shí)與美”。正如小說的題目為《橋》,廢名也說最先定下的題目是《塔》,其實(shí)“橋”與“塔”只是意象而已,在小說中也曾出現(xiàn),卻并非實(shí)實(shí)在在的物,只是心生的幻象而已。比如《塔》一章中細(xì)竹向小林解釋她畫塔的原因,只是因?yàn)榍僮咏o她講的故事中出現(xiàn)了塔,而她就將話語之塔經(jīng)過頭腦中的成像而轉(zhuǎn)為畫上之塔。其實(shí)這個(gè)塔并非實(shí)在,只是虛幻的象而已,也是廢名所說的夢(mèng)。類似的意象遍布整部小說,而廢名想要透過這些意象來構(gòu)建他的理想桃源,實(shí)現(xiàn)生命的存在價(jià)值。在廢名所造的夢(mèng)境里或許可以擺脫生存的困境,可以對(duì)生命的哀痛產(chǎn)生短暫的麻醉,然而這種理想畢竟太過消極頹廢,太過沉靜而喪失了生命的力度,因此有人評(píng)價(jià)廢名的《橋》呈現(xiàn)“僵尸似的美”,美而沒有生氣。這一點(diǎn)恰是沈從文超越廢名之處。
廢名與沈從文都思考生命,認(rèn)識(shí)到死亡、變數(shù)等哀與樂所帶給生命的沉重與困境,廢名選擇歸于自然,歸于夢(mèng),在靈魂深處創(chuàng)造桃源,讓生命在寧靜中實(shí)現(xiàn)其價(jià)值。沈從文與廢名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能在融入自然之后超越自然,他認(rèn)為“極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義務(wù),‘愛’與‘死’。人既必死,即應(yīng)在生存時(shí)知其所以生”,真正的“向死而生”是承擔(dān)生命中必經(jīng)的哀與樂,絕不逃避。所以《邊城》里的爺爺會(huì)說,“做一個(gè)大人,不管有什么事皆不許哭,要硬扎一點(diǎn),結(jié)實(shí)一點(diǎn),方配活到這塊土地上”,這才是沈從文提倡的優(yōu)美、健康的生命形式。他承認(rèn)“一個(gè)人的一生可說即由偶然與情感乘除而來。你雖不迷信命運(yùn),新的偶然與情感可將形成你明天的命運(yùn),決定他后天的命運(yùn)”,而他也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所帶來的勇敢可以戰(zhàn)勝一切苦難困境,這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這也是沈從文在自然中追求生命的純粹、靜謐的同時(shí)所把握到的動(dòng),即生命的力度。
注釋
①沈從文.燭虛[A]//友情集[C].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2:280.
②沈從文.美和愛[A]//友情集[C].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2: 329.
參考文獻(xiàn)
[1]廢名.橋[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3.
[2]沈從文.邊城[M].北京:中國(guó)工人出版社,2012.
[3]沈從文.友情集[M].長(zhǎng)沙:岳麓書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