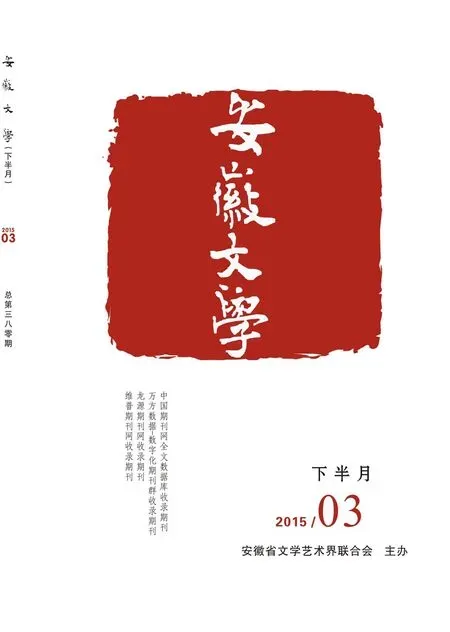從“人的文學”到“自由”“寬容”——淺析周作人的文藝思想
袁文卓喀什師范學院
從“人的文學”到“自由”“寬容”
——淺析周作人的文藝思想
袁文卓
喀什師范學院
摘要: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我國文壇的地位可與魯迅相提并論,但是隨著日軍侵華、周作人出任偽華北教育督辦之后,他從神壇跌落到谷底,特別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還被一度以“漢奸罪”論處,這位曾在我國近現代的文學史上開風氣者的作品和文藝思想究竟給人以何種啟示?本文試圖通過對周的文藝思想由“人的文學”到“自由”再到“寬容”的發展脈絡,試圖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文藝評論脈絡,以期更好地指導新時期的文學實踐。
關鍵詞:上世紀周作人文藝思想重新審視
周作人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著名的散文家、民俗學家和文藝理論家,但一直以來由于歷史原因,周作人的文藝思想和文藝批評理論一直為學界所忽視,盡管有國內著名學者錢理群等人對其著作和思想進行重新認識、整理和推介,但是學界對其文學地位和文藝思想的認識依然有限。隨著我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周作人的文藝思想逐漸閃耀出他的光芒,到底應該如何重新評估、客觀認識其文藝思想?本文從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學”“自由”“寬容”的文藝思想出發,在對這三種文藝理念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力求全方位展現周作人先生的文藝思想。
一、何謂“人的文學”
在1918年12月刊的《新青年》里面有一篇題為《人的文學》的文章。作者是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年僅33歲的周作人。當時的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匯集了全國各地的優秀學者和青年才俊,雖然胡適是最早提倡白話文寫作并被尊稱為領袖級人物的人,可真正開始對新文化運動在道德和心理方面進行嘗試工作的卻是魯迅的弟弟——留日學者周作人。
周作人在1917年回國后便任教于北京大學,回國后的他以散文著稱,對民俗學的研究以及兒童文學的研究頗深;可在他寫作《人的文學》期間,他研究的方向卻是心理學和西方文藝學。采取的研究方法也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沐浴到的西方實證主義思想。至今不論是從何種眼光來看待《人的文學》,這其中閃耀的思想光芒無不令人嘆服。
在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已故哥倫比亞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的夏志清教授的專著《中國現當代小說史》中曾介紹過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學》一文,著作中認為人具有靈肉二重性。而我們平時所談到的靈肉本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而這兩個方面絕不是對抗的二元,即這兩個方面絕不是對立的;而在我們的古人看來,這兩個二元是根本對立并且永遠是沖突不可能調和的。文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的反映,正因如此,這種不可調和的、靈肉對立的思想表現在我們的文學上就形成了鮮明對立的兩個派別,第一個派別我們稱之為“贊同理性的文學”,這種聲稱為理性、為文學的派別即是為政治集團服務的。為政治集團服務的特點決定了它與生俱來的特征——即壓抑人的欲望和情感。與之相反,另外一個派別是贊同人的真情實感自然表露之文學,這種文學一方面是主張感情之自然流露和表達,而另外一方面這種文學由于感情和抒情真切抒發往往卻充滿了色欲和幻想以及容易陷入萬事無一物虛無之中。
通過比較可以看出這兩種派別的文學都具有偏頗,也就是都不能夠真正地反映并再現真實的文學。即這兩派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夠真正地刻畫出人性,更別說真正地反映和超越生活了。
周作人認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文學重新呼喚理性的時代,也就是人應該是具有理性并且具有批判力的,由此以來為我們文學的發展指出了明確的發展道路。在其作品中,他談到了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的文學樣式,究其重點是讓作家更加尊重人生、更加尊重人性。為了闡釋他的文藝思想,他引用了國外著名作家如哈代和屠格涅夫等例子來闡明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描寫的人物僅僅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而且這些普通人的人性中卻無不折射和透露出了美好的人性光輝。
夏志清教授認為《人的文學》的認識雖然很獨到,但是作者所鼓勵的僅僅在道德上,周氏認為人類幸福的理想境界應該是《天國與地獄結婚》這部作品中所描繪的靈肉統一的境界。
二、從“自由”到“寬容”
縱觀周作人的文藝作品,不難發現其文藝批評上的關鍵字眼乃是“自由”和“寬容”。這種文藝批評思想也使得他早早地奠定了我國上世紀早期最著名的文藝評論家之一的地位。
以魯迅、周作人、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者是走在歷史潮流前列的新一代,而這種新一代被賦予的歷史使命是充當引路人,并且在指引文學發展道路的過程中還肩負著探索出一條符合新文學批評樣式的發展道路的重要責任和使命,周作人之所以成為五四以來文學批評家中的翹楚,筆者認為這與他的獨立自由批判的品格有很大的關系。
首先,周作人對文藝批評中的“自由與寬容”下了明確的定義:“當自己求自由之發展時,對于迫壓的勢力,不應該采取忍受的態度;而當自己成為了已成勢力之后,對于他人的自由和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態度”,“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于新興流派的態度”。[1]86在這個地方,作者說的自由和寬容應該更多地指的是對舊事物的反抗和對新事物的倡導。這樣一來,我們很顯然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文藝思想具有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戰斗品格。
其次,周作人是第一個對郁達夫的作品《沉淪》以及對汪靜之的作品《蕙的風》做出評論的文藝批評家。當郁達夫的作品《沉淪》發表之初,學界一片嘩然,大體認為是淫穢之作且對郁達夫本人也是猛烈抨擊,在此背景下,周作人也是第一個對郁達夫作品中的性苦悶進行科學解釋和定義的第一人。他指出,作者在作品中表現的實際上是“青年的現代的苦悶”,他在文章中反復強調了《沉淪》是一件藝術作品,并且反對舊時的文人從所謂的傳統道德觀念出發來抨擊郁達夫及其作品。[2]此外對于汪靜之的《蕙的風》這部作品,在人們普遍認為汪靜之的作品是不道德之作的情況下,周作人毅然站起來為后輩說話,對那些蓄意攻擊汪靜之情詩的人給予了有力的反擊,并且預言,那些對新文學打壓的分子,一定會被歷史嘲笑;表面上看是占據優勢,但實際上只不過是“獻丑”。
還有在其兄長魯迅的名著《阿Q正傳》最初發表的時候,官僚們惴惴不安之際,周作人也是第一個對《阿Q正傳》中所蘊含的反封建意義以及藝術風格等方面進行深層次剖析的評論家,無論是從當時還是從歷史的發展來看,周作人的這些評論不僅具有強有力的震懾力,而且也彰顯出評論家的慧眼識才,顯現出評論家不同于一般讀者的敏銳力和時代把握感。
對于晚輩的寬容和提攜使得青年作家能夠迅速成長,以至于后來郁達夫在《郁達夫代表作》的扉頁上面特地寫下了這么一段文字:“此書是獻給周作人先生的,因為他是對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國第一個批評家。”[3]111
時間和歷史也證明了周作人的慧眼識才,郁達夫和汪靜之不負眾望地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三、誰能“寬容”
五四時期的周作人并不僅僅停留在打破舊文學的正統地位,在新文學取代舊文學之際,他還向新文藝批評家們提出了“誰能寬容”的命題。
周作人經常強調,“文藝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離而不是合并;[1]86文學究其本質是要求個性和獨特性的。它天然具有“排他性”的特征,既不能夠定于一尊,也不能夠“以多數決的方法來下文藝的判決”,[4]55-58在一同和一統的旗幟下抹殺創作者的自我個性,而這對于文藝的發展是致命的。
什么是文學批評中的“自由”“寬容”?也就是說要在文學欣賞和文學考評之前評論家得明確文藝批評的職責,僅僅是向讀者提供一種你對文章的看法,任何的批評家和文藝鑒賞家沒有權利以自己的意見去決定受評價者的地位,也更別說去決定作家或者及其作品的命運了。他還進一步指出,對作品的評價也只是一個尺度,不能夠把話都說完,也就是說任何人對一件事物的評價不可能是完全客觀或是絕對正確的,由于每個人都在不經意地受自身條件或者知識結構的束縛等等。
由此,周作人一再強調我們要積極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要爭取自己發展個性的充分權利,同時我們也要真正地做到尊重他人發聲的權利和機會,任何企圖通過自己的打壓來達到壓制別人觀點和意見的行為都是對自由和寬容原則的背棄。
總的來說,周作人從文藝批評的角度出發,提出的“人的文學”“自由”和“寬容”是符合文學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而時間和實踐也證明了這位偉大的文藝批評家思想的獨到和犀利,對于“批評自由與寬容”原則的深刻的理解和闡述,不僅僅成為周作人文藝理論中的最核心部分,也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取得的最寶貴的成果之一,她昭示著現代文學批評觀念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而這一思想對于我們今天從事文藝工作的學者來說無疑指導意義重大。可是我們長期以來由于受資產階級自由論思想的影響,一味地把周作人打入“冷宮”,認為其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等等,這都是不利于我們的文學成長和文學批評理論的形成的,由此,我們應該全面地、辯證地看待周作人,看待周氏的文藝思想。
參考文獻
[1]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文藝上的寬容[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86.
[2]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N].晨報副刊,1922-11-1.
[3]阿英.夜航集·周作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111.
[4]周作人.自己的園地·詩的效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