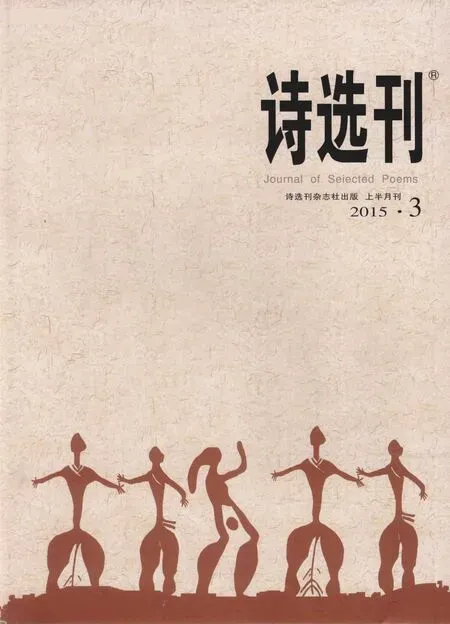詩藝清話一百一
陳 超
詩藝清話一百一
陳超

詩藝清話一百一陳 超
碎片時代詩歌何為 霍俊明
1
對詩,我們采取什么態(tài)度最好?有個老老實(shí)實(shí)的道理值得每天重溫:把詩當(dāng)詩。讓詩說出那些只能經(jīng)由詩才能說出的東西。
詩就是詩,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詩人都應(yīng)記住這一點(diǎn)。詩畢竟只是詩,它永遠(yuǎn)應(yīng)該是讓人夢縈魂?duì)康臇|西。一個詩人的尊嚴(yán),或是有尊嚴(yán)的詩人,首先體現(xiàn)在對詩的藝術(shù)本身的信義承諾。
讀詩、讀詩,讀的是詩。因此,最佳的詩歌閱讀,就是記住“我讀的是詩。”不要小瞧這一點(diǎn)。沒有這一點(diǎn),就談不上對詩歌真正的閱讀。
對這一點(diǎn),古今中外真正的內(nèi)行有著共識。嚴(yán)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guān)書也。詩有別趣,非關(guān)理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詩道惟在妙悟。”(《滄浪詩話》)讀詩之道亦在妙悟,讓它激活你的審美感興、感性、直覺,感受生命的情趣。
為什么說詩“言有盡而意無窮”,因?yàn)榭梢匝员M的是意義,而生命的情趣是言不可盡的。
糖的化學(xué)成分可以言盡,“甜”你怎么言?
2
詩歌是感官經(jīng)驗(yàn)、生命情緒與活潑潑的心智相遇,所產(chǎn)生的審美趣味,而不是僵硬的觀念的推演,哪怕是“正確的觀念”。審美趣味,趣味,還是趣味,這是真詩與贗品的分野。
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給詩歌下的定義也不是詩歌。很難給令人迷醉的東西下嚴(yán)格的定義,詩不是凝固的“存在物”,而是“去存在……”過程本身。
3
對于詩歌寫作來說,訓(xùn)練、專注、沉湎、教養(yǎng),如此等等是必要條件,但還是有一個決定性的致命條件——我應(yīng)該直接說嗎?——天才。
可嘆的是,沒有對詩歌的審美敏銳也是一種“天生”,對這樣的人,任何知識、修養(yǎng)都幫不了忙。
納博科夫說,無論現(xiàn)代還是古典,優(yōu)異的文學(xué)其實(shí)只有一個流派,就是天才派。
4
海德格爾說,“藝術(shù)把真理固置于個別的事物”。這句話對外行和內(nèi)行,語義重心是不一樣的。外行認(rèn)為,這里的關(guān)鍵詞是“真理”;內(nèi)行會認(rèn)為是“個別”細(xì)節(jié)。
沒有大視野的詩人,其實(shí)不會發(fā)現(xiàn)真正有力量的細(xì)節(jié)。
5
單就情感經(jīng)驗(yàn)的提供而言,好的詩歌,或啟人心智,或給人安慰,或讓人活得更自覺;或撫慰你,使你覺得生命的困境是難以逾越的,我們不必再自我折磨。但所有這些指標(biāo)背后,還有一個總指標(biāo),就是作者必得是一個有性情的、有語言才能的、有趣的人。無論表達(dá)什么,詩,首先要吸引人看下去,得有活力和趣味。無趣的詩,讀幾行就會厭倦,用不著讀完。
6
詩歌可以追求“深度”,但不能以趣味、活力和技藝的讓步為代價。這正是一個純粹的詩人,與借用詩歌來“說事”的詩人的根本不同。
詩人葉芝說,智慧是一只蝴蝶,不是陰沉的食肉獸。
純粹的詩人是美麗的,值得信賴的,他們使詩歌恢復(fù)了骨子里的純正性。讓我們相信,趣味、活力和技藝會帶來詩歌意味的富足,讓我們在乏味的時代挽留住審美趣味這一恰如其分的財(cái)富。
趣味、活力和技藝,是寫作歡愉的保證。歡愉消除了話語權(quán)勢,歡愉恢復(fù)了漢詩原曾有過后來被中斷了的生命血色素。有趣味的詩,有效地避免“濫情”與“說教”兩大宿疾,讓我們得以從一個具有美好性情和心智的詩人眼里去看看人生。
蜜蜂采蜜同時也給花授粉。詩人勞動的快樂,就是蜜蜂似的美麗的快樂。詩人應(yīng)有能力來勝任快樂。
7
舊體詩的基本語義單位是句子,而現(xiàn)代詩的基本語義單位卻是詞語。在此,每個詞被迫變得格外敏感,關(guān)鍵處,若果一腳踏空,全盤皆輸。
8
詩歌之美主要不在于傳達(dá)某個語義信息,而是它的傳達(dá)方式值得我們沉浸、賞玩。所以,內(nèi)行的欣賞者不太重視“詩所言”,而更喜歡注意“怎么言”。
“詩者,志之所之也”,后面這個“之”,是強(qiáng)調(diào)情志言說的過程與方法。它才是秘密所在。
詩歌引起我們對語言的特殊沉浸,驚愕,驚喜。當(dāng)語言偏離了實(shí)用性,而帶給我們喜悅時,詩現(xiàn)身了。
9
與那些自詡的“有教養(yǎng)的”讀者、批評家一樣,我也喜歡“深刻”的詩歌。不過我看中的是它的趣味、活力和技藝。這么一來,喜歡的原因就頗不一樣了。我說,恰好是為了使詩歌更有趣味,詩人需要在其中涉入更復(fù)雜深邃的意義;恰好為了滿足詩人對寫作技藝的高難度游戲,他必須對心靈的幽秘有更多的發(fā)現(xiàn)。可以這么說,趣味和活力、技藝,其實(shí)也是對詩歌深度的考驗(yàn),同時也檢驗(yàn)著詩人對藝術(shù)的真誠。
“深刻”可以名實(shí)不符,趣味、活力和技藝卻總是表里如一。
10
不只是你怎樣看世上萬物,還有萬物怎樣看你。詩人的高下在此見出。
11
詩歌是需要高度專注的語言藝術(shù),與小說家不盡相同,在特定意義上說,詩人不僅需要“開放”信息,同時更需要必要的“自我封閉”,凝神,靜心默想。
12
呈于境,感于目,親乎情,切于事,會于心,達(dá)乎靈。簡單嗎?不,這就是最難得的詩歌。
不要強(qiáng)行推銷你的驚世駭俗和歇斯底里,寫一首虛假的詩,往往是在作弄自己。
我說詩歌要有活力,生氣灌注,我要的是活力和生氣,而不是瞎抖機(jī)靈、不消停。此言唯真詩人懂得。
13
不要用舞臺上矯揉造作的范兒寫詩。不要使用與你膩友調(diào)侃時的輕佻語調(diào)。詩是與處于喑啞之地的潛在知音的交流,要質(zhì)樸,謙遜,誠懇,還有一點(diǎn)點(diǎn)羞怯的自我克制。
14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寫詩這件事無疑源于詩人的極度自戀。而詩人最令人討厭的品質(zhì),恰恰就是自戀、自戀、還是自戀。
天吶,身為詩評家,我看到多少自戀的家伙!誰愿意陪著你自戀呢?記住,要把自我迷戀,轉(zhuǎn)換為對詩本身的專注和沉浸,這樣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詩。
艾略特比之華茲華斯,并非更不自戀,其間的區(qū)別是,艾略特知道這一點(diǎn),并提出“非個人化”。
15
有人說,在“讀圖時代”,現(xiàn)代詩出局是必然的。我以為,恰好是讀圖時代,現(xiàn)代詩更有用了。現(xiàn)代詩的隱喻、暗示性,是畫不出來也拍不出來的。你可以畫、可以拍花開,但“通過綠色導(dǎo)火索催動花朵的力,催動我綠色的歲月”,你怎么畫?畫一只炸藥包在花叢中爆炸?
詩歌有鮮潤的感性,同時有形而上的靈魂體驗(yàn),而且它們總是化若無痕地融會一體。所以,圖畫和詩,各有勝境,不可妄言誰取代誰。
16
寫作不是描摹世界的表象,而是讓“存在現(xiàn)身”。詩人不應(yīng)照相式地反映事物,而要潛入對象的內(nèi)部,將對象“從它自身中解放出來”,讓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替他說話,達(dá)到心與道合的天地同參之境。
詩的神秘性不在于詩的措辭(從措辭上看,許多好詩反而是樸實(shí)明澈的),而在于存在本身的神秘。詩人毋庸去制造更多的玄想,他對著感知對象凝神領(lǐng)悟,直到對象向他走來,并“要求”著在話語中展露它自己。
17
詩歌不必要你懂,而是要你感覺。無論古今,面對真正的好詩,在“懂”之前,我們已被感動。“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暗水橫橋,矮屋香茅,看黃花都放了”。
你懂什么?無須懂,你已被詩的境界所喚醒、已被詩的興味觸動。
“黑夜比我更早睡去/黑夜是神的傷口/你是我的傷口/羊群和花朵也是巖石的傷口……今夜九十九座雪山高出天堂/使我徹夜難眠”(海子),“這城市如冰海上/燃燒的甲板/得救?是的,得救/水龍頭一滴一滴/哀悼著源泉”(北島)。
你懂什么?在“懂”之前,你已感覺到來自脊梁骨和內(nèi)臟的寒冽、緊張、無告。
18
差的詩人往往在該含混的地方太清晰,而在該清晰的地方又太含混。
19
提醒忿忿不平的詩人注意,經(jīng)常被批評家闡釋的詩,未必自動等于好詩。有些詩,只不過有很大的闡釋空間而已。有些詩很好,但不必闡釋。
20
好的詩歌,像真佛,是有“后光”的。那光圈,看得見,摸不著,那是我們難以磨滅的茫然無知的美妙頃刻。
21
詩不是求知識。它無限擴(kuò)展我們感知的邊界。
22
詩人是世間一條柔韌的神經(jīng)纖維。
通常人們認(rèn)為,詩中的意象,隱喻,“象征”無非就是借一個具體的形象來表達(dá)抽象觀念,在詩中形象是處于從屬地位的,目的是為了表達(dá)觀念。
這是一種誤解。對詩人而言,整個宇宙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外界事象與人的內(nèi)心能夠發(fā)生神秘的感應(yīng)與契合;因此,“象征”等不是一種一般的“修辭”技巧,而是內(nèi)外現(xiàn)實(shí)的“相遇”、“相融合”。詩中的形象決不是從屬的工具,它自身擁有自足的價值。在此,主客體不再區(qū)分,不是詩人外在地描寫世間,而是他自身就是世間一條柔韌的神經(jīng)纖維。
23
有許多詩人在作品中不厭其煩地訴說自己心靈的苦難,但并不能打動我。
詩人責(zé)問道:“我說的還不夠多么?”
——讓我們告訴他:“不。一個致命的原因恰恰是你說的太多,而‘詩’說的太少。”
24
優(yōu)秀的詩人感念自己的讀者。但寫作時并不考慮讀者。
或者說,他尋找的是幽靈般的知音讀者。
李商隱寫詩時,何曾考慮過未來的人閱讀,可他感動了今天的我們。
25
詩歌不僅僅是傳釋你的情感、經(jīng)驗(yàn)、智識,詩還有屬于它本身的情感、經(jīng)驗(yàn)、智識。詩人的高下,在此區(qū)分。
26
一首詩如果真正出色,內(nèi)行的讀者就不能從書寫過程的蹤跡上轉(zhuǎn)移視線,迫不及待地奔向它的所指。因?yàn)槟苤概c所指在這里契合無間,它就是寫作本身。尋找這首詩所指的理念,只是一件次要的事,而且常常名實(shí)不符,詩的魅力或是魔力卻表里如一。
27
用詩是表達(dá)經(jīng)驗(yàn),來PK詩的本質(zhì)是抒情,其實(shí)還是沒說到點(diǎn)子上。
詩的本質(zhì)不是抒情,不是經(jīng)驗(yàn),而是詩本身。不管你屬于哪種創(chuàng)造力形態(tài),每個真正的詩人生命內(nèi)部,都有個“絕對的詩”的幽靈,或舍利。
28
弗萊說,“詩歌是咿呀之語和信手拈來的東西(babble and doodle),它們的根基是魅力和難以理解(charm and riddle)。”
可以這么說。但關(guān)鍵是此咿呀不是彼咿呀,此信手拈來不是彼信手拈來。要使咿呀和信手具有詩的意義,具有詩人自己的文體風(fēng)格,有多少你看不到的規(guī)則和漫漫路途啊。
29
詩的含混和清晰一樣,本身不等于詩的價值。詩的價值:含混,必須有內(nèi)在的精敏做基礎(chǔ);清晰,必須有“光明的神秘”。
“你的美是月光下的庭院”(含混),比“你是一朵紅玫瑰”(清晰),前者更精敏。
對這類詩人來說,使用復(fù)雜感受力帶來的詩歌的特殊語言“肌質(zhì)”,同樣出自于對確切表達(dá)個人靈魂的關(guān)注。在他們看來,不能為其它語言轉(zhuǎn)述的言語,才是個人信息意義上的“精確的言語”,它遠(yuǎn)離平淡無奇的公共交流話語,說出了個人特殊感受力,和個人靈魂的獨(dú)特體驗(yàn)。
30
寫詩是詩人在過一種個殊化的語言生活,它像下棋一樣沒有實(shí)用目的。棋局既千變?nèi)f化,又有規(guī)則。但規(guī)則增加了趣味,沒有限制格局的美妙多變。
31
什么是有創(chuàng)造力的大詩人?我的標(biāo)準(zhǔn)是,既不仿寫前人,又無法讓后人仿寫。難矣。非常遺憾,任何時代,有創(chuàng)造力的大詩人都是鳳毛麟角,極其罕見。
詩,是個體生命和語言的瞬間展開。與其它文體相比,在于它的不可復(fù)制性,不可復(fù)制別人,也不可復(fù)制自己。
32
優(yōu)秀的詩歌關(guān)心的不只是可以“類聚化”的情感,更應(yīng)是個體生命的經(jīng)驗(yàn)。類聚化的情感只能“呼應(yīng)”我們已有的態(tài)度,而個人經(jīng)驗(yàn)才會“加深”乃至更新我們對生存和生命的感受與洞識。因此,我們在讀那些優(yōu)異的詩作時,會感到詩人是將自己的生命經(jīng)驗(yàn)一點(diǎn)一點(diǎn)“捺”入文本中去。
經(jīng)驗(yàn)是“呈現(xiàn)的”,感情是“告知的”,對真正的好詩而言,“呈現(xiàn)”總是比“告之”的信息量更多,藝術(shù)的勁道更足。是呵,浪漫主義濫情詩歌的衰退早已警示過我們:允許寫得不好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
33
詩歌是由感性而生的。但是,再好的感性,也無法絕對地保證我們寫出一首好詩。詩是語言中的語言,這意味著,從你感到的世界到你寫出的“詩的世界”,中間還有與語言艱辛地提煉、磋商的考驗(yàn)。而缺乏技藝,你感覺的濃度就被磨損掉了。
你必須從普泛的人類感受中提取出真正屬于詩的特殊的東西,在現(xiàn)實(shí)經(jīng)驗(yàn)與美感經(jīng)驗(yàn)中謀求到美妙的平衡——體驗(yàn)和感性,當(dāng)然要求詩人“能入”,但真正寫好感性,其奧秘卻還在于審美觀照的“能出”。入與出,是詩歌旨趣中的“悖謬”所在,也是對詩人創(chuàng)造力的舒心的折磨。如果把握好這一分寸,就會使我們的詩在“可言之境”的上層,有力地暗示出另一個更鮮潤、更神奇,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博大的“無言之境”。
技藝的加入,使詩可供心靈去反復(fù)體驗(yàn)而不至于在“達(dá)意”之后發(fā)生耗損;在日常經(jīng)驗(yàn)和人文話語的“可言之境”無所作為的地方,詩歌縱身一躍,帶著我們領(lǐng)受了生命體驗(yàn)中“無言之境”所暗示的“緘默”的啟發(fā)力量。
34
好詩人的技藝,如球星的“手感”,精敏有效,一點(diǎn)不顯匠氣和板滯。他在自發(fā)和自覺之間保持了一種活力:既有“深思熟慮”的精審,又葆有著“即興”般的鮮活感。
在好詩人筆下,即興的靈感不是詩思的最終落點(diǎn),而只是跳板;詩人依然伴以清醒的頭腦,久經(jīng)磨練的手藝。直到耐心地刻劃或挖掘出生命中經(jīng)久而內(nèi)在的經(jīng)驗(yàn)的紋理。形象地說,一般化的詩人筆下表達(dá)的靈感像被“吐出”的一口氣;而好詩人的靈感則是復(fù)被“吸進(jìn)”的一口氣,攜有經(jīng)驗(yàn)在涵泳后的洞察力,二級光暈,晶體合適的壓強(qiáng)與生命恒久的溫度。
35
詩的聲音,是詩人生命的節(jié)奏,也是他對世上萬象的觀感。
詩歌要有適合于特定題材的流暢、美妙、自如的聲音,但這種聲音效果是詩人久經(jīng)磨礪、反復(fù)調(diào)試的結(jié)果。
音義協(xié)調(diào)的好聲音,自然的聲音,其實(shí)等著詩人提煉,和發(fā)明。
找到并校準(zhǔn)那絕對的聲音!
別相信自然而然就會流暢的說法,這么說,不是外行,就是自矜的謊言。
36
詩歌的聲音也是意義的一種。它聚攏、塑型了時空。余未嘗見過哪個好的詩人,對聲音沒有特別的敏感。
對現(xiàn)代詩而言,聲音起到的絕非裝飾,它也是詩的創(chuàng)造性存在本身。
對好的詩人來說,聲音也要求原創(chuàng)性。聲音本身也是講述、吟述、回憶、暢想、譏誚、反諷……
聲音,語言在抖動。
噢,別忘了,寂靜,原始寂靜也是詩的聲音之一……
37
驚動了詩人,使他覺得值得以詩歌處理的那些事物,都有自己內(nèi)在的節(jié)奏,詩人尋找它,呈現(xiàn)它。好的現(xiàn)代詩,節(jié)奏像是事物自身的;壞的現(xiàn)代詩,節(jié)奏是詩人強(qiáng)行嵌入的。
對詩歌的“耳感”,帕斯一向極為重視。他說過:“何謂理解一首詩?其意義首先是:聽見它。節(jié)奏是區(qū)別和類似的關(guān)系:這個聲音不是那個聲音,這個聲音近似那個聲音。節(jié)奏是原始的比喻,而且囊括了其它一切。它說的是:連續(xù)就是反復(fù),時間就是沒有時間”。(《總結(jié)》)
38
有些詩,聲音躍居首位,我們只消打開感官深深浸入、出聲吟詠即可,未必要去“破譯”什么“密碼”。
我甚至想拎起來“抖一抖”這首詩,它準(zhǔn)會發(fā)出單純悅耳的“泠泠”聲響!
39
詩歌話語區(qū)別于其它話語的特征,一般地說表現(xiàn)在以下四組差異對比上:音樂性/松弛性;創(chuàng)造性/約定俗成性;表現(xiàn)性/平面性;構(gòu)成性/單維性。這里暫且不談后三組對比,只談其“音樂性/松弛性”的方面。
傳統(tǒng)詩歌也非常講究音樂性,但它的音樂性是由預(yù)先設(shè)置的聲律音韻決定的。也可以說是“音在筆先”。而現(xiàn)代詩的音樂性,是與詩人瞬間生命體驗(yàn)的節(jié)奏共時生成的,聲音是特殊的“這一個”意義的回聲。正如伯克茲所言:“好的詩歌是對聲音和意義的一種復(fù)合性認(rèn)可。在其中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聲音是意義的一種,意義也是聲音的一種。意義對應(yīng)于心智,聲音對應(yīng)于心境。”(《指定繼承人》)
重讀舊作,發(fā)現(xiàn)我年輕時寫的詩,元音發(fā)得很足,那是因?yàn)闈撘庾R中是寫給別人看的。中年之后,有喑啞感,摩擦感,觸及感,那是自言自語。
40
格雷夫斯說,“詩是一種極敏感的物質(zhì),讓它們自己凝結(jié)成型比把它們裝進(jìn)預(yù)設(shè)的模型效果更佳。”(《現(xiàn)代派詩歌概論》)在此,不同的生命體驗(yàn)決定了聲音流動的不同型式。比如,詩歌的回旋(表現(xiàn)基本主題的句型旋律屢次反復(fù)),和聲(同時發(fā)生的幾個主題樂音的協(xié)調(diào)配合),變奏(由一個基本主題生發(fā)開去,保持主題的基本骨架而在裝飾、對位、音型、速度、調(diào)性等方面加以自由發(fā)揮),如此等等,都是意義與聲音的整一呈現(xiàn)。也可以說,現(xiàn)代詩的節(jié)奏是與“意義”相互發(fā)現(xiàn)、相互選擇的,聲音與意義同步發(fā)生。
現(xiàn)代詩的聲音,不等于“韻腳”。在我看來,詩歌韻腳的有與無,都不會自動帶來一首詩的成敗。
在使用現(xiàn)代漢語的情況下,許多時候,規(guī)律而密集的押韻,反而會毀掉一首詩的音義諧和——就像一個人的“好事”做得太多、太急切、太機(jī)械,反而讓人不適或生厭一樣。
現(xiàn)代詩人雖普遍追求非韻化,但其實(shí)特別重視個人的生命節(jié)奏。成功的詩歌既是心靈的運(yùn)動,也是“聲音的運(yùn)動”。高妙的聲音,能在語義、字詞結(jié)束之處繼續(xù)鳴響,召喚出語義不能說出的東西。
非韻化并不意味著詩歌的“非體化”。好的自由詩是“非韻而有體”的。體,與聲音也有密切關(guān)系。
非韻化不是刻意反韻(在恰當(dāng)?shù)牡胤皆娙瞬槐乜桃饣乇茼嵞_),但他們更重視的是“體”的自覺。詩是汩汩的泉源,但卻是一道“被引導(dǎo)的泉源”。在聲音節(jié)奏上保持著語感、語速款款的奔逸性,在境界上逡巡著前行—回溯力量。
41
不同的詩的節(jié)奏,也暗示詩人對時間的重塑。
42
如何判斷一個詩人作品的成色,當(dāng)然有許多方面。多年來,在我卻有一個不會稍事放寬的衡量維度,就是看其是否有值得“被再聽的聲音”。
我們眼見著有多少詩歌生手“破馬張飛”地認(rèn)為,現(xiàn)代詩嘛,就是“自由”,聲音問題無關(guān)緊要。我以為,與其說現(xiàn)代詩不重視聲音,不如說在現(xiàn)代詩中,“聲音”其實(shí)變得更重要、也更難了。
傳統(tǒng)詩歌的聲音是“預(yù)設(shè)”的,時常反倒不必付出更多心思。而所謂新詩里的“新格律體”,如果拘泥過分,常常也會導(dǎo)致表面化地理解詩歌文體,進(jìn)行“常識”意義上的形式鑒定,無多新意地呼吁“常體”的重建,不外是音韻、節(jié)奏、建行、段落格式的均量均質(zhì)等。
我以為,成熟的“現(xiàn)代詩”,應(yīng)使聲音成為意義的延伸,意義成為聲音的延伸。好的詩歌,真正教我滿意之處,必包括詩人對聲音的塑造。
于堅(jiān)表述過這樣的意思,道是“猶如中國書法的美感不是基于字義本身,而是來自線條流動的氣韻,詩歌的美感來自語感的流動。它是詩人生命的節(jié)奏,而不僅僅是音節(jié)的抑揚(yáng)頓挫”。
詩人把直覺到的組合成有意味的形式,成為內(nèi)/外契合無間的語感,詩歌的生命就得到了表現(xiàn)。是故,沒有生命真氣的詩歌沒有語感,故意制造的口吻和做作的行文特點(diǎn)沒有語感。沒有詩人的生命灌注的詩,更沒有語感。
我們讀優(yōu)秀的現(xiàn)代詩,所感到的既不是“預(yù)設(shè)”的聲音模式,也不是表面的類聚化的“音韻悅耳”。而是諦聽有個人化波長的聲音。
好的詩人,不惟有“道”,還有個人的“氣息”,貌似隨興,其實(shí)專注地提煉出了個人化的節(jié)奏和口氣,這種個人的聲音模式,已像指紋一樣捺進(jìn)文本中。
是否有能力將情緒、境界、思想,和聲音融為一體,是考量一個詩人水準(zhǔn)的可靠尺度,能經(jīng)受住我的挑剔、檢驗(yàn)的詩人,并不多。
43
詩的聲音,不僅是指清澈悅耳。還有一種發(fā)自生命深處的重濁的舒適。
44
戴望舒早期的《雨巷》系列,追求“耳感”。后來的《我的記憶》系列反對“耳感”。可按我的標(biāo)準(zhǔn),后者反而更有個人的聲音效果。
45
好詩,還要在潛意識中激起幽鳴……
46
隱喻詩歌的修辭復(fù)雜含混,但能更清晰地把詩歌說話的聲音和寫作者自己的聲音區(qū)分開。
47
保羅·策蘭說:“詩歌從不強(qiáng)行給予,而是去揭示。”
所謂“強(qiáng)行給予”?就是詩人處理材料時,以單一的視點(diǎn)和明確的態(tài)度直接“告知”讀者,他的倫理判斷、價值立場、情感趨向。這樣的詩表面看清晰、透徹,但實(shí)際上往往成為枯燥的道德說教,成為一篇被精心修飾過的“美文的訓(xùn)話”。如果詩歌變?yōu)楹唵蔚牡赖鲁兄Z,詩人會在不期然中標(biāo)榜所有正義、純潔、終極關(guān)懷都站在自己一邊,這樣就取消了詩歌的多樣性和與讀者的平等對話。表面看這種詩歌獲得了“統(tǒng)一性”,但這種統(tǒng)一是貧乏的,對事物的“清晰透徹”認(rèn)識恰好遮蔽了事物固有的復(fù)雜內(nèi)容——它“透徹”到了獨(dú)斷地壓抑透徹的程度。而“揭示”,就是保持對事物多樣性的認(rèn)識,如其所是地呈現(xiàn)它鮮活的狀貌,將含混多義的世界置于詞語多角度的光照之下,揭露或呈示它自身內(nèi)部的種種豐富性,同時維護(hù)著讀者沉思、提問、自由二度創(chuàng)造的權(quán)利。
48
情感經(jīng)驗(yàn)像是一塊布,做成體面的衣服靠的是詩人的“裁”能。
49
唯有有雄強(qiáng)創(chuàng)造力的詩人,能夠把“詩家語”和“非詩語言”熔煉為行氣貫穿揮浩的一體。
50
一首真正有創(chuàng)意的詩,不只是結(jié)束一次成功的創(chuàng)作,同時為其它的詩作敞開可能性。
51
隱喻,只是詩歌的語型之一,不應(yīng)形成“專權(quán)”。
詩意的經(jīng)驗(yàn)未必都要用隱喻表現(xiàn),有不可言說的神奇,也有可用口語言說的平中見奇,表面波瀾不驚中,內(nèi)在心靈的陡峭。
52
不一定奇詭。這也是好的詩歌語言:踏實(shí)而腴潤,經(jīng)過淬礪又像是脫口而出,單純又有骨子里的豐富感。平和深邃不再蠱惑,誠懇自尊又觸動人心。
53
秀才人情半張紙,詩家情誼一首詩。詩人之交看重“知音”。很多時候,一首好的贈詩,就是一首波瀾不驚又深厚緬邈的友情的頌歌。詩人的友情,不是那種強(qiáng)加于人的生死相托、剖肝瀝膽的表述,不是熱烈如火的戲劇化傾吐,而是詼諧、沉潛、明凈、誠樸、老派的君子之交,是一座夏日的“涼亭”:散朗,善良,明心見性,坦率誠樸,一無造作。
我給朋友寫過贈詩,也得到過朋友們的贈詩。讀這些詩,一座座友誼的“涼亭”佇立于我的生命,詩中雖沒有易感的措辭,而我已被溫?fù)幔驯桓袆樱瑹o法忘懷。
贈詩是“一對一”,故完全容不得表演,要實(shí)現(xiàn)心靈狀態(tài)和話語方式的合一。最好的話語方式是,筆隨心走,既不夸張,也不矜持,輕逸與溫厚融為一體,有如風(fēng)雨之夕圍爐談心,月下林中漫步,把隨興與雅馴,化若無痕地連成一氣。
54
以出世的眼光,寫入世的詩歌。能真切得教你恍惚,熟悉得教你陌生,是為上品。
55
好的詩人,不是煽情的“啊——”,他的藝術(shù)個性是沉毅的。這種沉毅既是面對世界與人生的神秘,而持有的優(yōu)雅的審慎的態(tài)度,也是一種緘默的、恭謹(jǐn)?shù)挠^察事物細(xì)節(jié)的風(fēng)度;同時,審慎、緘默和恭謹(jǐn),還體現(xiàn)了“寫作的倫理”——詩人要避免給人以虛張聲勢號令般的專橫壓力,要刪除那些突兀的刺耳的聲音,為“音高設(shè)限”。希尼在《舌頭的管轄》一文中談到畢曉普的詩歌的特點(diǎn)時準(zhǔn)確地指出:“仿佛她要強(qiáng)調(diào)她的詩歌……通過對細(xì)節(jié)的持續(xù)關(guān)注、通過穩(wěn)定的分類和語調(diào)平淡的列舉而與世界建立起一種可靠而謙遜的關(guān)系。”
56
好的現(xiàn)代詩,既可“有我之境”地寫人,亦可專注地描寫“物”。就后者而言,詩不應(yīng)以強(qiáng)烈的主觀性來扭曲或強(qiáng)加于物,“物”本身就含有詩性,而將之接引出來就是詩人的工作。
比如,蓬熱的詩多為詠物詩,他凝神觀察客觀事物,將之細(xì)致鮮活地呈現(xiàn)于筆下。在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詩風(fēng)大行其道的情勢下,這種客觀詩反而顯得充滿“另類”般的新意和獨(dú)創(chuàng)性。他說,“物,即詩學(xué)。我們的靈魂是及物的,需要有一個物來做它的直接賓語。問題之關(guān)鍵在于一種最為莊嚴(yán)的關(guān)系——不是具有它,而是成為它。人們在物我之間是漫不經(jīng)心的,而藝術(shù)家則直接逼近這種物態(tài)。是的,只有藝術(shù)家才懂得這個道理。它是完美無缺的。它是我們內(nèi)心的清泉。”(《物,即詩學(xué)》)蓬熱的詩歌語言有極強(qiáng)的塑型性,冷靜準(zhǔn)確地呈現(xiàn)物象,于不動聲色中顯露新奇。
寫物時,詩人要有能力提供物的本真自然之美,更重要的是,他應(yīng)提供一種陌生化的“說法”,一種全新的“冷客觀”的措辭方式。
我們常說,“詩是命名”,這話不錯。但別忘記了詩不僅為“我”的經(jīng)驗(yàn)命名,它還應(yīng)向現(xiàn)象敞開,為物自體命名。后一種命名常常是更為困難的,它意味著你要將觀察力、專注力和書寫力突入到喑啞未名領(lǐng)域的極限。
57
好的現(xiàn)代詩,每三句之內(nèi),應(yīng)有個趣味點(diǎn)。六行之內(nèi),應(yīng)有個“炸點(diǎn)”。九行過后,應(yīng)讓人既心領(lǐng)神會又無從轉(zhuǎn)達(dá)。三、六、九者,約數(shù)也。
58
在“說什么”確定之后,“怎么說”就凸現(xiàn)為更重要的問題。而說到底,對藝術(shù)本體而言,詩歌還就是個“怎么說”的問題。
葉芝說,“有話語力量的詩人,要敢于重新處理被別人處理過的題材”。在似乎已被過度開伐,幾乎耗盡的語言密林中,詩人要有能力在那些樹干上,以新異的方式雕刻出個人化的、細(xì)膩深邃的詩的紋理。
59
“詩人是孤獨(dú)的”。這種說法似乎是詩人的另一種定義。
其實(shí),如果你心智和情感反應(yīng)正常的話,誰不孤獨(dú)?我以為,詩人不只是孤獨(dú),更重要的是他有能力將孤獨(dú)話語化,他觀照孤獨(dú),尋找友情和對話的安慰。
語言比詩人更孤獨(dú)。
60
詩歌是操勞生活中可貴的瞬間迷失,寬懷。
61
詩人天真,詩人復(fù)雜,詩人是天真和復(fù)雜的奇特融合。
62
詩有詩的運(yùn)氣。我看到,有運(yùn)氣的詩人,必有天賦:有天賦的詩人,未必有運(yùn)氣。教我嘆息。
63
余寫詩、評詩已逾30年,雖然對不同類型的詩我趣味廣泛,但前提是它必須是某種類型中的上品。“多元化”不應(yīng)是平庸者的遁詞,關(guān)鍵是詩人據(jù)何自詡構(gòu)成了藝術(shù)意義上的一“元”?這么說我的眼光其實(shí)很挑剔,能滿意的詩作不多。
我的基本想法是,現(xiàn)代詩可以有不同的類型,相應(yīng)也有不同說法。但對我來說,有個樸素但最主要的尺度,說起來簡單,真正做到很難——詩,一定要讓人讀得下去。
要有趣味,要有活力,無論你是親乎情、切于事,是智性,是抒情,還是另類式的鋒利詼諧,還是奇境式的隱喻,如此等等,前提是都要有詩特殊的勁道或魔力。為什么讀詩?因?yàn)樗凶屛覀冇淇斓摹⑽覀儽灸艿刳吔恼Z言磁力。
詩歌是文學(xué)中最精短的文體,如果它讓人讀不下去,說到哪兒都是有問題的。現(xiàn)在我整天就面對不少詩,收到刊物也好詩集也好,想看看,但完全讀不下去,不是不讀,而是一首詩看三五行就意興索然。沒意思,沒趣味,既無真情實(shí)感,真知灼見,又無奇思異想,“說什么、怎么說”,一切都像是死面饅頭,難以下咽。
64
現(xiàn)代詩更喜歡“實(shí)驗(yàn)”。但你“實(shí)驗(yàn)”得讓真正的內(nèi)行都看不下去,無論它多么“前衛(wèi)”,你沒什么可爭辯的,因?yàn)槟銓懺伊恕?/p>
檢驗(yàn)是否是好詩人有一個看似不通,卻十分有效的標(biāo)志,即你在詩壇的“敵人”是否真看你的作品,不僅為了攻擊。
65
好的詩歌,心靈大于學(xué)養(yǎng),性情逾越頭腦。只有個人才有心靈。
66
普遍認(rèn)為,詩是青年人的藝術(shù)。但真正的好詩,必能經(jīng)得起成年人分享。有種見解有道理:“中國新詩,沒有培養(yǎng)起成熟的成年詩歌文化”。成年人詩歌,是有意探尋生命真相的人之間的非常誠懇的交流。中國的詩人跟著青少年趣味走,青少年則跟著流行時尚走,約等于說青少年膜拜流行時尚,詩人則膜拜青少年。
青少年需要的是抒情,刺激,反叛,需要身體的發(fā)泄,這也使得詩人對語言、文體的理解淺薄。
青少年趣味有一個特點(diǎn),詩歌寫得比較輕松了。但輕,變成了一種草率的輕,而不是鄭重的輕。真正的詩歌應(yīng)該是“輕逸”的,不一定要沉重、艱澀,鄭重的輕才會帶來藝術(shù)意義上的輕逸,草率的輕,帶來的常常是輕浮。
卡爾維諾說得好:要寫得像鳥一樣輕,但不要像鳥的羽毛一樣輕。
67
對那些真正成熟而優(yōu)秀的詩來說,無法截然分出“悲觀”與“樂觀”,“堅(jiān)信”與“遲疑”。它像堅(jiān)實(shí)潤澤的蛋白石一樣,它的光能在慢慢轉(zhuǎn)動的不同角度下放射出不同的色彩,成人寫作,經(jīng)驗(yàn)的包容力在此產(chǎn)生。
68
一個有雄心、有才能的詩人,應(yīng)該廣泛閱讀不同類型的經(jīng)典。不是為了仿寫,而是為了知道應(yīng)該超過什么。
海明威說得對,“好的作家要寫出前人沒寫過的東西,或者說,超過死人寫的東西。”
因?yàn)榛钪脑娙说拿暎蠖嗍窃u論家應(yīng)時制造出來的,而經(jīng)典卻經(jīng)由歲月公正殘酷的選擇、積淀。這好比真正的跳高運(yùn)動員,他爭的是橫桿上的高度,而不僅是同他一起比賽的人。
69
最好的詩,是活著的有機(jī)自在物,會隨著讀者年齡和閱歷的豐富,而不斷煥發(fā)豐富的意味。次一等的詩,使讀者愿意重溫原來的語境。再次一等的詩,既不能接引讀者超越原來的語境,也無法吸引他回到原來的語境。
70
一首詩能讓人讀下去,除有趣味外,還有個要素,簡單說就是確系有驚動了詩人自己的什么東西要表達(dá)出來。
所謂言之有物——“充實(shí)之為美”(孟子)。
說起來這是常識,可我是有特定語境的,我感到當(dāng)下詩壇沒話找話,或把有話故意說沒了的人越來越多。
充實(shí),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特點(diǎn)。對中國近年詩歌而言,它們往往在詩里體現(xiàn)在程度不同的“事實(shí)性”,不是蒸汽,是固體,讓人看得見,摸得著。有些是詩人對本事的提煉、揭示,有些是虛構(gòu)的帶有熔點(diǎn)性的真切的生存情境。那些寫好了的詩歌,都是經(jīng)由纖敏、尖厲而幾乎無所顧忌的詩的眼睛發(fā)現(xiàn)和想象出的,它們本身就含有貨真價實(shí)的詩歌難度和趣味。
“難度”不在表面的修辭效果,而在陡峭的角度和精審地刪繁就簡,表現(xiàn)出的貌似隨興般的風(fēng)度。
新鮮、坦率、詼諧、角度刁,會激發(fā)經(jīng)驗(yàn)讀者的興趣。“舞蹈和舞者怎么分開”,“寫什么和怎么寫”不能簡單二分。現(xiàn)在的閱讀環(huán)境與八、九十年代不同,經(jīng)驗(yàn)讀者的趣味變化不小。那種直奔形而上的玄學(xué)寫作、奇境寫作遜位了,與生存發(fā)生真切摩擦,帶著生活質(zhì)感和鼻息的詩,恰逢其時成為顯豁潮流。
當(dāng)然,說詩歌要“充實(shí)”,還難以完全盡意,關(guān)鍵是充實(shí)本身的質(zhì)量如何。生活細(xì)節(jié),體驗(yàn),感悟,思考,不僅要誠實(shí),還得真正有新意有新鮮清冽味道,像早晨猛然打開窗子一樣。
詩歌既可能被過度修辭吞噬,也可能被雞零狗碎的無聊事實(shí)吞噬,把真話說成真詩,難度很大。
71
詩歌要有具體感,但同時應(yīng)注意“用具體超越具體”。詩歌源于個體生命的經(jīng)驗(yàn),經(jīng)驗(yàn)具有一定的敘述成分,它是具體的。但是,僅僅意識到具體還是不夠使喚的,沒有真切的經(jīng)驗(yàn)不行,但再好的經(jīng)驗(yàn)細(xì)節(jié)也不會自動等于藝術(shù)的詩歌。一旦進(jìn)入寫作,我們的心智和感官應(yīng)馬上醒來,審視這經(jīng)驗(yàn),將之置于想象力的智慧和自足的話語形式的光照之下。“用具體超越具體”,其運(yùn)思圖式或許是這樣的:具體——抽象——“新的具體”。
72
余參與先鋒詩運(yùn)動30余年,奇才、高才、怪才詩友不在少數(shù)。靜心細(xì)辨,可嘆的是,竟很少看到始終能健康而深穩(wěn)、沒有讓詩歌毀掉的詩人,更多是“忍看朋輩成混蛋”。
才子們腦子夠用又肯下功夫,天上的老爺子也不虧待他們,他們終于成功了。但成功后的他們,卻被自己曾熱愛的東西鬧亂了。他們失去了寫作的本真與快樂,變得特別重視“象征資本”和別人的看法。為把自己變成可供欣賞的對象,他們刻意發(fā)展怪癖,自我戲劇化,把好好的生活弄得一團(tuán)糟。在人前,他們簽名簽得都快忘自己姓什么了,而獨(dú)處時,卻焦慮、痛苦、疲憊不堪。由于丟失本真,他們也不能把這焦慮和痛苦轉(zhuǎn)化成新的寫作材料和動力,而只是靠炫技瞞天過海。
對詩歌我持一種平和的看法。沒有人強(qiáng)迫你寫作,我們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從事這件事,是因?yàn)樗刮覀兛鞓泛托陌玻刮覀兏械綄ι?jīng)驗(yàn)的留戀,并保持對人性秘密的好奇。寫詩者的魅力體現(xiàn)在,當(dāng)他用語言使生存的遮蔽敞開時,自身的生命也逐漸變得扎實(shí)、透亮。
如果寫詩帶來的是心性的迷失,它就是一樁可怕的勞作。因此,我認(rèn)為讓詩歌毀掉的人,必有僭妄之心。忠誠于藝術(shù)的健康寫作者,理應(yīng)是歡愉敏識、鎮(zhèn)定自若的。
再寫不出好詩,至少可以不寫。
這不寫,算不算對詩歌嚴(yán)肅敬意中最高級的那一種?我想,它就是。
73
多年來,詩歌界總是充滿方法論的膚淺論爭,什么隱喻還是口語,抒情還是敘述性,知識分子寫作還是民間寫作……我以為,面對復(fù)雜的情感經(jīng)驗(yàn),我們的寫作辦法(不完全同于“手法”一詞)其實(shí)還不是太多,似乎不必過度人為地在話語型式意義上老死不相往來地“站隊(duì)”。我們應(yīng)提煉一種帶有個人特點(diǎn)的“融合性”。
融合,當(dāng)然不是抹平個體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上的基本姿勢基本旨趣,而是在此基礎(chǔ)上深思熟慮地增補(bǔ)。至于如何有個分寸?可能言人人殊。如果融合創(chuàng)造力最后變成沒有個性的亦此亦彼的“平不塌”,那就是令人厭倦的壞詩。
這個挺難,屬于經(jīng)驗(yàn),難以明確“量化”。無疑,“通脫”、“融合”,與書桌上平面的“雜糅”不是一回事。前者屬于修煉到一定段位后自然產(chǎn)生的寫作自覺。唯大詩人能完成大融合。
74
有人說現(xiàn)代詩的修辭基礎(chǔ)是暗示、隱喻。未必如此。我看到,有些現(xiàn)代詩,回避間接性,其最打眼的反而是一系列準(zhǔn)確、本真的細(xì)節(jié)提煉。你簡直就勿需用“言此意彼”方式進(jìn)入,也不必調(diào)動你的直覺,它快捷跳脫,不留余地,“嗒”一下就撞在你心上。
說實(shí)在話,這類不飾險崛的細(xì)節(jié)提煉,更是衡量一個詩人“手藝”的重要尺碼之一,因?yàn)樗y以蹈襲,愈顯其功實(shí)倍。
75
口語詩歌表面看好寫,其實(shí)更難魚目混珠。
沒有天賦的人,莫以為口語詩是捷徑。
成功的口語詩,其實(shí)是口語目的性的秘密變體天吶,我沒想到口語詩“現(xiàn)”了這么多人。
76
針對有人說新詩散文化,在一種抗辯的語境中,艾青干脆提出了“詩的散文美”,他是指新詩的語言要鮮活、真切。
我以為,散文的語言,如果寫好了,就是詩。試看海明威一部小說的開頭:
“那年深夏,我們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過河和平原,可以望見群山。河床里盡是卵石和大圓石,在陽光下顯得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流得很快,而在水深的地方卻是藍(lán)幽幽的。部隊(duì)行經(jīng)我們的房子向大路走去,揚(yáng)起的塵土把樹葉染成了灰蒙蒙的。樹干也蒙上了塵土。那年樹葉落得早,我們看到部隊(duì)不斷沿著大路行進(jìn),塵土飛揚(yáng),樹葉被微風(fēng)吹動,紛紛飄落,而士兵們向前行進(jìn),部隊(duì)過后大路空蕩蕩,白茫茫,只有飄落的樹葉。”(《永別了,武器》,湯永寬譯)
你可試著分行。它多么干凈,真切,肌理鮮活,節(jié)奏(即使是譯文)呼之欲出。這樣的語言富于真正的質(zhì)感,這難道不是詩嗎?新詩,沒有嚴(yán)格的詩型成規(guī),它更重視的是把活在現(xiàn)代人口頭的語言,完美地提煉出來。
77
詩就是自由。但與其它自由不同,它尤其要求有自由的能力。好的詩人之間,無論彼此采取什么語型,還是能一眼看出詩之成色。
有些外行見到用口語寫詩,即驚呼:“不是詩!他使用的是我們說話的語言。”
是啊,就因?yàn)槟阒豢吹搅嗽娙耸褂昧斯餐恼Z言,所以你和詩人永遠(yuǎn)沒有共同語言。
78
一些現(xiàn)代詩所描述的事物,從表面看沒有必然聯(lián)系,但它們卻有內(nèi)在的呼應(yīng),它們都與變化和生長密切相關(guān)。如果說在哲學(xué)家眼中“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的話,那么一個詩人則應(yīng)對生活保持“太陽每天都是新的”這種審美的自由的高傲態(tài)度。正所謂“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
79
現(xiàn)代詩人不僅專注于經(jīng)驗(yàn),他們依然在抒情。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代抒情詩不是我們習(xí)見的浪漫主義詩歌。其現(xiàn)代性和獨(dú)特性體現(xiàn)在,它們不是那種陳腐的抒情詩中出現(xiàn)的類型化的道德自詡和單向度的濫情。現(xiàn)代抒情詩的特性體現(xiàn)在,在整體的濃郁的情感氛圍中,巧妙地包容了個人本真的身世感,經(jīng)驗(yàn)細(xì)節(jié),無意識的沖涌,生命記憶,乃至自我盤詰與自我爭辯。
還有同樣重要的,詩人表達(dá)直覺的天賦,冷靜的詞語塑型與控制能力,和對個人化詩意空間的結(jié)構(gòu)能力。如果深入細(xì)辨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抒情詩還成功地挽留了現(xiàn)代“智性詩歌”的有益成分,運(yùn)用曲折復(fù)雜的現(xiàn)代修辭技藝,以及對生命體驗(yàn)的多視角吟述,避開了以往抒情詩中由于濫情易感,缺乏本真細(xì)節(jié)經(jīng)驗(yàn)、意義畛域,從而使詩情最后被蒸發(fā)掉的險境。
80
一個合格的詩人一定會有夢幻般的體驗(yàn),有時還會有“靈感”光顧。但一個優(yōu)秀的詩人卻知道,一旦進(jìn)入寫作,詩人應(yīng)馬上醒來。詩人提供的不是來去無蹤的“靈感”,而是一件件精美的語言藝術(shù)品。
“靈感表現(xiàn)”是不錯的,但靈感并不必然達(dá)致“詩的表現(xiàn)”。
81
好的詩歌無疑應(yīng)有質(zhì)實(shí)的精神重量,但從詩的本體依據(jù)上看,詩歌畢竟是輕逸的生命靈韻或性情之光的飛翔。在許多時候,如何以輕御重,以小寓大,以具象含抽象,就成為對詩人詩藝和真誠的雙重考驗(yàn)。艾茲拉·龐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藝考驗(yàn)真誠。如果一件事沒有用技藝去敘述,它的價值就比較差。”
這里,真誠不僅指情感發(fā)生學(xué),更主要是指詩歌完成以后的審美成色——如果沒有詩的技藝,很可能你情感的真誠就要打很大折扣。
我們眼見著不少的詩人,由于缺乏技藝的自覺,而把真實(shí)的情感活活寫“假”。
82
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有一種“堅(jiān)實(shí)”的力量。在《漫游、歷險》一文中他說,“我無意中得到了詩的真諦:言簡意賅。”這句話除了“削去虛飾,使詩臻于簡潔”這一含義外,還意味著詩人在處理材料時的“慳吝”態(tài)度:用最少的精審的材料投入,“產(chǎn)出”最多的內(nèi)涵。
但是,我們要知道,詩歌的“簡潔”與否,并不簡單地事關(guān)詩歌篇幅的長與短。它不是一個體積概念,而是一個載力概念。一首飽滿的長詩也可能是“簡潔”的,而一首空泛的短詩,也會冗長得足以令人厭倦。
83
“氣”,作為中國古典詩學(xué)的審美范疇,難以用邏輯思辨語言傳釋,但每個真正的詩人都不會不理解它。現(xiàn)代詩同樣應(yīng)注重完整的境界,內(nèi)凝的骨力,淳樸的情韻,渾重的氣格。
對詩人而言,詩歌之“氣”,源于你的語言與生命體驗(yàn)的交感注息、升沉開合。骨氣干凈,行氣貫穿,鋒藏氣逸,皆源于心樞。詩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真正的詩人,清楚這里的玄機(jī)。
84
詩歌永遠(yuǎn)只是詩歌,它首先在語言上應(yīng)令人沉醉和玩味,否則題材再“重要”也在審美上無效。好的詩人,不止提供新的經(jīng)驗(yàn)和境界,同樣重要的是他必須提供新的“令人產(chǎn)生快感的說法”。
“快感”,是啊,閱讀的喜悅,專注,對心智的激發(fā),沒審美快感我們干嗎讀詩歌?詩歌應(yīng)提供只能經(jīng)由詩歌所提供的勁道,即使談到“深度”,那也是特殊意義的,它絕不是對哲學(xué)、歷史的卑屈圖解。
我認(rèn)為,雖然詩歌的構(gòu)架可以決定一部作品的“意義”,但只有“肌質(zhì)”,才能決定它是不是好詩,進(jìn)一步說是不是真正的藝術(shù)品。
優(yōu)秀的詩之所以能使我們手不釋卷、激動人心,就在于它吟述著不能為其它話語所轉(zhuǎn)述、所消解的,幽邃的心智,生存和生命的紋理,個體心靈的迂回升沉的奧秘。
85
成色十足的“肌質(zhì)”,乃是無法用散文的語言轉(zhuǎn)述的部分。它是一種具有生命質(zhì)感的“活物”,它自有脈息、搏動、渾茫、天成,它不承載明確的觀念,甚至不可言說,卻又直指人心。
肌質(zhì)像顆粒般細(xì)小,卻具有無法言說而神完氣足的“彌漫感”。
噢,“彌漫感”,就是這個詞!它不是個規(guī)范的理論批評術(shù)語,但很可能比既有的術(shù)語更有效。詩是一種構(gòu)架與肌質(zhì)有同樣價值的語言,但詩的秘密卻在于是一種為了肌質(zhì)自身之美的語言。
從語言本體論向度看過去,那些在“我說”之后,有能力進(jìn)一步讓“語言言說”的詩語,才是彌足珍貴的詩歌“肌質(zhì)”,也是現(xiàn)代詩存在的本體依據(jù)。
86
法國詩人讓·貝羅爾說,在“詩最成功的瞬間,總有一個‘我說’和‘它說’交相輝映。有時詩人掌握話語,有時話語支配詩人;有時詩人使用話語,而有時是話語在呼喚詩人。”(《詩在話語的空間相互追逐》)
貝羅爾的話,是一個成熟詩人的經(jīng)驗(yàn)之談。作為受到超現(xiàn)實(shí)主義影響,但又能將之問題化,保持有分寸的反思性的貝羅爾,雖然不反對詩人話語的澄明性,但更不愿放棄詩歌話語的“神秘的偶然性”。所謂“有時……有時……”,不是指詩人的不同寫作階段,而是“我說”與“它說”往往是在一個神秘的共時性中穿逐的。
“它說”,即讓語言自身說話——語言言說。因?yàn)樵姼璨粌H是表述“我”的情感,詩也是表述“元詩”本身的,它突然將美妙地攫住自己的陌生新鮮的東西往前一推,或驟然轉(zhuǎn)向,那即是詩。
我想將這種寫作稱為極端的“寫作”,而非極端的寫“詩”。寫——詩,通向的是約定俗成的關(guān)于“詩”(包括現(xiàn)代詩)的成規(guī)(Decorum)。而“寫作”,強(qiáng)調(diào)的是寫的過程,在不斷地探尋“寫”
的過程中,對詩可能性的新的理解和接納。
87
海德格爾在《詩·語言·思》中嘗言:“語言言說。人言說在于他回答語言。這種回答是一種傾聽。其言說在它被言說中為我們言說。”
海德格爾的話值得我們深思。他揭示了真正優(yōu)異的詩歌,不僅是詩人言說,還要激發(fā)出“語言言說”,要保持“我說”和“語言言說”之間的美妙張力。
在“我說”(即詩人言說)之后,保持“語言言說”的魔力,即讓語言進(jìn)一步言說,看似玄奧,其中卻有更深的道理,每一個有經(jīng)驗(yàn)的優(yōu)秀詩人都不會不理解它。
我們常說,詩人發(fā)現(xiàn)語言、掌握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當(dāng)一個人的寫作水平進(jìn)入更高階段,他必會體悟到“語言言說”的性質(zhì)。
好的現(xiàn)代詩,會呈現(xiàn)“語言言說”的魔力。語言在詩人結(jié)束言說之后,依然帶著高強(qiáng)度的自身的“電荷”,進(jìn)一步工作。詩中的語言,不只是為其負(fù)荷著的固定語義而存在,它似乎具有了獨(dú)立的“被再聽、再看”的生命,把我們引向更神奇、迷蒙,卻又更能擊中心靈幽微之處的力量。
88
當(dāng)我說“語言言說”的實(shí)驗(yàn)詩,不再是詩人出來說話,而是由字詞本身出來說話時,我是為使表意更明晰、避免平庸的相對性,而有意采取的“絕對”說法。其實(shí),對這個問題的“正確”的表述應(yīng)當(dāng)是:語言結(jié)構(gòu)與詩人之間,不再是后者賦予前者,而是一種雙方彼此的照亮、選擇和發(fā)現(xiàn)。在沒有寫作之前,傳統(tǒng)的寫作是詩思已先然存在,“胸有成竹”;而實(shí)驗(yàn)詩“寫作”則是,詩思是在寫的過程中,才與語言同步發(fā)生的,詩意是被偶然地一點(diǎn)一點(diǎn)豎立起來。詩人循著一種神秘的預(yù)感前進(jìn),他并不清晰語言結(jié)構(gòu)的深處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奇跡,他必須承受“天才”所喚醒的壓力,忘掉“詩所言”,專注“寫作本身”。
如果說常規(guī)的詩歌,其語義是潛在散文式的似斷實(shí)連的“線條”,那么“語言言說”的詩就是發(fā)散式的晶體點(diǎn)狀面,是依靠純語言事實(shí)來支撐的。前者直線運(yùn)動到一個終的結(jié)束,后者互動、摩擦,分裂出更小的“話語微粒”。前者構(gòu)成“意思”,后者構(gòu)成“意味”。前者是由糧食釀成的酒,后者像是酒精燃燒時發(fā)出的熱能。前者是存在,后者是空無。前者是地面,后者是地面和天空兩面拉開的力量:看不見卻可以觸摸,聽不到卻可以感受。
89
一個詩人應(yīng)該記住,詞語也有自己的生命,它們會朝向靈韻的滿盈,也會對我們言說,而不僅僅是我們把它說出。如果按照結(jié)構(gòu)主義的觀點(diǎn),語言受深層文化結(jié)構(gòu)的制約,不亞于受特定個人心態(tài)的制約;那么我們同樣也可以說,語言受深層潛意識的召喚,不亞于受詩人顯意識的召喚。一首有真義的詩,必會出現(xiàn)“我說”和“語言言說”的共鳴與對話關(guān)系。存在在思中形成詩后,詩人和內(nèi)行的讀者還要學(xué)會再聆聽“語言言說”。因?yàn)椋刑厥飧惺芰Φ摹罢Z言言說”,會超越本身而自動地“吸附”我們未知的存在,而那些被“吸附”而來的存在,一定與我們的深層神秘生命體驗(yàn)休戚相關(guān)。
赫塔·米勒說得多干脆:“我們每一次都要凝神聆聽,探詢言語之下暗藏的深意。在每一句話語中,也就是說,在每一次說的行為中,都坐著別的眼睛。”
90
語言在為某物命名之后,年深日久它的光華和力量也會日漸磨損,使原初的、充滿活力的發(fā)現(xiàn),變?yōu)楣擦魍ǖ念惥刍闹阜Q工具。
比如,今天當(dāng)我們說“鵝毛大雪”,我們再也不會驚喜地意識到“鵝毛”與“大雪”的象喻關(guān)系,我們抓住的不再是有命名力的“存在”,而只是接受了“雪很大”這一個氣象學(xué)事實(shí)。再如,當(dāng)我們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時,我們也不會領(lǐng)受到此言在原初命名時蘊(yùn)涵的天人同根的、深厚的彼此呼應(yīng)關(guān)系,而只是將之簡化為“人應(yīng)自勉”這一陳舊教條。至于隨便想起的“人老珠黃”、“一帆風(fēng)順”、“馬革裹尸”、“五體投地”、“引而不發(fā)”、“運(yùn)斤成風(fēng)”……如此等等,這些曾經(jīng)創(chuàng)造性地照亮過“存在”的詩意的語詞,如今都已衰落為惰性的符碼了。
正是有感于語言積垢的遮蔽,海德格爾才對詩歌語言進(jìn)行了高度的評價:“詩決非是把語言當(dāng)作在手邊的原始材料來運(yùn)用,毋寧說,正是詩首先使語言成為可能。詩是歷史的人的原初語言,所以應(yīng)該這樣顛倒一下——語言的本質(zhì)必得通過詩的本質(zhì)來理解”,“詩意讓敞亮發(fā)生,并且以這種方式使存在物發(fā)光和鳴響……我們必須學(xué)會傾聽詩人的言說”。(《詩·語言·思》)
91
要區(qū)分:創(chuàng)造性的晦澀;頭腦一鍋粥的晦澀。
海明威說,“真正的神秘不應(yīng)當(dāng)與創(chuàng)作上的無能混淆起來,無能的人在不該神秘的地方弄出神秘來,其實(shí)他所需要的只是弄虛作假……神秘主義包含一種神秘的東西,和許多種神秘的東西。但無能,并不是一種神秘。”(《海明威談創(chuàng)作》)
92
1979年7月,帕斯在墨西哥大學(xué)作了一場名為《寫與說》的演講。他說:“我們像看幻影戲一樣,心中感到詞語被賦予血肉之軀的那個時刻。詞語確有生命,它把我們放逐。詞語在對我們訴說,而不是我們把它說出”。
這是詩人多年以來在寫作中冷暖自知的經(jīng)驗(yàn)之談。但它只能指望有深入的寫作經(jīng)歷的人理解。無疑,詩的語言由詩人創(chuàng)造,從常識意義上講,這個理念是正確的。但是,當(dāng)一個人的寫作水準(zhǔn)進(jìn)入“更成功的瞬間”,他會發(fā)現(xiàn),真正的寫作更像是一種“聆聽”:聆聽語言自身的言說,聽從語言對你的引導(dǎo)和召喚。
語言作為存在的現(xiàn)身,既含有內(nèi)部的自動性成分,又含有全部歷史使用過的語義積淀,同時還有著詩人潛意識、直覺的投射。因而,當(dāng)它被如上諸種因素調(diào)動時,才會帶著全部豐富性而自成格局,令人驚愕并喜悅。
帕斯的《驚嘆》,就道出超越固定語義后,直覺中對“靜”的領(lǐng)悟,使語言獲具了進(jìn)一步自我言說的魔力:
靜
不在枝頭
在空中
不在空中
瞬間
一只蜂鳥
“靜”在哪里?詩人留下諸多空白、斷點(diǎn),但語言本身并沒有停止工作——靜,在即目即景卻“心與道合”的無言喜悅之中,在澄懷味象的瞬間,人與一只蜂鳥猝然相遇,天地同參,靜與動彼此融會,互證真身。帕斯喜歡中國古代詩歌,這里也有“鳥鳴山更幽”式的禪機(jī)。
93
與傳統(tǒng)詩歌具有的幾大類結(jié)構(gòu)形式殊為不同的是,現(xiàn)代詩的結(jié)構(gòu)形式是變動不居、非常多樣的。可以說每一首真正意味豐盈、技藝高妙的現(xiàn)代詩,都需要臨時“發(fā)明”出自己的結(jié)構(gòu)形式。正如喬恩·庫克在《詩歌理論·序言》所言:“每一個‘具象化的此刻’,都不同于另一個,因此每一個都必須被不同地意識到:規(guī)則必須每次都從內(nèi)部重新而來。”
因此,將亂花迷眼的現(xiàn)代詩結(jié)構(gòu)種類,硬性總結(jié)出幾種大的“范型”,是泛而不切的外行做法,對于寫作它基本是無啟發(fā)性的。
94
現(xiàn)代詩人在重新打量“抒情”在詩歌中的價值。過去,“情感飽滿,表達(dá)生動”就可以成就一首好詩了,現(xiàn)在,“情感”卻成為一個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我以為,抒情本身不會自動給詩帶來成與敗,關(guān)鍵是抒情的內(nèi)蘊(yùn),抒情的技藝高下。
重新打量“抒情”是有道理的。我看到,過度依賴抒情,會發(fā)展為“濫情和表演”,這是許多中國詩人的宿疾。似乎身為詩人,就應(yīng)像一鍋開水,咕嘟咕嘟挺熱烈。但最終一切都蒸發(fā)了,“詩本身”沒啦。這種宿疾也反應(yīng)在讀者那里,比如對戴望舒的作品,只是迷戀于“雨巷”之類,而完全沒有能力欣賞或感悟他真正出色的“我的記憶”系列。正是中國詩人和讀者的雙重宿疾,導(dǎo)致中國詩歌的水準(zhǔn)儀只定位于“抒情”,忽視了扎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和智性。
如何防止情感被“蒸發(fā)”?要有貨真價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和感覺、智性的加入。接著“一鍋開水”的比喻,我想引申到一鍋豆?jié){。如果說情感像豆?jié){,那么本真的經(jīng)驗(yàn)就是鹽鹵,它使詩凝成塊。而智性,則像是肉眼看不著的營養(yǎng)成分。
95
許多現(xiàn)代詩,有神秘的特點(diǎn)。對詩來說,我只認(rèn)可一種神秘,即“詩本身的神秘”。有些詩也神秘,但那是詩人在玩玄學(xué),或用詩去費(fèi)勁地顯現(xiàn)某個已成的文化哲學(xué)認(rèn)識。我有些煩。但我從來不煩“詩本身的神秘”。畢竟我們寫的是詩,是語言的快樂,不是向傲慢得一塌糊涂的哲學(xué)家卑屈地“套瓷”,也不是科舉考試的“試帖詩”。
值得提出的是,詩的神秘,也可用透明的語境出之,不一定“意味”一神秘,語言也跟著扭曲起來。總之,神秘不是個簡單的語言風(fēng)格概念。而不論何種方式,詩,總得有詩本身的秘密勁道才行。
96
現(xiàn)代詩中的象征,不是一種簡單的意義傳遞形式,更多情況下,還是參與意義生產(chǎn)、重新分配意義的形式。
因此,現(xiàn)代象征具有多義性、暗示性、雙重視野、超越性。——此象征不同于彼象征。
97
詩的結(jié)句,非常重要。既要結(jié)束,又不能封口。它不是關(guān)好一扇門,而是打開另一個空間,“篇終接混茫”。
98
現(xiàn)代詩呼吁挑戰(zhàn)習(xí)見的閱讀期待,發(fā)明出自己的讀者。馬拉美傲慢地說,一個健全人的重要天職之一,就是成為詩人藝術(shù)家。
99
20世紀(jì)以來,有創(chuàng)造力的寫作者漸漸顯豁地出現(xiàn)了模糊或松動文體界限的趨勢。文學(xué)家的“身份”變得較前曖昧起來。現(xiàn)代語言意識的普遍自覺,使眾多的寫作者意識到,寫作,無非就是人與“話語”發(fā)生的特殊周旋、磋商、交鋒,以此揭示生存,挖掘生命體驗(yàn),挽留想象力,享受書寫的歡愉。人與語言的關(guān)系,比人與文體的關(guān)系更致命,更有難度,更緊張。不是恪守文體的規(guī)范,而是探詢、挖掘語言的奧秘,構(gòu)成了有效的寫作者創(chuàng)造力的向度。
一個成熟的寫作者面對的不僅是狹隘的“文體意識”,而是更為開闊的“調(diào)動整個文學(xué)話語去說話”的能力。不論是詩歌,還是小說、散文乃至文論,無非都是“文本”;而寫作者最終需要捍衛(wèi)的,不是什么先驗(yàn)設(shè)定的絕對文體界限,而是保證寫作的活力、自由和有效性,“在詞語的密林中,我找尋引動我的東西。”至于這個東西是否適合于某文體的元范式,則是第二義的問題,甚至不再是問題。那些給文學(xué)帶來沖擊和新的可能性的人,恰好都是敢于異質(zhì)混成地松動文類界限的寫作者。先鋒派作家詩人自不待言,即使是理論家如羅蘭·巴爾特、本雅明、德里達(dá)、布魯姆、德魯茲、保羅·德曼等等,也都是自如地運(yùn)用多種語型、語碼的“多功能文士”,遂成為廣義的“作家”一員。
我看到,90年代先鋒詩人有意消除文體“等級觀念”,與其它文體“調(diào)情”,讓散文話語嫁接(甚至“焊接”)到詩歌中,的確有助于擴(kuò)大詩歌的載力、韌度、鮮潤感、可信感。詩歌于此不會消解,它的根莖反而成為隨機(jī)應(yīng)變、多方汲取養(yǎng)分的精靈。為你的詩文本注入越界搞來的“強(qiáng)心劑”。
100
詩歌不應(yīng)拒絕對日常生活的表現(xiàn)。但是詩歌不能成為枯燥的生活小型記事。一個詩人無論怎樣對生活的召喚殷勤備至,他都不應(yīng)放棄對藝術(shù)本身的信義承諾。好詩不乏生活的力量,但更具有“挖掘語言奧秘”的藝術(shù)魔力。
101
作為一種文體,詩歌會引起讀者的特別的“注意類型”和“閱讀態(tài)度”。詩歌的特征在于它擁有一定標(biāo)記,用來向讀者提供信號:“這是詩,應(yīng)按讀詩的方式閱讀、欣賞。”這樣,讀者的心理活動產(chǎn)生了定向反射,形成特殊的注意類型,詩的其它種種特征在這個基礎(chǔ)上才得以充分發(fā)揮作用。
“分行”,是最明確、最通行、最有效的定位法。讀者看到分行,其注意便按照一定的期待進(jìn)行閱讀。主要有三種期待:個體節(jié)奏化期待;非指稱化期待(深遠(yuǎn)的暗示);整體化期待(相信詩歌短短數(shù)行便可自我完成,其跳躍的部分由經(jīng)驗(yàn)讀者的想象連接)。
不要小瞧分行,“結(jié)構(gòu)主義詩學(xué)”正是從分析分行開始,對我們沒有自覺到,但實(shí)際上存在的約定俗成的理解模式給予了理論說明。
靜極——誰的嘆噓?
密西西比河此刻風(fēng)雨,在那邊攀援而走。地球這壁,一人無語獨(dú)坐。
這首《斯人》,是昌耀作品中最常被選入各種詩歌選本的詩作,它只有短短三行,卻境界幽獨(dú)而曠遠(yuǎn),意緒神奇,“言有盡而意無窮”,即使我們在閱讀時不加入詩人“傳記”的因素,也會被“三種期待”的魔力所攫住,激發(fā)出豐富的聯(lián)想。寥寥數(shù)語,目擊道存,一無依傍的突兀話語,卻“自動地聚攏”起我們的想象力、經(jīng)驗(yàn)和潛意識記憶。
102
“詩歌并非只是情感,而是經(jīng)驗(yàn)”(里爾克)。
那么,詩歌可以不要情感嗎?非也。好的詩人,把情感伸延至“情感命題”。讓蒸汽結(jié)晶化,寄托深邃的智慧和超越性。
103
威廉·黑恩說,“通常詩人第一本詩集中的作品是他們認(rèn)為詩歌應(yīng)該寫的內(nèi)容,然后他們的第二本——甚至更后期的——詩集中才開始挖掘?qū)λ麄儊碚f根本重要的東西。”
這句話令人深思。我以為,他談的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詩集出版問題。
成熟的詩人應(yīng)警惕精美的平庸之作。
104
假如要我揀出一條寫作現(xiàn)代詩的體會說與你們,我想它會使許多人感到詫異:現(xiàn)代詩是最不自由的詩歌形式。它不僅關(guān)涉詩章,而且關(guān)涉詩句;它不僅關(guān)涉詩句,而且關(guān)涉詞語;它不僅關(guān)涉詞語,而且關(guān)涉詞素;它不僅使詞素用力,而且要求“詞根”用力。
甚至,它讓標(biāo)點(diǎn)帶上生命的吹息。它讓空白成為更強(qiáng)烈的表意部分。
105
優(yōu)秀的詩歌,往往既涉入語義甚至潛意識的艱澀,又值得以意識去體驗(yàn)?zāi)酥猎忈專凰粫蛟忈尪⒓埽_的詮釋往往使它更為誘人。
布爾頓說,“理解增強(qiáng)了快感,而詩意也不至于被破壞了。一首好詩,在第二十遍閱讀時要比在第一遍閱讀時更饒有意趣。我們總能夠從中發(fā)現(xiàn)新的東西。而且,無論我們把它肢解得多么零碎,只要再退后一看,那些碎片即會一躍而重新合為一體。”(《詩歌解剖》)
106
讀一首好詩,我們是在欣賞一個教我們愉快的生命,他/她的活力,他/她的魅力,他/她的魔力。他/她略略超出我們,既令我們羨慕,又看得真切,而不是凌空高蹈地“失聯(lián)”了。
107
詩人與“寫詩的人”之不同,有一個硬指標(biāo),看他在專業(yè)共同體中,有無站得住的代表作。
108
有的詩乍看之下會讓我們的感悟力造成崩潰,但深入細(xì)辨,它又是維度豐盈、結(jié)構(gòu)俊逸、意味澄明的。自由閃灼的意象、開闊的語境,像滿天風(fēng)箏一樣美麗,但它們的線繩卻被穩(wěn)穩(wěn)抓在詩人手中。詩人知道,風(fēng)箏有合適的載重,風(fēng)箏線上的拉力保持很好,它才會迎著風(fēng)力的沖擊越飛越高——寫詩也同樣道理。
109
與散文比較,詩歌應(yīng)有“無法結(jié)束的部分”。維特根斯坦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對不可說的東西,應(yīng)保持沉默”。這句話對早期的維特根斯坦而言具有確指性:堅(jiān)持經(jīng)驗(yàn)證實(shí)的原則,認(rèn)為語言是表達(dá)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的,凡是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都是可說的;而超經(jīng)驗(yàn)的東西是不可說的,對這部分內(nèi)容應(yīng)保持沉默。
但是,許多人將維氏的“不可說”誤讀并普泛化了,他們把“不可說”的東西等同于“不存在”、“無意義”。我們知道,語言把握不住的東西肯定也是存在的,且不說你說不出未必別人也說不出,就是某些生命體驗(yàn),審美奇境,宗教,信仰,天地之道,靈魂?duì)顟B(tài),大自然呈現(xiàn)的“混沌”場域乃至氣功等……我們雖然難以清晰言說,但能簡單地否認(rèn)它們的存在嗎?因此,維特根斯坦后來又說,“世界是神秘的”,“上帝”、“靈魂”都有存在的道理。
詩人海森畢特爾在《表述可以表述的一切……》中寫道:
表述可以表述的一切
了解可以了解的一切
決定可以決定的一切
達(dá)到可以達(dá)到的一切
重復(fù)可以重復(fù)的一切
結(jié)束可以結(jié)束的一切
那無法表述的
那無法了解的
那無法決定的
那無法達(dá)到的
那無法重復(fù)的
那無法結(jié)束的
不要結(jié)束那無法結(jié)束的一切
海森畢特爾是德國“具體主義”詩人。具體主義詩人受到維特根斯坦理論的影響,這首詩就與維特根斯坦前、后期對語言的完整理念有關(guān)。此詩由兩個意義群落構(gòu)成。上一部分是講,詩人應(yīng)全力呈示自己的經(jīng)驗(yàn)世界,對可說的一切進(jìn)行命名。下一部分是說,詩人也不要認(rèn)為只有“經(jīng)驗(yàn)世界”才是詩歌表述的一切,經(jīng)驗(yàn)世界和靈魂世界還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關(guān)乎“真”,后者更時常關(guān)乎人的超越能力和審美想象力。對后者有賴于以隱喻或轉(zhuǎn)喻的方式部分地說出。而且,詩人應(yīng)捍衛(wèi)世界的神奇、鮮潤和混沌的元?dú)猓瑧?yīng)在詩中容留美妙的跳躍所帶來的“斷點(diǎn)”、“空白”。就像書法的“飛白”,以貌似“結(jié)束”來表達(dá)“那無法結(jié)束的一切”。
優(yōu)秀的詩歌,“空白”、“沉默”會成為表達(dá)的另一半,這就是詩人的想法。
110
人們說,詩歌要想自我證明,必然要有文體的儀軌。
這是只知其一。
其二是,先鋒詩就是對“從來如此”、“眾所周知”的儀軌的質(zhì)疑和超越。
其三是,先鋒詩若要具有藝術(shù)的意義,在對儀軌的顛覆之后,必須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