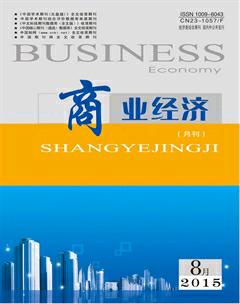公司視角的商業賄賂研究發現與啟示
高利芳++馬露
[摘 要] 商業賄賂是商業領域給予和收受賄賂的行為,它危害社會經濟秩序,是實務中治理監管的重點對象。國內外研究者從誘致商業賄賂發生的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以及它們對公司商業賄賂傾向及支付金額的作用。基于微觀的公司視角,研究發現,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有:較多關注公司對政府官員的賄賂,忽略了其他受賄對象;就公司賄賂的經濟后果提供的經驗證據不足,且缺乏長期的動態考查等。治理商業賄賂的途徑有:嚴厲打擊,提高商業賄賂的違法成本;嚴格防范,抑制商業賄賂的誘發因素;道德教化,形成反賄賂的社會文化。
[關鍵詞] 公司;商業賄賂;動因;經濟后果
[中圖分類號] F203.9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我國對于商業賄賂最早的法律規定見于1993年發布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這一概念正式提出是在國家工商總局1996年發布的《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2007年中央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在《關于在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中正確把握政策界限的意見》中,將其定義完善為“在商業活動中違反公平競爭原則,采用給予、收受財物或者其他利益等手段,以提供或獲取交易機會或者其他經濟利益的行為。”該意見也明確了商業賄賂的主體既包括各類工商業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及其從業人員,也包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等,從而為在更大范圍內認定和治理商業賄賂行為提供了政策依據。商業賄賂妨害公平競爭、惡化投資環境、破壞經濟秩序,易滋生政治腐敗與經濟犯罪行為,歷來是各國治理監管和反腐敗斗爭的重點領域。如美國通過《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針對美國在境外的公司和個人在商業活動中的賄賂行為進行定罪處罰。我國也隨著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進行,加大了對商業賄賂犯罪的打擊力度。2014年英國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因在華商業賄賂違法行為而被罰30億人民幣,多位公司高管被判刑,成為迄今為止我國政府針對公司商業賄賂開出的最大罰單。
商業賄賂行為對國家社會而言,無疑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學者們已經檢驗了在宏觀層面上賄賂的后果,且得出的共同結論是賄賂后果是災難性的,但是在微觀的公司層面上尚沒有一致的研究結論(Nichols,2012)。加強對商業賄賂犯罪主體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理解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經濟政策的互動關系,也有助于實務中對商業賄賂進行更為有效的治理。
二、公司商業賄賂動因的理論解釋
就公司商業賄賂行為的動因,國外研究給出了較為全面的理論解釋,主要圍繞三個方面:一是公司賄賂的主觀期望;二是公司賄賂的客觀壓力;三是公司賄賂的決策過程。
(一)公司賄賂的主觀期望
公司為何會進行賄賂,學術界有“潤滑劑”(grease money或speed money)與“保護費”(protection money)兩種假說(李捷瑜和黃宇豐,2010)。公司積極的行賄可能是為尋求不平等優勢和特殊待遇,賄賂加速了企業獲取經濟資源的效率,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Leff,1964;Huntington,1968),而在不利的制度環境中,公司也可能被動行賄,賄賂是一種非自愿的“稅”、“傭金”或“保護費”,是企業避免受到壞的監管、懲罰與掠奪的策略選擇(Fisman和Svensson,2007;Zhou和Peng,2012)。在高度腐敗的環境中,公司可能沒有選擇,只能支付“疏通費”獲取他們本應獲得的政府服務,但是許多賄賂交易是公司自行開始的,如為了免交或少交稅,確保獲得公共采購合同,繞開法律和監管,或者是為了設置壁壘阻止潛在的競爭者進入。
“潤滑劑”與“保護費”兩種假說,其主要區別在于解釋公司對商業賄賂的意愿方面有差別,但從公司賄賂的期望結果來看,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潤滑商業活動的車輪。然而商業賄賂的潤滑作用是有條件的。Myrdal(1968)提出“內生的騷擾”(endogenous harassment)理論,認為掠奪性的官員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會根據目標公司的支付能力而要求相應水平的賄賂支付。Kaufmann和Wei(1999)也認為只有當繁文縟節(red tape)或監管負擔是外生的,即獨立于官員索取賄賂的動機時,“有效率的潤滑”理論才是成立的。否則如果官員對于既定的監管規則有自由裁量權,就可能根據公司的支付能力“訂制”規則的性質和數量來騷擾公司,以盡可能多的索取賄賂。結果是支付了更多賄賂的公司實際上可能面對更高而不是更低水平的繁文縟節,賄賂像沙石一樣阻滯了企業增長的車輪,導致了管理的延遲。
(二)公司賄賂的客觀壓力
Lee等(2010)基于剩余控制權理論,論述了官員索賄如何驅動公司行賄:一是政府官員擁有的剩余控制權越大,官員索取賄賂的能力也越強,而公司就政府官員剩余控制權的接觸度(exposure)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有差別的。二是接觸度指外部事件給公司帶來的壓力,公司對腐敗的接觸度取決于國家腐敗的普遍性,以及公司與政府官員接觸的頻度,二者與公司被索賄的機率以及公司拒絕賄賂的壓力正相關。三是脆弱性指公司承受壓力的能力,公司對腐敗的脆弱性采用反向度量,以公司所擁有的、可以用來抗爭腐敗壓力的財務和政治資源測度,其與公司的行賄傾向負相關。Lee等(2010)的理論揭示了公共權力尋租是商業賄賂存在的重要原因,并且用接觸度和脆弱性兩個詞很形象地闡釋了索賄與行賄之間的互動關系。
公司被動行賄感知的壓力除了來自于政府官員,也可能來自于其他公司。如Carmichael(1995)指出盡管一個公司認識到賄賂是道德錯誤的可還是會從事它,因為“大家都這么做”。Lambert-Mogiliansky(2002)從官員和公司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商業網絡所形成的“關系經濟”角度,解釋了公司被迫進行商業賄賂的原因:首先,公司通常會屬于特定的商業網絡,作為網絡成員對公司是有利的,特別是在獲取內部人信息方面。其次,公司和官員存在信息不對稱,官員就合法事項所提供的私人信息對公司而言是有價值的,因此官員能夠從非法的合謀中獲利。當法律和行政制度越不穩定和越復雜,官員的內部信息越有價值。最后,如果有公司不愿意進行賄賂,官員就會威脅說不再披露他的私人消息給網絡中的公司,除非將不遵守非法契約即拒絕支付賄賂的公司驅逐出網絡。其他公司就會選擇對該公司實施懲罰,將其排除出網絡因此在商業網絡中,各公司在賄賂支付上會產生互律的誘致行為,以免受到集體性懲罰。endprint
由此可見,公司的賄賂行為通常是外部制度環境與自身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能簡單地認為公司只是腐敗的旁觀者或者受害者(Wu,2009)。公司的賄賂行為更可能是一個理性的、深思熟慮的決定,是計劃的行為(Powpaka,2002)。
三、公司商業賄賂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除了理論闡述,國內外研究者還從誘致商業賄賂發生的具體因素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囊括了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因素,以及它們對公司商業賄賂傾向及支付金額的作用。
(一)影響商業賄賂的宏觀因素
宏觀因素指國家層面的綜合性制度環境因素。學者們主要研究了如下與公司賄賂相關的宏觀因素:
1.政治。政治對公司賄賂行為有影響在于各國對權力制約和權利保障的程度有差異,而賄賂是權力尋租的產物。普遍的社會福利、高水平的政治制衡和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能夠減少公司的賄賂行為(Martin等,2007;Lee等,2010;Cheung等,2012)。而當政府控制經濟資源、服務效率低下,政策具有不確定性時,公司更可能行賄(Wu,2009;Zhou和Peng,2012)。
2.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司賄賂傾向及金額負相關(Sanyal,2005;Lee等,2010;Cheung等,2012;Zhou和Peng,2012)。以收入差距度量一國經濟發展的均衡性,則其與賄賂的關系不確定。Sanyal(2005)發現賄賂行為更多發生在收入差距較小的國家,Cheung等(2012)則得到相反的結論。
3.法律。普通法系的國家,賄賂發生的機率較小(Chen等,2008)。公司在法律體系質量較高的國家經營時,其賄賂成本較低(Zhou和Peng,2012)。良好的法制環境也能減少企業在融資時面臨的銀行借貸腐敗(Beck等,2006;Barth等,2009)。而當面對腐敗的司法體系、復雜的許可要求、不透明的法律和監管解釋時,公司更可能行賄(Wu,2009)。特別是在有關投資者保護的信息披露和法律訴訟較少、官員收入信息公開披露制度較少、董事會受托責任法規不嚴格的國家,公司的賄賂支付較多(Cheung等,2012)。
4.文化。依照Hofstede(1980)對國家文化的度量,男性度的國家文化與公司賄賂傾向正相關(Sanyal,2005;Chen等,2008),權力距離較大的國家賄賂行為也更普遍(Sanyal,2005)。權力距離大,意味著國家中個人和群體間的權力分配不公普遍存在。男性度與女性度相對應,男性度的文化崇尚個人成就的取得,對金錢和權力的追逐強烈,女性度的文化注重生活質量和同情弱者。Martin等(2007)也證實了高度成就導向的社會文化與公司賄賂傾向正相關,而集體主義和人道主義導向的社會文化與公司賄賂傾向負相關。人們的道德觀念也是社會文化的直接體現。Tian(2008)問卷調查了中國企業經理人員對商業賄賂的道德認知,發現道德相對主義是一個預測中國企業經理對賄賂和回扣偏好認知的重要因素。道德相對主義者通常較多地依賴環境而不是倫理原則來做判斷,高度的相對主義經營者傾向認為相比于組織效率,倫理和社會責任并不重要。Cheung等(2012)發現國家報紙發行量的大小與公司賄賂傾向或者官員的受賄傾向負相關。報紙發行量的大小代表媒體監督的力量,可以視作一國文化透明度和開放性的反映。
(二)影響商業賄賂的中觀因素
中觀因素指公司經營所處的行業狀態及業務關系等外在要素的集合。諸多研究都證實了公司所處行業的競爭激烈程度,作為一種外在壓力會增加公司行賄的傾向性(Martin等,2007;Chen等,2008;Lee等,2010;Cheung等,2012)。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公司行賄的對象組織所處行業市場競爭程度越高即壟斷程度越低時,公司行賄的傾向則是下降的。因為這意味著公司有更多的選擇余地和議價空間,所需資源的稀缺性及對其依賴性降低,不通過賄賂也可能獲取。如Clarke和Xu(2004)以21個東歐和中亞轉型經濟國家中公司向公用事業單位雇員行賄的數據,檢驗發現在公用設施服務能力有限、公用事業部門競爭水平低、且公共設施國家所有的國家,公用事業單位雇員更傾向索取和接受賄賂。Barth等(2009)證實了銀行業間的競爭和信息共享能夠有效減少貸款腐敗。而借款人產品市場的競爭增加了公司的違約風險,降低了其議價能力,從而導致更多的貸款賄賂。除了行業競爭,行業屬性也會影響到公司賄賂,不同行業的公司賄賂水平有顯著差異(Lee等,2010)。我國的情況亦是如此,商業賄賂高發于醫藥、建筑、房地產等行業。
(三)影響商業賄賂的微觀因素
微觀因素指公司自身的經濟特征和賄賂對象的個體特征。研究者選取某些公司特征測度公司的賄賂支付能力或者拒絕賄賂的議價能力,這兩種能力影響了公司行賄的決定以及賄金的多少。這些公司特征包括:
1.公司規模。公司規模與公司賄賂傾向負相關(Chen等,2008;Wu,2009;Lee等,2010)。這是因為由于資源所限,小公司拒絕賄賂的議價能力較弱,而且小公司內部控制不如大公司完善,對包括賄賂在內的商業腐敗行為防范不足。
2.公司年齡。公司成立時間越長,其擁有的資源越多,拒絕賄賂的能力也越強,因此公司年齡與賄賂傾向負相關(Clarke和Xu,2004;Lee等,2010)。
3.股權性質。當公司在向政府官員行賄時會經受股權性質的歧視。國家股、外資股比例越高,公司被索賄的機率越小,或者支付的賄金較少,而民營企業更可能被索賄且賄金支付較多(Clarke和Xu,2004;Barth等,2009;Lee等,2010)。這種差別對待也是基于不同股權性質的公司在賄賂議價方面擁有的政治資源和能力不同。
4.盈利能力。有研究發現公司的盈利能力與賄賂傾向和金額正相關(Svensson,2003;Clarke和Xu,2004),其內在邏輯為:一是公司較強的盈利能力表明有較強的賄賂支付能力,所以相對較愿意通過賄賂實現某種意圖。二是依據“內生的騷擾”理論,公司被索賄的金額與其自身支付能力正相關。也有研究發現公司業績與賄賂傾向及金額是負相關的(Chen等,2008;Cheung等,2012)。其原因可能是盈利能力也代表了公司拒絕行賄的能力,公司盈利能力強就有更多的資源采取法律行動,保護自己免受索賄的威脅。而盈利能力弱的公司可能通過賄賂改變困境的愿望更為迫切,因而在賄賂議價中處于不利地位。endprint
5.出口導向。Chen等(2008)發現產品出口的公司更可能支付賄賂,因為公司就出口事項與政府官員的接觸度高,被索賄的機率增大。然而Lee等(2010)驗證了產品出口越多的公司,越可能向政府官員支付較少的賄賂,其理由是出口型企業對于發展中國家和有結算支付問題的國家經濟而言是有重要貢獻的,官員就會抑制對這些企業的索賄企圖以避免受到政府的懲罰,政府間吸引出口型企業的競爭也會給這些公司更多的議價權力。這兩篇文章的主要數據來源都是世界銀行2000年的商業環境調查,但是截然相反的結論可能是二者對于出口型公司的度量方法不同造成的。
上述研究中就影響商業賄賂的微觀因素采用了常規的公司特征度量,使研究結論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這就啟示我們應改進研究的度量方法,提高其精確性和可靠性。有的學者就依據研究的具體問題,采用了其他變量來表征公司賄賂的議價能力。這些變量的選取原理基于正反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公司因業務關系與政府官員的接觸度越高,被索賄的機率越大,賄賂的議價能力越弱。Clarke和Xu(2004)、Azam等(2009)都證實公司對公共服務的依賴程度與賄賂傾向正相關。另一方面,如果除了賄賂公司別無選擇,則公司拒絕賄賂的議價能力就弱。譬如Svensson(2003)用不行賄的替代方案資本回報率度量公司拒絕賄賂的能力,替代方案的資本回報率較賄賂實現的回報率低的話,公司就會傾向行賄。Azam等(2009)以公司廠場設備的重置價值代表公司的沉沒成本表征公司拒絕賄賂的能力。原因是有較高沉沒成本的公司在面對官員騷擾時,不太愿意關閉、搬遷和在其他地方開展新業務,公司在賄賂議價中就處于不利地位。
賄賂涉及人員的個體特征同樣會影響賄賂傾向及金額,包括職權、性別、教育程度和社會關系等。Cheung等(2012)實證發現公司向更高級別、權力更大的政府官員支付了更多的賄金。Chi和Wang(2008)依據中國政府官員的腐敗信息,發現官員的級別和權力與賄賂收取金額正相關,而官員的受教育程度與賄賂收取金額負相關。性別影響方面,女性的行賄和受賄傾向都較少(Swamy等,2001;Kalaj,2015)。社會關系方面,以越南的公司為例,Jong等(2015)調查發現公司管理層與中央政府官員的私人關系減少了公司賄賂的傾向,而與地方政府的私人關系增加了賄賂的傾向。
四、公司商業賄賂的經濟后果
公司希望通過商業賄賂獲得一定的收益,有關經驗證據表明賄賂給公司帶來的經濟收益具有較強的條件依賴性,沒有確定的結論。公司賄賂是否能避免掠奪、提高效率,并無定論,與公司自身的規模和能力、所處的制度環境以及行賄對象都有關系。總體上,研究支持當公司位于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地區,公司從商業賄賂中得到的益處較大。
(一)賄賂給公司帶來的經濟收益
對賄賂帶來的經濟收益,研究中較多關注了公司生產率的變化。這是因為公司向官員行賄的目的之一是減少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干涉與掠奪,提高公司的經營效率。Kasuga(2011)使用柬埔寨服裝制造業的公司賄賂支付數據,驗證了公司的賄賂支付減少了行政服務中的官僚主義拖延作風從而提高了公司的生產率。然而Kaufman和Wei(1999)、Gaviria(2002)都發現公司的賄賂并沒有減少官員的干預,支付了較多賄賂的公司,花費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時間與官員協商監管問題。Cai等(2011)將中國公司的娛樂差旅費作為賄賂腐敗的度量,研究了它們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結果發現娛樂差旅費總體上對公司的生產率是負面影響,但當公司位于制度環境較差的地區,這種負面影響會大為減少,因為向政府行賄的費用有助于獲得政府幫助和減少稅負。除了生產率,另一反映賄賂經濟收益的綜合性指標是公司的增長率。Hellman等(2003)、李捷瑜和黃宇豐(2010)證明了在轉型經濟國家,公司賄賂可以促進企業增長。Fisman和Svensson(2007)卻發現賄賂支付的比率與公司銷售增長負相關,從而認為賄賂是政府官員的掠奪,對公司造成了損害。Zhou和Peng(2012)則強調了公司規模對賄賂與公司增長關系的調節作用,賄賂有損中小型企業的增長,但對大企業沒有負面影響。Mendoza等(2013)以菲律賓的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實證發現賄賂總體上對公司增長和業績是有害的,但當公司在商業環境較差的城市經營,過度受到官僚主義拖延作風影響時,賄賂對公司增長有積極作用。
也有研究對賄賂帶來經濟收益的測度采用了更為具體的指標。Cheung等(2012)基于手工收集的166個公司賄賂案例,關注通過賄賂獲得的合同在宣告日給公司帶來的市場回報,用公司市值的變化與賄賂支付金額的差值或比值度量賄賂給公司帶來的收益,考查了跨國貿易中行賄公司與受賄政府官員的所在國家特征、個體特征對公司賄賂取得收益的影響。結果發現:所在國家有較高的受托責任法律約束和較小的報刊發行量,經營業績好的公司,通過行賄獲取了較大的收益;公司在政治、經濟、司法都落后的國家向政府官員行賄獲得的益處較大;公司向較高級別的政府官員行賄并沒有帶來更多的收益,因為官員從公司通過賄賂獲取的合同抽租較高消減了公司的收益。Fan等(2008)也驗證了公司向官員行賄收益有限。他們以1995-2003年間中國高層政府官員與上市公司間的腐敗案例為對象,研究表明當公司通過賄賂與政府官員建立聯系后,公司在獲取銀行貸款特別是長期借款方面有相對競爭優勢。然而隨著問題官員被抓即聯系的中斷,公司的債務融資優勢隨之消失,且這些公司在賄賂事件曝光前的業績與其他公司沒有顯著差異,曝光后的業績顯著差于其他公司。
(二)賄賂使公司負擔的經濟成本
對于行賄的公司而言,賄賂的直接成本是金錢的支付和溝通時間的花費。賄金的支出還會推高公司的經營成本和資本成本(Kaufmann和Wei,1999;Wu,2009)。此外,賄賂還會使公司承擔很多間接的隱性成本。Wu(2005a)指出賄賂有如下隱性成本:首先,賄賂曝光會使公司面臨重大的法律和財務風險;第二,由于“內生的騷擾”,公司一旦打開腐敗之門,就很難再拒絕索賄方更多的要求;第三,賄賂最大的危害后果是侵蝕公司發展長期競爭優勢的動力。因為一旦公司經理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賄賂在商業競爭中獲勝而不需要提供更好的產品或服務時,他們就會忙于行賄而不是關注創新和更好的投資決策來發展公司的競爭優勢。Nichols(2012)對公司賄賂產生的成本也做了較為系統的歸納。除了提及賄賂可能使公司及個人面臨的法律責任及經濟處罰外,他還闡述了賄賂的關系成本,即賄賂對公司內外部關系的損害。就外部關系而言,賄賂行為使公司在客戶關系的建立與維持方面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在大多數國家民眾都厭惡腐敗,公司的賄賂行為曝光會影響公司形象,進而可能影響到公司的經營業績與融資渠道。另一方面,許多國際性或國家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都將卷入腐敗案件的公司列入黑名單,禁止與其簽訂合同或者合作項目。就內部關系而言,管理層的賄賂行為,向雇員釋放了“自利的不端行為是可接受的”信號,從而形成了一種不道德的氛圍,易引發雇員的不法行為。譬如公司的管理層經常鼓勵營銷人員給客戶單位的采購人員提供禮物以促進銷售,但是不允許公司的采購人員接受禮物,這種雙重標準就使公司形成了一種不誠實的氛圍(Badenhorst,1994)。筆者認為,賄賂對公司內部雇傭關系的損害還有其他負面影響。公司在賄賂丑聞曝光后往往會開除一些涉案雇員。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但會增加公司雇傭和培訓新人的成本。而且如果開除雇員被其他雇員解讀為公司是在找“替罪羊”以規避責任,那么就會引發雇員對自身的擔憂和對公司的忠誠度下降,無形中打擊公司雇員整體的工作積極性,影響到公司業績。根據中國首部反商業賄賂藍皮書(2015)的報告,葛蘭素史克自2013年被公安部門調查起,業務受到很大影響,一年內葛蘭素史克中國的員工離職比例超過50%,幾乎涉及所有的職能部門和事業部門,公司銷售跌入谷底。Kanu(2015)調查表明就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而言,賄賂是各種腐敗形式中對公司業績損害最大的。endprint
盡管公司賄賂可能招致多種成本,但這些成本究竟有多高,卻極少有相關的實證研究給出明確答案。Karpoff等(2014)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他們以1978-2013年間違反FCPA被美國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處罰的143家上市公司作為樣本,以賄賂換取的合同凈現值變化估計行賄處罰和聲譽損失的成本。結果發現因賄賂被起訴的公司成本取決于賄賂是否伴隨財務欺詐的指控。沒有財務欺詐的公司承擔相對較小的賄賂曝光成本,賄賂相關合同的事后凈現值雖有下降但仍然非負,有財務欺詐公司的賄賂相關合同事后凈現值顯著為負,而且有財務欺詐的公司在股價上的損失是只有行賄沒有財務欺詐公司股價損失的12倍。這就意味著賄賂行為的曝光沒有妨害到公司未來的經營或者盈利能力,公司的聲譽損失是由財務欺詐而不是賄賂引起的。Karpoff等(2014)的發現,讓我們對美國FCPA就商業賄賂的威懾作用有些失望,不過這也啟發我們對商業賄賂的治理需要增大公司的賄賂成本。
五、研究啟示
(一)關于理論研究
縱觀現有的商業賄賂研究,我們發現,首先當前研究較多關注了公司對政府官員的賄賂,公司與供應商、客戶公司之間的賄賂研究較為少見。因此在商業賄賂研究中通常將公司作為行賄者、官員作為受賄者分析他們的行為動因及其影響因素。行賄對象不同,應有不同的賄賂動因、金額及后果,今后可據此開展比較研究。其次,應動態研究公司的商業賄賂過程,縱向看,處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公司商業賄賂傾向是否有差異?就賄賂對公司的影響后果區分賄賂曝光前和曝光后的階段;橫向看,觀察特定公司商業賄賂行為的曝光對行業的影響。第三,關注商業賄賂案件中是否存在選擇性執法問題,如果有的話公司的一些微觀特征(如股權性質、公司規模等)是否與之相關,這些微觀特征又如何影響公司反商業賄賂的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媒體與公眾監督、會計信息質量等在公司商業賄賂發現及其后果影響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有待深入研究。最后,今后可更多考慮行賄者和受賄者的個人特征與公司賄賂之間的關系,譬如公司參與賄賂的雇員級別和人數,對公司賄賂結果的影響;賄賂曝光后,公司對參與賄賂的雇員處理方式是否會影響到公司以后的經營。
(二)關于實務監管
筆者認為,依據商業賄賂的動因和后果,治理商業賄賂的途徑有三種:一是嚴厲打擊,提高商業賄賂的違法成本;二是嚴格防范,抑制商業賄賂的誘發因素;三是道德教化,形成反賄賂的社會文化。最終的治理效果相應地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公司或個人有賄賂意圖,但是鑒于后果的嚴重性而不敢實行;中間層次是公司或個人有賄賂意圖,法律的威懾力不夠,但是嚴密的防范措施使賄賂不能實行;最高層次是公司或個人沒有賄賂意圖,對賄賂行為持否定或者厭惡態度。要達到最高層次的治理效果,使人們自覺自愿地抵制賄賂行為,顯然只依靠道德教化是不行的。鑒于人性的不完美,更有效的實現方式可能是通過打擊和防范增強后果的嚴重性,降低公司或個人從商業賄賂中獲取的收益,最終使商業賄賂對公司或個人而言得不償失,從而理性地主動放棄商業賄賂的企圖。而且長期有力的打擊和防范,可以將人們對商業賄賂的態度由“不敢”、“不能”固化為“不想”,習得性無助理論也為這種態度轉化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論支持。已有研究也大多從商業賄賂的動因和后果出發,探討了公司內外部的打擊和防范措施。公司外部的法律制度建設及會計準則規范(Kimbro,2002;Wu,2005b;Karpoff等,2014)、公司內外部的審計監督和公司內部的會計控制(丁友剛和胡興國,2008;Azam等,2009;Ryvkin和Serra,2012),是較為務實的治理措施。賄賂事件曝光后的公司通常都加強了內部的合規性控制。
中國作為轉型經濟國家,商業賄賂案件頻發,對商業賄賂的防范治理已刻不容緩。在商業賄賂的治理方面,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抓公司外部的法律監管。首要問題是立法,一是制定專門的反商業賄賂法案,改變當前有關商業賄賂的法律規定散見于各種法律規章司法解釋中的混亂局面。二是在法律規定中增加商業賄賂犯罪的法律責任和處罰金額,特別加大對企業高管個人責任的追究力度。在司法方面,要提高舉報的獎賞力度,有效保護舉報人,增加公眾參與和監督的積極性。此外要確保嚴格執法,國家審計監察機關需要特別關注執法機關和公司是否有合謀規避賄賂罪名及處罰的情形發生。除了外部的法律監管,就與公司賄賂傾向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我們需要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培育更加透明的市場經濟體系,實行公平競爭的經濟制度,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政治透明度和民主性,約束官員權力,反對官僚主義作風,持續深入地開展反腐敗斗爭;通過宣傳教育,糾正急功近利的短視現象,弘揚仁義道德的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全民思想道德素質,推動公司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企業從風險防控的角度看,也應在公司內部建立反商業賄賂的控制制度,保證公司合規經營。而且建立這一合規機制,也有助于節省賄賂成本,促使企業更健康發展。在控制點設置上,關注高風險領域(如采購、營銷、審批等)和高風險期(如公司業績不佳時)的監控。最后,公司還需開展大范圍、長期性的員工合規培訓,使合規觀念深入人心。
[參 考 文 獻]
[1] Nichols, P. M. The business case for complying with bribery laws [J]. 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2012, 49(2)
[2] 李捷瑜,黃宇豐. 轉型經濟中的賄賂與企業增長[J]. 經濟學(季刊), 2010, 9(4)
[3] Fisman, R. and J. Svensson.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 83 (1)endprint
[4] Zhou, J. Q. and M. W. Peng. Does bribery help or hurt firm growth around the world?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29 (4)
[5] Wu, X. Determinants of bribery in Asian firms: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7 (1)
[6] Kaufmann, D. and S. J. Wei. Does "grease money"speed up the wheels of commer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254
[7] Lee, S. H, O. Kyeungrae and L. Eden. Why do firms bribe? Insights from residual control theory into firms' exposure and vulnerability to corruption [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0, 50(6)
[8] Lambert-Mogiliansky, A. Why firms pay occasional bribes: The connection economy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8(1)
[9] Martin, K. D., J. B. Cullen, J. L. Johnson and K. P. Parboteeah. Deciding to bribe: A cross-level analysis of firm and home country influences on bribery ac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50(6)
[10] Cheung, Y. L., P. R. Rau and A. Stouraitis. How much do firms pay as bribes and what benefits do they get?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 worldwide. NBER, No. 17981, 2012
[11] Chen, Y., M. Yasar and R. M. Rejes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cidence of bribery payouts by firm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77(2)
[12] Barth, J. R., C. Lin, P. Lin and F. M. Song. Corruption in bank lending to firms: Cross-country micro evidence on the beneficial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1(3)
[13] Clarke, G. R. and L. C. Xu. Privatization, competition and corruption: How characteristics of bribe takers and payers affect bribe payments to utilitie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9-10)
[14] Svensson, J. Who must pay bribes and how much? Evidence from a cross-section of firm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 (1)
[15] Jong, G. D., P. A. Tu and H. V. Ees. The impact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bribery incid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cs [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15, 12(1)
[16] Fan, J. P. H, O. M. Rui and M. Zhao. Public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e: Evidence from corruption case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36 (3)
[17]Wu, X.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A cross-country analysis[J].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2005a, 18(2)endprint
[18] 法制日報-法制網.中國首部反商業賄賂藍皮書發布(全文)[EB/OL]. http://www.legaldaily.com.cn, 2015-01-10
[19] Kanu, A. M.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Perspectiv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015, 3(3)
[20] Karpoff, J. M., Lee, D. S. and Martin, G. S. The economics of foreign bribery: Evidence from FCPA enforcement action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4
[21] Kimbro, M. B.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cultural and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qualit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 Finance, 2002, 17(4)
[22] Wu, X. Firm accounting practices, accounting reform and corruption in Asia [J]. Policy and Society, 2005b, 24 (3)
[23] 丁友剛,胡興國.內部控制、契約秩序與法律要求——基于朗訊賄賂門事件及美國內部控制立法與司法實踐的思考[J]. 審計研究,2008 (4)
[24] Ryvkin, D. and Serra, D. How corruptible are you Bribery under uncertain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12, 81(2)
[責任編輯:王鳳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