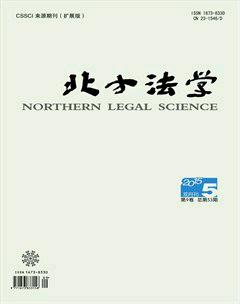清代“科道合一”得失之再認識
張世闖+程天權
摘要:清雍正年間的“科道合一”,是我國古代監察法制發展史上繼“臺諫合一”后的又一次重要變革。這一改制,使得六科給事中轉隸都察院,并于客觀事實上造成了我國古代監察法制中諫議制度的終結。通過對比“科道合一”前后六科給事中的權責變化,以歷史辯證法為分析進路,認為“科道合一”在鞏固皇權和穩定國家政權、實現監察機構和組織的規范化建設等方面發揮了應有的實效;然而,皇權專制下的“科道合一”更是加深了皇帝專權的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清中后期的官場腐敗。
關鍵詞:“科道合一” 監察法制六科給事中都察院
中圖分類號:DF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5)05-0132-07
諫議的思想和史實,自古有之,①迨至秦帝國建立以后逐漸得以制度化,變為由傳統職官體制內的專、兼職官員,通過各種形式②“匡正君主,諫諍得失”,以避免決策失誤,并促使君主改正自身錯誤。給事中制度是我國古代言諫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肇始于秦,權興于漢,以言諫封駁為主要職責。唐代為給事中制度的成熟期,其權力范圍涵蓋封駁、人事審查和部分司法等方面。③宋代給事中“掌規諫諷喻”,“分治六房”。④給事中分治六房,為明代六科給事中分科理事的制度本源。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裁諫官,“唯設六科給事中以監察六部及百官”。⑤此時,六科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⑥的法定權責及制度設置基本為后世清代所承襲。清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將給事中歸屬于都察院,至此,“科道合一”的監察體系形成,給事中的權屬職掌、效能實現由牽制皇權退居到了監察百官。
諫議制度與御史制度共同組成了中國的傳統監察法制體系。⑦“諫官司言,御史司察”,是二者基本分工的不同,但就服務皇權、保障傳統帝制時期官僚制度正常運轉、自身組織和職權規范化建設以及所起的效用等方面卻是殊途同歸的。近些年來,學者在對清代六科給事中制度與皇權建設關系方面的研究,主要著眼于中央集權下言諫系統崩潰的消極意義,即其在制約皇權方面效能的喪失,而于傳統法制視閾下權力變化的角度對“科道合一”的歷史原因、歷史價值分析不足或者著墨較少。⑧本文擬通過這一視角,從得失兩個維度重點分析“科道合一”前后,六科給事中的權責在影響皇帝決策和監察百官方面的異同,評論該制度存在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復制與借鑒:“科道合一”前六科給事中的權責
入關之初,清代職官和法制建設的基本國策就是借鑒、效法朱明王朝。清前期的六部建設,⑨以及為了牽制六部、強化中央集權的六科給事中制度也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得以成型的。⑩然而,這一時期仿行明制建立起來的給事中制度,由于缺乏進一步的完善和相應的配套機制,無論是制度建設本身還是制度要達到的效用,都不及明代六科給事中的品相,而純屬為了形式上管理的方便。入關以后,在 “參漢酌金”思想的進一步推動下,清代六科給事中制度的設計也開始融入到了職官建置體系當中。“六科自為一署,給事中無員限,并置漢軍副理事官。”此時,六科給事中雖為獨立的監察機關,鑄有印信,然而在人員編制方面并無明確的數額規定。迨至順治十八年(1661年),定每科滿、漢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各一人,漢給事中二人。康熙三年(1664年),由于六科人員削減,各科僅留滿、漢給事中各一人。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以給事中“廷議紛囂”“恣意自肆”為由,“詔以六科隸屬都察院,聽都御史臺考核”。至此,“科道合一”的監察體系形成,皇權集權達到鼎盛。
在主要權能方面,清代六科給事中完全復制了明代六科給事中的規定,以言諫和封駁權為主要內容;在權能行使方面,“凡制敕宣行,大事復奏,小事署而頒之。如有失,封還執奏。內外章疏,分類抄集,參署付部,駁正其違誤焉”。此時六科給事中的權責,在承襲明代職掌的基礎上,同都察院的職能有部分共通的地方,已不再是獨立的專司言諫的監察機構。為了方便研究“科道合一”前后六科給事中權能的變化,此處略去其與都察院相重疊的領域,重點分析那些對皇權約束和監察網絡建設有深刻影響的部分。
首先,在約束皇權方面。第一,論言諫議。科道官員,“所言公,則國家受其益;所言私,則國家受其害”。言諫職能,是給事中的本職,在其設置之初就肩負著“拾遺補缺”,匡正帝王不當言行的使命。清初,統治者對于言官的諫議較為重視。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諭:“國家設立都御史、科道官,以建白為專責,所以達下情而去壅蔽,職位至重”。為了確保言諫官員能夠恭秉圣意、正確履職,康熙帝又針對言諫職責的范圍和貞潔操守,作了正反兩個方面的訓諭。“國家設立言官,專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須詳切條陳,直言無隱,斯為稱職。若但敷衍虛文,浮冗剿襲,或以不急之務,草率塞責,非朕廣開言路之意”。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廣開言路,積極求言納諫,指示九卿、科道、詹事,“凡朕所行之事,或有過失,務盡言無隱。即所行無過,或更有應行事宜,亦各據已見陳奏,使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方得古大臣責難于君之義”。第二,封駁奏章。順治初年規定:“凡部院督撫本章,已經奉旨,如確有未便施行之處,許該科封還執奏。如內閣票簽批本錯誤,及部院督撫本內事未協,并聽駁正。”即封駁的對象包括臣下的奏章,以及皇帝的失誤詔令。盡管這里權力行使的對象包含臣工奏對,但實質仍體現在制約皇權的方面。
其次,在監察官員方面。第一,掌科抄。“科抄”是指各科給事中每日赴內閣接抄紅本,然后再按照不同的內容分給六部各相關衙門承辦。“科抄”的意義在于“封駁”權的行使。“科抄”又有正外抄之分:抄給承辦衙門的為“正抄”;抄給其他關系衙門的為“外抄”。第二,掌注銷部院文卷,稽察六部大小衙門工作。順治十八年(1661年)規定,各部院事務,無論奉旨與否、有科抄否,六科各差一員隨時稽查,發現有遷延怠期的,即行參奏。以上兩個權責,可以說是六科給事中區別于都察院系統監察官監督百官的獨特工作方式,且六科又由于自身所屬部門不同,各司其職,互不交叉。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發現,清初六科給事中的權能在制度規范和事實運作層面,主要仍舊以諫議為行為風格和監督范式,企圖弱化皇權,以達到制約皇帝恣意妄為的目的。然而,如此衡平君臣關系或是試圖實現民主決策的美好愿景,受制于傳統禮法結構下的政治形態,隨著雍正朝的改制,逐漸蛻變為強化皇權專制的傀儡。
二、削減與增加:“科道合一”后六科給事中的權責變化
清初的監察體系沿襲了明代的格局,都察院與六科并立,分別為獨立的監察機構,兩者互不隸屬。然而,從雍正朝開始,為了避免監察機構重疊,影響監察效果,同時也為了消除給事中封駁制度與皇帝集權的沖突,避免明末六科給事中“以無所隸屬,蓋得恣情自肆”,加劇朝政的混亂,通過內升外轉,將六科隸屬于都察院。“凡城、倉、漕、鹽與御史并差,自是臺省合二為一”。“臺省合一”,又稱“科道合一”,六科給事中在組織機構、人員歸屬、所司職的監察權能等方面統歸到都察院的監察體制當中。檢索清代的相關文獻,“科道合一”后,在監察法制建設方面,六科給事中權責的得失變化,至少可以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言諫權”的消亡。給事中“掌顧問應對”,初以言諫“有事殿中”,是我國古代監察法制中言諫系統下的職官,其最初始的權力就是言諫皇帝。秦代一方面皇帝專橫,另一方面宦官擅權,“忠臣不敢諫”,給事中制度也就形同虛設。漢初統治者為征集治國良策,消除前朝弊端,多次諭令“廣招直言極諫之士”。以后各代直至宋神宗改制,設立了專門職掌納諫的諫院,給事中的言諫權能才有所弱化。明太祖朱元璋分給事中為六科遣送六部以后,六科給事中的言諫職能更是進一步喪失。是故,有學者言,明代六科給事中“無面折廷諍之威風,由言諫之職,漸變為糾察之官,……決不足以言諫天子,糾朝廷也”。然而,從現有能搜集到的材料看,明代六科給事中尚能按照“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的規定直言面諫皇帝,尤以明思宗崇禎年間,六科給事中的言諫活動遠遠高于御史。清朝初年,順治帝訓諭百官,“朝廷設言官,原為繩衍糾謬,事關朕身尚許直言無隱藏”,鼓勵給事中直言善諫,提醒皇帝的失儀之舉。隨著“科道合一”和皇權專制程度的提升,“六科身處朝廷,但不能與都察院御史出巡地方,卻要求與各道御史一樣據實陳奏,也就限制了其言事的作用”。所謂“言諫”,形式層面的意義遠遠大于其實質內容,也逐步淪為皇帝專政和吏治的工具。
第二,“封駁權”名存實亡。封駁權本是給事中最基本、最獨享的職權,其內容涵蓋“封”“駁”兩項。一般來說,“封”權行使的對象是皇帝的詔令;“駁”權則針對臣下的失誤奏章。封駁制度完備于唐代,并對封駁的對象作了明確的規定。及至宋代,給事中下設“封駁司”,專司封駁。明初朱元璋諭令給事中積極行使封駁權,以指出皇帝詔令的違誤。此時給事中已下六部,其在行使封還皇帝詔令的職權時并不順暢,但其駁正臣下章奏和擬定“科參”的權力卻日益隆盛。清代自雍正始,一方面六科給事中歸屬都察院,其于封駁方面的職權喪失了皇權的支持,實際上行使的只有風憲奏事的監察權;另一方面,“今事或由廷寄,或由閣抄,其下科者,皆系循例奏報,無所用其參駁”。南書房和軍機處職權的擴充,以及“廷寄”(不經內閣明發,而由軍機大臣以書信的形式秘密發送有關人員或部門)、“密折”等制度的形成,使得六科給事中的封駁缺失了適用的條件,無法得以實現。乾隆年間,給事中曹一士上疏恢復給事中舊制,特提封駁狀況一事,也是明證。可以說,“科道合一”以后,六科給事中言諫權和封駁權的消亡,使得“中國古代監察制度諫君和糾官的兩種職能實際上已變為一種職能,即糾舉百官”,同時也宣告了我國古代傳統監察法體系內言諫制度的終結。
第三,組織結構更加規范。在品秩方面,“初制,滿員四品,漢員七品。康熙二年改滿員七品,六年復為四品。九年俱定七品”。雍正元年(1723年),內升外轉,歸屬都察院考核,組織上獨立性消失的同時品級并沒有立升,而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方“升正五品”。此時的六科給事中,一方面在職權行使上從專司言官轉為與各監察道一并監督百官;另一方面品秩的提升,使得其與各道職級平等(雍正七年官制改革,“十五道掌印監察御史……雍正七年,改由編、檢、郎員授者正五品”), 在規范組織管理的同時更利于方便察官。在人員編制方面,清初給事中無定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定每科滿、漢給事中,左右給事中各一人,漢給事中二人。康熙三年(1664年),由于六科人員削減,各科僅留滿、漢給事中各一人。五年(1666年),改都給事中為掌印給事中。雍正元年(1723年)并入都察院。乾隆二年(1737年)又裁六科筆帖式二十七人,余八十人。光緒三十二年,復裁六科名稱,改為都察院給事中,設給事中二十人,筆帖式三十人。這樣來,一方面避免了人員的臃腫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保證了六科的質量和所要實現的監察效果,更加吻合了“科道合一”制度設計的初衷。
第四,監察體系日益完備。清代中央的監察機關,除都察院為領導機構外,具體的職能部門為六科、十五道、五城察院、宗室御史處、稽查內務府御史處和理藩院、軍機處稽察御史,其中又以科道權職最重,所監范圍最廣,遠超宋元明三代。“科道合一”使六科給事中言諫權和封駁權歸于虛無的同時,加強了中央監察網絡建設,“由都察院統一管束和轄制六科,避免了監察系統重疊,相互傾陷造成的矛盾,遇有重大稽察事件,往往科道并用,共同負責,互相稽察,提高了監察效率”。首先,獨立監察六部的權能得以提升。“科道合一”后,六科組織上隸屬都察院,而其稽察六部、注銷文卷的職權行使卻在六部衙門。這種監督模式的設計,類似于當前的監察派駐機構,一方面能夠保證六科給事中獨立行使職權;另一方面又熟知自己的監管對象,進而提高監管的效能。其次,科道共職規范了監察程序、增強了監察力度。十五道與六科一樣,除了自身專有的監察權能外,還有一些共同職掌,使監察網絡更加縝密。全方位的監察網絡,促進了皇權的專制,同時在吏治整頓、預防腐敗方面發揮了較高的效用。最后,加強了科道互察、形成了接受行政機構監督的權力制衡機制。乾隆朝出臺的《欽定臺規》對科道互察的程序和內容設置了專款專條予以規制、調整。同時,來自行政機關的橫向監督,也起到了防范監察權濫用的功效。如乾隆三年(1738年),刑部侍郎劉統勛“疏劾丁憂御史毛之玉赴浙謁總督、藩司,受饋遺。上嘉公直,之玉嚴議”。“科道合一”后,賦予了被監察者監督監察者行使監察權力的部分權能,這也為防范監察官腐敗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得與失:“科道合一”之評價
秦漢之際,“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以皇帝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制得以形成和鞏固。其后歷代各朝,均是在此基礎上通過各種制度建置、權謀策略不斷地強化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可以說,自秦漢以來,傳統政權結構的發展就是一個皇權不斷強化而制約、監督皇權的機制不斷萎縮的過程。這一目標的達成,緩慢而又跌宕起伏,主要原因在于傳統諫議文化和制度的存在,制約了皇權的“恣意妄為”。然而,清雍正朝的“科道合一” 實際上是雍正帝在適宜的歷史條件下為強化皇權專制和中央集權做出的必然改制,這猶如平靜的湖面激起的浪花一般,看似偶然,實則是量變到質變的客觀反映。
“我們評價一個制度無論如何都不能以個別事件的實質性對錯為標準,而要做出總體上的利害權衡,而這種權衡是公眾在歷史中進行的”。任何一項制度在其形成過程中,彼時的社會政治狀況和所面臨的現狀問題,是其在邏輯建構中必須予以考慮的要素。當我們以后來者的眼光去評析“科道合一”制度的得失時,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是最好的研究進路。基于這一思路,筆者將“科道合一”之于清王朝政治法律的得失影響,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鞏固和強化了清王朝的“部族政權”,加深了中央集權統治的力度。清王朝,相對于其所取代的朱明王朝而言,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王朝的形成是基于外族勢力對“漢家天下”的繼受。公元1644年隨同滿族八旗一同入關的還有蒙古八旗以及東北亞的部族,因此,愛新覺羅氏族對清王朝統治權的行使,離不開蒙古族群和其他部族的共同支撐與扶持。然而,服務和供養這種“部族政權”的土壤卻是以“華夷之辨”為精神立足點的漢士大夫文化。鑒于兩種意識形態的迥然差異,以及治國理政、穩定政權的需要,清王朝初期的統治者們設計出了“參漢酌金”的治國方針,開始了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漢化”事務。清王朝的“科道合一”制度之生成,也只不過是清朝統治者在致力于“漢化”和族群自我認同過程中的實現方式之一而已。六科給事中本是明代監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諫議”為主要職掌,清朝初期予以承襲,同時也以“規諫”“封駁”為主要權責。然而,雍正元年(1723年)“內升外轉”,六科給事中隸屬都察院考核,征表了“漢化”在部族認同中的失敗。究其原因,漢文化中“面刺寡人之過”的言諫之風,在清王朝的部族意識內找不到自身的理論根基和文化土壤。諫議權能的弱化和消失,使得以皇帝為代表的部族政權在進行發布命令、制定法律、行政決策等國家治理活動中,由于缺失相應的制約和監督因素,進而能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對國家、官僚的統治,同時為部族政權的穩固和中央集權的強化掃清障礙。沒有了言諫官員的“廷議紛囂”、“恣意自肆”,初生的外族政權不僅實現了雍正朝的順利改制,而且為自身的權力集中和長久存續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因而,單就在漢文化的土壤里實現外族(部族)政權良好建設而言,“科道合一”是具備進步性歷史意義的。
第二,規范完善了監察秩序,使得監察效率得以提升、監察網絡日益嚴密。首先,雍正元年(1723年)的科道改革,除了基于皇帝集權的考慮外,更大程度上還歸因于順康朝存在的科道權責交叉、互相推諉等積弊,從某種意義上講,“科道合一”是針對問題做出的符合發展要求的對策性改制,“將六科置于都察院之下,使科道兩途完全統一,解決了二者長期內耗的弊端”,并在客觀上對理清和明晰科道權責、修整現行的監察制度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次,“科道合一”,雖使六科的職權被削弱,卻增加了都察院的權力,擴大了它的監控范圍,進而使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的監察機構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六科和十五道并差,共同負責對中央和地方百官的監督,職權范圍共通、稽察信息共享,無論是察官的力度還是察官方式,均較前期有所加強與完善。
第三,皇帝“乾綱獨斷”,君主專制政權發展到了頂峰,同時傳統監察體制內的 “諫議”制度被破壞殆盡,皇權不受規制和監督,滋生了官場上新的、更為嚴重的腐敗。給事中屬于言諫監察系統,對維系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減少政治決策的失誤起著重要的監控作用,也可以說是傳統專制主義政治體制內部的自我調節器。然而,自宋歷明至清,給事中對君主的諫諍特權日益被剝奪,君主只注重自上而下對臣屬的監察,而不能容忍諫官對自己的束縛。皇帝的言行缺乏了相應的監督制約機制,就容易導致皇權高度專制集中。清朝監察體制內的“科道合一”促使了清朝專制主義的極端發展,同時又醞釀和產生于專制主義極端發展的過程中。在專制政治體制中,唯一可以對皇帝實行規諫和駁正的機關就此消失。所以當世宗將六科改并都察院時,不少科臣提出了異議。然而,此次規諫卻觸怒了世宗,而“立詔詰之”。由是,六科改隸都察院,“封駁”權隨之被完全否定、取消,皇帝的詔令也就不受任何阻礙,一切都可以“乾綱獨攬”了。同時,“給事中本以稽察六部、審駁注銷為職,臺諫合一后,將御史外出察巡之事,亦遣給事中分任,致使內外奔走、兼顧難周,對于重要章奏,未能詳細審讀,即行付部,以致判署紛紜,輕重倒置”。諫官系統職能的下降與消失,成為清代政治腐敗的因素之一。皇帝的言行缺乏相應的規諫、君主專權和察官的力度又空前強大、諫官行使言諫權的制度機制不復存在加上大興“文字獄”等情況,以致官員只能為了自身的切實利益,迎合皇帝需求做出相應的稽核行為,真正直言進諫、敢“逆龍鱗”的作為已然沒有了存活的空間。相反,一些投合皇帝喜愛、奉迎圣意的官員和行為,倒有了強有力的制度支撐和市場需要。因此,乾隆朝的“大蛀蟲”和珅,以及康乾盛世后官場大腐敗等現象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結語
清代“科道合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古代監察法制體系建設的基本走向,即對皇權制約程度的弱化甚至消亡,而對中央和地方百官的監察卻日益加強和突出。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和傳統禮法結構下皇權高度專制的發展需要密不可分的。當我們從價值評判的角度去審視這一史實時,要結合當時的歷史意義和之后的歷史教訓來辯證地分析。可以說,“科道合一”制度的生成有其歷史必然性,并實際上對鞏固皇權和穩定國家政權、實現監察機構和組織的規范化建設發揮了應有的實效,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然而,在傳統帝制時期的禮法政治結構下,一方面皇帝個人集國家的最高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大權于一身;另一方面皇帝又是禮制架構內百官臣僚的“君父”,其個人的好惡,影響和決定著帝國臣民的生存與發展,即使貴為“天子”,也難免決策的失誤。因此,自秦迄清,諫議制度往往是歷代監察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其隨著皇權專制的加強而逐漸弱化。清代“科道合一”后,諫議制度的名存實亡,更使得皇帝的言行不受監督,“君主權力的高度集中與行政監察權力的運用之間不可能真正相互制約”,皇帝專權也日益膨脹,隨之而來又出現了康乾盛世后大面積的官場腐敗現象。“科道合一”后,作為制約和監督皇權的“中間實體”的破壞造成的重點權力監督闕如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在制度建設過程中予以思考和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