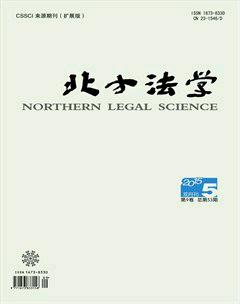英國法傳統中信托受益權的性質
吳至誠
摘要:源自英國法的信托受益權在本質上是一種對人權、債權,而非對世權、物權。從傳統角度看,在中國學界普遍存在的雙重所有權理論、分割所有權理論均是對信托制度的誤讀。信托受益權的物權化也是一個偽命題:無論從破產與執行豁免,所有權基本要素的分離,抑或財產取得權的角度均無法得出此結論。在英國法中,受益權不具備作為物權的普遍可訴性,不能直接對抗任意第三人;衡平法在歷史上并未改變英國財產法體系或帶來一套新的關于財產權取得和保有的規則;受益權也并不是通過對所有權要素的保留和分離而被創設,它只是一個加于所有權上的對人負擔。
關鍵詞:信托受益權雙重所有權分割所有權物權說債權說
中圖分類號:DF43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5)05-0150-11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信托受益人(cestui que trust)對信托財產享有的受益權(beneficial interest)之性質,中國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一方面沒有明確信托財產的歸屬(第2條),另一方面又突破信托法傳統給予委托人以大量權利(第20條至第23條)。立法上的這一模糊態度使得理論上對于信托受益權性質之爭論愈發混亂。物權說、債權說、物權債權并存說、特殊權利說等觀點,一時間讓人眼花繚亂。①要消除這種混亂的狀態,在理論上正本清源,最好的方法莫過于直接切入信托制度的起源來進行考察。作為一個產生于英國普通法傳統的獨特制度,②“信托受益權的性質在英國法中到底如何”是我們討論包括“信托受益權在中國法中的性質應當如何”在內的其他衍生問題的前提。然而對于英國法中受益權的性質,中國學界存在著廣泛的誤讀。
有學者認為“雙重所有權(dual ownership)”學說是英國的通說,即在根據信托目的將一定的財產轉移給受托人時,信托財產在歸屬于受托人的同時也歸屬于受益人。③也有學者將受托人的權利(legal title)翻譯為名義所有權,將受益人的權利(equitable title)翻譯為實質所有權即衡平所有權,進而得出“信托與大陸法系民法所建立之所有權絕對原則及一物一權主義迥不相同無法調和”的觀點。④另有學者認為從大陸法系的視角,難以解釋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相分離的雙重所有權現象。⑤還有學者進一步用歷史發展的產物(即所謂的“英美法歷史上普通法與衡平法長期對峙”)以及英美法從來沒有發展出絕對、單一所有權觀念和制度的這些事實來解釋所謂“信托財產所有權的分割性(split ownership)”在英國法中的存在。⑥與此同時,盡管有學者已經意識到受益人的權利是否應該在大陸法系國家被解釋為所有權是有爭議的,但并未深入討論下去,而是轉過來堅持了分割所有權的觀點,并認為信托的這種雙重所有權是其獨有的特點;聲稱如果沒有這種所有權分割的情況,信托本身的許多功能就無法發揮等等。⑦
中國信托法學界的誤讀一方面導致我國傳統私法學者為此普遍產生“信托與物權法不兼容”的觀點,進而不認為信托在學科歸屬問題上可以被納入民法體系。這意味著它只能被單獨放置于商法部門之中,使我國信托法實質上成為了商事信托法。另一方面,這種誤讀也影響了我國信托法的立法進程。全國人大法工委在解釋信托法立法背景時曾指出,英美法系國家的財產法更注重物的支配,大陸法系國家注重物的歸屬,因此,英美法信托和一般的財產契約在本質上有本質不同:即前者“擴充了”物權的內容,信托財產在實質上應歸屬于委托人或受益人,⑧這是因為“英美法系國家對信托財產的基本理論是:信托財產的所有權具有雙重性,也就是一個財產可以有兩個所有權……這種理論在我國難以接受。”⑨這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另外,我國《信托法》中飽受爭議的第2條之所以回避了信托設立時所有權轉移的要件,其原因之一也是當時立法者對英美法系信托法的誤讀,他們誤以為所謂的“普通法系模式”中的受益人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權”與受托人的“普通法上的所有權”形成了“一物二權”,這違背了大陸法系的一物一權原則,進而得出了“我國在信托立法時對于所有權的歸屬問題最好避而不談”的結論。⑩
筆者試圖通過對英國法學說判例的系統梳理來糾正存在于我國學界的兩個基本誤讀,并分別論證:信托受益權雖然看似具有一些不符合人權概念的特征,但其在英國法上仍然屬于債權而非財產權(物權);所謂的分割所有權(或雙重所有權)理論是對英國信托本質的一種完全錯誤的解釋,信托制度的存在并未改變財產法的基本結構和原則。
二、英國法上信托受益權的債權本質
在英國法的權利體系中,信托受益權一直就是作為一種債權而非物權存在,這可以通過對信托受益權的權利性質以及其在英國法歷史傳統中的演化的考察來加以說明,透過這一考察,我們認識到在英國信托制度中沒有分割所有權、雙重所有權理論存在的空間。
(一) 普遍可訴性的缺失
在英美法傳統上,普遍可訴性(universal exigibility)是區分對物權(right in rem)和對人權(right in personam)的核心標準。
所謂普遍可訴性,即指權利人可以直接起訴任何不法侵犯該權利的他人,并請求其停止侵害、回復原狀或賠償損失的能力。根據霍菲爾德的法律相關關系(jural correlatives)模型,任何權利都是對人的,不存在“針對某物”的權利:所謂對物權也只是一人向另一人主張的、與某物有特定聯系的權利。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物權和對人權沒有區別:從義務人數量的角度,對人權是一個權利枝、單數權利(paucital right),連接權利人與特定的一個(或幾個)相對人;對物權則是一個權利束、復數權利(multital right),連接權利人和不特定的多數人。此說大體代表了英美法學界在理論層面區分物權債權的主流標準。
普遍可訴性的意義在于其可被用作判定一種權利性質的標尺。界定一個被新創設出來的權利是物權還是債權,需要看這個新權利的持有人有沒有普遍可訴能力。眾所周知,無論是在大陸法系中的所有權人創設出一個抵押權、質權、地役權、地上權或是永佃權,或者是在英美法系中的永久產權人(fee simple absolute in possession)創設出一個終生產業(life estate)或是租權(lease),由于此新生權利的權利人B均可以對抗(直接起訴)任何侵犯或妨害其保有該他物權的第三人X而無需借助自物權人A的幫助,所以這些由所有權人分割出的權利具備普遍可訴性的特征,是他物權而非僅僅是一般的對人權。與此相對,所有權人所創設出的權利也可能僅僅是一個債權,比如英美法中的許可或者大陸法中的租賃就不具有普遍可訴性,因而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對人權。
但是用這一標準衡量信托受益權時,問題就出現了。根據英國判例法的解釋和學者的概括:當第三人X侵犯了作為所有權人的受托人A的物權,進而間接侵犯了A的受益人B的信托受益權,抑或是第三人X直接侵犯了受益人B的信托受益權時,因為X只對A負有不侵犯的義務并違反了這項義務,而X對B并不負有此項義務,所以只有A有權利起訴X。同樣因X的侵權行為而利益受損的B不可以直接向X主張權利,他只能借助其受托人A的幫助代為向X主張權利。誠然,歷史上受益人B可以向衡平法庭申請一項法律救濟(relief),責令A必須為了B的利益起訴X,然而正如Smith教授指出的,B的這項能力就好比合同第三人丙侵犯合同一方當事人乙的合同標的物從而間接侵犯到合同當事人甲的利益(third party interference with obligations)。即使丙不構成法定的第三人侵害債權,甲作為債權人依然有權利請求乙為了甲的合同利益向丙起訴——只是這與物權無關,甲并不會因為有了對乙的影響力就被認為有了針對該合同項下財產的所有權;同理,B也不會因為衡平法給了他一個對A的影響力就被認為有了信托財產上的財產權。這也是McFarlane教授指出的用所謂“衡平法上的財產權(equitable property right)”來表述信托受益權的本質是一種很不準確的說法的原因。總而言之,信托受益權無論在英國普通法上還是衡平法上均不具備普遍可訴性,受益人不能直接對抗第三人對信托財產的侵擾,而必須借助作為所有權人的受托人為其行使。因此,信托受益權本質上應屬債權,而非被分割出的新物權。
(二) 衡平法并沒有創設新物權
雙重所有權理論的歷史基礎在于:基于衡平法傳統,存在一種區別于普通法所有權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權。要反駁該理論,必須從普通法與衡平法的關系入手,探討衡平法是否真正創設了一種新的物權類型?
英國《1873年司法法》第25條規定:“大體上就所有上面未作特別規定的問題,如果它可適用的普通法規則和衡平法規則存在沖突或差異,衡平法規則優先。”梅特蘭指出,大家理解這個規則的難點在于衡平法與普通法“沖突”的存在與否:有些看似沖突的地方其實沒有沖突,信托正是這樣的一個例子。用歸謬法可以發現,沿著雙重所有權的思路:一方面,受托人可以根據普通法主張所有權人是自己而非受益人,因為普通法只規定受托人是法律上的所有權人;另一方面,受益人可以根據衡平法主張自己是所有權人而受托人不是,因為衡平法規定了受益人是實質上的所有者。進而在1873年之后,根據司法法第25條的規定,因為受托人和受益人分別根據普通法和衡平法主張了同一個權利(所有權),那么邏輯上的結果就是衡平法規則優先——這意味著普通法關于受托人享有所有權的規則將作廢——可事實上普通法關于受托人取得所有權的規則從未被作廢過:不管是受托人通過受讓委托人的財產而取得信托財產的所有權,抑或是委托人聲明自己成為受托人而保有信托財產的所有權。對于該條的實證分析說明了關于所有權的歸屬問題,衡平法從來就沒有與普通法出現過不一致或制造過沖突,司法法也從來沒有廢除普通法上關于信托受托人所有權的規則。這就是梅特蘭為何一再強調“衡平法從來沒有說過受益人是土地的所有權人,它是說受托人是土地的所有權人,只是該受托人被一項義務所束縛,即必須以維護受益人利益的方式持有這塊土地”。 正如他的經典名言所概括的,“衡平法從未去破壞普通法,而是在完善它。”落實到信托法中,恰如澳大利亞Brennan大法官在DKLR上訴案中所概括的那樣,“盡管受益人的權利構成一個衡平法上的權利,它只是被雕刻并鑲嵌在了普通法權益之上,而非是從普通法權益中被切割并分離出來的。”易言之,英國法中的受益權只是作為一項新的對人負擔,由衡平法放置在作為所有權人的受托人頭頂。
(三) 信托受益權的創設方式與時點
第三個論點來自于對信托受益權的創設方式和產生時點的探索。對信托受益權的財產權解讀和分割所有權解讀都違背了“任何人不能給予他人自己沒有的財產權”的原則。對于財產的繼受取得而言,一項財產權,無論是它的最高級別所有權抑或是低級財產權(他物權),均最終來自于原初的所有權。創設出這項財產權的方式本質上無非有兩種:第一,切割出所有權中的一部分權能,或稱要素(incidents),以建構出受讓人的一項或數項他物權;第二,切割出所有權中全部要素,并將全部這些權能轉移給受讓人以成就對方的自物權。無論如何,要適用這種分割所有權的模型,受讓人所得到的必須是在轉讓行為發生之前出讓人已然擁有的。顯然不僅自物權的讓渡可以這樣解釋,他物權的產生也可以這樣解釋:比如地上權就是從所有權中分割出了管理和收益的權能,地役權分割出了部分的使用權能,抵押權分割出了處分權能,留置權則分割出了占有權能等等。
但這個模型到了信托領域就不能適用了,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事先存在的、為所有權人所擁有的、且可以代表信托受益權的權能或者要素。英國兩個古老的判決早早確立了如下規則:一個永久產權人(fee simple owner)在一開始并不是同時享有普通法上的財產權和衡平法上的財產權,他只有普通法上的財產權,且該財產權承載著全部的權能和要素。正如Hope法官說的那樣,以明示信托(express trust)為例,當一個受托人由于委托人(settlor)的意愿而被指定之后,無論是通過財產轉移的方式還是聲明信托的方式,該受益人的衡平法上的受益權并沒有切割出任何事先存在的要素,完全是以一個全新出現的負擔的形式加在了普通法所有權(legal title)的頂部。據此,在創設明示信托的過程中,根本不存在一個可以被衡平法從普通法所有權中“分割”出來以供受益人持有的要素。
事實上,分割所有權模型的邏輯矛盾不僅存在于上述基于合意創設的信托,非基于合意創設的信托也不例外。Upjohn大法官在介紹自動的歸復信托(automatic resulting trust)的原理時曾說道,如果一個人自愿讓渡出其物上所有的權能,但是由于法律的原因導致此處分行為無效或者部分無效,那么其中的受益權將根據法律的擬制而“保留”在他的手中。易言之,推定信托的法理基礎在他看來是出讓人對自身衡平法上權利的保留。Wilberforce大法官雖然也同意了在該案中適用他的這種直白解釋,但另一方面也承認了這種解釋并不嚴謹,忽視了使用更為精煉的理性化術語。至于究竟何為歸復信托中的理性化的術語,Browne-Wilkinson大法官在另一著名案件中指出,一個完全的永久產權人從一開始就不享有衡平法上的財產權,是他手上唯一的、普通法上的財產權承載著物的全部權能和要素。“除非存在著普通法和衡平法財產權能和要素的‘分離,不然不可能存在著衡平法財產權的分割,進而‘保留衡平法財產權的說法也就是沒有意義的了……我們真正要考慮的問題是該案的轉讓行為是否足以構成一個法律上的信托,若是,則受益權從這個(歸復)信托出現的那一瞬間起首次問世。”而McLelland法官指出,事實上這種“分離(separation)”的說法(即認為財產權可以被分成普通法上的財產權和衡平法上的財產權)同上面“保留”的說法一樣不嚴謹。他指出,信托的本質不是由衡平法上的權利承載著一部分的權能和要素,而是物的全部要素只由受托人在普通法上的所有權所全部承載,信托只是讓受托人負擔了一個對受益人的為其利益并依據信托條款而妥善管理信托財產的義務。“就算受益人對應的權利可以被看成某種財產性權益,但這也不是從普通法所有權中剝離出來,而是新鑲嵌上去的”。綜合二位法官的觀點,我們可以知道將推定信托的本質解釋為“衡平法上權利的保留”也是錯誤的。
這種觀點也能得到來自制定法的支持。《1925年財產法》(Law of Property Act 1925)第53條第1款b項規定:“任何針對土地權益的聲明信托(declaration of trust)必須有書面文件作為佐證,且須有聲明人的簽名。”此項意為:聲明信托并非一定要通過書面形式才算有效成立,而是只需要有事后的書面證據證明其存在即可。本條同款c項規定:“任何對已存在的衡平利益的處分,必須以書面形式做出,且須有聲明人的簽名。”此項意為:針對已存在的信托受益權的處分必須要通過書面形式。如果我們沿著分割所有權的邏輯,即信托受益權是從所有權中剝離出的一部分,那么受益權就是一項“已存在”的衡平利益,因為我們不可能分割出一項事先不存在的衡平利益。那么根據第53條第1款b項的規定,通過聲明信托剝離出一項已存在的受益權,無須以書面形式完成;但是根據第53條第1款c項的規定,通過聲明信托剝離出一項已存在的受益權(衡平權益),則又必須以書面形式完成。歸謬至此可知,分割所有權的觀念會造成對《1925年財產法》第53條的誤讀,即人為地造成了第53條第1款b項與c項在法律適用上的沖突。其實這兩項規則在立法時本不存在沖突,因為立法者根本不認為信托受益權是從普通法所有權中分割出的權利。
三、信托受益權的物權化現象
前文論述了英國法傳統中信托受益權的債權本質以及不存在分割、雙重所有權的解讀,但這并不意味著信托受益權債權說在英國一直以來都是毫無爭議、不可動搖的學說。哪怕支持債權說的梅特蘭都不得不承認,“雖然受益權一直都是對人權(jura in personam),從未成為過對物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逐漸表露出越來越多的疑似對物權(jura in rem)的端倪。”易言之,若要全面解釋英國法傳統中信托受益權的債權本質,其在演變過程中出現的種種類似物權化的現象不應被回避。
(一) 基于執行豁免和破產豁免的物權化
受益權物權化的第一個表征在于破產法和執行法。受托人所有的有兩種財產,一種是沒有負擔信托的財產,另一種是負擔了信托的財產。若受托人不能償還個人債務,第一種財產可以作為受托人的個人債權人的執行標的,第二種財產卻不能被這些債權人執行,此為受益權在執行層面的物權化。若作為公司的受托人因不能償還個人債務而進入破產程序,那么第一種財產可以作為破產財產供債權人團體分配,但第二種財產不能被債權人團體取得,此為受益權在破產層面的物權化。這兩個現象真的可以說明信托受益權變成了物權嗎?簡言之,破產豁免是基于商法政策考量的產物而非基于民法權利屬性判斷的產物;執行豁免則是一個片面的假象,因為它不適用于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務本身所產生的債務。
1受益權在破產法層面的物權化。其實破產法有這樣的規定本身并無不可,問題在于此規定不能用于判斷其規定背后的權利性質。在英美法上普遍認可的一點是,破產法規則的取舍在很大層面上與法院的判例法及邏輯分析并無關聯,而是與制定法背后的政策考量有關。依大陸法語言,此意為:破產法規則的存廢更多的是基于商業立法政策的需要,而非傳統私法概念體系的銜接。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私法中我們所普遍認可的物權債權區分原則在破產法立法者們的眼中并不總是那么重要——例如不管是英國法還是中國法,破產財產(破產財團)的范圍顯然不僅包括債務人公司所有的有體物和無體物(知識產權),還包括了各種形式的債權。如根據《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二)》第1條的規定,只要一項權利符合“可以用貨幣估價并依法轉讓”的要求,破產法就可以將其認定為債務人財產。破產法對債務人無體財產外延的突破反映了其與傳統羅馬法體系中無體物概念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也反映了其與私法中根據注重權利本質將物權債權嚴格區分的做法大相徑庭。破產優先權的分配也不例外:哪些權利可供一般無擔保的債權人分配,哪些權利可供有擔保的債權人全部取回,哪些權利只可以由浮動擔保債權人(floating charge holder)部分取得,這些都是立法者的政策考量,而非權利的本質使然。正如有學者總結的,從破產法的角度判斷物權的存在與否是一種結果主義的(consequentialist),非基于演繹或歸納的推理。這種結果主義的產物本身無可厚非,但一來它不可以成為獨立于財產法外并與之平行的另一套判定物權的標準;二來即便可以,它也只能限于破產法內部使用,就像我們不能將破產財團那樣寬泛的“財產”定義適用于傳統民法中那樣。
2受益權在執行層面的物權化。誠然,“信托財產免于受托人的個人債權人的追索”等于是說受益人對受托人的各項請求權(尤其是金錢請求權)相對優先于受托人的所有個人債權人;若個人債權人非法獲取了這筆錢,則受益人可追索之。法國學者Lepaulle的雙重財團理論(dual patrimony)正是對信托財產此特征的一個很好的大陸法解釋。但正如Smith教授在批判Lepaulle的這種物權化誤讀時提到,執行豁免并不足以說明物權性質的原因在于這個視角只看到了信托財產在財產持有層面的特征,卻忽視了它在責任承擔層面的另一個特征:受托人處理信托事務所產生的債權人不同于受托人個人的債權人,前者可以在執行債務的時候將信托財產納入執行標的;受益人在權利實現的層面與之平等,并不享有相對的優先權。比如在Smith舉的例子中,受托人有一個負擔了信托的房屋,如果他邀請工人修繕這個房屋(為了受益人的利益)并拒付工資,那么這個工人可以從信托財產中執行債權,且不會受到受益人的執行豁免權的制約。Honoré也對這個問題給出了很好的解釋。他認為這種基于執行豁免的“衡平法財產權”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它忽視了這種豁免優先權不是受益人的專有品,該權利同樣也被其他的信托債權人平等地享有。比如當信托財產縮水時,如果受托人為打理信托財產而邀請的律師和會計對信托財產行使了他們的報酬請求權,受益人也只得吞下無收入的苦果,他不能追索這些信托債權人實現的債權——但這類信托債權人(諸如信托上的律師和會計)顯然對信托財產不享有物權。既然這種豁免優先權不是一種排他的權利,那么我們就不能只是根據受托人的個人債權人的執行豁免便輕易地把受益權看成物權,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么受托人的另一部分債權人可以執行到信托財產,且這個過程就仿佛和受托人從這筆信托財產中獲得收入的過程一模一樣。
(二) 基于所有權基本要素分離的物權化
之前反駁過基于執行豁免的物權說的Honoré也并不是一位傳統債權說的絕對支持者,因為他關于所有權的另一套理論似乎與關于信托法的分割所有權理論相呼應。他從自己創立的所有權11項基本要素的學說出發,認為雖然受益權不是物權,但信托本身卻依然破壞了所有權的完整結構。Honoré指出,“一個完整的所有權的本質是一束權利和要素(incidents)的集合體,并以此構成一項專有……但是當這些要素和權利束被分離時,比如信托,那么這項壟斷就不復存在了。”這種基于所有權基本要素的分析本身非常正確,但這種思路極易給不了解其背景的讀者們造成誤解。正如有學者所準確概括的,他提出這個學說的背景在于探索出一種可以用普通法的權利理論所解釋的絕對所有權概念,因此他的模型力圖展示出一個完整的、最高的、無負擔的所有權概念的內涵。這就是說,Honoré并無意通過他的基本要素模型去解釋物權(財產權)的取得方式,我們不能因為某一項基本要素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被剝離,就貿然斷定一項他物權、甚至新所有權的產生。例如其理論中第二項基本要素:使用權(right to use)的分離就不一定導致一項物權的繼受取得。反過來看,這些被剝離了基本要素的原初權利雖然已不是那種完整的、最高的、無負擔的所有權,但這依然未改變其作為所有權的本質。當然,這種基于基本要素的標準用在信托受益權的屬性判斷上,也確實易于造成“信托受益權物權化”的推論,包括收益權、處分權和安全保障權三個層面。首先來看收益權的問題。
收益權(right to the income)是最具爭議的一個基本要素。從表面上看,我們可以發現受托人并不具備獨享或任意處理信托財產所產生的孳息及其他收益的資格,他必須將這些收益或是按信托文件的規定交予受益人,或是為了受益人的利益將這些孳息妥善保存并繼續經營。然而此規則不足以進一步推導出收益權已然從完整所有權中被剝離的結論,因為二者并沒有邏輯關系:首先,試想某甲通過與所有權人乙的合意,約定該所有物將來取得的全部收益都必須歸甲所有而不得為乙獨享,但這顯然不意味著乙因為一紙合同喪失了所有權,或是甲因為一紙合同取得了所有權中的收益權權能;其次,在信托關系中,受益人不能直接從日常經營中取得收益,他必須從受托人已取得的收益中請求——且受托人取得收益的名義并不是基于代理或者行紀,而是基于作為所有權人固有的收益權能。易言之,如果信托財產的經營中第三方拒絕給付作為收益的價金,真正有權向該第三人請求給付價金的人是受托人而非受益人;如果信托財產的收益被侵犯,有權起訴該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的也是受托人而非受益人。誠然有人可以反駁:當信托終止時所有的收益都將歸于受益人,受托人必須全數交付,或許這也可以理解為收益權最終歸于受益人。然而我們探討的問題是在信托關系存續期間內收益權的歸屬,而非信托關系終結之后孳息和收益的歸屬——要知道如果信托關系結束且財產交割完畢,則受益人保有收益的理由也并不是基于此前受益人的身份而是所有權人,且再也沒有受托人這一角色存于其間了。總而言之,收益權并未被信托從所有權權利束中抽出,它依然歸屬于作為所有權人的受托人。
第二個爭議來自于對處分權(right to the capital)歸屬的判斷。一個完整的所有權包括自由處分標的物的權能,無論是轉讓、毀壞抑或放棄。Honoré指出,在信托關系中受托人既不能絕對自主地處分標的物(必須受制于信托文件和受信關系),也不能使用這份信托財產沖抵個人債務(即不能成為個人債權人的執行標的)。但這兩點并不足以成為受益權物權化的證明。前文已述,限制所有權人“自由”的方式既可以是一個新物權,也可以是一個債權。事實上從霍菲爾德開始,大家就已經意識到自由權雖然是憲法意義上所有權的重要元素,但在私法層面用自由權的存在與否來判斷一項權利的物權/債權屬性是很不穩妥的,更為準確的標準應當是排他性(excludability)的存在與否。因為且不論用一項對人合同就可以限制住所有權人的自由權,就算是Honoré所指的完整、原初、無負擔的所有權,其基本要素中也包括了第九項即禁止有害使用(prohibition of harmful use)這一條對自由權的限制內容。至于信托財產不能成為受托人個人債權人的執行標的,這看似是受益人享有針對物的處分的消極防御權,但其本質只是:如果信托財產被個人債權人取得,一般情況下受益人也只能基于與受托人的信托關系請求受托人以原所有權人的名義得到該財產的返還——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比如第三人構成事實受托人(trusteeship de son tort),或知情接受(knowing receipt),或不誠實幫助(dishonest assistance),受益人才得以直接追究該人的財產返還性責任(liability to account),且這種直接責任對應的權利為對人權,而非對物權。
第三個爭議來自于對安全保障權(the right to security)歸屬的判斷,這是被上訴法院在2010年做出的一個極富爭議的判例所引發的新興問題。從本案中抽象出的事實和法律為:如果第三人X因為疏忽而違反了其不能侵犯A的土地所有權的義務(即陌生人X侵犯了A的所有權),而A的該物權上有一個以B為受益人的信托,則X不僅要賠償A的直接和間接損失,也應對B遭受的間接經濟損失承擔侵權責任,至少當A參加了B對X的訴訟時情況就是這樣。如果本案的裁判是正確的,那么它就從側面承認了信托受益人的對世防御權,至少所有權中的安全保障權要素不再僅僅屬于受托人,受益人也得以享有并對侵權人行使了。然而這個判例的正確性在英國遭到了廣泛的批判。首先,這個案件無限放大了X要承擔的責任——因為無論X知曉受益人的存在與否X都要對他們的間接損失負責,而受益人的間接經濟損失和受托人的間接經濟損失在內容上往往是不同的,如果一個信托財產上存在多個受益人,則X的間接經濟損失賠償責任就會被不公平地翻倍。其次,這個判決違反了先前的判例法——即如果A以B為信托受益人而保有一個有體物,那么陌生第三人X并不對B負有一項不侵犯該有體物的義務(該義務的權利人只是A而不包括B)。再次,正如McFarlane所指出的,這個判決本身也存在邏輯問題——法院不可以一方面把受益人B視為“實際”所有權人(real owner),而另一方面卻將純粹經濟損失作為B的請求權基礎(眾所周知,所有權人因其財產被侵犯而承受的間接損失不可能是純粹經濟損失);法院也不可以援引基于“原告和被告的特殊關系”而產生的純粹經濟損失的賠償,因為侵權人X在侵權行為發生時甚至尚未了解受益人B及其利益的存在。退一步說,即使本案不被推翻,它也不能成為受益權物權化的判例依據。因為本案討論的問題是作為所有權人受托人參與侵權損害之訴時,受益人是否可以獲得賠償:受益人最終獲賠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受托人以所有權人的名義對被告主張了損害。這意味著,法官在論述時順帶提及的所謂“受益人可以視為實際所有權人,可以獨立主張損害”的觀點和本案爭議事實無關,因而此觀點在本案中只是附帶意見,并不構成判例法中具有約束力的判決理由。
總而言之,我們不能基于某些基本要素在信托中的疑似缺失而得出信托受益權物權化的結論。另外,雖然Honoré的確說過信托“分割”了所有權,不過這句話的實際意思和我們平時看到的所謂“分割所有權”的誤讀是完全不同的。Honoré用分割所有權這個詞組只是在強調信托抽出了完整所有權中的一部分的基本要素,但這并不等于抽出的那部分屬于受益人的基本要素就組成了“衡平法上的所有權”,且這種基于所有權基本要素的“分割說”也根本推導不出受益人享有物權(財產權)的推論。
(三) 基于財產取得權的物權化
與上述兩個受益權物權化的論點不同,此論點立足于英國法中悠久且通俗的語詞選擇:一是在基于合意的信托中特定情況下委托人或者受益人以優先取回信托財產為內容的財產性請求權(proprietary claim),二是在非基于合意的信托中特定情況下權利人從推定受托人手中優先取回標的物或價金的財產性救濟(proprietary remedy)。如果僅僅望文生義,邏輯上很容易得出的結論就是受益權在特定情況下的物權化——但若對這兩處語詞選擇的背后本質做出解釋,我們就會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先來看第一種情形中的財產取回權。一般而言,明示信托是不可撤銷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也不能在受托人無過錯情況下取回信托財產,但例外有二:其一,如果一個明示信托的受益人是一個或多個未成年人,那么當這些受益人均成年并且具有法律上的行為能力時,他們可以隨時與受托人解除信托關系并因此而取回全部的信托財產,成為它們的所有權人。受益權的這一特性與典型債權不同,因為在一般的債權債務關系中,合同第三人不能解除合同一方為該第三人的利益而與合同另一方締結的合同并取回該合同項下的特定標的物。另一個例外來自于英國的一個涉外財產執行判決。該案中,委托人創立了一個可撤銷的歸復信托且撤銷事由于事后成立,于是委托人的債務人向法院申請執行這份受益權項下的財產。依據本案適用的準據法,此請求實現的前提須為被執行人的權利被定性為財產權。法院支持該請求的理由為:雖然傳統意義上可撤銷信托中的撤銷權只是一種形成權(power),但委托人保留了撤銷權的信托財產取回權卻類似于財產權(tantamount to property),故而也可以成為執行的標的。
其實這兩個案件背后反映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對“物權取得權(right ad rem)”性質的界定。提及此概念就不得不交代其提出者霍菲爾德對權利理論的第三個貢獻:權利階段的觀念。霍菲爾德認為,法律關系在不同的階段會表現出不同的權利,彼此間不能混同也不能傳導。若某人對他人在下一階段的權利表現出對世性,這并不代表上一階段該權利就依然是對物權。比如執行階段債權人可以申請法院只針對某特定物權進行強制執行,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對物之訴的執行才能針對這樣特定的某個物權。此觀點在信托中也被承襲,如Swadling指出,把一個財產權放在信托的后面并不能改變該財產權的本質——比如把一個銀行賬戶(對銀行的債權)放入信托也不能使得受益人對該銀行賬戶的權利變成物權,他所享有的仍然是一個債權。事實上物權取得權在很多合同中也普遍存在,比如保險受益人在保險合同解除后或者保險事由發生后取得保險項下的對應財產的權利就是物權取得權,但我們不能說保險受益人因此就一直對保險合同享有“物權”;又比如買賣合同中已給付貨款的一方對出賣人的請求交付貨物的權利也是物權取得權,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說買受人此時獲得了對貨物的“物權”。
從第二種情況即非意定信托的角度也不能得出物權化的結論。按照發生原因可以分為基于合意的信托、基于不當得利的信托、基于侵權的信托以及基于其他特定事由的信托。 Birks教授通過對羅馬法傳統和普通法傳統在返還制度方面的比較,提出了“由不當得利觸發的信托本質上是對利益受損人的財產性回應(proprietary response)”的觀點。此說在英美法中有判例支持:原則上自始的不當得利能觸發物權性返還,嗣后的不當得利只能觸發債權性返還。但此說無法在大陸法中找到參照,因為在傳統大陸民法中,作為債的發生原因的不當得利和侵權行為不可能觸發財產性(物權性)救濟。雖然Birks成功概括了普通法世界的非意定信托在功能層面的價值,但是準確地說,這種“財產性”救濟本質上并不是財產權(物權)。它之所以被稱為財產性救濟,只是因為在結果上權利人可以優先于他人得到這筆財產,在最終效果上部分類似于擔保物權(實際上與擔保物權完全不同)。故而有必要繼續解釋一下英國法上非基于合意的信托(即基于法律規定的信托)的內容及其與物權的區別。
與意定信托相比,基于法律規定的信托在內容上有三個特點。其一,這里的受托人不像基于合意的信托中的受托人那樣,他并不對受益人負擔一個義務群(如保管義務、經營義務、知情義務等),而是只有單一的義務,即在對應權利人主張權利時,須返還特定標的物的物權或者返還特定數量的金錢的義務。此時受益人對應的權利自始至終也只有一個,即向推定受托人請求轉移對應物權或支付對應價金的請求權,這種對人權和對世性的物權顯然相距甚遠。其二,這種義務只須粘附于一項權利上即可,即必須存在著一項有該義務可負擔于其上的權利——此處的“權利”不像物權那樣被限定于某個特定的有體物,一項請求權或者形成權也足以在此適格,比如它也可以是一項可以特定化執行的承諾或合同標的,甚至是一組內部成分可以不斷替換的財產集合。其三,受托人的核心義務不管在意定信托還是非意定信托,不管在創立階段還是執行階段,都是一項消極的“核心受信義務(core trust duty)”,這個義務的核心要求是受托人不僅不得基于其受信地位和控制地位直接或間接獲利(no profit rule),也要避免個人利益與受信利益的沖突(no conflict rule),否則全部不當獲利的財產將歸于受益人。這和創設了他物權的自物權人的義務不一樣,因為有他物權負擔的自物權人仍然可以在不妨礙他物權人的利益的情況下為了自己的利益開發使用該物并從中獲取收益,比如一個有地上權負擔的所有權人依然可以在土地上設置抵押,又比如一個有擔保物權負擔的所有權人依然可以在土地上設置低順位抵押。綜合以上對推定信托在內容上的三點分析,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基于語詞的受益權物權化也不能得出受益權變為物權(財產權)的結論。
四、結語
19世紀英國著名法學家梅特蘭在討論法律移植的話題時曾說過,“……從歷史的經驗中可以得出如下的道理,如果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將要做什么的時候就貿然援引域外詞匯,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句話不應僅限于比較侵權法和訴訟形式的討論,對于信托法的比較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我們固然可以創設新的概念來解釋信托受益權從而使信托在離開普通法世界之后仍然可以和當地法律體系并行不悖,但這并不等于傳統英國信托法的模型也可以隨之被這些新概念重構。其實大陸法學者用雙重所有權、分割所有權甚至物權說去重構本土的變種信托制度是無可厚非的,重構變種信托的學說在某些國家已經被普遍認可,并且成為當地變種信托法的理論基礎。比如在法國,Lepaulle的雙重財團理論(dual patrimony)成功影響了2007年法國物權法的修改,為法國引入信托奠定了傳統民法上的基礎——這個理論恰恰就是雙重所有權理論的變種,只不過受益權的客體不再是某個特定物,而變成了一個財團(patrimonium)。蘇格蘭也受到了同樣的影響。又比如在南非,Honoré將來自荷蘭的托管制度(bewind)和英國普通法信托結合,使得信托財產根據南非法既可以約定由受托人擁有所有權,也可以由受益人擁有所有權——這個模型就可以理解為立足于信托受益權的物權說。再比如在魁北克,信托沒有所有權人,信托財產的基本要件被分割,受托人只是一個管理人——這個模型就可以理解為由于分割所有權從而導致所有權在邏輯上無人享有。然此種種現象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套用這些理論去解釋英美法信托的原貌,以至于以訛傳訛,掩蓋了英美法傳統中信托受益權的本質。易言之,本文并不是否定分割所有權、雙重所有權或是受益權的物權化等諸多學說在自身邏輯上的合理性,只是若用這類模型去解釋甚至重構英國傳統信托法將會導致嚴重的錯誤,并與英國信托法中的諸多制度和判例互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