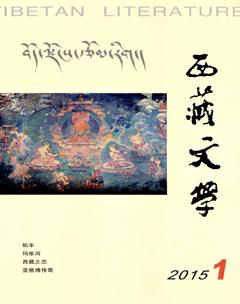一路向西
11月24日,寒風(fēng)瑟瑟的一個(gè)下午,我與八里莊的魯迅文學(xué)院作別了。離開北京,離開居住了兩個(gè)月的魯院408寢室,是早就注定的,但臨到轉(zhuǎn)身,卻還是讓我覺得萬(wàn)分眷戀,只好輕輕揭下那張貼在門上的我的名字,一同帶走……
來(lái)時(shí)因陌生而滋長(zhǎng)出的一大片好奇而愉悅的情緒此刻均變成了滿眼咸咸的不舍,哽得我心里一陣翻攪。
想著要偷偷溜掉,還是在樓下被同學(xué)與老師截住,我拖著行李快速行走,不敢答話,不敢揮手,耳畔隱約傳來(lái)年輕班主任孫吉民的叮嚀囑托,柔柔的聲音卻扎得我疼痛。
應(yīng)景飄落的銀杏葉、梧桐葉讓曾經(jīng)生機(jī)盎然的小院充滿了離愁別緒。步履再輕,踩在腳下,它們也會(huì)窸窣作響,像一聲聲無(wú)力的挽留又像無(wú)可奈何的心碎……經(jīng)歷了頭一晚告別晚宴的相擁而泣,我腫脹的眼睛再度模糊起來(lái),熟悉的街道變得透明又遙遠(yuǎn),唯有經(jīng)過(guò)的那些面孔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的在眼角的余光里清晰可見……走吧,走吧,落葉將沉睡,為了下一季脫胎換骨的醒來(lái);我也將一路向西,回到云端之上的城市。
一
沒(méi)想到與我結(jié)伴穿過(guò)長(zhǎng)長(zhǎng)地鐵線來(lái)到北京西站的是“—3”(我為我們?nèi)M起的昵稱)的鄭旺盛,他同一天回河南,順便幫我拎了一個(gè)行李。隨后,不同的候車室將我們分開。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起碼我這樣認(rèn)為。為了追蹤采訪花崗暴動(dòng)主人翁耿諄,鄭旺盛耗費(fèi)十年時(shí)間與精力,直至一個(gè)充滿青春風(fēng)姿的年輕人被歲月打磨成后來(lái)無(wú)比堅(jiān)韌有力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