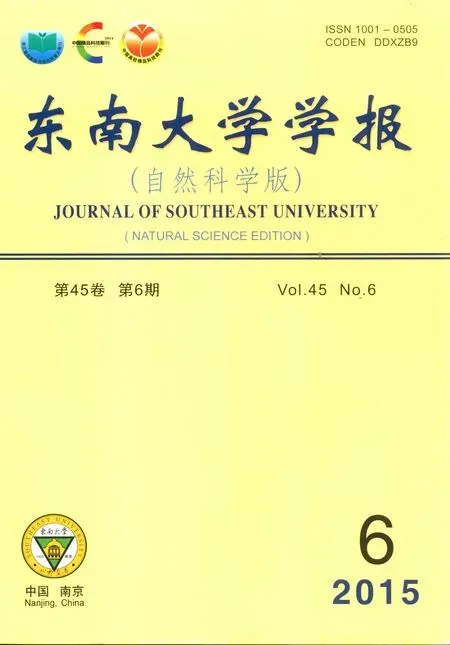城市空間形態與空間體驗的耦合性
李 欣
(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武漢 430072)
城市空間形態與空間體驗的耦合性
李 欣
(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武漢 430072)
摘 要:通過數據模型和實證檢驗,采用信息輔助分析技術研究城市空間形態與空間體驗的關聯耦合作用.通過對13組受試者的情緒數據和GPS信息進行采集,利用空間聚類分析和熱點分析確定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的有效采樣點,在此基礎上對其視域范圍內的建筑形態指標、視域參數、視覺熵、分形維數進行了多角度研究.結果表明,空間體驗受上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運用Logistic模型和接受者工作特性曲線(ROC)可確定關鍵的視域參數,模型具有較高的預測準確性.空間節點對空間體驗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主要反映在空間序列以及場景轉換的作用機制方面.最后,對城市空間的優化提出建議,應加強城市空間的連續性與網絡化建設,指出建設與管理并重的重要性,打造宜人的城市空間.
關鍵詞:城市空間形態;空間體驗;視域;邏輯回歸
城市空間作為人們賴以生存的載體,與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關.研究發現,視覺因素在諸多影響城市空間品質的因素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Hillier[1]認為城市的空間網絡及其可視性對于人流分布具有顯著的影響.一些學者對開闊度[2]、方向性[3-4]、復雜度[5]等空間因素進行了量化計算和研究,試圖了解人們如何通過這些空間屬性感知城市外部空間環境[6-7].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信息技術與計算機輔助分析逐漸被引入城市規劃與設計相關領域之中,為綜合分析城市空間環境提供了便利.Koenig等[8]利用智能手環對在城市中的行人進行了情緒測試,研究發現受試者在某些特定的地點會產生相同的情緒,并確定了這些產生顯著影響的地點.然而,此類研究尚有許多問題并未得到充分解決,例如:究竟是哪些空間因素對人的情緒產生影響;這些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機制如何測定;能否建立基于這些空間因素的情緒預測模型等.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簡要回顧了情緒數據的獲取方法以及如何確定具有顯著空間特征的地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運用視域分析技術對可能影響人們情緒的建筑形態因素進行提取,利用邏輯回歸建立了基于視域參數的預測模型,闡明了多因素的綜合作用機制,并基于視覺熵和視覺維數對這些地點的實景照片進行了圖像分析.進一步解析城市空間屬性與受試者體驗的關聯耦合作用,以便實現對城市空間環境的有效評估,并對潛在影響進行預測,從而提高城市空間設計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使得城市規劃與設計活動更好地服務于城市生活.
1 情緒數據采集
1.1 理論依據
根據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正常的嬰兒在2.5個月便逐漸開始表現出一些共同的情緒特征,例興趣、驚訝、喜悅、生氣和害怕等,被稱為 基本情緒(primary emotions)[9].當嬰兒成長到 2 歲左右時,逐漸發展形成各種較為復雜的衍生情緒(secondary emotions),反映了人們的主要心理傾向[10].
采集情緒數據的智能手環(smart band)由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信息建筑小組提供,該設備可以通過內置的金屬電極對受試者的皮膚電阻和溫度進行實時記錄,通過數據分析從而對情緒極性和強度進行分析判斷.利用便攜式GPS定位裝置與智能手環進行同步記錄,以5 s作為基本單位對智能手環的數據進行累加,實現與GPS的數據匹配.
實驗地點選擇瑞士蘇黎世北部約6 km的奧林岡(Oerlikon)新區,實驗路線全長大約2.2 km.實驗選擇在2013年10月14—22日天氣晴好的條件下進行,受試者的人數為13人,包括8名男性和5名女性.實驗途經的路線和地圖均事先發放給受試者,規定必須以步行的方式完成整條路線,并對路線中重要節點的空間環境進行拍照記錄.智能手環和GPS定位儀在實驗中將自動記錄測試人員的情緒數據和地理坐標,轉換為代表空間位置的點要素,并建立數據庫.通過參考情緒坐標圖將點要素集合劃分為2組,分別代表正面情緒(P集合)和負面情緒(N集合).
1.2 確定有效采樣點
影響受試者情緒的因素大致可以分為2類:①與特定地點的空間屬性有關,其受到時間和隨機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小;② 由時間和其他外部偶然因素等引起的變化.由于受試者的測試時間不同,彼此間不存在直接的相互影響,其情緒數據測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因此,利用空間聚類分析(spatial cluster analysis)強化P集合和N集合中由于空間因素而引起的情緒特征,并減少隨機因素的干擾.由于空間聚類分析受到分析范圍的影響比較顯著,需要利用增量空間自相關分析進行檢驗.通過設定多個閾值對模型的z得分進行觀察,當z得分最高時,表示在該閾值下的空間聚類特征最為顯著.分析結果顯示P集合和N集合的閾值分別在23.5和11 m時呈現最為顯著的聚類特征.在該閾值下利用Getis-Ord-General-G模型進行空間聚類分析,其計算式為[8]

式中,G為Getis-Ord-General-G模型的系數;wij為要素i與j之間的空間權重;n為要素數量;xi和xj分別表示要素值.
結果表明,P集合和N集合的z得分為2.87和1.96,表明2組點要素整體上呈現集聚模式,說明受試者的情緒在整體上具有較為顯著的共同趨勢.
為進一步明確情緒強度的分布模式,避免一些比較明顯的高值點可能是受到偶然環境影響所引起的,不具備顯著的統計學意義.因此,采用Getis-Ord-Gi*模型進行熱點聚類分析,其計算式為[8]

式中,G*i為Getis-Ord-Gi*熱點聚類模型的系數;Z(G*i)為模型的顯著性得分.
通過計算模型的顯著性得分(見式(3))后,在統計學意義上判斷高、低值的集聚區域和顯著性水平,并利用顏色將高、低值聚類標識出作為下一步分析的有效采樣點,其中紅色區域代表高值聚類,藍色區域代表低值聚類(見圖2).通過受試者的ID號對聚類要素進行標識,結果顯示這些數據分別屬于多個不同的測試者,說明受試者在這些采樣點反映出類似的情緒特征.利用熱點聚類共提取有效采樣點348個,其中具有正面情緒的樣本254個,大致集中分布在11個地點;負面情緒的樣本94個,大致集中分布在9個地點(見圖1).

圖1 熱點聚類分析
2 空間形態分析
基于以上計算獲得的有效采樣點,可進一步深入分析城市空間屬性的潛在影響,大致分為3個步驟:①提取受試者視域范圍內的建筑肌理,對其形態指標進行分析,獲得外部空間環境的基本數據;②計算有效采樣點的視域參數,利用二元邏輯回歸模型計算其對受試者情緒極性的影響概率,嘗試建立視域參數對于情緒極性的預測模型;③ 對有效采樣點的實景照片進行分析,綜合運用視覺熵和視覺分形維數分析受試者的情緒如何受到空間環境影響.
2.1 建筑形態比較
視域(isovist)的概念最早由 Tandy[11]提出,隨后Benedikt[12]對其進行了發展,其原理是將空間抽象為無數點集,視域可簡化為其與視點直接互視的子集.在此基礎上,通過一系列幾何參數對視域的空間屬性進行描述,并進行空間映射,從而形成覆蓋整個研究區域的視域場(isovist field).
以P集合(11組)和N集合(9組)作為有效采樣點,將視域半徑閾值設置為200 m,在ArcGIS平臺中可生成視域邊界,提取與該邊界鄰接的建筑平面輪廓,計算平均建筑面積、面積離散度、破碎度、建筑平均間距等形態指標,利用均值法對這些指標進行無量綱化.其中面積離散度和破碎度的計算式分別為

式中,VA為面積離散度;F為破碎度;Ai為建筑單元i的面積;Am和CA分別為與視域邊界臨界的建筑單元面積均值和總周長.
研究區域被鐵路分為東西2塊場地(S1和S2),圖2顯示了不同情緒極性的有效采樣點所對應的4組建筑形態指標.S1場地內主要為高檔辦公、大型商場以及集合住宅,有較多的開放空間,機動車較少,步行環境良好.在該區域內2種不同情緒下的建筑形態指標均呈現出一定的差異,例當受試者為正面情緒時,該采樣點所提取的建筑輪廓普遍較大,并均沿著實驗行進路線呈驟降趨勢(見圖2(a)),面積離散度呈現相對較低水平(見圖2(d)),破碎度總體趨于穩定(見圖2(b)).當受試者為負面情緒時,該采樣點所提取的建筑輪廓則相對較小,面積離散度變大,破碎度呈現輕微的先降后升趨勢.S2場地的城市肌理非常細碎,分布有大量私人住宅,其東側臨近奧林岡火車站和商業副中心,城市道路較為密集,車流量大,然而在該區域內2種不同情緒下的建筑形態指標呈現出比較一致的共線性特征,僅在破碎度這一指標上存在一定的差異(見圖2(a)).在統計軟件SPSS17.0中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對P集合和N集合中的建筑形態指標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建筑形態指標均未出現顯著性差異(p>0.05)(見表1).因此推測在S2場地中建筑形態對于情緒的影響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建筑形態指標的差異性雖然可以在部分有效采樣點之間進行對比,但難以對其他地點進行預測,可能存在其他更為顯著的空間因素,需要進一步對其他空間形態屬性進行深入分析,進一步查明原因.

圖2 建筑形態指標分析

表1 各建筑形態指標無量綱統計值
2.2 視域參數與情緒模型
為研究視域參數對人們情緒影響的綜合作用機制,在Depthmap平臺中建立視域分析模型,將分析柵格的精度設置為10 m,選取了6個主要的視域參數(視域面積、視域周長、視域緊湊度、視域虛邊界、最大視距、最小視距),這些視域參數可以較全面地描述受試人群在空間體驗時的視線特征.其中視域緊湊度和視域虛邊界的計算式分別為

式中,Gr為視域緊湊度;Cv為視域虛邊界;As為視域面積;Cs為視域周長;Cp為視域中實體邊界的總長.
將計算所得的各視域參數值按情緒極性分為2組,在SPSS中對視域參數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在置信水平為95%時,不同情緒極性條件下的所有視域參數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當置信水平為99%時,除最短視距外,其余視域參數均存在顯著差異(p<0.01).因此,可以利用二元邏輯回歸法(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計算視域參數引發正、負情緒的概率.在本案例中,邏輯回歸函數的響應變量為正、負2種情緒極性.設響應變量為陽性時的概率為Pp,其計算式為

式中,Pp為概率值,取值區間為[0,1];Xi為本文所選的視域參數;Bi為變量的估計系數.
通過ROC曲線對邏輯回歸模型的預測效能進行檢驗,將預測概率劃分為若干臨界點,得到每個臨界點對應的靈敏度(sensitivity)和特異性(specificity),連接各點繪制曲線,曲線下面積(AUC)可以從整體上反映該模型的預測準確性.AUC越大,則準確性越高;約登指數(Youden)最大時可以確定最佳臨界點,其計算式為

式中,Yd為約登指數;Se為靈敏度;Sp為特異性.
結果顯示,當僅使用單一的視域參數進行邏輯回歸時,反映模型整體擬合優度的Hosmer-Lemeshow系數均小于設定顯著性水平(p<0.05),說明回歸模型對于數據的提取并不充分,模型的預測值與觀測值存在顯著差異性.單一視域參數的ROC曲線均位于坐標軸的對角線附近(見圖3(a)~(e)),AUC值普遍較低,表明單一視域參數的回歸效果均不理想,因此可以判斷受試者的情緒難以通過單一的視域參數進行有效預測.隨后,將6組視域參數代入回歸模型,根據顯著性標準剔除相關性較差的視域參數,最終選擇視域緊湊度(X1)、視域虛邊界(X2)、最大視距(X3)作為協變量,納入回歸模型計算.通過選取效能最優的回歸方法進行迭代計算,結果顯示其 Hosmer-Lemeshow系數為0.128,大于設定的顯著性水平(p>0.05),且反映模型擬合程度的Cox和SnellR2系數大于0.3,因此可以判斷包含X1,X2,X3的綜合參數模型從總體上具有統計學意義,模型的預測值與實際觀測值的吻合度為83.9%,說明模型具有較好的預測效能.
綜合參數模型顯示,最大視距和視域緊湊度對受試人群的情緒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影響,而視域虛邊界雖然對情緒具有正相關影響,但影響程度相對較輕(見表2),這說明人們更傾向于形態較為規則緊湊的圍合空間,并且在某些方向具備較好的遠眺視野.以廣場為例,在設計中應確保建筑的邊界與廣場形狀的協調一致性,過于凹凸不平的建筑邊界或突兀的建筑輪廓容易遮擋人們的視線,妨礙視域輪廓與廣場形狀在人們頭腦中形成完形格式塔(gestalt)[13-14],從而降低正面情緒的發生概率,甚至引發負面情緒.視域虛邊界意味著建筑之間存在間隙,當視域接近或恰好為凸多邊形時,建筑物間隙的存在可能會對人們的情緒產生正面影響,而當視域變為凹多邊形甚至是星形放射狀時,過多的廣場開口則不利于形成規則而緊湊的視域,從而引發人們的不安定感.實際情況下,這3個視域參數都可能作為矛盾伴生條件而相互影響,即其中一個參數的增加可能同時伴隨著其他參數的降低,因此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綜合判斷.
通過ROC曲線對綜合參數模型進行檢驗(見圖3(f)),其 AUC 值為 0.849(p<0.05),說明基于該模型具有較好的預測效果(根據經驗,如果0.7<AUC<0.9,可定性為中等準確的預測范圍).利用約登指數計算得到綜合參數模型的最佳概率分割點位于0.51附近,與模型默認值(0.5)非常接近,因此接受模型分割點對預測結果的判斷.

圖3 ROC曲線分析

表2 綜合參數邏輯回歸模型結果
2.3 視覺熵與分形維數
人類視覺系統在感知圖像時,其注意力的分布是不均勻的,這種不確定性可以通過視覺熵(visual entropy)對視覺信息進行度量[15].視覺熵是反映主體通過視覺感知信息含量的量化描述,即城市實體環境所呈現的視覺復雜性和豐富程度.因此本文對有效采樣點的空間環境進行了實景拍照,對圖像進行視覺熵的估算,該方法被廣泛用于各種心理學實驗中,具有較高的可信度[16-17].本文通過將照片處理為0~255的離散灰度圖,將各灰度單元看作由圖像信號源發出的不同信號,通過像素點的灰度分布對其總體的視覺熵進行計算,計算式為

式中,Ev為圖像的視覺熵;Pi為像素灰度的概率.為消除圖像的噪音干擾,設定閾值為3%,小于該閾值的信號將被屏蔽(no data),只計算圖像中像素大于該閾值的區域.為簡化計算,本文將圖像灰度劃分為25個等級,由于綠色波段的亮度信息較為充分,具有較好的圖像反差[18],因此對該波段的灰度圖進行分析.
此外,Mandelbrot等[19]認為自然界具有不規則和自相似的分形(fractal)特點,因此,城市空間環境的復雜性還可以通過視覺分形維數(visual fractal)進行測度,以便對無序和破碎的形態進行描述.運用計盒維數法(boxing-counting method)對實景照片進行分析,其具體步驟為:①在Photoshop中將圖像尺寸調整為1 450×950像素,對所有照片的邊界進行強化處理并轉換為灰度圖;②以灰度值128為分割點進一步轉換為僅包含黑白兩色的二元圖像(binary graph),將二維網格覆蓋于圖像上,當網格的邊長為d時,覆蓋圖形白色部分的有效網格數量為n(d).根據分形原理,n(d)為d的冪指數函數,計算式為

式中,D為分形維數.為便于觀察和計算,將式(8)進行對數轉換,并將函數繪制在雙對數坐標圖中,

2.4 視覺數據解析

圖4 實景照片及圖像分析過程
沿實驗路線依次選擇了13組有效采樣點進行視覺熵和分形維數的計算.通過觀察圖4可見,在具有正面情緒的地點基本呈現出較強的秩序感,建其斜率D即為該圖像的分形維數,即筑的排布較為規整,建筑的圍合空間具有明確的界定(1,2號地點),視域范圍的形態比較完整緊湊,具有豐富的植物景觀和較好的綠化層次(7,11號地點).受試者反映在這樣的空間中易于獲得安全感,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這是形成愉悅感的重要前提;而負面情緒的地點則呈現出相對較弱的空間秩序,如方向性不強、空間破碎(如4,13號地點),8,10號地點雖然整體景觀較好,但受到路障和部分雜物的干擾,空間的連續性受到破壞,這也可能是受試者產生負面情緒的原因之一;此外,正面情緒和負面情緒在某些地點出現一定的重疊,如3號地點的照片顯示出強烈的景觀反差,豐富的景觀植被與刻板的廠房建筑并置于照片的左右兩側,因此推測受試者在該地點的情緒可能會因為關注對象的不同而發生改變,使得在這一地點采樣的情緒極性出現差別.

圖5 視覺熵與分形維數的相關性
分析結果顯示,視覺熵和分形維數整體上呈現較明顯的共振波動(見圖5),兩者的Pearson相關系數為0.694(p<0.01),呈較強的線性相關.說明隨著空間細節、層次、色彩等方面的變化,反映在圖片中信息量的增減也會使得空間的復雜程度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兩方面將共同對人們的視覺產生影響,從而引起人們情緒的變化.圖6(a)、(b)顯示的是視覺熵和分形維數在不同情緒時隨采樣點的變化情況,兩者的波峰和波谷均發生在具有正面情緒的地點,且呈現更為強烈的波動,而負面情緒下兩者的波動則相對平緩,主要反映在分形維數上(見圖6(b)).因此,視覺熵和分形維數的數值高低并不直接決定人們的情緒極性,當視覺熵和分形維數具有顯著特征時(如峰值),空間的信息量和復雜程度與其他空間發生強烈的反差,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從而產生諸如好奇、喜悅、興奮等較為正面的情緒.例如,2組視覺參數在7號、11號地點均處于較高的峰值水平,視野中建筑物處于非常次要的位置,層數較低,且被大量綠化遮擋,畫面以樹木和景觀構成視覺中心,天空所占比例較少,畫面的整體景觀條件十分優越,因此引發正面情緒的概率較高;而5號地點的視覺熵和分形維數位于波谷水平,整體畫面簡潔明快,視覺干擾幾乎降到最低,該地點具有開敞的空間和明確的道路,其空間的獨特性得到受試者普遍反饋認同;6號地點雖然同樣具有很低的視覺熵和分形維度,其視線開闊,景觀元素相對扁平,橋面和天空占據了視野的絕大部分,樹木較少,建筑的圍合感弱,但其恰好位于跨越2塊場地的鐵路上方,受到火車通行的影響較為明顯,因此容易引發人們的不安情緒.當視覺熵和分形維數處于中間值時,出現正、負情緒的概率則比較接近,不易直接判斷.

圖6 視覺熵和分形維數隨采樣點的變化
分別比較視覺熵和分形維數在不同情緒時的均值,雖然結果顯示正面情緒下視覺熵(2.899)和分形維數(1.714)略高于負面情緒的視覺熵(2.887)和分形維數(1.691),但對正、負情緒下的2組參數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時未出現顯著差異(p>0.05).因此,通過將視覺熵和視覺分形維數進行相加,得到兩者的綜合視覺指數,將當前綜合指數與前一個采樣點的綜合指數進行比較,觀察數據的變化趨勢,即

式中,E為綜合視覺指數;Ei為采樣點i的視覺指數;E*i為視覺變化指數.將各采樣點的變化指數與情緒極性進行匹配,結果顯示情緒極性與變化指數在13個樣本中的吻合度達到70%(見表3),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之前的分析,即受試者在行進過程中的情緒變化除了直接受當前視覺因素的影響外,還可能與體驗過程的時序組織有關,人們會將各個不同的空間節點聯系成一副連續的整體圖景,交叉路口、道路轉角、廣場、標志性建筑等均可能產生空間轉換的效果,這種影響具有一定的時間延續性.當人們進行空間體驗時,會自覺地與前一個或下一個空間的視覺屬性進行比較,對前后圖景差異的回顧或預期可能是引起情緒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3 視覺熵及分形維數檢驗結果
3 結論
1)利用平均建筑面積、面積離散度、破碎度、建筑平均間距等建筑形態指標對采樣點的城市空間進行了對比.研究發現,受試人群對城市空間的感受源于建筑群體的組合關系,尺度和形態差異的適度性有益于建筑群組形成均衡有序的城市空間,當較大尺度的建筑與友好連續的步行空間相互配合時,可以讓步行者形成便捷通暢的空間印象,進而激發愉悅的城市空間體驗.建筑是城市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保持建筑在形態、尺度、體量上的協調統一對于步行環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作用,可通過制定城市設計導則進行有效控制.
2)步行者的城市空間體驗還受到多種視域參數的綜合影響,其中視域緊湊度、視域虛邊界、最大視距的作用相對顯著,這3個視域參數互為伴生條件.本文利用邏輯回歸模型初步建立了視域參數與受試者情緒的預測模型,其預測值與實際觀測值的吻合度為 83.9%,ROC曲線分析的 AUC值為0.849,說明模型具有良好的預測效能.研究還表明,形態緊湊、輪廓規則、視野良好、并具有適度圍合感的城市空間容易激發步行者的正面情緒.因此,在城市設計中除了注重建筑物形成連續一致的邊界外,還應盡量保證建筑邊界與其他外部空間的協調一致,如適當提高街道的界面密度和建筑貼線率[20],并減少過于凹凸不平的建筑邊界或突兀的建筑輪廓,避免遮擋行人的視線.
3)本文還嘗試利用圖像分析輔助設計師了解行人從實際景象中所獲取的視覺信息.研究表明,豐富的視覺信息、良好的綠化景觀、安全的步行環境都有利于營造宜人的城市空間.如果城市景觀具有顯著簡潔明快的空間可識別性,亦可能引起人們的正面情緒.此外,人們對城市空間的認知依賴于一些重要的空間節點,以及由此所構成的整體圖景.因此,一方面可以通過點、線、網相結合的步行系統加強城市空間連續性;另一方面應當注重保護具有特殊歷史內涵的空間或場所,并在此基礎上塑造一些具有可識別性的公共廣場、街頭綠地、道路轉角等空間節點來強化人們的場所印象,從而形成城市整體空間圖景.
致謝 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信息建筑小組Reinhard Konig博士為情緒數據采集提供了設備和技術指導,巴勒斯坦納賈赫國立大學城市規劃工程系Ihab Hijazi博士為聚類分析的改進提出了寶貴意見.
[1]Hillier B.The city as a socio-technical system:a spatial reformul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levels problem and the parallel problem[M]//Digital Urban Modeling andSimulation.Berlin,Germany: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2012:24-48.
[2]Stamps A E.On shape and spaciousness[J].Environment and Behavior,2009,41(4):526-548.
[3]Dalton R,Holscher C,Peck T,et al.Judgments of building complexity&navigability in virtual reality[C]//Spatial Cognition.Portland,USA,2010:49-64.
[4]Wiener J M,H?lscher C,Büchner S,et al.Gaze behaviour during space perception and spatial decision making[J].Psychological Research,2012,76(6):713-729.
[5]Franz G,Wiener J M.From space syntax to space semantics:a behaviorally and perceptually oriented methodology for the efficient description of the geometry and topology of environment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to Design,2008,35(4):574-592.
[6]Handy S L,Boarnet M G,Ewing R,et al.How the built environment affects physical activity[J].Views from Urban Planning Am J Prev Med,2002,23(2S):64-73.
[7]Ewing R,Handy S.Measuring the unmeasurable:urban design qualities related to walkability[J].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09,14(1):65-84.
[8]Koenig R,Schneider S,Hamzi I,et al.Using geo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detect similarities in emotional responses of urban walkers to urban space[C]//Sixth Internationa Conference on Design Computing and Cognition.London,UK,2014,41.
[9]姚凱南.嬰兒的情緒發展及情緒障礙[J].中國兒童保健雜志,2003,11(6):389-391,393.
Yao Kainan.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obstacles of infants[J].Chinese Journal of Child Health Care,2003,11(6):389-391,393.(in Chinese)
[10]Russell J A.A circumplex model of affect[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0,39(6):1161-1178.
[11]Tandy C R V.The isovist method of landscape survey[J].Methods of Landscape Analysis,1967,10:9-10.
[12]Benedikt M L.To take hold of space:isovists and isovist field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1979,6(1):47-65.
[13]Rock I,Palmer S.The legacy of gestalt psychology[J].Scientific American,1990,263(6):84-90.
[14]高曉昧.基于視知覺組織原則的城市設計中群組建筑實體構成的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建筑工程學院,2010.
[15]Shannon C E.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1948,27(3):379-423.
[16]湯曉敏.景觀視覺環境評價的理論、方法與應用研究[D].上海: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2007.
[17]湯曉敏,王祥榮.景觀視覺環境評價:概念、起源與發展[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農業科學版,2007,25(3):173-179.
Tang Xiaomin,Wang Xiangrong.Landscape visual environment assessment(LVEA):concept,origin and development[J].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Agricultural Science,2007,25(3):173-179.(in Chinese)
[18]Sato T,Matsuoka M,Takayasu H.Fractal image analysis of natural scenes and medical images[J].Fractals,1996,4(4):463-468.
[19]Mandelbrot B B,Pfeifer P,Biham O,et al.Is nature fractal?[J].Science,1998,279(5352):783,785-786.
[20]周鈺.街道界面形態的量化研究[D].天津:天津大學建筑學院,2012.
Coupling research on urban form and spatial experience
Li Xin
(School of Urban Desig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data modeling and empirical study,information-aided analysis is involved to study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urban form and spatial experience.Emotion data was collected using smart band and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device for 13 subjects.Spatial cluster and hot-spot analysis are used to target the effective sampling locations.The shape indicators,isovist parameters,visual entropy,and visual fractal are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ithin each defined isovist.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spatial experience is under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multiple spatial factors above mentioned.The logistical regression model an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are used for determining some key isovist parameters with relatively high prediction accuracy.Urban space nodes also exert a certain degree of influence on spatial experience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spatial sequence and scenario shifting.Finally,some improvement should be mad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including enhancing the continuity and network of urban space.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both 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to create a pleasant urban space.
Key words:urban spatial form;spatial experience;isovists;logistic regression
中圖分類號:TU984
A
1001-0505(2015)06-1209-09
doi:10.3969/j.issn.1001-0505.2015.06.033
收稿日期:2015-04-07.
李欣(1983—),男,博士,講師,li-xin@whu.edu.cn.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51408442).
李欣.城市空間形態與空間體驗的耦合性[J].東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45(6):1209-1217.[doi:10.3969/j.issn.1001-0505.2015.0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