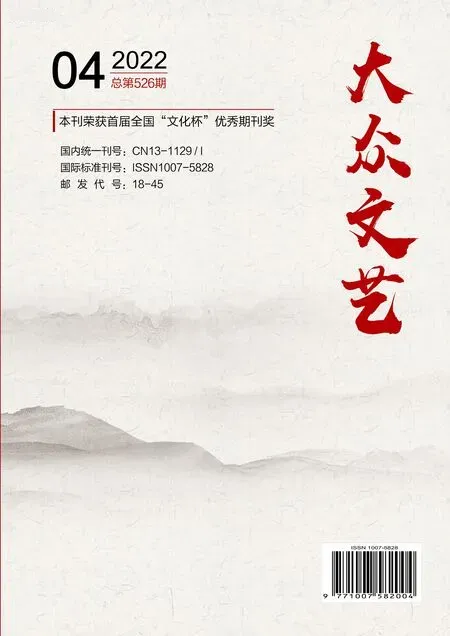析韓東的《爸爸在天上看我》
岳曉嵐 (山西師范大學 041000)
析韓東的《爸爸在天上看我》
岳曉嵐 (山西師范大學 041000)
韓東的詩歌扎根于個體現實經驗及生命體驗,在冷靜、銳利、直截了當的陳述中揭示了事物本質和對生活真實狀態。韓東提出“詩到語言為止”的詩學主張,恢復了口語寫作的活力。他以冷靜的口語入詩,使得他的詩歌有著動人的哲學高度,并在解構傳統的同時建構了屬于自己的哲思方式。
韓東;冷峻;語言
爸爸在天上看我
九五年夏至那天爸爸在天上看我
老方說他在為我擔心
爸爸,我無法看見你的目光
但能回想起你的預言
現在已經是九七年了,爸爸
夏至已經過去,天氣也已轉涼
你擔心的災難已經來過了,起了作用
我因為愛而不能回避,爸爸,就像你
為了愛我從死亡的沉默中蘇醒,并借助于通靈的老方
我因為愛被殺身死,變成一具行尸走肉
再也回不到九五年的夏至了——那充滿希望的日子
爸爸,只有你知道,我希望的不過一場災難
這會兒我仿佛看見了你的目光,像凍結的雨
爸爸,你在哀悼我嗎?
韓東作為上世紀80年代“反文化”“反英雄”“反崇高”、解構傳統詩學的“第三代”詩人的代表。在內容上“他們”完全否定了朦朧詩那種英雄主義傾向的道路,開啟了詩向生命本體的內在化的轉移,他們以普通人的身份表現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等日常生活細節。“第三代”詩的平民立場憑借的是通俗易懂的語言傳達。韓東作為民間寫作的代表,它的文論《三個世俗角色之后》實質上是對文學本質的重新鑒定,他所說的歷史和文化的動物,在去政治化前提下理解的歸屬就是語言。首先是從語言形式上開始覺悟,可以講是一場語言革命的開端,但也是一種矯枉過正。其中《你見過大海》,可謂登峰造極。在《爸爸在天上看我》這首詩里沒有詩人的自我膨脹,也沒有呼喊式的抒情;抒情主體而是以一個極端冷靜的面孔存在,相當克制。這也許正是韓東“詩到語言為止”的真意所在:讓經驗在語言中靜靜呈現,低的姿態,冷調書寫,語境自身在書寫中形成它反諷的張力。
韓東三個階段寫作(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三個時期)沒有一貫性,他的寫作存在著斷裂性。這種斷裂在現代時期表現得尤為突出,30年代進步詩人在40年代詩歌風格的變化,如穆旦和何其芳,人們對他們的描述是從現代主義回歸現實主義,這是審美和政治之間復雜關系的暴露。韓東不同時期創作風格的變化與中國詩歌觀念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歷的變動相關,在85年之后,鄉村意象進入詩歌,鄉村體驗成為他詩歌的主要經驗(如《溫柔的部分》),這一現象與當時文化尋根大潮相關。這首詩寫于90年代中期,這正是詩歌沉寂階段。
這首詩共十四行,這讓我們想到十四行詩的背景;詩人作詩時沒有逾越規矩,但是沒有分節。首句詩人敘述的調子是舒緩和富于情緒節制的,“九五年夏至那天爸爸在天上看我”,“夏至”這種時令入詩,這并不是偶然的手段,在古詩中就有春愁、秋愁的傳統;“爸爸在天上看我”說明爸爸已經去世。詩人在客觀冷靜的敘述中無疑暗含出了自己對父親的懷念。第二句詩人把重心集中在父親身上。“老方”韓東父親的筆名叫“方知”;“他在為我擔心”死人在為活人擔心,表現了個體時下生存的困境。朦朧詩的代表詩人們都沒有獲得合法的地位,朦朧之后的詩人的境況可想而知,而當時韓東辭去公職,成為一名自由作家。詩人對這句話的敘述中一定程度上體現著他對自己現狀的沉默與掙扎,其中也隱含了自己的某些情緒。“爸爸,我無法看見你的目光/但能回想起你的預言 ”這里用“爸爸”而不是上一句的“老方”,這個稱謂的變化是詩人當下的獨白,也可以說是人物在情景中的對白。這兩句話語結構混雜、結構繁復,但詩歌的張力正是在結構和情感的并置中得到完美的詮釋。父親在世時無疑已經預言過他日后的生活,所以他把自己和父親放在同一對象世界中,進行一次心靈的對話,并在對話之中飽含了他對現實世界個體命運的思考。“現在已經是九七年了,爸爸 /夏至已經過去,天氣也已轉涼 ”再一次重復“爸爸”,是最大限度上保留感情的回旋。回想97年這一年,汪曾祺、錢鐘書、王小波等文化名流的去世,韓東此時作詩和這一歷史現象相關,詩人通過對當下的思考,更深入地反思了父親的“預言”,反思探索者抗爭者最后難以逃脫的歷史命運,在回顧自己反叛性的同時表現了對自己未來擔憂的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詩中第一次出現押韻——“涼”與“光”。第7句“你擔心的災難已經來過了,起了作用 ”通過父子沖突隱含現代人生的變化,“已經來過了”是一種溫情表現的特殊形式,詩人沒有對悲劇性的事件直接呈露也沒有進行情感的直接宣泄,只是用冷峻的筆觸一言概之,使讀者在理解和感知中領悟其中蘊涵的思想。詩中第8句明確指出父親的預言變成了現實,詩人用“愛”命名,下一代人在重復著上一代人的悲劇,這也許就是一種歷史宿命的慣性滑動,以至“不能逃避”。從第8句到“為了愛我從死亡的沉默中蘇醒,并借助于通靈的老方”,這里出現了跨行的修辭手法,跨行是用間歇的停頓強制打破意義的連貫,這樣言說的聲音成為節奏的對抗,形成“陌生化”效果。荷爾德林指出,“意料之外的停頓不單單是韻律類型的改變,而且還是表示中止或暫停,使文本偏離中心,處于無法理解和到此結束的境地。”在這句詩中愛和死亡都沒有悲劇性意味,其實這也是“他們”詩人躲避崇高的慣用手法。第10句,“身死”和“行尸走肉”有著深層的聯系,身死就是身體的缺席,而行尸走肉是可以走到但沒有靈魂的軀殼,詩人以“愛”的名義迷失了自我,在這種凄清的詩境中傳達的是一種潛在的反諷意味。個體的反叛和抗爭在面對強大的歷史和現實力量時,最終都會被泯滅。一代又一代曾產生過希望、具有過抗爭的人最終屈于歷史的力量了,詩人寫到這里沉重的喟嘆:“再也回不到九五年的夏至了--那充滿希望的日子 ”,通過對時令概念和親情稱謂的重復,更深入地反思了個人對親情的反叛與回歸,同時又把歷史的感傷情緒表達出來。這也是朦朧詩存在的根據,從這點上看,詩人又回到他當年極力反抗的對面。把“希望”與“九五年夏至”并置在一起,暗含著一種調侃和反諷的意味。因為他希望的是“一場災難”。第13句第一次出現比喻句,“這會兒我仿佛看見了你的目光,像凍結的雨”。“目光”這一詞匯的再次出現,一下子與上邊所敘述的情感基調間的距離,也拉開了“我”與上面敘述的主體情緒的距離,從而體現了“我”的更深層的歷史判斷和思索。詩中最后一句結合反諷與抒情,這與魯迅《野草》中冷峭的情緒相似。
全詩結構繁復,出現了四次押韻,而且還一個重要線索就是重復手法,這似乎是為了喚起抒情性,但沒有回到傳統抒情的軌道上。這種日常世俗的描寫方式,消除崇高的同時并未減弱情感抒發的飽滿度,反而這種平凡而又不淺談的情感在讀者那里得到了共鳴,輕輕震撼了讀者的靈魂;并且把詩徹底從貴族氣中解救出來。
岳曉嵐(1989—),性別:女,民族:漢,籍貫:山西壽陽,學歷:碩士,單位:山西師范大學,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