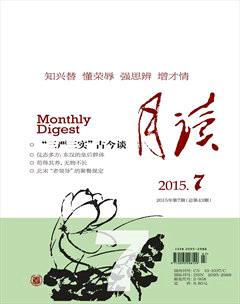中國古代職務與職級并行的歷史經驗
思泉
2015年1月,中央印發《關于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的意見》,明確提出在縣以下機關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職級與待遇掛鉤的制度。這項制度的實質,是通過強化職級的作用而未必僅以提拔職務的方式激勵基層干部,用以解決基層干部待遇低、晉升難的問題,保證基層干部隊伍的穩定。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類似的做法古已有之。
兩難抉擇
西漢元康元年(前65),漢宣帝親自主持實施了一次大規模人事調整,要求擇選朝中通達政事的博士、諫大夫外派出任郡國守相。在這次人事調整中,諫大夫蕭望之被選派擔任平原太守(今山東德州一帶)。但蕭望之卻不愿離京,不久上疏漢宣帝說:“陛下哀憫百姓,擔憂地方治理,所以悉派諫官以補郡吏,這份心情足以理解。但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這是憂其末而忘其本啊!希望陛下更加重視內臣選拔,只要朝廷納諫憂政,恪守治道,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漢宣帝與蕭望之的爭論,實質是對人才資源如何在中央(上級)與基層之間進行合理分配的分歧。一方面,在單一制中央集權制下,中央政府負責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需要將最優秀的人才集中到中央來,包括從基層遴選人才,以強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與向心力。另一方面,基層作為國家政權的神經末梢和政策實施的落腳點,與國計民生息息相關,同樣需要大量人才的聚集。但由于權力自下而上集中,各項政策指令、資源調配以及下級官員的進退留轉、待遇保障都來自上級,特別是在科層制下,越往基層,官員數量越多,級別越低,權力越小,上升通道也越窄,這就不可避免會對基層官員的向上流動愿望和抱負造成沖擊,從而,就產生了國家治理中如何保持基層官員穩定的兩難。
值得一提的是,兩漢之時,官與吏并無截然區分,不少重臣名相都是從佐吏做起,特別是縣令多取郡吏之尤異者。只是后來官吏分離,胥吏地位下沉,受到嚴格限制,沒有升遷希望,同時不像官員有回避、調任等約束,于是專于弄權,成為官場蠹害。這也告訴我們,重視基層“小吏”的“職業發展”,使他們保持良好的心態、狀態,對于吏治整飭,絕非小事。
解決辦法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解決這一難題的呢?盡管中國古代向來有守令擢入臺省、郎官出宰百里的傳統,中央政府經常將富有地方治理經驗的優秀人才選拔到中央,及至出任公卿將相,同時有意識地選派中央官員到地方任職,一可以豐富其經歷,二可以為地方輸送人才,正如唐玄宗即位之初頒布詔令所強調,“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永為恒式”。
然而,在金字塔形的權力結構下,不可能所有優秀基層官員都能得到提拔,京官外派也不可能成為地方官員選配的主要渠道,否則,客觀上將擠壓地方官員為數不多的上升空間,挫傷其積極性。換言之,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鼓勵基層官員安心崗位、勤勉工作。
對此,漢宣帝同樣給出了很好的回答:“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就是說,包括太守在內的地方官員如果任職飄忽不定,下屬及百姓知其在任不久,對其政策能否持久將失去信心,甚至陽奉陰違,只有知其任職將久,才不敢虛以應對。因此,對考核優異、吏民稱頌的太守,漢宣帝常以璽書勉勵、增進秩俸、賜予賞金及至封侯授爵等進行褒獎,而未必簡單以提拔作為獎勵,可謂多管齊下、用心良苦。
漢代保持地方官員任職穩定的做法,一直為后代所繼承。歷史上大多數朝代都規定了太守、縣令三年一任,非任滿不得遷轉。武則天時,史學家劉知幾上疏,建議“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唐德宗時曾下令對優秀縣令授予榮譽虛銜而命其仍居本職。明代對知縣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對任職屆滿而業績卓著的知府、縣令往往仍命其留任而以增進品秩作為補償。例如,明代知府品秩為四品,但況鐘守蘇州、陳本深守吉安,因深孚民望,一再留任,品秩增至三品;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四川布政司右參政,“仍視州事,在州二十余年,秩既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專門辟條“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總結“古來重吏治者,多以久任為效”,對保持基層官員任職穩定作出了強調。
待遇保障
在眾多對基層官員的激勵措施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提高薪俸。正如呂思勉先生在《中國制度史》中所總結的,“歷代制祿厚薄雖有不同,其足以養其身,贍其家,使其潤澤及于九族鄉黨而猶有余裕,則一也”,并認為“官祿至近代而大薄,亦為官吏不能清廉之原因”。顧炎武在《日知錄》中也談到,“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顯然,他們都意識到了官員俸祿與廉潔之間的客觀聯系。
盡管孔子曾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也曾說,“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這一思想也一直為后世士子所謹記恪守;然而,與此同時,孟子也承認,“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也就是說,入仕為官,目的在于弘道,但又不能不看到這也是謀生的一種手段,脫開物質利益一味高倡弘道,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事實上也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對于基層官員來說,承擔著大量繁重的日常事務,又和百姓直接打交道,如果沒有一定的物質保障,弘道難免就會流于空談,清正廉潔恐怕也是難上加難。
西漢神爵三年(前59),漢宣帝頒布詔令,強調“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東漢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下詔“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著重點都是提高基層官員的俸祿。
值得一提的是,漢代官員的俸祿,從號稱萬石的三公到百石以下的斗食佐吏,一共二十多級,但一些表現突出的郡縣佐吏,俸祿經常能到百石、二百石。漢代吏治之盛,與此亦有很大原因。
西晉泰始三年(267),晉武帝詔曰,“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代宗時,楊綰為相,欲推行廉政,卻先增益百官俸祿。可見,古人很早就意識到,若不能給予官員充分的物質保障,使他們免除后顧之憂,實現廉潔可謂
難矣!
歷代官俸,論者多以宋代為厚。事實上,宋代之前,官俸亦不可謂之為薄。唐懿宗時,畢諴為相。畢諴出身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也就是縣衙里一個役卒。畢諴深以為恥,一再派人勸其舅辭去差事,并允諾為他另授一官,其舅卻屢屢不聽。畢諴無奈,于是特意任命楊載為太湖縣令,“囑之為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載到任后,“具達諴意”,其舅一開始依舊推脫說:“我這么一個卑微之人,怎會有當宰相的外甥?”然而楊載反復勸說,其舅最后終于吐露實情:“我雖是小吏,每年都能拿到六萬的事例錢,倘不犯錯,終身優足,不知他到底還要給我升什么官呢?”楊載不得已,將這些話轉告畢諴,畢諴聽后,大為嘆賞,從此不再勉強其舅。可見,唐代基層官吏待遇之優,以至于一個不入流的州縣役卒都安于其位,寧可盡職于事不出差錯,也不愿升官遷移發生變故。
反觀之,歷代官俸,以明清最薄,而明清兩代吏治之墮落、腐敗之盛行,亦達到了頂峰,前述顧炎武之語可謂痛徹之言。事實上,當時已有人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上奏,指出今在外諸司文臣“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請求“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可惜意見雖對,卻終不得行。
必須指出,提高基層官員的待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目的仍是使官不敢貪、吏不敢瀆,只不過“必祿足以贍其身,而后監察有所施”。換言之,若不嚴以懲貪,則厚祿毫無意義。正如前述曹泰在所上“增祿”奏章中亦強調,“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
無赦”!
歷史啟示
對業績突出的地方官員,不簡單地予以提拔,而采取增進品秩等方式進行激勵,這與我們今天提出建立干部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可謂異曲同工。
目前,我國公務員采用了職務與級別兩條晉升通道,但實踐中,以職務為中心根深蒂固,級別被弱化、虛化。這也是“官本位”思想不能從根本上予以清除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強化職級對干部的激勵作用,對于穩定基層干部隊伍,解決他們“求進步,盼穩定”的愿望,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實行過職務與級別分離的做法,對職務重在權責,對級別重在待遇,因此出現級別大職務小或有級無職的現象,特別是對一些資歷老但行政職務不高的同志,定予了很高的級別,如當時中央機關有不少11、12級干部,職務卻只是干事。雖然這一制度并非只針對基層干部,但對于今天的改革亦有不少借益之處。
那么,回顧古人的實踐,又有哪些能為今天的改革提供借
鑒呢?
首先,暢通激勵各種手段。激發基層干部的積極性,勉勵其扎根基層、敬業奉獻。除了建立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提高其職級待遇,還包括上級遴選、提拔重用、榮譽表彰等,每種手段都有其作用,不可顧此失彼。
其次,監督與激勵相并舉。建立職務與職級并行制度,提高基層干部的待遇,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從反腐的角度上看,這更多的是解決“不必為”的問題,只有多管齊下、多措并舉,特別是強化考核監督,才能使“不必為”與“不敢為”“不能為”“不愿為”的機制同時發生作用。
最后,必須審慎推進改革。應當看到,干部待遇一直是社會輿論十分關注的敏感問題,提高基層干部待遇,既要實事求是,隨經濟社會總體發展循序漸進,又要照顧社會情緒,防止引發反彈,保證這項改革真正取得成果、發揮成效。